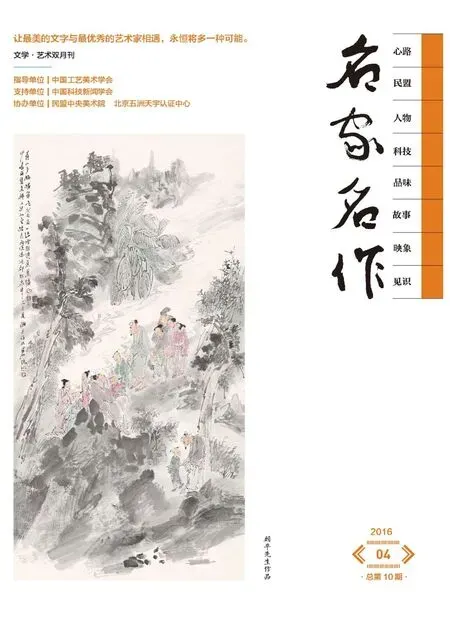浅析魏晋时期玄学思想对文学“自觉”现象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董 璇
浅析魏晋时期玄学思想对文学“自觉”现象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董璇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以抒发个人情感的辞赋创作为代表的魏晋文学,以建安文学的出现为标志,使文学本体从文史哲不分、诗舞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承接名教经学弊端日益显露而兴起的玄学思想,作为魏晋时期社会人文精神的共性意识体现,倡导对个体生命自然本质的重新审视,激发出人们自我的觉醒,对文学、音律、书画等方面的创作主体而言象征着一次精神与灵感的解放,尤其使得魏晋文学显示出强烈的主体性色彩和玄理意味,推动了其创作实践与文学审美理论的发展,对我国古代文学的自觉独立现象影响显著。本文试图从玄学思想的产生因素与魏晋时期的时代背景出发,浅析其对当时文人名士与文学作品的作用机制,以洞察玄学与文学自觉现象之间的呼应关系。
魏晋时期;玄学思想;辞赋;清谈
鲁迅先生在其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谈到,自魏晋曹氏建立政权开始,统治者力斥源于两汉时期的自命清流、固守礼教的社会风气,“文变染乎世情”,时代境况移风易俗的趋向逐渐影响到文坛,开始提倡文风宜“清峻”、“尚通脱”,“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玄学一派即产生于这种名教式微、各类思想流派重新“洗牌”的社会意识环境中。经学研究与发展的困顿不前为文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独立发展形成了契机,而波诡云谲的政治局势也令有识之士意识到官宦仕途的凶险,纷纷弃仕隐逸,为玄理探究与文学创作的融合提供了思考空间,从而形成了一种魏晋时期显著而特别的文学创作现象。
一、博采儒道,广纳哲思——玄学思想的本体形成
1.玄学思想的形成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思想的出现与延自东汉末年长期战乱、政局纷争的形势有所关联。昌盛之时汉风独尊儒术,但由于汉末乱世之中“佞诌日炽,刚克消亡”、“邪夫显进,直士幽藏”(赵壹《刺世疾邪赋》),士人忠而见疏,郁郁不得志,尤其是东汉末的政治腐败与宦官党政使儒家士子对所崇尚的“为政以德”等教义思想产生怀疑,痛苦与无奈之中多少表现出了一种“善恶不为”的道家倾向。因居庙堂之高亦朝不保夕,很多文臣只能选择独善其身,逐渐肯定人的享乐欲望,为了释放精神压力开始接触老庄学说等其他学派思想,寻求超脱达观的人生态度,因此促进了儒家走下神坛、融合其他学术思想的趋势,亦使得后期玄学取代经学的政治统治地位成为可能。
经学思想的衰落,既离不开其本身作为治国之道的局限性,又以汉代经学的神学化为体现。东汉后期,文士雅人将经学的研究学习视为“入仕”和沽名钓誉的必由之路,一度忽略了在继承中发扬,“不复以学问为本”;而随着东汉朝政的弥乱腐朽,以“谶纬”著称的儒家神学为东汉统治者所看重,成为预测未来政局稳定发展的思想工具。刘松来曾在《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中谈到:“谶纬盛行首次将经学、特别是今文经学的弊端暴露无遗,从而给经学以实质性的重创”。另一方面,统治者当局也渐渐不再单纯依附儒家经学的要义来规言断行、提拔贤士,更多依照个人推崇喜好确立主流思想,于是汉桓帝崇奉老子和佛学,汉灵帝设立鸿都门学、以书画诗赋技艺进士,上行下效,臣子跟风,导致经学式微,民间学派思想出现多元发展的趋势,为新的主流思想的确立提供了契机。
2.玄学思想的本体内容
“玄”出自老子《道德经》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意味着近似于无一般的幽深难测,最初用于解释“道”这一“究竟真实”。魏晋时人将《道德经》《庄子》与《周易》视作“三玄”,以老庄思想作为阐发玄学理论的核心根本。玄学,代表着超拔玄卓的理性思想,重视用心灵的自由、精神的解放使人达到物我合一的自然境界,“治身贵于肆任”,强调为人修养身心重在顺其自然,尊重人的自然本性,以此探寻或体察“道”的存在。玄学着力探求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倡导“清谈”的社会风尚,借机融合儒释道三种哲学思想,逐渐成为了一种抽象性很强的思辨理论。
玄学理论的发展最初以魏晋名士活跃的时代为区别,后人考虑到玄学理论前后一脉相承的完整性,又将玄学划分为正始玄学、竹林玄学、西晋玄学与玄佛合流四个发展阶段。
玄学思想正式形成于魏齐王正始年间(240—249),承接曹魏建安文学,由何晏、王弼等人在老庄学说的基础上,延伸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基本观点,主张“贵无”。刘勰所著《文心雕龙·论说》中对玄学一派的形成有简要记载:“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正始玄学发展期间,有关老庄哲学的阐释、批注著作不断问世,如夏侯玄的《本玄论》和王弼的《老子注》,著书者多出自官僚世家,其发散老庄思想的思路倾向于治世为君之道,因此正始玄学又被看做一门政治哲学。司马家族逐步掌权魏国之后,嵇康、阮籍、刘伶等坚持仕魏的文人名士对政事淡漠,逍遥山水,以“竹林七贤”之称为世所知,将玄学思想发展成为带有自身烙印的个人处世哲学观。他们生性傲俗放达、纵情不羁,对当时仍由儒家礼教秉持的压抑人性、克己复礼的主流道德标准进行批判,主张“越名任心”,认为修养理想的人格品质应做到顺任自我、不羡名利,这种观念不啻为对当时魏末政局被权臣操控专治的一种排斥现实的价值观选择。魏元帝景元年间(260—264),嵇康、阮籍相继离世,提倡探讨玄理与其他名教宗义的西晋玄学开始盛行,“清谈”这一志趣高雅的文人聚议活动广为开展,涉及到较多抽象理论的辨析。到了东晋时期,名士皆与佛教僧人交往频繁,玄学理论的主要内容多沿袭自西晋正始年间且日渐趋于成熟,同时掺杂佛经所悟。张湛所著的《列子注》标志着玄学理论本体发展的止步,其序言所提“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大归同于老庄”,便是明证。
二、政·哲·文的观照——玄学思想的作用机制
1.政治形态方面
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的三大选官制度之一,制定于魏文帝黄初元年的“九品中正制”,代表着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无论从制度内容方面考量或从社会影响方面参照,这一制度都无疑为玄学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弥漫创造了条件。
“九品中正制”的关键环节在于各级“中正官”这一选拔、品评人才的官职设置,州郡的“中正官”多由中央官员直接担任,便于统治者对人才选拔的直接控制。魏晋以来,帝王官吏对文学创作雅趣的推崇可见诸史料,魏文帝曹丕曾著《典论》,主张“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被后人视为玄学思想环境催生的典型文学主张。其后继者明皇帝曹叡亦能诗文善乐府,与曹操、曹丕并称魏氏“三祖”。魏朝统治者向来以文识才,曾征召文士置于崇文馆,鼓励其文学创作,君臣皆为政宽和,事从简易,一度为文学实践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九品中正制”对人才名士的品第依照所谓的“九品”制度进行,官吏选拔政策的贯彻引导魏晋时人形成一种观念,人应该在“九品”的等级中实现自身价值。“九品”起源于《汉书·古今人表》,其中最高品位一品是理想中的圣人,是无人可及的虚设;二品是“亚圣大贤”,此二者都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最高人格,在当时崇尚玄学的文人赋作中,皆有将这种理想人格描绘成拟人化形象的实例,出现了虚拟老庄式的玄学人物。
2.哲学文化方面
在魏晋两代更替之时,政局复杂多变,名士少有全者。落魄的政客士子多数转型为文学创作者,玄学思想中有关生死名利的哲学性观点被广为探讨。他们往往结合自身政治处境反思生命于个人、于社稷的利害关系,进而产生避世的人生态度与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这类名士为世广知的代表人物即“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向秀等七人普遍崇尚高雅超逸的风姿与荣辱不惊的做人品格,以实现并享受逍遥自在的处世境界为人生理想。“竹林七贤”之一嵇康向往“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的生活(《与山巨源绝交书》),刘伶淡视人生纵情享乐,常乘鹿车,备酒壶,使人荷锸跟随,谓曰:“死便埋我。”(《晋书》本传)。
由此形成的竹林哲学作为人生哲学,倡导一种无用即是大用、自由张扬、释放自我、纵情放任、散怀丘壑、随遇而安、守柔处弱的玄学人生观,直接影响着两晋时期文人墨客的价值选择。《晋书》中关于当时文人名士的传记描述,皆用到“性好山水”等词句。玄学思想的意识环境不仅转变了文学创作主体的性格与价值视角,也影响了当时文人的创作倾向和辞赋风格,使玄学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哲学社会思潮。
三、以小见大,化心成文——玄学思潮深化文学的独立性状
1.文学自觉现象之内涵
“文学自觉”指文学及文学创作主体意识到文学的独立性和价值性,自觉地对文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等进行探讨和认识,促进文学按其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因此文学的“自觉”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以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先导的,表现在创作主体对文学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没有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没有对人的个性、人格的尊重观念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
袁峰在《文学的自觉与玄学理论》一文中认为,“文学的自觉虽然已经包含有理性思想,但它却不就是理性思想本身,只有当汉魏之际的思想解放思潮在文学自觉的推动下步入正始时期以后,理性思想才以‘玄论’的形式实现了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说,玄学理论的形成又可以看作文学自觉的进一步深化。”文学的自觉形式成为魏晋时期社会思想解放之前奏,而思想的解放又利用这种自觉的形式不断革新着人们的审美与生活方式,更广泛地从文学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上加深了其独立性状。
2.玄学思想对文学创作实践的影响
(1)创作意图
魏晋时期的赋作者因身份地位和志向抱负的差别,在撰文作赋方面尽管显露出不同的创作动机,但均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玄学思想的濡染,且往往可通过其作品内容得以窥见。有些借用道家经著中的寓言典故或取材其意象形象达到针砭时弊、批判现实的目的,例如阮籍借用《庄子》中出现的逞能献媚的猕猴形象作《猕猴赋》,讽刺当时故作高深虚伪鄙夷的礼法之士。另一种情况则是表现创作者的意识体验与情感诉求,隐晦地探讨人生意义、生命价值等宏大的哲学问题。陆机在《文赋》中曾用“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等句,来表现赋作家创作之前丰富深刻的内心体验。
(2)题材体裁
魏晋文学作品的题材、体裁皆呈现出多元化表现。延自两汉时期规模宏大、文制工整的汉赋,在此时由于倡导纵情适性的玄学思想取代了经学统治地位,而逐渐演化成体制较小的骈赋。骈赋讲求对仗,词语华美,抒情成分增多,拓宽了辞赋的表现领域并活跃了其文学风格,成为魏晋时代美文的突出标志与文学创作的主流势力。此外,魏代“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五言诗成为诗歌创作的普遍式样;而在两晋时期,四言诗亦因个体抒情成分的出现呈中兴之势,咏怀诗、山水诗、玄理诗、田园诗歌等不同风格的诗作大量出现,传统的四言诗表现手法与艺术风格得以丰富。
(3)内容意象
《庄子·知北游》中写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玄学思想受庄子齐物论主张,认为万物皆浑然一体,事物与人的本质都归属于自然,具有相似性,因此人所体验到的情绪起伏乃至意识的自觉,都能在自然事物身上找到一种投射似的联系。这种观点反映在魏晋时期的文学实践中,可用“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赋作倾向高度概括。
第一,魏晋辞赋中出现大量的逸民赋、幽人赋作品,其中自然景致与人文情怀相交融,表现了作品内容上的超脱倾向。较为著名的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等词句均含有玄学意味,成为表现纵情山水的隐逸生活、宣扬隐逸思想、表现山水之乐的千古名句。
第二,魏晋文学创作者常常借物抒怀,或将描写对象细腻物化,擅于运用并歌咏玄学化的意象,囊括自然万物与各种气象现象为玄学思想所用,如水、井、酒、玉石、芳草、风、霜、雨、月等。这些作品不仅是赋作者个人审美意识的萌发与情感的依托,也结合了玄学思想内涵的对万物自然的体察、对阴阳生灵的敬重与仰羡情怀,如傅玄在《蝉赋》一文中感叹“美兹蝉之纯洁兮,禀阴阳之微灵。精粹之贞气兮,体自然之妙形……泊无为而自得兮,聆商风而和鸣”。陆机在总结文学的艺术特征时曾在《文赋》中认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魏晋赋作重视描绘事物的形象,以清晰明朗作为基本的审美标准。
第三,有些魏晋赋作不仅用于直接记录魏晋名士“清谈”的场景与内容或直接以辞赋阐发并品析玄学之意,还可以展现文人墨客淡泊名利的艺术化生活方式,如嵇康擅鼓琴,有作《琴赋》,王羲之书法一绝,曾作《用笔赋》。玄学思想所主张的享受生活、超然物外的价值观意识促使文学艺术家们敢于摆脱儒家礼教的政治桎梏,将更多的生活情趣投入艺术研究与文学写作中,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
(4)艺术风格
魏晋文学作品在艺术风格上可被视作“情”与“理”的结合。相比于汉代描写宫殿、祭祀等壮观场面的大赋,魏晋辞赋更加注重抒发个人情感,很多魏晋文学作者缘情作赋,感叹人生苦短,咏叹命运起伏,形成一种新颖的文学创作现象。这些抒情小赋清新飘逸,辞藻雕丽,句式多对偶排比,且诵读音韵和谐。许多辞赋在主观情怀中也添加了思辨色彩,引用老庄哲学思想探讨生死、入世出世之争,阐释玄理,达到了情理合一的文学审美效果。
3.玄学思想对文学理论的影响
魏晋时期由于玄学思想的影响,文学的内部规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此时的赋论家开始注重从艺术角度研究探讨辞赋的特点和构成要素,尊重辞赋的文学审美性,而不仅仅只强调附加于赋作的教化作用,降低了由儒家名教所提倡的文学作品在政治主张、道德观念、社会价值等方面的严苛要求,转而关注赋作辞藻的推敲与气韵的工整,强调文学作品意象本身的审美意义,使赋的文学性状愈发凸显。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诗赋欲丽”,主张凸显辞赋“丽”的本质特征。陆机为《遂志赋》作序比较“简而有情”“壮而泛滥”“俗而时靡”等审美形态之后,总结出“穷达异事” “声为情变”乃文学创作主体共性的规律,首次提出作者身世境遇对赋作内容与风格基调的直接影响。这些文学理论的探索与总结,是文学学术地位与艺术价值被肯定的标志。
[1]纳兰容若.饮水词笺校[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2]黎运汉.汉语风格学[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3]黎运汉.汉语风格探索[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4]程祥徽,黎连汉.语言风格论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5]郑远汉.言语风格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6]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7]刘勰.文心雕龙[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8]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9]张德明.语言风格学[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2015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