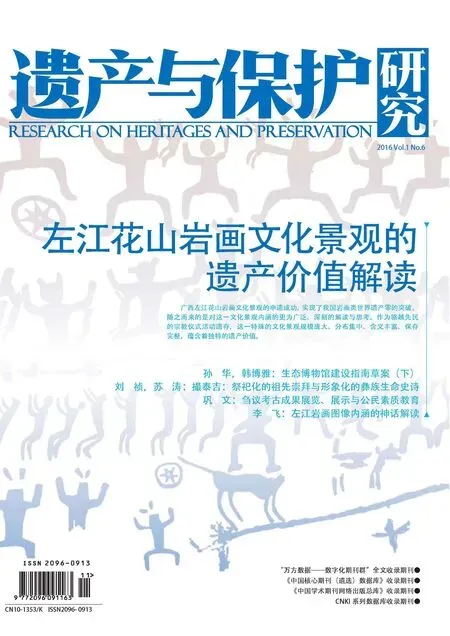左江流域岩画与岩洞葬关系试探
张 林
(故宫博物院,北京 100009)
左江流域岩画与岩洞葬关系试探
张 林
(故宫博物院,北京 100009)
左江流域岩画地点周边存在着不少岩洞葬,文章在分析岩画与岩洞葬两者在空间和时间上存在着一定关系的基础上,指出这种关系并非两者内在的直接联系,而是基于相似信仰的存在时间差的异时性关联。
左江流域、岩画、岩洞葬、异时性关联
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对其的保护更应该快马加鞭地跟进;而与左江流域岩画相关的各类其他遗址也应纳入到同一视野下进行统筹研究与保护。
西南诸省曾普遍流行岩洞葬。这是一种利用天然岩洞作为安葬之所的葬法,在峰丛发育、天然岩洞密布的广西、贵州的喀斯特地貌区,这类葬法尤盛,其中就包括左江流域。目前已查明的左江流域的岩画地点共79个,绝大部分都位于宁明到扶绥之间的左江干流两岸峭壁之上,而部分岩洞葬也高居于悬崖;在少数地点,岩画甚至就围绕着岩洞葬洞口四周的崖壁绘制。如此,不免让人对两者的关系产生好奇而想一探究竟。
早在1982年,张世铨在对广西的岩洞葬进行研究时就注意到了沉香角、驮那山、白龟红山3处岩洞葬附近的岩画,并且认为既然两者空间上紧密相邻,那时间上也应相差不远;于是利用岩画中的裸体、一字格短剑和环首长铁刀等元素,判定岩画年代的上下限为东汉至唐初,进而将这3个岩洞葬的年代也定为这一时期[1]。黄现璠与陈业铨也以花山岩画为例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过探讨,认为花山岩画是壮族首领安葬于岩洞之后所绘的,是起到类似汉族墓葬神道石刻作用的画面[2]。
此外,尚有旁证,似更能证明岩画与岩洞葬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四川珙县麻塘坝发现大量悬棺葬和与之共存的岩画,部分悬棺木桩的孔打破岩画,同时也存在岩画颜料流入插木桩的孔中和在人工开凿的龛内壁发现岩画的情况;其中,九盏灯和邓家岩都在棺木上发现与岩画色泽、画风一致的图像[3-4]。因此两者很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从始至终——并存共生。结合画面内容,多为“放牧、垂钓等反映生产的场面和舞蹈、武术等娱乐生活情境”[5],似与汉族墓葬壁画的功能相似,反映的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以此表达生者对死者
的追思与怀念。
具体到左江流域的岩画与岩洞葬,关系似乎并没有我们原本认为的那么清晰。邱钟仑[6]曾对前人论述的左江流域岩画和岩洞的关系进行过梳理,发现这些叙述多不分地区、不分时代,笼统而言,含糊其辞,缺少说服力。现对真实情况梳理如下。
1 左江流域岩画与岩洞葬的空间关系
统观西南地区桂黔滇川四省岩画与岩洞葬的分布,不难发现两者呈现的分布状态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岩画主要分布在广西、贵州和云南3省,四川仅在与云南交界的珙县麻塘坝一处有分布。桂黔滇3省的岩画除左江岩画和沧源岩画两处各自分布较为集中外,其余岩画点都呈散点状分散在3省各地(图1)。与之相比,岩洞葬的分布则明显呈集中态势,自桂西南、桂中,至桂北、黔南,再到黔中,分布区域边界清晰;整体而言集中分布,局部来看分散布局与密集分布并存(图2)。

图1 西南地区岩画分布图

图2 西南地区岩洞葬分布图
当我们将两者的分布置于同一视野下观察时(图3、图4)便会发现,虽然从大尺度上而言,两者的分布区在桂西南、黔南地区有一小部分重叠;但具体到每一个遗址点个体,岩画与岩洞葬共存的案例并不多,目前发现的仅有左江流域的6例。

图3 西南地区岩画与岩洞葬分布图

图4 左江流域岩画与岩洞葬分布图
左江流域岩画的分布特点鲜明,79个现已查明的岩画点中,有70个地点密集地分布在宁明到扶绥之间的左江干流两岸。而岩洞葬的分布则大相径庭,虽然每一个安置棺木的岩洞内可能会聚集有多至上百具棺木,但就岩洞而言,其分布是较为分散的。综合图3、图4可以看到,广西省境内的岩洞葬分布在桂西南至桂中再折向桂北一线,呈一定的集中态势;但与左江岩画的密集程度相比,仍显得极为疏朗。广西境内岩洞葬最为集中的区域在龙州、大新、天等、隆安、平果等数县境内,且多位于左江流域。其中,珠山第二地点①承蒙宁明县文管所朱秋平所长告知,左江流域岩画珠山第二地点所在崖面的东北方靠近地面处新发现一个洞穴,内有棺木,年代尚未能确定,或距今不远。、沉香角、宝剑山②承蒙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杨清平告知,在2013年对宝剑山临江一处洞穴遗址的发掘工作中,发现了一处与贝丘遗址共存的新石器时代岩洞葬,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研究。、棉江花山、白龟红山、驮那山6个地点,发现了岩画也有岩洞葬遗存,并且两者均位于同一崖面,部分岩画图像甚至就分布在岩洞葬所在的洞口四周。
珠山第二地点(图5)分布有7处岩画画面(A1~A7③图5~图10中,A1~An代表岩画画面所在位置,其分组情况据《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一书;B为岩洞葬地点。),几乎占据了崖面上所有适于作画的区域。崖面东北部靠近地面处有一洞口高敞的岩洞,内有棺木遗存。但因尚未进行清理或进一步研究,此岩洞葬的年代、族属等信息尚不明了。

图5 珠山第二地点岩画与岩洞葬位置关系图
沉香角共有16处岩画画面,图6中可见第5~9处(A5~A9)。崖壁上曾有木杆残留,推测为岩洞葬遗存;但因木杆被人取走而破坏,曾有木杆之处已不甚明确,或为A6左上角的小洞处。

图6 沉香角岩画与岩洞葬位置关系图
宝剑山(图7)仅有一处岩画画面,位于崖面较低处,距江面约10 m。其右下方有一洞口呈喇叭状外侈的岩洞,内有墓葬和贝丘遗址,前者叠压后者,且两个时期的文化大致相接。墓葬年代初步判断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不见葬具痕迹。

图7 宝剑山岩画与岩洞葬位置关系图
棉江花山(图8)共有5处岩画画面(A1~A5),分布于山体临江的灰黄色崖壁上,其中第A1、A4、A5三处画面几乎将低处崖面上所有适于作画区域完全覆盖。在B处的岩洞内发现两具上下叠压的棺木[7]28,而据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的调查人员介绍,其右下方的大洞内也发现有棺木碎片。

图8 棉江花山岩画与岩洞葬位置关系图
白龟红山(图9)崖面中部有一组锥状隆起的石棱,4组岩画画面(A1~A4)就分布在石棱与崖面的交界处。在A2画面上方的岩洞中发现3根木杆,但棺木已然不存。

图9 白龟红山岩画与岩洞葬位置关系图
驮那山(图10)共有2处岩画画面(A1、A2),位于临江崖面的灰黄色区域。由于仅存的木杆被取走,岩洞葬的具体位置已难以确认。

图10 驮那山岩画位置图
观察这6个地点岩画与岩洞葬在崖壁上具体分布位置,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两者在崖壁上的空间关系非常紧密,岩洞葬洞口附近几乎均有岩画。但综合考察其他未见岩洞葬的岩画地点后不难发现,关系紧密的并非岩洞葬与岩画,而是灰黄色的崖壁与岩画。石灰岩岩面经雨水冲淋后会产生或白色、或黄色、或黑色的水痕,不同颜色的崖面对岩画创作有不同效果,黑色崖面显然不利于画面内容的表现,因此几乎所有画面都位于崖壁上黄色或灰色部分——利于突显红色颜料所绘内容的区域,并且多择其中较平坦的部分,如此方能使所绘画面尽可能明显地展示出来。如果说岩画是为了岩洞葬而作,那么它应该以岩洞葬为核心来安排作画范围,但事实上我们只能看到它对灰黄色崖壁的追求,而没能发现岩洞葬的位置在岩画作画位置的选择中起到作用。
也就是说,左江流域岩画与岩洞葬在空间上存在着明显的关联,但这一关联是否是具有内在动因的功能上或意义上的联系,仍需进一步考察。
2 左江流域岩画与岩洞葬的时间关系
左江流域岩画的年代仍然存在一定争议,但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落在春秋战国至宋之间[8-11],更有学者认为这些岩画就是汉代前后(甚至西汉晚期后)[12],而岩洞葬的情况稍显复杂。
广西地区岩洞葬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先秦岩洞葬,这类岩洞葬利用天然岩洞作为安葬之地,尸体直接置于洞内地面,不用葬具装殓;在完成安葬后大多会用石块封堵洞口,将葬所与外界完全隔离,使得整个洞穴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墓室。这类岩洞葬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末段开始(如岜旺岩洞葬、弄山岩洞葬[13]),经商(如更洒岩洞葬[14]、敢猪岩洞葬[15])、西周(如鹞鹰山岩洞葬[16]、六桥岩洞葬[16]),直至春秋战国时期(如独山岩洞葬[17]、龙中岩洞葬[18])。此类岩洞葬与岩画对应的年代并不完全相符,独山和龙中两个岩洞葬虽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存,但其所处的位置却离左江及岩画的分布地点极为遥远。第二类岩洞葬为晚期岩洞葬。此类岩洞葬亦使用天然岩洞作为葬地,但使用棺木装殓尸骸,棺木置于洞中,且并不入土;完成安葬后不封闭洞口,并且会继续往同一个洞中放置棺木,整个洞穴相当于这一族群的族墓地。这类岩洞葬与先秦岩洞葬之间存在着数百年的
年代断层,大约自南朝晚期出现,延续至明清,部分地区甚至直至近代仍存此类葬法。
上述6个岩画与岩洞葬共存的地点中,沉香角、驮拉山、白龟红山3处的棺木如今已因各种原因被扰乱而不存;珠山第二地点的岩洞葬尚未进行详细研究,据附近村民介绍,或为晚近遗存。从目前仍存有完整棺木的棉江花山岩洞葬来看,《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将其定为一期,其年代相当于战国早期至中期[9];《广西左江岩画》则认为其贯穿整个左江流域岩画发展过程,从战国时期延续至东汉[10]。对棺木的14C测年结果显示,其距今1512±51年[7]242,约处南朝时期。鉴于石灰岩地区14C测年数据偏老的因素,其真实年代应更晚,或至南朝末期。宝剑山岩洞葬虽尚未完成所有整理研究工作,但据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参与发掘者介绍,从墓葬所在地层中出土的石斧、石锛、蚌刀等遗物判断,这些墓葬年代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如上所述,左江流域岩画的创作部分处于先秦岩洞葬和南朝以降晚期岩洞葬之间的空白时段;而大约在南朝末至宋这一时期,则与岩洞葬的使用存在重叠。同时,左江流域岩画和左右江流域岩洞葬都被认为是壮族先民的遗存。因此,在左江流域的特定区域内、在南朝末年至宋这一时期内,绘制岩画和实行岩洞葬的人群存在关联,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但因为两者在时间和空间上不能完全吻合,所以还不宜武断地做出两者是同一群人为同一目的所作的判断;即岩画是否是为岩洞葬的死者而作,仍可存疑。除此之外,有迹象表明左江流域岩画与岩洞葬之间除了曾并存过一段时间外,那些存在着时代差异的遗存之间,还可能存在着一种异时性的关联。
3 左江流域岩画与岩洞葬的异时性关联
大量民族志资料显示,“蛙”这一形象对壮侗语民族及其先民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甚至有学者认为它就是壮族的图腾[19]。在壮侗语民族的神话传说中,有大量关于青蛙或蟾蜍的故事,并且版本众多,但故事梗概基本一致:蛙是天神的使者,一是负责人间降水,二是负责传达天神旨意,并具有蜕皮后重生的能力。
广西是最早进行稻作生产并发展出稻作文化的地区之一[20-21],对生活于此的壮族先民来说,雨水多少直接关系着收成好坏,是关乎生存的重要因素。因此,和雨水有着“同步性”的蛙自然成了他们特别关注的对象,并希望它能满足人们对雨水的要求:久旱无雨便叫雷神造雨,久雨成涝便叫水神消灾,甚至不惜为此与雷神产生冲突[22],完全是人类守护神的形象。
基于大量日常生活观察的经验,人们也不难注意到蟾蜍的蜕皮现象。蟾蜍蜕皮后宛如新生的状态,使得人们很自然地将其与重生联系起来。通过蜕皮,老人可以重返青春,因此而永生;反之,丢了皮就会死亡[23]35。甚至蛙本身也是死亡的象征,在有的传说中,它剥夺了人类蜕皮的能力,把死亡带到人间[23]33-34。
这一切都让蛙成了壮族先民崇拜的对象。时至今日,在红水河流域盛行的蚂□节上,壮族师公仍会在做“道场”时跳“蚂□舞”——模拟青蛙的动作,唱“蚂□歌”——叙述蛙神的故事。而蚂□节最重要的环节,是捉到一对青蛙并杀死,然后给予隆重的葬礼和祭祀——仍然与死亡紧密相连[22-24]。
笔者因之而推测,左江流域实行岩洞葬的壮族先民在为族人寻找安葬之地时,其中一部分人偶遇了岩画。面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几乎铺满整面崖壁的图像,而且像极了象征着死亡与重生的蛙形,其心灵所受的冲击可想而知。清人汪森《粤西丛载》引张穆《异闻录》:“广西太平府(今广西崇左境内)有高崖数里,现兵马持刀杖,或有无首者,舟人戒无指,有言之者,则患病。”描绘的便是当时人们见到岩画时震惊又恐慌的情形;而比这还早近千年的壮族先民的惊恐程度,必定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将族人棺木置于被“蛙神”环绕的岩洞中,无疑是祈求重生的最佳选择。
左江流域岩画的作画者和左右江流域岩洞葬的使用者,虽然两者间存在一定的时代错位[10,25-28],但因为有相似的信仰基础,后来者被前人留下的遗产所吸引是完全合理的推测。
4 来自棺画的提示
值得注意的是,西南地区除了广泛分布有岩画与岩洞葬外,与之相伴的还有棺画。
“棺画”顾名思义是指在棺木上绘制的图像。在贵州惠水仙人桥岩洞葬[29]、广西南丹里湖岩洞葬[30]、贵州平坝岩洞葬[31]、贵州荔波瑶麓岩洞葬[32]以及四川珙县悬棺葬[3]的棺木上都发现有棺画存在。
这批棺画多用粗线条描绘形象,而少见左江岩画常用的剪影平涂的方式,寥寥数笔,虽抽象,但特征鲜明;多用白色颜料,显然是为了使画面能在棺木上更为显眼;各处棺画画面内容稍有不同。仙人桥岩洞葬以马和骑马人物为主,另有一定数量的带有光芒太阳状图案。除此之外,便仅有难以明确所指的几何纹饰(图11(5));里湖岩洞葬所见棺画不多,仅4幅,且画面不甚清晰,但是从可辨识的图案来看,也以马和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图11(8));平坝岩洞葬仅见少量鱼纹和钱纹,或绘或雕,并不固定;瑶麓岩洞葬棺画内容较为繁杂,女性绘绣花、凉亭、雨伞、鱼、鸟、镰刀、锄头、柴刀等,男性绘猎枪、狗、鸟、斗笠、犁、耙、牛等,都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不见对马或骑马人形象的描绘(图12)。珙县悬棺葬的棺画因风雨侵蚀与鸟兽破坏等原因而难以辨识具体内容。

图11 棺画与岩画举例
棺画主要分布在黔南、桂北、滇东南一带,与这一区域的岩画有着较高的一致性。贵州画马岩[33](图11(1、2))、傅家院[33](图11(3、6))、龙里巫山[34](图11(4))3处岩画都以马和骑马人物为主要描绘对象,并且采用粗线条描绘和部分剪影平涂并用的技法进行绘制。广西天等[35](图11(7))、宜州[36]两地岩画400余个图像中也以线绘马和骑马人物为主。这不免让人想到《岭外代答》对这一地区南宋“产马之国”的记载:“产马之国曰大理、自祀、特磨、罗殿、毗那、罗孔、谢蕃、滕蕃等。”据李飞所考,“特磨”“罗孔”与滇东南砚山、广南两地对应;“自祀”“罗殿”“毗那”“谢蕃”“滕蕃”则都是贵州岩画的分布范围[11]246。马市的设立,或使得马成为此区域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经济支柱,进而在岩画、棺画中予以大量表现。因此,此类岩画与棺画应属距设立马市不远的宋明时期。
考察贵州平坝、荔波岩洞葬,其棺画内容不同于其他,内容繁杂,多是对现实生活琐碎事物的描绘或纯几何纹饰(图12),表达的是对富足生活的向往;所用颜料也杂乱不一、色彩各异,墨、炭、牛血、粉笔均有使用。据14C测年数据及对画面内容的分析,平坝带棺画的棺木年代最早不过明代,荔波的棺木或晚至清中晚期[11]231。故而与以马和骑马人物为主要内容的棺画及岩画并不属于同一时期,其年代应更晚,部分棺画甚至可能是近代所绘。

图12 荔波瑶麓岩洞葬棺画
鉴于棺画应是丧葬仪式的一部分,与岩洞葬有着密切联系,而桂北、黔南、滇东南一带岩画与棺画,从地理分布到画面内容、作画技法上都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这暗示岩画与岩洞葬之间或许并非
毫无关系,在部分地区两者可能都曾作为丧葬仪式的组成部分,以重现死者生前的社会环境。所以虽然从目前来看,无论是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无直接证据证明左江流域的岩画与岩洞葬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但如李飞在《魂兮归去:从贵州惠水仙人桥岩洞葬棺画论中国西南系统岩画》[11]中所尝试的,结合民族学、神话学的相关研究,如果把视野放宽,将整个西南地区的岩画与岩洞葬纳入考查范围,那么两者的关系仍然有继续深入探讨的空间。
5 结束语
经过仔细梳理排查,厘清了左江流域岩画与岩洞葬各自在空间与时间上所处的位置之后,不难发现两者在一定时期(南朝末年至宋朝)和一定空间范围内(左江流域部分崖面)存在共存关系。同时结合民族学与神话学的相关研究,均属壮侗语族先民遗存的岩画和岩洞葬,虽有活跃共存期,但岩画并非直接为死者(岩洞葬)服务;而在岩画创作停止后的历史时期,作为后来者的岩洞葬和作为先行者的岩画,基于相似的信仰,虽然岩画并非为岩洞葬而绘,但客观上却对后来的岩洞葬在选址时产生了影响,两者存在着异时性关联。基于此,在进行左江流域岩画的研究与保护时,应给予岩洞葬足够的重视,并将其作为岩画相关遗址一并考虑在内。
(岩画与岩洞葬分布图为作者绘制;岩画地点照片为作者拍摄)
[1] 张世铨.广西崖洞葬和几个有关问题的商讨[C]//民族学研究∶第四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93- 123.
[2] 黄现璠,陈业铨.广西宁明花壁画与岩洞葬[C]//西南民族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394-399.
[3] 四川省博物馆,珙县文化馆.四川珙县“焚人”悬棺及岩画调查记[C]//文物资料丛刊(2).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187- 195.
[4] 涂朝娟.珙县僰人岩画研究∶宗教崇拜支撑下的图像[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4∶10.
[5] 陈明芳.中国悬棺葬[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138.
[6] 邱钟仑.也谈“花山壁画与岩洞葬”[J].广西文物,1986(2)∶40- 44.
[7] 彭书琳.广西古代崖洞葬[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28.
[8] 原思训,陈铁梅,胡艳秋.广西宁明花山崖壁画的14C年代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1986(4)∶27- 33.
[9] 覃圣敏.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138- 144.
[10] 王克荣,邱钟仑,陈远璋.广西左江岩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202- 208.
[11] 李飞.魂兮归去∶从贵州惠水仙人桥岩洞葬棺画论中国西南系统岩画[M]//南方民族考古∶第八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12] 蓝日勇.左江流域岩壁画始作年代辨正[J].南方文物,1997(1)∶88- 93.
[1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南宁市博物馆,武鸣县文物管理所.广西武鸣县岜旺、弄山岩洞发掘报告[C]//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06-237.
[14]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龙州县博物馆.龙州县更洒岩洞葬调查清理报告[C]//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63-73.
[1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南宁市博物馆,武鸣县文物管理所.武鸣敢猪岩洞葬发掘简报[C]//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74- 93.
[16]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南宁市博物馆.广西先秦岩洞葬[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97- 124.
[17] 武鸣县文物管理所.武鸣独山岩洞葬调查简报[J].文物,1988(12)∶29- 31.
[18] 贺县博物馆.广西贺县龙中岩洞墓清理简报[J].考古,1993(4)∶324- 329.
[19] 梁庭望.壮族图腾初探[J].学术论坛,1982(2)∶76-78.
[20] 梁庭望.水稻栽培∶壮族祖先智慧的结晶[J].广西民族研究,1992(1) ∶65- 71.
[21] 丁颖.中国稻作之起源[Z].农艺专刊第七号,1949.
[22] 莫俊卿.左江崖壁画的主体探讨[J].民族研究,1986(6)∶70-72.
[23] 李斯颖.从侗台语跨境民族的死亡起源神话到左江岩画[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5)∶33-35.
[24] 刘继辉.广西宁明花山崖壁画文化研究[D].南宁∶广西师范学院,2011∶17.
[25] 邱钟仑.左江岩画的族属问题[J].学术论坛,1982(3)∶70-75.
[26] .张一民.广西左、右江地区崖洞葬初步调查[C]//民族学研究∶第四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250- 260.
[27] 广西博物馆,田东县博物馆.广西左右江流域崖洞葬调查研究[J].江汉考古,1991(3)∶28- 36.
[28] 周继勇.广西崖洞葬问题探讨[J].广西文物,1991(2)∶31-40.
[29] 李飞.魂兮归去∶从贵州惠水仙人桥岩洞葬棺画论中国西南系统岩画[C]//南方民族考古.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225- 272.
[30]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南丹县里湖岩洞葬调查报告[J].文物,1986(11)∶71.
[31] 熊水富.平坝“棺材洞”清理简报[C]//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398.
[32] 席克定.荔波县瑶麓瑶族的岩洞葬[J].贵州民族研究,1982(1)∶99- 106.
[33] 王良范,罗晓明.贵州岩画∶描述与解读[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15- 53.
[34] 李飞.试论贵州龙里巫山岩画[J].四川文物,2006(3)∶54-58.
[35] 卢敏飞.天等崖画与左江崖画关系初论[J].广西民族研究,1985(2)∶68- 73.
[36] 李楚荣.广西宜州发现的铜鼓、画马崖画与古代马市、驿铺关系初探[J].广西民族研究,2001(2)∶108-110.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iff Painting and the Cave Burial in the Zuojiang River Valley
ZHANG Lin
(The Palace Museum,Beijing 100009,China)
There are some remains of cave burials around the cliff paintings in the Zuojiang River valley. Between the cliff painting and the cave burial, there is some certain kind of relationship which is not internal. The relationship is non contemporaneous and is based on similar faith.
Zuojiang river valley;cliff painting;cave burial;non contemporaneous relationship
K879.42
A
张林(1988-),男,助理馆员,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及新媒体传播。E- mail∶zhanglin@dpm.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