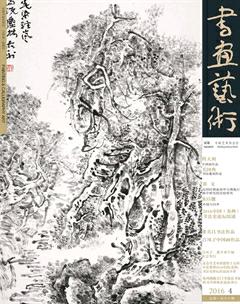中国画十题
程大利
一
中国传统绘画深受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和陶融。刘勰云:“人文之始,肇自太极。”(见《文心雕龙》)由此而出发的中国画与其他民族的艺术拉开了距离。它的不重写实的“心象”观,强调人格品操的中正观和以书法入画的笔墨观都与西方造型艺术不尽相同。它虽不长于以宏大叙事的方式直接参与社会变革,但仍表达着真切的生活感受和深刻的人生意义,它“内修心而外益世”“抒胸臆而振斯文”,通过养心修身和知世悟道完成“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归于至善,“渡己”也“渡人”。
讲究“人”“文”双修的传统中国画之所以不易于普及,是因为它对欣赏者有文化要求。“文”是进入中国画创作和欣赏的门槛。因“文”而“共成化育”,不是简单的“表现”“再现”问题,是“体道义之合,究圣哲之蕴”,画画是为了修为,修成君子。中国画的最高指归是“内美”,屈原有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内美修能”就是为人格塑造。在中国画里,热烈不是宣泄,冷静不是冷漠,最忌高远失中、偏激不平;观通不妨照隅,求末亦是归本。这是中国画的本质特征,它的最大功能是让人静下来、淡下来、最好也慢下来。传统中国画从不表现争斗和血腥,却亲近造化,是自然的歌者。它追求至静至远,调和天人。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知识分子无论达或穷,书画都是修为的手段。
二
“逸”是宋之后,贯穿中国画精神的一个核心命题,如果仅仅把“逸”看作是“文人画”的产物,这认识是狭隘的。“逸”是笔墨文化成熟的标志。“逸”关乎才情,更关乎修为和境界。历来对“逸”的论述可以概括为六个字:不象——不愿拘泥于物象,“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实在是不屑于那个“象”。自由——忠实于个人情感。不做,不刻,不雕,不期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如果做出来的也可能达到了“妙”和“能”,在流和做之间也能达到“神”,但“逸”必然是流出来的。出尘——与“意识形态”无关,不为谁服务,不为时风左右,不顾大众需求。当然它又绝然不是与社会对立,它是通过内省而达至善。人们欣赏它得先要提升自己,修养到一定的功夫,才能有所解悟。
三
气韵一词,最早见于钟嵘《诗品序》,内有“九品论人,七略裁士”句。“九品论人”是国家选拔人才时分人物为九品(见班固《汉书·古今人物表》),选才考试依据为“七略”(指刘向、刘歆所编诸子诗赋的总目)。由此形成了重视品藻人物的社会风气。《世说新语》等书中有很多当时品评人物的记载。气韵一词最初喻人,后用到文章诗赋的品评中,如梁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气韵一词成六朝文化的精神所在。南齐谢赫在论人时也用了“气韵”一词,他在《古画品录》中评张墨、苟勖时说到“风范气韵,绝妙参神”,我们能由此想像出这两人的气质。在六法中谢赫把“气韵生动”列为第一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在人物画发达的当时,人物的气质、韵致、风度、神采,乃至修养、性情均应是“生动”的。后来这个要求推广到对山水画和花鸟画的要求上,成为对画面境界的要求,经过自张彦远以来尤其是元明清以来历代评论家、画家的诠释,气韵生动成为对中国画的至高要求。但后人有气韵生动理解为技术上的墨法者,此大谬也。明唐志契在《绘事发微》中说:“画山水贵乎气韵,气韵者非云烟雾霭也,是天地间之真气。”故理解气韵生动着实须下番研究功夫。前入经验是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沉;有韵则远,无韵则局。物色在于点染,意态在于转折,情事在于犹夷,风致在于绰约,语气在于吞吐,体势在于游行,此则韵之所由生矣。气韵者是不修、不做、不雕、不刻意,气韵是“创作”不出来的,是流露、是生发、是无意而为,如行云流水,得之于心,应之于手,自然而然天成之物。气韵与急功近利相悖,与世俗也不相容。所以当下之“创作”,不见气韵也就不足为怪了。
汤用彤先生说:汉人朴茂,晋人超脱。又说:汉代相入以筋骨,魏晋识鉴在神明。画家当细细品味之。
四
明清以降,画论多为形而下的阐发,对技法的论述日益精细,成为审美经验和技巧的汇集。而早于此前一千多年的六朝画论则更倾力于艺术思想的阐发。再上溯至先秦,则是对艺术哲学的探究。老子《道德经》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出了中国画的本源在哲学。六朝的刘勰认为“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见《文心雕龙》)。太极之说见之《易经》,黄宾虹认为笔墨变化的一切规律均藏于那个太极图中。伏羲画卦见于《易·系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天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俞剑华先生解读这段话是“实借种种思考经验而后逐渐发明以归纳成”的符号,这种符号“为宇宙万物之抽象表现,已具备后世绘画写生之法”(见俞剑华《中国绘画史》)。而对于“道”与“器”的论述,《易·系辞》明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艺术思想通达天地之道,最神奇的是一部医书中有画学思想。《黄帝内经》有云:“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是画家的最佳状态,有通达天地的恬淡真气,有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就不会被世俗的干扰侵害,画面会有清净感。《老子·十六章》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心灵静寂虚明,才不为外物干扰,从而洞悉造化本质,澄怀观道即为此意。老子接着又说:“静胜躁,寒胜热,清净以为天下正。”这是中国画家的修为。认识到此即已不易,知行合一尤难。清人张式直接要求画家“学画当先修身,身修则心气和平,能应万物;未有心不和平而能书画者”(张式《画谈》)。这样一来,对追求时尚成为时代精神的当代,中国画的本旨已变成遥远而虚无的概念,今人若不潜心思考,所画者与本质意义上的中国画只能愈来愈远了。
五
石涛有句名言:“笔墨当随时代。”这句话造成数百年之误读。笔墨当随造化,山水画的笔墨来自山川,而山水是永恒的,在这种永恒面前,人的所有活动都是短暂的。研究山川宇宙的永恒是人类始终的兴趣。其实这也是石涛的认识,否则何以有“一画”和“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见解呢?石涛力主“笔墨当随时代”,结果笔墨较之弘仁、髡残、八大多了些“人间烟火气”,实际上是多了几分浮躁。他才华过人,留下不少好作品。但许多作品徒见个性,不见山川境界,或者说不见深邃的静寂,也鲜见笔墨的金石高趣,不少作品锋芒外露,处处机锋。石涛“丹青竞胜”“笔墨贪奇”,在传统画论看来,这都是毛病。为什么在20世纪大受追捧呢?因为20世纪的时代精神是革命和批判,同时把西方传人的对个性的张扬作为首要标准,并视为时代精神。所以,石涛上人的缺点便被当成优点,甚至作为典范。今天我们看石涛还是“古之面目”,但少了许多简古平朴之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