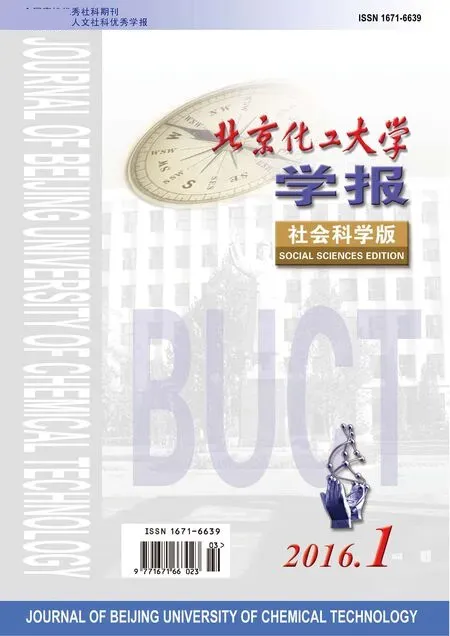双声部和弦:《老人与海》中的自我复调
张媛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8)
双声部和弦:《老人与海》中的自我复调
张媛
(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8)
《老人与海》打破了一元化的“独白”结构,呈现出多元的“复调”结构。复调世界是多种声音对话的纷杂世界,它的矛盾性、对话性、开放性和未完成性,恰恰切合了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世界的多元、暧昧和边界模糊的状态。大海上独自搏斗的圣地亚哥与自我展开对话,说出的话语与内心声音进行交流,充分展示了对自我的肯定、对它者的尊重,在探索人与自然复杂动态的生存经验中触摸独特的生态智慧。
《老人与海》;复调;独白性对话;平等
海明威在接受访问时曾说过自己在《老人与海》中写的是一个好男人和一个好男孩,而且海洋也像人一样,值得大书特书。就是这部关于老人、男孩和海洋的书使海明威获得了1953年的普利策奖,并且主要归功于此书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使海明威荣获195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此书出版后评论家就纷纷评论这则简单的故事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是一个多层次的寓言,对此,海明威在1952年9月13日致艺术史家伯纳德贝瑞孙的信中却这样回应道:“没有什么象征主义的东西。大海就是大海。男孩就是男孩,鱼就是鱼。鲨鱼就是鲨鱼……人们说什么象征主义,全是胡说。”他又说:“我试图描写一个真实的老人,一个真实的男孩,真实的大海,一条真实的鱼和许多真实的鲨鱼。然而,如果我能写的足够逼真的话,他们也能代表许多其他的事物。”[1]显然海明威是要抛开人为强加在小说上的多层涵义,而彰显简单故事的真实性。展示真实性是海明威一再声称写这部小说的创作意图。小说结构朴素,情节简单,诚如海明威自己所说,这本小说“本来可以写成一部一千多页的巨著,可以将渔村的每个人物都写进去,把他们如何谋生、出生、受教育和养儿育女的过程全部写进去”,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砍去芜杂的枝蔓,“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2]。
可以说这部小说的主旨不在于描述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描写跌宕起伏的性格命运,而是多维度看待人与自然交往中的复杂经验,强调不同个体的独立意识,不仅表现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而且还展现那些拥有各自主体世界、有着同等价值、具有平等地位的不同的独立意识,提供一个舞台让他们发出个性鲜明、独立自主的声音,这是一个由多种声音对话建构的复调世界。这些声音发自于老人、男孩、大海、鱼、鲨鱼、月亮与星星,他们都是独立的主体,他们在交流,在融合,力图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协调共存的关系,力图还原人性在现实社会、在自然中的真实状态,充分展示了对自我的肯定,对它者的尊重,在探索与追求人与自然复杂动态的生存经验中触摸生态智慧,或许这就是海明威所说的“我试图描写一个真实的老人,一个真实的男孩,真实的大海,一条真实的鱼和许多真实的鲨鱼”。
一、自我的复调
巴赫金认为“复调”不仅是叙事文学的一种认知方式,而且是作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3],这是“一种超出小说体裁范围之外的特殊的复调艺术思维,这种思维能够研究……人的思考着的意识,和人们生活中的对话领域”[4]。巴赫金将音乐中的多重声音引入到诗学批评中去,提出对话即复调,如作品中人物的自我对话形成自我的复调,这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彼此相互冲突的中心,它们各自独立,又曲折交叉,使得对话复杂而精彩。《老人与海》中主人公圣地亚哥的声音是“多声部的”,大海上独自搏斗的他与自我展开对话,说出的话语与内心的声音进行交流。这种自我对话或独白性对话形成自我的复调,既充分尊重自我,又揭示自我的弱点,展示一个真正的“我”。
圣地亚哥在小说中的形象很难归类于某种模式来评述,他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英雄,因为他只是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渔夫在做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捕鱼,捕鱼是他生存的唯一来源、目标和动力。他知道哪儿是捕鱼“十拿九稳”的地方,“钓丝垂得比什么人都直些”,他总是提醒自己“现在只应该思量一桩事。那就是我生来要干的事”[5];但他也绝不是十足的失败者,因为他独自一人在大海上与巨大的马林鱼周旋,和无数凶猛的鲨鱼搏斗,用尽一切可能的武器,用浆、短棍和舵把捍卫自己和鱼的尊严,虽然最终带回港湾的只是一副大马林鱼的骨架,但用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人生信条:“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6]
应该说圣地亚哥是一位个性没有经过修饰的人,确切地说是具有独立自我意识的人。在这里圣地亚哥没有作为客体被作者加以观察、分析和描绘,而是作为主体通过独白性对话展现自我,既充分尊重自我,又揭示自我的弱点。正如考夫曼曾说,这样的主人公“不需要浮面的装饰,心灵的活动已完全自给自足,然而这个心灵却能自觉它的每个弱点,并决定去揭发它,我们所听到的是个性之歌中未被听到的一首:不是古典的,不是圣经式的,也绝不是浪漫的”[7],这是圣地亚哥张扬自我个性之歌。
圣地亚哥的独白性对话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自我,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人。对话在这里不只是作为推进情节的有效手段,更主要是成为表达独立的自我存在的途径,这是出于创作目的的考虑。这种独立意识不能被旁观者所描绘,只能是圣地亚哥通过独白性对话一方面告诉读者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另一方面也在告诉、告诫自己要清醒地、正确地看待自我。在这里独白性对话是表明存在的唯一途径,离开了对话,他的意识仿佛也就不存在了。大海上独自搏斗的圣地亚哥通过与自我展开对话,肯定自我的存在,“我说”和“我想”两个声音同时存在,这就如同一人分别饰演两个角色的二重唱,两个声部既有不同之处也有一致之处,共同表达一个主题。“我”有时作为主体发声,有时又作为客体说话,又或是他们两者之间对话,说出的话语与内心声音进行交流。两种声音,三种状态,使“我”处于一种张力中,也是“我”每次遭遇困难但又马上振作起来顽强抗争的精神支柱。
刚开始出海时,读者所能听到的是圣地亚哥内心的声音,这个声音告诉我们他喜欢飞鱼——他在海洋上主要的朋友,会替纤弱的鸟儿伤心,“鸟儿的生活过得比我们的还要艰难”[8],把海洋当成女性,对她充满了好感,“如果她干出了任性或缺德的事儿来,那是因为她由不得自己。月亮对她起着影响,如同对一个女人那样,他想”[9]。此处内心宁静的诉说与海上的风平浪静相呼应,显示出他是一个热爱周边生物、体恤弱小、与自然和睦共存的老渔夫。在此刻,圣地亚哥视万物与人处于同一生命层次,他与自然亲近,视自然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心灵上与自然达成契合。
随后,当一只军舰鸟出现时,读者开始听到了圣地亚哥的另一个声音,“‘它逮住什么东西了’,老人说出声来。‘它不光是找找罢了’”[10]。大声说出的话语似乎是让所有的人包括自己都听见,声音里充满了兴奋,因为大鸟可以帮他找到鱼群,也就意味着钓到大鱼的机会来了。随着这个声音的出现,老人的形象与内心声音描绘的自我形象产生了矛盾。虽然热爱生物、体恤弱小,但作为一名渔夫,他又必须捕鱼,甚至要带着兴奋感、成就感杀死鱼。他曾经钓过一对大马林鱼中的雌鱼,连连用棍子朝它头顶打去,虽然看见雄鱼一直待在船边不肯离去,但还是马上把雌鱼宰了。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捕鱼是一种要用圈套、罗网和诡计欺骗的勾当。两种不同声音同时出现表现了两种对立的思想,这种既热爱自然界生物又要用残忍手段杀死它们的矛盾行为反映出美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两种思想的对抗,即敬畏自然与征服自然的矛盾冲突。在文中圣地亚哥坦然接受这对矛盾的存在,并未对此表示不安或试图找到解决之道,这种开放性和未完成性表现出他对这个世界多元化、模糊化的理解。
随着与大马林鱼开始展开周旋,圣地亚哥的这两个声音的交流日趋频繁:“‘鱼啊,’他轻轻地说出声来,‘我要跟你奉陪到死。’依我看,它也要跟我奉陪到死的,老人想。”[11]这是老人与鱼进行较量的初期,老人信心十足,决心把鱼杀死:“‘鱼啊,’他说,‘我爱你,非常尊敬你。不过今天我得把你杀死。’但愿如此,他想。”[12]两个声音互相呼应,彼此鼓励。当相持的时间过去了一夜和一个白天,老人的左手开始抽筋,身体的疼痛快要超出极限,但这两个声音依然保持乐观的态度:“‘你觉得怎么样,鱼啊?’他开口问。‘我觉得很好过,我左手已经好转了,我有可供一夜和一个白天吃的食物。拖着这船吧,鱼啊。”[13]虽然他并不真的觉得好过,但转念想到:“‘不过比这更糟的事儿我也曾碰过,他想。我一只手仅仅割破了一点儿,另一只手的抽筋已经好了。我的两腿都很管用。再说,眼下在补给营养方面我也比它占优势。’”[14]凭着毅力、智慧、自信,圣地亚哥终于钓到了这条足足有一千五百磅重的大鱼,这条大马林鱼健壮而美丽,有着庞大的身躯和周身的紫色条纹。
可是鱼腥味引来了穷凶极恶的群鲨,虽用尽各种武器,鱼肉还是被吃光了,这时的两个声音失去了往常的和谐,开始对驳起来:
光景太好了,不可能持久的,他想。但愿这是一场梦,我根本没有钓上这条鱼,正独自躺在床上铺的旧报纸上。
“不过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他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然而我很痛心,把鱼给杀死了,他想。现在倒霉的时刻要来了,可我连鱼叉也没有。这条登多索鲨是残忍、能干、强壮而聪明的,但是我比它更聪明。也许并不,他想。也许我仅仅是武器比它强。
“别思索啦,老家伙,”他说出声来。“顺着这航线行驶,事到临头再对付吧。”
但是我一定要思索,他想。因为我只剩下这件事可干了[15]。
“我说”与“我想”这两个声音互相驳斥,自相矛盾,把老人对鱼的复杂感情表现得一览无余,使故事达到高潮。一方面,老人把鱼视作自己的朋友,它的庞大、美丽、沉着、崇高令老人对它肃然起敬,而另一方面,自己作为渔夫面对生活的重担又不得不杀死这个朋友。看见被鲨鱼糟蹋得不像样失去往日尊严的大鱼,老人心中充满愧疚,后悔不该出海太远,钓上了这条鱼。
“我说”与“我想”两个声音的对话讲出了内心的挣扎与喜悦,让读者倾听到圣地亚哥心迹的自我表白,展现出一个真实的自我。
二、多元的“复调”结构
《老人与海》打破了一元化的“独白”结构,呈现出多元的“复调”结构。这种复调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是人与自然各自作为独立主体和谐共处的肯定。它打破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表明存在是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的交往与融合。大海上独自搏斗的圣地亚哥与自我展开对话,说出的话语与内心声音进行交流,既揭示自我的弱点,又充分展示了对自我的肯定及与其他生物、与大自然平等共生的和谐关系。这种“复调”结构不同于独白型结构,独白型结构取决于作者意识对描写对象的单方面规定,这里只有一个声音,即作者的声音在说话,一切主人公的语言、心理和行为都被纳入作者的意识,都在作者全能全知的观点中得到外来说明。而“复调”结构中的主人公具有独立的自我意识,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也是直抒己见的主体。圣地亚哥的自我不是由一个唯一的声音表达出来的,而是两个既对立又平等的声音展现一个真实的自我。“我说”与“我想”两个声音被赋予了极大的自由,平等对话,让他们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两个声音处于平等的地位上,缺一不可,互相阐明,互相解释。两个不同的声音紧紧围绕着一个主题,展现现实社会中的一名既与大自然抗争又敬畏自然的渔夫,他知己至深,十分清楚自身的优势,对于自己要钓的大鱼,他懂得如何运用技巧与耐力赢得战斗。他从不狂妄吹嘘,而是等待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这是自我的复调,凸显的是一种平等。
既对立又平等的复调结构不仅是对自我的肯定,也反映出人与自然复杂动态的共存关系,正如云得煜所说:“在大海这个生物圈里,不同的生物物种之间为了生存自然地组成了一个动态的生物链条。”[16]作为生物链上的一员,老人为了生存而捕鱼,杀死大马林鱼,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大马林鱼及其它生物的尊重:“他替这条没东西吃的大鱼感到伤心,但是要杀死它的决心绝没有因为替它伤心而减弱。它能供多少人吃啊他想。可是他们配吃它吗?不配,当然不配。凭它的举止风度和它高贵的尊严来看,谁也不配吃它。”[17]自然是圣地亚哥孤独生存的慰藉,是他的精神家园。在大海上他从来就没有感觉到孤独,他与星星、月亮、大鱼对话。他敬畏自然,承认自然是与人一样的主体,具有神圣性、神秘性与不可预测性。在他眼里,五彩斑斓的自然是如此艳丽、鬼魅而神秘;绿色、青色、蓝色、红色各种绚丽迷幻的色彩交织在一起令人神往:“陆地上空的云块这时像山岗般耸立着,海岸只剩下一长条绿色的线,背后是一些灰青色的小山。海水此刻呈深蓝色,深得简直发紫了。他仔细俯视着海水,只见深蓝色的水中穿梭地闪出点点红色的浮游生物,阳光这时在水中变幻出奇异的光彩。”[18]自然奇异的、让人捉摸不定的神秘一面令人敬畏、膜拜。
三、结语
大海上独自搏斗的圣地亚哥与自我展开对话,“他说”与“他想”作为复调的两个声部,说出的话语与内心声音进行交流,充分展示了对自我的肯定、对它者的尊重,在探索人与自然复杂动态的生存经验中触摸独特的生态智慧。圣地亚哥自我的复调正是由若干各自独立但彼此对立的声音或意识共存共在并且交流互动的统一体。他们在彼此对话的关系中互动共生,通过艺术手法将各种声音或意识加以组织。复调世界就是多种声音平等对话的世界,自我的声音、男孩的声音、大海的声音、大马林鱼的声音各自独立又相互交叉,组成了巨幅的社会生活图景。它的矛盾性、对话性、开放性和未完成性,恰恰切合了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世界的多元、暧昧和边界模糊的状态,描写出了生活的多种可能性和人性深处的矛盾,而不是灌输一种绝对的、千篇一律的思想,使得小说既具有辨证色彩,又包含多重维度的可能。人与自然平等共生,自然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条件而人类又是自然界平衡发展的重要环节。《老人与海》在深刻剖析现代人的生存面貌和精神状态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魅力的同时,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人与自然复杂动态的共存的生态美学观点。正如海明威所说:“《老人与海》花了我一生来写作,但是涵容了现实世界和一个人的精神的所有纬度。”[19]
[1][2]董衡巽编.海明威谈创作[M].上海:三联书店,1985. p145,p50.
[3]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p346.
[4][苏]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88.p363.
[5][6][8][9][10][11][12][13][14][15][17][18][美]海明威.老人与海[M].吴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p18~19,p24, p66,p16,p17,p31,p33,p34,p47,p66~67.p48,p51.
[7][美]考夫曼.存在主义[M].陈鼓应,孟祥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p3.
[16]云得煜.生态批评视野中的海明威自然观及其吊诡[J].求索,2013(8):p155~157.
[19][美]海明威.海明威书信集(下)[M].杨旭光,袁文星,译.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p763.
Self’s Polyphony in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Zhang Yuan
(School of English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Xi’an Shanxi 710128,China)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approach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nologic dialogue articulated by Santiago,the hero in the novella,hence projecting the thematic equalit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The novella goes beyond the boundary of the self-sufficient and closed authorial monologue and is open to dialogized heterogolssia.Fighting alone on the sea,Santiago converses with the self in confirmation of his value and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mong Nature and all the creatures.
The Old Man and the Sea;polyphony;monologic dialogue;equality
I712.074
A
1671-6639(2016)01-0068-04
2015-12-29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2014年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美国成长小说中的自然环境因素”(项目编号14JZ038)的阶段性成果。
张媛(1973-),女,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讲师。
——运动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