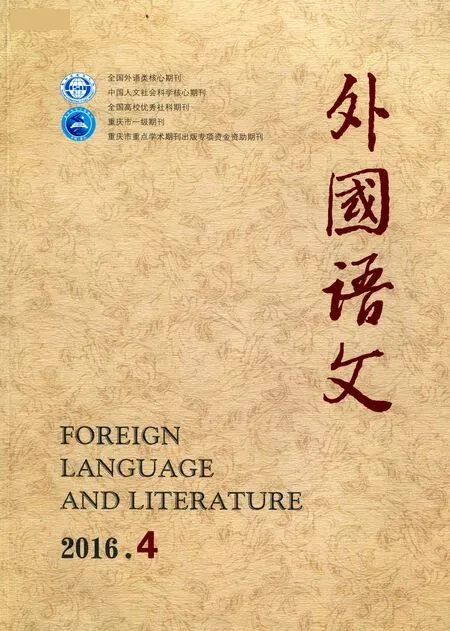论日本文化记忆场与文化传承的双向演进路径
姚继中 宋媛媛
(1.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重庆 400031;2.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应用外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论日本文化记忆场与文化传承的双向演进路径
姚继中1宋媛媛2
(1.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重庆 400031;2.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应用外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0)
文化记忆场与文化传承的关系问题,早已是学界公认的既定事实。然而,学界的公认并不等于我们对文化记忆场与文化传承的发生机制、以及两者之间自律与他律了然透彻。本文试图以日本文化记忆场与文化传承为研究对象,着重论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论述日本文化记忆场的文化传承机制;二是论述文化传承机制反作用于文化记忆场的信息载荷。通过文化记忆场与文化传承互补机制的研究,力求在日本文化研究方面力拓新视角、新认知、新方法。
文化;记忆场;传承;双向演进
0 引言
日本文化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常常会有“似曾相识”的错觉,那是因为日本文化中包含着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对于西方人来说,不乏同样的感觉,日本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层面所包含的西方的科学技术等,同样令西方人感到十分“亲切”。 正如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所说:“日本文明和表现该文明的日本艺术看上去时而非常‘中国’,时而非常‘日本’,时而非常‘西方’。”(艾伦·麦克法兰,2010:55)然而,日本民族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其文化有着日本民族区别于他人的本民族特质,它既不是属于中国文化体系,或者是西方文化体系中的哪一个,也不是对世界上哪一种文化的直接翻版。它是一个特殊的文化体系,即便是古代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引进,抑或是明治维新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大力输入,日本文化所呈现的状态其实已不是简单的中国化,或者西洋化,而已经充分地显示出了日本文化的独特之处。这种独特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有记忆,不会忘却更早的映像”(艾伦·麦克法兰,2010:55)。
日本小学馆出版的《日本大百科全书》对记忆一词的解释为:记忆是指保持某种经验,并用某种方法将其进行再现的功能。这里的经验指的是对来自外界的感觉和知觉的作用,或者是关于这种作用的意识。一个社会群体,无论是民族、宗族还是其他的社会团体,往往也和个人一样,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养成回忆和记忆的能力。日本的文化传承别具一格,正是来自于它深层次的文化记忆所致。
文化记忆,就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力。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所要问答的是“我们是谁”和“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文化认同性问题。任何一种文化,只要它的文化记忆还在发挥作用,就可以得到持续发展。相反,文化记忆的消失也就意味着文化主体性的消亡、文化的消失。
文化记忆是扬·阿斯曼用以概括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传承现象的极具当下意义的关键概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及社会群体不仅要时刻内省自己,同时也要向他人呈现。当记忆这个视角还未进入我们的视野中时,人们不停地通过历史去寻求自己的过去,从历史当中去找到自我的原初归宿,以得到在当下的身份认同。而当记忆成为我们探求过去的又一个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时,文化记忆就提供了人类“发现用以维持其本质始终如一地代代相传的方法”(简·奥斯曼,2011:67)。
对于日本的文化内核或者说是文化脊柱,我们一直都有着疑惑,甚至对于其存在本身也持有不同的见解。然而,当“文化记忆”这一概念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时,它就为我们进行日本文化研究尤其是文化内核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文化记忆是“用以概括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传承现象”(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2012:1)的,而某一文化的文化内核、文化脊柱就存在于其文化传承之中。
历史需要通过历史载体呈现,文化记忆(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的传承与体现同样需要文化记忆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文化记忆场”。日本文化的传承,是由许许多多能够唤起日本民族记忆的文化记忆场来实现的,它们构建起日本文化的整体形态,为日本人获得其民族身份认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文化记忆场包括代表性建筑物、历史遗迹、民俗、祭祀仪式、美术作品、历史人物、纪念日、哲学和科学的文本等,即能够唤起一个民族对其文化深层次的记忆的事物。这个事物可以是具体的物质性存在,也可以是一种象征性的行动,甚至包括精神层面的认知习惯。该事物指向的是具有文化张力的、能够构建民族同一性的文化。然而,我们决不能忽视另一个问题,当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场被“想起”的时候,因想起的人不同、想起的客观社会条件的不同,其记忆场所展现的侧重点也会不同,而这些不同的侧重点中不乏存在着未被历史认知的新事物,这些新事物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人们将有意无意地纳入文化记忆,并通过文化记忆与历史的关联性成为一种对当前历史认知的补充。这种补充能够使我们对该文化的把握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因此,在研究日本文化传承机制的过程中,以日本的文化记忆场作为考察对象,对于探讨日本文化的内核以及日本文化的传承机制不失为新的路径。
1 文化记忆场的文化传承机制
1.1 日本文化记忆场的研究对象
“文化记忆场”,与“记忆场”之间有着共同性,它是对“记忆场”的拓展,具有文化构建和身份构建作用。它们都具有物质性、象征性、功能性,它们都与群体相关联着,它们都是将记忆作为文化现象来进行探究的。诺拉在《记忆的场所》中列举了包括建筑物(凡尔赛宫)、档案馆、纪念碑、艺术品、文学作品、乐曲(如马赛曲)、教科书、历史人物、纪念日等在内的130个文化记忆场。所谓“记忆场”,它未必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事物或一个具体的场所,而是“任何能在集体层面与过去和民族身份联系起来的文化现象(无论物质的、社会的或精神的)”(阿斯特莉特·埃尔,2010:76)。这种文化现象可以唤起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使人们获得民族认同感,并以此延续着文化在后世的传承。
因此,日本文化记忆场的研究对象自然包括了代表性建筑物、历史遗迹、民俗、艺术作品、代表城市、祭祀仪式、历史人物、纪念日、哲学和科学的文本等,即一切能够唤起一个民族对其文化深层次的记忆的事物,都是日本文化记忆场研究的领域。顺着这一思路,我们曾在《日本文化记忆场研究之发轫》(《外国语文》,2013年第6期)中将日本文化记忆场做了以下分类:1)以物质表征的文化记忆场,包括以文字、非文字表征为基础的文化记忆场; 2)以社会表征的文化记忆场,包括概念型文化记忆场、传统节日、祭祀仪式、典型历史人物;3)以精神表征的文化记忆场,包括思想意识形态的文化记忆场、传统艺术等等。囿于篇幅所限,在此仅举二例稍加说明。
《万叶集》——文学“能与其他象征体系(如心理学、宗教、历史学、社会学等)对过去的阐释及其记忆纲领产生联系,并通过特殊的文学手段(如语言图像、意义形式或运用特殊的虚构形式,如对内心世界的描写)恰如其分地展现文化知识”(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2012:223)。《万叶集》作为日本最为古老的诗集,除了文学文本的意义内涵之外,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万叶假名”,它以汉字表音的形式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记述语言。它代表着日语由汉字向假名过渡的时代,承载着日本奈良时代由唐风文化开始向国风文化过渡的历史记忆。直到当今,日本民族只要提及《万叶集》,无论是个体记忆还是集体记忆,都会激发起对日本古代文字学、诗学起始的想象与文学文化发祥的共鸣。
传统节日(年中行事)——“社会并不是单个的人的简单聚集和相加,而是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的有机整体。某一社会群体的风俗、信仰、传统、制度、技术等因素必然会对社会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正是这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因素把某一群体内的社会成员结合并凝聚在一起,并成为这一群体与另一群体的区别性特征。”(张海燕,2011:97)日本的“年中行事”看似单纯的传统节日,其实它在文化记忆功能上已经超越传统节日的概念,在集体无意识中起到了社会统合与族群认同的作用。其实,纵观日本的社会传统,年中行事往往具有宗教性,反映着过去的人们对世界的宗教性认识。其内容同时也将过去的人们的生活状态集中地反映了出来,而这些随着年中行事的存在,被保留、继承到现在。例如,在日本的各种传统节日中,需要人们身着规定的传统服饰,其祭祀的场地与祭坛需要按传统要求进行装饰,所举行的仪式有禁忌和规矩,使用的道具、表现的传统舞蹈、技艺等都是代代相传而来的。
“在日常生活中个体的记忆受到其所属的社会群体的习俗、信仰、制度、思维模式等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社会因素会不断被同化为个体内在的行为标准,并以一个完全习俗化的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固定下来,从而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张海燕,2011:97)而这些个体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保留着他们关于过去生活的历史记录。这种从社会到个体、又从个体到社会的发展方式在无意识中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组成民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而这种传承方式正是传统节日对文化记忆的延续方式,也是宗教祭祀仪式对文化记忆的延续方式,因此,在探讨文化记忆场时不能将宗教祭祀仪式排除在外。
在这种宗教祭祀仪式的领域,“因人们共有的记忆内容作为媒介,在具体仪式和祭祀活动的反复作用下形成了记忆共同体。而祭祀仪式使该记忆共同体所共有的创始传说与当下的联系得到了巩固、加强”(アライダ·アスマン,2007:169)。如大尝祭、新尝祭这样的宗教祭祀仪式,其想起的对象是存在于绝对过去的神话传说,通过象征的祭祀内容和具体的祭祀活动,使其记忆保持着稳定性和持续性。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在一次次的提及、一次次的祭祀仪式的举行中不断延续下来。
1.2 日本文化记忆场的文化传承形态
在诺拉编著的《记忆的场所》刊行以后,日本国内关于“纪念馆”这一与记忆场有些类似的记忆媒介的研究也在文化社会史领域开展起来。其中代表性成果就是1999年由阿部安成等编著的《记忆的形式——纪念馆的文化史》。作者序文中这样写道:“本书所探讨的对象是纪念活动、铜像、祭祀仪式等‘记忆的形式’。这些‘形式’是怎样表现人们对过去的认识的,这些‘形式’是怎样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的,它体现着怎样的意义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具体的素材的基础上分析考察的内容……本书所述的‘记忆的形式’是在纪念、表现过去的事物、人物的行为发生时才得以形成的。”(阿部安成,1999:5)
从上述内容可知,阿部安成的“记忆的形式”与诺拉的记忆场在概念上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它仍为我们提供了日本学者已对文化记忆场展开研究的动向。在对日本文化记忆场进行探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厘清以下一些问题:即需要从历史、政治、思想、宗教、民俗、建筑、文学、艺术、文化、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论述具有“日本文化记忆场”功能的标志是如何承载文化蕴涵?如何传承文化蕴涵?在传承过程中如何不断更新和丰富自身的信息载荷?以及作为文化记忆场如何在意识形态与现实生活中对民族文化认同产生作用?我们往往会忽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在文化记忆延续和传承的过程中,大量的记忆内容会被整合、抹消、忘却、遗失,同时也有大量的记忆内容被重构,对这些被忘却、遗失,被重构的记忆的挖掘和整理,是文化记忆场研究中最为艰难的领域。
我们不妨以日本的祭祀仪式中的“大尝祭”为例稍加赘述。
历史是通过历史载体得到体现的,而文化记忆则是通过文化记忆场得以表现。所谓文化记忆场,它不一定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事物或是一个具体的场所,而是“任何能在集体层面与过去和民族身份联系起来的文化现象(无论物质的、社会的或精神的)”(阿斯特莉特·埃尔,2010:72)。这种文化现象可以唤起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使人们获得民族认同感,并以此延续着文化在后世的传承。文化记忆场的存在让文化记忆在具体的客观存在中得到展现。在日本文化中,祭祀仪式无疑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记忆场。
祭祀是人与神进行交流与沟通的方式,特别是在以神道为国家宗教的日本古代文化中,祭祀仪式更是在人与神灵之间建构沟通桥梁,是宗教范畴内被制度化了、形式化了的活动体系。祭祀仪式具有很强的文化认同性和传承性,因为“当一种文化执着的价值从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时,借助于仪式可以变得更加容易”(菲奥纳·鲍伊,2004:173)。可见祭祀仪式是一种使集体记忆得以存续的有效方式。它通过在特定场合、由特定人员定期举行的祭祀活动,将源自于过去的记忆和形象在当下显现,并将其继续保持和传承下去。这种在“当下的显现”让现代与过去形成直接关联,让人们能够形成对过去的文化认同,使文化记忆在祭祀仪式中能够继续存在并发展。
“大尝祭”是日本神道祭祀中最具代表性的祭祀仪式。在日本最为古老的史书《古事记》与日本最古的敕撰史书《日本书纪》中都有记载。它是由日本天皇这一在神道信仰中拥有着特殊身份的人物为中心而展开的祭祀活动,并由 “万世一系”的天皇代代相传直至今日。天皇将每年新收获稻米用作供奉其皇祖神衹,并与神衹共食,这项祭祀活动被称为“新尝祭”。“大尝祭”的核心内容与“新尝祭”基本相同,但“大尝祭”只在新天皇即位时举行一次,古来也有将“大尝祭”称之为“大的新尝”的说法。天皇驾崩后,新天皇首先举行“践祚”仪式继承皇位,然后举行大尝祭,得到神的认可,最后再举行“即位”仪式。若天皇继承皇位的时间是在这年的7月份以前(包含7月),“大尝祭”则在该年的11月举行;若在8月以后(包含8月),则推延到次年的11月举行。
“大尝祭”的起源与日本的原始信仰和其神话传说是分不开的,其源头是发生在绝对过去的具有原始信仰的祭祀活动。在日本神话中,太阳神以“天照大神”的具体形象出现,且被赋予了 “天皇祖先”的特殊身份。因此,在大尝祭中,天皇对天照大神的祭祀活动,不仅是对神灵的祭祀,也代表着对自己祖先的祭祀。这种将祭神与祭祖合而为一的特点正是大尝祭、新尝祭区别于皇室其他祭祀活动的地方之一。
“大尝祭”的原型编码中所蕴含的文化记忆信息异常丰富,且不说出自国家统治意义的需要,就普通日本国民而言,亦是无法抹去的民族认同的依靠。因为从日本神话这一日本传统文化的原型编码的记述中可知,在上古神话里,“天孙降临”与稻米有着直接联系。天照大神在得到稻米的种子之后,认为水稻是孕育苍生的根本,便在天孙降临日本时将其交予他,让其将稻谷种带到日本,从此日本成为一个“瑞穗国”。这是日本神话中对稻米文化产生的描述。而由天孙带来的稻种不仅成了日本的圣物,更成了神与日本人之间最为直接的联系。
在当今的日本,“大尝祭”已经不再是具有国家统治意义的祭祀仪式,但它仍然被保留了下来。虽然其中的原始的太阳神信仰的相关记忆已经淡化,甚至变成了一个不断被忘记的存在,但“大尝祭”的仪式却将这个忘记的存在不断提起,让现今的日本人不断想起,从而使这种记忆的存续得以实现。当然,其原有的太阳信仰在现今的日本文化中已经以一种象征的方式被重构,而且对天照大神等天神地衹的祭祀也只是一项保留着传统祭祀形式的象征化祭祀仪式。然而,天照大神仍然作为“皇祖神”存在于日本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它不仅能够唤起现今日本人对稻作文化的记忆,更重要的是构成了日本普通民众的族群认同。
如上所述,日本的大尝祭已不再是具有国家统治意义的祭祀仪式,它早已演变为一种极具“象征性”的文化记忆场。日本文化在这充满象征性的记忆场中传承延续至今。正如康澄在《象征与文化记忆》一文中指出:“象征的表现形式极为丰富,超出了人们的一般想象,但一切象征均具有超出其表现形式本身的广泛而普遍的意义,即象征是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能将人类丰富复杂、无形无相的精神世界以各种方式加以表达、保存和传承”(2008:55)。特别要说明的是,“象征因其高度的凝结能力构成了奇特而高效的文化记忆保存方式,是文化集体记忆机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康澄,2008:55)。象征性的文化记忆场不仅具有明显的循环性和重复性,同时能在新的符号语境中发生变化并使语境本身变化。这个过程既是文化记忆的“释放”过程,也是文化记忆的重构过程。而文化记忆的释放与重构的过程正是文化传承的演进机制。
2 文化传承机制反作用于文化记忆场的信息载荷
文化传承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产,是民族群体的自我完善,是社会中权利和义务的传递,是民族意识的深层次积累,是纵向的“文化基因”复制(赵世林,2002:10)。也就是说,文化传承是一个民族对其语言、行为、宗教、艺术、建筑、仪式、节日以及心理等各方面的承继。如何继承、传播和发展则是由该民族的文化传承机制所决定的。文化传承机制应包含文化的传承特征、传承形态、传承主体、传承载体以及运作模式。一个良好的文化传承机制能有效地发挥文化记忆场的作用,加厚记忆场的信息承载量。
日本在文化传承过程中,特别重视融合外来文化,有着明显的文化“内化”特征。这是因为日本是一个文化“内化”过程十分明显的国家,是世界上少有的以大量输入外来文化而闻名的国家。它不仅在古代大量吸纳中华文化,还在近代移植西方文化。在我们研究日本文化时,日本古代王朝时期(飞鸟、奈良、平安时代)和明治时期分别对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两次大的且集中的文化输入不容忽视,它们不仅改变了在输入前日本既有的文化形态,还致使日本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变化,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就出现了文化的“内化”。所以,对于“内化”这一非固定性的文化元素,在我们研究日本文化传承以及日本文化记忆时是必须引起特别重视的。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中曾提到过文化的“内化”,他认为:“内化的过程现在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关键部分,即真正的文化”(2010:37)。一种文化的结构与形式往往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元素也不可能是单一或唯一的。尤其是现代文化。现代文化中所含有的文化元素往往并不是产生于这个民族或者这个国家的历史本身,而是产生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所处在的社会对文化元素进行内化的过程当中的。现代文化的产生过程中,经常会看到多个民族文化相互冲撞、交融的情况,其产生后的形态,就是该民族在文化的冲撞、融合中将其内化后的结果。所以,当我们去探讨一种文化的元素时,或是去探究一个民族的文化整体时,我们不能仅仅只停留在文化成形后的状态,不能只是去分析该成形后的文化中的成分与元素,以及其对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影响,同样需要去分析、了解、探究在该民族的文化成形过程中是如何进行文化的“内化”的?其内化的特点、特征是什么?内化的动因、过程、影响又是什么?我们有必要对该民族在“内化”过程中所发挥的“文化上的”能动性进行解析。
这种“内化”,或者说这种具有民族性的文化能动性本身就是该民族的一种文化的展示。在这个过程中,该民族的文化记忆发挥着意识形态和客观存在条件方面的作用。文化记忆从民族有意识与民族无意识两个方面同时地、共同地影响着后世的文化“内化”活动。在文化的“内化”中间,包含着人们对既有文化的继承与改良,以及对它的舍弃。有的是在无意识当中就发生的,有的却是有意识地去进行的。这种对既有文化,或者说对“历史的”文化的继承、改良、舍弃本身就是日本文化传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我们对日本文化的文化传承路径或是记忆存续方式进行讨论时,文化“内化”这一特点就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这是日本这个有着内化过程十分明显的文化模式的民族的客观历史决定的,而“内化”的突出也反过来表明了日本文化记忆特点。
值得探究的是,日本这种“内化”的文化传承的特点并没有抹杀日本国民对固有文化的记忆,反而巩固,甚至加厚了日本文化记忆场在文化传承中的文化信息承载量。例如,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和本土化;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变异;西学在日本的传播和融合等等,都是在日本“内化”的文化传承演进中,加厚了其本身的文化信息承载量。
为何日本文化的传承会呈现出如此明显的“内化”特征呢?探寻其背后的民族记忆,也许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佐佐木高明在《多文化、多民族的世纪:日本文化的走向》一文中曾提到日本文化根植于人们朴素的“和”的美意识。他认为:“在出色融合各种外来文化要素,并经过提炼使之日本化的文化行为深处,潜藏着这样的美意识。这也是与传统的‘和’的精神相通的”(2000:37)。可以说,日本文化的传承之所以带有显著的“内化”特征,归根结底源自于日本人的记忆深处隐藏着“和”这个行为上的美意识。那么“和”这个美意识是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条件下产生的?“和”指的又是什么呢?据资料考证,日本从最古老的绳纹时代开始就不断地接受着来自外域的文化和技术。绳文时代末至弥生时代初水稻文化的传来,使稻米成为日本最主要的农作物。日本人尊崇稻米,认为稻米具有神的力量。稻米已成为日本社会和国民的集体记忆。正如艾伦·麦克法兰所说:“稻米是认知日本的关键” (2010:61)。稻米及其稻作文化深深地影响着日本人民族性格的形成。在古代,耕种稻米需要人们齐心协力共同完成。因此,长期的共同耕种,不但促使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集体意识,还使其在协同劳作中逐渐形成了“和”的精神与“和”的美意识。
日本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正是因为这自古就有的“和”的美意识才产生出强大的文化“内化”的动力。“内化”又使得日本文化跟外来文化碰撞时,不但没有丢掉固有的文化记忆,反而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厚了文化记忆场的内涵和信息承载量。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日本固有的“文化基因”之所以能在文化传承中始终保持稳定,并影响至今的原因。日本总能“根据自身需要有选择地吸收外域的先进文化,同时又保持着自身的文化特点,这不能不说是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一种承传”(王昌沛,2005:126)。
3 结语
“文化记忆场”是文化构建和身份认同的依附载体,是任何能在集体层面与过去和民族身份联系起来的物质的、社会的或精神的文化现象,具有唤起民族记忆的功能。记忆的场所,其记忆的内容是历史,而指向则是唤起记忆。
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文化记忆》中指出:“每个文化体系中都存在着一种‘凝聚性结构’,它包含两个层面:在时间层面上,它把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其方式便是把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对它们的回忆以某一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在社会层面上,它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对共同体的过去的记忆和回忆中剥离出来的。这种凝聚性结构是一个文化体系中最基本的结构之一,它的产生和维护,便是‘文化记忆’的职责”。(黄晓晨,2006:62)
文化借助记忆场的象征性传递沉淀在人类集体无意识心灵深处的记忆, 而象征中的文化记忆则是在创造与想象中得到有效的“释放”,“象征因其高度的凝结能力构成了奇特而高效的文化记忆保存方式,是文化集体记忆机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康澄,2008:56)。它不仅具有明显的循环性和重复性,同时能在新的符号语境中发生变化并使语境本身变化。这个过程既是文化记忆的“释放”过程,也是文化记忆的重构过程,而文化记忆的释放与重构的过程正是文化记忆场与文化传承的双向演进路径。
アライダ·アスマン.2007. 想起の空間:文化的記憶の形態と変遷[M].安川晴基訳.日本:水声社.
阿部安成.1999. 記憶のかたち―コメモレイションの文化史[M].日本:柏書房.
阿斯特莉特·埃尔.2010. 什么是文化记忆研究[G].饶珮琳,译∥冯亚琳,等主编.中外文化第1辑.重庆:重庆出版社.
艾伦·麦克法兰.2010. 日本镜中行[M].管可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菲奥纳·鲍伊.2004. 宗教人类学导论[M].金泽,何其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冯亚琳,阿斯特莉特·埃尔,主编.2012.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黄晓晨.2006.文化记忆[J].国外理论动态(6):61-62.
康澄.2008. 象征与文化记忆[J].国外文学(1):54-61.
简·奥斯曼.2011. 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G].陶东风,译∥文化研究:第9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昌沛.2005.论日本文化的兼容与传承[J].山西师大学报(6):125-127.
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M].杨东柱,王哲,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
张海燕.2011.城市记忆与文化认同[J].城市文化评论(4):96-104.
赵世林.2002.论民族文化传承的本质[J].北京大学学报(3):10-16.
佐佐木高明.2000. 多文化、多民族的世纪:日本文化的走向[J]. 郭洁敏,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5):35-38.
责任编校:肖 谊
第五届中国认知诗学高层论坛
会讯
文学的认知研究在21世纪以来发展迅猛,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视角、范式甚或流派,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域。为进一步与国外学者交流相关研究成果,促进文学认知研究的健康、深入发展,认知诗学研究会与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将于2016年12月1日—3日在海口市联合主办“第五届认知诗学高层论坛”。本次论坛将主要围绕新兴的文学认知研究理论、方法和范式进行交流与探讨,并将邀请国外知名专家与会交流。
主题:认知诗学·认知文学研究:当前热点与探索
议题:1. 认知美学
2. 认知酷儿理论
3. 认知后殖民研究
4. 认知生态批评
5. 认知空间诗学
6. 多模态认知诗学
7. 实验认知诗学
8. 认知叙事学
本论坛也欢迎其他相关议题。
会议时间:2016年12月1日—3日。
报到时间:2016年12月1日全天。
报到地点:海南金色阳光温泉度假酒店(海口市滨海大道278号)。
会务费、资料费:900元/人,全日制研究生500元/人。
联系人:蒋勇军(四川外国语大学):13436038751,邮箱:13436038751@126.com
苏海文(海南师范大学):13975078478
论坛竭诚欢迎对认知诗学和认知文学研究感兴趣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与会交流。有意与会者,请登录认知诗学网站http:∥www.cognitive-poetics.com/cn,下载报名表,并在2016年9月15日之前将报名表和中英文摘要发至信箱:cognitivepoetics@163.com。论坛组委会将在10月15日之前寄出正式邀请函。因会期房源紧张,住房需提前预订,务请有意与会者及时报名,提交回执。
Two-way Evolution of the Cultural Memory Field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Japan
YAOJizhongSONGYuanyuan
The mechanism of Cultural Memory Field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remain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even though their mutual dependence has been well-established in the academia. This thesis tries to expound how the Cultural Memory Field in Japan operates in the inheritance of its culture and how the latter exerts its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former. Hopefully,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offer a new perspective and approach to Japanese cultural research.
culture; Cultural Memory Field; inheritance; two-way evolution
2016-03-26
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特别委托课题“文化记忆场研究”(2012TBWT05)的子项目“日本文化记忆场研究”的中期成果
姚继中,男,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东亚文化研究所教授,日本国立山口大学研究生院东亚文化研究科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日比较文化研究。
G04
A
1674-6414(2016)04-0021-06
宋媛媛,女,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日语教师,硕士,主要从事日本历史文化、日语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