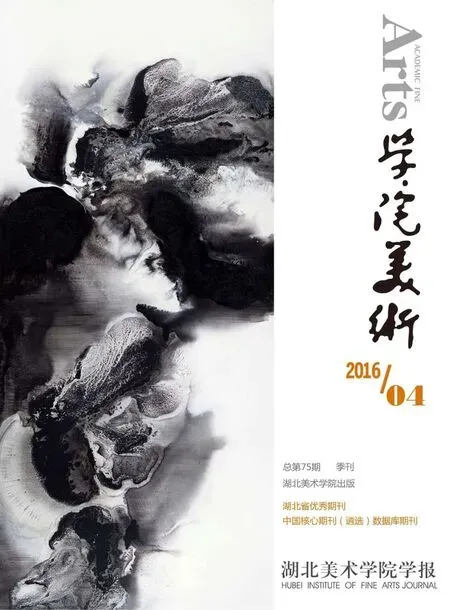毕加索作品中悲剧题材的分期研究及其美学价值
刘家慧
毕加索作品中悲剧题材的分期研究及其美学价值
刘家慧
本文以全新的视角,从绘画题材出发,另辟蹊径用悲剧的美学价值重新诠释了毕加索的整个艺术生涯,并结合当下的艺术生态进行深入思考。
毕加索;悲剧题材;美学价值
一、绪论
当下,艺术表面上一直处于一种激烈、持续的变化状态,在这场角逐中传统势力似乎日渐萎靡或者以一种伪装变形的状态在潜伏着,他们明面上有屈服于某些强硬的“革新家”的态势,然而,实质上许多自以为是的幻想家,仍在变着花样重复着上世纪那些真正的英雄重置的规则。例如:后印象派以高更为代表的回忆原始,追求表现生命本源和粗犷奇异的画风;以毕加索为领袖的立体主义完全抛弃传统的视觉经验,向着更主观的抽象艺术方向发展;波普艺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安迪·沃霍尔则打破了精英艺术和大众通俗文化的隔阂,促成了一种消费文明的生出。在这些英雄之中,巴勃罗·毕加索是一位毋庸置疑的影响深远的艺术家。
对于这样一位最负盛名的当代画家的生活和成就,相关的论述众说纷纭。但人们把大多数的笔墨都用来描绘他艺术生涯后期奇异的绘画规则和突破天际的想象力,而见微知著的研究所占比例显得有些单薄。以作品题材为出发点,绘画风格转变为研究阶段的分期,在此基础上做出的有关阐释似乎更加少之又少。因此,基于对悲剧美学的一些研究,本文选择毕加索作品中的悲剧题材为切入点,以其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为论据进行详细论述,探讨出其中的美学价值。
巴勃罗·毕加索1881年出生在西班牙马拉加,他虽是西班牙人,但在西班牙居住的时间,不到他的一生岁月的三分之一。1900年起毕加索一直往来于西班牙及巴黎之间,1904年定居巴黎,住在著名的“洗衣坊”。恶劣的生活条件而又受到德加、雅西尔与土鲁斯·劳特累克画风的影响,加上在西班牙受教育时染上的西班牙式的忧伤主义,这时期的作品弥漫着一片阴沉的蓝郁,被称为“蓝色时期”。1906年毕加索结识了马蒂斯,其后又认识了德兰和布拉克,与费尔南德·奥利维耶在蒙马特同住,其时他的经济已好转,生活要比以前愉快得多,画作用色变为轻快的粉红;绘画对象亦由蓝色时期的乞丐、瘦弱小孩和悲戚妇女转向街头艺人、杂耍艺人及风华正茂的妇女。1909年毕加索大部分的艺术家朋友都由蒙马特迁到蒙帕纳塞,他亦一起迁居至此,在此之前,毕加索从德兰的非洲面具中得到启发,开启其绘画创作的的“非洲时期”。他笔下的人体健硕而深沉,这种特征,在1907年的《亚威农的少女》中显露无遗。由不同组件组成的人体可从几个角度来观看,揭示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时期的来临。然而,整个时期仍有受塞尚影响的痕迹。1914年,战争使立体主义画家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毕加索则重拾自由与个人在色彩上的品味。无论从风格与绘画的对象上,他的“立体印象派”创作变得更加自由。大体上来看,多数艺术史学家赞同将毕加索的艺术生涯分为上述的蓝色时期、玫瑰红时期和立体主义时期。结合这个分期和本文研究的主题——悲剧题材,我们将其进一步分类为以毕加索青年时期写实绘画为主的早期;多表现生活在社会底层人民的蓝色时期,则被视为其悲剧题材发展的中期或者过渡时期;立体主义中以《格尔尼卡》为代表作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时期,是其悲剧题材创作的井喷期或称为鼎盛时期。

科学与博爱 布面油画 197cm×249.5cm 1897 毕加索
二、毕加索作品悲剧题材分期研究
1.青年时期
考虑到毕加索的父亲唐·霍塞从事的是绘画相关的工作,认识和接触的人从美术工艺学校的老师到当地美术馆的馆长,他的绘画启蒙对毕加索来说终生难忘。尽管唐·霍塞的绘画仍表现出明显的传统观念,风格也缺乏想象力,绘画题材也限于飞禽、走兽、鸽子和丁香等;但他继承了西班牙人热爱现实主义的习俗并乐于挑战一些拘谨保守人士会拒绝的实验。例如他曾购买过一个希腊女神的石膏像模型,以其为古典美的原型,创造了一尊“痛苦的圣母”形象的雕塑:在其面部写实性的勾勒,加上几滴金色眼泪,并用蘸了胶水的布包裹它的身躯。诸如此类的实验虽未取得实质性的成功,但都为毕加索的艺术生涯种下了叛逆的种子。并且,唐·霍塞作为父亲与儿子如此亲近的关系,对青年时期的毕加索更是起到了直接的引导作用。无论是在绘画技巧上的磨砺或是艺术生涯上的规划和选择,都有着无法磨灭的印记。
《科学与博爱》就是这样一幅作品,它在完成之初被称为“探望病人”,作为毕加索青年时期最重要的作品,其悲剧题材的选择应该是有意之举。那个时期的绘画题材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重要,所以唐·霍塞选择了能为儿子扬名的题材。为了密切地了解这幅画的绘制过程,他亲自做模特扮作医生坐在病人的床旁。画面中一个修女一只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正在给病人端水,病床旁的医生眉头紧锁地在为病人查看病情。整个画面构图严谨,绘画技巧娴熟,灰色和深黄色的基调渲染了整个画面情节的悲剧感。《科学与博爱》这幅作品完成后被送往马德里参加1897年全国美术展览会时赢得了不少赞扬,此后又送往马拉加,在那里获得了金质奖章。
从尺寸上来看,这是一幅非常大的作品,除了惊异于它出自如此年轻的画家之手外,在这样一个悲剧题材的表现上,毕加索的表现确实有异于常人的地方。此时的画家习惯于将这种题材安放于感伤压抑的氛围中,而毕加索所绘制的则是泰然自若和谨慎养病的情景,画面中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好像病痛从未打乱他们的生活节奏一般。虽然表现的是悲剧题材,但更像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暂停镜头,如此非仪式化的刻画让观赏者有种身临其境的奇妙感受。观者会被暂时带入这些角色去思考这样一个情景,无论是不幸患病的年轻母亲,还是博学的试图救治病人的医生,或者是内心在虔诚祈祷的修女,都会给我们一些深入思考的空间。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的写实,在那个习惯将绘画仪式化的年代,如此生活化的记录是不常见的。纵观年少时期毕加索的作品,这是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而在悲剧题材的表现上则成为了画龙点睛之笔。然而对于成年后的他来说,这样的表现则略显稚嫩,缺乏生活的阅历和磨练,悲剧题材的表现深度实为一般,画作虽然十分写实甚至生动但都停留在描绘一个悲剧场景上。人物形神的刻画,场景色调的选择都是为了还原一个浅显表面的悲剧题材。从宏观的整体艺术生涯上来看,毕加索青年时期的绘画风格又显得非常必要,经历了对形体的熟练塑造和整体构图的精准把握后,才慢慢过渡到对颜色的专注和某种偏爱时期——蓝色时期,形成了第一个个人风格突出的绘画时期。
2.过渡时期
毕加索天性爱好蓝色,曾经有好几年都一直把它选作调色板上的主色调,例如在1901年来到巴黎后的作品《蓝室》,从墙壁、浴盆、水壶、家具到窗外的阴影都是蓝色的,画面实质上表现了那时毕加索贫困潦倒的生活状态。大约在同一时期,他画了一幅在篇幅和内容上都很重要的作品——《招魂》,但在他的朋友中却以《卡萨吉玛的葬礼》而著称。画的主题是送殡这样一个悲剧题材,一群人低着头站在一个盖着寿衣横在前景的尸体周围,这些悲伤的送殡者和尸体在万里长空下显得很矮小;在具有迷幻色彩的烟雾中,一些神话人物漂浮着,当中是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是被一个裸体女人遮盖的黑影;周围还分布着三两群女人:母亲及其子女、两个紧紧相拥的女人和一群坐在云雾上的只有脚上穿着红蓝长袜的裸体女孩。这幅画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画面整体庄严肃穆超脱世俗的氛围与一些戏谑的类似于马戏团小丑和妓女形象的矛盾、支离破碎的构图和怪诞的故事情节。人物那种遮盖在外衣深蓝色褶皱里的拘泥和僵硬,加重了他们的悲伤程度,结合画面中种种不合理的因素,他们就像是幽禁在天堂和地狱之外被遗弃的幽灵一般。在这两幅画中,悲剧场景的写实刻画似乎已经不是重点,雕像一般的人物形象和忧郁的蓝色基调标志着他新风格的诞生。这两幅画最先反映出毕加索对雕塑形式的新发现和他本人象征主义的开始形成,标志着他青年时期画风的结束以及摆脱家庭影响的胜利。为了在绘画中摆脱从前父亲带给他的那些影响,在这个时期他似乎把悲剧题材作为一个反叛忤逆的武器,用深沉的蓝调,随性的构图并且揉合了新形式的人物风格,讲述了一些暗藏在绘画背后的个人遭遇。这样的悲剧题材表现十分具有感染力,就像一个导演的精心设计,用阴郁的背景音乐、支离破碎的片段和一些奇怪的大特写,引诱人走进早已准备好的寂静岭。

蓝室 布面油画 50.5cm×61.6cm毕加索

卡萨吉玛的葬礼 布面油画150.5cm×90.5cm 1901 毕加索

生活 布面油画 196.5cm×128.5cm毕加索
在1900年至1904年间,毕加索频繁地往返于巴塞罗那与巴黎之间,据说原因在于他的心情一直无法安定下来,到了1904年春,他在巴塞罗那呆了一年多,画出了一些最令人钦佩的作品。在主题和色彩方面别具一格的许多作品中,有一幅又大又特别的画——《生活》。就某些方面来看,这算是他那时间最有抱负的一幅作品,这幅画的篇幅相当可观,构图煞费苦心,并且在可阐释的层面上有一种同《招魂》一样的象征主义。画面中一个裸体女人把身体贴近一个男子,与之相称的是一个怀抱小孩穿着衣服的妇女,但男子暧昧地用手指着她;人物之间的背景上树立着两幅裸体习作,习作上的人都缩成一团,神情十分痛苦,似乎要给画面添上痛苦的象征。从三个主题人物的严肃姿态表明,毕加索想要通过画面探索两性的爱情与现实婚姻生活的矛盾;在背景上增加人物的做法,似乎在揭示一段感情从幸福到不幸的过程,这些都处处显示出画家的思索和有意探索一个错综复杂的主题。背景中拼贴的习作里人物蜷缩的痛苦姿态,为画面增添了一些负面的情绪,演变成一个有关于爱情和婚姻悲剧的载体。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这时候毕加索表现的悲剧题材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更像是一段深奥的哲学迷思,与初稿对比发现这幅画在完成时进行了不少改动,也从侧面证明了创作过程中画家对于悲剧问题的产生、发展与结果的思考,而创作的过程也帮助他思考并呈现了整个过程。此时,悲剧题材在毕加索的作品中,已经从最初的写实主义情境还原到画家个人情绪的宣泄,并发展到用象征手法再现普罗大众所经历的痛苦和纠缠。
除此之外,在蓝色时期,盲人这一形象一直像影子一样追随着毕加索。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令人费解的话:“事实上只有爱最重要,不管是怎样的爱,人们为了使金翅雀唱起歌来更动听,便把他们的眼睛弄瞎,对画家也不妨这么做。”也许是为了更加强烈地表现和更深刻地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一个完全靠眼睛过活的画家,居然会想到盲目的好处。更现实的原因是,在巴萨罗那,毕加索在每个街头都可以找到供他描绘的盲人模特,因此他创作了许多十分动人的悲剧盲人形象。在《盲人用膳》这幅画中,一个盲人正在用右手摸索着装着汤的罐子,相对于人物面部简单的勾勒,画家对这只漫无目的摸索的右手进行了精心刻画;他的另一只手则简单的捏着食物;人物面部凹陷,并未有过多的表情;蓝色深邃的背景空无一人,表现出盲人孤独无助的生活现状。画面构图简单,主题明确,与之前创作的《招魂》和《生活》表达复杂的主题和晦涩的象征主义形成鲜明对比,更像是一个悲剧的旁观者做的一个善举:简单的记录下一位盲人用膳的画面。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在蓝色时期这一短暂的几年时间内,毕加索对于悲剧题材的探索也从未停止,并处于一个过渡和变化阶段。具有象征意味的人物形象和不稳定的画面结构,以及平稳的刻画盲人等群体的创作都为他在悲剧题材上登峰造极的表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盲人用膳 毕加索 95.3cm×94.6cm 1903 布面油画

格尔尼卡 布面油画 349.3cm×776.6cm 1937 毕加索
3.鼎盛时期
1937年4月,在巴黎的毕加索听闻德国轰炸机把小小的古镇格尔尼卡炸毁。伴随西班牙多年内战下的郁结情绪,这场全世界法西斯战争下的暴行,对毕加索义愤填膺的心情起到了催化作用,《格尔尼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
画的中央是一匹重伤将死的马,右边一条腿已经跪下,极度痛苦地仰天长啸,舌头在紧张的情绪下化为一把利剑,眼睛化成两个圆圆的圈;马身马腿都布满了报纸般密密麻麻斑斑点点的小字。马的身下是一个身体被炸碎的士兵雕像,仰面朝天,一只手径直伸向前,另一只残臂正挥舞着断剑。受伤的一朵小花是唯一寓意美好的事物。马头的上方是一只眼睛,闪烁着尖锐的光芒,寒气逼人。原本初稿中这是一个太阳,毕加索在完稿时加进了一只灯泡变做了瞳孔。画中最动人的是那四个女人,她们的姿势和表情都表示出惊慌、恐惧和极度的忧伤痛苦,这些显然是得力于毕加索在人物外形的变形描绘上的长期经验。从着了火的房子里跳下的女人,向上伸出双臂和脖子,令人信服地表达出她所处的绝境的真实性;她那位在下面的同伴,害怕来自天上的危险,惊慌失措地半裸着身体从屋里跑出来,她的双脚生动有力地说明她多么需要依附大地;在她们中间还有一个从窗中探出头来的女性头部,她的身体淹没在窗内的黑暗中,面对眼前的灾难,她张大嘴巴似乎想要求救,或者只是被眼前的一切震撼得目瞪口呆;画面的最左边,依偎在一具死去的尸体旁的是最后一个女性形象,她跪在牛头前,脸朝着天上投下炸弹的方向,张着大嘴痛苦地嚎叫着,她的眼睛离开正常的位置在脸颊上形成眼泪的形状,欲哭无泪。将《格尔尼卡》与其他悲剧题材的伟大作品相比较,例如席里柯的《梅杜莎之筏》,构图上的相似性显而易见。两者均使用了三角形构图,在视觉上使人产生刺痛感和尖锐感,画满中底部的封闭和左右两边明显的界限,都营造出一种紧张压抑的气氛。从不朽的魅力这一层面上看,画家都使用了那个时代的表现手法描绘出已经真实发生的悲剧。
然而不同的是,毕加索在《格尔尼卡》中找到了一个普遍的方法,传达以战争这一悲剧事件为中心的情绪,塑造出一个永久的、超越的形象。“立体主义的发现,新古典主义时期线条的纯正,以及后来的裸体画不受拘束的描绘,都合而为一,这给毕加索以力量,使他在这一年的夏天创造出这件表达幻灭、失望与破坏的不朽之作”,这是他所在的年代给出的最精准的评论。画面中这些人物和头部包含的悲伤所引起的解体,几乎无可比拟,面部的每样特征都惊人地随意处理:两个鼻孔,一对眼睛和两只耳朵都压缩在同一侧面,这就可以不丧失这些部分的表达力;但令人俯首称赞的不只是变形描绘,而是一个事实——观众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的象征意图,而且心悦诚服地承认他所描绘的悲剧的真实性。这种悲剧情感传递的普遍性一部分来自于画面的单纯朴素,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其本质精神表现上的矛盾。《格尔尼卡》在绘画上的单纯朴素使之成为一幅容易理解的画,人物外形上没有多余的会使人产生混淆的复杂之处,从着火的房子上的火焰和跳下的女人衣服上的火苗都是用和原始艺术同样的不致误解的图像。那只钉上铁钉的马蹄,那只皱纹很深的手掌,那轮如眼睛般的太阳,都是用一种近乎孩童般稚嫩朴实的手法画出来的。这种手法是几世纪以来由于艺术技巧的不断精炼而丧失埋没的。毕加索证明,在表现这种极度悲剧的题材时那种巧夺天工的美点是不必要的,甚至对于理解灾难的现实和残酷有所阻碍。在更深层次来看,这种准确地传达出近乎于歇斯底里甚至疯狂的悲剧画面的,是其所要传达的两种内在本质的精神抗衡所致:尼采在其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反复论证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日神精神的美感是把生命力的丰盈投射到事物上的结果,酒神精神的悲剧快感更是强大的生命力敢于与痛苦与灾难想抗衡的一种胜利感。画面中无处不在的痛哭嚎叫、扭曲变形的人们,从侧面反映出生命存在的丰盈和情感的饱满,甚至是情感的悲伤;而另一方面举着火炬的手、残臂上的小花和马嘴中伸出代表反抗的利剑又在书写着另一种伟大——来自敢于与悲剧抗衡的某种希望和胜利。至此,无论是从绘画的造型或者毕加索寓意于战争带来的这一悲剧中的精神,《格尔尼卡》这幅画的成功无不彰显着,在悲剧题材的表现上他已经到达了其艺术生涯的顶峰。

梅杜莎之筏 布面油画 491Ncm×716cm 1819 席里科
三、结语
悲剧题材作为一种艺术的载体,原本是中立空白的性质,但在表现艺术家个性和风格时,又显示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力量。对于当代艺术来说,艺术的形式革命纵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显得无比重要,但在今天,线条的横竖、拉伸、重复,色彩的解读或者两者的组合,似乎变成了一种套路或者捷径,远远脱离了艺术的本源。严苛地阅读中国的当代艺术历程,几十年的时间甚至称之不了为历史,因为我们的创作相对于这个多样化和信息爆炸的时代太过于单一了,政治波普风靡一时后所谓的抽象艺术填满了大大小小的画廊和我们的视线,然而真正理解当代艺术中的抽象这个词和它所代表的一种精神传承和沉淀的艺术家少之又少。也许这篇文章的研究,就是意在为渐渐消失的某种意义上的写实形式的呐喊。
毕加索作为形式主义革命的开山鼻祖之一,身体力行地做出了榜样。绘画作品在强调某种自我风格和标志性的形式时,如果与其所承载的内容完美融合,将会是一举两得的美事。纵观毕加索的整个艺术生涯,他的创作表面或者背后总是蕴藏着痛苦或者某些压抑的情绪,形成了一些神秘的吸引力,这就是悲剧美学的一大显著特征。整篇论文围绕着悲剧题材这个载体展开,毕加索则是连接全文悲剧题材的美学价值和其内在规律的显性因素,通过对他各个阶段创作的深入探讨,总结并印证了一些规律:1.悲剧题材在写实主义的绘画中对于细节的凸显和形象的感染力塑造优于其他题材。2.在绘画出现象征主义弱化写实性时,主题深度的把握在悲剧题材中得以更好实现。3.当主题内容、象征主义和创作形式逐渐成熟时,悲剧题材或者是现实中的灾难情感对于促成具有批判性的杰作有辅助作用。简单来说,相对于表现喜剧的创作,直面悲剧的艺术也许更能让人产生情感上的波动。
因此,本文的研究是基于简单的对当代艺术的伟人毕加索的尊敬以及对悲剧美学的热爱,但同时也希望有一些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在发展方向上的倡导。真诚地放下虚伪和狂躁,追求艺术创作的初心是解救无数迷茫画家的良药,对于仍在发展中的中国来说,贫富差距大、人民整体素质不高和潜在的精神文明缺少等都是时时刻刻在发生的悲剧,或许这些鄙陋带给我们的思考就是悲剧美学带给我们最原始却又最有效的灵感之源。
刘家慧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
[1]雷纳尔.毕加索评传[J].劳诚烈,译.美术译丛,1981,(3):23.
[2]毕加索语录点滴[J].丁拙,译,美术译丛,1981,(3):35.
[3]潘罗思.毕加索传[M].周国珍,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4]董冰峰.与格尔尼卡的距离[J].当代艺术与投资,2011,(3):4.
[5]高木,毕加索.与沃泽的谈话[J].世界美术,1981,(1):21-23.
[6]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7]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4.
J205
A
1009-4016(2016)04-002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