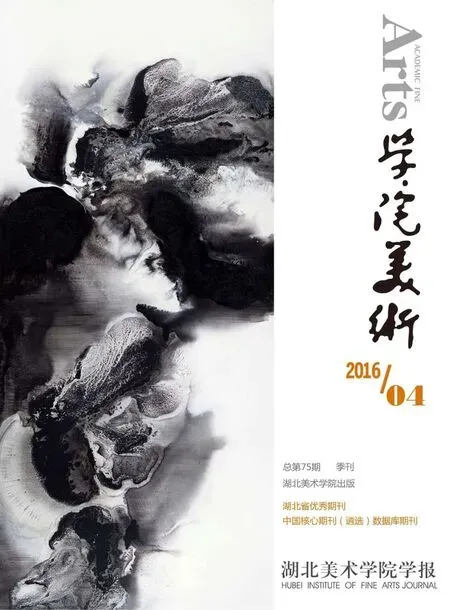图像学视角下莫高窟龙车凤辇图式形成研究
于奇赫
图像学视角下莫高窟龙车凤辇图式形成研究
于奇赫
敦煌莫高窟隋代石窟中出现许多被学界名为“龙车凤辇”的图像。许多学者偏重于讨论图像所代表的宗教含义,而没有对其形成做探讨。本文从图像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比《洛神赋图》、麦积山127号石窟与敦煌北朝、隋朝莫高窟中的龙车图式,就龙车图像到龙车凤辇图像的组合进行分析,描绘隋代龙车凤辇图式形象演变的过程。龙车图式在魏晋时期从中国南部向西北部逐渐传播,最终形成了龙车凤辇的图式。莫高窟隋代龙车凤辇图式的形成吸收了中国本土的道教升仙的思想,受到佛教思想的改造后流传于佛教的石窟寺中。
龙车凤辇;敦煌;麦积山;洛神赋图;佛教思想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有一类名为“龙车凤辇图”的图像,其画面往往表现一男子御龙车出行、一女子乘凤辇出行,四周飞天与神兽环绕的场面。现存最早的莫高窟“龙车凤辇图”出现在于西魏第249窟窟顶上,并且目前的研究都集中在第249窟“天井图”的图像上,探讨乘坐“龙车凤辇图”的人物形象的身份与宗教意义。对于其“龙车凤辇图”的研究,学者们也注意到了麦积山石窟中同样的壁画内容与顾恺之《洛神赋图》的形象类似,但是基于图像学角度而对于这类图式的形成与流变的研究还比较少。田中知佐子目前是对龙车凤辇图式的意义与源流梳理得较为清晰的一位学者,但是其《敦煌莫高窟“龙车凤辇图”源考》一文谈及“龙车凤辇图”时“特别与龙车图有直接关系的当属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中洛神乘御的六龙云车。关于此图与莫高窟龙车图部分的制作是否有相似之处,目前,因为还没有对图像学方面作充分的比较研究,所以不能妄加评论”[1]。并且由于古汉语文法的问题,田中知佐子对于部分图像产生了误读。只是以“龙车”和“凤辇”单体为研究对象,而对于图像本身的含义理解产生了偏颇。
现存敦煌莫高窟中可以辨识的“龙车凤辇图”一共有16幅8组,分布在8个洞窟之中,且位置不同。其中北朝时期的石窟是第249窟、第296窟和第294窟,而隋代的石窟则占了大多数,有五个窟,分别是第305窟、第401窟、第417窟、第419窟和第423窟。[2]从洞窟序列上和图式、风格来说,隋代敦煌莫高窟龙车凤辇图式无疑受到北朝时期敦煌莫高窟龙车凤辇图式的影响。与“龙车凤辇图”相似的图像还出现在麦积山127号石窟与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中,我们要探寻这四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要详细地对这些图像进行比较与梳理,才能找到敦煌莫高窟龙车凤辇图式的形成轨迹。
一、《洛神赋图》与麦积山127石号窟、敦煌北朝石窟云车图像的比较
我们习惯上把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直接与敦煌石窟中的“龙车凤辇图”进行对比,并且似乎找到了一些相似之处。这两种图像缺失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是从整体画面的构图上来说,并不存在直接关系。首先,敦煌石窟中的“龙车凤辇图”都是成对出现的,而《洛神赋图》只出现了一辆云车;其次,《洛神赋图》中有一辆世俗的马车,而敦煌石窟中的“龙车凤辇图”中没有出现;最后,《洛神赋图》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敦煌石窟中的“龙车凤辇图”只是作为一个单体形象出现在壁画中的。所以说,将二者直接比较显然不妥。
《洛神赋图》是根据三国时期曹魏文学家曹植创作的《洛神赋》绘制而成的。《文选》注:洛神又名宓妃,是伏羲的女儿,溺死在洛水后成为洛神。其原形为袁绍的儿媳甄氏,因曹植追求未果后嫁与曹丕,后来被皇后郭氏谗死,当曹丕把甄氏的玉镂金带给曹植看的时候,曹植痛苦不已并写下《洛神赋》[3]269。《洛神赋》后来成为东晋流行的书画题材,像东晋明帝司马绍就画过《洛神赋图》①见于唐代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和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的记载.,但已失传。现在存世的《洛神赋图》大都传为顾恺之或是陆探微所做,据林树中先生统计,共有七个版本②它们分别是一、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卷;二、辽宁省博物馆藏卷;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高卷,主要为宋人画,缺六朝气息;四、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名绘集珍册》中有一开名为”顾长康《洛神图》五、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传顾恺之画卷;六、弗利尔美术馆藏传陆探微画卷;七、伦敦英国博物馆藏宋人画卷,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高卷略同。参考林树中:《传为陆探微作<洛神赋图>弗利尔馆藏卷的探讨[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01(3):113-117.,大多被认为是宋代摹本。邵彦先生根据对比1960年南京丹阳南朝宋齐时代大墓中出土的拼镶砖画《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和1965年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屏风漆画《列女图》,得出《洛神赋图》的底本确实出于从顾恺之到南朝齐梁时代(4世纪后半期到6世纪前半期)的结论。[4]这就说明了《洛神赋》的确是当时流行的一个绘画主题。
《洛神赋图》中的云车图像是画者根据曹植《洛神赋》中“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3]271一句绘制的(图1),所以后世根据文献将这一图像定名为云车。田中知佐子在分析“龙车凤辇图”时说到“车驾两侧的二条类似鱼的巨大神兽应该是鲸鲵吧”,并且还注:“《洛神赋图卷》中云东下方绘制的带斑点的形似鳗鱼的怪物有可能表示的就是文鱼的形象。”这一分析有着明显的疏漏。古代鲸和鲵时常作为一个词组在唐代以后诗文中大量出现,像李白“君去沧江望澄碧,鲸鲵唐突留馀迹”[5],白居易“疑是斩鲸鲵,不然刺蛟虬[6]”。但鲸和鲵应该是两种动物,并不能混为一谈。“鲸”是古代诗文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但不是现在生活在海洋中的鲸鱼,而是一种带有鳞片的大鱼。《尔雅》记:“鲵,大者谓之鰕。”郭璞注:“今鲵鱼似鲇,四脚,前似猕猴,後似狗。声如小儿啼,大者长八九尺。”[7]《说文解字魚部》:“鮎,鰋也。”[8]鲵鱼俗称娃娃鱼,体长可达一米左右,口大,四肢短小,叫声如幼儿。所以“鲸”体型较大,韩愈在《鳄鱼文》说“鲸鹏之大,虾蟹之细”[9],而鲵体型较小,并且二者在云车的位置是“夹毂”,即出现在车轮附近。所以,体型较大、带鳞片的鱼就是“鲸”,像鲶鱼一样细长的就是“鲵”。

图1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洛神赋图》局部(1)
《洛神赋》关于描写云车:“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3]271画面右上方到画面左边依次出现了飞上天空张口吞云的雨师“屏翳”、手持竹制鱼竿站在河里的“川后”、飞上半空的洛神、正在击打鼓的“冯夷”四个男子站在树下、乘坐“玉鸾”的洛神和六龙拉云车的画面,并没有出现“腾文鱼以警乘”的形象,也没有出现“水禽翔而为卫”的形象。由于“赋”这种文体从声韵上与辞藻上的要求,所以诗人是这样描写洛神的护卫的。而对于画家来看,“文鱼”与“水禽”的作用都是护卫洛神的云车,从构图与画面的要求来说,用三只独角四爪的神兽形象就可以进行概括了,也达到了诗人所体现的一种意境。所以关于这个神兽的形象,辽宁省博物馆藏本(图2)与故宫博物院藏本(图3)是有出入的,但大体上都是基于一种动物的变形。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云车的标准图式应该为牵引车驾的神兽、带有华盖旌旗翅羽的北朝式车、两侧车轮处的鲸鲵和车驾周围的护卫四个要素。
但是传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中的云车图像与麦积山127号石窟的云车图像有着高度的相似点:第一,这两组图像在整体的画面中同时出现了世俗的马车和神仙的云车形象,并且处于一个连续的叙事性故事中。壁画内容一说是萨埵太子本生故事[10],但根据项一峰考证,麦积山127号石窟中的壁画内容是根据《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绘制的经变画[11]。世俗车是当国王得知栴檀摩提太子出事后,赶赴出事的现场所乘坐的交通工具。虽然这辆车的形象缺失了牵引车辆的动物,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车身的构造:车子整体较高,车毂较大,车辐的数量多,车毂中的彗和辖隐约可见,并且车上还有两层装饰华丽的车盖,车尾还挂有条带状旌旗,所以这辆车子应该是这一时期等级最高的车子。
第二,根据画面所反应的故事内容来看,这两组图像中乘坐世俗马车的人物和乘坐神仙云车的人物并不是同一个人,所以不存在乘车直接从世俗升天的寓意。《洛神赋图》中乘坐云车的是洛神及仙女,乘坐马车的是曹植及仆人。在麦积山127号石窟壁画中乘坐云车的是仙人,世俗车上虽然没有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国王准备上车的场景。关于乘坐云车的人物形象至今存在争议,根据《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云:“如是我闻,一时佛游乾陀越国毗沙门波罗大城,于城北山岩荫下,为国王臣民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说法教化度人无数。”[12]所以该人物形象应该是天人中等级较高并且能够说法的人。
第三,这两组云车图像中世俗的车与神仙车的结构、装饰都较为一致,并且《洛神赋图》与麦积山127号窟的云车结构一致。虽然麦积山石窟壁画的保存状况不好,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有牵引车驾的神兽、带有华盖旌旗翅羽的北朝式车、两侧车轮处的鲸鲵和车驾周围的护卫四个要素。所以麦积山石窟127号窟的云车图像的绘制受到了传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中图式的影响。
莫高窟北朝石窟的龙车凤辇图像和麦积山127号石窟中的云车图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开凿于西魏时期的第249窟为例,窟顶上绘有一神人乘坐在由三只凤鸟牵引的车子上,凤车上有双层垂盖,杆头上还挂有飘扬的彩幡,车尾处斜插着一面飘动的条带状旌旗,和麦积山127窟内的云车图像一致。但是不同的是,第249窟凤辇的车轮部分的“鲸”的形象变成一条带有翅膀的鱼,并且鱼的背和腹鳍的特征消失了,鱼尾也被抽象化了,似乎变成了《洛神赋》中所记载的“文鱼”形象。“鲵”的形象较麦积山127窟于《洛神赋图》中的形象相比,下部多出了两条腿,并且向夔龙的形象变化,整体变得修长。第296窟北周石窟很可能是根据第249窟的图像绘制而成的。但是从构图和比例来看,第296窟的鱼车图式中车的体积和透视过大、整体画面没有第249窟表现得轻盈、协调,对于动物的描绘也稍显羸弱与刻板,车体的翅膀也略去了,可见北周时期画匠的绘画水平不及北魏时期。

图2 辽宁省博物院藏《洛神赋图》局部

图3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洛神赋图》局部(2)

图4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洛神赋图》局部(3)

图5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洛神赋图》局部(4)

图6 麦积山127号窟云车图像
龙车凤辇图式在敦煌北朝石窟壁画中正式形成。首先,麦积山127号石窟壁画中是一辆云车,但是到了敦煌北朝石窟壁画中,出现了由凤鸟牵引的车,并且与龙拉的车成对出现。车上的人物形象至今存在争议,但是可以确定是一位男性和女性的形象,这以后在隋代成为石窟壁画的一个固定题材。龙车凤辇图式在北周时期画面缩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图像的轮廓线,并且四周的飞天形象减少,逐渐成为一种程式化的装饰图案,其宗教意义的内涵被完全剥离,被重构入佛教石窟的画面中,并赋予新的含义。
最后,在敦煌的的石窟中,《洛神赋图》与麦积山127号石窟壁画中的世俗的马车消失了,所以龙车凤辇图式只是作为一个单体图像,并不存在于一个完整的叙事性的画面中。但是由于其图像主题的车形象来源于世俗的马车,所以本身具有一种叙事性功能,很容易在画匠的改造后被置于新的画面,在新的佛教的语境中进行叙事性的表达。并且,敦煌石窟中的龙车凤辇图式往往处于一个繁复的天空图中(图9),其图像最原始的道教升仙思想在佛教石窟中被无限放大,完全脱离了世俗的世界。所以造成了目前对于这组图像是东王公和西王母、帝释天帝和释天妃还是“上士登仙图”的争论。

图7 麦积山127号窟壁画局部

图8 敦煌莫高窟249窟窟顶(1)

图9 敦煌莫高窟249窟窟顶(2)
二、敦煌莫高窟龙车凤辇图式的形成、传播路线与宗教含义
隋代敦煌莫高窟龙车凤辇图式较《洛神赋图》和麦积山石窟壁画和敦煌莫高窟西魏、北周时期的云车图式与龙车凤辇图式,车的体量大,车尾处的旌旗十分华丽,四周的飞天形象变化丰富。通过上述对比公元4世纪左右的《洛神赋图》、麦积山127号石窟和敦煌北朝和隋代的诸多石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公元4世纪左右的《洛神赋图》的粉本先流传到了麦积山石窟寺地区,之后麦积山石窟寺的龙车图式传入敦煌地区。从时间上看,《洛神赋》流行于公元4世纪至6世纪。虽然目前学术界对麦积山127号窟的创建年代还存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开凿年代在北魏末期,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在西魏开凿的③关于第127窟的时代问题,董玉祥、李西民、魏文斌、项一峰和东山健吾等学者与国家文物局教育处编《佛教石窟考古概论》一书认为开凿于北魏时期;金维诺、郑炳林、沙武田等学者认为开凿于西魏.。但不论是北魏还是西魏,都属于公元6世纪左右的北朝时代,这一点毋庸置疑。敦煌石窟最早的西魏龙车凤辇图式位于第249窟窟顶上。从空间上看,画史中关于《洛神赋图》作者的记载,活动范围都在江南地区。《洛神赋图》最初流行在中国南部,随着南北朝之间文化的交流与战争,向北地传入长安地区,后向西传入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后向西北最终传到敦煌地区。日本吉村怜认为南朝在思想、学术、文化方面要比北朝先进[13]147,并且他认为天人诞生图像“看来在敦煌从‘北魏-西魏-北周-隋’流行了很长时间,到唐初才消失了踪影”[13]157。这条图线与本文基于图像学视角下的比较研究结论一致,所以从南朝传入北朝的图式不止这些,在北朝的佛教图像系统中还能找到很多南朝图像的影子。
从最终隋代敦煌莫高窟龙车凤辇图式的形成还可以看出:首先,龙车凤辇图式由魏晋时期初创的写实逐渐走向隋唐时期的写意。美国佛利尔美术馆传藏陆探微的《洛神赋图》图式画面描绘得十分真实生动,并且注重装饰与细节的绘制,这应该是接近六朝时期陆探微的笔意的。由于受到绘画材料的限制,卷画轴的材料大多是由纸或者是绢制成,面积较小,便于细致地绘画;而壁画立面相对粗糙、面积较大,不适宜过于精细地描绘。所以隋代至唐代壁画与墓室壁画的绘制,则追求一种流畅、大气的写意精神,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车子还是人,造型简练准确、线条流畅飘逸,丝毫没有拘谨的感觉。这背后其实也寓意六朝时期与隋唐时期时代的精神气息的一种转变。这可能是一种地域文化的影响,亦或是族属的不同,南朝人的精致细腻明显不同于北方的粗犷豪迈。所以从莫高窟龙车凤辇图式的形成过程中能看到中国绘画气韵发生的转变。

图10 莫高窟296窟凤辇图像

图11 莫高窟296窟龙车图像
其次,隋代敦煌莫高窟龙车凤辇图式的形成是在继承汉魏以来中国传统的神仙思想基础上,吸收外来佛教艺术的形式和表现技法,最终形成一种新图式,充分显示了佛教思想和佛教艺术的包容性。曹植的《洛神赋》本身就描绘了一种充满道教色彩和神仙意蕴的故事,所以才会有传为顾恺之等人绘制的《洛神赋图》。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而云车形象体现的是一种升仙思想。云车中的鱼形象在西汉时期的墓葬中已经是十分常见的升仙题材[14]。后来随着佛教的传入,这种云车图被画匠提取出来,纳入到了佛教石窟寺的壁画中。佛教对于本土的神仙思想,不是一种简单地吸收,而是一种改造。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本土化,并且借助佛教的思想将中国的神仙体系与佛教的神仙体系建立一种对应关系,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佛教的思想体系。从东汉开始,佛教与统治者、本土的宗教观念经过了数次礼佛与废佛、排斥与融合,最终在石窟壁画中以一种佛道融合的画面呈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两种因素不断地重构并且被置于不同的语境中,说明当时的宗教思想相互之间也在发生着碰撞。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龙车凤辇图式的一种从东南到西北的线性传播方式,这也仅反映出中原文化的一种吸引力、改造力与生命力。龙车凤辇图式的原型来源于世俗的物质文化,并被赋予了不同的宗教含义。从魏晋时期图像的诞生及流行开始,延续到隋唐,至宋代仍有大量的摹本,这一时期中国发生多次政权分裂与统一,政治中心不断地转移。依附于本土升仙思想的龙车凤辇图式被以礼佛崇佛为主的中原文化所吸收,传播到西北的石窟寺中,这一主题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以《洛神赋》为代表的六朝志怪题材,对以唐传奇和宋代神怪故事为题材的绘画创作提供了素材,其图像本身终发挥着叙事的功能,并对后期的文本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龙车凤辇图虽然在唐以后消失不见了,但是在明清时期山西寺观壁画与一些佛经版画、《太上老君八十一化图说》中还能看到龙车的影子,但是凤辇已经较少看见,这又与后期三教合一的深化是分不开的。
于奇赫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
[1]田中知佐子.敦煌莫高窟“龙车凤辇图”源考[J].敦煌学辑刊,2009,(2):100-120.
[2]中国敦煌石窟壁画全集编委会.中国敦煌石窟壁画全集[M].天津美术出版社,2006.
[3]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邵彦.《洛神赋图》是顾恺之画的吗[J].紫禁城,2005:70.
[5]李白.赤壁歌送别[M]//王琦.李白全集.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417.
[6]白居易.折剑头[M]//朱金城,朱易安.白居易诗集导读.四川:巴蜀书社,1988:127.
[7]郭璞.尔雅[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7.
[8]许慎.说文解字[M].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91:244.
[9]韩愈.韩愈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0:386.
[10]甘肃省文物考古所.中国敦煌壁画全集11:敦煌麦积山 炳灵寺[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13.
[11]项一峰.麦积山石窟第127窟造像壁画思想研究[J].敦煌学辑刊,2015,(1):99.
[12]王煜.也论汉代壁画和画像中的鱼车出行[J].四川文物,2010,(6):51-56.
[13]吉村怜.天人诞生图研究:东亚佛教美术史论文集[M].卞立强,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4]法盛.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M].大正藏3卷:172.
G209
A
1009-4016(2016)04-003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