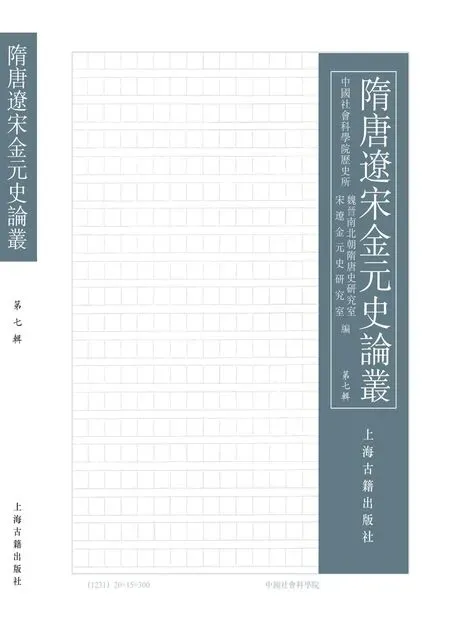中古墓誌研究三題
陳 爽
層出不窮的墓誌史料極大地拓展了中古歷史研究的空間,也直接引領了研究的潮流,短短十餘年間,墓誌研究已從較爲邊緣的專門之學發展爲學人競相預流的犖犖顯學。本文僅就中古墓誌研究中具體操作層面的幾個實際問題略陳管見,希望引起學界的重視。
一、 強化問題意識
新出墓誌的數量雖呈井噴之勢,令學人應接不暇,但墓誌研究繁榮的背後存在著歧路亡羊的“碎片化”隱憂。一些學者盲目地跟風追新,“使得很多新出石刻的學術價值尚未被充分挖掘,便已成爲少人關注的舊史料”*仇鹿鳴《中古石刻研究如何超越傳統金石學》,《澎湃新聞》2015年4月17日。。墓誌數量的增長並未改變墓誌的史料屬性,我們對墓誌在中古史料學中的定位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出土墓誌數量雖然巨大,並不能改變和取代傳世史傳中完整而系統的既有史實框架。
一般説來,墓誌所提供的史料信息都是支離零散的,在此基礎上進行的考訂就存在很大的隨意性,儘管學者們努力拓展視野,力圖以小見大,但主要方法是將墓誌文獻與傳世系統的文獻比對,以證史、補史爲主要解決方案。十年前,陸揚教授曾呼籲墓誌研究應“從内容和方法比較單一的史料考證走向對墓誌的内涵作全面的史學分析”,引起了學人的普遍共鳴*陸揚《從墓誌的史料分析走向墓誌的史學分析——以〈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爲中心》,《中華文史論叢》2006 年第4 輯,95—127頁。。
關於石刻史料的綜合性研究,前輩學者曾經做了很多開拓性嘗試,馬長壽先生在半個多世紀前完成的《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一書*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中華書局,1985年。,通過文獻與碑銘相互印證,梳理了前秦至隋初兩百年間關中少數部族的歷史變遷,堪稱石刻研究的經典之作,也爲墓誌研究做出了垂範。其宏大的視野和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學界至今難以企及*詳參羅丰《關中胡人: 馬長壽和他的〈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西北民族論叢》第六輯,2008年,119—132頁。。
近年來,給我個人印象較深的一篇墓誌研究論文,是青年學者仇鹿鳴所撰《“攀附先世”與“僞冒士籍” ——以渤海高氏爲中心的研究》*仇鹿鳴《“攀附先世”與“僞冒士籍” ——以渤海高氏爲中心的研究》,《歷史研究》2008年第2期,60—74頁。。文章没有以墓誌作爲標題,“墓誌”甚至没有出現在提要和關鍵詞中,但卻是一篇質量上佳的墓誌研究作品。作者借鑒“古史辨”學説,提出“攀附先世——士族譜系的縱向延伸”和“僞冒士籍: 士族譜系的横向疊加”這樣兩個重要概念。在具體研究中,作者結合史傳記載,選取了從北魏到隋唐數十方渤海高氏墓誌進行對比和考察,發現“透過《新表》(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與相關墓誌的記載,高氏先祖的活動似乎清晰可見,魏收尚不明了之事,到了數百年之後的唐人那裏卻完全不成爲問題,不僅是姓名,連字號、官位、事蹟都瞭解得一清二楚。可見時代愈後,士族祖先的事蹟也就越詳細”。通過多方墓誌的對比考察,揭示出“渤海高氏本非漢晉舊族,但是通過攀附陳留高氏和齊國高氏,成功地將其家族先世追溯到春秋時期。隨著渤海高氏郡望的形成,高崇、高肇、高熲、高歡等房支紛紛通過各種手段冒姓渤海高氏,這些冒入的高氏在唐代構成了渤海高氏譜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墓誌史料對於中古研究一個最爲直接的推進就是促成了士族個案研究的繁榮,但一段時期内,個案研究卻成爲令人乏味的跑馬佔圈運動,多數學者對於相關墓誌的利用無外是辨證世系、考證仕履、考察婚姻、闡述家學等,重新陷入了以婚宦論士族的窠臼。這篇文章的新意在於把墓誌中記述的譜系提升到“僞冒”與“攀附”的大視野下展開研究,在這個視角下,每方墓誌中的世系記述,就不再是一個簡單非此即彼的正誤問題,而是探究譜系作僞的具體過程和主觀意圖,以墓誌爲坐標,渤海高氏冒入之跡斑斑可見,其對祖先譜系的構建過程也昭然若揭。文章開闢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形成了一種新的研究理路。在這一思路的影響啓發下,近年來,學界對太原王氏、弘農楊氏、南陽張氏譜系塑造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范兆飛《中古郡望的成立與崩潰——以太原王氏的譜系塑造爲中心》,《廈門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28—38頁;尹波濤《北魏時期楊播家族建構祖先譜系過程初探——以墓誌爲中心》,《中國史研究》2013年第4期,101—116頁;仇鹿鳴《製作郡望: 中古南陽張氏的形成》,《歷史研究》2016年第3期,21—39頁。。
優秀的史學研究要求作者具有敏鋭的問題意識,克服“以誌證史”的思維局限,使墓誌本身成爲史學分析的對象,需要我們對其墓誌的文本内容及其藴涵的時代特徵有細膩而周全的把握。就墓誌研究而言,一些重大問題與重要思路或靈感往往不是來自具體的墓誌本身,而是來自傳世文獻的知識積累,源於作者對某一問題的長期思考。馬長壽在《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之前,剛剛撰寫完成了《氐與羌》《鮮卑與烏桓》等著述,而仇鹿鳴則在發表《渤海高氏》一文之前,剛剛完成了士族研究的博士論文《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
提倡綜合研究,強調問題意識,並無貶低文字釋讀和史事考證之意,畢竟這些工作是墓誌研究的基礎和出發點所在。在此需要強調的是,作爲中古時期“新史料”最爲重要的載體之一,出土墓誌文獻中無疑藴涵著大量全新的歷史問題,但是,“新问题”並不一定總是伴隨著“新史料”的出現而自動呈現。研究視角的轉换與研究方法的革新,必須建立在對基礎史料的精準把握與深入思考之上。
二、 重拾義例之學
時下墓誌研究最爲主流也最爲基礎的方式是對單方墓誌的考證,多以新出墓誌爲研究對象,以點斷文句、考釋文字、考訂墓主職官和生平履歷爲主要内容,並參照墓誌形制、平闕格式、出土時地等,通過與傳世文獻的比對闡釋時代背景,其操作流程基本上依據了傳統金石考證之學的傳統和規範。
就學術史的發展脈絡來説,考證之學只是傳統金石學的流派之一。梁啓超在總結有清一代金石學研究的脈絡時談道:“顧(炎武)、錢(大昕)一派專務以金石爲考證經史之資料,同時有黄宗羲一派,從此中研究文史義例。宗羲著《金石要例》,其後梁玉繩、王芑孫、郭忿、劉寶楠、李富孫、馮登府等皆有續有作。别有翁方綱、黄易一派,專講鑒别,則其考證非以助經史矣。包世臣一派專講書勢,則美術的研究也。而葉昌熾著《語石》,頗集諸派之長,此皆石學也。”*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東方出版社,1996年,52頁。
作爲古代金石學的重要分支,義例之學,或稱括例之學的主要内容是概括總結石刻,特别是碑刻與墓誌的文本特徵,通過採集古代諸家金石文例,討論碑、碣、墓誌等石刻文獻的起源、規制、格式等基本問題。對銘誌品級、塋墓、羊虎、德政、神道、家廟、賜碑之制一一詳考,對碑誌家世、宗族、職名、妻子、死葬日月之類咸條列其文,標爲程式,以爲括例。所謂“石例”,係墓誌碑文的寫作體例,其編纂的初衷是闡釋古代碑誌文體的格式和義例,爲時人墓誌寫作提供模仿和參考的依據。金石義例之學的發端是元代學者潘昂霄《金石例》,受其啓發和影響,明清以來,續補之作層出不窮,如明王行著《墓銘舉例》、清黄宗羲著《金石要例》、梁玉繩著《誌銘廣例》,嘉、道間金石義例專著接踵問世,有梁玉繩《志銘廣例》,李富孫《漢魏六朝墓銘纂例》,郭忿《金石例補》,吴鎬《漢魏六朝墓誌金石例》、《唐人誌墓金石例》,梁廷艷《金石稱例》,馮登府《金石綜例》,王芑孫《碑版文廣例》,劉寶楠《漢石例》,鮑振芳《金石訂例》等,光緒十一年(1885)朱記榮輯編成《金石全例》*朱記榮輯《金石全例》,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收入相關十種金石義例研究著作,標誌著金石義例之學在清代的成熟。
金石義例類著作編纂刊行的初衷在於指導墓誌的寫作,而隨著時代的變遷,碑墓寫作失去了現實意義,金石義例之學也就此中衰。清末以來,考據之學逐漸佔據金石研究的絶對主流地位,而括例之學式微,自葉昌熾《語石》和柯昌泗《語石異同評》*葉昌熾撰,柯昌泗評《語石·語石異同評》(考古學專刊丙種第四號),中華書局,1994年。之後,鮮有力作。
時下的墓誌研究,重考證而不重義例,墓誌義例只見於一般通論性著述,鮮有深入系統的探討。新出論著中,僅見的成果是楊向奎先生的《唐代墓誌義例研究》*楊向奎《唐代墓誌義例研究》,嶽麓書社,2013年。。在學科分化日益精細的今天,義例之學似乎被劃入了文學史的範疇,只有在研究墓誌文體結構時纔被提及。關於金石考證的流弊,葉國良先生有精闢的分析:“考證之學,自陶宗儀《古刻叢鈔》以降,著書者無慮數百家。諸家皆本宋人方法,取石刻資料與經史相補正,其精者如錢大昕、王昶、羅振玉等,於學術研究之貢獻,可謂巨矣。至其缺失,則或視爲治經讀史之餘事,隨手題跋,誤謬不免;復以忽略括例之學,缺乏歸納分析觀念,故有見樹不見林之弊,所得或趣瑣碎,或有重要結論而竟失之交睫,實爲可惜。蓋考證精則所括之例確,括例確則考證之功省,二學雖可分而實不可分也。”*葉國良《石學蠡探》,臺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2頁。
在新出墓誌層出不窮的當下,重拾金石義例之學顯得尤爲緊迫和必要。墓誌的撰寫有其固定的書式和體例,而不同歷史時代、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墓誌文本所採用的書法義例都有所不同,總結其書法義例,概括其書寫規律,對歷史研究具有重要的輔助作用。
關於義例著學對中古墓誌研究的作用,可以舉一個我個人研究的實例。談及魏晉南北朝的嫡庶關係,我們通常會引用《顔氏家訓》“江左不諱庶孽”、“河北鄙於側出”等經典描述*王利器《顔氏家訓集解》,中華書局,1993年,34頁。,但傳世史傳所載的具體史事和史證十分有限。我從墓誌中記述家庭成員的書法義例入手,對比了南北朝的多方墓誌後發現,南朝墓誌中,庶出子在婚姻、仕履等方面與嫡子差異不大,如《陳詡墓誌》中,庶子孝騫與正妻所生的五子統一排行,並未受到歧視,不僅如此,在墓誌中還記述了墓主“辭老還鄉”後,“第二息孝騫昆季男女,久違膝下,忽奉慈顔,悲喜不勝,如從天落,相率盡養”。看來因墓主長子孝柴早亡,庶出的次子孝騫實際承擔了家族繼承人的角色。而北朝的情況則與此相反,《元乂墓誌》等多方墓誌中出現了年幼的嫡子在前、年長的庶子在後的文本書寫;東魏《李憲墓誌》的譜系記述中,庶長子“長鈞”則排列在嫡長子之後,次子之前。我特意選取了同一家庭的三方墓誌: 《李祖牧墓誌》、李祖牧之妻《宋靈媛墓誌》、李祖牧之子《李君穎墓誌》。對比三方墓誌可以看到: 李祖牧共有八子,第四子以後皆爲庶子,三方同時刊刻的墓誌對譜系的記述有很大區别: 《李祖牧墓誌》將八子的譜系全部列出,但標明嫡、庶以示區别;《李君穎墓誌》記其諸弟,亦有第五至第八弟,但並未標明庶出。而《宋靈媛墓誌》只記四子四女,第五至第八子闕如,四個庶子都没有列入譜系。三方墓誌對於庶子譜系的不同記載,非常典型地體現了各家族成員因在家族的身份、角色不同而與庶子的不同關係,也反映出庶出子和嫡子的社會地位和身份差異是十分明顯的。除此之外,甚至在墓誌中還發現了北朝嫡庶之爭的具體實例: 在《席盛墓誌》中,有多位家庭子女的名諱疑因嫡庶糾紛而被人爲鏟去*陳爽《出土墓誌所見中古譜牒研究》,學林出版社,2015年,183—190頁。。
以上這些具體而生動的珍貴史料,不經過多方墓誌的對比分析和對書寫體例的總結,僅憑單方墓誌的考證幾乎不可能發現。充分吸收古代金石義例之學的研究成果,借鑒現代文本分析的研究手段,對中古墓誌的書寫體例和書寫格式進行系統歸納、對比和分析,纔有可能發現一些通過單一墓誌考證難以察覺的歷史現象與歷史問題。
三、 審慎對待僞刻
在中古墓誌的研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是史料的辨僞。商賈射利,乃使僞誌泛濫,魚龍混雜,爲禍學術,令人深惡痛絶。僞誌形態多樣,舉其大端,一爲臆造,二爲翻造,三爲變造。其中,臆造墓誌,如《陶潛墓誌》《張猛龍墓誌》等,破綻明顯,容易識别;翻造墓誌通常對石刻内容等不作變動,真僞與否只關乎其文物價值和書法價值,不影響文獻本身的史料價值。比較而言,對史學研究爲禍最大的是變造的僞誌,多是通過文本嫁接,使其真僞莫辨,給研究造成困擾。如《元伯陽墓誌》《給事君夫人韓氏墓誌》等,曾長期佔據在權威著録著述中,一直到近年纔得到糾正。關於墓誌辨僞,學界已經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鑒别手段,如從書法不類、避諱不知、職官不對、世系混淆、干支錯誤等問題入手,此不贅述。
僞誌遺害無窮,令學人深惡痛絶。某方墓誌一旦被學者質疑爲僞刻,即成爲史料禁區,學人避之唯恐不及,唯恐因出現錯誤徵引而貽笑大方的硬傷。在此,筆者提請留意學界留意的問題是: 石刻辨僞,如法官斷案,有一定的主觀性,存在誤判的可能。
2002年出版的由洛陽文物局編纂的《洛陽出土北魏墓誌選編》一書,以體例嚴謹、圖版清晰、録文準確而廣受學界好評,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在此書的僞刻存目部分,收録了《吕達墓誌》和《吕仁墓誌》兩方僞刻*洛陽文物局編纂,朱亮主編《洛陽出土北魏墓誌選編》,科學出版社,2001年,79、201、208頁。,其内容與《選編》正編所收被確認爲“真跡”的《吕通墓誌》*《洛陽出土北魏墓誌選編》,79頁。相比較,錯漏甚多,不少内容相互矛盾。如《吕達墓誌》中“祖父台”名下内容,在《吕仁墓誌》中完全被移到“祖父安”名下,而與前者中“父安”的内容不符。《吕達墓誌》中“父安”的職官,在《吕仁墓誌》“祖父安”名下已無,相關事蹟和頌辭則被移到“父達”名下,甚至“吕達”與“吕通”雖事跡相同,名諱卻不同。如此多的錯誤,似乎僅憑内容即可斷定其爲僞誌無疑。
事實的詭異之處在於,兩方墓誌並非來歷不明的民間藏誌,而全部是按照科學規程的考古發掘所獲。據2011年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在《考古》雜誌上發表的正式考古報告*程永建《河南洛陽市吉利區兩座北魏墓的發掘》,《考古》2011 年第9期,44—57頁。,1987 年 8月,洛陽市工作隊在洛陽市黄河北岸的吉利區配合洛陽煉油廠三聯合裝置車間的基礎工程開展考古工作,發掘了兩座規模較大的北魏墓葬,出土有三方墓誌,誌主分别爲吕達(吕通)、吕仁父子。《吕通墓誌》與《吕仁墓誌》均被放置在墓室的東南角;《吕達墓誌》爲重刻墓誌,被放置在後甬道近墓門處。有學者分析認爲: 《吕達墓誌》乃因胡太后復辟後給予吕達贈官和謚號一事而刻,刻寫時間必定在吕達下葬之後,此誌二以《吕通墓誌》舊志稿爲底本,但刻好後並未改題新的刻寫日期*張蕾《讀北魏吕達、吕仁墓誌》,《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647—653頁。。考古報告所述情況幾乎完全排除了墓誌作僞的可能,證實這種一人二墓誌真實存在於墓室之中,具備不同的功用。
尚可補充説明的是,這種一誌二石,或者一誌多石的現象在中古碑刻中雖罕見,但並非孤例,如南朝的《宋乞墓誌》即有磚誌三方,内容相近,據羅新、葉煒先生分析,這三方墓誌的誌主,一爲宋乞本人,一爲其妻丁氏,另一方爲最終合葬的標誌,“各有所屬,非可互相代替”*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修訂版)》,中華書局,2016年,42頁。。
三方吕氏墓誌從所謂“顯而易見”的僞誌還原爲貨真價實的真跡的過程頗有戲劇性,其間引出的問題值得深思。如在《洛陽出土北魏墓誌選編》一書中,附有49方僞刻録文和34方僞刻圖版,均無辨僞文字,亦無墓誌來源的交待,其中是否還有類似的誤判?既然經科學發掘的墓誌都有可能被錯誤認定爲僞誌,那麽以往諸多疑僞墓誌中,是否還存在著這樣的“冤情”?
中古墓誌形態多樣,必須充分認識其複雜性和多樣性,在證據不夠充分的情況下,僅憑墓誌文本内容的一些錯誤與矛盾,不宜轻易做結論,需要更爲審慎的態度。我們不能讓僞誌擾亂研究,但也要盡力避免因研究者主觀誤判而使有價值的史料湮没無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