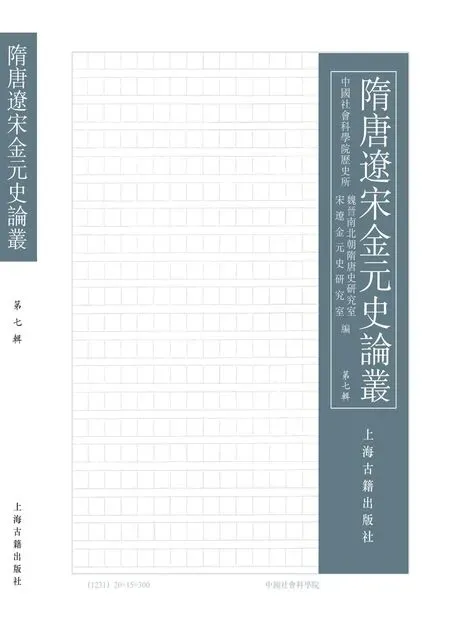敦煌文書與中國古文書學
黄正建
一
中國本來没有古文書學,到2010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幾位研究者的倡導下,成立了以商周金文、秦漢簡帛、(隋唐)敦煌吐魯番文書、(宋元)黑水城文書、(明清)徽州文書爲主的“古文書研究班”。到2012年召開第一届“中國古文書學研討會”,正式宣佈成立了“中國古文書學”。此後,分别於2013、2014、2015年連續召開了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古文書學研討會。通過幾次研討會,大致確定了“古文書學”研究的對象、内容、方法等。雖然仍有不同意見,但中國終於有了自己的“古文書學”,而且其影響也在逐漸擴大。採用“古文書學”的立場和方法研究出土或傳世古文書,已經越來越成爲學者的共識。
中國古文書學之所以能夠成立,是因爲出土和傳世古文書的發現越來越多、研究越來越深入。這其中,敦煌文書的發現與研究,是古文書學得以成立的一個重要基礎。
二
“古文書學”中的“文書”,是指狹義的“文書”。用古文書學的定義來説,就是指具有“發出者”與“接受者”的、具有移動意義的文書。這種文書保持了原有的“書式”,未經後人删改。典型的文書如官文書中的牒、符、帖、狀;私文書中的契約、書信,等等。敦煌文書中保存了大量這類“古文書”,因此是“古文書學”得以成立的重要史料來源與基礎。
但是,由於中國過去存世的中古時代的古文書數量極少,學人心目中没有“古文書”的概念,因此在“敦煌遺書”(以下暫稱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所有紙質文字資料爲“敦煌遺書”)發現的當時,很少有學者關注其中的“文書”。即使看到這些文書的巨大價值,也没有從文書學的角度予以關注,更少有稱其爲“文書”者。
林聰明《敦煌文書學》*林聰明《敦煌文書學》,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1年。在第一章第一節“敦煌文書總名的商榷”中,按時代先後列出了中國學者對“敦煌遺書”的不同稱呼,分别爲:
書: 羅振玉,1909年
遺書: 羅振玉,1909年
經卷: 李翊灼,1911年
佚書: 羅振玉,1913年
寫本: 羅振玉,1917年
古籍: 羅振玉,1917年
本: 陳寅恪,1929年
叢抄: 向達,1931年
殘卷: 王重民,1935年
寫經: 許國霖,1936年
舊抄: 聞一多,1936年
寫卷: 吴世昌,1937年
秘笈: 羅振玉,1939年
卷子: 向達,1939年
遺籍: 袁同禮,1940年
古抄: 陳祚龍,1961年
文件: 韓國磐,1962年
文獻: 陶振譽,1962年
藏經: 蘇瑩輝,1965年
遺經: 雨弟,1972年
從這個列表看,没有一位中國學者稱其爲“文書”。我們還可以補充幾個例子。比如中國科學院歷史所編寫的《敦煌資料》第一輯*中國科學院歷史所《敦煌資料》第一輯,中華書局,1961年。,“對推動我國敦煌文獻研究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劉進寶《敦煌學述論》,甘肅教育出版社,1991年,285頁。,收録的全部是經濟文書,但總名則稱之爲“資料”。又,姜亮夫《敦煌學概論》*姜亮夫《敦煌學概論》,北京出版社,2004年。,是“根據他在1983年的講課録音整理而成的。……是我國第一本講述敦煌學的簡明教材 ”*參見《敦煌學概論》柴劍虹序。。在這本《概論》中,總稱敦煌這批發現物爲“卷子”。在介紹“卷子”内容時,又稱之爲“經卷”。我們所説的狹義“文書”資料,被稱之爲“史地材料”或“社會史材料”,統統放到“經卷簡介”章節中予以介紹。
當然,實際上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除敦煌遺書“總名”外,中國學者對這批敦煌發現物中的“文書”類,倒也有稱之爲“文書”者。例如上述《敦煌資料》第一輯,在“前言”中介紹本輯所收内容時,就提到有“契約文書”類。唐師長孺先生1964年發表的論文《敦煌所出唐代法律文書兩種跋》*見《中華文史論叢》第五輯。,也是徑直稱了“文書”的。
直到20世紀90年代以後,稱“敦煌文書”或稱其中某部分爲“法制文書”“田制文書”“賦役制文書”等*劉進寶《敦煌學述論》,200頁。纔多了起來。但學者們並不清楚這其中“文書”的概念究竟爲何,因此不僅“文書”與“遺書”混用,而且往往還將“文書”與其他典籍甚至宗教文獻混同*參見1990年代以後出版的多種敦煌學概論類著作。。
總之,對於中國學者而言,由於不甚瞭解何爲“文書”,也没有“文書”的意識,因此自“敦煌遺書”發現伊始,就没有從“文書”的角度予以關心,以致後來即使使用了“文書”一詞,但對它究竟有何種含義,仍是不太明瞭。這些都是因爲中國當時還不存在“古文書學”。
三
但是反觀日本,則有所不同。上述林聰明所引關於“敦煌遺書”的不同説法時,唯一一個稱“文書”的,就是日本學者那波利貞。説法出自其文章《佛、獨、英に於る敦煌文書の調查》,時間是1933年*林聰明《敦煌文書學》,3頁。。那波利貞在這篇文章中將所有“敦煌遺書”都稱作“文書”,實際反映了他對其中狹義“文書”類的高度關注。所以有時他會有意識地區别狹義“文書”之外的“敦煌文書”。比如在其他文章中對其中的《唐令》或《史記·孝景本紀》,就稱之爲“唐鈔本”而非“文書”(1935年)*那波利貞《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創文社,1974年,687頁。。
日本學者大致從得知“敦煌遺書”開始,雖然對其也有不同稱呼,但將其稱爲“文書”的已經比較多了。神田喜一郞《敦煌學五十年》*原書由二玄社於1960年出版。譯文爲高野雪、初曉波、高野哲次翻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譯文因爲有日本學者參與,用詞應該比較準確。以下引文均據譯文。是1953年在龍谷大學演講時的演講稿,涉及内容自“敦煌遺書”傳至日本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在本書中,作者引用了大量當時的第一手資料(包括報紙報導、學者交往記録、講演文字等),如實反映了日本學術界面對“敦煌遺書”時對它們的用語。
根據本書中《敦煌學五十年》一文,作者是將“敦煌遺書”統稱爲“古書”的*神田喜一郞《敦煌學五十年》,2頁。。但同時又提到,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黑板勝美從歐洲回國,向日本學界介紹各種出土文物時,介紹了斯坦因藏品,其中提到有“唐代咸通九年的金剛經版本,還有稱爲書儀的文書類别”*神田喜一郞《敦煌學五十年》,14頁。。這裏直接稱“書儀”爲“文書”。書中也提到在昭和十年至十一年(1935—1936年),日本學者紛紛到法國調查敦煌古書的事情,“其中在較偏僻的領域取得成績的首推京都大學的那波利貞教授。調查研究敦煌古書的學者一般都將注意力放到佛典和漢籍上,而那波博士抄寫了大量史料文書帶回國”*神田喜一郞《敦煌學五十年》,23頁。。這裏的“文書”主要指社會經濟類文書。
在《敦煌學五十年》的《敦煌學近況(二)》中,雖然還在使用“敦煌古書”一詞,但使用“敦煌文書”的明顯多了起來。比如説介紹榎一雄教授“親自執筆的《敦煌文書攝影回想》”;説“如今我們就可以自由地查閲收藏於大英博物館的敦煌文書”;説印度維拉博士“進行拍攝北京圖書館所藏超過四千八百八十八卷敦煌文書的艱巨工作”*神田喜一郞《敦煌學五十年》,40—41頁。。特别“要提到的就是與社會經濟史和法制史相關的文書研究。東京大學的仁井田陞博士過去在這一方面曾經取得過出色成績……在《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上接連不斷地發表了……《斯坦因在敦煌發現的唐代奴隸解放文書》、《斯坦因發現的唐宋家族法相關文書》等多篇論文。同時山本達郎博士在《東洋學報》雜誌上發表的《在敦煌發現的計帳文書殘簡》、在《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上發表的《在敦煌發現的户制田制相關文書十五種》等等,皆爲飽含心血的作品……大阪市立大學的内藤乾吉教授則選擇了伯希和帶回法國的敦煌文書中的《唐律》作爲研究課題”*神田喜一郞《敦煌學五十年》,41—42頁。等等。可以説“敦煌文書”的使用逐漸普及開來。
日本學者之所以很快就以“文書”命名這批“敦煌遺書”,原因可能有兩點。第一,日本保留了從中世紀以來的大批古文書,以至從“正倉院文書”開始,一直將刻本以前的寫本稱之爲“文書”。第二,日本早在19世紀末就建立了自己的“古文書學”,界定了古文書的定義、範圍、研究方法等。日本學者很多接受過有關“古文書學”的教育,因此心目中具有“古文書學”意識,一旦看到與日本古文書類似的文物,就很自然地將其稱爲“文書”了。
關於後一點,還可舉一個例子。在《敦煌學五十年》中有一篇《内藤湖南先生與支那古文書學》的文章。文章説: 内藤湖南先生從明治末年到大正末年在京都大學東洋史課程中開設了支那古文書學講座,當時稱爲“公牘”,講解了漢代公文書、唐代制文、《元典章》、清朝公文書等,使學生們(包括神田喜一郎)“掌握了正確閲讀公文書的技巧”*神田喜一郞《敦煌學五十年》,84頁。。“内藤先生是我國支那古文書學的開拓者”*神田喜一郞《敦煌學五十年》,83頁。。可以想見,接受過這種古文書學訓練的學者,當接觸到“敦煌遺書”中有類似作品時,會很自然地以“文書”來稱呼它們了。這與没有古文書學、没有接觸過古文書學知識的中國學者就有著很大的不同。
稱“敦煌遺書”爲“文書”,並有意識地與古文書學聯繫起來的是那波利貞。他在《千佛岩莫高窟と敦煌文書》的長文*載《西域文化研究第二: 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資料(上)》,法藏館,1959年,13—68頁。中談到了敦煌文書的四點價值。其中第四點價值爲*文字爲我所翻譯,缺乏推敲,請讀者見諒。:
中國中世以前的古文書,傳世遺存者稀有。故而諸種文書本來的書式,現今不明者甚多。此乃不必絮説之現象。文書的文字雖然往往登載于《全唐文》、《唐文粹》、《文館詞林》殘卷等已刊刻的圖書中,使我們得以知道其内容,但記録的書式則被完全破壞。因此想要知道文書書式,殆屬不可能之事。甚至只能以我國王朝時代的現存古文書——其范式仿照唐制——的樣式類推。然而敦煌文書中保存有自南北朝至北宋初期豐富的文書,包括有任命官吏的任命書、官吏致地方長官的書信、買賣借貸契約等契書、民間結社的社條、官署的告示等種種文書的書式。單是能知道這些文書通行的是何種書式,就已經很多,何況其中還有不少帶有花押、指畫。僅此,即這些文書僅在研究中國中世時期文書的各種樣式方面,就具有絶大的史料價值了。特别是,若站在法制史的立場上,應該關注的最貴重的文書,是那些可以稱爲“公文書書式樣本”的遺存。在那遺存上面列舉、登載了唐代官署的公式文書樣式。登載此種文書樣式的唐代書籍現今已基本佚失,能夠知道唐代過所書式的,只有我國滋賀縣三井寺所藏智證大師圓珍在唐時使用的越州都督府發行的旅行許可證。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看到了法國第二八一九號紙背文書。文書雖然首尾闕如,是個殘卷,但尚完整保存了關式、牒式、符式、制授告身式、奏授告身式共五種書式的格式。單是記録了關、牒、符等書式名稱,就能補充不能提供這些書式格式的《大唐六典》的闕文。這在中國古文書學、中國法制史的研究方面,是難得的好資料。確實可以評價爲唐代古文書書式的吉光片羽了*《西域文化研究第二: 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資料(上)》,67頁。。
那波利貞先生提出的敦煌文書的其他三點價值分别是: 提供了構成編纂史書的根本性資料;提供了研究東西文化交流的資料;提供了衆多已亡佚的書籍。將“提供了古文書的書式”列爲敦煌文書價值的第四點,可見日本學者對古文書“書式”的關注和重視,而這一點正是古文書學的精髓所在。
池田温先生也是深諳古文書學的日本學者。他在《敦煌文書的世界》*原書由名著刊行社於2003年出版。譯文由中華書局於2007年出版。譯者爲張銘心、郝軼君。據“譯後記”,譯文還經過日本學者廣中智之的修改,因此是可以信賴的。以下引文均出自譯文。但要説明一點:“譯後記”説“池田先生主張統一使用‘敦煌文獻’的名稱,但是書中有的地方用‘敦煌文獻’,也有的地方用‘敦煌文書’等等。鑒於各章節的行文内容,我們基本上没有進行統一處理”(313頁)。没有統一處理是對的,因爲實際上池田先生使用“文書”一詞時有著特定含義,並非隨意混用。又,本譯文在翻譯英文時,存在用詞不統一的地方。比如山本達郎、池田温等編纂的英文版的《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史文書》,在本譯文中就有4種不同譯法: 1. 《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史資料系列》(92頁)。2. 《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資料集》(163頁)。3. 《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史料集》(262頁)。4. 《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史文書》(279頁)。可見如何翻譯“敦煌資料”“敦煌文書”,是個很複雜的問題。中主張使用“敦煌文獻”一詞,認爲它“是對在敦煌地域發現的古代文字資料的總稱”。他還辨析説:“另外‘文書’一詞在歷史的史料學和古文書學中,是有别於書籍的帶有限定的專門用於記録的意思(是有特定發信人和收信人)的文件*這句關於文書的話,翻譯得很彆扭。,因此對包含有典籍、文書、記録在内的敦煌資料,比起稱爲‘文書’來,使用‘文獻’的通稱更好一些。”*池田温《敦煌文書的世界》,41—42頁。
這就明確了狹義“文書”的特有性質。在這一立場上,池田先生把敦煌文獻區分爲“書籍和文書”*池田温《敦煌文書的世界》,190頁。,並且特别強調了其中文書的價值,以及日本學者因具有古文書學立場而擁有的優勢。他説:“文書類雖只佔全體數量的百分之幾,但是在傳世古文書幾近絶跡的中國,其珍貴的文物價值就非常值得重視了。”*池田温《敦煌文書的世界》,45頁。“宋代普及了刻版的結果,使唐末之前的寫經、寫本在中國傳承下來的幾近於無,與繼承了不少8世紀之後寫經和舶來的唐鈔本的日本相比有相當大的差異。敦煌寫經對中國人來説可以説是頭一回到手的此類古代遺物,同類的古寫經在日本也有少量傳存下來,在對它們進行研究時應該掌握的常識日本人已經具有了。在適應實物(?)的古寫本學、古文書學的領域*“在適應實物的古寫本學、古文書學的領域”一句不通,似有誤字,因未見原文,不能確定,特加問號以存疑。,日本研究者所做出的顯著貢獻,由此背景看是理所當然的結果。”*池田温《敦煌文書的世界》,62頁。换句話説,在“文書”研究領域,日本學者正因爲具有古文書學的常識,因此會很快在“敦煌遺書”中找出“文書”,並立即採用古文書學的方法對其進行研究。而對於此前很少古文書存世的中國,學者没有古文書學的常識,對“文書”的關心就相對要遲緩一些,對“文書”書式的關心就會很淡漠了。
四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在“敦煌遺書”公佈後,對其中的“文書”類資料,日本學者基於其自身的古文書學傳統,很快以古文書學的立場和方法,對其進行了研究,並進而出現了將這批“敦煌遺書”稱之爲“敦煌文書”的做法。嚴謹一點的學者,也會將書籍和文書區分開來,用“文書”特指那些非撰述的、原始的記録,甚至是具有發信者和收信者的,即有一定格式的文件。
現在尚不能判定中國學者稱這批資料爲“敦煌文書”是否受到日本學者的影響。從前引林聰明《敦煌文書學》排列的史料看,中國學者在60年代之前,很少將其稱爲“敦煌文書”,而如前述,那波利貞早在1939年就使用“敦煌文書”稱謂了,到1959年更發表了全面介紹“敦煌文書”的長文,並用很大篇幅指出了它在古文書學上的貢獻。由此來看,中國學者稱“敦煌遺書”爲“敦煌文書”很可能是受到了日本學者的影響。當然,要想落實這一推測,還需要更多的資料支持。
不過,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儘管中國學者也使用了“敦煌文書”的稱謂,但其實並不清楚這其中“文書”的含義,因此纔有與“遺書”“文獻”等的混用。究其原因,就是因爲中國没有自己的古文書學,學者們没有掌握古文書學的知識,也没有受過古文書學的訓練。因此,要想真正弄懂“文書”的含義,弄清日本學者區别書籍和文書的用意,瞭解文書書式的價值,就必須學習古文書學。這也是我們成立“中國古文書學”的初衷之一。
前述神田喜一郎認爲内藤湖南是日本“中國古文書學”的開拓者,但實際上,當時並没有多少可供研究的中國古文書,因此一般並不認同神田喜一郎的説法。直到敦煌文書發現、特别是對“敦煌遺書”中的“文書”研究成果斐然之後,纔可以説日本的“中國古文書學”出現了。而日本的“中國古文書學”其實就主要建立在敦煌文書和吐魯番文書(大谷文書)研究的基礎上*參見黄正建《中國古文書學的歷史與現狀》,《史學理論研究》2015年第3期,137頁。。换句話説,如果没有敦煌文書的發現,日本的“中國古文書學”就不會出現。敦煌文書及其研究是日本“中國古文書學”建立和發展的基礎所在。
這就是敦煌文書與中國古文書學的關係。回望中國,敦煌文書及其研究,也是中國“中國古文書學”建立的基礎之一。由於在出土文獻的研究中,敦煌文書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水準高,特别是其中關於狹義“文書”的研究,包括公私文書的紙張、字體、書法、簽署、畫押、書式、内容、性質等的研究,走在整個古文書研究的前列,甚至帶動著其他如黑水城文書的研究,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説,敦煌文書及其研究,也是構成“中國古文書學”建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
從中國古文書學的立場看,敦煌文書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這一點上述那波利貞已經談到了。如何有意識地從古文書學的視角,使用古文書學的方法,去研究敦煌文書中那些典籍之外特别是具有“書式”的文書,是我們今後努力的方向之一。也只有有意識地從古文書學的立場去重新審視那些“文書”,纔能使敦煌文書的意義和價值更加升華,反過來促進中國古文書學的進步。這一點,也是我們所深深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