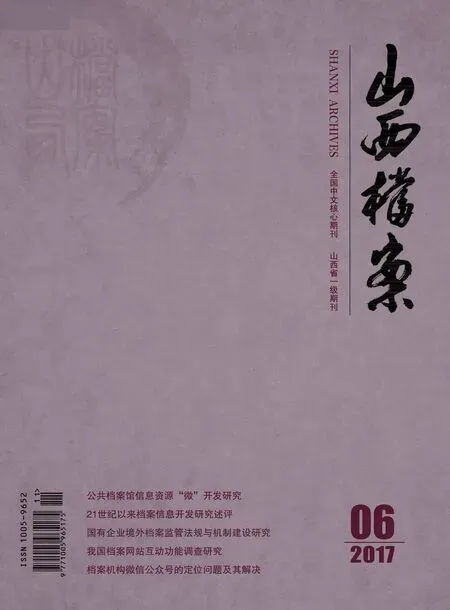家谱叙事的主观虚构性
文 / 王忠田
家(族)谱从其本质上说是拒绝叙事的,但宗族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宗族成员。也就是说,宗族成员只有通过预先文本化的家谱才能较为清楚地了解本宗族史。国内外历史叙事日臻成熟,而作为中国历史重要文献来源的家谱,其叙事性少有学者涉足。家谱叙事是历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正史文本、方志文本还是家谱文本,编纂者在叙述过程中总会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即按照事物或事件的本来面目再现这一事物或这一事件的过程。在叙述过程中尽可能不加任何主观意识的修饰,即便是这样,这一意图最终也无法达到。每部家谱的编纂者皆为本宗族成员,“族谱在成为职业历史学家进行历史研究的资料之前,本身已经是一部包含着对本族过去经历的解释与主张的‘历史叙述’”[1]17。这一“历史叙述”本身就带有一定的虚构性。当历史学家对家谱这一文本进行考量的时候,即便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尽可能摒弃自己的主观意识或情感,但受制于学识、历史、政治及环境等方面的影响,研究成果也难免会有虚构的成分,其中一部分研究成果也就成为虚构。其实,家谱叙事旨在成为宗族历史进程中特殊环节的一种语言模式。这种模式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宗族文献记录并没有描绘出他们所验证的事件结构的清晰形象。编纂者为了描绘出过去“真正发生的事件”会怎么做呢?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必须首先预设一个可能的认识客体,也就是文献中报告的整个事件。这种预设行为是诗意的,因为在历史学家自己意识的经验中,它是前认知的和前批判的。它是诗意的,也因为它所构成的那个结构后来将在历史学家提供的语言模式中变成形象,作为对过去‘真正发生的事件’的解释和再现。但它构成的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可能用作(精神)观照客体的一个领域。它还构成了许多概念,历史学家将用这些概念识别于那个领域里的客体,描写这些客体相互间维持的那些关系。”[2]404这就涉及到家谱场的重新编排了。
一、编纂者对家谱场的重新编排
编纂者在家谱编纂过程中进行的叙事,最主要的功能是要建构一个本宗族的知识体系。这一体系建构过程是叙事的。也就是说,这个体系不是一个可以用科学的标准来证实的知识系统,而是以编纂者自身的情感、意志、修养、学识、伦理价值等综合因素为依据,借助家谱场来建构的一个知识体系。该体系的核心是宗族里的人,是关于本宗族世系中人的知识。家谱场是宗族文献与事实的载体,是宗族史情节结构或某一事件构成的要素场。这里所说的事实并不是编纂者直接接触到的家谱或宗族的感性材料,而是编纂者思考着的某种经验或某个客观的事实,“这种客观性不是给予的,而总是包含着一种活动和一种复杂的判断过程”[3]221。这就涉及到编纂者对事实的阐释和推测。因此,这里的家谱场并非实在的世界。它具有非在场性,即不在场。家谱场的不在场是以某时某地为标准,一类是在某时某地不存在,但在非某时某地亦或某时非某地存在过;一类是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后一类家谱场中的数据是编纂者为了宗族的繁荣昌盛或宗族权威幻想出来的叙事对象。
(一)编纂者对家谱场的选择
编纂者在叙事过程中,对家谱场的选择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所选择的家谱场要符合自身编纂的需要,同时还要有利于宗族的发展。在微观层面,家谱场可以是事件简单数据的堆砌;在宏观层面,家谱场可以转化为整个宗族文化的发展历程。
编纂者对家谱场的选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家谱场中有很多事实数据,编纂者在以叙事再现宗族史或阐释某一特定时刻时,不可能把全部事实都表达出来。这就需要编纂者对家谱场一部分数据进行“阐释”,把与叙事目的无关的事实数据在预想的故事模式里删除。其次是编纂者预想的故事模式与家谱场中的文献或事实并非完全对等。在不对等的情况下,编纂者一般会运用三种方式对其进行选择:一是在既定文献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某一部分事实,放弃一部分事实数据;二是遵循既定的文献进行选择,采用转述的形式叙述事实;三是否定既有文献,重新立事,这种情况极少,不代表没有,但是这种情况脱离了叙事的虚构范畴,滑入了虚假行列。再次是在重建宗族史上某一时期发生的某一事件时,编纂者在叙事中必定要对这一事件进行“合理”的叙述,对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解释。但是家谱场中事实数据毕竟有限,在缺少事实数据支撑的情况下,编纂者不得不以假定数据或假定事实,又或某些理论来填补家谱场的空白,同时对家谱场中所选择的一些事实数据进行充实和阐释。“一个历史叙事必然是充分解释和未充分解释的事件的混合,既定事实和假定事实的堆积,同时既是作为一种阐释的一种再现,又是作为对叙事中反映整个过程加以解释的一种阐释”[4]63。这样,编纂者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家谱场,按照故事的叙事类型赋予事件序列以不同的宗族文化意义。
(二)编纂者对家谱场的情节编排
在家谱叙事中,如何建构宗族状况取决于编纂者对家谱场中某一组宗族事件与情节结构的合理编排,而这一合理编排也具有一定的虚构性。编纂者以家谱场为基础,以一事物或事实思考另一事物或事实,使家谱场中的事物或事实之间具有了连贯性。编纂者把诸多文献或事实编织成一个整体或情节结构,并将这种情节结构赋予事实事件,就形成了某一情节的编排模式。笔者翻阅了河洛地区诸多家谱叙事文本后,根据编纂者的情节编排分析了其中潜含的意识形态,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无论编纂者的叙事以何种方式进行,河洛地区家谱文本的所有编纂者都潜含一个共同文化因子——祖宗崇拜。受这一因子的影响,情节编排模式可以分为三种:励志型编排模式、炫耀型编排模式与含蓄型编排模式。它们是编纂者赋予家谱场的文献、事件以特殊意义(可以是励志、炫耀、含蓄)而形成的不同情节类型。编纂者通过不同的情节编排模式把宏观叙事体例内容编纂成一个连续的世系体系,把中观叙事体例内容建构成一个本宗族完整的宗族史,同时将微观叙事体例内容尽可能详实地叙述出来,从而为本宗族建构了一个宗族知识体系。这将使宗族成员在精神上有一个心灵的栖息地,在生活中存在于一个叙事建构的宗族文化世界里。
二、编纂者对宗族历史时间的把握
在宗族发展史中,可以见证历史时间的事物有三类:一是家谱和宗族其它文字记载的事物;二是宗族保留下来的物品或建筑物;三是宗族成员的回忆。宗族成员将这些事物进行固化,作为宗族史的内容传承下来。同时,历史时间也被纳入这一内容中,以一条线性链把事件串联成一个宗族文化体系。宗族成员以“点”的形式固化在历史时间链上,且留下了永恒的生活轨迹。对于时间与历史的关系,陈新教授认为:“过去的事件已经成为历史,现在的事件正成为历史,将来的事件也将成为历史,过去、现在、将来这时间的三维组成便以已经静止的过去为核心构成了历史显现的形式。”[4]因此,编纂者在对家谱场中文献和事实进行梳理时,历史时间在其思维中具有五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指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刻,可称之为时点;其二指宗族史中某一情节内部各个事件或某一事件内部各小事件相继发生的次序,可称之为时序;其三指宗族事件时间长度与家谱文本时间长度的对比,可称之为时距;其四指某一连续事件在整个叙述过程中的持续期限,可称为时段;其五为“实际编纂族谱的时间与族谱所记载的早期祖先的时代之间,就存在一个巨大的时间差,”[5]可称之为时差。在这个“巨大的时间差”中,编纂者借助历史时间的时点、时序、时距、时段对家谱场中的文献和事件重新建构叙事模式,这是一个追溯性的过程。濑川昌久为了方便考察家谱的可能性和虚构性,将其分为三个层次,“‘新层’(最近的祖先)、‘中间层’(宗族的开基祖)和‘老层’(移居本地以前的远祖系谱)”[1]6。在河洛地区的家谱文本中,无论是编纂者还是应编纂者之邀写谱序的作者,对宗族历史时间的把握存在三方面的共性:一是时间越近的年代,编纂者在编纂过程中对家谱场中文献、事物或事实的阐释或推测就越少;二是时间越久远的年代,编纂者在编纂过程中对家谱场中文献、事物或事实的阐释或推测就越多,也更具挑战性;三是时间相同的年代,本支系比他支系的编纂在对家谱场中文献、事物或事实的阐释或推测也较少。如《邵氏家谱》以邵雍为第一世即河南邵氏宗族的开基祖,自开基祖之前的远祖系谱,观其谱序可见一斑。“优秀的职业历史学家的特征之一就是不断地提醒读者,他在总是不完整的历史记录中所描写的事件、动作和动因都具有纯粹的暂时性”[2]33。这一暂时性具有非事实性,即可能性,也就具有了虚构的意蕴。也就是说,编纂者主观意识的投射并非与读者的思维意识相契合。因此,这将导致编纂者与读者之间逻辑思维相去甚远。
在编纂过程中,编纂者的主观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宗族过去的怀念与崇拜。家谱场中的这些文献描绘的宗族世界是不可接近的,具有模糊性。每编修一次形成的新家谱不过是增加了家谱文本的数量。若要忠实地反映过去特定宗族历史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编纂者就必须对过去的家谱文本进行阐释,并且需要分析过去的历史与通过分析家谱场中的文献而创造出的家谱文本之间的区别。不过,我们知道编纂者对过去了解得越多,概括起来就越难,主观意识的投射就越少。但是在编纂者的思维意识中,对过去的怀念和先祖的崇拜使这一意识从未停止和间断过。二是对当前现实宗族的关怀。家谱是宗族文化的载体,编纂的目的之一就是敦宗睦族,对宗族成员进行道德教化。冯尔康认为:“分清族人支派,明白互相间的亲疏关系,是修谱的一个实际原因。”[5]322编纂者作为本宗族的成员,在编纂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当前宗族的关怀。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聚族众;明世系,辨尊卑;促教化。家谱的编纂并非是一次性完成的工作,而是一个不断地被编辑、被补充和被修正的过程。编纂者在编纂过程中所投射的对未来的展望,主要体现在寄望宗族子嗣的繁荣昌盛、光宗耀祖及宗族世系连绵不绝等方面。
综上所述,文学叙事与家谱叙事的根本性区别并非在于真实性与虚构性,而在于文学是将叙事形式强加于事件,家谱叙事则相反。编纂者创造家谱文本的过程包含着对宗族的阐释,并努力赋予家谱场里那些片段性的文献或不完整的事件以意义,且不得不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将自认为有用的素材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编排,形成整体,再赋予一定意义,从而编纂出极具主观虚构性的家谱叙事文本。
[1][日]濑川昌久.族谱:华南汉族的宗族·风水·移居[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2][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7.
[3][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4]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5]冯尔康.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