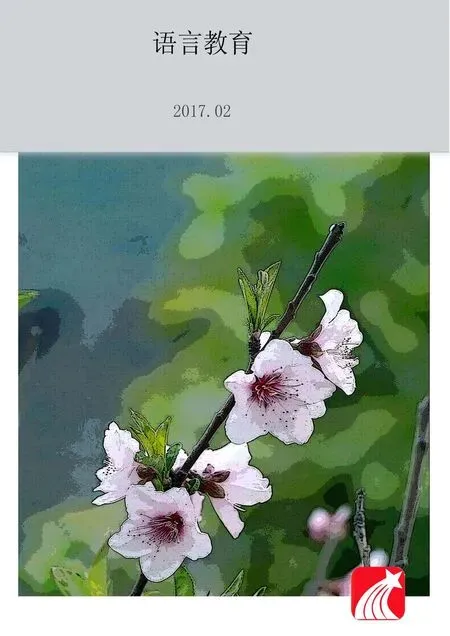译者主体性差异在圣经翻译中的体现
——以马礼逊和郭实猎圣经翻译为例
陈艳敏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
译者主体性差异在圣经翻译中的体现
——以马礼逊和郭实猎圣经翻译为例
陈艳敏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译者主体性包括能动性和受动性。圣经译者的信仰背景塑造译者主体性,译者能动性是建立在信仰背景上的能动性,同时,译者能动性的发挥又受制于译者的信仰背景。在圣经翻译中,译者主体性是建立在信仰背景基础上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本文分析马礼逊与郭实猎的信仰背景,指出二者基于信仰背景的主体性差异,通过译经原则、态度及术语翻译,阐释译者主体性在马礼逊与郭实猎译经中的体现。
马礼逊;郭实猎;译者主体性;信仰背景;翻译原则
1 .引言
圣经作为基督信仰的典籍,经数世纪,已被译成两千多种语言,而且存在同一种语言的多个译本。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圣经译者主体性差异息息相关。本文之所以选择马礼逊和郭实猎的圣经译本来分析译者主体性差异,是因为二者都是以往圣经译本的修订本,且相互关联。马礼逊1823年出版的《神天圣书》中的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及保罗书信是白日昇版本的修订版,郭实猎1839年出版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是马礼逊《神天圣书》的修订版。可以说马礼逊是新教第一代中文圣经译者,郭实猎是新教第二代中文圣经译者。本文通过比较马礼逊与郭实猎的信仰背景指出:信仰背景是圣经译者主体性差异之源。不同的信仰背景塑造不同的译者主体性,基于不同信仰背景的译者主体性体现并制约译经原则与态度,而术语翻译的差异是译者主体性差异的突出标志。
2. 译者主体性内涵
自从翻译研究向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便受到译界关注,并成为译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学界展开了如何界定译者主体性内涵的讨论。王玉樑认为,“主体性是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本质力量的外化”,具有“能动地改造客体、影响客体、控制客体,使客体为主体服务的特性。”(王玉樑,1995: 35)“译者主体性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查明建田雨,2003: 22)“主观能动性包括目的性、自主性、主动性、创造性等,能动性是主体性最为突出的特征”(查明建 田雨,2003: 21-22)。主体性不仅包含能动性,而且也包含受动性,“译者的受动性是其能动性的前提和基础,而译者的主体性也正是建立在其受动性基础上的能动性的发挥”(阮玉慧,2009: 85)。能动性与受动性二者的关系恰如硬币的两面,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受动性是能动性的内在基础,是主体之所以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依据”(查明建 田雨,2003: 22)“主体性是包含受动性的能动性,是受动性转化的能动性,是受动性基础上的能动性,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由能动性到受动性,再到能动性,这就是主体性形成的辩证过程,后一个能动性是前面能动性与受动性在更高阶段上的统一”(王玉樑,1995: 38)。
在圣经翻译中,“译者所具备的能力或要求中,第一重要的是必须是神学家,其次是精通两门语言。神学家说明译者具备翻译专门知识的才能。精通两门语言说明译者具有翻译家最基本的技能”(陈梅,2006: 51)。圣经译者是有基督信仰的人,圣经译者主体性范畴必然是界定在信仰背景框架内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信仰背景是圣经译者主体性的本质特征,圣经译者的主体性是建立在信仰背景基础上的能动性、是受信仰背景制约的能动性。圣经译者的圣经翻译活动受信仰背景的制约与限制,具有受动性。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受译者信仰背景制约,信仰背景包括对圣经的认知程度、神学体系构架及差会派别等,这些因素制约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使译者无法超越信仰背景的制约。译者的信仰背景是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基石,译经原则的确立、神译名的翻译就是建立在信仰背景基础上的。
3. 译者主体性差异之源:信仰背景
前文提到圣经译者主要是神学家或虔诚的基督徒,他们都有共同的基督信仰,都明白圣经。然而,由于译者在不同的环境对基督信仰有不同的经历,所以他们的信仰背景也各不相同。圣经译者的家庭背景、信主经历、信仰生活、神学院学习、侍奉领域与经历等构成了译者个体的信仰背景。这些信仰背景之差形成了各自的译者主体性,这些因素都会对他们日后的圣经翻译实践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马礼逊和郭实猎也不例外。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于1782年1月5日出生于英国北部诺森勃莱郡的小镇莫佩思,他的基督信仰受家庭的影响很大,他父亲雅各·马礼逊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带领全家人信耶稣,一直坚持带领全家做家庭礼拜。他不仅从父母那儿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且从赫托恩牧师主持的主日礼拜中明白了圣经。1798年(16岁)初,马礼逊受洗加入了英国长老会,他经常读经、参加祷告会及主日聚会。1801年(19岁)6月19日,他开始跟雷德罗牧师学习拉丁文,他还认真地学习了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为他今后的中文圣经翻译工作打下了基础。1803年(21岁)1月7日,马礼逊进入达霍克斯顿神学院学习。伯德牧师回忆马礼逊在霍克斯顿神学院时,说他勤奋读书、敬畏神灵、敬虔度日,获得了师长和同学的信任和敬爱。1803年2月23日起,马礼逊开始在沃夫牧师的教会做礼拜。1804年5月27日,马礼逊向伦敦宣教会审议委员会的主席亚历山大·沃夫牧师申请做伦敦宣教会派赴海外的传教士。在申请书中,他说自己到霍克斯顿神学院接受训练的目的就是要当一名传教士。5月28日,委员会通过决议接受马礼逊成为伦敦宣教会的传教士,并派他前往高士坡宣教学院接受专门训练,5月30日,马礼逊前往高士坡。1804年9月, 高士坡宣教学院董事会做出决议,计划命马礼逊前往中国宣教,赋予他的使命是将圣经翻译成中文。1805年8月,马礼逊回到伦敦,伦敦宣教会安排他学习医学、天文学、数学和中文知识。马礼逊在伦敦期间跟中国人容三德学习中文。1807年1月3日乘船经纽约于同年9月8日抵达广州(马礼逊夫人,2004: 11-39)。
郭实猎(Karl August Gtzlaff, 1803-1851)于1803年7月8日生于普鲁士波美拉尼亚省的皮里茨,四岁丧母,之后父亲与一位带着八个孩子的寡妇再婚。之后的八年里,继母对他粗暴,使他变得忧郁,父亲的再婚使他没有安全感,造成他很难与人建立和睦持久的关系。1811年,8岁的郭实猎进入普里茨的一所拉丁语学校学习五年,此间,他掌握了学习语言的技巧,为他以后翻译圣经奠定了基础。13岁时他辍学,结识了一个热衷海外宣教的商人。郭实猎热衷探险,也想去宣教,但他目的不纯,想借宣教之名实现探险之梦,由于资金问题宣教的事也不了了之。19世纪初的德国盛行浪漫主义、个人主义、异国情调,虽然这几种思潮是相互矛盾的,但郭实猎却几者兼之。当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访问什切青时,郭实猎和一个朋友大胆地将欢迎诗投到他的马车里,看了欢迎诗的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喜出望外,就给他们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指定郭实猎到柏林神学院学习。1821年(18岁)郭实猎进入柏林神学院学习,最初他并不适应这个小的虔信派神学院,他想成为善辩的牧师,并没有过一种祷告的生活,对属世的学问兴趣十足,甚至发展到蔑视圣经、不关心信仰的地步(Lutz, 2008: 19)。他的室友赖卡特(Reichard)指责了他的傲慢,并劝他自己首先经历耶稣基督的福音,否则不能担当传福音的重任。1821年7月初的一个晚上,郭实猎经过悔改和祈祷,经历了重生,而后获得了共同体的接纳(Lutz, 2008: 25-26)。1823年进入荷兰宣教会神学院学习三年,1826年7月被荷兰宣教会按立为牧师,同年9月启程前往巴达维亚,跟麦都思学汉语和马来语。1828年到新加坡,因与荷兰宣教会意见不合,1829年他脱离荷兰教会,成为独立的传教士。1831年初他搭帆船前往中国,6月中旬登陆,9月抵达天津,由此北上辽东湾,复南下,于12月抵达澳门。他在澳门悬壶济世,入乡随俗,身穿唐装,取汉名为郭实猎。
可见,马礼逊和郭实猎虽然都是基督徒,都是传教士,但是他们的信仰背景形成的环境不同、信仰根基的深浅不同、对神的敬畏程度不同,这些塑造了二者不同的主体性。马礼逊出生于基督化家庭,父亲的信仰感染了他,从小养成了虔敬的信仰生活,他对神有敬畏的心,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基督,为基督而活,以至于他在神学院刻苦学习、忠于圣经,立志当一名传教士。而郭实猎出生于破碎的家庭,从小受到很多伤害,没有基督信仰环境的熏陶,他本人不是很明白基督信仰,在神学院学习期间缺乏对神的敬畏及对圣经权威性的认识。二者的这种信仰背景差异塑造了二者不同的主体性,这也在二者的圣经译本中留下了烙印。
4. 译者主体性差异之体:译经原则与态度
在圣经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采用何种翻译原则、对圣经翻译持何种态度,取决于译者的信仰背景,此信仰背景构成了译者主体性的本质特征,译经原则与译经态度的发挥受制于译者的信仰背景。同时,译者在自己信仰背景允许的范畴内,发挥主观能动性,制定翻译原则,确立翻译态度。信仰背景是译者主体性的根基,它决定译者自主地探究翻译原则,又制约翻译原则的制定与选择,译者无法逾越自身信仰。马礼逊和郭实猎虽然都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他们信仰根基的深浅不同、对神的敬畏程度不同,因此,在翻译原则与态度的确立上,二者体现了不同的主体性,二者的能动性得到不同程度的发挥。
正如前一节所评述的,马礼逊是信仰成熟又敬畏神的传教士。他认为翻译肩负双重任务,其一是准确理解原文,感知原作的精神;其二是忠实地、明晰地、符合语言习惯地(如果可能,尽可能优雅地)将原作的精神与感觉表达出来。在这两项任务中,前者比后者更重要,因为文章的优雅不能弥补对原文语义的曲解。为了实现这两个目的,他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参照了英文公共版圣经、原文圣经、拉丁文圣经、七十士希腊文译本等,以便弄清经文意思。与此同时,他孜孜不倦地学习中文、研读白日昇译本、参照拉丁中文词典。他在翻译圣经时,遵循忠诚、明晰、简单的原则;宁愿使用常用词,也不使用罕见的或古典的词;避免使用异教徒的哲学术语和宗教术语;宁愿自己的翻译被认为是不雅的,也不愿被认为是难懂的;为了弄清难理解的段落,他拜访请教当地人,使用了公认的最严肃、最虔诚的表达。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他带着虔诚惧怕的心,力求以准确的思维方式表达,唯恐曲解神的话。他认为在翻译圣经方面,这种态度是必不可少的(Morrison, 1839: 8-10)。
1823年出版的马礼逊译本——《神天圣书》存在不足之处,马礼逊也认识到这一点,他希望他的儿子马儒翰修订他的原译。第一次的修订由美国圣公会发起,由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 Morrison, 1814-1843)、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郭实猎四人组成修订小组。1834年4月马儒翰和裨治文从路加福音开始修订马礼逊的原译,由于裨治文中文功底薄,马儒翰工作繁忙,修订工作进展得很慢,1834年8月,马儒翰因父亲的去世及工作的变故没能投入圣经翻译中。1835年1月,郭实猎加入这个修订小组,成为这个修订小组的主要译员之一,并用全部时间和精力修订圣经(苏精,2012: 9)。1835年6月麦都思加入,之后由于麦都思从写《福音调和》得到翻译心得,郭实猎有翻译圣经的经验,曾将圣经分别译成泰语、老挝语和柬埔寨语,加上娴熟的中文,因此修改圣经的任务主要落到麦都思和郭实猎的肩上。1836年1月修订完新约,旧约由郭实猎负责修订。虽然郭实猎是四人小组的主要译员,但他翻译圣经的态度令人堪忧。裨治文评价郭实猎极少检查或校阅自己的稿件的内容,这造成了马儒翰和裨治文要花费比他还多的时间校对他的文稿。马儒翰也批评郭实猎的轻率态度,如果让郭实猎独自遣词,他用的不会是最适当的,甚至出乎他们所知的范围之外(苏精,2012: 18-19)。
郭实猎没有形成自己的翻译原则,而是遵循了麦都思的翻译原则。麦都思翻译圣经的原则是让中国人容易理解并接受。他认为圣经翻译必须坚持中文写作风格,而不是拘泥于西方语文的文法结构,无关紧要的字或虚字不必全部照译;使用双音节短语代替马礼逊的单音节词,较少使用小品词和代词,使用明喻,而不是隐喻。马礼逊非常不认同麦都思的主张,直到过世的两个多月前仍在批评麦都思,说他想要以较好的文体将圣经译成适合中国异教徒胃口的轻松读物。基于此种翻译原则的1836年译本没有得到圣公会的认可。虽然如此,郭实猎仍然坚持己见,坚持使用麦都思的翻译原则,继续翻译,并自找门路,获得赞助,于1839年在新加坡出版了郭实猎译本。
可见,基于信仰背景的译者主体性差异在翻译原则与态度上体现出来,译者在基于信仰背景的主体性范畴内,发挥主观能动性,制定翻译原则、确立翻译态度。在圣经翻译方面,马礼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本人努力准确理解圣经、感知圣经精神,并忠实、明晰、符合语言习惯地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在翻译中避免使用异教徒的哲学术语和宗教术语。马礼逊译本的翻译出版发行也得到大英圣公会的支持。而郭实猎在圣经翻译方面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他追随了麦都思的翻译原则,力求让中国人容易接受和可以接受,在翻译圣经时大胆地改写,四人小组翻译成员批评他缺乏严谨的态度,但郭实猎仍坚持己见,自寻门路出版译本。
5. 译者主体性差异之标:术语翻译
马礼逊修订了白日昇的 《若翰攸编耶稣基督福音》,命名为《圣若翰传福音之书卷四》;郭实猎修订了马礼逊的《圣若翰传福音之书卷四》,命名为《约翰传福音书卷四》。以下以《约翰福音》第一章为例,比较白日昇译本、马礼逊修订本、郭实猎修订本、委办译本及和合本的文本,分析马礼逊、郭实猎二译者主体性差异在术语翻译中的体现。
当始已有言。而言在神怀。且言为神。当始由此于神怀也。万有以之得作。且凡受作者。无不以之而作焉。……且言成为肉。而居于吾间。吾辈已见其荣光。若由父之独子之荣光。满有宠真者也。
白日昇 《若翰攸编耶稣基督福音》 第一章
一节当始已有言而其言偕神、又其言为神、二此者当始偕神也。三万物以之而得作、又凡受作者无不以之而作焉。……十四其言变为肉而居吾辈之中、且吾辈见厥荣、夫荣如父之独生、而以宠以真得满矣。
马礼逊 《圣若翰传福音之书卷四》 第一章
一节元始有道。其道与上帝共在。道即乃上帝也。二是道当始共上帝在也。三万物以道而造,又凡被造者,无不以道而造作矣。……O十四夫道成肉身而居吾中间、可以看其荣仪、即天父独生子之荣、以恩典真实得满也。
郭实猎 《约翰传福音书卷四》 第一章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2这道太初与神同在。3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和合本 《约翰福音》
白日昇对中文《新约全书》的翻译做出了巨大贡献,形成了《新约全书》翻译的雏形。马礼逊对白日昇的文本进行了修订,在格式上白日昇只注明了章,没有给文本注节,马礼逊在修订时给每章注上了节,便于诵读、查找,这种注节的方式影响至今;白日昇句与句间都用句号隔开,马礼逊对小句进行了整合,如将“当始已有言。而言在神怀。”合并成一个小句“当始已有言而其言偕神”,在句间使用顿号和句号;在句法上,马礼逊添加了代词,如“其言”、“此者”、“厥”、“夫荣”;在重要专门术语上,马礼逊沿用了白日昇的用词,如“言”、“神”、“言变为肉”。
郭实猎沿用了马礼逊的章节标记法,将马礼逊整合的小句重新划分成两个小句,回归到白日昇的原译格式,如将“一节当始已有言而其言偕神”修订为“一节元始有道,其道与上帝共在,”,在句间除了使用顿号和句号外,还使用黑点,添加了段与段之间的分隔符,用“O”表示;在句法上将单音节词修订为双音节词,如将“偕”修订为“共在”、将“肉”修订为“肉身”、将“荣”修订为“荣仪”、将“父”修订为“天父”、将“宠”“真”修订为“恩典”“真实”,双音节词的使用一直延续至今。在重要专门术语上,郭实猎大胆地修订了白日昇、马礼逊的用词,如将“言”修订为“道”、将“神”修订为“上帝”,神译名的修订引发了日后长达数年的“译名之争”,这些修订的术语一直延续到和合本,如“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
可见,马礼逊修订白日昇译本时,谨慎地保留了重要神学术语“神”、“言”,对希腊文的Logos(英文译成Word)沿用了白日昇的“言”,并且在下一节中,在白日昇的原译中特别加上“此者”,“此者”二字点出“言”是“那一位”,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三节指明“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对应创世纪第一章记述神创造天地万物,使用了十一个“神说”,然后“事就这样成了”。神创造天地是藉着“话”(即“言”)造的,这正与约翰福音的“万物以之而得作”相呼应,可见“言”的翻译是合乎圣经的。郭实猎修订马礼逊译本时,大胆地将“言”修订为“道”、将“神”修订为“上帝”。“道”的翻译虽然便于中国人理解,却容易使中国人混淆《道德经》的“道”与“成了肉身”的“道”。至今有些中国人仍然将希腊文的Logos (英文译成Word)与中国道教的“道”混为一谈,甚至有的牧师在讲台上把老子的“道”跟圣经拉上关系。这种术语翻译的差异是二者基于自身神学思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同时此差异又是受制于二者神学思潮的主体性的再现。马礼逊忠实原文、不使用异教术语,而郭实猎受自然启示神学思潮的影响,认为圣经启示的那位真神,各国各族人民在本民族的信仰中可以找到原型,因此,引入了道教术语“道”、“上帝”。郭实猎的修订本虽然在文体上比马礼逊的修订本更加优雅,但是他将道教术语渗入圣经中,造成真理的混乱,是受自然启示神学思潮影响的结果。
5. 结语
圣经作为基督信仰的典籍,包含了基督教教义。圣经译者冲破种族、民族、文化、语言的限制,将圣经翻译成上千种语言。为了使圣经译本更加完善并适应时代的变化,一种语言的圣经,经多次修改或重译后,出现多种译本就不足为奇了。译本的差异是译者主体性差异的彰显,圣经译者虽然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信仰成长背景不同、对圣经认识的深浅不同、信仰成熟度不同、对神的敬畏程度不同。这些可以统称为信仰背景,它是圣经译者主体性差异的根源,它塑造了译者不同的主体性,它是圣经译者主体性的本质特征。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制于译者的信仰背景,同时,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又在信仰背景的基础上发挥出来,译者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统一在信仰背景之中。译者主体性的差异在译经原则与译经态度中凸显,术语翻译的差异是译者主体性差异的标志特征。出生于基督徒家庭的马礼逊从小就敬虔度日,常常读经祷告,参加聚会,他读神学的目的也是为了能更好地服侍神。他对神的敬畏,使他在翻译圣经时,存敬畏的心、考究翻译原则,特别强调不使用异教术语,以免混淆基督的福音。而第二代译者四人小组译者之一郭实猎直到读神学时仍然缺少读经祷告的生活,比起专研圣经,更喜欢属世的学问。在翻译圣经时,没深入探究翻译原则,遵循了麦都思的译经原则。他受自然启示神学思潮的影响,修订圣经时,使用中国道教术语。这些差异是二者主体性差异在圣经翻译中的再现。
[1] Lutz, J.. 2008.Opening China: Karl F.A. G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William B[M]. Grand Rapids: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 Morrison, A. 1839.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ert Morrison[M]. London: Longman.
[3] 陈梅.2006.外部力量与译者主体性的建构[J].外语与外语教学,(6):50-52
[4] 郭实猎.1839.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M].新加坡:新加坡坚夏书院.
[5] 马礼逊.1823.神天圣书[M].马六甲:马六甲英华书院.
[6] 马礼逊夫人.2004.马礼逊回忆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 阮玉慧.2009.论译者的主体性[J].安徽大学学报,(6):85-89.
[8] 苏精.2012.中文圣经第一次修订与争议[J].编译论丛,(5):8-19.
[9] 王玉樑.1995.论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与特点[J].天府新论, (6):34-38.
10] 查明建 田雨.2003.论译者主体性[J].中国翻译,(1):19-24.
Embodiments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Differences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A Case Study of Morrison’s and Karl August Gtzlaff’s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the Bible
Translators are the subject of translation activity. Their subjectivity can be divided into initiativity and passivity. The faith background of translator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The initiativity of translator is based on the faith background of the translator. In contrast, the faith background of the translator restricts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on the bible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based on the faith background of the translator is dialectical unification of initiativity and passivity. By the analysis of the faith background of Morrison and Karl August Gtzlaff.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e differences of their subjectivities based on their faith background, elucidaties the embodiments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Morrison and Karl August Gtzlaff Chinese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the Bible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and attitude of Bible translation as well as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Morrison; Karl August Gtzlaf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the faith background;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H059
A
2095-4891(2017)02-0092-05
本文系华中师范大学2016年中央高校科研专项项目“基于译者主体性的中文圣经韩译研究”(项目编号:CCNU15A060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陈艳敏,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语言学、翻译学
通讯地址:430079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152号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