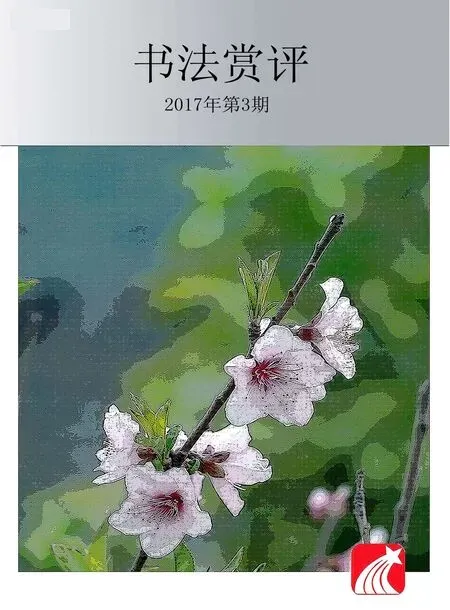从唐代敦煌写卷看佛教与章草的发展
■吕丽军
从唐代敦煌写卷看佛教与章草的发展
■吕丽军
章草兴盛于汉代,其与篆书、隶书、草书的关系密不可分,留传至今的汉代章草多为刻本,墨迹极少。当代许多学者都认为汉代是章草发展的高峰,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中有:“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至逸少变索靖法,稍以华胜。世传书《诸葛武侯对蜀昭烈语》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书也。萧景乔《出师颂》虽不迨魏晋人,然高古尚有遗风。自其书中观之,过正隶远矣。隋智永又变此法,至唐人绝罕为之,近世遂杳然无闻。盖去古既远,妙指弗传,几至于泯绝邪!然世岂无兹人,顾俗眼未之识耳。”[1]宋人黄伯思认为章草在唐代“绝罕为之”,因囿于材料所限,今人也是如此认识唐代章草。
19世纪末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文书的发现震惊了考古界、学术界,吸引了大批外国学者,如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橘瑞超等等。在汗牛充栋的敦煌文书中,有一批唐代佛教内容的章草墨迹长卷,如P.206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和《因明入正理论后疏》、S.2436《大乘起信论略述》、P.2141《大乘起信论略述》、S.2700《佛经疏释》、P.2118《妙法莲花经明决要述卷第四》、P.2176《妙法莲华经玄赞卷第六》,现在这些珍品早已流失国外。唐代以前文人书写章草墨迹如今能见到的有陆机《平复帖》和隋人《出师颂》,比起这两件作品及唐代几件不太出色的文人章草作品,敦煌的这批章草墨迹可谓是可以改写当前章草书法史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中国书法史的书写一向只注重名人名作,撰史者把名人当成了历代书法家的全部,把名人之作当成了书法史的全部,这在当前新资料不断发现的情况下显然是不科学的,我们应当把眼光投向更广阔的民间,投向新发现的资料,这样,对书法史的认识方能更为客观、更接近真相。就唐代章草来讲,现在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惟有建立在真实的、广泛的材料基础之上的研究,才是有说服力的。
一、P.206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和《因明入正理论后疏》
20世纪初,法国学者伯希和来到敦煌,带回法国汉文文献4000多件,藏文文献4000多件,还有部分粟特、龟兹、回鹘、西夏文文献,其中一件是《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和《因明入正理论后疏》,刊于《敦煌宝藏》第138册自164页至183页,二者是两个内容,写在一个长卷上,用一个编号P.2063,从书法的角度可以看作是一件作品。此卷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卷子总长1396.4厘米,高约29厘米,现存954行25842字,无书写时间。《后疏》首、尾不缺,共508行13364字,《略抄》前七行右下角呈直角形残损,现存446行共12478字。按照未残损的第八行来看,一行约25字,第一行损字最多,约为一行的三分之二,之后自右上向左下残损,到第七行残损约整行的四分之一,残损处右下角用法文标签标明伯希和的名字“Pelliot”,文字内容类别为汉文“chinois”,敦煌地名“Touen-houang”,及编号“2063”。《后疏》是重新接纸后开始书写,而所接前纸尾部尚有大面积空白,显然作者有意将两个内容分开,第一行为卷名及撰者,顶上横线书写“因明入正理论后疏”,中间空几字后书写“慈门寺沙门净眼续撰”,后面距下边线空约五字距离,此空字处有一圆形外文印章,内容不清。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唐代孙过庭《书谱》首行顶上边线书写“书谱卷上”中间空约三字后书写“吴郡孙过庭撰”顶下边线,《书谱》高26.5厘米,长900.8厘米,与P.2063同样为纸本,同样为多张纸拼接成为一个长卷。由此看来,长卷的第一行会说明卷名及作者信息,从《后疏》首行可知所书内容为“因明入正理论后疏”,撰者为“沙门净眼”。《书谱》内容的作者是孙过庭,书写《书谱》长卷的也是其本人,这就是《书谱》比其它历代书法作品更为宝贵的原因。《后疏》的作者与书写者均为僧人净眼,其书法水平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位章草大家,也不亚于唐代任何一位文人书家。《略抄》前部残损,从《后疏》与《略抄》的结字、用笔、气息、风格来看,二者均为“沙门净眼”书写,书写技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其书写心理状态如怀素书写《小草千字文》,已经忘却了法度的存在,一任自然,如苏轼之嬉笑怒骂皆为文章,如圣人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因明之学非中国本土所有,乃因佛教入华而随之而至,唐代因明学者窥基著有《入正理论疏》,释因明之义为:“因乃诸法之因,明乃彻法之智,乃至万法之因,明了无碍。”“因”是推理的依据,“明”就是知识。唐代文轨著有《因明入正理论疏》,其中对因明的功能作了精辟的解释:“因明之用也,为谤者而制之。”佛法高深,因理解层次不同会有不同解释,甚至不分是非、颠倒黑白,而因明的学问就是要“楷定正邪、褒贬是非、鉴照现比。”因明学是为维护佛法真理而设,是一种防御“谤者”的技术。因明学问就像是太阳普照大地,像霖雨灌溉土地。可见因明学者将因明学在佛学中的重要性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即“因明总摄诸论”。既然因明学如此至高无上,那它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和命运又如何呢?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学者玄奘,他即是小说《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玄奘于隋朝仁寿二年 (602年)出生,唐太宗贞观二年 (628年)不畏险阻远赴天竺取经,贞观十九年 (645年)正月回到长安,带回佛典526筴657部,其中取回因明学经卷36部,这只占取经总卷数的极小部分。这些经卷不是汉文,需译成中文后方可在中土传播,玄奘未作停歇又开始了长达十九年的译经事业,所译有关因明学最重要的一部是《因明正理门论本》,其作者汉译名为陈那,是印度人,生活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时期,80岁去世,陈那对印度逻辑学的发展居功至伟。但是此著作内涵太过高深,通常人不易读懂,陈那的学生商羯罗主写了《因明入正理论》,这对进一步学习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本》是一个阶梯,所以玄奘法师最先翻译的即是此入门之作。这是因明学的两部重要著作。玄奘在佛学界及民间的声望极高,门人众多,窥基、文轨、净眼皆为其学生,由此推断,净眼生活于初唐,则此P.206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和《因明入正理论后疏》也书于此时。根据玄奘众多门人寿命罕有跨过公元700年者,则净眼亦当在此列,其最晚不会超过武则天执政终止的706年,或者与初唐的孙过庭 (646-691)是同时代人,即生活于太宗高宗武后时期。仅因明学一科,门生根据玄奘的讲述并加入自己的理解所作著作就有几十种,其有影响力者有二人的疏释,即文轨《因明入正理论疏》《正理门论疏》。窥基《入正理论疏》《因明大疏》,尽管作“疏”者众,但因明学在唐代只如昙花一现,大多数著作还尚未流行传播就消失踪迹。静处于敦煌的净眼撰文并用章草书写的《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因明入正理论后疏》为至今为止所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因明学“疏”类著作,其章草水平的高度值得书法界重视。
二、P.2141《大乘起信论略述》
敦煌文书中,《大乘起信论略述》有多种写本,如北7250、S.2431、P.2051、S.964等等,各写本字体不一、字数不同、残损不一,但内容可以相互参照。编号为P.2141的《大乘起信论略述》风格最为独特,与《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和《因明入正理论后疏》一样,P.2141《大乘起信论略述》也是20世纪初由法国学者伯希和从敦煌带出中国的,残存889行,约二万四千字,未写明书写时间,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其图片刊于《敦煌宝藏》第138册第282页至311页,第一行为标题“大乘起信论略述序”和讲述者信息“沙门澄漪述”,第2至16行为序文,用行楷书写,第18行为正文标题“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和撰者信息“建康沙门昙旷撰”,按照“吴郡孙过庭撰”的书写习惯来理解,此卷的内容与书写者均为昙旷。昙旷生于建康,具体生卒年不详,这给我们确定P.2141《大乘起信论略述》的书写时间带来问题。但昙旷在其《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之首,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学术经历及撰写这些著述的根本目的,最有价值的是最后一句:“其时巨唐大历九年岁次 (子六月一日)。”“大历”为代宗李豫的年号,唐代宗在位自762年至779年共17年,用了三个年号,分别是广德、永泰、大历。762年四月十五日唐肃宗李亨改元“宝应”,762年四月宦官李辅国软禁张皇后,唐肃宗受惊吓而死。四月二十日,李豫于肃宗灵柩前即位,即位时仍沿用肃宗年号“宝应”,此年号共用一年又两个月,后于宝应二年七月改元“广德”。“广德”只用了一年多,是从763年七月至764年,“永泰”用了近两年,从765年正月至766年十一月,“大历”用了13年,从766年十一月至779年十二月为止。779年五月二十日李豫去世,李适即位,次年改元“建中”。因此,“大历九年”当是775年,昙旷在这一年能有此重要著述,则可以推理,昙旷主要生活于代宗时期,且其主要学术著作也成就于此时期,这为我们确定无书写时间的P.2141章草《大乘起信论略述》的时间提供了重要信息。763年二月,即宝应二年二月“安史之乱”已经被代宗平息,《新唐书》中评李豫:“代宗之朝,余孽犹在,平乱守成,盖亦中材之主也。”“安史之乱”后,国家走向衰败。佛教在中国的兴盛也正是由于政权更迭频繁、人人朝不保夕,由此促成了大量的写经、开窟、造像,帝王与百姓都希望在佛教当中找到精神慰藉。
昙旷出家后虔心佛法,在长安时专门研究《大乘起信论》和《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据澄漪序文,《大乘起信论》为印度马鸣所著,其出发点是为“发挥真谛。括众论绾群经。破二边协中道。作此正论以奖将来”。全文约一万一千字,是大乘佛教经典之作。扬州僧人智恺作《大乘起信论序》将此论的作用说得极为清楚:“夫起信论者,乃是至极大乘,甚深秘典。”澄漪序文中有:“先造广释后学赖焉。包含事理网罗邪正。”昙旷为了能让大众更好地学习《大乘起信论》,而特意写了《大乘起信论广释》以助理解,但是依然难懂,于是又写了更为简单明白的《大乘起信论略述》。自第18行至66行皆为纯正行楷,到67行前四字“门缘差别”开始突然转为标准章草,66行与67行书写风格泾渭分明,67行至154行笔画较轻,到155行首字开始笔画明显加重,且渐有不断厚重的趋势,笔沉墨饱,酣畅淋漓,这种状态保持了很久,一直到末尾的“次说解释分”,后又另起一行写了四行,笔画又明显变轻,且字体又成为与卷首相同的行楷,当中的一些字仍有前面的章草意味,之后为残损部分。与中间的章草对比,发现此卷上的行楷与章草之间有紧密联系,从笔迹来看为一人所写,即使字体不同,但用笔习惯是一致的,不能因为字体不一而认为是不同人所为。随情绪变化字体也在变化,这是中国许多经典书法作品的共同规律,王右军手札,颜真卿文稿全是如此,同时说明P.2141《大乘起信论略述》不是供养、做功德、传播之用。考查敦煌文书,以供养、传播为用者,即使是皇帝写经也一定是用一丝不苟的楷书以表尊敬,此卷或者只是一个草稿、笔记,留为自用,因而能够更多地流露情绪,不顾工拙,字体自由变化。这也可以反证此卷的书写者绝不是普通的以写经糊口的写字匠,而是一位书法修养极高的不知名的书法家,只是因官位不显或者视书艺为末技才不为后世所知。
编号为S.2436的《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在20世纪初由英国斯坦因从敦煌带至英国,现藏英国。此卷首尾完整,亦用章草书写,刊于《敦煌宝藏》第19册自411页至428页,据日本学者池田温先生的《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第307页,本卷尾题记为:“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宝应贰载玖月初于沙州龙兴寺写记”。为数不多的几位研究此卷的学者均将此卷书写时间定为代宗李豫的年号。“宝应”实为唐肃宗李亨的最后一个年号,李豫即位仍沿用“宝应”。“宝应贰载”即763年,宝应二年正月,经三代皇帝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平息,李豫于宝应二年七月改元“广德”。此题记作者书写“宝应贰载玖月”时,已无此年号,此时正值国家内忧外患,763年(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兵占领长安,代宗任命郭子仪为最高指挥反击吐番,半月之内成功收复长安。因战事或者信息传递不及时,边陲之地的年号与中央政权使用的年号不统一,这在敦煌遗书中也比较多见。虽然月份不对,但是可以确定S.2436《大乘起信论略述卷上》书写时间是在763年,昙旷书写《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的时间是“大历九年”即775年,二者书写时间相距只有12年,两个年号代宗都使用过,均属于代宗时期即762至779年,且一为沿用,时间较短,一为改元年号,所用时间较长,可推知P.2141《大乘起信论略述》也应当在同一时期,上下不会超出15年。二者书风相同,内容相近,也可推断为昙旷一人书写。
P.2063《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和《因明入正理论后疏》写于初唐,P.2141《大乘起信论略述》写于中唐,还有其它一些敦煌石室所出的唐代章草长卷,这些卷子书法风格相似,均为技法一流的章草,对他们的关注与研究可以改变当前书法界对唐代章草的认识。书法的发展与佛教的发展有紧密关系,历史上很多著名书法作品均为佛教题材,通过对唐代敦煌文书章草长卷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唐代佛教的兴衰有准确的把握,进而理解唐代章草发展的真正高度,而不是以名人的高度为绝对高度。
注释
[1]《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崔尔平,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07第一版.83页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书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