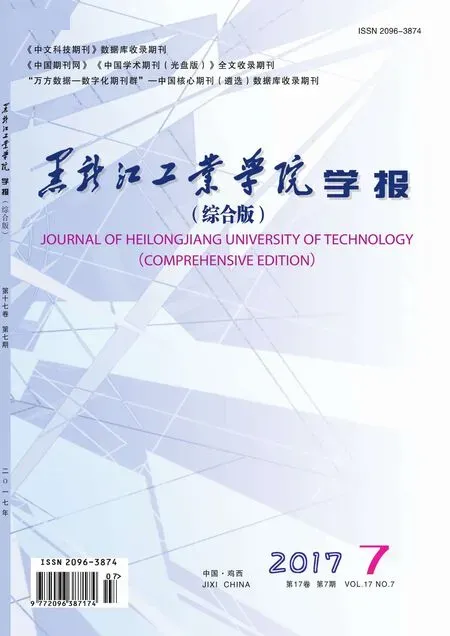温情中的乐教浸润
——论《诗经》“征妇”的社会特征
孔英民
(阜阳师范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温情中的乐教浸润
——论《诗经》“征妇”的社会特征
孔英民
(阜阳师范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西周到春秋时期,战争徭役不断,大批男子被征去服役,家中的女子被迫和征人长期分离,忍受别离之痛。对于统治者来说,只有获取征妇的支持才能安抚征人,保证战争政策的顺利推行。为此周统治者选择了上古传下来的乐教方式,编撰了融汇社会教化用意的诗歌来教化民众。受明确的社会教化目的的影响,《诗经》中征妇的两个突出特点:对丈夫的依恋、痛苦中的支持和坚持,都被赋予了丰富的社会教化内涵。《诗经》中征妇的社会现实特征反映了周王朝对战争政策推行的重视,也表明了周王朝礼乐教化国策实施的特色。
《诗经》;征妇;教化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周王朝虽然结束了商王朝的暴政,建立了对民众来说相对清明的社会制度,但是西周从建朝开始,叛乱和外族入侵一直就没停止。“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2]周公辅成王时,先平定了东夷部落的三监之乱。灭武庚、管蔡之后,为了天下安定,周公又继续东进征剿叛乱的东方诸国。不仅周公,周天子在战争上也身体力行,成王在位期间,录国谋反,成王亲自领兵出征,战争成为了周王朝政治中的主要内容,天子、诸侯、朝臣、民众、士卒,都和战争有脱不了的关系,没有哪个阶层能全然置之度外。对周统治者来说,战争关系国家安危、民族存亡,因此周王朝特别看重战争,在战争政策的推行上也是煞费苦心。
征妇为留守在家征人的妻子,西周到春秋时期,战争不断,征役不息,大批男子被征去服役,家中的女子被迫和征人长期分离,忍受别离之痛,在《诗经》中,思妇诗约有15首,表现征妇生活的作品就占了10首左右,由此可见当时征妇数量的众多,征妇独守家园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国家强迫男子服役,把有着琴瑟之好的夫妻硬生生地分开,很容易让民众生出不满之意,对国家战争政策产生抵触的情绪。如何安抚社会上千千万万的被迫分离的夫妻,《诗经》的编定者充分利用乐歌的易传播和被民众接受的特点,把反映征妇生活的作品收入诗集,一方面用这些作品呈现社会现实,让统治者体恤民情;另一方面把统治者的教化用意融入诗中,通过强化认识,让征妇形象发挥出来对社会的影响力,很自然的《诗经》中的征妇形象带有统治者明显的社会教化用意。
一、 对丈夫的依恋——家庭稳定不可或缺的因素
郑玄注《周礼· 小司徒》云:“有夫有妇, 然后为家。”[3]夫妻是家庭的基本构成单位,《礼记·昏义》强调:“男女有别, 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4]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要想家庭稳定,夫妻关系必须和谐。而夫妻关系和谐的前提,男权社会早已设定好,《说文》云:“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5]男权社会对“妇”字的设定是女子拿着扫帚做家务,认为这就是家庭中女子的位置,并且赋予了它和“服”相同的音义,认为女子服从才能保证家庭的稳定和谐,因此男权社会中妻子的符号是女子把自己作为男子的附属物,尊敬、爱恋男子,死心塌地地愿意为男子付出,《诗经》也是在潜移默化地宣传这种思想。
征妇是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她们的处境是自己的依靠——丈夫被国家征用,自己被迫和丈夫长期分离。古代女子出嫁从夫,结婚后的女子没有自我,在家庭中只是被动地履行男权社会结构赋予她们的义务,她们把自己和丈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把自己的感情和生存价值依靠全部倾注在丈夫身上,一切听任丈夫安排。而一旦丈夫不在身边时,需要独自面对生活的变化往往会让她们变得无所适从。《卫风·伯兮》中的女子因为悦己的男子不在身边,而整天一副“首如飞蓬”的慵懒神态;《召南·殷其雷》中的女子每天会不厌其烦地呼唤丈夫“归哉归哉”;《召南·草虫》中的女子会控制不住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自说自话“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未见君子,忧心惙惙”,“未见君子,我心伤悲”;《唐风·杕杜》中的女子因相思难以排遣,经常靠卜筮得来的征人归期临近的预测来化解自己的痛苦;《周南·卷耳》中的女子甚至因过度思念丈夫而出现了幻觉,清代方玉润言“念行役而知妇情之笃也”,[6]女子对丈夫的深情可鉴,而女子对丈夫依附的程度也可想而知。女子生活中反常的表现从本质上来看是女子生活中失去生命依靠的痛苦的折射,在《诗经》中,多数征妇因自己的主心骨不在身边而深陷相思的痛苦之中,《伯兮》中的女子因为相思而头痛、心痛、痛不欲生,丈夫走了之后,她的生活是无聊、苍白、痛苦的。《唐风·杕杜》中的女子在丈夫出征后,每天的生活状态是“伤止”“伤悲”“悲止”“忧心孔疚”而最终病倒,对这些女子来说,丈夫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丈夫主宰着她们的快乐和幸福,而一旦丈夫离开自己,自己的生活就失去了颜色,甚至无法正常维持下去。《诗经》中独守家园的征妇在丈夫离去之后生活是非常规的甚至有点空虚的,她们的特点表明了男权社会中男子在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婚姻中的女子除了男子,并没有可以独自开展生活的空间,从主题反映的角度来看,《诗经》中的征妇诗不约而同地集中笔墨刻画征妇在丈夫离去之后非常规的甚至有点空虚的生活,表现出的是编定者强化男权的意图。
男权社会结构使得婚姻中的女子过度依赖丈夫,她们选择了由丈夫来主宰自己的情感生活,喜怒哀乐全部系于丈夫一身。《诗经》中的征妇诗不单单是从别离影响了女性的生活,给女性带来痛苦这个角度来表现征妇对丈夫的依恋,《诗经》还往往通过女子对丈夫由衷的赞美和崇拜来表现征妇对丈夫的依恋。《卫风·伯兮》中的女子对伯有“伯兮朅兮,邦之桀兮”的由衷赞叹,《秦风·小戎》中的女子对“温其如玉”“温其在邑”“秩秩德音”的丈夫有着诉不尽的崇拜和喜爱,在丈夫离开家之后,她们有痛苦,但也有回忆丈夫的美好所引发的快乐,通过这些内容不难看出她们对丈夫的浓情蜜意,丈夫在他们心目中的高大、伟岸,但不论是痛苦还是快乐,女子都失去了自我的世界。这些作品对统治者而言有助于宣传丈夫主宰女子的情感生活、女子依附于丈夫的思想,这种思想符合家庭稳定的要求,同时也更符合周王朝统治者的教化政策、统治需求。
《诗经》所涉猎的诗歌产生的时间段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周初的统治者对于商王朝末期的动乱仍心有余悸,周朝建立以后外族入侵又接连不断,维护社会的稳定就很自然地成为了周统治者治天下的首要任务。“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7]“古之人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于其国, 先齐其家”。[4]古人普遍认为家国一体,赵炜总结古代的家国模式是“往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将家庭之伦理规则, 作为建构社会规范尤其是政治规范的模本, 将个体的道德建树、家庭的结构模式作为立国之本、治国之道, 所谓修齐以治平, 内圣而外王, 从而形成一种由家及国、即家即国、家国一体的政治模式。”[8]在古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家”的内涵在不断变化,但家国一体的思想在古代始终是一致的。西周以来,家国同构的观念就占据了主流,对于周朝的统治者来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先把社会的基础——家庭的问题解决好,诸侯之家和普通百姓之家的和谐稳定是天下有治的关键。《关雎》为 “风天下而正夫妇”[9]典范之作,《关雎》之所以被编撰者放在《诗经》之首,就是因为这首诗歌中的男女婚姻带有帮助稳定家庭的特点,表现了统治者对家庭稳定的看重。
对于统治者来说,他们需要表现女子对男子的依恋、丈夫主宰妻子生活和情感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中的女子没有自我,对丈夫只是服从、依恋,这有助于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的稳定,也体现出了统治阶级需要的男权意识,用这些作品去教化天下男女、治理社会,意义重大。《诗经》编定者不仅选录征妇类的民歌,而且对这些民歌进行一定的加工改造,侧重强化女子对男子的依恋,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统治阶级能更好地统治考虑。
二、 痛苦中的支持与坚持——国家大义的典范教育
朱熹《论语集注》言:“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10]朱熹认为诗歌应该内容纯正,发挥出教育作用。《诗经》中的征妇形象在编定者那里,另外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具有教化色彩浓厚的“义”。
国家的战事,君主的徭役,使夫妻别离成为了一种经常的现象,家中的女子要长期忍受与丈夫别离的痛苦和煎熬,从常规的心理来看,在家中独自承担养亲抚子重担的女子是最容易由别而生恨的,离愁和愤怒应该是思妇的正常情感表现,《诗经》之后的征妇诗注重客观展示征妇生活,如实反映征妇的情感世界,在这些诗歌中充斥的多是独挑家庭重担征妇的怨和恨。“蓬鬓荆钗世所稀, 布裙犹是嫁时衣。胡麻好种无人种, 正是归时底不归!” (葛鸦儿《怀良人》) “河湟戍卒去, 一半多不回。家有半菽食, 身为一囊灰。官吏按其籍, 伍中斥其妻。处处鲁人髽, 家家杞妇哀。” (皮日休《卒妻怨》)丈夫离家之后,家中的生产全留给了柔弱的妻子,而且最让女子难以忍受的是丈夫多年不归家,对于大多数惯于依靠丈夫满足全家衣食住行需要的妇女来说,丈夫离家的日子是一段恐怖难捱的日子,这些女子无所适从之后的生活是痛苦无奈之中度日如年地应对艰难的生计。尤其对于新婚的妻子来说,在自己的身份还没完全转换过来,还没适应新的生活时,就要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不论女子有多少修养,也难免不满和怨恨,这是新婚中女子遭遇丈夫被征时一个自然的反应,也是最真实的情感。“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张籍《征妇怨》)丈夫不在家的时候生计艰难,在担惊受怕的惶恐中度过,如果说这些还可以承受的话,丈夫永远回不来的噩耗,对依恋丈夫的女子来说则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征妇怨》中的两句独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失去丈夫后女子的艰难、无助、迷茫和痛苦,而这也是古代社会千千万万征妇可能会遭遇的情况。追根溯源,君主、战争是一切痛苦的根源,这些诗歌在展示征妇痛苦的同时也把矛头对准了朝廷和君主。
《诗经》中的征妇是略显反常的,在通常被看作是后世征妇诗源头的《诗经》征妇诗中很难看到征妇的不满与愤怒。《召南·殷其雷》中的女子渴望从役的丈夫快快归来,“归哉归哉”的呼喊表明她的不可遏抑的相思,但就是这样一个在痛苦煎熬中辗转的女子却出乎意料地对自己不归的丈夫表示理解,甚至对从役的丈夫有着一种鼓励,叮嘱他认真服役,“莫敢或遑”“莫敢遑息”“莫或遑处”,这些叙述显示出了女子的深明大义,对国家战争的肯定,对生活的坚持,对服役丈夫的支持。《毛诗序》言“《殷其雷》,劝其义也,召南之大夫,远行从政,不遑宁处,其室家能闵其勤劳,劝其义也。”[11]毛公赞美的出发点是女子懂事理、明大义,这也是《诗经》中征妇的一个突出的共性特点。《卫风·伯兮》中的女子在介绍自己的丈夫时“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满心的自豪,对服役不归的丈夫有着诸多的认可与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子的相思一天比一天深,一天比一天难排遣,以至于最后突发奇想,想要找到传说中的忘忧草,把它“言树之背”,以减轻自己的相思之痛,但一切努力徒劳无益,痛苦还是排遣不了,即使这样,女子对于导致自己痛苦的源头——君主和国家,没有半点的怨恨,而只是独自承担相思之痛,只是默默地在痛苦的煎熬中挣扎、坚持、期盼。
这些征妇超越常规的表现是反常情的,对于普通的女子来说,她们的思想很难普遍上升到舍家卫国的高度。对大多数的妇女来说,她们更看重的是自己的小家,自己和家人的长相厮守,不会轻易允许外在的因素毁掉自己的幸福,“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 。(张籍《征妇怨》)能和丈夫一起呵护小家,哪怕是吃糠咽菜妻子也愿意,这是古代依恋丈夫的女子对丈夫,对家庭的最基本的要求。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看,普通女子应是抵触丈夫被国家征用的,但《诗经》却不论征妇贵贱,不管其接受教育与否,把她们刻画成了一个个明大义的模范。《王风·君子于役》中的女子在夕阳西下,牛羊下坡时倚门远眺,期盼征人归来,这时的女子是落寞的、孤寂的,作品营造的凄清氛围凸显了她的悲伤、柔弱,但是诗歌结尾女子对男子的“苟无饥渴”的祝福使得这个妇女带有了深明大义的特点,形象瞬间高大起来。女子结尾的形象和其处境格格不入,也给读者一种割裂感。但对于统治者来说,毫无违和感,他们正是要通过把《诗经》中的征妇塑造成深明大义的典范来发挥征妇诗的社会教化作用。
更值得一提的是《秦风·小戎》中的女子,“无怨旷之志,则能闵念其君子”,[10]同别的女子一样,在丈夫走了之后百般思念丈夫,但思念中的她毫无别离后的悲悲切切,而是开朗地赞扬自己“秩秩德音”戎装出行的丈夫,表达自己的信任与支持,语言明朗、大气,而一个大义、大气的豪放女子也呈现在读者面前。《诗经》中的征妇多是这些高大的女子形象,她们泯小情于大义之中,为全天下的女子做出了很好的表率,统治者用她们的潜意识去影响天下女子的价值取向。
对于在外的征人来说,《诗经》中征妇的深明大义或多或少会对他们的价值观产生影响。《诗经》中的征妇对出征的丈夫没有埋怨,而只有崇拜、思念、支持、祝福,她们往往把国家大义置于一切之上,看起来都是一些通达、无私的女子。从接受的角度来看,在外的征人通过社会上传唱的诗歌了解到这种情况,在大义的感染下,会不甘示弱,自觉与女子看齐,甩掉牵挂家园、家人的包袱,以国家战事为重。征人的心思放在战场上,全心全意地为国家而战,这些有利于国家的兵役、劳役制度的推行,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进而帮助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10]周朝的统治者是聪明的,他们深谙诗在潜移默化中所发挥出的道德教化作用,通过征妇诗来宣传有利于统治的价值观念,《诗经》中征妇的“义” 鲜明地表现了周统治者用《诗经》教化民众、进行道德重塑的意图。
周王朝,战争徭役不断,而征人、征妇也成为了国家战争徭役政策的一部分,是国家战争徭役政策不可回避的一个内容。对于周朝统治者来说,在大量男子被征用的时候,如何安抚别离的夫妻,确保社会稳定、社会生产正常进行,这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因而《诗经》中出现了带有浓厚教化色彩,渗透着统治阶级教化思想又易传唱的征妇乐歌,周统治者意图通过对《诗经》中征妇社会现实特征的定位,达到自己教化的目的。《诗经》中的征妇乐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服务于统治阶级礼乐教化的性质身份,而这种性质身份也正是统治者奉《诗经》为神圣经典的主要原因。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861.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132,1206,1235,132,133.
[3]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77.
[4]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620,1592.
[5]许慎,著.臧克和,校订.说文解字新订[M].北京:中华书局,2002:816,695.
[6]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 中华书局, 1986:77.
[7]赵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92.
[8]赵炜.西周社会政治秩序的伦理建构[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139.
[9]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9:29.
[10]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75,414,76,220,51.
[11]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7.
Class No.:I222.2 Document Mark:A
(责任编辑:蔡雪岚)
Characteristics of Soldiers’ Wives Portrayed in “the Book of Songs”
Kong Yingmin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236041,China)
Because a large number of men were conscripted because of wars from Xi Zhou Dynasty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ir wives were left at home who felt lonely and painful. Soldiers’ wives in the Book of Songs were described as models by the ruling class because of their roles played at that time: their loyalty to their husbands was conducive to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their support and persistence to their husbands which reflected a national ethics. The roles of soldiers’ wives portrayed in “the Book of Songs” is served for the ruling class, and reflected the ritual indoctrination policy of the Zhou Dynasty.
“the Book of Poetry”; Soldiers’ wives; indoctrination
孔英民,副教授,阜阳师范学院;在读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朝鲜汉诗学研究”(项目编号:15YJC751024)阶段性成果;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东亚诗学视域中的韩国诗话”(项目编号:2014FXSK08)阶段性成果;阜阳师范学院教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中文师范生专业素质培养导向的古典诗歌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2015JYXM54)阶段性成果;安徽省教育厅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卓越文科人才教育培养计划”(项目编号:2016zjjh048)阶段性成果;安徽省教研项目“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质量的探索与研究”(项目编号:2014jyxm720)阶段性成果。
1672-6758(2017)07-0137-5
I222.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