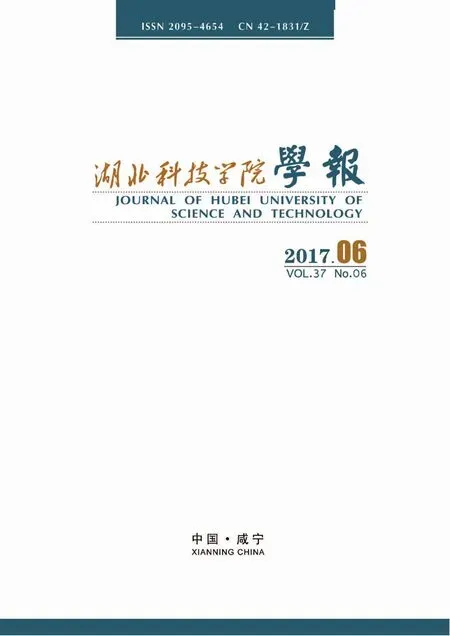西南乡村民间信仰的结构分析
赖智娟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西南乡村民间信仰的结构分析
赖智娟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传统上学者们对民间信仰的结构有不同的观点和认识,通过对南方各少数民族的分析,文章指出西南民间信仰的结构包括神系统、鬼系统、巫系统等三个明确区分又有机联系的领域,从一个独特角度解析了西南民间信仰的结构特点。这三种系统组成不同,功能不同,场所不同,民众对其信仰态度也不同。神系统的体系性较为明显,有相对区分的不同等级的神祗;鬼系统则是比较散乱,体系性弱;如果说前述两种系统都是虚幻的、抽象的,则巫系统就是现实存在的、具象的表现。
西南;民间信仰;结构
宗教信仰是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其有不同的结构认识。吕大吉先生较早地提出了“四要素”说,并称之为宗教要素的结构性分析。他指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客观存在具有一些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分为两类:一类是宗教的内在要素,其中有两部分:宗教的观念或思想;宗教的感情或体验。一类是宗教的外在要素,也有两部分:宗教的行为或活动;宗教的组织和制度。一个比较完整的成型的宗教,便是上述内外四种因素的综合。宗教的四种基本要素在宗教体系中有其一定的关系和结构。 即通称的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四个要素,长期以来对学界有较大影响。王雷泉先生提出“三层次”说,并形象地称之为苹果理论。最核心的是信仰核心,就是佛教的修证精神;第二个社会层次是果肉部分,佛法在世间,必须要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发生联系;第三个就是文化层次,佛教要守住信仰本位,若没有苹果核,就是个烂苹果。但没有苹果肉、苹果皮,佛法就没有办法在世间传播、生长起来。 即包括了精神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牟钟鉴先生则主张宗教“四层次”说(宗教信仰、宗教理论、宗教实体、宗教文化)。 借鉴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结合西南乡村民间信仰的现存实际状况,本文拟从神、鬼、巫三种不同视角探讨西南乡村民间信仰的结构。
关于民间信仰的分类,有学者倾向于将其分为大自然信仰、动植物信仰、图腾信仰、祖灵信仰, 或是自然崇拜、灵魂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等系统, 或是依照人类学领域的文化研究范式,将民间信仰划分为物质信仰与精神信仰。具体而言,西南地区民间信仰的多样性决定了民间信仰的结构可分为神系统、鬼系统、巫系统,这三种系统共同构成了西南民间信仰的结构。这三种系统是客观存在于西南地区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于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里和头脑认识中,但并不一定是具象地被划分为这三个部分,在少数民族的信仰中,这三种系统是错综复杂的、难以截然分开的有机体。
一、神系统
神是一种人为创造的偶像和崇拜对象,它首先在宗教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比如,在佛教中,神是佛教三宝之首。由于神的数量不同,逐渐演化成了一神教和多神教。当今三大世界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仔细观察在西南地区普遍存在、影响深远的佛教就会发现,佛教供奉佛祖释迦牟尼,这是佛教的至高无上的神。佛教是一神教,其最高崇拜对象是佛祖释迦牟尼。佛祖之下,依次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佛。佛教倡导度化,大乘佛教追求度人,小乘佛教追求自度,因此,佛理认为佛在心中,不仅有三世佛、三身佛及其他佛,而且人人皆可通过修炼而成佛。
第二层次是菩萨。菩萨因其证得的果位低于佛,他的职责就是作佛的助手,用佛的教义、宗旨解救芸芸众生,将他们度脱到极乐世界。菩萨的队伍很庞大,著名的有文殊、大势至、弥勒、金刚手、虚空藏、除盖障、普贤、地藏等“八大菩萨”,其中文殊、普贤、地藏和观世音又在汉化佛教中被尊为“四大菩萨”,并依托五台、峨眉、九华、普陀四大名山形成四大道场。
第三层次是罗汉集团。在大乘佛教中,罗汉是修证的第三等果位。而在小乘佛教里,就以罗汉为修行第一果位了。大乘对罗汉指明的任务是在世间流通佛法。早期跟随佛祖的四名弟子成为了四大罗汉,后来逐渐形成十六、十八乃至五百、八百罗汉等称呼。
佛教还包括许多法神祗,如由一天,二龙,三夜叉,四乾达婆,五阿修罗,六迦楼罗,七紧那罗,八摩呼罗迦组成的护法天龙八部;由大梵天王、帝释天、四大天王、大自在天、散脂大将、大辩才天、大功德天、韦陀天神、坚牢地神、菩提树神、鬼子母神、摩利支天、日宫天子、月官天子、娑竭罗龙、阎摩罗王组成的二十诸天、十大明王等。
不仅在佛教中存在等级分明的神祗系统,在西南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中,也存在类似的民间信仰神系统。
白族的本主信仰是一种多神崇拜体系。徐嘉瑞较早将白族本主分为十四类:(1)神帝;(2)神后;(3)山岳之神;(4)海神;(5)战神之家属;(6)战神;(7)日神;(8)狩猎之神;(9)医药之神;(10)帝王将相;(11)有功于民之神;(12)节义女神;(13)纯孝之神;(14)神之家属等。这是从本主的功能、属性来划分的。如果从本主的来源又可划分为九类:(1)自然崇拜与农业有关者;(2)英雄崇拜者;(3)有功于民者;(4)开国神话;(5)以死勤事者;(6)坚贞女神;(7)类似图腾者;(8)孝子;(9)神之眷属与亲戚。 而张文勋也是从本主的来源将本主分为六大类:与土著人物有关者、与巫教有关者、与佛教有关者、与儒教有关者、与道教有关者及与中原文化有关者。 上述分类有一定合理性,但从神祗等级来看,白族地区的白族信仰具有结构性特征。
本主信仰的最高层次是“神王”段宗牓。段宗牓又被称为“五百神王”,意为诸多本主神的最高统治者,是大理洱海地区地位最崇高的本主。供奉段宗牓的本主庙被称为“神都”,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二至二十五日,都要围绕“神都”为中心举办盛大的“绕三灵”祭祀活动。从“绕三灵”活动的过程来看,都明确反映了白族人民对鬼、神、巫等系统有明确的区分,同时又有机地将鬼、神、巫等系统整合入白族文化,“绕三灵”祭祀活动按照官方的说法分别经过崇圣寺(佛都)、庆洞村本主庙(神都)和河矣城村洱河神祠(仙都)三都。
本主信仰的第二层次是各个白族村寨的本主神。本主,白语为“武增”,意为本地主人,是佑护一方的神灵。村村皆有本主,寨寨皆有本主庙。白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大到五谷丰收、六畜兴旺、上梁起屋、婚丧嫁娶、出门远游、经商从业,小到清吉平安、逢年过节、学业工作等,事无巨细均到本主庙祭拜本主,希望得到本主的佑护及祝福。如此频繁的祭拜本主,导致人们认为一个村寨没有本主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即使是两个或几个村寨共有本主也是可以接受的,可见本主在白族生活中的重要性。
此外,白族信仰多元化,有许多神祗并不能归入白族的本主信仰体系,但也是白族的祭拜对象,如山神、土地、财神、雷公、电母、送子娘娘、痘二哥哥等,他们也分别扮演着特定的功能,对白族生活产生不同的影响。还有一些神祗,是白族信仰吸收了其它宗教或巫术从神祗,如佛教中的观音菩萨、夜叉,道教中的财神等。
从上可见,白族本主信仰具有一定的体系性,但是这种结构性特征并不鲜明,甚至是模糊的。严格来说,本主就是佑护一方的村寨最高神,甚至是“神王”段宗牓也更多只是一个虚衔,“神王”远不是白族本主的最高统治神。即使如此,还是可以界定白族本主信仰具有自己的神祗体系,只是不那么等级森严而已。
在其他许多民族中,还可以看到类似的神体系的存在。这些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所反映出来的神体系的共同特点是:(1)大多具有崇高地位的某种神祗,如天神、大神,他们往往受到极高的尊崇,地位明显高于其他神祗。(2)此外还具有名目繁多的各自神祗,不一而足。如四川凉山彝族认为天有天神,地有地神,日有日神,月有月神,举凡山川、雷电都有神在主宰。四川羌族有主神与次神之分,最为崇拜的是天神,其次是山神、火神、树神、羊神、水神、土地神、白石神等。云南怒族崇奉天神、水神、山神、树神、石神等。云南哈尼族把“奥玛”尊为最大的神和万物的创造者,“竜树神”则被认为是人类的保护神,此外还有山公、山母、家神等神祗。
二、鬼系统
提及“鬼”,人们总会有不同的异样感觉。从绝对无神论者的角度看,世间不存在鬼,鬼只是人们虚构出来的一种幻象。而在唯心论者看来,鬼是存在的。尤其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看,鬼就是人的灵魂,而古代先民原始宗教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灵魂,灵魂是不灭的。在医学、心理学、物理学、宗教学等不同领域,学者们对“鬼”的讨论方兴未艾。
西南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最初也是孕育于原始宗教,并发展为一个庞杂的体系。
表现形式之一是,认为众多的鬼信仰中,有一定的等级体系,并逐级发展出凌驾于其它鬼之上的地位尊崇的鬼。 景颇族认为,人是活的实体和灵魂的结合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灵魂(称为“南拉”)。人的死亡只是肉体的终结,而灵魂不死,只是从阳间转入到阴间,成为鬼魂。根据灵魂不灭的观念,景颇族社会产生了“万物有灵”的宗教世界观,认为世界万物与人一样都有灵魂,举凡山川草木、日月星辰等都有灵魂。
景颇族社会中的“鬼”形象体现出一定的系统性。景颇族把鬼灵分为“天鬼”、“地鬼”、“人鬼”三大类。
“天鬼”包括太阳鬼、月亮鬼、星辰鬼、风鬼、云鬼、雷鬼、雨鬼、闪电鬼、虹鬼等。这些鬼有统属关系,其中以太阳鬼最大,统管天上众鬼灵。
“地鬼”包括山鬼、水鬼、火鬼以及众多的动、植物鬼,如树鬼、谷堆鬼、韭菜鬼、豹子鬼、老熊鬼、鹰鬼等。其中以地魁鬼最大,称为“咪南”,统辖地上众鬼。
“人鬼”主要包括人死后其灵魂转变为能保护人的家鬼、家堂鬼、寨鬼。在村寨中,除各氏族、家庭供奉的家鬼外,作为统治者的“山官”专供“木代鬼”。“木代鬼”既是山官家的家鬼,又是天鬼之一,所以权力最大,专管一切家鬼及人鬼。传统上,只有地位最高的“董萨”(称为“斋瓦”)才有资格祭祀“木代鬼”,而一般的“董萨”可以祭祀除了“木代鬼”以外的其它宗教活动。景颇族的重要民族节日“目瑙纵歌”就是祭祀“木代”的盛大祭典。
此外,还相信自然界中有能使人头、脚、眼、耳疼痛的“纳干”鬼,有使人死于刀、枪、水、火、惊吓的砍头鬼“昆鬼”,有使人皮肤溃烂、让牲畜生病的“布坎”鬼和“述刚”鬼等等。围绕这些鬼的存在,有很多祭祀仪式。
类似的,虽然许多西南少数民族对鬼系统并没有明晰的层次划分,但都认为有地位较高的鬼存在,如天鬼是许多民族中常见的信仰对象。如傈僳族的天鬼(白加尼)、拉祜族的最高神是厄霞、德昂族的天神“困土戛”、水族的水神“霞神”、彝族的天神“格滋”等。
表现形式之二是,更多的西南少数民族将鬼概化为两大类,即善鬼和恶鬼。水族崇拜的鬼种类极多,有“好鬼”类,如“保财鬼”、“保命鬼”、“送子鬼”、“保子鬼”等,崇拜祖先也属于好鬼类。第二类是恶鬼类,如“拦路鬼”、“跌伤鬼”、“生疮鬼”等。纳西族称鬼为“弛垮梅”,也有善恶之分。阿昌族把给人们带来好处和利益的尊为善神,如山神、土地、猎神、“榜”等,而作祟加害于人的被称为恶鬼,如太阳鬼、月亮鬼、饿痨鬼、棒头鬼、毛虫鬼、藤子鬼、狼鬼等。
还应看到,许多民族中对鬼的认识并无系统性,是“杂乱无章”的。傈僳族把在冥冥中主宰一切自然现象的精灵称作“尼”,也就是通称的鬼。主要的鬼多达30余种,如白加尼(天鬼)、海夸尼(家鬼)、“结林尼”(路鬼)、米司尼(山鬼)、爱杜斯尼(水鬼)、屋豆尼(虎氏族鬼)、奥别尼(疮鬼)、密加尼(梦鬼)、疑甫尼(刺鬼)、爱起尼(慢性病鬼)、欠阿加(血鬼)、茹姑尼(病鬼)、曲尼(触犯鬼)、尼拍木尼(妇人鬼)等。另外,还有一些鬼则反映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在信仰上的反映,如勒墨鬼(白族鬼)、麽些鬼(纳西族鬼)、摆依鬼(傣族鬼)、怒族鬼、汉人鬼等。各种鬼灵掌管着人们的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的大灾小祸、生老病死都是各种鬼灵作祟的结果,因此,为了祛病免灾,不被疾病侵扰,傈僳族群众常常举行各种各样的祭祀鬼神的活动。佤族认为有水鬼“阿容”、风鬼“达务”、树鬼“达瓦”、掌管谷子生长的鬼称为“司欧布”、使人手、脚、筋骨疼痛的鬼“吉轴”、使人皮肤发痒的鬼“阿瑞”、夜间变为鸡、狗害人的鬼“司呢”、使人耳痛的鬼“阿入格”、使人耳聋的鬼“各若”等等。 白族社会中也有拦路鬼、水鬼、饿死鬼、冤死鬼等等。以上复杂的鬼信仰,并无系统性可言。
从上述鬼系统可以看出:首先,一般对鬼的认识往往是负面的形象,实际上,在许多西南少数民族的观念中,鬼也有善、恶之分,鬼并非都是“害人精”;其次,鬼信仰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对未知世界、未知事务的无法解释,遂寻求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来主宰;最后,鬼信仰不仅仅是一种初级的信仰诉求,在灵魂不灭观念牵引下,亡者被奉为祭祀对象,祖先崇拜兴起,从鬼信仰到祖先崇拜,使得民间信仰不再是无法捉摸的,而已知的现实生活与未知的灵魂世界通过血缘观念联系为一体,发展成为祖先崇拜。
三、巫系统
“巫”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为复杂的一个名词。 巫系统的重要组成包括巫师与巫术。学界也常将巫师称为卡里斯马(charisma),原意为“神圣的天赋”,来自早期基督教,初时指得到神帮助的超常人物,引申为具有非凡魅力和能力的领袖,此处指民间信仰中的巫师。巫师则包含了为达到特定目的而举行的仪轨、仪式、禁忌、占卜等行为。童恩正先生深入探讨了中国古代的巫,指出与巫相关的三类宗教人员的不同特点:巫师是指原始宗教中的非专业神职人员,男女两性都有,具有交通神灵和要求神灵为人类服务的能力,如占卜、治病、祓禳、祈福等。巫师与鬼神的交通,基本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请神附身,另外一种是巫师的灵魂可以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找到鬼神;法师一般由男性充当,其工作多为业余性质,但亦有专职者。他们所具备的超自然的能力来自他人的传授,而其害人或致人于死的手段主要为“法术”,包括符咒、下毒、放蛊、利用仇人的毛发、指甲、衣物等行厌胜之术;祭司是专职的宗教人员,祭司不能自封,其知识亦非神灵所授,而需要系统地学习。他所担任的神职也必须得到宗教团体的正式认可。一般而言,他们本身并没有像巫师或法师那样的超自然的能力。当然,实际情况中,以上三种角色往往相互叠加。
西南乡村民间信仰中包括许多巫术信仰、禁忌,构成为一个巫系统。从巫师层面而言,大致可以被概括为“一玛二巴,三师四萨”的巫师组成结构。这是就西南乡村民间信仰中巫师的主要类型而划分,并不存在排名先后、层次高低的区别,毕竟从文化相对论而言,每种文化形态都是独特的,并无高下之别。
第一类是“玛”。如彝族的“毕摩”,傣族的”“波摩”、“咪摩”,哈尼族中,“儒玛”负责祭祀寨神,“贝玛”、“尼玛”负责祭祀竜神。布朗族的“白摩”,怒族的“尼玛”,基诺族的“卓巴”、“卓生”、“白腊”等。
第二类是“巴”。如纳西族的“东巴”,傈僳族的“必扒”、“尼扒”,拉祜族的“魔巴”,哈尼族祭祀竜神的巫师有的也被称为“龙巴”,还有等级较高的“龙巴头”。
第三类是“师”。如土家族的“土老师”,苗族的“苗老师”,白族的“道师”,部分白族地区的“三元老师”,羌族的“端公”,布依族的“魔公”。水族、侗族、仡佬族均称为“鬼师”。
第四类是“萨”。如景颇族的董萨,独龙族的纳木萨、夺木萨。
从以上四种不同称谓的巫师人员来看,首先,不同民族的巫师有不同的称谓;“玛”、“摩”、“巴”、“师”、“公”、“萨”等均为某一类特定人员的称谓,这种称谓不同主要是不同语境下的产物,是不同民族语言的译称。其次,巫师往往有男女之分,各司其职。中国古代施术者女称巫,男称觋。
傣族社会中,不仅全民信仰小乘佛教,巫术信仰也非常普遍。傣族女巫称为“咩莫”或“雅莫”,男巫称为“波莫”,“莫”有智者、知识渊博等涵义,“波”则是指父亲,由此可见巫师在傣族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傣族巫师相互之间是没有明确的统属关系的,甲寨的巫师只能祭祀甲寨的寨神,乙寨的巫师只能祭祀乙寨的寨神,各司其职,不能替代。
巫师被认为具有通神的功能,常常扮演人神之间的中介,通过鼓、音乐和歌舞进入精神的另外一个境界,通过鼓、舞、音乐固定节奏、频率影响人的脑电波,集中注意力,转入另外一种精神世界, 傣族社会中的巫师也被认为可以交会人神,根本的原因在于巫师波莫和寨神、勐神之间具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人们经常说:“不是××当巫师,神就不高兴了。”“不是××献神,寨神就不吃”。因此,傣族巫师是世代沿袭的。
民国初年,今天的云南元江曼弄寨,地方不太平,寨里的巫师远走他乡。恰巧,这年庄稼长不好,人畜多病。人们说这是巫师离开了寨子的缘故。不久,打听到巫师停留在新平县的嘎洒,于是寨老们议定,派专人牵上高头大马把巫师接回寨子。此后,这个巫师及其子孙世代在该寨任职,一直到今天,其直系后裔白云亮就是曼弄寨的巫师。类似的,在云南瑞丽市弄岛乡的芒隘寨,寨中的巫师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逃到缅甸,到20世纪80年代,当寨中又要恢复祭寨神的活动时,便一致议定要去把波莫找回来。可是,当寨上的人前往缅甸寻到波莫家的时候,波莫早就已经去世,于是,他们接回了波莫二十多岁的儿子噶喊,集体出力帮助他建了房,由嘎喊继承了芒隘寨波莫的职位。
彝族的巫术繁复多样,以占卜为例,常见有:羊骨卜,选用羊胛骨,先用手指将胛骨摩擦,再用火烧,然后根据胛骨裂纹的长短以定吉凶。裂纹分为上下左右四纹,左为自己,右为鬼怪,上为外方,下为内方。卜法原理和古代商周时期用龟甲、兽骨占卜是相同的。
打木刻,毕摩口中念经,同时在木刻两侧以刀锯成若干锯齿,并在当中划一长道。上方为鬼怪,下方为自己,奇数为吉,偶数为凶。在作战或出行前,多用此法。
鸡卜,在彝族占卜中非常重要。如看鸡头卜,是将鸡头盖骨的皮撕开,看头盖骨颜色,洁白为吉,有红点为不好,有黑点要死人。又如看鸡头的方向以定吉凶,将鸡打死后扔出户外,鸡头朝外则为吉,朝内则为凶。还有看鸡腿骨或鸡舌头等卜法。彝族谚语谓“看鸡腿骨要看叉,听话要听关键处。看鸡舌要看尖,听话要听关键处”等,说明鸡卜在彝族生活中的重要性。
鸡蛋卜,常用于占卜疾病或家门亲戚外出未归,不知其生死存亡等事宜。方法是先将鸡蛋放在病人或外出人的衣服上摩擦,然后在清水碗中打开,看蛋中的星点是人形或是鬼形,以定吉凶。
此外,还有苦胆卜等。
从上述可知,神系统、鬼系统、巫系统构成了西南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结构。这三种系统组成不同,功能不同,场所不同,民众对其信仰态度也不同。
神系统的体系性较为明显,有相对区分的不同等级的神祗,但这种体系性相对于佛教等制度性宗教而言,其体系性是模糊的、不确定的。神系统往往居于民间信仰中较高的层次,神通常是善的、好的,因而成为较多信众信仰的偶像,神所发挥的功能涉及范围比较广泛,或者是一个区域,甚至造福整个民族。神祗也有较为固定的庙宇、建筑等场所,大到本主庙、山神土地庙、城隍庙等,小到神龛。
鬼系统则是比较散乱的,没有体系性,有路鬼、山鬼、水鬼以及各种各样的病鬼和名目繁多的孤魂野鬼。俗谓“敬鬼神而远之”,实际上,对神系统更多体现出来的是敬仰,而对鬼系统体现出来的则是畏惧,避之唯恐不及,因此产生了诸多禁忌。鬼系统通常涉及的对象是个体和家庭,所以日常生活中的琐事等,人们往往认为是恶鬼、厉鬼作祟,于是要压鬼、镇鬼,鬼信仰的场所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常常是房角地头、荒郊野外等处进行。
巫系统与前述神系统和鬼系统又有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前述两种系统都是虚幻的、抽象的,则巫系统就是现实存在的、具象的表现。在原始社会里,巫是氏族的精神支柱,是智慧的化身,是灵魂世界和现实世界一切疑难的解答者。 巫系统在民间信仰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通常认为巫师具有通神的能力。人们要将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祷告神祗,诉诸鬼神,祈福消灾避难,以求得心灵安慰和思想解脱。然而,种种祭祀通过何种途径得以实现呢?答案就是通过巫师。在此,巫师扮演了神人交会的中介,巫师通过各种祭祀仪式将人的诉求传给鬼神,又将鬼神的信息反馈给信众,从而贯穿民间信仰,使西南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成为一个既有起点又有终点的完整过程;既解决了人神不能交会的尴尬,又实现了人的精神诉求;从虚幻的鬼神系统,到具有特异通神能力、似真似幻的巫师系统,再到现实中的日常生活,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日渐清晰,不再虚幻,这也正是民间信仰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广泛信仰的深层次原因。
[1] 覃光广,等.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2] 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3] 路遥.民间信仰与社会生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 陈建勤.当代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3.
[5] 朱德普.傣族的巫师及其历史演变[J].民族研究,1994,(2).
[6] 童恩正.中国古代的巫[J].中国社会科学,1995,(5).
[7] 陶思炎,铃木岩弓.论民间信仰的研究体系[J].世界宗教研究,1999,(1).
[8] 朱和双,李金莲.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性禁忌及其民间信仰[J].宗教学研究,2005,(1).
[9] 黄彩文.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以双江县一个布朗族村寨的祭竜仪式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10] 王守恩.论民间信仰的神灵体系[J].世界宗教研究,2009,(4).
2095-4654(2017)06-0001-05
2017-07-29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子项目“西南乡村基层社会民间信仰与社会控制研究”(13JZD027)阶段性成果
B916
A
熊 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