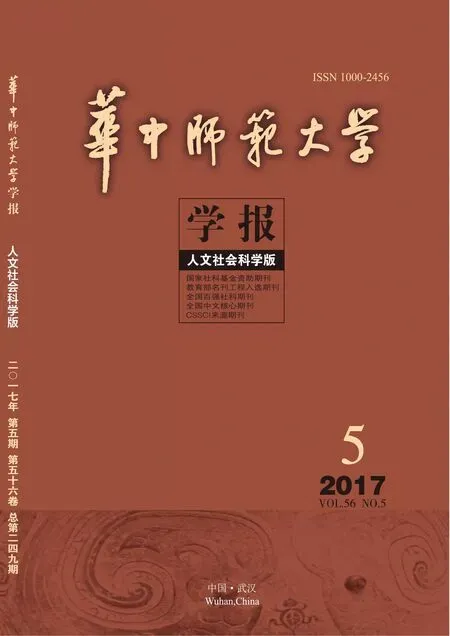海德格尔媒介本体论思想阐述
张三夕 李明勇,2
(1.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2.贵州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18)
海德格尔媒介本体论思想阐述
张三夕1李明勇1,2
(1.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2.贵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贵州贵阳550018)
在西方哲学史上,海德格尔第一次将媒介纳入到哲学研究的领域。他在存在论哲学思想基础之上区分了存在与存在者,突出了此在与世界之间的距离特征,并对此在与世界进行联系的技术媒介进行了本体性追问。他的这一媒介本体论思想与以往的媒介功能主义有别,从媒介生成论视角对媒介进行形而上分析,开启了媒介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对反思当今的媒介功能主义所存在的弊端大有裨益。
海德格尔; 技术媒介; 媒介本体论; 媒介功能主义
以往人们主要是从哲学(包括艺术哲学)的视角对海德格尔进行研究,很少有人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其进行审视。然而,当代传媒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却开始注意到海德格尔的媒介思想理论,在《走向媒介本体论》一文的摘要中认为,在西方哲学中,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智者,还是阿奎那、笛卡尔、费希特、康德等大哲学家,都没有对作品自身的技术媒介给予足够的关注,“只是到了海德格尔时期,对技术媒介的哲学意识才第一次出现,数学与媒介的连接、媒介与本体论的连接也以更精确的术语而得到阐明”。①由此不难看出,海德格尔是最早将技术媒介作本体论思考的哲学家,无疑对媒介本体论有着创建之功。但基特勒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大课题,即海德格尔的技术媒介本体论思想是如何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具体体现出来的?以及他的技术媒介本体论思想给我们今天的媒介研究有何启示?为此,本文通过海德格尔一系列的重要哲学著作分析海德格尔的媒介本体论思想,并探讨其在当今传播学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
一、媒介本体论的哲学基础
基特勒在对西方哲学史的考察中发现,哲学家们对哲学自身媒介的忽视起源于亚里士多德。亚氏的本体论只涉及各种事物的内容和形式,却不去研究各事物之间在时间和空间的相互联系。只有到了海德格尔那里,他通过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区分,使“距离”成为世界存在的特征。此时,“技术媒介已经取代了心理媒介。在其终结和毁灭之时,本体论也就成了距离、传播和媒介的本体论”。②也就是说,在海德格尔存在理论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之下所提出的“距离”,已经不再将技术媒介作为感知领域进行考察,而是从本体论意义上进行思考。
通过基特勒对海德格尔技术媒介的本体论思想阐述来看,存在论哲学成了媒介本体论思想的哲学基础。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首先是对存在的追问,即存在之“思”。他认为存在问题是一个如今被遗忘的问题,这种遗忘从柏拉图就开始,因此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强调,“追问存在的意义的问题第一次在哲学史上被特地作为问题提出来并得到发展了。”③他之所以如此这般的说,就在于传统形而上学所探讨的并非是存在,而是存在者。存在不同于存在者,现象界的实存事物都是存在者,而存在是确定存在者为存在者的那种东西,是使一切存在者成其为自身的先决条件。但“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④存在就体现在存在者中。存在普遍存在,却又难以定义。存在既不能用定义方法从更高的概念导出,又不能用较低级的概念来表现,只能通过此在(人)去领悟。因此,它不属于知识学和科学的研究范围,而属于哲学的研究范畴。海德格尔这一思想,可谓是对传统西方哲学的颠覆。正是这一颠覆,“距离”才成了这个世界的特征,对媒介的存在之“思”才可能成为媒介的本体论探讨。
如何理解这里所说的“距离”?陈静将其理解为“一种媒介所起到的关联性作用”。⑤这种理解并不错,但只是说出了结果,没有道出原因。因为必然先有距离,才可能有媒介所引起的关联作用。海德格尔对距离的阐述主要是通过存在者的空间性表现出来的。在《存在与时间》中,空间性是此在的基本属性,因为此在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在世”,即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在者,这里的“在之中”就意味着存在者具有一种空间属性。空间性是由此在生发的,也由此在扩展。此在的“在世”忙于与世内其他存在者打交道。与此在最近的存在者是“上到手头”的东西,即上手的存在者或用具。“在此在中有一种求近的本质倾向”,⑥也就是说将其他存在者带到此在近处。这里的近处不是根据距离来衡量的,而是通过寻视“算计着”的操作和使用得到调节。此在通过用具寻视着的规定方向与周围世界打交道,此在的寻视同时可以通过用具的定向来确定近处的东西,从而构成了一种场域,一个由“此在”展开的因缘整体性空间。
海德格尔所说的空间性中的距离不等同于物理学意义上的距离,所说的“近”是指“处在首先上手的东西的环围之中”,⑦并不是与身体相处得最近。作为媒介的用具虽然是“最切近”的东西,但往往人们并不把它作为最近的存在者。海德格尔举了例子进行说明。眼镜虽然就在人的鼻梁之上,但它并不比墙上的画要近,往往人们最后才把它找出来。作为最切近此在的用具本身只是充当了连接人与周围世界之间距离的媒介。人与外部世界具有了一定的空间距离之后,作为用具的媒介才起到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作用。
海德格尔所说的距离不仅表现此在与外部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表现此在与艺术世界之间的关联。艺术世界是一个意义世界,人们并不是直接与艺术世界中的真理发生关系,而是通过艺术作品的物因素才能达到艺术世界。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他首先强调了艺术作品的物因素,“因为作品是被创造的,而创作需要一种它籍以创造的媒介物”⑧,例如建筑艺术中的石材、语言艺术中的言语等。就艺术作品的物因素来看,与纯然物并无二致。一幅画挂在墙上,就像一支猎枪或一顶帽子挂在墙上。艺术作品之所以是艺术作品,它不只是一种被创作的物,而且还意味着“别的什么”。“作品中唯一的使这别的东西敞开出来,并把这别的东西结合起来的东西,仍然是作品的物因素。”⑨因此,我们只能通过艺术作品的物因素这一媒介物去把握这“别的东西”。在梵·高的《农鞋》中,我们通过对这双农鞋的欣赏把握了那妇女的世界。因此,艺术作品的物因素在人与艺术世界之间起到了关联性作用。
二、媒介本体论的具体呈现
海德格尔在存在论哲学基础之上,通过此在的空间性来突出人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作为连接人与世界的技术媒介,也只是一种存在者,在它背后还有更为本源性的存在。在存在论哲学中,对技术媒介的存在分析,成了海德格尔技术媒介本体论思想的具体呈现。
(一)器具的存在分析
器具作为此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技术媒介,是理解存在的“前课题”,成为海德格尔哲学中一个较为重要的概念。在早期的著作《存在与时间》中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不是一种认识关系,而是与世界打交道。此在在日常操劳的打交道中切近照面的存在者就是用具或器具。这里所说的照面,也就是一种关联性,存在者进入到此在的生活世界中并与此在发生某种关联性。器具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用具,成为与人最近的存在者,正是这用具将人与外部的生活世界联系了起来。那么器具的存在何以显现出来呢?在海德格尔看来,器具的存在不是通过我们的凝注观察,而是通过在打交道的过程中器具所具有的上手性自显出来的。如对锤子这一器具越少瞠目凝视,用它用得越是起劲,对它的关系也就变得越原始,它也就越发昭然若揭地作为它所是的东西来照面,这种状态被海德格尔称为“当下上手状态”⑩。也就是说,用具只有在使用的过程中而不是摆在某个地方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上手性。
到了《艺术作品的本源》那里,海德格尔在批判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对物之物性的批判之后,将物分为纯然物、器具和艺术作品三类。由于器具有一种特殊的优先地位,即介于纯然物和艺术作品之间,从而成为优先考察的对象。器具作为一种存在者,它是通过人的制作而存在的,并以它的有用性与人发生关联,它的存在就体现在有用性中。田间的农妇穿着鞋,只有在这里,鞋才存在。与此相反,如果把鞋设置为一个空空无人的对象,我们就无法寻找到鞋的存在。器具的有用性是最为根本的器具存在吗?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有用性还不是最为根本的本源,它根植于器具的“可靠性”。什么是可靠性?即“器具之本质存在的充实”,也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器具产生的依赖或者信任,越是上手的器具人们越是依赖它和信任它,从而产生一种人与器具的亲切关系。因此,有用性只不过是可靠性的本质后果,没有可靠性就没有有用性,器具存在就存在于可靠性之中。器具之器具存在的获得不是对一双实物鞋的描绘和解释,不是通过制鞋工序的讲述,而是对梵·高一幅画的观赏所得。在梵·高所画的农鞋的作品里,农鞋在作品所筹划的世界里得以展现出来,“艺术作品使我们懂得了真正的鞋具是什么”。为此,海德格尔进一步追问作为艺术作品物因素的本体性存在。
(二)艺术作品物因素的存在之“思”
海德格尔在探讨艺术作品的本源时,首先否定了传统那种艺术家是艺术作品的本源、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的本源的思想,认为艺术作品的本源就是艺术。艺术就体现在艺术作品中。关于什么是艺术的问题只能通过对艺术作品进行考察才能获得答案。因此他采用现象学的方法,直接面向艺术作品。所有的艺术作品首先是具有物因素,亦即一种符号或象征的媒介物。艺术作品的物因素,并非是指向那些现存的质料,而是指“一切涌现者的返身隐匿之所,并且是作为这样一种涌现把一切涌现者返身隐匿起来”,海德格尔称之为“大地”。在涌现者中,“大地”显身为庇护者。
“大地”何以显现出来?那就是在大地与世界的争执中显现出来。大地与世界是一种对立的统一体,世界立身于大地,但由于世界的本质是一种自行敞开,不能容忍大地的任何锁闭,从而试图超升于大地。但是大地是庇护者,本质是自行锁闭,它总是倾向于把世界摄入到自身并扣留在自身之中,于是两者之间就产生了一种“争执”。争执的本质不是分歧、争辩,而是一种亲密性,因为两者之间既有冲突也有内在统一性。在本质性的争执中,争执者双方相互进入其本质的自我确立中,大地的存在就体现在争执的实现过程中。作品建立一个世界的同时,也制造了一个大地。例如古希腊神庙,它那坚固而耸立的圆柱式门厅开启了一个神圣的领域,使神的形象获得了在场。同时也将与此关联的诞生与死亡、灾祸与福祉、胜利与耻辱、忍耐和堕落聚集在自身的周围,获得人类命运的形态。当神庙把这世界重新置回到神庙的石柱时,这种物质材料也就获得了在场。用具制造使自己的质料消失在有用性中,而作品因创造一个世界,它不但没有使质料消失,反倒使质料得以凸显。之所以大地能在这一争执的实现过程中显现出来,就在于大地与世界的争执背后还有一对更为原始的争执,那就是澄明和遮蔽的争执。澄明与遮蔽的争执打开了一个敞开领域,存在者被带到这一敞开领域,它们就获得了去蔽,自身的本体性存在得以显现出来。“大地”作为争执的一方,被带入到澄明与遮蔽的原始争执中,真理便随之发生,“大地”也就获得了它的本体性存在。“只要真理作为澄明与遮蔽的原始争执而发生,大地就一味地通过世界而凸显,世界就一味地建基于大地。”
(三)“技术”的本质追问
海德格尔在对器具的存在和艺术作品的物因素的分析之后,最终落实到了对技术的本质追问。他首先否定了传统将技术视为合目的的工具和人类行为的观点,因为技术的工具性并没有揭示出技术的本质,工具性本身也应有所属。为此,海德格尔首先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了技术。在希腊文中,“技术”一词(τεχμκσγ)首先代表了“τεχγη”(技艺)所包含的一切,既代表手工艺,也代表精湛的艺术,因此是一种“生产”。其次,“技术”还是一种“知道”(Wissen),即“对在场者之为这样一个在场者的觉知(Vernehmen)”,是存在者的解蔽。现代技术也是一种解蔽吗?“它也是一种解蔽。唯当我们让目光停留在这一基本特征上,现代技术的新特质才会显示给我们。”只不过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不是技艺中的“生产”,而是一种“促逼”,是对自然提出蛮横的要求,要求自然能够提供和储存的能量。现代技术不仅“促逼”自然,而且还“促逼”着人,把人聚集到摆置着自然的订制(Bestellen)中。
是什么促逼着人,并把人聚集于订制之中呢?那就是“座架”。什么是“座架”?在《艺术作品的本源》后记中解释为“它是生产之聚集,是让显露出来而进入作为轮廓(περαδ)的裂隙中的聚集。”也就是说“座架”是将被生产的东西聚集为“一”,并将这个“一”带入到无蔽领域、带入在场者中。后来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进一步解释了“座架”。“座架”是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促逼着人,使人以订制的方式把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来解蔽。因此,“座架”不是什么技术因素,而是一种解蔽方式,现代技术的本质就居于“座架”之中。“座架”从何而来?来自于解蔽之命运。所谓命运,就是给人指出的解蔽道路。技术的本质居于座架之中,座架的支配作用又归于命运,因此,命运为人们所指引的解蔽之路可能就会出现危险,即人们一味地去追逐、推动在订制中被解蔽的东西,并且从那里采取一切尺度。这时,作为解蔽的“座架”不仅遮蔽着前一种解蔽方式即产出,而且也遮蔽着解蔽自身,人也随之失去了自由的本质。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危险也不是厄运,只有在危险逼近的时候,人们才能听到“座架”的呼救,才能经验到人自身与存在的归属关系。那么这种危险是否可以救渡?“救渡乃植根并发育于技术之本质中”。如果我们不将技术经验为一种工具,而将其视为一种真理的守护者,那么救渡就可以升起。技术作为真理的守护者只能在艺术之中才可能实现,因为艺术既与技术有亲缘关系,又与技术之本质有根本的不同。
三、媒介本体论思想的当下价值
通过对海德格尔技术媒介本体论思想的阐述不难明白,技术媒介本体论是对技术媒介本身的哲学思考,去发现隐藏在媒介背后的东西,从而获得媒介之所是的本质规定性。媒介本体论研究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除了基特勒之外,德国的另一位媒介学家鲍里斯·格罗伊斯认为:“每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媒介理论,如果它还对得起这个称号,必须就媒介本体论问题来追问亚媒介空间的性质,并以此超越了停留在媒介表面上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空谈。”格罗伊斯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在强调媒介本体论对当今媒介研究的重要作用。海德格尔的技术媒介本体论对今天的传播学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一)有助于对媒介自身的本质性思考
媒介在当今的传播学、新闻学著作中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是运用得比较多的一个词,但同时也是一个极为混乱的一个概念。正如美国丹尼尔·切特罗姆在《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一书的后记所言,“曾经围绕着传播(communication)这个词所产生的语义学上的那种模糊现在又似乎围绕着媒介(media)这个越来越含混的词而重新出现。”之所以媒介一词越来越含混,就在于人们并没有把握和获得媒介的本质规定性,从而媒介在不同的场域呈现不同的意义。从词源学来看,媒介的英文为“media”,是“medium”的复数形式,源于拉丁语的“medius”,具有“中间”的意思。它具有联系各事物之间的介质之意,也就是说,凡是使两种存在物发生联系的中介物都可以称为媒介。但在传播学领域内,媒介必然与信息相关,它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渠道、技术或工具,有时候可以指称例如电视台、广播站等这类信息传播机构。在媒介环境学派那里,更多的是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待媒介一词,如在麦克卢汉更是将服装、住宅、道路、货币、时钟、汽车、飞机、打字机等都视为媒介。然而在经验学派那里,他们的媒介主要是指向传播媒介,对媒介的分析主要涉及的是书籍、报纸、广播、电视、计算机之类的大众媒介,有时也指向媒体。如施拉姆就认为,大众媒介“可能是复制和发送信息符号的机器,也可能是报社或电台之类的传播机构”。
从以上传播学家们使用媒介一词所指向的内涵不难看出,媒介一词涵盖了传播媒介、媒介技术、媒体,从而导致媒介内涵的模糊、混乱。海德格尔的技术媒介本体论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即必须要弄清楚媒介之所以成为媒介自身的本质规定性,才有可能避免这种混乱。媒介只是一种现象,一种现实的存在者,在它的背后必然有某种东西使媒介成了自身。只有我们把握了隐藏在媒介背后的使媒介成为其自身的那种东西,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媒介的内涵,同时在使用这一词的时候就会更加小心谨慎。
(二)开创了一种新的媒介研究领域
媒介研究是传播学的重要研究部类,与传播学的发展相伴随行。媒介研究在传播学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环境学派三大流派中都是重要的研究领域。但三者之间对媒介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即经验学派主要是研究媒介内容对社会、个人的积极影响;批判学派则是指出媒介内容对社会和个人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学派则从媒介自身发展变化所起的社会作用方面进行研究。如果我们将媒介的发展过程归纳为媒介生成——媒介——媒介效果这三级的话,以上传播学的三大流派对媒介的研究主要是对媒介和媒介效果这两级进行了研究,而更为原始的媒介生成这一级却处在媒介研究的边缘状态。
海德格尔的技术媒介本体论思想为我们打开了媒介生成这一媒介研究领域,拓展了当前的媒介研究空间。在海德格尔技术媒介本体论思想中,对器具、艺术作品的物因素以及技术的本体论追问都是从生成过程的视角对其进行本体论追问的。从生存论的视角来考察媒介,将媒介与人的存在状态联系起来,从而使媒介自身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理论基础。这与当今的媒介研究只注重媒介自身和媒介效果具有本质的差别,也是当今媒介研究理论停滞不前的原因所在。因此,媒介生成论的研究是媒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更为本源性的研究,只有将这一领域纳入到媒介研究之中,媒介研究才能是一个完整的研究整体,同时也是获得自身理论基础的关键所在。
(三)媒介功能主义研究的反思
当今媒介研究要么强调媒介内容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要么突出媒介自身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尽管表现出各自研究的不同层面,但他们都是从工具论的视角出发,强调媒介的传播效果和社会控制作用,无疑是一种功能主义的媒介研究。媒介功能主义研究有其自身的弊端,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的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在当今的传播学研究横跨了多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但却与作为母学科的哲学相距较远,对相关的传播现象缺乏哲学上的思考,导致传播研究缺乏自身的哲学基础。胡翼青认为,“一旦媒介和受众的关系被简化为需求满足的功能性关系,这种阐释只能给我们提供知识,无法形成理论,也无法形成思想。”他强调当今的传播研究应该与海德格尔、舒茨、曼海姆、马克思·韦伯和卡尔·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一种对话,建构一种传播学理论与哲学之间的联系。诚然,在当今的媒介功能主义研究中,尤其是在经验学派那里,主要采取一种调查研究的方法,研究者不断忙碌于各种数据的收集、分析和清算。虽然在整个研究中做到了数据的精确性,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知识,但这种忙碌却只呈现于数据的表达,对传播学的建构没有多少理论帮助。海德格将其视为具有“企业活动”的性质,其结果是“学者消失了。他被不断从事研究活动的研究者取而代之了。是研究活动,而不是培养广博知识,给他的工作以新鲜空气。研究者家里不再需要图书馆,他反正不断在途中”。
另一方面,对媒介功能的过分强调,容易陷入媒介中心主义和技术决定论。海德格尔的媒介本体论是反对将媒介作为工具性质对待的,从“技术”的本体性追问就可以见出。海德格尔的媒介观不仅是一种反工具主义的,而且还将媒介的存在与人的存在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孤立的分析媒介。但在今天的媒介功能主义那里,不仅从工具性角度来分析媒介,而且还把媒介作为一种对象孤立出来,脱离了与人的存在之关系,这既不能形成自身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会陷入技术决定论或媒介中心主义的泥潭之中。
注释
①②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走向媒介本体论》,胡兰菊译,《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④⑥⑦⑩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2页,第131页,第133页,第86页。
⑤陈静:《走向媒介本体论—向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致敬》,《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
责任编辑王雪松
On Heidegger’s Thought of Media Ontology
Zhang Sanxi1Li Mingyong1,2
(1.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2.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18)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it was Heidegger who first introduced media into the research field of philosophy.He distinguished being and beings on the basis of ontology philosophy, highlight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being and the world,and made an ont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technical media which connected being with the world.Difference from the communication study centering around the study of media functions and media itself, Heidegger’s thought of media ontology made metaphysical analysis of media from the media generative point of view, which opened a new field for the study of media,and benefits to the retrospection of contemporary media functionalism.
Heidegger; technical media; media ontology; media functionalism
2017-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