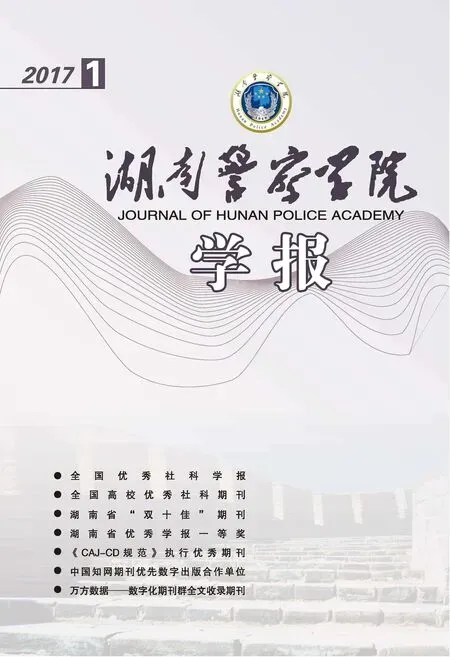新型城镇化下农村土地法律制度适应性变革
——以“三权分置”为视角
陈宏寿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惠州 516057)
新型城镇化下农村土地法律制度适应性变革
——以“三权分置”为视角
陈宏寿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惠州 516057)
城镇化率的快速提高,一方面有利于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成为解决“三农”问题和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农村土地资源有效配置不足的问题,如土地经营权的性质有待明确、农村土地流转有待“去行政化”、农村土地流转操作细则有待完善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在“三权分置”的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法律制度却面临的现实困境,成为发展现代化农业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道路上的障碍,而再次释放土地改革所带来的经济“红利”,须在协调市场化与行政化的关系中有序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三权分置;新型城镇化;农村土地;创新与变革
与城镇化不同的是,新型城镇化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为己任,其理念之新和目光之远,不仅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协调城乡两个市场可持续发展,还能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丰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人的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以我国基本国情为立足点,不能为了达到城镇化而片面追求数量上的“城镇化”,而应因势利导,逐步实现向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户籍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转变的自然发展过程。在改革开放之初设立的“两权分离”(即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基础上衍生出土地承包权)土地法律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但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导致农村土地因无人耕种却被大量闲置,造成土地资源在有效配置上的浪费,影响我国粮食生产安全与社会稳定,据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以下简称“三权分置”),为完善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明确改革方向,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各方按照规定,是我国适应新型城镇化的重大土地改革与创新。
一、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土地利用的概述
(一)新型城镇化的界定
城镇化是由城市化演变而来,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这场社会变革,只是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经历所需要的时间不同,即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但新型城镇化这一界定更符合我国的国情。城镇化是一多层次、多角度、动态性的概,需要在系统、全面界定城镇要素、功能和内涵的基础上定义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与城镇化相比,不是城镇化率数字的变化,也不是以简单的“户籍”和“楼房化”为评价标准的城镇化率,而是更加注重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使从农村迁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有序地、更好地融入城镇,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提高农村土地综合利用效率,又通过城镇化促进“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转型发展,所以,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大的方面关系到社会稳定,小的方面到农民能否体面地融入城市,是一个涵盖社会、生态、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新型社会关系。
(二)农村土地利用
在“三权分置”办法出台之前,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一是错位的农业补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由土地集体所有权分离出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之初,因为城镇化程度不高,其存在的弊端并没有显现出来,但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吸引更多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然而,在人地分离后,农民以土地承包者的名义继续领取农业补贴,而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却因主体资格不符现行规定,无法得到应有的补贴,违背提高种粮积极性的农业政策本意。二是分散的经营模式。论历史贡献,“两权分离”在农村土地改革中功不可没,是适应当时“三农”特点和发展水平的经营模式,但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因农民所承包的土地具有地块分散和规模小(即一亩三分地)的特点,耕种起来其成本高、劳动生产效率低和增收难,以致种与不种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在“三权分置”办法出台之后,农村土地利用始终坚持集体所有不动摇,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村土地经营权中的作用,将耕者有其田的传统农业经营模式向善耕者用其田转变,既可完善现有农村土地制度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方面,以集体方式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又能让农村土地改革的红利更多的释放出来,充分调动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者的财产性收入。
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要求
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使城市土地日趋短缺,土地成为稀缺资源,因而推动土地及住房价格上涨。现阶段,我国城镇化已由发展期、增长期转向加速期,2001年城镇化率从37.66%增至2015年的56.1%,年均增长约1.3个百分点,此数据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转向非农产业,加上农业仍以于粗放型生产方式为主,过分注重产量和盲目跟风生产,虽然连续六年来,我国农民人均收入高于GDP和城镇居民收入增幅[1],但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行压力加大和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成本增大的“双重阻力”下,农民实际收入增长呈现“明升暗降”的趋势,甚至部分农村因为毗邻城市,为在城市开发当中获取更大利益,不惜破坏耕地,违规占地建房,使农民对土地生产的依赖性有所降低。“三权分置”的出台,打破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流转困境,使农村土地经营权成为现实,从而为我国粮食生产安全提供保障并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当前农村土地经营发展明显落后于社会发展需求,土地虽然对于农户来说仍存一定的心理依赖,但已不再那么明显,因为农民除了种地之外,还有家庭成员在城镇就业,其经济收入渠道有较大的调整,加上“三权分置”明确规定加快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为市场资本推动传统农业生产规模和释放“土地红利”提供了制度保障,只要有序、控制规模发展农村土地流转,不仅不会造成农业生产的减少,反而会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促进农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法律制度面临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之初,“两权分离”激活广大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从而解决为温饱问题奠定物质基础。但随着区域经济纵深发展,原有的土地法律制度已无法适应城镇化的要求,如人地分离、农业生产效益不明显、农村土地长期撂荒和承包经营权无法分离等问题,为了适应城镇化所提出的新要求,对农村土地制度进行创新设计,即“两权”变“三权”,然而一旦将涉及中国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各项政策和要求上升为法律制度之前,必须经得起法理的推敲,以防出现法理上的尴尬,“三权分置”理论也应属该范畴。
(一)土地经营权的性质有待明确
民法理论认为,一项权利分解为多项权能,权利是内容,权能是权利的具体表现方式,如物权中的所有权,不是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简单的组合,也不是同时使用各项权能,而对物的全面支配的权利。“权能分离”理论认为,母权(自物权)是产生子权(他物权)的基础,如物权作为母权,可以分离出去形成其他权利,同时,所有权也作为母权,也可以分离出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能,而他物权是物权、所有权所产生的子权。“物权”理论认为,《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一物一权”,即一物不能存在两个以上在性质上相互排斥的物权[2]。在“三权分置”理论之下,将“土地经营权”确定为一项用益物权,违反上述要求,因为用益物权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排他性,作为两项独立的用益物权,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无法同时并存于同一块土地,所以,须在法律逻辑层面厘清“土地经营权”的性质。
(二)农村土地流转有待“去行政化”
2015年,自启动33个试点区域农村土地改革以来,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向规模化、现代化转变已初具雏形,但在加快农村土地规模流转过程中,一些潜在的风险逐渐显现出来,一些新的矛盾又正在涌现,在土地流转成本高、粮食直补的错位、农资价格逐年走高等情况,致使农村土地经营者种粮成本居高不下,一旦资金吃紧或粮食价格下跌,“紧箍咒”便开始制约种粮大户,如重庆万亩“粮王”破产、江苏种田大户被迫退田、吉林种粮大户毁约“跑路”。因此,在实现农村生产经营规模化转变过程中,不是比谁地块大,也不是看有没有集约化生产方案,而是在于是否建立与农村土地流转相配套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如中东国家以色列,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沙漠小国,但就是在这种缺水又缺地的自然环境下,却造就世界闻名以色列农业,原因在于强化政府对农业科技的投入意识、构建现代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和农业生产产学研配套政策的实施,所以,我国全国耕地面积、土地资源情况和自然气候与以色列相比,先天条件应该比较优越,与2010年相比,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2014年达到4.03亿亩[3],年增长率高达43.6%,在缺乏科学规划和出台配套政策下,通过行政命令强推土地经营权流转,以求快速实现农业现代化。不同国家,资源禀赋各异,不能简单的通过规模化,就能实现农村土地“红利”的释放,只能重蹈菲律宾大土地集中生产的惨痛教训。虽然土地承包者的经营规模比原先要大,但拥有的只是一个债权,而在债权履行期限内,土地经营者须单独面对各种复杂多变的因素,如农业生产科研的投入、资金渠道单一、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和农村集体产权界定不清晰等问题都会影响投资者积极性,只有根据我国国情,政府应科学、有序和合理推进土地流转,才能指导土地经营者科学从事耕地生产和避免土地非粮化、违约现象的出现,真正发挥农业用地应有的价值。
(三)农村土地流转操作细则有待完善
土地的“三权分置”的出台,在承包经营权中分离出来的土地经营权,不管是信托模式的农业投资,还是民营资本直接参与,这一制度的确立,为民间资本从事农业投资提供了制度的保障,以避免市场因政策缺而产生的忧虑,因为只有民间资本进入传统农业生产活动,其资金瓶颈才能得到有效破解,而现阶段,农村土地产权交易方面的操作细则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土地经营权能否作为抵押物。土地经营权能否作为抵押物,在法律制度上缺乏明确依据,而银行和土地经营者在国家政策未明的前提下,对是否给予办理抵押、如何申请和评估抵押物、抵押物如何处置、流转过程中抵押权实现难易程度的保障机制等方面都感到迷惘,加上农业生产不确定性因素,使土地经营权从承包权分离出来后,面临最大的制度瓶颈。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条规定,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担保法》未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抵押财产,因为作为抵押物,首先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财产,而相关的法律规定都未进行配套修改,影响其认可度。其次是所有权归属无争议的财产。据此,土地经营者若用土地经营权(流转地)申请银行贷款,一般申请很难获批,因为一旦土地经营者无法按时还款,作为债权人的银行无法通过变卖、拍卖抵押物,获得优先受偿,所以,在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或明确的政策规定的情况下,土地经营权能否作为抵押财产存在瑕疵。
二是有关土地流转的纠纷日益增多。如作为我国农业大省之一安徽省,早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因家庭劳动力严重不足,其所承包的土地要么采取弃耕、抛荒,要么由亲戚邻居间代耕代种,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不规范,如流转合同的形式、调整地租费用、粮食差价补贴归属等问题的纠纷不明显,相关既得利益并未受到影响。但随着国家惠农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双方的争议呈逐年增加的趋势[4],“三权分置”办法的出台,虽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由一变二,但有关的权益却未进一步明确,加上农村土地流转大多欠缺法定形式要件合同,其稳定性易受经济利益影响,一旦发生经济纠纷,如粮食差价补贴归属,当事人便摆出“寸土必争”的阵势
三是,农村流转土地“非粮化”趋势加剧。与传统的土地细碎化经营模式相比,近年来,在国家有关土地法律制度的改革下,土地流转呈现出流转速度提速(土地流转率已经达到30%)[5]、农业经营主体多元化、农业规模化经营初显雏形等特点,与此同时,随着农村流转土地速度的加快,我国用于种粮的耕地面积,特别是优质耕地正面临重大挑战,一是因为耕地占补平衡政策玩出“数字游戏”。作为对耕地“占一补一”的补救措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出台的目的在于守住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不动摇,既能满足城市建设用地需要,又能平衡国家粮食生产,但从实际来看,新增耕地虽符合复耕标准,但因缺乏水源,根本达不到耕作要求,而若想达到同样优质耕地的要求,因县级政府财政有限,无力提质改造新增耕地,在部分地方,只要在新增耕地两年内种植农业作物,一旦验收合格后,便能进入新增耕地储备库[6],符合耕地面积不减这一要求。而不考虑新增耕地是否符合农业生产需要,这一“数字游戏”使城市占用耕地“合法化”。二是因为流转成本高催生耕地“非粮化”趋势。在国家土地法律制度改革下,土地经营权的正式确立使我国产生“职业农民”,虽然土地流转解决无人种地、谁能种好地的问题,但流转后“职业农民”却不得不面临流转成本高的现实困境,以全国优质小麦之乡——河南省延津县为例,种粮大户陈长海流转了2亩地,玉米、小麦两季种植,每亩总生产成本875元,玉米1100斤,每斤0.75元,小麦打1000斤,每斤1.1元,刨去地租,每亩要赔150元[7]。若粮食价格走低,加上错位的农业补贴政策和缺位的金融支农政策,必将面临更大的亏损和经营风险,“非粮化”好像成为“职业农民”应对比较收益明显下降的自然反应,但会给我国粮食安全埋下隐忧。
四、“三权分置”下农村土地法律制度适应性变革与创新
(一)遵循法律逻辑明确土地经营权的性质
任何法律权利的实质必须符合内在的法律逻辑,强调法理学命题具有普适性的原则。而“三权分置”正式确立后,学界对此莫衷一是,原因在于《物权法》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权,造成有的认为是用益物权,有的则认为是债权。面对土地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归属不清这一法律困境,在“三权分置”办法出台后,在严格遵循现有权利生成逻辑的前提下,尽快在理论上统一认识,扫清制度障碍。支撑土地经营权在“三权分置”理论中得以成立的依据是将土地经营权定性为债权,因为一旦确立后债权,便可产生合同法律关系,从而将土地经营从土地承包权中分离出去,解决了“一权一物”的矛盾,同一块土地上又同时存在用益物权(承包权)与债权(经营权)。在土地流转成为农村土地规模化发展的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尽快确立土地经营权性质,需要遵循法律权利的生成逻辑,避免现有土地权利体系进行大幅度变动,改变农民单一渠道的财产性收入和强化实际种地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土地流转各方公平分享土地改革红利,理应成为当前农村土地法制改革的核心。
(二)以“市场化”为方向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从党和国家有关耕地保护工作的政策可以看出,农村土地流转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要始终坚持规范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流转[8]。因为《宪法》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农村土地改革必须长期坚持这一基本制度毫不动摇,所以,在如何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上,作为行政部门应根据我国“三农”实际情况(如:加大农业技术服务支撑、增强农民现代农业种植意识和构建新型农村土地流转合作形式等),以“市场化”为主导,坚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辅以前瞻性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而不是简单的以城镇化率作为参考的依据,更不是以土地流转的面积为标准,来推进农村土地这一复杂又敏感的改革,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却把农村土地流转误解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只要实现这一目标,那就是农业现代化,当然这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特点,不是全部,不能用行政命令替代市场运行,“扎堆”推进土地流转,这是政府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越位表现。同时,土地流转过程中也不能放任不管,因为经营权的放开,让民间资本得到松绑,其天生的逐利性,有可能给农业生产带来“非粮化”趋势和“掠夺式”经营,这是政府缺位表现。对中国农民来说,土地承担着生活基本保障的观念仍比较强烈,虽然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有所降低,但作为一个整体,农民有偿“退地”仍须稳慎探索,因此,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政府应综合评估流转后对农民生活产生的影响,通过制定完善的“经营权”准入监管机制和“承包权”退出后的保障机制,实现土地流转与农民的真实需求紧密结合,既增强经营者抵御风险的能力和为“退地”农民提供保障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又有效地减少土地流转改革风险和提高农村土地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三)细化农村土地流转的操作细则
1.明确土地经营权作为可抵押的财产。2016年3月,央行、银监会等四部委联合印发《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对试点地区首次明确了农村土地经营权可以办理抵押贷款相关事宜,在法律层面首次为土地经营权的性质作出探索,此举目的在于坚守耕地保护红线前提下,为当地实际农业生产者从事规模农业生产提供有效的金融政策,从而提升农业竞争力。目前该规定尚处于试点阶段,而面向全国范围内的行政法规尚未正式出台,应在试点地方及时总结成功经验和反思失败案例的基础上,提炼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物的有效处置机制,做到事前规则说明,以便明确相关权益人的知情权,事中辅以配套政策,增强银行和土地经营者抵御流转风险的能力,事后建立资金流向跟踪机制,调动涉农金融机构参与惠农政策和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所以,盖楼要先打地基,土地改革也离不开法律,在土地流转成为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应当做好制度的顶层设计(即法律先行),否则,因无“法”适用或缺乏配套政策,必定使市场各方无所适从。所以,应在法律法规层面明确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物的规定,及时弥补法律滞后造成的乱象,使得涉农金融机构、承包者和经营者分析与防范抵押物风险,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产权交易风险补偿机制,实现城镇化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良性循环。
2.落实对实际种地农民的“直补”政策。粮食“直补”政策的本意是为了调动实际种地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各省根据补贴实施方案对实际种地农户给予一定数额的补贴资金。2016年6月,财政部发布《关于建立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不仅标志着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实现玉米临储制度向“市场化收购加补贴”转变,而且旨在激发实际种地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虽然政策已作出了明确规定,就是要补给实际种地的农民,但同在东北三省的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却有不同的表现,从吉林省农业局网站查询后,并没有发现有关吉林省玉米生产者补贴的公开文件,具体由各地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要求制定补贴方案,并未落实谁是玉米差价补贴的受益者,只能由承包者和经营者协商确定,但面对平均0.15元/斤的玉米价差补贴,双方都互不相让,在缺乏协调人(政府部门)或协调无果的情况下,这笔价差补贴最终不了了之。而在黑龙江省早在2016年7月就公布《2016年黑龙江省玉米生产者补贴实施方案》,确定全省统一补贴标准,对本省内合法实际种植者兑付补贴资金[9]。这笔看似较低的补贴,但对实际种地农民来说,却意义非凡,因为这份补贴直接关乎实际种地农民从事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和是否具备来年继续种地的资格。在土地流转经营剩余期限内,经营者每年向承包者支付的地租是固定,承包者的利益并不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但经营者却与之相反,如果这个新补贴不给实际种地农民的话,一旦价格下降几毛钱,加上为改善土地质量所付出的必要成本,实际种地农民蒙受巨大损失。所以,作为先行先试的玉米收储制度的改革,已经明确对实际种地农民的“直补”政策,各地以后在落实有关农业补贴政策方面,应坚决执行“直补”政策,因为在保护承包者的利益的同时,也在调动实际种地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3.建立流转土地监管机制。其实,法律对流转土地的用途,已经明确规定只能用于生产粮食作物,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安全,但在具体流转过程中,在经济成本占主导情况下,多地农村流转土地“非粮化”亟待引起重视,如在河南、山东和安徽等粮食主产区,本应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却变成成片的葡萄、蔬菜、林果等经济作物,“非粮化”这一比例在2014年攀升至60%[10]。而面对农地“非粮化”利用形式,主管部门却采取默许的方式,这也导致农地流转日益“非粮化”的推手。为遏止这种“非粮化”经营趋势,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规定严禁擅自将耕地“非农化”,但面对地方政绩考虑,仅靠一纸规定无法制约土地流转后不规范利用行为。为了确保农地流转后粮食生产用途不改变,要建立流转土地监管机制,做足流转土地用途、风险、法律责任等配套政策,让农民安心从事粮食生产活动,并宣传有关流转土地政策,设置违规使用流转土地举报奖励机制,鼓励村民积极举报违规行为,对实施“非粮化”生产行为的经营者追究违约责任,给予取消1-3年的农业直补政策,情节严重的取消土地流转资格和承担违约责任,以保证流转土地依法依规利用。
综上,推进新型城镇化是我国调整产业结构和释放内需潜力的重要着力点,特别是在“三权分置”的背景下,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借市场资本之力推动城镇化建设,使有限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得到充分发挥,又要注意发挥政府在设计法律制度的职能,理顺土地流转相关法律性质,使利益相关方更好的理解法律“真谛”,再次激发农村土地法律改革释放“红利”的推力,实现有序、又好又快的建设新型城镇化。
[1]于文静,王宇.2015年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已突破万元[EB/ OL].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2/24/c_128564780. htm.
[2]单平基.“三权分置”理论反思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困境的解决路径[J].法学,2016,(9).59.
[3]王宇.全国耕地流转面积占总承包耕地比重超过三成[EB/ OL].http://www.gov.cn/xinwen/2015-08/27/content_2920879.htm.
[4]唐欢.土地流转不规范导致纠纷频发[N].安徽法制报,2016-09-07(A1).
[5]韩长赋.流转面积占总承包耕地比重超三成[N].经济日报,2015-08-28(2).
[6]周勉.耕地“占补平衡”怪象多[EB/OL].http://www.banyuetan. org/chcontent/jrt/20151015/156995.shtml.
[7]赵永平,常钦,马跃峰.地,究竟该咋种?——来自河南、山东两个农业大县的调查[N].人民日报,2016-05-29(09).
[8]新华社.依法依规做好耕地占补平衡规范有序推进农村土地流转[N].人民日报,2015-05-27(01).
[9]黑龙江省人民政府.2016年黑龙江省玉米生产者补贴实施方案[J].黑龙江粮食,2016,(8).
[10]新华社.山东河南多地土地流转“非粮化”趋势加重[EB/ OL].http://sd.youth.cn/2014/0904/372066.shtml.
Analysis on Rural Land Legal System Adaptive Changes During the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Taking Three-right Separation as the Example
CHEN Hong-shou
(Huizhou Economic and Polytechnic College,Huizhou,516057)
The rapid improve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rate,on the one hand is advantageous to the country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becomes the solution of“three agriculture”question and the important way of coordinating the region development;on the other hand,it also possibly creates the problem which the countryside land resource effective disposition is insufficient,such as the nature of land management rights to be clear,the circulation of rural land needs to be de-administration,the operation regulation of countryside land transfer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so on.Th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our country to realize modernization and build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hree-right separation, rural land transfer legal system is facing the reality of the pligh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obstacles.And once again release the land reform brought about by the economic dividend have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ket and the executive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three-right separation;the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mrural land;innovation and change
D902
A
2095-1140(2017)01-0005-07
(责任编辑:天下溪)
2016-12-02
陈宏寿(1981-),男,广东汕尾人,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经济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