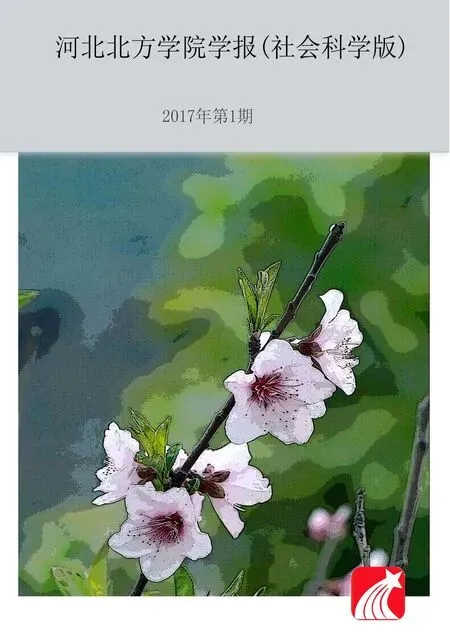巴金家庭题材小说中的人性思考
李 向 东
(河北北方学院 文学院,河北 张家口 075000)
巴金家庭题材小说中的人性思考
李 向 东
(河北北方学院 文学院,河北 张家口 075000)
巴金的家庭题材小说蕴含了他有关人性问题的思考。这些小说中体现出作家关注制度变革和精神启蒙的嬗变轨迹,集中表达了对于人性的思考过程:即从倚重制度变革与精神启蒙对人的提升和改造,到以宽容与谅解的姿态面对人性深处带有“原罪”性质的痼疾。
巴金;家庭题材小说;人性思考
网络出版时间:2017-02-28 14:11
巴金总是从社会政治层面对其作品加以诠释,作品本身蕴含了作家对人性问题的思考,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家庭题材小说的创作中。可以从两条思想脉络看取巴金此类小说中呈现的人性思考。
一、制度变革之思的嬗变轨迹
批判封建家族制度是巴金家庭题材小说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巴金看来,只要颠覆了这种压迫人戕害人的制度,人性就能获得健康发展[1]14。巴金对于人性本身是有信心的:“我绝不悲观,在中国还有不少的好人,我认识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死去的更是极小,极小的部分。”[1]120然而巴金也说过,他自己的创作是在“挖掘人心”。即是如此,其作品就无法不触及人性的复杂。对于主要凭借体验与情感进行创作的巴金而言,这种复杂性的呈现同样引人注目。在巴金家庭题材的系列小说中,对封建家族制度的批判和对人性内蕴的开掘均有明显的嬗变轨迹。从它们的演变中,可以发现作家对于人性问题的思考。
巴金的早期家庭题材小说《家》控诉了封建家族制度的极端不合理性。到了其后期创作的《秋》中,这个大家族终于分崩离析,这标志着巴金对传统家族制度的彻底否定。在《秋》的尾声,大哥觉新给离家出走的觉慧和淑华的信里这样写道:“我们搬出老宅以后,生活倒比从前愉快。”[2]654对于这样的结局,巴金是深感欣慰的。然而,其之后的创作中,类似的小家庭所展开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秋》之后的《憩园》,描述的也是一个从没落大家族分裂出去的小家庭的故事。在那里,已经很难看到封建家长专制的影子,可是这个小家庭却不再有《秋》中觉新一家的平静与温馨。给这个家庭带来不幸的正是《憩园》主人公杨梦痴的人性弱点,即人的情感欲望对道德和责任的僭越。杨梦痴瞒着妻子与一个四川女子相好,还以押款做生意的名义从妻子手中骗钱供她花销。事情败露后杨梦痴被赶出家庭,最后默默死去。
在这部小说中,巴金并没有单纯从道义上进行谴责,而是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小说所描述的那份婚外情是真挚的。当那个叫“芳纹”的四川女子无奈地离开杨梦痴,他“就像害过一场大病一样”[3]77,只在家里呆了4天,就又出去寻找那个女子。当杨梦痴一无所获回到家时,“人比从前更瘦,一件绸衫又脏又烂,身上一股怪味”。后来,那个女子给杨梦痴寄来了数目不小的一笔钱,并请杨梦痴原谅她。杨梦痴的小儿子这样评价那个女子:“我觉得她还是个好女人,她现在还没有把爹忘记。”[3]85而正是这份看似真挚的感情却给小说中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憩园》之后,出现在《寒夜》中的汪文宣的家庭已经完全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小家庭。它不仅没有封建家族制度的羁绊,甚至比一般的现代家庭更为激进。汪文宣和妻子曾树生是自由恋爱,未婚同居,他们连组成一个家庭的合法形式都舍掉了。巴金曾在小说《春》里借琴之口对五叔克定和妻子沈氏的吵闹评价道:“这有什么稀奇?不自由的婚姻都是如此。”[4]164可是在《寒夜》中,痛苦压抑仍然是每个家庭成员必须面对的生活状态。在这部现实感很强的小说里,蕴含了巴金对人性的深层思考:“《寒夜》写出了人与人无法沟通的悲剧……它植根在文化中,植根在人的存在中。”[5]301这些在特定伦理关系制约下表现出的人性弱点,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了广阔的涵盖性。
从巴金的《家》《秋》《憩园》再到《寒夜》,封建家族制度的束缚逐渐消解,可人们的生存境遇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巴金家庭题材小说所呈现的就是愈益复杂的人性状态。
“以往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人即使不是天生就是善良的,也是天生就有社会性的。这种假设不可避免地要求实现极为不切实际的目标;他们认为,只要给予自由、足够的收入和时间以医治他们的精神创伤,人类就会开始表现出完美的社会性。”[6]45显然这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源于人性自身的局限性使人类只能是负伤前行,更无法奢求什么完美的社会性。巴金是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作家,但他的家庭系列小说已然超越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局限。
二、精神启蒙之思的嬗变轨迹
巴金还有一个与人性相关联的重要观念:青年人只有接受精神上的启蒙,才能真正使自己获得解放。青少年巴金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受到西方近代启蒙运动极大影响的时代,而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相信人性是可臻至善的[7]29。如果说对于制度变革的关注体现的是作家对束缚人性发展的外部因素的思考,那么对思想启蒙的看重则体现了巴金在人性的自我完善方面所抱有的积极态度。在巴金家庭题材的作品中,青年人接受思想启蒙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接受现代教育;一个是走向民间,参与社会运动。
青年人对现代教育的向往,早在《家》的第二章就已被作家写出:琴所在的学校不能男女同校,读的书总是《古文观止》一类的“老古董”。而觉民弟兄就读的是一所外国语学校,接触的多是新思潮和新观念。所以,当琴听说那个学校要招女学生时,她“恨不得你们底学校马上就开放,我好进去”。
觉新见到怯懦萎顿的枚表弟,也曾质问:“现在男人进学堂读书是很平常的事情。光是在家里读熟了四书五经,又有什么用?”[4]122觉新希望枚表弟不再去私塾读书,而能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显然他相信现代教育会改变一个青年的精神面貌。在《秋》中,继母支持了女儿淑华到琴就读过的学校念书的请求。那虽然是个女子师范学校,但终究不同于传统的私塾教育,淑华“差不多欢喜得跳起来”[2]548。
现代教育在年轻人心目中是多么神圣,仿佛接受了这种教育就能脱胎换骨,迎来新生。可是巴金作品中那些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物并没有给人们一个满意的回答,人性中的缺陷在他们身上依然存在。这种现象在小说《家》中已有显现:
面对城内的败兵流窜,琴深感自己的软弱无能:“这时候什么新的思潮,新的书报……对于她都不存在了。”面对强大的异己力量,生命的脆弱显露无疑:“她绝望了,她这时候才开始觉得她和梅,瑞珏这些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她实际上是和他们一样无力的。”[8]216-217
封建家族的叛逆者觉慧同样体验到了无奈和绝望。鸣凤投湖死去了,觉慧表现了深深的自责:“我从前责备大哥和你(指觉民——笔者注)没有胆量,现在我才知道我和你们一样,我们是一个父母生的,在一个家庭里长大的,我们都没有胆量[8]285。”
之前,觉慧认为他与周围的环境是尖锐对立的,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他所认可的精神联系,一切丑恶的东西都没有他的过错。可是经历了鸣凤事件后,他认识到自己人性深处难以祛除的弱点。
在巴金的后期创作中,《憩园》中的主要人物姚国栋大学毕业又留过洋,做了3年教授,两年官。可以说他不仅接受了完整的现代教育,还曾为人师表。可他最后还是“回到家里靠他父亲遗下的一千亩的田过安闲日子”[3]4。姚国栋为人热心但又刚愎粗俗,在他身上丝毫没有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痕迹。他的儿子小虎在小说中出场时的装束就是“咖啡色西装上衣,黄卡叽短裤,衬衫雪白,领带枣红”,小小年纪在生活方式上就与传统迥异,可是他却不爱去学校读书,时常旷课到外婆家赌钱,且在接人待物方面表现出惊人的冷漠。
《寒夜》中的汪文宣夫妇是大学生,汪文宣的母亲曾是当地的才女。可是这不仅没能改变黑暗现实对他们的压迫,反而成为导致他们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小说中母亲痛苦地对汪文宣说:“我只后悔当初不该读书,更不该让你也读书。我害了你一辈子,也害了我自己。”[9]375汪文宣和妻子在大学是学教育专业的,他们幻想着毕业后能够用自己的学识改进教育,可当他们真正走上社会,却只能被冷酷的现实剥夺了幸福甚至生命。
在巴金家庭题材的小说中,青年人接受思想启蒙的第二个途径是走向民间,参与社会运动。
在小说《家》的结尾,觉慧终于去了上海。他的朋友说:“你到下面去,在学识与见闻两方面,都会有大的进步……在上海新文化运动比较这里更热烈得多。”大家相信走向民间,投入到运动中接受新思潮的洗礼,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很有利的。
在小说《春》中,淑英也脱离了高家,投奔觉慧。她以轻松的笔调,在给琴的信里记述了与觉慧在一起的愉快心情,“姐姐,我真高兴,我想告诉你:春天是我们的”[4]510。
《激流三部曲》中的《家》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初,《春》和《秋》则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在后两部小说中,巴金并没有延续《家》的叙述线索,去记述青年人走向民间参与社会运动的生活,而只是通过侧面描写对他们在外面的状况稍有涉及,作家的视角始终没有离开那个封建的大家庭。可是一旦巴金在此后的创作中将关注的视点离开那个封建的大家庭,就再也看不到这些激进的青年人辉煌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有着种种人性弱点的小人物和他们卑琐的生活。
其实在《家》中就已潜藏着可能发展成为这种趋势的迹象:与作家对封建大家族的激烈批判和坚实细致的描写相比,小说对青年人所谓社会运动的讲述则显得虚浮、空泛和无力,他们“有的只是一点勇气,一点义愤,一点含糊的概念”[4]246。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去描述青年人的社会活动尚且如此,作家又如何呈现那些远离家庭的青年人的生活?这些激进的青年不过是巴金美好的社会理想的载体,作家仅是借他们来抒写自己朦胧的乌托邦之梦。这已不再是巴金所熟悉的生活,当他继续执笔创作,内心的良知与情感依然会引导他写出自己切身感受到的真实人生,写出那些在无奈与痛苦的生活中挣扎着却又永远不能自由选择,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普通人卑微的生存境遇。
巴金希望通过颠覆封建体制和进行思想启蒙的方式使人们获得解放的思路被他笔下人物的行动否定了。他们在作家营造的一个个艺术世界中越来越强烈地显示出幽暗人性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困境,这是《家》中人性内蕴符合逻辑的发展结果,是体制变革和思想启蒙所难以改变的。
三、复杂的精神世界
有着强烈“革命者”情怀的巴金,在创作中关注制度变革和思想启蒙,甚至到晚年,作家还会不顾自己的现实身份,去追认那个“革命者巴金”[9]118。而另一个沉浸于文学创作的巴金,则富于诗人气质,有着出于优异禀赋的对于人类命运和存在本身的形而上的直觉和洞察。这使他的创作具有了超越性,使他的作品具有了表现人类普遍的生存境况和永恒人性的可能。
这种复杂性在巴金早期小说《家》中体现得非常典型。众所周知,控诉封建家族制度的罪恶是《家》的创作初衷。但细读文本,会发现巴金矛盾的思想意识在作品中也一并存在着。小说除了承载社会政治层面的意义外,还呈现了人性的复杂状态,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溢出了巴金创作《家》的初衷。
20世纪80年代中期,徐中玉在其《评巴金的家、春、秋》的文章中谈到:“决定着这个资产阶级大家庭的崩坏的命运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环境两个因素,在这三册书里并没有得到过适当的足够的反映。”[10]579“在他的认识与表现之间,还存在着一些距离,是明白的。这样的距离,多少不免妨害到作品的坚实性和深刻性。”[10]579-580徐中玉是敏锐的,巴金在认识和表现之间的距离,正是由于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小说实际内蕴的偏离造成的。当然,《家》中人性意蕴的表现是极为曲折隐晦的,它和具体的时代、人物与事件结合得过于紧密,即使从隐喻和象征的意义上也很难将其完整地抽取出来,总要首先突破被社会政治意义包裹着的厚厚外壳,才能窥见其中隐藏的深层意义。
20世纪40年代后期,很多中国现代作家都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认为人世的一切邪恶与不公会随着“历史的进步”而销声匿迹。黄子平说:“巴金本人在1950年的上海首届‘文代会’上曾真诚地说:‘会,是我的,我们的家,一个甜蜜的家。’那么在这样新的笼罩着更大空间的‘家’中,还会不会有迫害,倾扎,阴谋、牺牲和梦魇呢?”[11]439巴金自己从“家”到“群”再到“牛棚”的经历给出了回答。惨痛历史的再现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但是显然不应忽视人性弱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现代人被迫承认,人性并没有随文明的进步,改善多少。人的天性中仍然有黑暗的罪恶渊薮。”[12]45当然,人性中还有另外的一面,还有源于本性的良知,有对于爱和善意的渴望与追求。在很多时候,尤其是在那些疯狂的年代里,正是这些支撑着社会,使之不至垮塌。巴金就是禀赋着这样复杂的精神元素在艰难前行,一路留下他的迷茫与挣扎。
[1] 李小林.巴金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2] 巴金.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3] 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七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4] 巴金: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5] 王富仁.王富仁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6] 珀林·M·特里.当代无政府主义[M].吴继淦,林尔蔚,姚俊德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7]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8] 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七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9] 陈思和.中国现代文学名篇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 李存光.巴金研究资料(下)[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
[11] 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
[12]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版)[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白 晨)
The Reflection of Ba Jin on Humanity in his Family Novels
LI Xiang-d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ebei North University,Zhangjiakou,Hebei 075000,China)
Ba Jin expresses his reflection on humanity in his family novels.The evolution of the writer——from the reliance on the promotion and change of humanity brought about by the system reform and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to the tolerant and forgiving attitude toward the serious ills of humanity——represents his reflection on humanity.
Ba Jin;family novel;the reflection on humanity
2016-06-03
李向东(1977-),男,河北张家口人,河北北方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I 246
A
2095-462X(2017)01-0020-004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70228.1411.0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