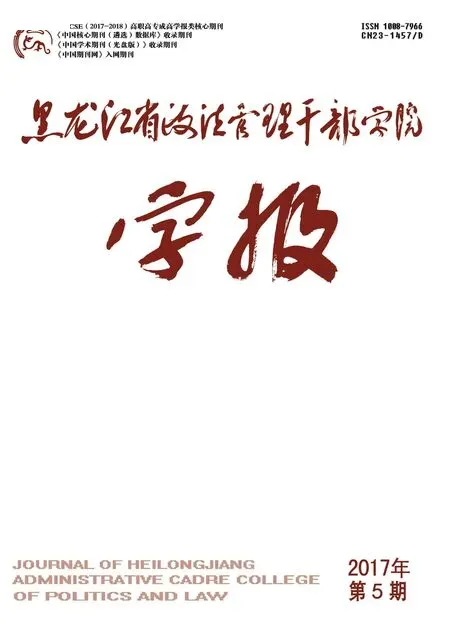论网络著作权领域ISP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论网络著作权领域ISP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
何雨菁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网络环境下网络用户可以匿名实施多种行为。尽管虚拟的网络环境给网络用户带来了好处,但侵权者身份的隐蔽性却为打击盗版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网络服务提供者(以下简称ISP)作为具备技术优势的网络控制者可以获得侵权用户的虚拟信息及部分个人真实信息,负有协助著作权人追诉直接侵权者的义务,但ISP随意披露侵权用户的信息可能导致个人信息被不当利用。ISP信息披露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是平衡权利人与侵权者利益的关键。
ISP;直接侵权者;个人信息保护;信息披露
一、ISP承担信息披露义务的必要性
网络世界提供给网络用户在此虚拟空间以虚拟身份进行活动的自由,但却为著作权领域的文件共享侵权活动的肆虐埋下了隐患,加大了著作权人网络维权的难度。识别网络侵权者的身份是权利人维权的前提,ISP有必要披露侵权用户的个人信息。
(一)P2P技术诱发大量网络盗版
P2P技术的发展无疑创造了一个信息大爆炸时代,网络无形载体的特性决定了用户复制并上传这些共享内容成了轻而易举的事,共享行为有可能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下进行,这就使得P2P技术沦为盗版盛行的“沼泽地”。自P2P技术出现以来,各国法院收到著作权侵权起诉的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美国法院认为P2P文件共享的过程是指数式的,而不是线性的,将可能形成大规模的著作权侵权[1]。在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 诉Streeter案中,美国法院描述了P2P技术,认为P2P技术使原告作品“易受大规模、重复和世界范围的侵权”[2]。2005年,未经许可的音频文件交换数量将从2001年的51.6亿上升至74.4亿。并且,随着全球范围的宽带建设升温,影视文件也将成为P2P用户交换的主体。2003年全球约有价值800亿美金的软件被安装到计算机中,但其中只有510亿美金的软件为合法版本,其余的都是盗版*P2P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网络版权的威胁,http://www.chineseinla.com/f/page_viewtopic/t_1381.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6-01-20。。P2P文件交换技术已对网络知识产权构成巨大威胁。利用法律手段禁止网络用户通过P2P技术实施著作权侵权行为,维护著作权人的权利势在必行。
(二)追诉直接侵权者所必需
网络用户可以为自己注册任何形式的网名以进行网络活动,这些网名代表了网络环境中的网络用户。P2P平台上的用户可以匿名上传及分享文档、歌曲、电影等等,其他用户可以下载分享在P2P平台上的内容。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盗版作品出现,ISP作为盗版信息提供的平台在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应当对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我国《著作权法》中没有引入“间接侵权”的概念,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规定,ISP在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与直接侵权人一起承担的是连带责任。司法实践中只要其中一方给予著作权人赔偿,著作权人就不得再向另一方主张赔偿。在ISP构成间接侵权的情况下,著作权人自然能从ISP那里获得赔偿,ISP作为间接侵权者,在侵权责任制度的震慑下也会积极寻找直接侵权者以追偿,信息披露没有显示出其重要地位。然而美国DMCA(数字千年版权法案)的“避风港”规则却为ISP提供了一定的免责条件。在免责条件下,ISP不对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再加上受著作权保护的任何作品都可能通过不同的用户以及不同的平台进行传播,权利人有必要从源头打击盗版,起诉侵权的网络用户。但直接侵权者在网络空间中的虚拟身份却使著作权人主张权利救济陷入了困境。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起诉必须有明确的被告,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6条。。获取侵权用户的真实个人信息就成为了提起侵权诉讼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ISP的信息披露义务是“避风港”规则延伸而来的义务。
(三)ISP拥有获取侵权用户信息的技术优势
相对于著作权人身份因其权利存在而具有广知性及易于识别性,侵权者的身份却很难识别*Huunting Down India’s nameless infringers,237 Managing Intell.Prop.36 2014。。作为服务中介者的ISP可以为用户获取侵权者真实身份提供帮助。网络用户在享受ISP提供的服务时通常需要进行用户注册,网络中介服务提供商拥有几乎所有登录其系统或网站的用户的个人信息,有些网络空间平台服务提供商甚至要求必须提供个人的真实信息,例如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地址、邮箱等。至于网络搜索平台服务提供商,虽然其没有用户注册这一程序,但是其可以对网络用户的IP地址进行反追踪,锁定并掌握侵权用户的信息[3]。用户作为个人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仅仅只能查看到显示在网页上的部分关于侵权用户的信息。ISP相当于网络中的一个个信息站,聚合了大量的内容信息及用户信息,集运营、管理、监督等职能于一体,既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同时也是控制者,其技术优势决定了他负有协助著作权人获取直接侵权者的真实身份的义务,这也是ISP主要民事义务之一[4]。
二、个人信息保护与ISP不当信息披露之冲突
(一)ISP负有用户个人信息保密义务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明确了用户享有匿名言论的权利,不得被侵犯。互联网用户已经习惯于认为他们的在线活动是私密的:“许多人很少评估网络监控带来的风险,并继续从事网络活动,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导致信息暴露。”他们通常在完全匿名的情况下访问互联网, 他们的身份被认定为是私有的,除非有正当的原因才会被揭露[5]。一般来说,用户在注册时都会与ISP之间存在协议,ISP负有用户个人信息保密义务,必须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防止他人盗取用户个人信息,同时不得随意泄露用户个人信息,否则将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例如违约责任。我国《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2条中明确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业务活动中收集、使用公民个人电子信息的规范。第3条则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公民个人电子信息进行保密,不得泄露。在《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第9条中同样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收集用户个人信息应当遵循一定的规则。
根据我国《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第4条的规定,个人信息突出的是“识别性”特点。而“隐私权”主要指那些常人不易获得的个人信息,具有较大私密性。个人信息中有一部分属于隐私,他人不能随意获取并泄露,一旦泄露将触及法律责任,这部分信息强调的是私密性。而剩下的部分则是不涉及隐私的个人信息,这部分个人信息的私密程度不高,更多强调的是识别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部分个人信息能够全部被他人知悉。虽然姓名、性别等个人信息在传统隐私权中并不被当成是隐私内容,但在网络环境下由于他们之间的联系形成了具有商业价值的个人信息,可以直接或间接确定个人的身份,随意披露有可能对个人造成损害,因此ISP负有保密的义务。至于联系方式及住址这类具有更高私密性程度的信息,随意披露还有可能涉嫌侵犯隐私,对ISP保密义务的要求就更加严格了。
(二)个人信息保护受到ISP不当披露的威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ISP在网络著作权领域所承担的信息披露义务似乎与其个人信息保密义务相悖,不可并存。但从利益平衡角度来看,有保护就必然有限制,任何权利都不可能进行绝对的扩张,基于特定事由个人信息保护存在一定的限制。TRIPS协定中规定对未披露的信息予以保护的同时将“保护公众所必需”作为例外*Trips Article 39.3。。在Promusicae v. Telefónica案*Article 12 of Law 34/2002 on 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s and Electronic Commerce of July 11, 2002, Spain。中,欧盟法院反驳被告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不能成为阻止网络著作权维权的法定事由,依据是《欧盟个人信息保护指令》第13条第一款专门对信息保护做出的限制,将“他人的权利与自由”作为限制个人信息保护的事由之一。信息披露只要控制在合理限度内就能与个人信息保护并行不悖。
按照前述欧盟法院的观点,著作权属于他人的正当权利,著作权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要求ISP披露侵权用户的信息本应当属于限制个人信息保护的合理事由。然而由于披露标准的缺位,ISP极易对用户个人信息进行不当披露,使得个人信息得不到合理的保护。美国DMCA(数字千年版权法案)第512(h)条规定的传票制度是为了追究实施直接侵权行为者的责任而设计的,著作权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向ISP发送传票要求披露直接侵权者的真实信息。在解决网络盗版问题的压力之下,披露侵权者的个人信息成为了侵权诉讼的必由之路。但披露侵权者个人信息的标准始终很低,原因在于法院认为著作权侵权与其他涉及网络言论自由的案件不同,在网络中进行文件共享的行为有别于发表具有价值的言论的行为,打击盗版的需要已经超越了保护侵权者身份本身,不需要第一修正案对侵权者身份进行扩张保护*Sony Music Entmt, Inc. v. Does ,326 F. Supp. 2d at 564。。尽管宪法及程序法保护用户的匿名权利,但许多法院并不因此对涉嫌著作权侵权者进行任何保护,即使原告主张的理由并不充分[6]。一方面,著作权人在维权过程中理所当然地认为出于诉讼维权的目的,涉嫌侵权者的个人信息应当被披露;另一方面,法院对侵权事实等证据没有进行审查就发送传票,这些都导致了ISP不当披露侵权者个人信息的现象出现。美国无名氏诉讼是后期发展而来的一种针对未知被告提起的诉讼,它还一度被认为是可以取代传票制度的理想诉讼形式,能够适当保护侵权者的个人信息。但无论是传票制度还是无名氏诉讼,都有可能因为ISP的不准确披露导致识别的并非是真正侵权者,并同时引发程序滥用、他人信息被不当利用等问题。
我国曾在已失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中赋予著作权人请求ISP披露侵权用户信息的权利,但对于ISP进行信息披露应当满足的条件却只字未提。依照学界的观点,这种救济模式属于私力救济。该解释失效后,在新的司法解释中没有将该条款重新纳入,主要原因就在于该条款赋予了著作权人太过宽泛的权利, ISP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判断是否有披露信息的必要,也很难把握信息披露的程度。私力救济的弊端在此体现得很明显,这种救济模式为ISP的不当信息披露提供了“温床”。除此之外,在《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第25条规定下行政机关更是无须初步的侵权证明即可直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相关侵权者的信息。为避免个人信息因为ISP的不当披露而受到威胁,任何主体以侵权之名行滥用程序之实的做法都应当得到遏制。
三、信息披露制度的救济模式及要件
(一)信息披露采用复合救济模式
学界采公力救济说的学者居多,他们普遍认为目前世界各国主要是权利人向法院提出披露申请,由法院要求ISP进行信息披露,这种途径能够保证侵权用户信息的安全。采私力救济说的学者认为我国不能完全采用类似于DMCA的公力救济模式,应当秉持自由开放的网络精神,建立宽松的信息披露制度[7]。私力救济的典型代表是“通知—反通知”规则,即著作权人可以向ISP发送通知,由ISP经审查后进行判断,对涉嫌侵权的在有效期内将通知转发给该用户,该用户可以提起“反通知”,主张其不存在侵权行为。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反通知”的,将不予披露。
笔者认为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这两种模式相得益彰,可以结合二者的特点形成复合的救济模式。著作权人可以首先采取私力救济。笔者将“通知—反通知”模式进行了完善:著作权人将通知发送给ISP请求信息披露,若用户在有效处置期内已经移除了相关内容则ISP不得披露用户信息,除非是反复侵权者;若用户在有效处置期内没有移除侵权内容,则ISP经审查认为确实存在侵权并移除侵权内容后,著作权人仍要求披露的,那么ISP可以将通知发送给用户,用户可在3日内提起“反通知”主张自己未侵权,一旦发送了“反通知”即使最后法院认为用户确实侵权了,ISP也不承担不披露信息的责任。而对于3日内未提出“反通知”的用户,ISP无正当理由不进行信息披露将承担相应的责任。此处一定要与“通知—删除—反通知”规则相区分,即使ISP认为用户内容涉嫌侵权予以移除,也不能据此在用户提起“反通知”的情形下披露用户信息。在ISP不披露用户信息的情况下,著作权人可将ISP诉至法院要求信息披露,寻求公力救济。由法院对用户行为进行完全审查考虑ISP是否有信息披露的必要。但寻求公力救济的前提是立法者将著作权人的信息披露请求权纳入到著作权法中,使著作权人的请求有法可依。
(二)信息披露需要满足的要件
1.著作权人:证明侵权存在+必要途径+主观善意
美国法院在著作权纠纷中对信息披露的标准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从刚开始的“动议——驳回”测试标准仅要求提供正当理由*Columbia Insurance Co. V. Seescandy.com,185 F.R.D. 573 (N.D. Cal. 1999)。,到考虑请求的特殊性、获得信息途径的可替代性、需要的信息以及被告对隐私的期待等*②Supra n.9 at 566-567。,再到“具有说服力”标准*See Twombly, 550 U.S. at 561-562。。著作权人在进行主张时不能仅仅表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还必须提供具体的证明侵权的材料,例如侵权的网址链接、侵权者的网络名称、作品名称及内容、作品上传时间、权利证明等等。权利人提供的事实信息及法律证据必须达到足以使人信服其合法权利正在遭受侵害的程度。有学者甚至认为,信息披露只能指向侵权人,而不能针对涉嫌侵权人,以防著作权人滥用信息披露而导致无辜信息主体个人信息的泄露[8]。在浙江东阳天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上诉案中,法院认为著作权人要求ISP披露直接侵权者真实信息的前提是在无法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获得的情况下,并且这些信息是维权及诉讼程序中所必要的,由著作权人向法院申请,法院审查后下达信息披露命令的方式来实现*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一中民终字第 2232号。,这样ISP进行信息披露才是必要且合理的,即非必要不申请披露。ISP只可以披露著作权人提起侵权诉讼所必需的用户信息,根据不同情况披露不同程度的用户信息。例如,有些情况下,ISP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直接侵权人,侵权行为为网络用户所为,需要披露部分用户信息,这部分用户信息不得涉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地址等,只需要能够使人明确直接侵权人的存在即可。在著作权人进一步要求披露直接侵权者的真实身份以追究其责任时,才能遵循私力救济程序决定是否披露。实践中还可能会出现他人因为其他涉及网络言论自由的事由或非法目的,为了获得网络用户的真实信息而假借著作权侵权之名要求ISP进行披露,以达到低标准获取他人信息的目的。鉴于此,著作权人要求ISP进行信息披露的目的必须是善意的,即维护权利之必要,而非其他目的。笔者认为法院可以通过一系列事实证据来推断申请人的主观意图。
2.涉嫌侵权用户:知情权+异议权
在大规模侵权诉讼中,著作权人往往无法准确提供侵权者的IP地址,且提供证据不全面,导致ISP进行错误披露,使得与侵权无关者的信息被公开。除此之外,在许多情形下,ISP很难判断是否有披露信息的必要,也很难把握信息披露的程度,为避免错误披露的情况发生,无论是在私力救济还是公力救济的环境下,ISP接到信息披露的请求之后都应当告知涉嫌侵权用户,并且允许涉嫌侵权用户提出异议并证明自己并非侵权人或者这种披露超出了合理的限度。
在私力救济情形下,一旦涉嫌侵权用户提出异议,ISP就不得随意披露用户信息,除非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侵权用户的侵权行为正在进行并且损害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或者侵权者实施了重复侵权行为。当私力救济无法满足著作权人的要求时,进入公力救济程序。此时信息披露也必须遵循民事诉讼法中的正当程序原则。在原告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向ISP下达原告的披露申请之后,应当要求ISP将相关情况通知给侵权用户,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知情权。如果根据ISP提供的IP地址查找到的并非真正的侵权用户,那么他人可以提出适当的动议来证明其利益的存在,例如撤销传票的请求。美国民事诉讼法第45(d)条要求用户在提出撤销传票动议的同时,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并不是侵权者或者并没有实施侵权行为。如果侵权用户在规定期间内对此提出异议,并提供了未侵权的有力证据,则ISP不能进行信息披露。要求披露对象提起的撤销申请有助于法院对事实进行更全面的了解,进而作出决定。披露对象的异议权还体现在管辖权异议方面。原告在向法院申请披露之初不知道侵权者的身份及住址等信息,可能存在法院对被告没有管辖权的情形,被告可以在收到披露通知之后对管辖权提出异议。信息披露的程序正义对于平衡著作权人和网络用户之间的利益具有现实意义。
四、ISP不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民事责任
ISP不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可能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甚至是侵权责任。首先,ISP应当对网络用户承担违约责任。ISP与网络用户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ISP提供平台或者发布信息被视为是一种要约,而用户利用平台或者打开页面接收信息视为一种承诺。前文已述,大多数网络服务需要用户进行注册,其中的《用户须知》可被视为电子协议,ISP对用户信息的保密义务属于一种附随义务,ISP无正当理由披露信息将构成对合同义务的违反,承担违约责任。其次,当用户提起了“反通知”,ISP仍然进行信息披露并且是涉及隐私的个人信息时,ISP还需要承担侵犯隐私权的责任。如果用户没有提起“反通知”,由此错误披露信息给用户造成的损害由著作权人承担责任。如果今后我国颁行《个人信息保护法》,那么ISP将可能侵犯个人信息保护权。如果ISP不当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可能还需要对著作权人承担无正当理由未履行披露义务的责任。在没有用户“反通知”或者ISP没有通知涉嫌侵权用户的情况下,ISP无正当理由拒绝披露用户信息而导致著作权人无法起诉侵权者,根据曾经的《解释》中第5条规定,应遵照《民法通则》第106条的规定,独立承担过错责任。笔者赞同《解释》中的此观点,而不赞同部分学者主张的ISP与用户作为共同侵权人对损害的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的观点。该观点将未履行披露义务的ISP当作间接侵权者。该观点的法律依据是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没有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扩大部分与侵权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但披露侵权用户信息是否属于“必要措施”?笔者认为,披露侵权用户的信息与该条明确列举的“删除、屏蔽、断开连接”三种措施相比具有不同的性质。披露侵权用户信息并不能在技术上实现防止损害的进一步扩大,其仅仅是为协助著作权人追诉直接侵权者,本质上只是一种附随义务。ISP是否承担间接侵权责任与信息披露义务无关,仅仅与“红旗”规则及“避风港”规则相关。故ISP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著作权人造成的损失须通过追究其未履行该义务的责任来弥补,ISP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综上,除非ISP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而无法获取用户的真实信息,并提供了其他协助义务,否则在合法的信息披露程序下无正当理由拒绝披露侵权用户信息的,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1]Elektra Entertainment Group,Inc. V. Bryant ,No. CV 03-6381, 2004 WL 783123, at *7 (C.D.Cal. Feb. 13, 2004).
[2]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 v. Streeter, 438 F. Supp. 2d 1065, 1073 (D. Ariz. 2006).
[3]卞豫.论网络中介服务提供商的侵权责任[D].北京:北京邮电大学,2012.
[4]蒋志培.网络与电子商务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02-205.
[5]Alice Kao, RIAA v. VERIZON: APPLYING THE SUBPOENA PROVISION OF THE DMCA. 19 Berkeley Tech. L.J. 405 (2004),at 419.
[6]Patrick Fogarty, Major Record Labels and the RIAA: Dinosaurs in a Digital Age? 9 Hous. Bus. & Tax L.J. 140, 157 (2008),at 156.
[7]郭娟,易健雄.网络服务提供者(ISP)信息披露制度——以著作权法领域为中心[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8]李舒.网络著作权执法中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5.
[责任编辑:刘庆]
D923.41
:A
:1008-7966(2017)05-0071-04
2015-04-20
何雨菁(1993-),女,福建福州人,2015级知识产权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