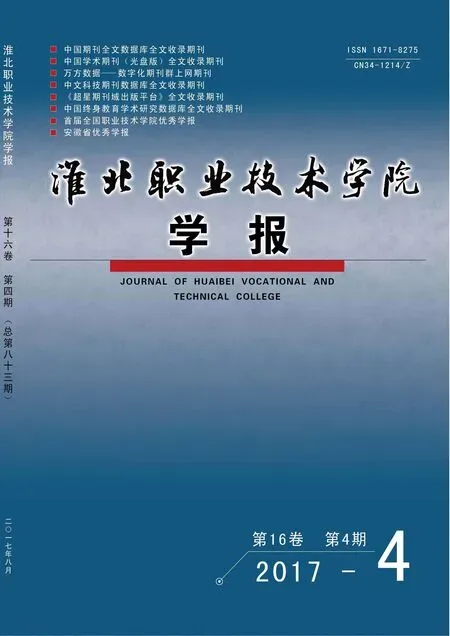盗窃毒品行为定性及量刑研究
李莎莎
(西南科技大学 法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盗窃毒品行为定性及量刑研究
李莎莎
(西南科技大学 法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虽然我国理论通说对盗窃毒品行为均认定为盗窃罪,且司法解释中也进行了如此规定,但实际上,盗窃毒品行为的定性与量刑仍然存在诸多争议。从毒品的性质来看,毒品不属于盗窃罪行为对象,且司法解释对盗窃毒品行为的定罪量刑仅以“情节轻重”作为标准,缺乏可操作性,因此,盗窃毒品行为的入罪标准与量刑标准值得深入研究。
盗窃;毒品;财物;定罪量刑
毒品作为危害社会的毒瘤已严重侵害了公民的身体健康及国家对毒品的管理秩序,虽然我国对毒品犯罪的规制已渐趋完善,但部分地区的毒品犯罪依旧十分猖獗。目前大量的毒品犯罪案件都集中在贩卖、运输及走私毒品,已出台的文件也主要针对这类型的毒品犯罪的定罪量刑做出了详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但是,在毒品犯罪多发地带,时常会发生盗窃毒品的案件,基于毒品的特殊经济价值,多数人会利用偷盗而来的毒品进行贩卖,而另一部分人则可能为吸食毒品而盗窃。
2000年《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南宁会议纪要》)中规定对盗窃毒品的以盗窃罪定罪,盗窃数额以当地毒品非法交易价格为参考;2008年《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大连会议纪要》)中同样将盗窃毒品行为定为盗窃罪,但不计犯罪数额,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定罪量刑;2013年4月4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次规定,盗窃毒品等违禁品,应当按照盗窃罪处理的,根据情节轻重量刑。[1]从常人的价值观念看来,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具有合理性,但从刑法理论的角度而言,将盗窃毒品归于盗窃罪显然无法形成逻辑自洽的体系,甚至与目前的刑法理论产生了诸多矛盾。
一、盗窃毒品行为之性质辨析
关于盗窃毒品行为的认定,我国刑法理论界存在以下观点:一种认为毒品具有一定的价值,具有财物的属性,能够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毒品属于违禁品,是法律明令禁止之物,不属于财物,因而不属于盗窃罪的行为对象。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盗窃罪保护的法益是他人的占有,即使毒品不属于财物,不能体现出所有权关系,但只要为他人所占有,一旦对毒品实施盗窃行为,仍应以盗窃罪定罪量刑。虽已有司法解释对该行为予以规制,但刑法规定的缺失使得盗窃毒品这一行为的认定显得不甚合理,笔者认为盗窃毒品不应构成盗窃罪。宾丁提出,犯罪的本质在于对规范的违反,盗窃毒品这一行为虽不应以盗窃罪来评价,但不能因为毒品的非法性质而否认盗窃毒品这一行为的违法性,根据规范违反说,这一行为侵害了法规范,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其独立成罪。[2]
第一,毒品属于违禁品,不能直接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犯罪对象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过程中对之直接施加影响的,并通过这种影响使某种客体遭受侵犯的具体的人或物。这里的“人或物”必须具有合法性。毒品作为非法物品,不能反映刑法直接保护的社会关系。并且,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必须是公私财物,而毒品显然不具备刑法上要求的财物之属性。张明楷指出:“既不具有交换价值,也不具有使用价值的财物,难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毒品基于其本身的致瘾性和毒害性而不存在使用价值及交换价值,这与盗窃罪所要求的财物有明显差别。除去毒品本身的性质,刑法理论通说认为,作为盗窃罪犯罪对象的财物必须体现出财产所有权关系,依据国家规定,毒品的占有即违法,更不存在某人享有毒品所有权一说。虽然有的学者认为盗窃罪所保护的法益为他人的占有而非所有权,但盗窃罪保护的法益并不只是独立存在的占有权。占有这一项权能源自于所有权,占有权是盗窃罪保护的直接对象,但所有权则是本罪名保护的终极目标。因而针对毒品这一违禁品而言,行为人没有所有权,占有也属于非法占有。所以,盗窃毒品的行为不可能侵犯占有人的权利。
第二,纵观我国对盗窃毒品行为的规定,皆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南宁会议纪要》规定盗窃毒品以盗窃罪处罚,盗窃数额参考当地非法交易价格。照此情形,只有盗窃的毒品数量达到当时规定的盗窃罪入罪门槛才能够入罪。但实际上,对于盗窃毒品供自己吸食之人,为规避法律只偷数量甚微的毒品,被抓获后若盗窃数额无法达到最低入罪标准,只能以行政处罚的方式处理。并且以毒品非法交易价格认定毒品金额实际上肯定了毒品的经济价值,这与我国的现实状况相违背。此后,《大连会议纪要》去掉了盗窃数额的认定,直接根据情节轻重定罪量刑,2013年出台的《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次确定了上述定罪量刑标准。这样一来,盗窃毒品行为的认定及量刑即具有很大程度的随意性。普通盗窃罪的成立要求数额较大及以上,盗窃毒品行为并非入户盗窃、扒窃等不要求数额的特殊盗窃行为,上述规定却排除了数额适用,体现出司法解释与刑法理论的矛盾。
虽然我国理论通说认为,盗窃毒品的可以定盗窃罪,但刑法规定的缺失以及司法解释的含混不清使得该行为的认定存在诸多疑惑。为厘清盗窃毒品行为的性质,首先应从该行为侵犯的客体入手。盗窃行为侵犯了他人财产权利,而毒品并非财物,因此盗窃毒品侵犯的客体并非公私财产所有权。但作为行为对象的毒品的非法持有状态不能成为盗窃行为的免责事由,盗窃毒品这一行为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行为人盗窃毒品后实施运输、贩卖等活动,将直接导致毒品的流通,严重侵害国家对毒品的管理秩序。
与此同时,我国刑法将盗窃枪支、弹药、爆炸物以及危险物品的行为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对盗窃这类违禁品的行为不以盗窃罪处罚,实际上为盗窃毒品行为的单独成罪提供了借鉴。枪支弹药、爆炸物及危险物质相较于毒品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定为财物,而刑法不将其作为盗窃罪中的公私财产是因为这些物的流通对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了威胁,不能为私人所有,因此以其可能侵害的更为广泛的社会公共安全作为犯罪客体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
二、盗窃毒品行为的定罪量刑研究
(一)盗窃毒品行为量刑规范之缺陷
我国针对盗窃毒品这一行为在刑罚配置上缺乏合理的量化标准,仅以“情节轻重”定罪量刑,不利于司法实践中的操作。首先,在理论层面其刑罚具有不确定性。根据罪刑法定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法排斥绝对的不定期刑,但现行司法解释规定模糊,没有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定刑区间,且对盗窃毒品行为的危害性程度和量刑标准未进行进一步划分、规范,没有区分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其次,由于立法规定的模糊,法官对盗窃毒品行为的认定具有极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防止刑法走向机械主义,实现实质正义的重要内容,但是法官的个体特性及自由裁量权本身的权力特性决定了权力有被滥用的风险,权力的滥用必然会导致量刑失衡,刑法的权威性将会受到严重的破坏,刑法的预防功能也无法发挥。
目前,我国对盗窃毒品行为直接以盗窃罪定罪量刑,而盗窃毒品行为的量刑标准尚不明确,不能以犯罪数额进行法定刑的区分,也不属于盗窃罪中的“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从量刑的层面来说,这显然切断了盗窃毒品行为与盗窃罪之间的内在联系,即便最终以盗窃罪定罪,但最终的量刑结果则会因为上述原因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
(二)盗窃毒品行为之定罪量刑意见
1.盗窃毒品行为之入罪情节
盗窃罪的基本犯罪行为是以盗窃数额作为入罪与否的条件,而毒品却缺乏价值衡量的基础,不能进行数额换算,因此司法解释将该行为一概认定为盗窃罪有失偏颇,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在量刑层面也难以取得社会认同。行为的入罪与否,考量的是该行为是否具有法益侵害性或者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有超越了这一底线才能成为刑法的规制对象。盗窃毒品的行为在常人看来,的确是一个应受刑法惩罚的行为,但仍有必要对其入罪门槛进行有效划分,否则无法契合罪刑法定原则。
盗窃毒品行为同样属于毒品犯罪,因此,毒品犯罪的入罪标准同样适用于盗窃毒品犯罪。我国刑法第348条非法持有毒品罪中规定了非法持有毒品入罪的最低数量标准,因而盗窃毒品行为同样应以该数量标准作为入罪标准。考虑到行为人盗窃毒品时的主观心态,可以从以下两种情形对行为人的入罪与否进行分析:
第一,行为人盗窃毒品仅为个人吸食的,如果所盗得的毒品数量没有达到348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那么对该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对其只需要进行行政处罚。盗窃毒品毕竟是一种隐秘行为,且并没有对他人的财产权益产生侵害,其社会危害性不如暴力犯罪,没有必要对其进行刑罚处罚。但是,如果行为人多次盗窃毒品供个人吸食,每次盗取的毒品数量又极少,应当对行为人定罪量刑,按盗取的毒品数量累计作为量刑标准。在行为人多次盗取毒品进行吸食的情况下,由于本人的毒瘾性和心中存在的不受刑法追究的侥幸心理极易形成常习犯,一旦行为人形成固定的犯罪习性,那么刑罚的惩戒以及社会预防措施都会归于无效。
第二,行为人为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而盗窃毒品的,要充分考量其行为目的,秉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客观行为进行定罪量刑。目的犯是指以特定目的作为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3]行为人抱着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目的而盗窃毒品的,其主观恶性显然强于盗窃毒品供个人吸食的情况,因此,只要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上述目的,就应当对其以盗窃毒品罪与相应的贩卖毒品罪等进行数罪并罚。但是在这种情形下也应当区分具体的入罪情节。首先,如果行为人盗窃的毒品数量超过了348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那么就应当对行为人进行数罪并罚。如果行为人盗窃的毒品数量并未超过最低数量标准,那么,对该盗窃行为不再定为犯罪,而是作为其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量刑情节进行从重处罚。
2.盗窃毒品行为之量刑标准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刑法又一保障人权的铁则。贝卡利亚认为,如果不符合刑罚与犯罪相适应的原则,所判处的过轻或者过重的刑罚都是实现刑罚目的的障碍。对一犯罪行为的法定刑配置应当根据其社会危害性进行程度相当的刑罚分级处理,才能有效实现刑罚矫正犯罪、预防犯罪的效果。因而对盗窃毒品行为应根据其违法性及社会危害性划分不同法定刑标准。
对于盗窃毒品行为法定刑的划分,可以参考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相关规定。首先,对于盗窃鸦片不足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足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未达到较大的,对该行为不定罪处罚;对盗窃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盗窃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其它毒品数量则参照2016年4月1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进行认定。对“情节轻重”的认定,则可以参考盗窃罪中多次盗窃、携带凶器盗窃等特殊盗窃行为及“其他严重情节”综合盗窃毒品数量进行评判,以确保达到最优效果。
除了依据毒品数量对法定刑进行划分,还应该注重毒品纯度的分析。目前毒品犯罪中也存在掺假的情况,如果对掺假的毒品直接以数量认定,会造成量刑结果严重失衡、罚不当罪的情形。因此,将毒品的含量分析作为盗窃毒品案件的量刑标准有利于正确量刑,更能体现刑法的公平公正。毒品纯度与其社会危害性密切相关。首先,毒品的纯度分析可以确定该毒品的毒害性程度,能够充分反映出毒品可能对社会产生的危害性,毒品纯度越高其危害性越大;其次,在有些数量较小的盗窃毒品案件中,对毒品纯度的分析能够使量刑更为准确,实现罚当其罪的目标。[4]因此,在毒品数量的认定过程中辅以毒品纯度的定量分析,能够使毒品犯罪的认定更为准确,不仅可以严惩犯罪人,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刑法人权保护的机能。
[1] 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29.
[2]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4-5.
[3] 何勤华.西方刑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2.
[4] 谷君.盗窃毒品处罚问题研究[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5):40-43.
责任编辑:寸 心
2017-03-01
李莎莎(1993—),女,四川广安人,刑法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
D924.3
A
1671-8275(2017)04-007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