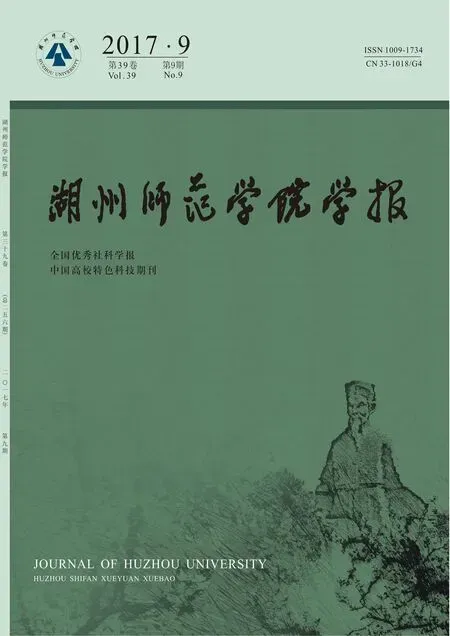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核心问题*
程广丽
(湖州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核心问题*
程广丽
(湖州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内容丰富,其核心问题则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伴随工业资本与工业文明的兴起与发展,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类环境被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被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被异化。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将资本逻辑批判与生态危机批判结合起来,并提出了解决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物质交换的方式,以最终消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割裂与异化,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正确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
人与自然;物质交换;一体性;断裂;和解
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思想与生态文明所需要面对的首要的和核心的问题。面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与生态文明问题,面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人们从多维度思索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在当前理论界,粉墨登场的“深生态学”(“深绿”、“浅绿”以及“绿红”、“红绿”等)思潮,围绕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进行了激烈的辨析,为我们思考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迪,然而,这些方案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即便是上升到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方式高度上的“红绿”思潮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因其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理解存在偏差,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视角,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立场,最终也无法成为实践上的行之有效的可操作性路径而呈现出浪漫主义的乌托邦的色彩。因此,辩证地看待西方生态思潮的理论得失,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进行阐释,发掘其积极意义与当代价值,是摆在生态文明建设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体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与自然原本是一体的,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原本是和谐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却遭到了破坏。
首先,人是自然界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本身不是为人而存在的,自然具有先在性。恩格斯指出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P32)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需条件,人对自然界来说是一种依附关系。不管人类社会怎样发展,都改变不了人离不开自然界这一客观事实。也就是说,人类永远不能离开自然界而存在,人类的存在与发展始终受到自然资源与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P669)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绝不是没有前提的,必须在一定的生存条件下进行。由于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自然也就是作为人生存的条件而存在着。自然能够满足人的生存的需要与身体的所有需要,用马克思的话说,自然就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在不同的生存条件下,人的存在状态是不一样的。自然对人的生存的制约性是非常明显的。人类发展所需要的空间和资源也都是从自然界那里得来的。缺失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自然空间,也就无所谓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伴随着人们对自然的开发的深化,自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更加巨大。因此可以说,对自然空间和自然的掌握程度,决定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真实状态。正因为此,马克思指出说:“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3](P516)历史是属于人类的历史,但同时也是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统一,自然史与人类史之间相互关联,两者不可分割。马克思曾指出,在人类社会全部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3](P519)自然界居于优先地位,自然界是人得以栖息的基本场地,是人们所有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所依赖的材料和对象,是人类无法离开的对象世界。“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的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3](P161)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对现实的人来说,更为根源性存在的是自然界。“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4](P167)。虽然受制约与受限制,但是人是能动的存在,他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从根本上说,“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2](P45)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着“交互作用”,人与自然的正常的物质交换是人类社会存在的首要前提。
其次,人与自然交互关系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强调自然的先在性,决不意味着否认人的存在的意义,相反,是为了在更为基础的意义上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P519),而且,任何一个有生命的个人“不是处于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人,而是处于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P525)全部人类历史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没有了人的存在,就不会有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更不会有生态问题的出现。因为从根本上看,“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3](P209-210)自然界对于人来说,是感性的对象性存在,自然界的存在与人的存在是一体的。“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3](P161)自然也是生命本身,自然存在物和生生不息的进化结合在一起,成就了有生命的人本身,因此,“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5](P58)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人与自然的根源性关系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同一性和一体性,人与自然处于不可分离的状态。
最后,人与自然界相联系的纽带是社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与自然交互关系的前提是现实的人的存在,但是,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并不是随意的和凌乱的,而是由社会这条纽带联结起来的。马克思指出说:“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6](P83)在人类社会生活发展进程中,起根本性作用的是劳动,“劳动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7](P181)没有了劳动,人类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无法完成。恩格斯对此更是明确指出说:“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任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3](P187)正是在社会中,自然界的存在和人的存在才有意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明确指出,由于劳动的异化而导致的对自然的破坏,现代城市的污染带有普遍性,人们的需要也是异化的,“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完全违背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8](P133-134)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异化了。尽管这个时期的青年马克思还是抽象人本主义历史观,但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问题是人与人关系的问题,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和谐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前提条件。因为从根本上说,“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8](P119)脱离了社会生活的基本语境,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社会生活中,在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才具有现实价值。
总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眼中,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不可分离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是依赖于自然而存在的,“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的,我们连同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4](P383-384)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具有自然特征,人是从自然界分化出来的,人本身就是“作为自然物存在”的个体。因此,人类应当善待自然和尊重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二、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破坏
人对自然的依附关系、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决定了人不能离开自然界而存在。如果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根源性与一体性关系一旦被打破,那么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将被破坏,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与失衡,集中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破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出现了“裂缝”。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人口的不断减少,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土地自然力遭到严重破坏,土地变得日益贫瘠。这样一来,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就失去了和谐与平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9](P393)在不断满足人的需要的欲望支配下。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导致这种断裂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据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汇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自然条件。”[10](P552)“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技巧的进步,同时是掠夺土地技巧的进步,在一段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0](P552-553)马克思认为,在资本追求无限增值的过程中,带来的是土地荒漠化问题、森林砍伐问题、煤炭耗竭问题、污染问题等一系列人与自然不和谐问题的出现。人类对自然的粗暴式的掠夺,带来的必然是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对此,恩格斯有这样一个经典论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1](P383-384)对于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后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例如英国学者戴维·佩珀指出:“‘开采’资源——获得它们的价值而不考虑对未来生产率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而成本外在化部分地是将其转嫁给未来:后代不得不为今天的破坏付出代价。”[12](P136)在佩珀看来,在资本不断追求利润的欲望驱使下,人类对于资源的无限度的开发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位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指出,在资本不断增值的过程中,自然遭到了破坏,进而的结果就是资本走向自我否定,不可避免地带来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他明确指出说:“那些没有涉及资本主义运行方式以及资本主义无法在其中进行运转的方式的环境政策,和那些没有在总体上涉及生产条件的问题以及没有在具体的层面上涉及生态学的问题的经济政策,都将可能是失败的,或者甚至会对环境条件的恶化起推波助澜的作用。”[13](P294-295)奥康纳认为,如果不涉及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思考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都是无济于事的,资本的不断积累必然会带来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
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的失衡,使得人们不得不正视眼前的现实,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维持这一关系和谐的重要性。恩格斯指出说:“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地、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14](P999)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使用的“物质交换”的概念,其实是新陈代谢的意思,它不仅具有生态意义,而且也具有社会意义。在客观上看,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交换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现实的。
三、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合理调节
人与自然是一种依附关系,然而在工业文明的作用下,这种依附关系却被破坏。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协调与和解,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最终价值旨归。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异化的原因在于工业资本不断增值,因此,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是资本不断追求利润的产物。在不断追求利润的冲动下,人们盲目地创造着各种需求,并不断发展技术以满足这种需求。当然,这种需求之所以被马尔库塞指认为“虚假需求”,是因为它不是真实的,是工业资本疯狂扩大再生产的结果。资本的疯狂逐利,必然会无限制地榨取自然资源,破坏环境,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打破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交换。 “人类同自然的和解”[3](P63)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异化的物质交换需要被打破,人与自然的割裂需要被消解,人需要在热爱自然、尊重自然、顺从自然的基础上,保护自然,从而实现社会的发展进步。恩格斯因此明确说:“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着两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及人类自身的和解。”[15](P603)而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正常的物质交换,需要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按照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的要求改造自然界,更为根本的则是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首先,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自然有自然的规则和存在之道,不会为了某一个好的君主或者坏的君主而存在。恩格斯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4](P518)“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16](P541)尊重自然,并在此基础上承认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尊重自然的前提是正确地认识自然,把握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只有正确地理解并把握了自然的客观规律,人们才可能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人们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4](P384)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最为紧要的问题是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并自觉地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认识到自然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人类自我中心化的后果就是把自我的利益与自然界对立起来,割裂了二者的统一,看不到大自然其实就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一客观事实。一旦我们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就会克服那些一味地试图摆脱自然界而去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占有自然的错误想法。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说:“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14](P518)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史与人类史始终是紧密联系和彼此制约的,我们应当看到二者的整体性,而不能割裂它们的统一关系。
如前所述,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各种活动不得不受制于自然的活动周期,宇宙进化本身是有周期性的,地球只是宇宙中的一个天体,适合人类生存,但地球也只是宇宙天体演化过程中的短暂瞬间,适合人类生存的阶段一旦过去,人类还能不能继续寻找到新的适合自身生存的环境,目前还无法确定。因此,人的生存是有极限的。明确了这一点,人们才会看到,对于每一代人来说,人们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都受制于自身所处的自然条件的限制,而不能超越这一条件而肆意活动。在有限的自然条件下做有限的事情,就必须承认自然的基本规律并自觉受制于这一规律的制约,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实践活动。
其次,按照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来改造自然界。“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3](P196)意味着整个自然界其实就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指出:“只有一个在其中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生产一般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4](P275)在恩格斯看来,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生态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人类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原本就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一个混乱的、无节制的生产与分配的社会生产组织,必然会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甚至恶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合理调节,人与自然和解的达成,还需要人们“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P163)在人类的实践过程中,列宁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1](P183)人若要实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改造自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地突破自然的限制,创造出作为自己肢体的延伸的工具。马克思对此指出说:“自然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18](P209)在人们不断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身的需要一个个得到满足,但遗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2](P159),正是由于人的不断制造出来的永无止境的各种需要,使得已经满足了的需要又引发新的需要的产生,人与自然原本的维系的和谐关系才被破坏,人与自然正常的物质交换才会异化,人最终成为悲剧性的存在。在人类不断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支配和征服自然,使自然成为人自身存在的一部分,最终使得自然成为人的工具和人类自身活动的替代品。“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性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3](P163)“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9](P273)这说明,实践使自然成为人活动的对象,没有实践,自然不可能成为人活动的对象。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的实践对象越来越复杂,因此,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们的实践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自然的存在状态,决定了什么样的自然能够成为人的实践对象。人不但认识自然,还在不断地改造自然,人改造自然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更好地让自然为人类造福。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应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9](P928-929)马克思认为,自由王国在物质生产的彼岸,是我们追求的理想世界,因为在那里,人与自然的矛盾能够得以真正完全的解决。在必然王国阶段,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也需要合理地调节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共同控制”,决不意味着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工具理性式的控制,而是说,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如果不去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那么,自然界必然会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控制人类,而且,生产者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也不能正常进行,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达不到“合理”的水平。马克思认为,在物质生产领域,只要能够真正实现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就可以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自由王国阶段,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就能够完全彻底地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直接的斗争的真正解决。”[8](P120)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得以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界就会实现真正的和谐统一,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孜孜以求的理想。
最后,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不断追求利润的动机的驱使下,不可避免带来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恶化,带来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失衡。马克思曾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0](P928-929)“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现在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4](P1000)意思是说,人与自然和解的实现,需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需要超越资本主义主导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形态,构建新的价值观,实施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目标。鲍德里亚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追逐利润的方式是多样的,不仅是资本逻辑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各种渗透,甚至连“保护环境”这样的口号,以及发展“生态产业”这样的行为,实质上都是资本为了不断追求利润而创新发展的产物,因而不过是一种新的资本话语表达方式罢了。在他看来,甚至“生态恐怖主义”的实质也是资本不断创新、获得更多利润的手段。
我们看到,在资本不断增值和不断拓展的强大力量面前,西方近些年来一度盛行的生态主义运动所显示出来的力量就显得相对弱小。换句话说,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态主义运动的目标就难以真正实现。因为从根本上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7](P32-33)不改变一定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仅仅靠观念上的或者意识形态的运动,是难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目标的。
四、结 语
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面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出现的生态危机,面对大机器工业下人类对大自然的无限制的索取,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正是大机器工业与以及大机器工业下的大农业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与失衡,人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建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内容丰富,其理论的逻辑起点就是通过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探索,实现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探究。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思想,更加有助于我们将环境的可承受度与社会发展的速度结合起来,把发挥人的主体性与生态持续改善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方式的飞跃,切实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建构起全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实现人与自然、生态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1] 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13] 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 列宁.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杨 敏]
MaterialExchangebetweenManandNature:theCoreIssueofMarxandEngels’sEcologicalThought
CHENG Guangli
(School of Marxism,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uzhou 313000, China)
The ecological thought of Marx and Engels is very rich, and the material exchang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the core issue of Marx and Engels’s ecological thought. The capitalist society has brought abou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and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as been changed, therefore it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of material exchang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acing the ecological crisis brought by industrial capital an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Marx and Engels take capital logic criticism and ecological crisis criticism together to criticize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capitalist system, and put forward the solution to normal material exchang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so as to ultimately eliminate the separation and alien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o realize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ecological thought of Marx and Engels h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for us to correctly 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hich will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an and nature; material exchange; unity; fracture; reconciliation
2017-05-15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7NDJC006Z);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16@ZH005);湖州师范学院人文社科预研究项目“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脉络”(2016SKYY10)。
程广丽,副教授,博士后,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A811
A
1009-1734(2017)09-0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