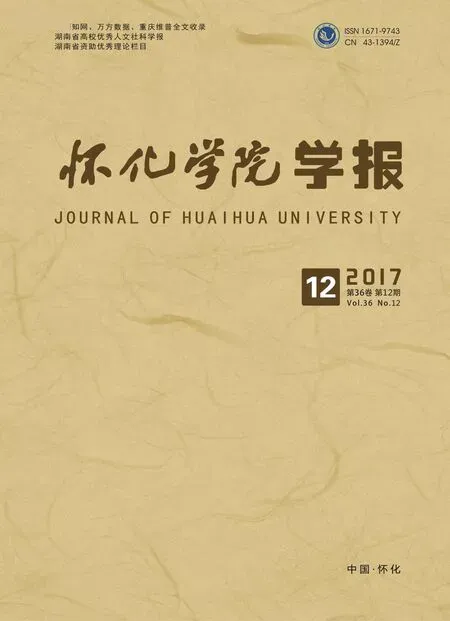民族文化生态变迁中的侗族文献内涵界定
田 收
(怀化学院图书馆地方文献研究中心,湖南怀化418008)
一、侗族文献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生态
侗族文献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存在于以族系和地域为特征的自然生态和以侗族历史更迭中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态因子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它与侗族文化生态相互依存,相互耦合,既是侗族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承载者,也是其民族文化生态产生和发展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并随着侗族文化生态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延续。
(一)侗族文献存续和发展的自然环境
据《宋史·西南溪洞诸蛮》载:“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靖州有仡伶杨姓,沅州生界有仡伶副峒官吴自由”[1]14192。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记载:“在辰、沅、靖州之地,有仡伶、仡览”。《老学庵笔记》为南宋陆游晚年所作,成书于公元1210年之前,上述文献所记的辰、沅、靖州之地就是今天的新晃、芷江、玉屏、天柱、三穗、靖县、会同一带,正是侗族聚居区的中心地带。证明侗族先民居住该地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唐代就已成为单一民族载入史册[2]1-2。
侗族主要聚居在我国大西南的东缘,东起雪峰山脉,西有苗岭支脉,北至武陵诸山,南绕九万大山,群山绵延,水江罗布,复杂多样的自然生态不仅形成了丰富的动植物群落和多样生态系统,为侗族人民创造多样的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让侗族长期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单元,以致在其内产生的侗族文化呈现出复杂、多样和相对稳定性,让侗族人民能完整保存、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使其不易被外来文化所同化。
(二)侗族文献存续和发展的社会文化生态
侗族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态随着时代更迭,不断演变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因子也随之发生变化,以此为文化土壤的侗族文献也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样态。
1.侗族文献萌芽阶段
侗族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很长一段时间是处于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原始社会阶段,侗族人民以渔猎为生,自给自足,没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一直以刻木为契、结绳记事、口耳相传等原始记录方式传递着侗族的历史记忆、神话传说、故事史诗、民族歌谣等。
侗族人民认为天地间的一切皆有鬼神主宰,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树有树神,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神灵。为了取悦自然,侗族法师定期向大自然和上天献祭,为了传承延续法师掌握的民族历史、风物掌故、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占卜星相、念咒画符、草医草药等知识,初期都是通过师徒、父子口口相传流传下来。
《侗族起源》中说:“古时人间无规矩......村寨之间少礼仪,内部肇事多,外患祸难息,祖先为了立款约,定出了侗乡的规矩。”[3]43-44宋人朱辅在《溪蛮丛笑》中载:“当地蛮夷,彼此相结,歃血誓约,缓急相援,名曰门(盟) 款。”[4]4从款词中记述的“汉王(男头领)理事在岩穴,姝王(女头领)理事在石洞”,可推知侗款产生于母系氏族衰亡、父系社会确立,原始社会解体、私有制确立的原始社会末期。此时侗族的款组织遵循“款场立规,以岩为证”习俗来作为侗族的习惯法,这类习惯法中的原始的款词称之为无文本的石头法,初期只是依靠款首们口头宣布,采用词话的形式在侗族人民中传颂。
这些原始记录已无文献可考,只是依据民间流传的口头文献推断而得。如侗族古老的传说和歌谣《人的起源》、《祖公上河》等侗族口传文献的经典之作就是论述了侗族的族源等问题。这些原始记录起初就是侗族文献萌芽样态。
2.侗族文献形成阶段
从秦汉开始,中央王朝就派兵入五溪。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秦王朝派“尉屠唯将楼土南攻越人”,“发卒五十万人,分为五军”,其中一军进入湘西南“驻潭城之岭”[5]1289-1290,光武帝刘秀派刘尚帅兵入五溪,屯兵辰溪县东南,筑城戍守[6]23等等,但都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治五溪,从秦汉到隋唐五代千余年,中央王朝虽然在侗族地区建立了郡县,但多为“入版图者存虚名,充府库者亡(无)实利响之地”[7]14182。但在此期间,也有一些文人,学者先后来到了侗族地区,宋熙宁(1068-1077)末,诚州大姓首领杨光僭父子“请于其侧建学舍,求名士教子孙”,朝廷准其所请,并派长史执掌教育,开办学校[8]14198。此后,在侗族一些地区纷纷建立了一批书院,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促进了侗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但在整个唐、宋、元时期,由于历史、社会和自然条件方面的原因,侗族社会的发展极不平衡。州县治所所在地的封建经济文化较为发达,而广大农村和边远山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极为缓慢,因而未能形成侗族文献传承延续的肥沃土壤。
元、明、清王朝为了有效地控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都竭尽全力地经营黔东,控扼进入云、贵的通道。元代,中央封建王朝在侗族地区设置军民长官司,由当地首领任官员,邑子孙世袭其职。明清两代,封建王朝对侗族地区采取“屯军”、“圈地”、“改土归流”等政策,加强对侗族地区直接统治,明末清初形成里甲制、保甲制与侗款制并存的社会组织形式,使得侗族地区头领多为其封建统治服务。因而在侗族地区,中央王朝下发的告示和公文,都会以碑刻以及公文的形式晓谕地方,随之效仿的,在侗族地区产生了大量的款组织条约的款碑和契约文献。例如,在贵州锦屏地区,随着中央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渗透,到了清代雍正、乾隆时期,木材贸易十分繁荣,人工造林已成了锦屏地区人民赖以生存、社会赖以发展的强大支柱产业。相应地,产生了大量的买卖、租佃、典当的契约、字据、簿册,官府文告,家谱,碑刻,以及反映锦屏县历史发展情况的有价值材料和民间文学(艺)作品、民间故事、古歌、传说记录和反映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经济特色的各种实物。这些数量繁多的锦屏文书成为侗族文献中亮丽的瑰宝。
中央强有力的控制,促使“科举制度”,兴办“府学”、“县学”、“义学”、“馆舍”、“书院”之风席卷侗族广大地区,“凡有子弟者皆令入国学授业”使得当地侗族青年也获得较多的读书机会,开始学习汉字和封建文化。其中不少侗族子弟考取了“秀才”、“廪生”、“贡生”。许多有志侗族青年和民间歌者利用汉字记侗音的方式记载了许多侗族文化。如款词、巫词、歌谣、戏曲等等。诸如流传于民间的200余首《耶·萨岁》或《嘎·萨岁》以及《东书少鬼》、《占推遮地多藤》、《请神圣安社堂言语》、《招谢圣母咒语》等这些脱胎于侗族原始宗教手抄本,成为侗族文献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此外,侗族人民侗族也仿借汉字构件偏旁以及造字法自制了一些酷似汉字的方块侗字,但所占比例非常小,没能形成新的文字系统,只是作为汉字记侗音的一种补充,但也为我们挖掘侗族文献提供了新的思路。
文化的传承与繁荣建立在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生态系统中,更源自于本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侗族是一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民族,虽然身处封闭的山区,却也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侗族人民是一个非常乐意接受教育而且善于学习的民族,尤其是在文化适应性和包容性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既能顺应王朝势力及其规章制度,又能主动吸收中原文化和本民族文化加以重新整合,然后将其转化到本民族的本土文化中,从而使侗族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更具有生命力,因而侗族人民成为侗族文献最虔诚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侗族人民在追求文明进步的历史过程中,与周边民族不断进行经济、文化交往,创造了大量物质和精神文明财富,在诸多的神话传说中,侗族与许多兄弟民族,尤其是苗族,都拥有类似的血缘始祖或民族起源传说,并随着口传或其他方式流传下来,形成了研究民族关系和起源的珍贵文献。
3.侗族文献的新生阶段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落实中央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的指示精神,1958年8月18至23日,经各方专家的讨论研究,《侗文方案》 (草案)表决通过。同年12月,经国家民委批准试验推行。从此,侗族人民有了自己的规范文字。在此期间,成立民族语文学校,培育了侗文师资,开始了侗文扫盲工作。贵州民族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侗汉简明词典》、《农民侗文识字课本》、《干部侗文识字课本)、《汉侗简明词典》、《侗语方言调查》以及一些科普和通俗文学读物。侗族文献终于获得了其民族承载体。但60年代以后,由于诸多原因,侗文的试点推行工作被迫停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侗文重新获得新生,各项民族工作和民族出版社和双语学校等机构开始恢复工作,期间,培训了一大批侗族文字使用者,他们用侗文来撰写各类文书、记录诗歌故事。侗族文献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之态。在侗族有些地区还出版了各类侗文版的报纸和书籍读物。如《苗文侗文报》、《侗汉词典》、《汉侗词典》、《侗语课本》、《法律法规选译:侗文译本》等,这些读物和工具书为侗族文献的发展和研究奠定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许多民间文学工作者深入侗族地区调研,搜集了大量侗族民歌、史诗、传说、故事等并翻译出版,如《侗族风情录》、《侗款》、《侗族琵琶歌》、《侗族百年实录》等等,形成了一大批侗族民间文学著作和侗族古籍资料。
4.侗族文献的蓬勃发展阶段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和各省市颁布了诸多大力发展民族语文和民族语言文化工作的决定,侗族双语工作迅速发展,培育了一批侗族双语教学师资和双语民族干部。相关的民族语文教材、读物的编写和出版取得突破,编制出版了诸如《侗汉词典》、《侗语研究》等教材,与此同时,有关侗族文化的侗族文献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在侗族文献内容研究方面,涌现了一大批就侗族服饰、建筑、音乐、习俗等文化要素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侗族卷》,这是侗族古籍文献的综合整理成果。在侗族文化研究成果方面,随着研究成果的日益丰硕,一大批侗族优秀文化产物进入国家级、省(区)级和市(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也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侗族文献。在侗族文化传播方面,许多侗族有识之士,建立了独树一帜的侗族网站,侗族微信公众号以及多种类型的侗族文化传播自媒体。这些新兴的新媒体承载了大量的有关侗族的文献资料。同时,随着侗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侗族地区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意识的不断提高,侗族地区涌现出了许多侗汉双语的各种旅游、文明道德标语等等双语文献。由此可见,侗族文献正以各种新的样态展现在人们面前。
二、民族文化生态变迁下侗族文献的内涵确定
在民族文化生态变迁的过程中,侗族人民在不同时期、不同学科、不同地域、以不同方式进行着社会实践,对这些知识和经验总结记录的侗族文献呈现出来的特点与样态,以及阐述的侗族文化内涵,都是基于其当时当地的民族文化生态中的各个因子。随着其中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因子的变化,侗族文献也不断发展延伸,从而形成一个广泛而丰富的概念系统。对于侗族文献内涵的界定我们不仅要从侗族文献的外部特征认识侗族文献的基本样态,同时要从侗族本身的民族属性出发,形成系统的资料性,三者合一才能真正实现侗族文献全部内涵的完整界定。
(一)从侗族文献的外部特征看侗族文献
侗族文献的外部特征是侗族文献构成的基本要素,同时也是侗族文献内涵系统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到侗族文献内涵的外在因子。
1.布局分散,形式多样
在地域和内容分布上,侗族文献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湖北,广西四省。另外,历史上对于侗族的记载主要散落在中央王朝零散的官方文献中,以及游历到此的文人骚客的游历笔记中,数量极少,内容极为分散。绝大多数侗族文献都只是流传于侗族人民的传说和歌谣中。从其分布可以了解侗族文献形成的主要地域状况。
在载体形态上:侗族文献呈现出多种多样样态,从传唱、碑刻衍生到汉字记侗音文本,汉字文本到最终的侗文文本等等,都是民族文化生态因子变化的必然结果。可以推断出侗族文献是随着其自身的民族文化生态的发展而发展的。
2.记载奇特,传承曲折
侗族文献的记载奇特主要是指口传古籍,在1958年以前,侗族是没有自身特定的文字的,唯一独特呈现的就只是汉字记侗音侗族文献,但由于这种记录形式没有统一规范的标准,以致此类侗族文献也仅限内部交流,随着朝代的更替和先辈的逝去、传承的断层,此类文献出现了无人翻译的“死文献现象”,因而流传下来的数量极少。因文字的缺失和弱化,侗族文化传承绝大部分依托于侗族人民的口耳相传,独特的传承方式使得口传文献成为侗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侗族文献的收集和整理过程中,我们不能因口传文献传递的易变性而忽视其在侗族文献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应积极采取有效的技术和手段对侗族口传文献加以保存和整合,尽可能完善侗族文献的全部内涵。这为我们研究侗族文献的内涵提供了良好的切入点。
(二)从侗族文献民族性来看侗族文献内涵
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民族在文献中所反映的民族文化,是民族文献的研究对象,即民族性或民族特色。从文献分类学概念角度讲,是“文化的民族性”[9]155。
侗族文献的产生与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侗族人民在本民族地域范围内,依照本侗族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去创造自己的文化而产生的记录。从而使其文献的产生和积聚就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由此可见,民族性即侗族文献内涵的本质属性。
1.侗族文献的民族性的外部体现
从文献的民族语言来看,语言和文字通常是民族感情的纽带,是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播的途径,也是鉴别文献民族性的最明显的标准。侗族口传文献中完全以其民族语言的传承的主要是其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侗族各种叙事歌和琵琶歌,以歌相传,涵盖了侗族生产生活、民俗风情、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从文献的作者来看:侗族作者作为侗族共同体的成员,他们不仅能体现本民族特点的深刻内涵,并能将其熔铸在作品中。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作者的民族成分不能决定文献内容的民族属性,只有致力于侗族传统文化研究的成果才真正是侗族文献内涵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非侗族籍作家创作的有关侗族各类体裁的作品,也应包括在侗族文献的内涵中来。
此外,在侗族文献内涵的确定过程中,我们还应对侗族作者进行整合和排序,形成一定的侗族作者体系,从作者出发,链接出其研究本民族文化相关文化成果,从而形成新一轮的侗族文献体系,丰富侗族文献内涵。
2.侗族文献的民族性的内容体现
侗族文献的民族性在文献内容上的体现是界定侗族文献内涵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文献内容涵盖侗族内容的数量,不能说有点民族内容的文献就算做是侗族文献,需要我们进行提取汇集成册,形成一定的知识体系,才能算作是完整的侗族文献。
一方面,我们需要从侗族整个民族文化生态发展的过程中,梳理出侗族文献独特的形成状况,这是侗族文献民族性的历史范畴,这种民族性历史范畴正是侗族文献逐步区分与其他民族的有力见证。但由于历史上侗族文字的缺失和发展的滞后,侗族文献民族性的历史范畴文献需要结合其重要的口传文献、其他民族以及各中央王朝对侗族地区记载的零星文献进行阐述。
另一方面,侗族文献中最集中体现其民族特色的就是侗族文化积淀。即在民族文化生态中的经济、政治、宗教、宗族、传统信仰等因素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献,从侗族古籍中的各类传说故事、叙事歌谣、契约文书到现在逐步形成体系的对侗族建筑、服饰、宗教信仰的研究性文章等等,都是侗族文献中民族性的集中体现。
最后,侗族地区自然生态系统不仅是侗族文献形成和延续的地理空间,同时侗族文献所呈现出来的样态大多数都能在当时当地的自然生态中找到对应的参照物,侗族文献中记载的内容很大一部分也是反映侗族人民适应改造自然的活动。因而根据侗族自然生态系统的描述和记载也能体现出侗族文献的民族性属性。
(三)从侗族文献的资料性属性界定侗族文献内涵
侗族文献的资料性属性也是侗族文献内涵的本质属性之一,它是基于对侗族文献外部特征和民族属性的梳理而形成的,对侗族形成延续和发展变化进行系统性概括的文献体系。只有系统成套、不断发展的侗族文献体系才能体现出侗族文献映古照今、传承延续真正价值。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从侗族文献的形成时间来看:
一是指侗族历史文献:一方面是侗族人民以各种形式,如汉字记侗音,铭刻、口传等各种形式的侗族古籍文献,另一方面是从其他民族历史文献上加以组织和综合有关侗族的文献形成的二次文献。二是指侗族再生文献:一方面是从侗族文献中挖掘出来,重新认识和加以利用,另一方面是在民族振兴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并通过现人记录而呈现。
2.从侗族文献的构成部分来看
一是在侗族文献内容上,应具备系统完整性。
侗族文献内涵首先应包括该侗族地区的自然生态资料,这是侗族文献形成发展的生存空间和民族地域特色,能很好地研究侗族民族生存、迁徙和民族融合的发展路径;其次应涵盖侗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与政治演变、人口变迁、人物、生产生活、民族融合等资料,这是侗族自身延续的发展的历史记载。最后就是民族文化特色资料,这是侗族文献内涵中最具民族代表性的资料,一方面包括无文字记录时期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口碑文献,另一方面包括从古到今,侗族形成的语言文字、风俗、宗教礼仪、文物、诗文戏曲等方面的文献。
二是在侗族文献内容上,应具备传承延续性。
民族文化生态系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其中的文化因子也随着不断变化,对其进行记录的侗族文献在形式和内容上也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我们不仅要看到侗族古籍中诸多的侗族文献,目前收集的大多数是侗族口传文献,我们还应看到当今学者在研究古籍文献以及对侗族地区民族文化生态调研过程中,基于侗族音乐、民俗等民族文化因子而形成的一大批侗族文献研究成果。这是我们梳理侗族文献内涵不可或缺的部分。
综上所述,侗族文献内涵的界定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内容总结,而应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中,认识到侗族文献内涵的研究是一个整体性、动态性的研究,需要通过在其民族文化生态系统中对目前研究成果和当下侗族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梳理出侗族文献全部内涵体系。其次,侗族文献的研究是民族性、活态性的研究,需要我们走出书斋,进入田野,传承已有侗族文献,固化侗族文化精髓部分,构建侗族文献内涵新样态。
[1][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94《蛮夷二·西南溪峒诸蛮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侗族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3]杨锡光,杨锡,吴治德整理译释.侗款[M].长沙:岳麓书社,1988.
[4]朱辅撰.溪蛮丛笑[M].北京:中华书局,1991.
[5]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6]《侗族简史》编写组.侗族简史[M].民族出版社,1985.
[7][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93《蛮夷一·西南溪峒诸蛮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94《蛮夷二·西南溪峒诸蛮下》[M].北京:中华书局,1977.
[9]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辑委员会.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四版)[S].北京:北京图书馆,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