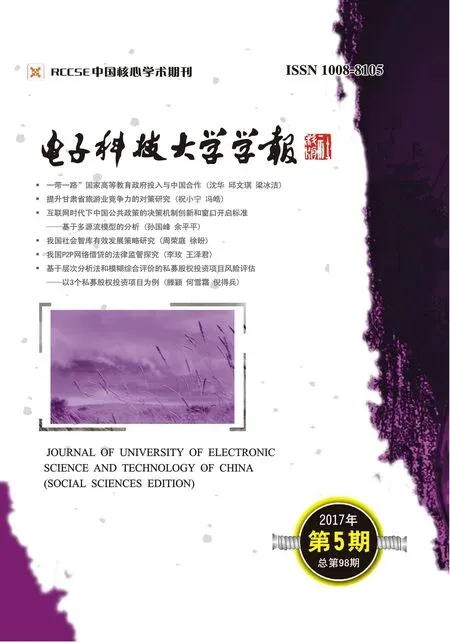积极刑法观视野下的互联网金融犯罪风险防控
□冀 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100029]
积极刑法观视野下的互联网金融犯罪风险防控
□冀 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100029]
互联网金融行为极大的改变了传统金融业的存在方式和运行模式,虽然促进了金融自由化的迅猛发展,同时也带来诸多犯罪风险,为洗钱罪、诈骗罪、非法集资等犯罪创造了温床。目前我国刑法正在出现积极刑法观的转向,刑法对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干预,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与刑法的整体性功能性转向是一致的。积极刑法观以追求安全和稳定为首要目标,但仍要给金融创新预留足够空间,需保持与其他法律的有机结合,同时继续坚持区分刑民案件之间的界限。
互联网金融;犯罪;积极刑法观
当前,我国的互联网金融产业迅猛发展,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现代金融的深度结合,金融产业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与传统金融行业相比,互联网这一平台的特殊性赋予金融业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均不同的机会与手段。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弥补了传统金融的不足,一方面以大数据为依托,创造出低门槛的直接竞争型金融市场,符合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型融资要求;一方面又带来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滋生犯罪风险,在不断“试错”中触及金融红线。各级立法者陆续出台多项法律法规,对这一新型的业态领域进行规制。
与此同时,刑法学界在近些年来也在经历着“风险刑法”“预防性刑法”的思潮,虽然目前对于刑法功能转向的认识已经更加深入,但是从社会变革大背景下研究积极刑法观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以及反思刑法的自身演变,都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即从积极刑法观的角度,分析互联网金融行业所可能带来的违法犯罪风险,实现转型中的刑法与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互动。文章提出刑法应当继续坚持目前的积极刑法观,发挥能动作用,防范金融风险,同时也要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的创新提供足够的自由空间,减少干预范围。
一、互联网金融的犯罪风险
(一)互联网金融概述
互联网金融发端于3年以前,依托于现代数字技术,从以支付宝为代表的支付结算类,逐渐发展出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存款负债类业务,最后又成功进入以P2P为代表的贷款资产类业务,已经逐步触及到传统金融业务的核心,全面冲击了传统金融业,并改变了金融业的生态[1]。就目前而言,互联网金融的业务发展也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支付类的有支付宝、快钱、财付通等,融资类如阿里小贷、拍拍贷、众筹和红岭创投等,理财类包括余额宝、众安在线、融360等,另外还有虚拟货币类如比特币、Q币等。与传统金融业最关键的不同在于,互联网金融依托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大数据统计计算,具有快速、高效与低成本的优势,和场外、涉众、混同的特征,并能打破金融垄断,实现消费者福利[2]。这种服务大众的创新模式,可以有效降低投融资者的进入门槛,并最大限度的实现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是“金融普惠”和市场化的重要创新领域。在这种数字化的直接金融市场里,互联网金融将传统金融难以惠及到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化的社会公众都覆盖其中,突破了地域和规模限制,可以迅速共享金融社会资源,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三年也指出,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并为被传统金融行业边缘化的普通个人和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机会,以聚集闲散资金,方便普通融资者入市,并形成对民间流动资本的有效配置。
基于互联网金融的存在样态和历史演进,学者们将互联网金融的特征总结为金融资源的共享性、资金供需的直接性、网络经济的虚拟性以及新型业态的风险性等[3]。具体而言,互联网金融服务于大众创新创业,又被称为众筹金融,体现了金融资源的共享性;同时,不通过银行中介,运用平台直接完成,体现了资金供需的直接性;另外,因为要依托网络经济,利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具有虚拟性的特点;最后,互联网金融作为互联网经济的一种,也会引发多重风险。互联网金融既可能存在互联网风险,也存在金融风险,如网络技术风险、业务管理风险以及法律法规风险、洗钱犯罪风险等[3]。本文关注更多的是犯罪风险,即互联网金融演化成犯罪行为的类型化以及风险防范。
(二)互联网金融犯罪风险
互联网金融在推进金融创新的同时,会导致诸多互联网金融犯罪的滋生和蔓延。在互联网金融领域,一方面可能引发的风险是经营互联网金融业务本身存在的刑事风险,主要会涉及到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等;一方面是将互联网金融作为工具,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风险,如洗钱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等[4]。
具体而言,根据互联网金融类型的不同,第一类互联网金融涉及到互联网金融的核心——支付,主要分为网上支付,第三方支付以及目前已经兴起并发展迅速的移动支付,如支付宝钱包、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可能涉及的违法犯罪主要包括洗钱和诈骗行为。例如,第三方支付机构主动或被动为犯罪分子提供资金流转和结算服务,将非法资金通过第三方支付凭条转换为合法资金,就完成了洗钱行为。而诈骗行为主要是犯罪分子通过支付宝等第三方平台,冒用被害人身份信息,将被害人银行卡内资金套现转走。除了此两类犯罪行为之外,第三方支付机构也可能涉嫌非法集资,一是第三方支付机构自身通过对预付卡内资金非法挪用,一是作为托管机构,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P2P平台未尽到审查义务,从而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互联网金融的第二类是电商平台、互联网搜索公司等应用互联网技术的在线金融理财销售,比如余额宝、百度百发百赚等,目前在线金融理财已经成为非法集资的重灾区,典型的如“中晋系”理财平台利用虚假业务、关联交易、虚增业绩等手段骗取投资人信任,向不特定公众大肆非法吸收资金340亿元,受害人超过13万,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等罪名[5]。互联网金融的第三类是P2P网贷及众筹等,至2015年年末,我国P2P网贷平台约2595家,历史累计成交金额约13652亿元,贷款余额约4394.61亿元,涉及人数约3000万人。可目前许多P2P网贷平台、众筹的发起并未获得央行、证监会等部门的审批,其中有不少就涉嫌非法集资。由于缺乏明确的监管,P2P网贷平台一直处于少监管状态,容易陷入非法集资犯罪的陷阱。
总结起来,互联网金融犯罪容易触发的罪名主要是非法集资类罪名,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另外还可能涉及合同诈骗、诈骗罪、非法经营罪以及非法向公众发行股票、债券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等其他罪名。互联网金融犯罪社会危害性巨大。普通公众对于吸纳资金方的资质及审批程序并不了解,在所谓高额利润的诱惑下,只是听信其一面之词就参与投资,具有盲从性。并且同时,互联网金融活动往往以投资波动的自然随机性掩盖了行为人的有意而为,即使出现损失,交易对手也会误认为是市场风险所致[6]。可一旦出现犯罪风险,涉及金额都可能过亿。因此,“无论是从经营正当互联网金融业务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利用互联网金融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角度来看,都凸显了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的必要性[4]”。
二、互联网金融犯罪与积极刑法观
(一)互联网金融犯罪监管
以“四大”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力量力主“严加监管”;而一些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们则认为,将互联网金融纳入传统金融监管框架会扼杀新生经济力量[7]。但是,既然互联网金融的存在对于消除金融资源垄断、活跃市场经济、合理配置资金需求都有所助益,在技术进步的驱动下,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融合必将是未来金融的基本模式。那么“堵”不如“疏”,建立以行政监管先行刑法作为最后屏障的法律规范层级体系就是当然之选。针对互联网金融的法律监管,也成为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多种规范性文件,对互联网金融行为进行规制。例如,自从2011年开始,对于P2P网贷平台的意见和态度,银监会就下发各银监局及银行系统《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通知》,对网贷平台态度谨慎,认为其容易演变为非法金融机构,法律性质不明,且业务风险难以控制。2015年7月,工信部等10部委联合下发《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勾画了巨大的互联网金融蓝图,对互联网支付、股权众筹、互联网保险等持认可和鼓励态度,并明确了“分类指导、分业监管”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思路。但在市场盲目乐观自信的同时,风险和泡沫也在滋生,E租宝、大大集团等事件纷纷爆发。2015年12月,行业草案《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出台,该草案正式对行业列出负面清单,并给出了18个月的整改过渡期限。同样是12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准予成立。2016年7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自律惩戒管理办法》出台。2016年10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各监管部委也纷纷出台相应的监管文件。2017年2月23日,银监会发布《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要求P2P平台进行资金存管,意味着对于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监管正一步步落地与执行。
上述对2011年以来规范性文件的梳理体现出,从最开始的定位不清监管缺位到逐步的细化并形成系统化的管理办法,我国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在不断的发展成熟。金融曾经是经典的高门槛行业,监管门槛高,资金门槛高,专业门槛高,一旦遭遇互联网的解构,必然会出现先期的乱象,违法犯罪行为也会应然而生。在对互联网金融的刑法规制问题上,首先,学者对于从刑法角度对互联网金融犯罪进行规制已经达成部分共识,认为基于目前互联网金融缺乏完备的征信体系和规范的融资模式,刑法应当有所作为[8]。但是学者们也同时指出,不能纯碎依靠企业和行业自律进行自我管理,也不可以过度封杀,刑法的规范应当保持应有的限度,否则会适得其反。但是,对于互联网经济犯罪的问题上,已有文章并没有结合目前刑法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而只是着眼于具体金融领域内的刑法规制。结合我国刑法向积极刑法观的转向对互联网金融犯罪问题进行分析,将给我们提供新的思路。
(二)积极刑法观视野下的互联网金融犯罪
近年来,随着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正案九的陆续出台,我国刑法立法开启了刑法观的转向,刑法规制社会生活的范围拓展、力度增强,刑法对社会的回应性增强[9]。积极刑法观的具体表现如,刑法不断拓宽处罚领域,加大处罚范围,前置化倾向明显;并且刑法更加重视公共法益和社会秩序,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加社会管理。刑法的这种功能性转向以追求安全保障和社会稳定为核心,引起不少学者的争论,有学者认为应对这一刑法转向持谨慎态度,反对过度犯罪化;也有学者提出刑法与刑事政策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密切是大势所趋,积极刑法观符合时代精神,刑法只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10]。与此同时,刑法学界还提出“风险刑法”“民生刑法”“反恐刑法”“安全刑法”或“预防型刑法”等各种理念[11],作为积极刑法观的几个面向,来展现刑法在整体大环境和具体领域中的变革。
在此社会背景下,积极刑法观对互联网金融犯罪的规制值得研究。目前语境下,追求安全保障的刑事政策往往与恐怖主义犯罪和暴力犯罪相联系,与经济犯罪相关的罪名似乎被忽略了,对安全与自由的权衡也忽视了对经济犯罪以及经济自由的思考。在互联网金融犯罪问题上,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规模和影响比较突出,会危害社会稳定。分散型的小(微)投资者受限于专业知识、个人精力及收益精激励,不了解或不关心投资风险。当全民参与互联网金融时,“非理性”投资者行为会加剧市场的敏感性、脆弱性。金融市场的信息交叉感染性特征可能与非理性的集体行为迅速结合,转化并传导为整体性恐慌[7]。比如众筹模式的参与对象十分广泛,一旦引发诉讼,波及面很大,甚至会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对互联网金融犯罪的预防与打击,比如在潜在受害者群体人数众多的非法集资案件上,或P2P借贷平台公司跑路的问题、众筹行为触碰非法集资红线问题,积极的刑法干预其实起到了社会稳定的安全阀作用,体现出对整体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维护,是与刑法整体的功能性转向相互一致的。
追求安全管理和风险预防的积极刑法观以现代社会风险增多、公众风险意识增强为生长点。而此社会景观在经济犯罪领域的影响可以体现为:从事实角度来讲,新技术的发展带来更多投融资机遇,但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引发网络技术风险、违法犯罪风险等多重风险。特别是在当前新媒体的影响下,公众的风险意识不断提高,监管者的关注度也会随之增长,继而会对刑事立法与司法产生影响。
而从刑法的立法与司法角度来看,在互联网金融方面,刑法的能动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综合历次刑法修正案即可看出,刑法修正案中对经济领域的刑事犯罪行为修改或添补的数量最大,如刑法第三章“妨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直是刑法修正案关注的重点领域。其中,第一百七十六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就是2006年被《刑法修正案六》新加入的。这一表征与我国处于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之中,违法犯罪行为方式激增相符,体现了我国刑法的能动性与灵活性;第二,在经济领域,除了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进行犯罪化以外,运用司法解释,也可以在某些罪名,如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中,在实质上扩大刑法的使用范围,如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非法经营罪”的第四款“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就是通过颁布司法解释的方式增加了非法经营外汇的行为,进一步实现了犯罪化;第三,除了刑事立法,在司法实践中,互联网金融犯罪所涉最多的为刑法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及集资诈骗罪。不少学者提出“金融准入型”罪名,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包容性过分扩大,导致罪与非罪的界限不清[7]。之所以会有此种主张,是由于准入型罪名构成要件的延展性、包容性所具备的“堵截功能”,可以在诈骗类犯罪出现证明困难时起到兜底作用;第四,虽然针对互联网金融的违法犯罪行为,与不断出台的金融行业规范和行政法规相比,还尚未出台新的刑法修正案或司法解释,但现有案件可以表明,实务领域已经综合运用刑法目前的罪名设置和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应对,打击了一系列非法集资犯罪行为。因此,无论从立法还是司法上,为了打击互联网金融犯罪,积极的刑法观都在发挥巨大的现实作用。
三、互联网金融犯罪的法律治理
在积极的刑法观的影响下,刑法功能主义、积极主义的特征逐步显现。积极刑法观是符合时代精神的,而这种偏重主观主义、社会保护、犯罪预防、超前能动立法的刑法观必将对互联网金融犯罪领域产生影响。金融的本质是资本跨时间空间配置,金融业强调对风险的控制,在目前强调风险预防、安全为先的社会中,如何通过法律包括刑法来进行风险干预,以及以合理的法律规范反应、规避这些风险是问题的关键。积极的刑法观天然具有扩张刑法的趋势,但是刑法的规制也应有限度,未来的互联网金融犯罪治理应坚持以下几点基本原则:
(一)积极刑法观仍应给金融创新预留足够空间
虽然积极刑法观主张对于转型社会中的风险应当及时甚至进行预先干涉,但是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金融业的创新,总是在试错中进行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监管机构所给予的宽容态度。如果过早干预,特别是通过刑法干预,则会严重抑制市场发展。多数经济模式、经济产品都是在试错中逐渐完善的,如果需要创新个体承担试错的刑事责任,则会束缚个体的手脚,也会冲击金融责任体制本身的正当性。因此,应当以P2P行业规范和行政法规的逐步出台为例,事先以适度的金融监管规则将各种互联网金融活动纳入监管框架,只将最为严重的诈骗类犯罪,如社会危害性且主观恶性均较大的集资诈骗行为进行犯罪化处理。
但是同时,新的社会背景往往赋予刑法新的机能,需要刑法从消极主义转为积极主义,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突出矛盾。由于新技术的发展、运用与传统监管手段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刑法的谦抑性并不排斥设立新罪,也不排斥对严重犯罪行为加重刑罚处罚。比如,行政和民事责任无法体现国家对严重金融犯罪行为的谴责,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护金融客户的合法权益,并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刑法仍应打击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向公众发行股票、债券及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甚至在将来,出于必要可以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加入新的互联网金融犯罪罪名。只是目前,互联网金融作为新生事物,对新生经济样态的发展要预留足够的空间。严厉的刑法必须要保持住必要的限度,以实现防范金融风险与维护金融自由的平衡。
(二)坚持刑法与其他法律的有机结合
我国目前仍属于监管体制与创新模式的探索期。对于新事物的产生,法律的应对并不会非常及时有效。而法律对行为规则的界定不清,就会出现大量违规者。例如国内第三方支付公司在开始时,网络支付业务长期出于灰色地带,《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颁布以后,监管当局明确了第三方支付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方的市场地位,并对第三方支付进行风险管理,其行为边界也就随之明确。再以P2P网贷平台为例,此前行业的低准入门槛和监管的缺失,造成大量网贷平台角色发生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金融机构的性质。例如早在2013年7月,重庆监管部门就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已经异化的P2P网贷平台,将债权包装成理财产品向公众销售,年收益率在12%~20%之间。P2P网贷平台由单纯的“资金供需撮合”逐步演变为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机构,构成了违反准入要求的金融犯罪行为。但目前,相关的指导意见和细则已经出来,并给予了过渡期,要求P2P平台首先需要在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进行备案,备案之后有一系列的程序,比如第三方资金托管、获取相关的资质,这些程序都在逐步进行当中。通过立法方式将P2P网贷机构和从业人员的准入门槛和行为模式进行细化与明晰,可以逐步清理互联网金融领域积累下来的违法犯罪问题。
因此,虽然仍以刑法为后盾,但前提是通过其他基本法律明确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准入门槛、行为标准、责任分配和惩戒机制,将刑法与其他法律有机结合起来。而不是等到系统性风险长时期积累爆发时再适用刑法。
(三)继续坚持区分刑民界限问题
在经济犯罪领域,尤其是互联网金融领域,仍然要继续把握好刑民之间的界限问题。对于利用互联网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刑法应予以惩治和预防,但对于正常经营互联网金融业务时,由于经济风险不小心触及刑事法网的行为,则应格外谨慎处理,切不可因为社会影响和压力而侵犯经济自由和公民权利,过度犯罪化。积极刑法观虽然强调以安全和稳定为先,但仍以刑法基本原则为基石,以刑法的谦抑主义作为标准。
四、结语
金融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建立起一个更加高效、多元、安全的金融生态体系。很多互联网金融活动不仅涉及到基础性的资金支付与结算,而且还日益深度渗透到其他各项金融业务,对金融交易的对象、方法、准入规则、行为规范等要素都进行了重塑。针对日益复杂的互联网金融犯罪的治理,也应形成防控、监管、整治和管理的综合对策。在当今社会转型背景下,刑法作为综合对策的一环,即使比过去更为积极能动,也应保持必要限度,有所为,有所不为。
[1]杜静. 从“数据大”到“大数据”: 银行如何蜕变.[EB/OL]. [2017-02-20]. http://bank.hexun.com/2017-02-20/188211596.htm.
[2]杨东. 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路径[J]. 中国法学,2015(3): 80-97.
[3]任春华, 卢珊. 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及其治理[J]. 学术交流, 2014(11): 106-111.
[4]刘宪权. 论互联网金融刑法规制的“两面性”[J]. 法学家, 2014(5): 78-82.
[5]百亿级理财平台中晋系被查. [EB/OL]. [2017-02-10].http://news.163.com/16/0407/02/BK12SH2K00014Q4P.html.
[6]田光伟. 论互联网金融犯罪风险防控[J].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3): 41-43.
[7]毛玲玲. 发展中的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4(5): 4-9.
[8]傅跃建, 傅俊梅. 互联网金融犯罪及刑事救济路径[J].法治研究, 2014(11): 20-23.
[9]周光权. 积极立法观在中国的确立[J]. 法学研究,2016(4): 23-40.
[10]劳东燕. 能动司法与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论[J]. 法学家, 2016(6): 13-28.
[11]卢建平. 加强对民生的刑法保护—民生刑法之提倡[J]. 法学杂志, 2010(12): 10-13.
AbstractInternet finance has greatly changed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finance. On one hand, it facilitates financial innov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brings in a number of crimes, such as money laundering and illegal fund-raising. At present, the Chinese criminal law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ctive.Control of Internet Financial crimes helps to seek public secur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However, the current criminal law should still protect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work with the other laws, and maintain the clear boundary of criminal and civil cases.
Key wordsInternet finance; crimes; active criminal law
编 辑 邓婧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ternet Financial Crimes: with the Active Role of the Chinese Criminal Law
JI Y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D912.28;TP393.4
A
10.14071/j.1008-8105(2017)05-0056-05
2017 - 04 - 20
冀莹(1985- )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