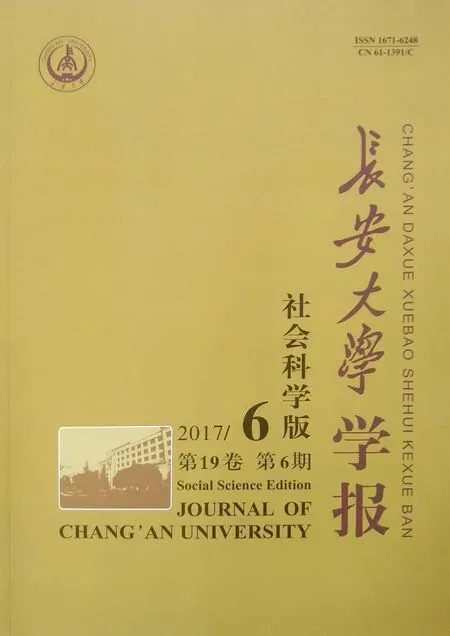拟声词拟态化在《诗经》中的应用研究
朱丹宁
(台湾政治大学中文所,台湾台北 11605)
《诗经》中存在大量拟声词,其中有部分也能拟态。这类有拟态功能的拟声词应该是onomatopee。《诗经》中拟声词可拟态的现象为人所发现较晚,1992 年欧秀慧在硕士论文[1]里开始提及,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胡晓清在《〈诗经〉:叠字构词及其对后市的影响》(《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 期)提到词语从拟声到拟态的发展,但语焉不详。[2],有的甚至在承认拟态的前提下仍基本上限定相关词语用于形容声音,或者在表意时仍直接与声音相关*欧秀慧《诗经拟声词研究》(嘉义:台湾中正大学,1992年第115 页)称:“拟声词也有它的引申义(如以声状貌之属),但使用时常用于拟声,而且使用的对象未必就是造字当初所拟的发声物,而是假借所拟之声的特征,来表示另一特征相近似的自然声响。”第118 页又称:“有些拟声字,以声状貌,可兼言发出声响的情态,所以有时会转化为拟态词或动词。如,‘行人彭彭’,传训‘多貌’;‘后稷呱矣’,屈注为‘啼也’。”。田守育启在其《日本语オノマトペの研究》*田守育启的书名意为“日语onomatopee 研究”。[3]中,针对日语的onomatopee,指出表意时其一定程度受所谓“音象征性”限制。有働真理子、苎阪直行指出任何语言中这种由拟音词而来的拟态词表意与拟音对象的样态相关,而并不限于直接与音相关*分别见有働真理子《オノマトペから学ぶもの》(《兵库教育大学研究纪要》2002年第22 期)文章题目意为《从onomatopee 学到的东西》;苎阪直行《感性の認知脳科学——擬音語?擬態語の脳内表現》(《国文学》2008 年第10 期)文章题目意为《感性的认知脑科学——拟音词、拟态词的脑内表达》)。[4-5]。在《诗经》中,也很有可能有些词可以看作是由拟声词而来,用于拟态,且并不再与声音直接相关。
鉴于《诗经》的拟声词多为重叠词,故以下打算从重叠词着手研究。有关《诗经》重叠词的专门研究,最早当自清王筠《毛诗重言》起。《毛诗重言》已经留意到这些重叠词中的同形多义、异形同义。当代仍多泛论性质的研究。以时间为序,如周棉等从《诗经》中的重叠词讲到文学作品中运用叠音词的原因与汉语叠音词的发展,发展趋势包含脱口语化[6];肖永凤讲《诗经》中的重叠词源于口语,指其因音节美感与含义模糊所以适于描绘[7];回敬娴综合地介绍了下《诗经》中的重叠词[8];高锐霞侧重于《诗经》中叠音词的语法功能[9]。分类研究则主要为语法与用法这两个层面。在语法层面,主要探讨重叠词的构词,包括叠音词的词性及其词根的词性。以时间为序,郭珑着重考察了《诗经》中叠音词的构词[10];杨爱娇特别分析了以名词作为词根的重叠词本身词性、词义与其词根间的关系[11];杨皎特别指出某些由不同字组成而其一是助词的词为“变格叠音词”[12];李磊等也考察了重叠词的构词[13]。这些研究还包括语法功能、语言风格等的探讨。以时间为序,张保宁考察了重叠词在《诗经》中与主体情感表现间的关系[14];周延云认为除修辞、音韵等形式上的美感外,中国古人独特的语义阐释方式是《诗经》重叠词所以广泛运用的原因[15];李波分析了《诗经》中重叠词的修辞方式[16];姜守阳指出重叠词在《诗经》中塑造意向或意境,有时以局部代整体[17];何海菊以重叠词为主考察了《诗经》中连绵词的韵律特点[18];刘亚科分析了《国风》中重叠词的句法功能[19];张猛刚从后代文学传承使用《诗经》重叠词的角度考察其价值[20];魏薇考察了重叠词在《诗经》中的功用与诗句中的位置[21]。综合性的研究最近的则有2013 年徐荻硕士论文[22]较全面地总结了在其之前的相关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有许多见解是共通的,对词义的理解偶有差异。重叠词的定义与分类也或有不同,但这些都是描述层面的问题——比如邓春琴等特别区分了所谓叠音词和重叠式[23],虽然名义上并非专门针对《诗经》的重叠词,但多以《诗经》为例进行研究,所揭示的争议也可见于前文所指文章;其实在同样的界定下,各家的说法没什么区别。除了特别针对《诗经》的之外,也有针对同为先秦作品的《论语》《楚辞》中重叠词的研究[24-25],他们所观察的现象及所提供的解释也大同小异——可是针对作为考察对象的重叠词究竟是拟声还是拟态,各家意见并不一致,且留有更深入探讨的空间。李静惠考察《诗经》中叠音拟声词时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没能在这方面深入探讨[26]。这应该与既往研究所谓中国古人独特语义阐释方式或重叠词的语义模糊相关,或者与所谓以局部代整体的修辞方式相关。王箕裘尝试探讨过这些“模糊”的成因,但所提“动因”“内因”“催化剂”云云没有一个能说明为什么重叠词得以模糊[27]。
《诗经》中有一些词之所以难分拟声或拟态,或者语义模糊,应该不是《诗经》语言或古汉语特有的现象。日语拟声词、拟态词号称发达,其中不少词兼具拟音、拟态这两种功能,有些词也有显著的多义性。一般认为是拟声词发展而具有了拟态功能,即使现今只用作拟态的词,其源头很可能也是拟音的。拟音扩散为拟态,这在日本学者中已是共识。井出俊哉在其2008 年硕士论文《日语与汉语的拟声词对比》中也再次介绍日语onomatopee 的引申是从拟声扩散引申[28]。2010 年,Yeldos Rakhimzhan 在其博士论文中比较日语与哈萨克语的onomatopee,指词义的引申只能是单方向的,从具体(拟音)到抽象(拟态)[29]。《诗经》拟声词中,有一些在不同场合有作为拟态词使用的痕迹。以下将试举出一些在《诗经》中有时拟声有时拟态的词以说明。由于这些词例并非全采用重叠形式,所以首先将证明一些词形式上的重叠与否不影响词义。接下来再类推《诗经》中适用此观察结果的一些经常成对出现的词例,指出各词例的拟声或拟态情形。由于这些词例经常成对出现,加上从语境可以看出其拟声与拟态时意义有所牵连,故可推定这些拟声词与拟态词同源;再适用前述关于日语onomatopee 的既往研究,可以推定这些拟态词出于拟声词。最后利用所得结论,回顾并分析前人在训释《诗经》中onomatopee 时的分歧。
一、一些重叠词的字根可以独立成词
《诗经》有些重叠词,其拆分成单字使用时,在一些情形下,也能表现原重叠词的语义。比如“明”与“明明”*《诗经》中多见以“明”或“明明”表示光艳、清洁、高尚等。其一诗之内即兼有该二词的如《大明》“明明在下……会朝清明”、《泮水》“明明鲁侯,克明其德”。但《泮水》中“明”与“明明”可能词性不一。,援用邓春琴等的见解[23]:这种情况下,构词单字本身就是词,或者在其自身重叠所成词中是自由词素。这时如果单字与该重叠词的差别只在于形式,则该单字与重叠所成之词彼此互为同位素,实际仍是同一词;如果并非如此,则重叠词之于其中单字词是新词,但是合成词*若单字在重叠词中是附着词素,本非词或自由词素,则自不待言该重叠词是单纯词。。
《诗经》中还有些重叠词,其构词单字可以与助词连用而表达与该重叠词相同的意思*这些助词诸如“其”“斯”“思”“若”“有”等。所称“助词”的这些词在这些场合的词性,是有争议的。由于非本文重点,权以“助词”称之。这个现象也早为人所知。其实归根结底这仍是其中的实词单字在表意,换言之这些实词单字可单独表示与其重叠形式相同的意思,不必与这些助词结合。
杨皎在其论文中称这些作“变格叠音词”[12]。我们认为,这样的词已非叠音,则自非叠音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无所谓变格叠音词。这么称呼不妥当。其实杨皎的用意是指出所谓变格叠音词虽与作为原型的叠音词形式不同,但语义与功能相同;而之所以使用“变格叠音词”一语,显然是因为预设“正格”的重叠词都是单纯词。但杨皎没有说明这“变格”与“正格”之间是同一词的互为同位素关系,还是不同词。如认为是不同词,则即认为在所谓变格叠音词中,与那些正格叠音词的构词单字同形的构词单字,本身既不是词,也不是自由词素。
这样的词(不限于拟声词)有:“北风其喈”(《邶风·北风》)之“喈”被视为与“喈喈”相同;“其叶沃若”(《卫风·氓》)的“沃若”与“沃沃”同;“依其在京”(《大雅·皇矣》)的“依其”“有依其士”(《周颂·载芟》)的“有依”与“依依”同……其中“喈”“喈喈”通说为拟声。“喈喈”“沃沃”“依依”等分别见于《周南·葛覃》《郑风·风雨》《小雅·出车》《小雅·鼓钟》《大雅·卷阿》《大雅·烝民》(以上“喈喈”出处)《桧风·隰有苌楚》(“沃沃”出处)《小雅·采薇》(“依依”出处)等。例如“其鸣喈喈”(《葛覃》)“夭之沃沃”《隰有苌楚》“杨柳依依”(《采薇》)。以上所举的重叠词是在《诗经》中出现了的。此外《诗经》中还有些形式与功能类似的带助词单字并没有对应的重叠词出现于《诗经》,但根据以往的解释以及惯例,可视为存在相应的重叠词符合上文描述。比如“有鷕雉鸣”的“有鷕”(《邶风·匏有苦叶》)、“击鼓其镗”,(《邶风·击鼓》)的“其镗”,并没有相应的“鷕鷕”“镗镗”出现于《诗经》,但鉴于被释作拟声而《诗经》中拟声词多采取重叠形式,所以如果承认是拟声词的话,《诗经》之外当有“鷕鷕”“镗镗”之类的词。
以上所举非重叠形态的词例中,所连用的“其”“斯”“思”“若”“有”等究竟是语法功能的助词(包括词头、词尾),还是只具备音节功能,尚有争议。杨皎认为是后者。但这样就无法否认作为附着对象的字——即组成重叠词时的字根——有作为词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上述“喈”“沃”“依”“鷕”“镗”之类单字虽与那些助词结合,但实际仍是单字成词。如果这样,则其所谓“变格叠音词”与“正格”之间,除非互为同位素,否则“正格”的也不是单纯词。也就是说,在这类助词只具备音节功能的前提下:
第一,若“正格”“变格”互为同位素,则“正格”固然是单纯词,但“变格”中那些非助词单字即已蕴含了该“正格”叠词的全部意义,可证明这种单字表意不须采用叠音形式。
第二,若“正格”“变格”本是不同词,则“正格”也是由相同的单字所表达的简单词符合而成的,也证明这种单字表意不须采用叠音形式。
第三,又杨皎所归纳的这类所谓“变格”之中,有“~其”形式。该“其”字究竟属上还是属下是有争议的。属上则如历来所释“彼其”之“其”,虚词而已*郑笺《王风·扬之水》“彼其之子”:“‘其’或‘作’记,或作‘己’,读声相似。”又《郑风·大叔于田》“叔善射忌”,毛传:“‘忌’,辞也。”郑笺“‘忌’读如‘彼己之子’之‘己’。”。如果属下,则“~”所代表的单字就并没有与助词结合为词,而是在形式上也独立成词。属下是很有可能的。 《周颂· 有瞽》有“喤喤厥声”。其“喤喤厥”不被认为成词,“厥”属下。“喤喤厥声”与“虺虺其靁”(《邶风·终风》)形式相同,故“虺虺其”也不成词。 同样描写雷声,“虺虺其”不成词而“殷其雷”(《召南·殷其雷》)的“殷其”成词,则非常奇怪。 “其~”形式是更常见的,在《诗经》中也多有。如“其雨其雨”(《卫风·伯兮》)明显如此。“其雨”与“其雷”正相当。因此“殷其雷”中“其”当属下。
推而广之,不存在“~其”形式的词*如前所述,“叔善射忌”的“忌”与“彼其之子”的“其”或可视为相当。但“射忌”固然在句末,恐怕不可视为一个词,“彼其”亦难认作一个词。故可以认为不存在“~其”形式的词。,其“其”属下。虽然《诗经》中未见直接以“殷殷”拟声者,但前举“击鼓其镗”等例时提到当存在拟声词“镗镗”但《诗经》中未见,同理可推论存在拟声词“殷殷”。于是可知“殷其雷”中的“殷”相当于“殷殷”。因此可知重叠词的单字根,可以独立成词,甚至在形式上也不借助助词。
以上虽立足于这些助词只具备音节功能的前提而论,以“殷其雷”为例,这类助词也不会是词尾(因为只有“~其”被当作这种词尾例);又从此例中“殷”可独立成词,可推知纵使作为词头,也不妨碍所缀单字独立成词。
二、构成拟音词的字非拟音用法
在构成叠音词的单字可独立成词中,有的有时用作拟音词,有时则否。固然拟音词的意思不着于形而着于音,所以可以借用一些本有其义的字。但是作为拟声词使用的情境与不作为拟声词时使用的情境非常类似的话,则不得不说二者可能并不只是同形而已,或许有意义上的贯通。比如“雝”(及其同音字)与“肃”。这两个字不作为拟音词使用时经常对举,不作为拟音词时也可与声音相关。
以“A”代指“雍”或“雝”等同音字叠音词,“a”代指其中单字:以“B”代指“肃”字叠音词,“b”代指其中单字。 “A 鸣雁”(《邶风·匏有苦叶》)“和鸾A”(《小雅·蓼萧》)“凤凰鸣矣……A 喈喈”(《大雅·卷阿》)等。其中“和鸾A”中描绘铃声,其余描绘鸟鸣。
“B 鸨羽(翼/行)”(《唐风·鸨羽》)*《毛传》解为“鸟羽声”。“B 其羽”(《小雅·鸿雁》)*《毛传》解为“羽声”。中A、B 或a、b 本身常对举。如“曷不ba,王姬之车”(《召南·何彼襛矣》)、“A 在宫,B 在庙”(《大雅·思齐》)、“于穆清庙,ba 显相”(《周颂·清庙》)、“喤喤厥声,ba 和鸣”(《周颂·有瞽》)、“有来A,至止B”(《周颂·雝》)。这里与声音相关的是“喤喤厥声,ba和鸣”。但鉴于其中既已有“喤喤”明显拟声,故此“b”或“a”不应仍为直接拟声,只是形容其气氛。《毛传》即释为:“肃,敬;雝,和。”《礼记·乐记》引该诗:“《诗》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
如上所举,虽然《诗经》中A 与B 或a 与b 对举时都不作为拟声词,但其他古诗中有作为拟声词对举情形。如阮籍《咏怀诗》(第七首)有“肃肃翔鸾,雍雍鸣雁”;而陆云《赠郑曼季诗四首鸣鹤》有“一鸣鹤在阴,戢其左翼,肃雍和鸣,在川之域”。
A、B 或a、b 对举,说明其拟声时所描绘的事态相近,非拟声时所描绘的事态也相近。除非认为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巧合,否则只能推测这里所涉的词在拟音与非拟音之间,有同源关系,而不仅仅是拟音时借用了别的词字。
如前所述,已经有很多研究证明了日语中的拟声词与拟态词相关。如果《诗经》中的拟声词及同形的拟态词也有类似关系,也并不意外。但值得一提的是,拟声词,或至少《诗经》中的拟声词,有许多本身就是具有一定拟态效果的*如前所述,欧秀慧等曾有所考察,在此不必重复。《郑风·清人》三章,每章前两句都是“清人在x,驷介yy”形式,各章x 及yy 互不相同;其中yy 是重叠拟声词。又《郑风·风雨》前两章的每章前两句都是“风雨XX,鸡鸣YY”形式,两章间XX 及YY互不相同;即使XX 不能遽定为拟声词,YY 无疑是重叠拟声词。除非这些彼此相似的语句只是出于修辞原因避免重复,否则不得不认为这些拟声词间在意义上是不同的,即其分别具有拟态意义。
于是可以推论上述A、B 或a、b,在意义上有所牵连。在“曷不ba,王姬之车”“A 在宫,B 在庙”这样的例中,纯用其意,与声音无关。大抵A、B 或a、b 所描写之声,安详和谐,故而抽象出安详和谐之意,因而引申出庄严敬穆之意。
以上虽然只是通过“肃”“雍”(或其各自同音字)为例论证《诗经》中有部分拟声词与拟态词同源,但结论应该可以适用于更多场合,比如“喤喤厥声”的“喤”与“皇皇者华”(《小雅·皇皇者华》)、“皇矣上帝”(《大雅·皇矣》)等。
三、拟声拟态词的注释分歧
以上论述了《诗经》中部分同形词有拟声与拟态的两个方面,且该拟声词与拟态词应当同源。于是《诗经》中一向被视为拟声的词,在诗句中是否只用其音,或者主要用其音,就值得怀疑了。或许有时候实际上只是借音表意,所拟之音本身并不重要。譬如现代汉语形容人“哈哈笑”或“咯咯笑”,所形容对象的笑声究竟如何在此往往并不重要,而是借拟声词来形容笑的状态而已。
正是因为拟声与拟态时词形混一,所以针对《诗经》中的这类词,古人训释时采其音还是采其态,就成了分歧点。
比如《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毛传“‘营营’,往来貌”,是用拟态;《说文》引此据为“謍謍青蝇”,并释“謍”为“小声也”。《说文》没有明言其认为“营”(或“营营”)是摹拟细小的声音,还是摹拟发出细小声音的状态(前者拟声,后者拟态),但显然纵使是拟小声音的状态,也源出拟小声音。而其与毛传所谓“往来貌”的关系,恰似今人说“蚊子嗡嗡飞”,“嗡嗡”在摹拟蚊子的声响时也营造了蚊子飞来飞去的景象。于是毛传、《说文》在此只是侧重点不同导致训释表述上有差异。
这是针对同一首诗同一处的分歧。也有针对不同诗对同样字词的解释分歧。如“交交”在《秦风·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棘”和《小雅·小宛》“交交桑扈,率场啄粟”中毛传“小貌”,在《小雅·桑扈》“交交桑扈,有莺其羽”中郑笺“犹佼佼,飞往来貌”,《小雅·桑扈》正义以为之所以不同于《小雅·小宛》毛传,是“作者各有所取”。正义的态度表明这2 种“交交”同源或本就是同词而有语境意义差别。实际也可看作是“注者各有所取”。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于《黄鸟》称:“‘交交’通作‘咬咬’,谓鸟声也。”[30]马瑞辰所指“交交”的拟声义当即“小貌”“飞往来貌”原点。其与“小貌”“飞往来貌”的关系,即类似前述“营营”之声与“小声也”的“謍”及“往来貌”的“营营”,或“蚊子嗡嗡飞”的响声与飞往来貌。
另外,本文已证一些叠音词单字可成词,“蝇营狗苟”的“营”当与“营营青蝇”有关,但可不必视为“营营”的省略。而在“蝇营狗苟”中,“营”已明显不用作拟声词了,这也能印证上述所推测的不少汉语非拟声词源出拟声词。
四、结语
由以上阐述,可以推测《诗经》中存在拟声词往拟态词转化现象。论述过程可归纳如下。
《诗经》中部分重叠词的构词单字可独立成词且其词义与所构成的重叠词相同。重叠使用时及单独使用时都成对出现的词例存在较多。 由于多次成对出现,且语义有关联,于是推测在这些的词中,相同单音节词或重叠词应同源。 由于这些词中有拟音的,也有拟态的*所举“肃”“雍”例中,如前所述,在《诗经》内各自使用时有拟音用法,但对举时只拟态不拟音,然而在其他古诗中有对举时用于拟音的情况。借鉴日语onomatopee 由拟音向拟态引申的共识,推定这些词中的拟态者源自拟声者。
这种拟声词拟态化现象在现代汉语也可以见到。比如北方有“大扑棱蛾子”这样的表述,“扑棱”本身是拟声词,描绘翅膀煽动的声音,确实有大蛾子煽动翅膀时声音明显。但这个表述很多时候只是指蛾子,不限于那样的大蛾子。固然可以认为“大扑棱蛾子”是采取夸张的修辞手法,或者本身是指大蛾子但是转喻引申后泛指蛾子,不过从结果上看,依然改变不了“扑棱”在这里已经作拟态而用的事实。东北话中以明显来自拟声词的词来拟态的现象很明显,比如“雨下得嗷嗷大”“嗷嗷有钱”中,“嗷嗷”本是拟声,而在此处已是程度副词,并非拟雨声或者富人的叫声。同时基于本文的猜想,或许能进一步探讨汉语中很多非拟声词的语源。
汉语的形容词,有很多可能如日语的拟态词一般本出于拟声词。而日语的拟态词之所以被认为很发达,是因为其形态与动词、形容词等迥然有别;汉语之所以一般不特别单立拟态词的名目,乃至于汉语文献中关于拟态词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日语的探讨,可能正是因为形态上与其他实词难以区分,尤其当其不采用重叠词形态甚至在此情形下重新构成多音节词时。比如形容词“活泼”乃至与“死”“呆滞”相对的“活”这个词,或许和《卫风·硕人》“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中的“活活”“发发”不无关系。
[1] 欧秀慧.诗经拟声词研究[D].嘉义:台湾中正大学,1992.
[2] 胡晓靖.《诗经》:叠字构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6,26(4):61-64.
[3] 田守育启.日本語オノマトペの研究[C].神户:神户商科大学经济研究所,1991.
[4] 有働真理子.オノマトペから学ぶもの[J].兵库教育大学研究纪要,2002 (22):13-21.
[5] 苎阪直行.感性の認知脳科学-擬音語·擬態語の脳内表現[J].东京:国文学,2008 (10):50-57.
[6] 周棉,胡相峰.从《诗经》中的叠音词说起[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 (3):56-61.
[7] 肖永凤.婉转附物怊怅切情——试析《诗经》中的叠音词[J].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15(1):4-5.
[8] 回敬娴.《诗经》叠音词研究[J].科教文汇:上旬刊,2009 (8):236.
[9] 高锐霞.《诗经》叠音词探微[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1,27(11):65-66.
[10] 郭珑.《诗经》叠音词新探[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6(2):49-52.
[11] 杨爱娇.《诗经》中名词作叠根的状态形容词探析[A].中国诗经学会.诗经研究丛刊(第四辑)[C],2003.
[12] 杨皎.《诗经》叠音词及其句法功能研究[D].银川:宁夏大学,2005.
[13] 李磊,王超.《诗经》叠音词探析[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 (8):289-290.
[14] 张保宁.《诗经》叠音词与主体情感表现[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5(2):51-54.
[15] 周延云.《诗经》叠字运用研究[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65-70.
[16] 李波.《诗经》中的叠音修辞[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8(1):98-100.
[17] 姜守阳.浅析《诗经》中叠词的作用[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8-19.
[18] 何海菊.《诗经》联绵词韵律特点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1.
[19] 刘亚科.《诗经·国风》叠音词分类及句法功能探析[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3(5):161-163.
[20] 张猛刚.《诗经》中叠音词语言现象传承探析[J].文教资料,2013 (36):27-28.
[21] 魏薇.《诗经》叠音词研究[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34(7):93-94.
[22] 徐荻.《诗经》重言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13.
[23] 邓春琴,李小云.叠音词和重叠式的区别[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19(1):46-48.
[24] 褚立红.《论语》叠音词浅析[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10 (11):42-43.
[25] 胡良.《楚辞》叠音构词探析[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01-103.
[26] 李静惠.《诗经》中拟声词的重言现象探究[J].东方学报,2009 (30):118-127.
[27] 王箕裘.《诗经》叠音模糊词成因初探[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2):128-130.
[28] 井出俊哉.日语与汉语的拟声词对比[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8.
[29] Yeldos Rakhimzhan.日本語とカザフ語のオノマトペ語彙の対照研究[D].札幌:北海道大学,2010.
[30]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M].陈金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