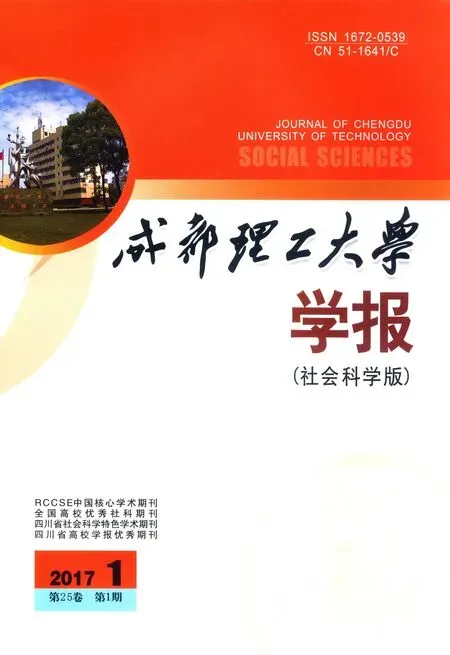略论梁启超的学术观
陈绍西
(三明学院 思政部,福建 三明 3650004)
略论梁启超的学术观
陈绍西
(三明学院 思政部,福建 三明 3650004)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梁启超更新传统“学术”概念,对“学”与“术”进行区别,把求真与实用作为一个互动的过程,消除了“中体西用论”和“西学中源论”的影响。他把中国传统实学与实事求是相联系,推动了新的学风的形成,但由于他没有明确地把二者对立统一视为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因而对“学术”的理解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梁启超;学术;科学;东方与西方;贯通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影响深远的启蒙思想家,他学识渊博、思维敏捷,以“执中鉴西”的精神和方法探讨当时关系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许多领域都有建树。在许多问题上他虽然有与革命家和政治家不同的立场,因而有许多观点常常受到人们的非议甚至是批判,但作为一个学者却在许多方面开了一代新风。他对问题的研究侧重学术,对解放人们的思想,启发人们的思考往往又有比当时的革命家和政治家更大的影响。他对学术与社会变革关系的研究至今能给人们有益的启示。
一、梁启超对“学”与“术”内涵的揭示
中国近代文化变革是与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冲击联系在一起的。严复在《天演论》等著作中阐释的进化论对中国人以西方为背景探讨中国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打开了中国学人的视野,提供了观察世界与认识中国的新方法,也促使中国学人检讨许多在历史上形成的成见,在“执中鉴西”中认识文化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树立一种新的学风。
如何界定学术是文化变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说:“吾国向以学术二字相连属为一名辞(〈礼记〉乡饮酒义云:‘古之学术道者。’〈庄子·天下篇〉云:‘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又云:‘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凡此所谓术者即学也)。惟〈汉书·震光传〉赞称光不学无术,学与术对举始此。近世泰西学问大盛,学者始将学与术之分野,厘然画出,各勤厥职以前民用。试语其概要,则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1]2351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将学术作为一个名词而用,西方人将二者分开,学是带有普遍性的真理,术是运用它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和办法。
梁启超还论述了“学”与“术”之间的关系,即“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1]2351他一方面批评中国有些人搞考据帖括学,皓首穷经,而不能为治世所用;另一方面又批评有些人离学论术,导致轻视学问,造成了照抄外国经验。因而不论是学与术相混和学与术相离都没有理解学术之真谛。他认为,中国缺少经济管理人才,缺乏经济学之研究,是因为脱离现实的学风所致。这犹如读兵书不临阵,读医书不临症,并不是说兵书医书无用,而是因为空谈学理,他说:“我国之敞,其一则学与术相混;其二则学与术相离。学混于术,则往往为一时私见所蔽,不能忠实以考求原理。术混于学,则往往因一事偶然之成败,而胶柱以用诸他事。”[1]2351
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明接触中,西方人不仅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而且也以一种求实的学风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西学中源”说。这种观点认为,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形成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迫害士人,一些人携带经典逃向了西方。后来,这些经典在西方发扬光大,不仅造成了西方各国科学技术的发达,而且造成了西方哲学和政治、经济的发达。梁启超认为,西方文化有自己的源头和发展脉络,“希腊者,欧罗巴之母也。政治出于是,学术出于是,文学出于是,技艺出于是。乃至言语风俗有形无形之事物,无一不出于是。虽谓无希腊则无欧罗巴,非过言也。希腊学派,至繁极赜,而其目的,皆以考万物蕃化之现象于其变迁无定中,而推见其本体,以求其永远不动之原理为归。”[2]1015而“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3]3079而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人们言必称孔孟,以阐释孔孟的方式为统治者的意志作注,造成了学术服从政治,以政治为归旨,而视应用技术为技艺,不足为道,不重视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从而不能实现学与术的贯通,阻塞了学术发展的道路。他说:“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3]3101他称赞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想有科学精神,所以开一代新风,并且说:“凡一学术之发达,必须为公开的且趣味的研究,又必须其研究资料比较丰富。我国人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旧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不能为讳也。”[3]3107他还认为,研究学术必须有研究的精神,敢于大胆怀疑,坚持实事求是。只要研究精神和努力方向不错,就可以取得成就。
二、梁启超对文化启蒙与学术发展关系的阐述
文化启蒙是破除传统的束缚,解放人们的思想,在激发人们创新精神的过程中从传统走向现代。在中西文明交会与撞击、传统与现代交织的背景下,如何以“执中鉴西”的方式,吸收西方学术精神,并从激活传统中形成中国学术发展的生命力,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重大问题。文化启蒙首先是批判传统的学风,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以面向未来的精神,把握社会发展要求,探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道路。这种学术不是脱离实际的空论,而是应当去改变现实、追求未来的研究。梁启超作为学贯中西的启蒙思想家,自觉地承担起了这种使命。
在新的世界形势和文化背景下,中国学术思想的建设必须吸收西方的经验,更新传统学术的偏执。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思想家,梁启超重视学术创新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并常以西方学术思想为参照分析和研究问题。他对西方思想家以学术更新推动社会变革给以髙度评价。在评价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社会的影响时,他说:“自此说一行,欧洲学界,如平地起一霹雳,如暗界放一光明,风驰云卷,仅十余年,遂有法国大革命之事。自兹以往,欧洲列国之革命,纷纷继起,卒成今日之民权世界。”[2]558在论及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时,不仅称它以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把其他国家的新思想移植到本国,造福于同胞,而且说:“托尔斯泰,生于地球第一专制之国,而大倡人类同胞兼爱平等主义,其所论盖别有心得,非尽凭藉东欧诸贤之说者焉。其所著书,大率皆小说,思想高彻,文笔豪宕,故俄国全国之学界为之一变。”[2]559
针对中国300年来之学术变迁,他说:“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3]3072针对理学家阔论性理而不关心国民生计的积习,他髙度赞扬中国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在论及颜元的学术思想时,他认为颜元在办学时信仰劳作神圣,为学讲究实用,在躬耕、习医、学技击、习礼、习乐上下功夫,使人各执一艺,并且说:“质而言之,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此元之根本主义也。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与最近教育新思潮最相合”[3]3077。
挖掘文化的源头活水,以返本开新的方式形成新的发展路向,是社会变革时期学术发展的特点。梁不仅把西方学术发展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而且把先秦文化视为中国学术思想的源头。他在评价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发展时说:这一时期“经唐虞三代以来一千多年文化的蓄积,根柢已很深厚,到这时候尽情发泄,加以传播的工具日益利便,国民交换智识的机会甚多,言论又极自由。合以上种种原因,所以当时思想界异常活泼,异常灿烂。”[4]3695这一时期学术的特点是“以济世安民为职志”,“百花齐放,万壑争流”,所以成就了许多学术大家。所以在社会变革时期,人们以复古求解放,摆脱现有成见的束缚,追求科学的研究精神,直到清末,人们所发挥的学术命题都没有走出这个范围。他评述先秦儒墨道等各家思想,在挖掘传统思想的现代价值中判断现实和追求未来,努力为中国学术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寻求新的思路。
严复《天演论》中宣传的历史进化思想从根本上扭转了西学中源论,也对梁启超学术思想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梁启超髙度评价严复译介西方著述给中国学界带来的影响,他在给严复的信中说:“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5]71并且认为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远不能与严复的学术思想相比。他说:“海禁既开,译事萌蘖。游学欧、美者,亦以百数,然无分毫影响于学界。惟侯官严几道(复),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等书,大苏润思想界。十年来思想之丕变,严氏大有力焉。”[2]619严复对西方名著的译介不同于坐而论道的形上空谈,也不同于专注于技的操作方法,而是在道与技、学与术的结合中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和经济理论,论学以实证为参照,论术以理论为根据,体现着一种全新的学术精神,所以也就得到了梁启超的髙度评价。
三、对梁启超“学术”思想的解读与评价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变革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他以中西对比的方式对“学术”的含义进行探讨,改变了历史上形成的旧观念,推动了新的认知规范的形成,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学”与“术”的关系,对于形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思维方式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有重要意义。
把“学”与“术”视为一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统一体,就既可以消除“西学中源”的思想影响,又可以摒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主张,有助于推进中国学术思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明撞击中,许多中国学人以天朝大国的心态看待西方的强势,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是把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发扬光大。这就意味着中国学术是本,西方物质文明是末,从而把应用性科学技术排斥于学术之外,以维护坐而论道的空谈风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模式则是把西方的技术附会到中国的传统道统之上,借用西方的技术成果维护中国传统封建秩序。梁启超不仅把“学”与“术”相区分,又把二者相关联,在二者的统一中定义学术,并认为西学也有“求真”和“实用”两种属性,同时又在讨论明末以来的学风转变时推崇实学和肯定了实事求是的学风,这就改变了把西学限定在“术”的层面的片面认识,又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上挖掘求实学风,从而打开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缺口,为它注入了面向现实的精神。
在学与术、道与技、求真与实用的关系中也包含着对传统学术思想的辨析,所以,梁启超不仅探求西方学术思想的渊源,而且把西方人的学问视为学与术的统一,并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变迁中探讨西方学术思想的演变,以及它是如何推进了西方文明进步的。但是,他并非认为科学技术发展给西方国家带来的全都是积极的后果,而是发现和指出了由于科学发展和个人主义的联系,造成了“文明的破产”。他说:“这种自由研究的精神和尊重个性的信仰,自然会引出第二个时代来,就是所谓科学万能自然派文学全盛时代。这个时代,由理想入到实际,一到实际,觉得从前什么善咧美咧,都是我们梦里虚构的境界,社会现象,却和他正相反,丑秽惨恶,万方同慨。一面从前的理想和信条,已经破坏得七零八落,于是全社会都陷入怀疑的深渊,现出一种惊惶沉闷凄惨的景象。”[3]2976因此,他并不是认为科学是拯救人类的灵丹妙药,也不主张科学万能,而是把科学发展与社会价值取向结合起来,并力求形成一种正确的学术观。
学术问题与社会变革密切相关,梁启超虽然肯定实学,主张实事求是,但并没有把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视为一个过程,动态地认识“学”与“术”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把实践引入学术领域。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与“术”互相促进,实践是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必不可少的关键性环节,这一点又是梁启超所没有把握的。同时,他把学术发展仅仅看成是认识一个客观世界规律的问题,而没有把这一问题与世界观和方法论联系起来。实际上,虽然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角度谈论学术问题有助于摆脱脱离实际的传统空谈的学术积习,但这又容易走向实证主义,把认识局限在现象界,从而在对“术”强调中使对问题的认识失去“学”的维度,或者无法透视出普遍的内在规律。而这个问题又不是在学术自身的范围内可以解决的。从根本上讲,这又涉及把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看成什么,自然科学重大发现对人类的认识论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自然科学的划时代成果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推进,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选择又以什么方式影响着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所有这些又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而在梁启超对“学术”问题的研究中,这些问题又涉及不多或语之不详。
“学”与“术”的问题是一个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学术思想的变革是一个在现实判断和未来发展中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认识真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按照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思维范式并不能有效推进学术的发展,纯理论的思辨或逻辑推演也不能成为学术发展的唯一有效途径。只有吸收传统文化中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精神,从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中提炼出新的思维方式,在道与技、学与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才能使学术形成和保持不竭的生命力。
[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四册) [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册) [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五册) [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六册) [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5]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 [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编辑:黄航
The Study of Liang Qichao’s Academic View
CHEN Shaoxi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Fujian 365004,China)
In the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Liang Qichao renewe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learning”, describing it as “learning” and “skills”. He treated the pursuing of truth and the practicing as a process of interaction, which offset the influence of the two theories: “Chinese learning as main part and western learning for using” and “eastern academic thoughts deriving from China”. He related Chinese traditional practical learning to the practic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helping to shape a new style of learning, but since he failed to se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 which formed a unity of opposites, as a dynamic process of practice, his understanding of “Xueshu” also had certain limitations.
Liang Qichao; learning; science; orient and west; coherence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1.015
2016-04-15
陈绍西(1967-),男,福建尤溪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B259.1
A
1672-0539(2017)01-008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