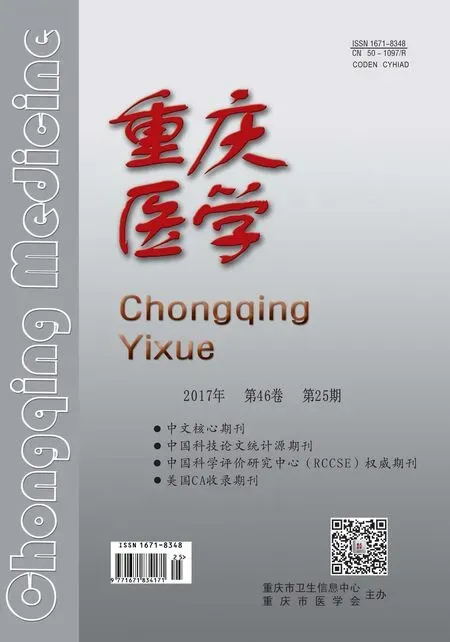特发性肺纤维化病情评估和预后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李 炯 综述,苏 立 审校
(重庆市中医院:1.呼吸科;2.肿瘤科 400021)
·综述· doi:10.3969/j.issn.1671-8348.2017.25.045
特发性肺纤维化病情评估和预后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李 炯1综述,苏 立2△审校
(重庆市中医院:1.呼吸科;2.肿瘤科 400021)
特发性肺纤维化;生物标志物;预后
特发性肺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是间质性肺疾病中最常见的类型,不同文献报道的年发病率在百万分之十几到几十之间,且有上升趋势。IPF患者总体预后极差,平均生存期约3年,甚至短于很多恶性肿瘤[1]。因此近年来IPF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在发病机制、诊断模式及治疗方法方面都有较大突破。2011年美国/欧洲/日本/拉美呼吸、胸科协会联合推荐了新的IPF诊断模式,其结合临床、影像、病理,并将多学科会诊作为IPF诊断的金标准[1]。这种新模式的确立,使得大部分的IPF患者能够明确诊断。但不同IPF患者间异质性很大,单个患者生存期难以预估,其病程可以是急进性发展,也可以在数年内相对稳定,或在稳定期突然恶化,出现急性加重(acute exacerbation of IPF,AE-IPF)。大约有5%~10%的IPF患者会出现AE-IPF,此时往往救治困难,病死率高,但特定患者是否或何时发生AE-IPF目前尚无评估方法。由于IPF的上述异质性,判断个体疾病的进程、预后及是否有AE-IPF倾向是IPF继诊断之后的重要临床问题,这直接关系到临床决策的制订,如:是否或何时开始服用抗纤维化药物或是否推荐肺移植。当前临床上估计IPF患者病情和预后主要依靠临床特征,准确性不高,也不能发现具有AE-IPF倾向的高危患者,因此IPF精确的临床诊断和个体化治疗需要探索新的标志物。同时IPF的新药临床试验也迫切需要可靠的指标来实现病例准确分层,以提高试验对药效的检验效能,并敏感反映药物干预后病情的变化。
随着IPF研究的深入,近年来发现了很多有希望的IPF病情评估和预后判断的生物标志物,这是解决IPF患者分层、预后判断、个体化治疗和疗效监测等问题的研究方向,也预示着IPF的诊疗将进入分子化、个体化的时代。本文简要综述当前IPF病情评估和预后判断的方法和近期报道的相关生物标志物,并着重介绍一些具有较高循证医学证据,有潜在临床应用前景的生物标志物。
1 IPF的临床评估指标
IPF患者的某些临床特征,包括一般情况、肺功能结果、影像和病理学特点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示其预后,这是当前临床评估IPF患者病情和预后的主要依据。通常认为:高龄、男性、吸烟史、低体质量指数、合并肺动脉高压或肺气肿提示预后不良[2]。研究显示年龄小于50岁的患者预后相对较好,而50岁以上的患者则预后差,且随年龄的增加,平均生存期进一步缩短。IPF好发于男性,有研究指出女性患者较男性有生存优势,危险比(hazard ration,HR)为0.63,95%可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95%CI)为0.41~0.97。但年龄、性别和IPF预后的关系在其他研究中并未能重复[3]。患者6 min步行距离小于250 m或24周内步行距离下降大于50 m均提示死亡风险高[4]。有研究报道经右心导管测定的伴肺动脉高压的IPF患者1年期病死率为28%,显著高于肺动脉压正常患者的5%,然而侵入性的心导管检查在IPF诊断中并不具备临床实用性,后续也缺少类似实验来验证心导管肺动脉压测定在IPF病情评估中的价值,而非侵入性的超声肺动脉压检测被认为有较大的误差。
肺功能测定是IPF的基本检查之一,多种指标中通常认为提示预后的是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和一氧化碳的弥散量(diffusing capacity of the lung for carbon monoxide,DLCO)。因FVC和DLCO的基线水平常受到其他肺部并发症如肺气肿等影响,所以其下降速度更能反映预后,通常认为DLCO下降达15%时可认为疾病进展,而文献提出FVC在6个月中下降5%~10%提示患者后续1年中死亡风险增加2倍[4]。
高分辨CT (high 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HRCT)是IPF的标准影像检查方法,除用于诊断,也可用于判断预后。研究报道HRCT上纤维化范围半定量评分与IPF患者病死率显著相关,此种评分的主要缺陷在于结果受评判者的主观影响大,重复率不高,近年来各种计算机辅助自动化定量CT技术迅速发展,有望实现对病变范围客观、数字化定量,其在IPF监测中的价值和具体运用方式有待今后研究确认[5]。
由于单一临床特征的预测准确性不高,研究中发展出整合数种临床特征的多参数预后评分系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GAP评分,其纳入了性别、年龄和肺功能这些临床最常见的参数,根据GAP指数将患者分成3期,1年预期病死率分别为6%、16%和39%[6]。相对于单一临床指标,多参数系统应该能提高IPF预测的效能,但上述评分系统建立于回顾性的数据基础上,其准确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总体而言,单独依靠临床特征来判断个体IPF患者的病情和预后准确性不够理想,也没有临床指标或评分模型能够预示AE-IPF的风险,且不能反映IPF患者发病的主要机制。因此对IPF患者更准确的病情和预后判断还有待于其他指标,比如生物标志物的发现。
2 生物标志物
2.1基因标志物 自2000年以来已经报道了数十种基因多态性与IPF的发病或者预后相关,涉及多个参与免疫或炎性反应的功能基因,提示在基因层面蕴含着IPF患者的预后信息,但很多结果来自于小样本研究且尚未被其他研究验证[7]。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数个大样本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AS)的完成,发现数个基因标志与IPF发病和预后高度相关。
MUC5B基因编码黏蛋白参与气道防御反应,2011年发现其启动子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点rs35705950上携带次要等位基因的个体IPF发病率明显增高[8-9]。后续研究发现携带rs35705950次要等位基因的IPF患者较其他IPF患者预后更好,其疾病表现为一种较缓慢的进展过程[10]。这一结果随后被多个研究团队独立重复,使得MUC5B启动子SNP成为IPF发病和预后较明确的标志物。
TOLLIP基因编码一种重要的免疫调节蛋白,参与Toll样受体介导的天然免疫反应及转化生长因子信号通路。一个大样本、多中心的GWAS研究发现:TOLLIP基因上3个SNP位点与IPF的易感性相关,其中rs5743890的次要等位基因携带者患IPF的风险低,但同时此基因型的IPF患者病死率显著增高[HR=1.72;95%CI(1.24,2.38)][11]。
新近的一项队列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携带不同TOLLIP和MUC5B基因SNP的患者对IPF药物(吡非尼酮、硫唑嘌呤、N-乙酰半胱氨酸)反应的差异,结果发现TOLLIP基因rs3750920位点为TT基因型的患者服用N乙酰半胱氨酸能显著降低其死亡、肺移植、住院或FVC下降超过10%的风险[HR=0.14;95%CI(0.02,0.83)],若此位点为CC基因型,使用该药物反而有增加患者上述风险的趋势[HR=3.23;95%CI(0.79,13.16);P=0.10][12]。
除了基因多态性以外,端粒长度是另一个关注较多的IPF预后基因标志。大约1/3的散发性IPF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端粒长度低于同龄人,而Stuart等[13]检测了370例肺纤维化患者(其中149例为IPF)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端粒的长度,并探讨其与非肺移植生存期(transplant-free survival)的关系,结果发现端粒长度是IPF患者独立的预后指数[HR=0.22;95%CI(0.08~0.63)],IPF患者生存期随端粒缩短逐步降低,而非IPF的间质性肺病患者生存与端粒长度无相关性。这一结果在后续3个独立队列研究中得到了验证[14]。
2.2蛋白标志物 外周血中蛋白标志物是IPF生物标志物中研究得最多的一类,由于标本易于获得,检测技术如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等较为普及,很多研究都尝试在血液中寻找能预测IPF疾病过程和预后的蛋白标志,研究发现参与IPF 3种核心发病机制:肺泡上皮细胞损伤、纤维沉积、免疫功能紊乱的多种蛋白都在外周血中升高,且与IPF的预后不良或快速进展相关,包括:肺表面活性蛋白、黏蛋白1(krebs von den lungen-6/ mucin 1,KL-6)、趋化因子CXCL13、CCL18、白细胞介素8(interleukin -8)、细胞间黏附分子1、基质金属蛋白酶1和7(MMP-1 and MMP-7)等等[2,15]。
KL-6是Ⅱ型肺泡上皮细胞膜上的大分子糖蛋白,其外周血浓度升高反映了肺泡上皮细胞功能的紊乱或损伤,是IPF发病机制中重要的一环,研究发现患者血清中KL-6升高与包含IPF在内的多种间质性肺病的预后不良相关,另外较高的血液KL-6水平还可能预示患者具有发生AE-IPF的风险[15]。
肺泡表面活性蛋白是另一类灵敏反映肺泡上皮损伤的生物标志,其在IPF病情和预后判断中的价值也被很多研究所关注。早期的小样本回顾性研究显示外周血SP-A和SP-D浓度与HRCT显示的肺泡炎症范围呈正比,且3年后随访存活的患者较死亡的患者有较低的血清SP-A和SP-D基线水平。后续研究也显示血液SP-A和SP-D升高均是IPF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并且SP-D在AE-IPF患者中表达更高[16]。
CXCL13是一种介导B淋巴细胞向炎症病灶迁移的趋化因子,参与许多免疫性疾病的发病过程。研究报道IPF患者血浆CXCL13水平显著高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和健康对照,IPF患者中CXCL13水平最高的亚组生存时间较其他组患者明显缩短[HR=5.5;95%CI(1.8,16.9)],且CXCL13在AE-IPF的患者中明显升高,连续测量中若CXCL13增高50%以上,则提示患者将出现呼吸衰竭[17]。
另一个可能预测患者预后的趋化因子是CCL18,文献报道CCL18血清基线水平与6个月内患者肺功能的下降程度呈正相关,以150 ng/mL作为CCL18的截断值,CCL18高水平组较CCL18低水平组死亡风险明显增高[HR=7.98;95%CI(2.49,25.51)][18]。
骨膜蛋白能促进细胞外基质沉积,与器官纤维化有关。一个小规模的前瞻性研究发现骨膜蛋白在IPF患者外周血和肺内纤维化病灶中异常高表达,血浆骨膜蛋白水平较高者其48周内的疾病进展风险较高[HR=1.47;95%CI(1.03,2.10)][19]。
上述研究显示出外周血蛋白标志物作为IPF病情和预后标志的良好前景,但许多指标的可靠性还需进一步验证。比如在另一个较大样本(n=118)IPF回顾性研究中,未能证实外周血KL-6 和SP-D是IPF独立的预后不良的因素[20]。此外抗纤维化药物吡非尼酮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连续检测血清KL-6、SP-A和SP-D变化并不能反映出患者对治疗的反应[21-22]。这些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是因为很多早期研究多为小样本、回顾性分析,且通常只选择性地检测一个或几个感兴趣蛋白。因此很多蛋白标志物的临床价值,需要更有力的研究设计来验证,比如大样本、多中心、前瞻性实验设计并采用蛋白组学层面的方法,避免单独检测几个指标带来结果的偏倚。
Richards等[23]使用多重免疫分析等技术同时检测了49个血浆蛋白,从中发现MMP-1、MMP-7、MMP-8等5种蛋白的增高能特异性地鉴别IPF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其他肺疾病,并且血浆MMP-7的水平与患者FVC%和DLCO%检测值呈负相关。Richards研究小组后续报道了通过对231例IPF患者的92个候选蛋白的检测,在推导队列中(n=140)发现血浆MMP-7、IACM-1、IL-8、VACM-1、S100A12是排除年龄、性别、肺功能差异后的独立预后因子。并经过验证队列(n=101)测定,证实了这5种蛋白的增高都预示患者的非肺移植生存期缩短,且MMP-7、IACM-1、IL-8显著升高预示患者总生存期缩短[24]。MMP-7对预后判定的价值在另一项纳入了438例IPF病例的大型队列研究中得到进一步验证,血浆MMP-7水平大于5.7 ng/mL是独立于性别、肺功能和MUC5B基因型之外的预后不良因素[HR=2.06;95%CI(1.05~4.07)][10]。
PROFILE研究是迄今为止关于IPF较大规模的前瞻性多中心队列研究,使用蛋白组学的检测技术,旨在发现新的蛋白标志并验证之前报道过的多个蛋白标志物在IPF患者中的表达情况。一项来自该研究的结果探讨了血浆中基质蛋白降解产物对IPF的预后的判断价值,发现某些胶原蛋白降解片段在IPF患者中较对照人群升高,更重要的是不断增高的胶原降解片段浓度与IPF进展显著相关,其中6种片段每3个月的增长速度对患者生存有预测作用,这提示蛋白标志物的连续测定能够动态地反映IPF的疾病进程和预后[24]。
2.3微生物标志物 细菌和病毒感染在IPF的发生和进展中可能起一定的作用。目前尚无病毒感染指标物能提示预后的报道,而最近有两项研究显示了细菌感染指标对IPF预后判断的潜在价值。在IPF的另一个大样本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COMET研究中,患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以焦磷酸测序分析其中微生物的构成,结果显示:在IPF患者肺内若存在某些特定类型链球菌和葡萄球菌则其无进展生存期短[25]。另一项研究显示IPF患者的肺部细菌负荷是患者独立的预后因素,以定量PCR测定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细菌16SrRNA的基因量,拷贝数较高者相对于较低者死亡风险显著增高[HR=4.59;95%CI(1.05,20)][26]。
3 临床指标联合生物标志物的预测模型
在发掘新的生物标志物的同时,将现有生物标志物和临床指标联合是运用生物标志物的另一思路。研究发现临床预测模型联合SP-A和SP-D检测或SP-A、MMP-7、KL-6检测,较单独使用临床预测模型提高了预后判定的准确性[20,27]。而以性别、FVC、DLCO和MMP-7水平构成患者的危险指数公式,可将患者分为高危和低危两组,高危组平均生存期仅为1.56年,显著短于低危组的5.13年[23]。这些结果说明了临床指标和生物标志物联用可提高对疾病评估和预后判定的有效性。
4 小结和展望
对于IPF这样高度异质性的疾病,运用基于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的分层管理策略,是提高其疗效的必然途径,因此寻找对IPF的病情评估和预后判断的有效方法,是目前临床上急需解决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已发现很多的IPF相关生物标志物,它们可能对疾病程度、患者预后、AE-IPF的风险有预示作用,但应该看到,IPF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报道的生物标志物要运用到临床尚缺乏足够的循证医学证据。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指标,如MUC5B基因多态性和MMP-7等具有较多高级别的证据支持,初步具备了临床应用的前景。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高通量的检测技术的发展,更多大样本前瞻性队列研究的实施,在不远的将来会出现一批准确率高、重复性好的IPF生物标志物,这些生物标志物将帮助实现患者危险程度的精确分层,预测其疾病发展的特点,为治疗决策提供依据,并灵敏地反映治疗效果,这将显著地改变当前IPF的诊疗模式,并最终改善IPF患者的预后。
[1]Raghu G,Collard HR,Egan JJ,et al.An official ATS/ERS/JRS/ALAT statement: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evidence-based guidelines for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J].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11,183(6):788-824.
[2]Ley B,Collard HR,King TE.Clinical course and prediction of survival in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J].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11,183(4):431-440.
[3]Du Bois RM,Albera C,Bradford WZ,et al.6-minute walk distance is an independent predictor of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J].Eur Res J,2014,43(5):1421-1429.
[4]Du Bois RM,Weycker D,Albera C,et al.Forced vital capacity in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test properties and minimal clinically important difference[J].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11,184(12):1382-1389.
[5]Hansell DM,Goldin JG,King J,et al.CT staging and monitoring of fibrotic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s in clinical practice and treatment trials:a position paper from the Fleischner Society[J].Lancet Respir Med,2015,3(6):483-496.
[6]Ley B,Ryerson CJ,Vittinghoff E,et al.A multidimensional index and staging system for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J].Ann Int Med,2012,156(10):684-691.
[7]Kropski JA,Blackwell TS,Loyd JE.The genetic basis of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J].Eur Respin J,2015,45(6):1717-1727.
[8]Zhang YZ,Noth I,Garcia JG,et al.A variant in the promoter of MUC5B and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J].N Engl J Med,2011,364(16):1576-1577.
[9]Seibold MA,Wise AL,Speer MC,et al.A common MUC5B promoter polymorphism and pulmonary fibrosis[J].N Engl J Med,2011,364(16):1503-1512.
[10]Peljto AL,Zhang YZ,Fingerlin TE,et al.Association between the MUC5B promoter polymorphism and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J].JAMA,2013,309(21):2232-2239.
[11]Noth I,Zhang YZ,Ma SF,et al.Genetic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susceptibility and mortality:a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J].Lancet Respir Med,2013,1(4):309-317.
[12]Oldham JM,Ma SF,Martinez FJ,et al.TOLLIP,MUC5B,and the response to N-Acetylcysteine among individuals with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J].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15,192(12):1475-1482.
[13]Stuart BD,Lee JS,Kozlitina J,et al.Effect of telomere length on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an observational cohort study with Independent validation[J].Lancet Respir Med,2014,2(7):557-565.
[14]Vij R,Noth I.Peripheral blood biomarkers in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J].Trans Res,2012,159(4):218-227.
[15]Ohshimo S,Ishikawa N,Horimasu YA,et al.Baseline KL-6 predicts increased risk for acute exacerbation of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J].Respir Med,2014,108(7):1031-1039.
[16]Collard HR,Calfee CS,Wolters PJ,et al.Plasma biomarker profiles in acute exacerbation of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J].Am J Physiol Lung Cell Mol Physiol,2010,299(1):L3-L7.
[17]Vuga LJ,Tedrow JR,Pandit KV,et al.C-X-C motif chemokine 13 (CXCL13) is a prognostic biomarker of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J].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14,189(8):966-974.
[18]Prassel A,Probst C,Bargagli E,et al.Serum CC-Chemokine ligand 18 concentration predicts outcome in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J].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09,179(8):717-723.
[19]Naik PK,Bozyk PD,Bentley JK,et al.Periostin promotes fibrosis and predicts prog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J].Am J Physiol Lung Cell Mol Physiol,2012,303(12):L1046-L1056.
[20]Song JW,Do KH,Jang SJ,et al.Blood biomarkers MMP-7 and SP-A predictors of outcome in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J].Chest,2013,143(5):1422-1429.
[21]Ley B,Brown KK,Collard HR.Molecular biomarkers in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J].Am J Physiol Lung Cell Mol Physiol,2014,307(9):L681-L691.
[22]Rosas IO,Richards TJ,Konishi K,et al.MMP1 and MMP7 as potential peripheral blood biomarkers in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J].PLoS One,2008,5(4):e93.
[23]Richards TJ,Kaminski N,Baribaud F,et al.Peripheral blood proteins predict mortality in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J].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12,185(1):67-76.
[24]Jenkins RG,Simpson JK,Saini G,et al.Longitudinal change in collagen degradation biomarkers in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an analysis from the prospective,multicentre PROFILE study[J].Lancet Respir Med,2015,3(6):462-472.
[25]Han MK,Zhou YE,Murray S,et al.Lung microbiome and disease progression in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an analysis of the COMET study[J].Lancet Respir Med,2014,2(7):548-556.
[26]Molyneaux PL,Cox MJ,Willis-Owen SA,et al.The role of bacteria in the pathogenesis and progression of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J].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2014,190(8):906-913.
[27]Kinder BW,Brown KK,Mccormack FX,et al.Serum surfactant protein-A is a strong predictor of early mortality in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J].Chest,2009,135(6):1557-1563.
R563
A
1671-8348(2017)25-3591-04
2016-12-14
2017-07-01)
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学科研面上项目(20142072)。
李炯(1979-),硕士,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呼吸病学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E-mail:drsuli030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