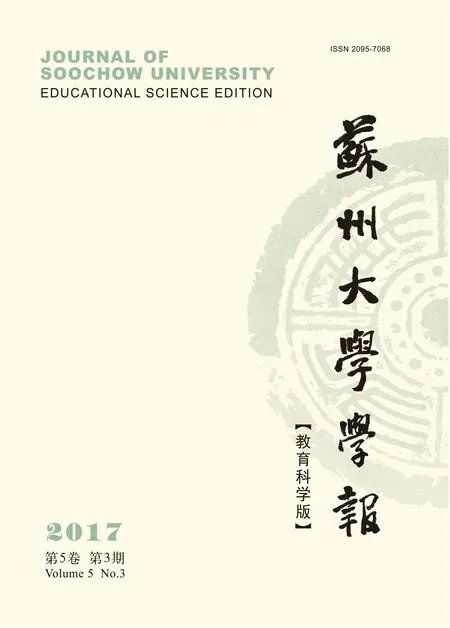辩护与认同:现代我国教育哲学研究的自知之明
刘 远 杰
辩护与认同:现代我国教育哲学研究的自知之明
刘 远 杰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现代我国教育哲学研究与发展需要有一种自知之明或自觉,即自知教育哲学之所是、所能与所不能,进而达致自明、认同及联合“他者”之可能。必须实现中国教育哲学传统的自知、自信、传承及时代性转化,特别是对近现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传统的自觉认同与发扬。教育哲学具有教育与哲学的双重规定性,教育构成本体及价值之限度,哲学构成工具或方法之限度。乌托邦精神、逻辑整合与生活回归乃是教育与哲学的真正统一。
教育哲学;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自知之明;文化自信;认同
教育哲学自产生以来就不断遭遇质疑,其合法性之辩由来已久。这些质疑声中有的来自教育实践层面,有的来自教育学术领域层面,后者中又包括非教育哲学或非教育基本理论的其他学科。不解的是,质疑者中却不乏教育哲学者自身(青年群体尤甚),其苦闷于教育哲学有何“用”或者说教育哲学不如其他一般经验科学、技术科学、应用科学等实效显著,又疑惑于“既生哲学何生教育哲学”等问题。这其中反映出来的深层问题就是,不但“他者”对教育哲学的认同度不高,就“我们自己”也尚未建构起基本的教育哲学认同与自信。为何如此?可能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缺乏必要的自知之明。所谓自知之明,简言之,“自知”方能不惑,“名正”方能言顺。以此为态度、原则与方法,塑造教育哲学独立、自信与包容之品质,是为“自我”认同之需,也是“他者”认同之源。
一、自知之明:当前我国教育哲学发展之应有态度与方法
(一)关于自知之明
我们讲的自知之明,具有日常通俗所谓“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意蕴,但不完全是。其也指学术范畴中的自知之明,当然,学术意义上的自知之明又是源自生活的,只不过是有了某种程度的学术化改造进而成为学术范畴。日常所说自知之明一般源自《老子》三十三章所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就是讲人要能够清晰正确地认识自己,知道自身的所长所短,做一个“自明之人”。自知之明表达的是一种谦逊自省的态度和扬长避短的积极价值取向,作为一个自明的过程,它又涉指一种基于认识、明了之上的自我认同的建构。
我们讲学术意义上的自知之明,主要从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理论得来。所谓文化自觉,用费孝通的话讲,就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行为”[1]207-208。从这段表述来看,其实“文化自觉”的“本体”也就是指能表示“文化自觉”本身的那个“存在”,它正是自知之明——恰恰在费孝通的“‘自觉’乃‘人’有此‘自觉’”的意义上体现了“文化自觉”作为人的意向性行为的“动词”本性。本质上,自知之明就是文化自觉本身。在费孝通的学术实践或语境里,“自知之明”强调对民族、民族文化、学科或学术本身的现实情况与发展困境有所反思和自知。在传达着费孝通作为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民族情怀与坚定文化使命感的同时,“自知之明”又作为一种方法或学术态度贯穿于费孝通的整个学术实践,不断推进其社会科学研究的反思性建构。
从而可以说,自知之明反映为人的一种自省态度、处世修养与价值担当,又是一种“自我”溯源、澄清、正名和改造的方法。一言蔽之,人之所以要有自知之明,其目的就是为了更为理性客观地认识自己,达到一种自明之境,建构起自我认同并最终实现自我超越。
(二)教育哲学需要有自知之明
言之教育哲学需要有自知之明,也就是教育哲学研究者要有此自知之明,其原因可作如下解释:首先是教育哲学者对“自知之明”本身的自觉度不够,或者说教育哲学的研究与实践缺乏必要的自知之明意识与行动;很多时候要么因教育哲学“实用性”低而自卑,要么凭借哲学的“名号”(如“科学之母”“形而上”“思辨”“深刻”等)而傲慢自大或目空一切,“我们”难以理性客观地认识“自我”而达致“自明”。其次,面对当前我国教育哲学研究与发展中的一些误区、质疑及时代困境(如教育哲学地位与价值的认同危机,经验主义、技术主义、实证主义教育学盛行时代背景下教育哲学学科特性式微,有学者就指出“毫不夸张地说,教育哲学迄今陷入了一种可以作为‘迷失自我’的困境”[2],又如教育哲学的理论品性与实践追求的矛盾性关系,教育哲学的本土观照能力不强等),教育哲学研究缺乏一种基本的“自知之明”。第三,之所以要有“自知之明”,乃在于力求通过“自知之明”,增进我们之于中国教育哲学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为当前我国教育哲学发展的实践与走向供给能量与动力。
鉴于上述原因,教育哲学应在如下意义上体现自知之明:
首先,教育哲学研究与发展应充分汲取吸纳“自知之明”所蕴含的思想、情怀和价值担当。主要在于:一是民族与文化情怀,正如“文化自觉”始终观照文化认同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问题,并“以小见大”而关切中华民族与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命运问题乃至人类文化命运问题;二是学科责任感,这一点在费孝通晚年的“学术自觉”中有充分体现,如其晚年通过“反思”与“补课”而从社会学的“实用性格”、“从实求知”方法寻求弥补与超越之“道”——充分认识与揭示出社会学研究应有的人文性以及中国丰富的文化传统在社会学研究中应具有的巨大价值——以及对“人”、“心”的关注。
某种意义上,作为思想、情怀与价值,自知之明应成为教育哲学发展进程中反思性建构与自我认同的重要内容。如费孝通说:“我觉得,人类学也好,社会学也好,从一开始,就是要认识文化、认识社会。这个认识过程的起点,是在认识自己。”呼应于此,我们也应有此“自觉自知”:一方面是从教育哲学与其对象的关系来认识“自己”,即教育哲学应一开始就要认识人、文化、社会、自然以及它们的关系,要通过认识教育实践及其与人生、文化、社会、政治等形成的复杂、多元、变动不居的关系结构,进而建构教育哲学的实践自觉与时代自觉;一方面是要从教育哲学自身的历史性与文化性来认识“自己”,即现代中国教育哲学研究要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有自知之明,不但应达到哲学体认与文化认同,更应实现传统教育哲学的现代实践转化,成为“有用之学”或“活的哲学”;再一方面是教育哲学要从自身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来认识“自己”,这也就是在强调教育哲学的民族性与现实性特征,即中国教育哲学研究与发展必然要以中国实践为动力源泉、理论基石和价值指向,中国教育哲学要观照中国现实教育问题,以“先声”的姿态,自觉以哲学的身份反思与把握现实,最终“改造”现实。
其次,教育哲学研究可在方法论意义上体现自知之明的意蕴。此时,自知之明意指反思、认识自我、认同、现实超越等动词之间的循环往复,就是不断澄清自我,通过对自身历史、价值、属性、状态、过程、趋向等方面的认识与判断而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为什么,建构学科认同。自知之明强调不断否定自我,勇于揭露和承认自身的局限性或限度所在,知“我”所不能,寻求与“他者”合作之可能,“否定”并非是贬低或摒弃自我,须知“否定之否定”才是自知之明的本义所在。自知之明又在于知“我”所能,坚守“自我”,扬我擅长,提升“自我”的独特品质、价值担当和意蕴精神。
总之,坚持通过自知之明的学科实践,首先要肯定学科本身的历史性、现实性与动态发展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内部关联意义。其次要肯定学者(个体或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对本学科的价值与情感认同。同时又在于承认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内不同学科之间所共有的文化使命、社会情怀与人类观照。在此意义上,不论是教育学、哲学,还是社会学等的自知之明,皆意味着是一种将“自身”与“他者”(人、文化、社会、民族、国家等)紧密关联起来进而建构“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在方法论意义上,同样地说,无论是社会学的自知之明,还是教育哲学的自知之明,实质上它们皆可统称为“反思的科学”,皆在于以自知而达致自明。就教育哲学而言,以自知之明作为价值原则与方法以回答我国教育哲学发展实践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在强调一种辩护与认同,目的是为实现教育哲学的反思性建构。
二、我国教育哲学的传统自知:文化与历史的自觉与认同
自知之明首先是历史自知亦即历史自觉,此“历史”即我国教育哲学传统。中国教育哲学传统的自觉自知表达为一种自我溯源,是立于当下教育哲学发展的一种回眸与寻根,此为建构我国现代教育哲学认同的基本任务。即明了当前教育哲学之文化根据,探源其文化基因;弄清其来历,反思其正谬,探索其逻辑演进之可能。这意味着我们可从对历史的认知、判断与认同中获取养料,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承,甚至而言,这又不是为了获取什么,而是教育哲学发展本身就应含有的历史意识与认知,是一种内生性的对传统的敬畏与传承,又体现为教育哲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或学科其内在发展的规定性。
(一)中国教育哲学传统思想的认同与转化
在我国,学科意义上的教育哲学始于20世纪初,而作为思想的教育哲学却古已有之并形成了悠久的中国教育哲学思想传统,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并且,“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同中国古代哲学与教育的发展历程是分不开的”[3]3。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在不同时期均有变化发展,但纵观整个发展史,可以说儒家教育哲学思想始终是主干,并由儒家中“天人合一”“政教统一”“文道结合”“知行一致”“师道尊严”等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之精华。不过,儒家未提出过“教育哲学”概念,也未明言自家的“思想”即“教育哲学”,却是儒家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实践释放出浓厚的“教育哲学”意味。孔子、孟子、荀子等的行为、主张无不体现为“教育哲学”,实是实践中的“教育哲学”。实际上,儒家哲学本就是“教人”“修道”“名礼”之学,亦即“经世致用”之学:社会哲学与人生哲学。张岱年认为:“哲学家都有其生活经历,都有其活动经验。哲学家的思想学说经常都是与他们的生活经历、活动经验有密切联系的。……儒家以道德为最高价值、在政治上提倡德治,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儒家都是教育家。儒家哲学是教育家的哲学。”[4]这就是说,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与知识与其自身的社会实践、社会生活往往具有同构性。换言之,儒家即教育家,儒家哲学实为教育哲学。除儒家教育哲学思想,我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还体现在墨、道、法等哲学流派中,不一而足,如墨家重“利”贵“义”的价值取向和文科、实科并重的教育哲学思想,道家脱俗求真的价值取向与学以求“复其初”的教育哲学思想,法家重利求强的价值取向与“壹教”与农战和法治的教育哲学思想,等等。但不论哪家哪派,它们“往往把教育问题提升到哲学(如天人关系、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人生哲学等)的高度做宏观把握,故与其称之为教育思想还不如称之为教育哲学思想更为确切”[5]引言2。我国古代哲学以人的道德发展、人生境界为旨趣,以塑造理想人格为终极归宿,如钱穆先生在其《国史新论》中说:“全部中国思想史,亦可谓即是一部教育思想史。至少一切思想之主脑,或重心,或其出发点与归宿点,则必然在教育。中国一切皆有思想,又可一言蔽之,曰:‘在教人如何做人’,即所谓做人的道理。”[6]253
由此看来,当前我国教育哲学建设与发展须重视对我国古代丰富教育哲学思想的流派、观点与方法的研究与发展,分析这些思想形成的原因与发展逻辑,从而为当下研究提供参见;更为根本的是,我国现代教育哲学研究理当继承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根本精神(哲学信念、知识与哲学家生命体验的同一关系)及重视社会伦理与“塑造人格”的哲学文化性格,这对于当前我国教育哲学研究普遍呈现的重“西化”、偏逻辑、“玩概念”与轻转化的风气无疑具有冲击、稀释与纠偏的重大意义,尤其有利于从根本上构建一种源于国人性格、文化传统与实践基础又作用于“中国人”的教育哲学文化。遗憾的是,当前我国哲学与教育哲学研究领域却总有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之声,从而我们认为,对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的认知、正名、认同与传承乃是当务之急。
特别要强调的是,如果这种正名与认同只是“自知之明”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就在于转化与应用(理论转化与实践转化),也就是一种“文化自主能力”的形成,这其中蕴含“否定之否定”和“反思性超越”的辩证法精神。对于中国教育哲学传统,我们不仅要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提炼归纳,实现理论的重塑与再现,比如“运用分析哲学的方式,通过概念的辨析、理论内涵的揭示、逻辑关系的重构,来具体把握以往哲学的理论体系和内涵”,以这种方式“回溯、考察中国哲学,同时意味着赋予中国哲学以现代的形态”[7]11;更重要的是,要使之在人类当前、现代化背景下获得“改造”与“重生”,为现代教育、未来教育所“用”。“用”乃“重生”之根本途径,“用”即“重生”,也就是重返人类生活与实践,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人们的成长哲学、社会哲学与实践哲学。但我们同时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哲学之“重生”的关键不在于它究竟是哲学还是思想①,而是首先必须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简言之,“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原因、目的和标准集中于一点,就是看它是否能够积极地、建设性地并且有其独到之处地回应现时代的现实问题”[8]。
(二)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及其认同
20世纪初期以降,教育哲学学科在我国逐步建立与发展,教育哲学“学科化”与“科学化”同步进程。从我国第一本教育哲学著作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1923)问世到20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范式在我国的确立,我国近现代教育哲学学术积淀不可谓不深厚,无论如何,皆是前辈学者基于学科发展与实践改革之需而艰辛探究之结晶。无疑,这种结晶及其背后蕴藏的学人品格已镌刻为重要的教育哲学学术传统,这是需要引起我们当下乃至今后予以高度重视的。跨越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期所呈现的不同发展特点,从整个20世纪来看,这个进程呈现两个基本的发生逻辑,由此逻辑,我们可洞见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哲学学科演变发展的总体特征(而逻辑本身又是一大特质)。首先,教育哲学学科萌生于西方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科学的直接而巨大的影响,如康德、纳托普(Natrop)、伯格森等人的哲学,夸美纽斯、赫尔巴特、杜威等人的教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共同构筑起近代我国教育哲学发展的元理论大厦或理论基石。我国教育哲学学科建设一开始便烙上了明显的“西方”印记:形式上多表现于教育哲学著作的范畴、框架、内容与思路等,实质上则体现为西方哲学所特有的强烈的科学思维与逻辑分析方法特征。遵循这一逻辑,我国教育哲学学科构建与发展逐渐走向系统化、科学化和工具理性的演进之路。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教育哲学研究或学科发展具有一种现实观照的巨大内动力与基本品格,它与我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与国家命运、社会变迁与人们生存生活密切相连,具体表现就是哲人们论及的“教育哲学”多指向现实的民族生存、社会转型和国家公民的培育,较多学者甚至希望建立一种改造民众素质与推动社会变革的教育哲学,这又是对我国传统文化性格中“实用理性”维度的延续。从而,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与现实关怀——成为我国教育哲学学科化道路上逐步凝结的一个重要传统,较为根本。虽然在第一个逻辑支配下,我国近代以来诸多教育哲学著作很大程度地成为西方哲学与教育哲学的注解与套用,存在忽视具体教育实践而过于注
①如黑格尔、德里达等人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他们认为中国哲学不能称为“哲学”,而是“思想”。在这一点上,我国学者有过很多的辩护,这种“辩护”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西方人说中国没有“哲学”乃是从他们自身的概念、科学思维出发的,他们所提出的“质疑”属于“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重抽象“哲学化”的问题,值得反思、警醒。但与此同时,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其巨大的启蒙与积淀意义,西方哲学与文化的融入无疑很好地弥补、改进了我国传统教育哲学所存在的不足(如缺乏逻辑分析方法、哲学框架等);另一方面,在我国教育哲学学科创制发展进程中,始终贯穿着教育哲学家们的实践情怀与民族精神,此为根本,只有认识到此“根本”所在,才能真正克服第一个逻辑的规约作用,教育哲学建设才能找到正确方向。
我国近现代教育哲学的“实践情怀”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紧密深刻的联系:一方面,教育哲学的“实践情怀”品质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相通相承;另一方面,教育哲学的实践品格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中国化”改造与转化,实质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与方法在“中国观照”下的教育哲学塑造。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得以产生和确立,如张栗原、杨贤江、林砺儒等人的“教育哲学”便是如此。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于俄国“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乃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之所以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因为他们首先习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理论武装自己,并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和革命立场,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他们坚持“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去分析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去探索总结中国近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发生的重大问题,力图建构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5]455。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我国教育实践改革与发展的方法论指南为起点,一种泛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便悄然诞生并熔刻为中国学术传统之重要构成,首先即体现为广泛而深刻的实践品格。学科发展意义上,我国教育哲学初创以来,也始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与方法,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度被视为教育学的哲学基础,得到普遍认同。改革开放初我国重建教育哲学学科,教育哲学建设的总基调便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和基础地位,当时我国现代教育哲学奠基人黄济先生就明确指出:“教育哲学的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基础,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的一些根本问题,综合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作出有创见性的回答,以实现教
育哲学学科所肩负的科学任务。”[3]294-295并且,“教育哲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教育基本问题的论述外,更为重要的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分析和解决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结合当前生产和科技发展的新形势,作出新的结论”[3]657。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们的认识与立场也始终没有动摇,依然坚定“研究教育哲学必须以一定的哲学观为基础,中国教育哲学研究,理所当然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9]。
三、教育哲学的教育规定性:本体及价值限度
(一)教育哲学以教育为实践与价值本体
人类创造哲学,因生活与实践而起,又以生活与实践为皈依,循环往复。哲学解释世界与实践,最终又“改造”世界与实践。进而,教育哲学即在于解释与“改造”①教育实践本身及其主体,这便是教育哲学的教育本质规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哲学乃实践哲学——一种蕴涵教育价值与功能指向的哲学。这是教育哲学认同的基本起点,并由此而建立起教育哲学与其他非教育哲学的本质区别,否则,教育哲学存在的合理性难以自洽,其价值合理性不免招致怀疑、批评乃至否定。换言之,不坚守教育的本体性的教育哲学就是伪教育哲学,教育性构成了教育哲学的根本限度。
这种教育本体性是两个基本维度的统一:教育价值之维和教育实践之维。真正的教育哲学不是中立“无为”的,对教育实践的解释与改造不但是价值渗入的,而且指向一种“教育善”;教育哲学的“有为”乃是基于自身之本性、逻辑和旨趣而为,而非基于其他而为,此是教育哲学功能限度所在。教育哲学是一种实践—服务型哲学,其意义正在于,一方面教育哲学的合理性源于与教育实践逻辑的契合度,一方面教育哲学的旨趣在于服务教育实践的存在与发展之需(如反思、批判和超越),这是对教育哲学本体属性的自觉确认。如果说强调实践旨在突出教育哲学的自在性,那
①教育哲学并不直接改造教育实践,而是转化为人的智慧、方法或作为人的生活组成之部分,通过改造人固有陈旧的观念,提升人的思想与精神境界,促使人的行为合乎“理智”而具有“修养”,进而孕育为实践变革的内动力。么提出“服务”则重在彰显教育哲学的自觉性与能动性。在此次意义上,教育哲学本质是实践哲学。
所谓实践哲学,主要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实践哲学至少存在两大传统:一是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道德实践论传统,一是由培根在反叛亚里士多德传统基础上所创立的技术实践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正是基于对这两种传统的批判而建立。较之于“传统”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展现了“实践意识的完整性”,“实践行为的完整性”和“人的存在的完整性”,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技术理性与超越理性,“事实”意识与“价值”意识,理论世界、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本质上是人类学实践哲学”,它“既具有哲学发展的必然性,更反映了时代的根本问题,同时它本身又具有哲学的完整性”[10]56-65。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现实”概念便具有同义性,实践即现实,现实即实践。“马克思不是把‘现实’理解为超感性的概念世界……而是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实’。把‘现实’当作‘实践’去理解。”这意味着,第一,“‘现实’不是静止的‘现在’,而是在感性实践中不断自我生成并向未来敞开的历史性过程”;第二,“‘现实’不是永恒的‘现存’,而是要在实践活动中不断被改造和超越的对象”;第三,“‘现实’不是价值中立的僵死的‘事实’,而是一个在感性实践活动中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价值空间”。[11]从而,教育哲学作为实践哲学,其观照、批判和改造的实践或现实本身所指的就是一种完整实践、真实而统一的现实。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从人的生存出发,从人的劳动实践状态中认识人的本质及其存在。换言之,其实马克思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也就是生存论的本体论。马克思确立的“哲学思维的实践—生活即主体性的生存论维度,使传统的人学研究发生了根本性转向:从对‘人自身’的‘实体—属性’式研究转变为对人的生存、生活的‘实证—批判’(或‘描述—规范’)式研究”[12]。马克思指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13]30马克思同时批判了历史决定论和观念先验论,认为“应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13]43。这就意味着,首先,教育哲学不能离开现实、具体、历史、情境而抽象地谈论人或“教育问题”,教育哲学的“立脚点”是教育实践或教育生活——这里充满矛盾、个性与活力。教育哲学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与时代背景而空论“普遍教育”,如若说教育乃时代的教育,那么教育哲学必然也是时代的教育哲学。而那些超越时空限制的“历史必然性”①亦需纳入独特个体、现实境遇中加以认识,即所谓“相对之绝对”(孙正聿语)。其次,教育哲学并非是凭借“哲学观念”去纯粹地解释教育实践或教育现实世界,而是反过来由实践本身解释观念。换言之,即要实现对实践本身的尊重及承认教育实践的本体地位,进而确立起教育本身对“教育哲学”性质的根本规定性,而不是相反。
(二)教育哲学的问题本质上是教育问题
教育哲学作为实践哲学体现为教育对哲学的规定,具体又可以说成是教育哲学的问题源于教育实践,教育哲学的责任是解释并“改造”教育现实。现实即实践中的现实,就是人及其生活;现实即实践本身,它既是教育实践,又是教育实践与其之外的“现实”的整体关联;现实就是教育哲学的源泉——永不停息的当下。所以教育哲学永远处于不断地自我改造和生成之中,“没有变革现实的需要,就不会产生哲学的变革,而没有哲学变革,就不可能有指导变革现实的哲学”[14]。然而,只有是有“问题”的实践,才能成为教育哲学的对象。也就是说,教育哲学是一种基于“问题”的哲学。此“问题”是通过“哲学的方法”在教育实践中提出的,此“问题”是教育实践中的真问题,是教育问题。陈先达先生指出:“哲学之所以是哲学,就在于它对人们实践(生活中的一切领域和各门科学)中已经存在但习以为常或从未研究过的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哲学问题是哲学的生命线。没有哲学问题,就不可能产生哲学”,“而哲学中的问题是变化的。变化着的哲学问题表现的是哲学的时代特点、民族特点和哲学体系的个
①“历史必然性”讲的是“历史”本身的必然性,即“历史”的绝对性、积累性,事物是人类世界经验及其意识、思维的不断的继承、生成,这是客观的。参见: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北京: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1-32、42页。人特征”。可见教育哲学同样是“问题中的哲学”,但这种“问题”是指“科学研究中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中所蕴含的哲学问题。这不是直接的哲学问题,而是形而下的问题,是需要哲学家从中捕捉的问题。哲学中的问题只有来自问题中的哲学才是具有生命力有现实性的哲学问题”[14]。
教育哲学是实践哲学与“问题中的哲学”的统一。唯有自觉认识到这一点,教育哲学才不至于陷入僵化和狭隘的形而上之中;唯有自觉认识到这一点,教育哲学才能真正具有生命力。
教育哲学始终要为其教育合法性辩护,而这又是在为自身的存在与价值辩护,只有当教育哲学自觉地立足教育提出问题,“批判和揭示教育与人所遭遇的时代困境,并绘制更好的发展蓝图,它才算是真正实现了‘自我’”。叶秀山先生指出:“‘哲学’与‘社会—时代’联系得最为紧密,‘哲学’‘全面地—全方位地’联系着‘社会—时代’的发展。‘哲学’不仅仅从一个或某些方面联系着‘社会—时代’,不仅仅联系着‘社会—时代’的现象,而且联系着‘社会—时代’的本质。”[15]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描绘共产主义理想,雅斯贝尔斯之所以写下《时代的精神状况》批判现代技术与机器支配下的生活秩序和精神衰亡并提出人类可能的未来,而很多学者又不断批判现代社会的技术祛魅和道德祛魅、价值危机和世俗主义猖獗等,亦无不是立足“社会—时代”而批判反思、理性追问和人文关怀的结果。由此来看,教育哲学的“问题”又是从“社会—时代”中来的,反过来讲,教育哲学的“问题”总是源于教育哲学对人类文明的“时代性”的自觉意识或是对时代困境的反思批判与积极表征。如,哲学家孙正聿所认为:“哲学源于生活,源于对时代的迫切问题的理论自觉……真正的哲学之所以是‘自己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就在于它自觉地体悟到自己时代的人类的生存困境,自觉地捕捉到自己时代的人类的迫切问题,并自觉地把人类文明的时代性的困境和问题升华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16]当然,教育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且是人类文明演变与发展的基本动力,人类文明的时代性或时代困境在某种意义上正反映于教育文明或者通过教育文明凸显出来,因为教育无疑体现着时代性、民族性、文化性及地域性中人们的精神与生命之境遇。而当下所谓真正的时代性的“教育困境”和教育意义或唯有借助人类的哲学自觉以哲学方式才能得以把握——这种哲学方式用孙正聿的观点讲,就是“以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的方式”,“以人类文明的时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以及对“规范人类的思想与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的批判性反思。
四、教育哲学的哲学规定性:工具或方法之限度
教育哲学不仅姓“教”,也姓“哲”,它具有教育与哲学的双重规定性。于是我们就要有一种教育哲学作为哲学的自知之明,建构和捍卫教育哲学的哲学性。但这种哲学性相对于教育性而言,却不能构成教育哲学的本体,而是作为一种世界观①、视角或方法而存在。
(一)教育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哲学规定性
作为理论或学科形态的教育哲学,以教育价值为本体,而以具有哲学性的理论为形式表征,呈现理论品质的系统性、逻辑性和严谨性,凸显哲学理论的理性或思辨性。理论性是教育哲学的立身法则,这也是教育哲学在教育学学科体系中一直处于“原理”或“基本理论”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反之,这种理论性则构成为教育哲学之限度所在,否则教育哲学难以自洽。
首先,教育哲学是实践—服务型哲学,旨在“服务”教育实践,其理论形态需拒绝晦涩艰深、玩弄辞藻和故弄玄虚的形式风格,避免陷入理论傲慢或自言自语。就形式本身而言,那种以不变或恒常为追求的哲学理论注定是违背“哲学”的自由与开放性本质的,它只会将教育哲学引入机械僵化和固步自封。如叶秀山先生所言:“‘哲学’的概念不像经验科学概念那样是必然的,而是‘自由’的,‘哲学’运用‘自由’的概念。辩证的概念,就是‘自由’的概念;概念是辩证的,也就意味
①“世界观”本是一个值得且有必要讨论的范畴,但限于篇幅,本文不对其详述。此处引孙正聿的观点对其加以规范,而此观点正反映为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的重要变革。孙正聿在指出传统“世界观”向现代“世界观”的变革时,特别强调现代“世界观”“最为重要的是把世界观理解为‘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哲学理论,并且从人的历史性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对‘世界观’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新的理解: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这一观点,在思维方式上以实践观点突破和超越了构成传统“世界观”的那种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又以辩证法超越了传统的绝对主义。参见:孙正聿:《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着,概念是‘自由’的。概念是‘自由’的,不等于概念在词语上没有稳定的意义,‘自由’的概念首先意味着它是‘活动’的,不是‘固定’的。”[15]当然,我们说“哲学”的“自由”,很大程度又是在实践哲学意义上讲的。换言之,“哲学”的“自由”乃由其本身的实践性所决定。实践是自由的,充满偶然性,则“哲学”是“自由”的,非是定论或一成不变的。
其次,如果上述所讲的“理论”仅作为教育哲学之哲学性的理论形态的一种呈现形式,教育哲学哲学性的理论形态的内在特征则要体现出哲学与其他诸如科学、文学、艺术等的区别所在,从而展现哲学的独特理论性质及其价值内涵。这种区别,用孙正聿的话说,就“在于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即以理论形态所体现的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关切和回答,对人类生活意义的关切和回答”,就在于哲学“是以价值诉求为目的而展开的对存在的反思和对真理的追求,因此不是独立的、单纯的存在论或真理论或价值论,而是融真、善、美于一体的存在方式”[16]。也就是说,教育哲学在哲学理论意义上与科学所单独追求经验事实与科学真理以及艺术以单纯情感表达为圭臬有所区别,并通过价值追求将它们进行了统一。
(二)教育哲学作为方法的哲学旨趣
作为方法的教育哲学即作为动词的哲学,此时,哲学被理解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寻根问底和不断反省的思想态度”[17]5。一般认为,哲学源自于对生活本身、人生存的思考,如冯友兰说:“哲学始于经验”。古典意义上,哲学表现为“爱智慧”或“惊异”,毋宁说哲学是一种对现实生活与生存的觉悟、反思与询问,孰不知“‘批判’是一切真正哲学的灵魂”[18],其展现了“哲学”的工具属性。
哲学的这种方法性或工具性又蕴藏于其理论性之中。如若说学术形态意义上的理论指的是形式的理论、解释的意义系统和改造的价值取向,那么哲学的哲学性的另一个理论性则在于理论本身。也就是作为哲学的理论,它其实反映为哲学本身的内在旨趣:理论即一种“眼光”或方法,理论本身蕴含批判和辩证思维品质。作为一种“眼光”或方法的理论,是指“以理智的形式去观看存在”即“理性地观看”,是一种超越了以某种具体经验为规定性的“经验地描述现象”和“感觉器官观看”的认识活动,或言之为经验的“抽象”①化,抑或理解为一种“高位目光”和“普遍视野”②。但此种哲学的理论本身的理性品质又必然是批判和辩证的,故它又超越了纯粹的认识性而充满人文情怀和价值感。理论既是意义解释的过程,也是价值批判和辩证思维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霍克海默、吉鲁等人所认为:“理论必须承认自己包含一定的价值预设,并且对它的价值倾向做出批判性反思”,“理论不可争辩地具有批判性”,同时,对于真正的理论而言,“辩证的概念十分关键”,因为它揭示了“‘完备’思想体系的缺陷和不完整性……揭露了所声称的完满的非完整性,包含了否定中的肯定、不可能之中所蕴含的可能”[19]28-29。
批判不是无理性或仅凭感官直觉的批判,而是基于理性的、对生活生命充满同情与价值关怀的批判,是一种自我反思与超越。批判乃是“对生命的自由和丰富性的辩护。生命的‘自由’与‘丰富’,是哲学批判最为根本性的价值旨趣。这意味着:哲学批判并非流俗所理解的消极被动的‘否定性’和‘拒斥性’活动,而是呈现出十分自觉和鲜明的建设性和肯定性向度和意蕴”[18]。批判的目的不是批判本身,而是为寻求“善”的生活与生命价值而不断反思当下的种种限制力量。批判是解构与建构的统一,它一方面在于解构现实不合理、不自由,另一方面又在于建构理想世界与人生,创造新的教育与生活图景,所以说“‘创新’就是‘哲学’的‘常规’工作”[15]。如贺来教授所认为,哲学的批判本性“源于对人生命特性的自觉理解和表达,它根植于人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生命本性,其根本旨趣在于破除一切与人生存发展不相适应的因素,否定一切阻碍人的自我发展、妨碍人的生命自由的异化力量,以实现人不断的自我超越和自我提升”[20]。
①马克思、恩格斯曾严厉批评那种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抽象,但他们不会认为一切抽象都是形而上学的。“现实的探究需要抽象甚至很高的抽象”,“作为哲学抽象,完全可以具有实在的经验基础”。参见:刘森林:《重思马克思恩格斯的“形而上学”观》,《哲学研究》,2017年第1期。
②这种“高位目光”和“普遍视野”即“不断超越片面和局限的视角”,继而“最终让我们更加具备获得教育实践智慧的内在基础”,“最终获得同时包容教育实践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整体性理解”。参见:余清臣:《培育对教育实践的高位目光与普遍视野》,《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三)教育哲学研究的非实证主义范式特性
教育哲学不能是纯思辨或纯哲学的研究而应更多专注教育实践问题,这已作为当前我国教育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共识。然而,教育哲学对现实问题的把握与研究却不同于其他经验、技术的科学研究,教育哲学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对现实的理性审视、价值辩护与澄清、反思与批判教育实践的种种前提性观念等,而为教育实践与人的生存发展建构价值基石、思想归属和理性秩序。教育哲学当然不会离开经验而空谈实践,但教育哲学不会拘泥于对某经验性、事实性、具体技术性的问题而给出实证主义理性①把握或工具理性控制。可以说,教育哲学是在现实的具体问题中抽象出问题的一般性与必然性,而这种“抽象”本身构成了教育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即“‘哲学’坚持‘必然’通过‘偶然’而成为现实”。也就是说,教育哲学“在离开实践具体的形式方面时,自觉地借助于抽象力深入到人的生活实践的本质或底蕴之中,从而更深刻地把握住了人们社会生活实践的矛盾本性”[21]。与此同时,教育哲学依然不会是价值中立的,教育哲学正是要凭借价值与情感深入实践中,进而真正观照教育问题的本真,从而实现理论理性与实践关怀在实践中的统一。
在这一点上,叶秀山先生的如下观点极具启发意义。先生认为,那些“科学的”、具体而实际的、技术与过程性的工作不属于哲学的“常规工作”,哲学需借助经验科学(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而把握现实世界,但哲学的“常规工作”是反思、批判与“创造”,“‘哲学’与‘科学’有着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这种关系,帮助人们去理解现实世界,处理具体事物,目标明确地、有原则地解决现实的难题,其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然而,我们不必将这种有意义的科学性工作也看做一件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工作。‘哲学’就是一种‘没有常规工作’的工作。真正的‘哲学家’都在做‘非常(规)’的工作,在做‘创造’的工作,在做‘范式转换’的工作,在做‘革命’的工作”[15]。
五、乌托邦精神、逻辑整合与生活回归:教育与哲学之统一
(一)乌托邦精神:教育与哲学的“超越性”统一
“教育哲学”即“教育”改造“哲学”和“哲学”改造“教育”的双向作用的结果,同时又是二者相互适应的结果。在这个相互改造和适应的过程中,“教育”与“哲学”达成了统一。这种统一就如上面所论及,是“哲学”在价值与问题上的“教育化”和“教育”在语言、方法和生活上的“哲学化”。不过,当我们回到教育与哲学都作为人的意向性和实践性存在的本质时,不难发现,正是一种从现在指向未来的情趣与精神使得二者深深相吸、相互融贯,即教育永远指向“人”生命的成长和未来的价值意向性和哲学那永不枯竭的“乌托邦精神”②共同孵化着教育哲学的基本品格——或许我们不妨称之为一种“现实超越性”——总希冀为现实指引更加美善的未来,总要试图提出更加合理的价值主张,呼唤人们过上良善、理性、意义、智慧、自由的生活,于是教育与哲学似乎在此意义上实现了内在统一。
对于现实,教育或者哲学都总是不太满意的。哲学总要试图洞察现实,并加以反思和批判,似乎只有“在这种对于‘现实性’的理解和关注方式中,哲学才显示了它的特殊功能和作用,即通过对现存世界的超越和否定和对一种‘更高的现实’的想象,去批判现存世界,规范和引导人们的生活,开拓未来社会”[11]。也难怪雅斯贝尔斯会说:“一般大众满足于文化和进步,而具有独立头脑的人却怀着不安的预感。”[22]9而教育则在其历史演进的长河中不断镌刻着一种以人类前行和人的生命成长为使命的文化基因,它永不满足于人的生命样态和生活遭遇,生生不息,改革不断,似乎其所向往的那个人的形象和人的生活永远存在于不久将来。
事实上就是教育与哲学共同拥有着一种乌托
①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理性”所作的批评:它秉持着逻辑经验主义忽视了“经验”背后的历史、关系、权力和观念,压制道德问题,对基于“经验”的“科学知识”盲从致使其失去了理性本身具有的批判性,更将自身置于若干虚假的二元论(如事实与价值、科学知识与规范标准、描述与规定)之中,从而消解了一切现实存在与可能性之间的紧张关系。“结果,原本具有洞察力和批判力的理性走向了它的反面,即非理性”或者说“在实证主义的规则下,理性满怀敬畏地站在事实面前。它的功能仅仅限于描述事实,当对事实做出了肯定和说明之后,它的任务就终结了……在实证主义的规则下,理性缺少了批判,不可避免地走向末路。”参见:吉鲁著,张斌、常吟、左继容等译:《教育中的理论与抵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7页。
②哈贝马斯说:“如果乌托邦这块沙漠绿洲枯干,展现出的就是一片平庸不堪和绝望无计的沙漠。”参见:薛华:《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邦精神,而“教育哲学”则难免成为“现实的批判者”和“未来的构想者”,其所指向的便是那个应有①的人与生活的未来。如果说教育哲学这个指向源自教育本质的规定,那么,哲学在此所作的贡献就正如胡塞尔所说,是一种“回到事情本身”的方法,其意义在于理性地“直观”和不断追问那个“教育本身是什么”的问题,也从而引领人们朝向“教育本然”去思考、行动或实践,追寻那个关于人的完满形象及其生活的丰富意义。然而,教育对这个“未来人”或“本然的人的形象”的追寻却不能陷入平庸、虚幻或空洞的“教育幻想”,从而,哲学却又不能止于“本质直观”。哲学的另一大贡献还在于赋予教育一种理性的乌托邦精神,正如伯恩斯坦所说:“乌托邦精神是所有真正哲学的灵魂,并且,哲学不仅是乌托邦式的,而且要为一种理性的乌托邦辩护。”[23]或用孙正聿的话讲,这种乌托邦精神就是哲学内蕴的一种“本体论追求”品质。孙正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传统本体论占有绝对真理的幻想,但并不拒绝基于人类实践本性和人类思维本性的本体论追求。事实上,本体论追求符合人性及人的实现的可能性、无限性,哲学上的本体论追求是哲学成其为哲学的不可能消失的本性所在,其“合理性是在于,人类总是悬设某种给予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理性目标,否定自己的现实存在,把现实变成更加理想的现实;本体论追求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它启发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终极的指向性与历史的确定性之间,既永远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又不断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使人类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始终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和审美意识,永远敞开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空间”[24]98-99。从而我们说,借助理性与本体论追求的哲学光芒,教育哲学成为教育在现实与未来之间的桥梁,教育哲学永远是基于现实却又超越现实的,这正是教育哲学的基本精神。
(二)逻辑整合:哲学与教育的“对话”
凸显教育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属性,本质上就是要求实现哲学理性逻辑与教育实践逻辑的统一。这种统一本身是为了克服这样一种矛盾:教育实践不能完全服从哲学理性逻辑的规导,但教育实践不能任凭自身“自在”运行,教育实践必然需要哲学理性逻辑的指引。因为,在这种“指引”下,教育实践能够避免感性认识带来的“弯路”并合理地抗拒“惯习”的过度规约性,以及避免人们所热衷批判的当代教育正遭遇的资本逻辑的支配。同样地,哲学理性逻辑如若不顾及教育实践本身,那么其指引力将会无的放矢。于是我们说,唯有在这种基于“顾及”的“指引”中,教育哲学完成了自我建构,走向一种逻辑合理性和价值正当性的统一进程。
这种统一在本质上表现为两种逻辑的相互契合,也可以说是哲学方法论对教育实践本身的“应合”,进而构成为“教育哲学”本身。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就是那种特别被接受并且自行展开的应合,对存在者之存在的劝说的应合……哲学以应合的方式存在,应合乃是与存在者存在的声音相协调”,“应合就是符合”。[25]22、25-26此“应合”,在这里可看作是“哲学”对于“教育实践存在”的符合,事实上,又是教育存在对于“哲学”的符合,所以海德格尔又进一步指出,“符合”其实表示为一种“对话”。故从概念上看,“对话”可能要比“符合”更加恰切一些,也就是说,教育哲学产生于教育与哲学的“对话”。设想,若没有这种“对话”,则“哲学”不“理解”“教育”,而“教育”同样不“理解”“哲学”,其后果就是“教育哲学”不构成“内部”契合性,成了一种处在“哲学”与“教育”之间的“尴尬之物”。
(三)生活回归:教育实践与哲学同构“善”和理想未来
教育实践乃生活本身的美好形式,这是教育本性的追求。而哲学作为人的沉思、追问的创造性体验无疑表征“人的善”和“生活意义”本身。于是,教育与哲学在“人的善”或“生活善”的意义上实现了有机融合,那便是教育哲学的现实还原,即教育哲学成为人的生活本身。换言之,教育哲学超越了自身之于教育本体的方法限定,而成为一种教育生活,就如杜威所说,“在这一点上,哲学与教育的密切联系就表现出来了”[26]347。
正如胡塞尔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使一种哲学的生存方式成为可能。”[27]34教育哲学的任务也应在于使“哲学的生存方式”成为可能,这种生存方式可如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的栖居”,
①虽然教育哲学指向“人”应然和未来的“善”,但它不能是一种虚幻的冥想。在此意义上,教育哲学必须接受亚当·弗格森的建议:“如果哲学家预设人可以获得超出其能力之外的东西,那他们就必然非常荒谬了。”参见:亚当·弗格森著,孙飞宇、田耕译:《道德哲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可如亚里士多德的“审视的生活”,又如冯友兰所认为的哲学的任务“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28]373,强调人的心性修养、生命品质与人格境界的提升。进而言之,教育哲学无疑富有哲学作为“生活方式”的意蕴,它要求“教育哲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完成对教育实践主体“哲学生活方式”的营造。教育实践中,应是教师首先要主动而充分地过一种“哲学生活”(如上所述,这种生活应是非自私、非功利、非肤浅、非贪婪、非纵欲的,而是民主的、公共的、自由的、诗意的,并且富有理性和反思批判精神),进而对学生产生积极的教化意义。事实上,在我国教育实践正日益被现代工具理性、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所裹挟的当前,我们不仅要在“私人”的意义上培育一种“诗意”、富有活力的生活方式,使教育归还人的完整生命形象;更要在“公民”的意义上促使教育肩负起培育人的公共理性和价值理性并因此而过上民主生活与联合生活的责任。教育哲学生活要以独特的理性品格、辩证法和乌托邦精神改造教育生活的极端倾向和狭隘的现实主义,把人们的“眼光”从眼前功利、个人利益和各种肤浅诱惑之中转移出来进而更加注重人格境界、公民素养的自修,强化个体的主人翁意识使其更加关注身边人、家庭、社会、民族、国家、自然和人类的困境和未来,“修己善群”,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
六、结语
教育哲学的自知之明,简单地讲,即一种教育哲学自觉。如果说,正如孙正聿所言“对哲学的自觉就是对哲学以何种方式把握世界的自觉,也就是对哲学方式的特殊性质和独特价值的自觉”[16],那么也不妨可以说,对教育哲学的自觉也就是对教育哲学方式的特殊性质和独特价值的自觉。只不过,当我们在强调教育哲学者需要在认同教育哲学的性质、价值或功能的同时,还要有一种敢于承认教育哲学的限度或局限的勇气,或“知其所能与所不能”的谦逊,进而才能扬教育哲学之所能和避之所不能,最终达致“自明”及与“他者”之联合。就此而言,自知之明或自觉其实即可作为教育哲学者的一种基本品格,乃为推动教育哲学研究和哲学发现的内在动力。就如苏格拉底所认为,哲学家的品格乃是“自知其无知”,永远处于无穷追问与求知的过程。
值得说明的是,本文强调自知之明并非要将“我们”引向一种妄自菲薄,也不是要通过建构起一种关于教育哲学的认同感、自豪感和使命感,而妄自尊大。所谈之限度也并非在鼓吹“关起门来搞学问”或刻意修造学科壁垒,相反,强调限度意识,乃是“我们”走向自我认同与开放合作的基本起点,而对限度的无知则无疑是此认同与合作的障碍。本文的旨趣正试图在“我们”与“他者”之间建构起一种限度意识和理性准则,促使不同科学实践活动更为恰切合理,推进各学科或学术共同体之间实现相互独立、相互尊重和相互联合。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是教育哲学,可能其他任何一门学科或一个学术领域都需要有此“自知之明”。
[1]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
[2]雷云.教育哲学三题:对象、主题与地位[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
[3]黄济.教育哲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
[4]张岱年.儒家哲学是教育家的哲学[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9,(1).
[5]张瑞璠.中国教育哲学史:第1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6]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7]杨国荣.分析哲学与中西之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8]张志伟.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2).
[9]王坤庆.论现代教育哲学体系的改造与重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90,(6).
[10]丁立群,等.实践哲学:传统与超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1]贺来.超越“现实”的“现实关怀”——马克思哲学如何理解和关注现实?[J].哲学研究,2008,(10).
[12]袁祖社.新思维方式的实践——生活维度及其“现代性”祈向——马克思人学理论变革的实质[J].理论学刊,2004,(6).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4]陈先达.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6,(2).
[15]叶秀山.哲学作为哲学——对哲学学科性质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05,(6).
[16]孙正聿.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J].中国社会科学,2016,(1).
[17]石中英.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8]贺来.何谓哲学意义上的批判[J].探索与争鸣,2016,(6).
[19]吉鲁.教育中的理论与抵制[M].张斌,常吟,左继容,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
[20]贺来.乌托邦精神与哲学合法性辩护[J].中国社会科学,2013,(7).
[21]张曙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有的现实性与超越性——一种基于人的存在及其历史境遇的思考与批评[J].中国社会科学,2006,(4).
[22]卡尔·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3]R.J.伯恩斯坦.形而上学、批判与乌托邦[J].哲学译丛,1991,(1).
[24]孙正聿.孙正聿哲学文集:第5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25]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M].孙周兴,陈小文,朱明锋,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6]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27]泰奥多·德·布尔.从现象学到解释学[M].李河,赵汀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8]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赵复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责任编辑:罗雯瑶]
Defense and Identification:Self-reflection and Self-consciousness in Moder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Research in China
LIU Yuan-jie
( School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
Self-awareness is requir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n our country. This self-awareness means by understanding what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s, what it can do and can’t do, people manage to reach self-consciousness, self-identification and even the possibility of uniting“others”. It’s also of great necessity to gain the self-awareness, confidence,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radition, especially to push forward the self-recogni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tradition of Marxisteducational philosophy in modern time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has the dual stipulation in both education and philosophy. Since Education defines its ontology and value, and philosophy defines its tools or methods, the total unity of education and philosophy rests in the pursuits of Ontology, logic integrity and lifereturning.
educational philosophy; Marxist practical philosophy; self-recognition; cultural confidence;identification
G40-02
A
2095-7068(2017)03-0061-12
2017-01-12
10.19563/j.cnki.sdjk.2017.03.009
刘远杰(1986— ),男,贵州仁怀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广西社科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特约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与教育哲学研究。
2016年度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项目“文化自信的内在逻辑与生成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6MJ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