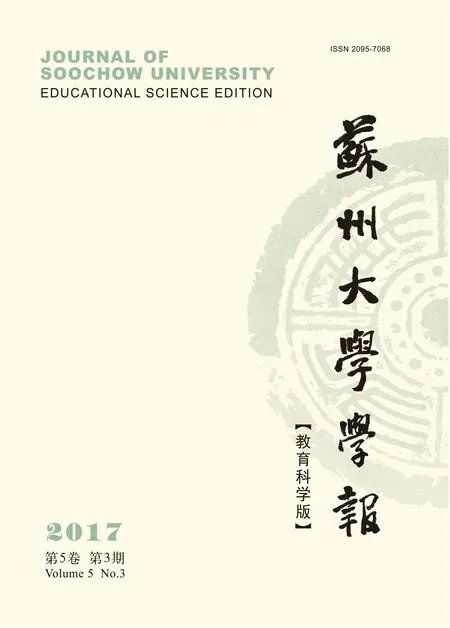大学治理:被滥用的时髦词语—对“我国大学治理问题研究”的反思
肖 卫 兵
大学治理:被滥用的时髦词语—对“我国大学治理问题研究”的反思
肖 卫 兵
(苏州大学 教育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诸多对我国大学治理问题的研究不是在“治理理论”的范式下开展的。治理具有过程性、协调性、多主体性和持续互动性等特征。我国的大学治理在“备受质疑”与“主动探索”的夹缝中艰难行进。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与大学主体性的缺失是我国大学治理实现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通过变更管理模式,打破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使大学治理成为可能。
大学治理;治理概念;治理特征;行政主导;大学主体性
一、问题的提出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概念之后,“治理”一词在政治学及社会其他领域被广泛应用。当前,治理在我国的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哲学、文学等领域是一个热名词,与此有关的研究成果比比皆是。“在较短时间内,治理理论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几乎席卷中国社会科学界,许多学者尽管还没有弄清楚其基本理论图式,还来不及细细地琢磨,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裹挟进这一‘热潮’,并将其嫁接到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之中——这不是理论研究的科学态度。”[1]治理在我国的滥用,使得“治理”成了“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2]55。
在高等教育学领域,探讨大学与外部主体,特别是与国家的关系时,往往使用诸如“大学管理”“高等教育管理”之类词汇,隶属于教育管理的范畴。在“治理”横空出世之后,“大学治理”也悄然兴起,似有取代“大学管理”和“高等教育管理”的趋势。在国家的政策文本《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大学治理”一词也赫然在目,文本提及“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有人认为这一表达表明“大学治理结构议题在我国已获得政治合法性并进入政策流程”[3]。政府的这一导向使得诸多高等教育研究者将“我国大学治理问题”作为研究的主题,并且对这一问题的关注逐年递增。在“中国知网”的“篇名”中以“我国大学治理”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找到期刊论文49篇,其中,2005年至2013年之间发表的年均2篇不到,2014年至2016年分别为10、8、12篇。若以“大学治理”为关键词搜索,共有687篇期刊论文,其中,2014年至2016年分别为91、140、116篇,很多论文也都涉及与“我国大学治理”相关的主题。①如蒋达勇、王金红的《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大学治理——中国大学治理历史演进与实践逻辑的整体性考察》梳理了中国大学治理的历史演进与实践逻辑;宣勇、钟伟军在《论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校长管理专业化》中提出外部治理的管制化和内部治理的行政化是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困境;成洪波的《试论地方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探讨了我国地方大学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问题;等等。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将我国大学治理认定为事实,并在此前提下将“协调大学与政府、社会等利益关系的‘外部治理’和协调大学内部各种权力关系的‘内部治理’”[4]的结构、模式、体系、特点等问题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
当前的教育政策文本表述以及对“我国大学治理问题”的研究似乎表明,我国大学发展已具备治理的基础,大学治理是一种“实然”的状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诸多脱离治理理论范式的大学治理研究是对“治理”的误读与滥用。虽然“治理”一词在古汉语中早已存在,但此“治理”明显非彼“治理”,政策文本和相关研究把“大学治理”不加证明地视为理所当然,不在“治理”的基本范式中,就野蛮地将这一外来语“嫁接”到中国大学发展的实践语境中,这么复杂的一个主题研究就建立在这样一个简单假设的基础之上,实在难以令人信服。不得不承认,“大学治理”在我国成了一个被“滥用”的“时髦词语”。然而,大学治理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对“治理”一词的内涵和特征的准确把握上,也只有在这种语境下探讨我国大学治理问题才是有意义的。
二、“治理”的概念及特征
治理的概念目前还处在一个日臻丰富与充满争议的讨论阶段。何为“治理”?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是众说纷纭。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对“治理”作如下阐释:“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活动。”[5]4-5简而言之,治理具有过程性、协调性、多主体性和持续互动性特征。
(一)治理的过程性
治理首先是“一个过程”,不是“一种”活动。在泰勒模式的影响下,人类的行为越来越关注预设的目标及其结果,这一特征在象征国家意义的公共管理领域更加明显。预设目标容易将活动单一化,即将本来及其复杂的活动变成了单一活动,变成“权威”的单一主体开展的活动。在这一目标模式的影响下,管理活动变成了管理者的一种活动,被管理者成了管理者管理活动的对象。治理的过程性必须要破解活动单一性的困局,突出多种活动共时参与的多样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不是“一整套规则”作为权威规则发挥决定作用,而是诸多规则共同发挥作用。在公共领域,现代国家的执政党通过其组建的政府代表国家行使公共职权,他们通过制定一整套的规则去规范行政机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行为。这一整套的规则包括法、政策、制度、纪律等,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被视为一个国家“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但是在治理过程中,不仅是这一整套的正式制度与规则发挥作用,其他的非正式的制度(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同样发挥作用。同时,治理的过程性不仅不是“一种”活动,更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统治”活动。统治活动强调一整套规则的规范,强调公共权力行使中的上传下达;治理不是这种活动,而是突出多种活动的意义,包括各种主体以符合其利益而开展的各种活动。总之,治理具有过程性而否认其是一整套规则或一种活动,意味着在治理过程中,不是由某一主导力量(如国家或执政党)预先制定的规则或安排的活动,而是治理对象在与之相关的不同主体共同作用下发展的过程。该过程不受某一占支配力量的主体决定,具有不确定性、动态性、复杂性与多样性特征。
①搜索时间均为2017年6月19日。
(二)治理的协调性
协调性本指身体作用肌群之时机正确、动作方向及速度恰当,平衡稳定且有韵律性,后引申至管理活动中,如企业管理协调性、政府管理协调性等。管理活动中的协调,强调管理者依据规则化(主导规则)的管理权限,协调好人、财、物、时间、空间、信息等之间的关系,做好资源的优化配置,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使管理绩效最大化,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是控制的过程。管理活动中协调依据的是权威的制度规范,治理的协调性与之不同。从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界定中可以看出,协调性是治理过程的基础,治理就是使相互冲突和不同利益调和的过程。治理的协调性旨在调和治理过程中相互冲突的、多主体的利益诉求。在缺乏权威规范下,不同主体在治理发展过程中相互冲突和妥协的过程,是平衡—不平衡—再平衡的循环往复向上的过程。治理的协调过程是一种达到更加平衡的过程,是动态的发展过程,而非静态的外部规范。正如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所描述的那样,治理“作为一种独特的协调机制,其逻辑同市场和自上而下发布命令的协调相区别”[2]60。治理中的协调过程,其权力运用的向度不是“统治”那样自上而下的,而是相互的、多元的。所以,治理的协调性本质上意味着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
(三)治理的多主体性
主体,从权利与义务的角度而言是指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即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从哲学的角度而言,是指对客体具有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人。治理的主体也应含“人”之应有之义。具体而言,治理的主体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指治理过程中的参加者,是治理过程中发挥不同作用的“人”,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前文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治理的主体包括各种公共机构、私人机构或者个人。这里的公共机构主要是代表国家的国家机关,可以是行政机构、司法机构或立法机构,也可以是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或机构;私人机构主要是指一些社会组织或者团体,包括具有法人地位的社会组织,如企业法人或事业法人,也包括一些不具有法人地位的社会组织,如学术团体组织等;个人主要是指在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独立个体。治理主体的第二层含义体现为治理过程中的参加者在治理过程中要有主体地位,要能平等地发挥主体作用。参加者的主体地位主要是依法享有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或能力。具备这种资格的主体不一定能发挥主体作用,这需要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作为保障,需要社会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和可能性作为补充。治理的多主体性表明不同的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可以主张自身的利益诉求,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推动治理进程。总之治理的多主体性意味着在治理过程中,国家、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在治理过程中共同发挥主体作用。
(四)治理的持续互动性
互动是一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自然科学领域中,物理学较早地阐述互动概念来说明能量守衡定律。社会学领域也形成了社会互动理论,用来解释社会发展问题。一般认为互动起因于共同的目的、共同的利益,或者是由于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利益所致,前者称为合作性的社会互动,后者称为对立性的社会互动。合作性的社会互动中,主体间的利益并不是直接矛盾冲突的,表现为合作、适应、模仿、同化等形式;对立性的社会互动中,主体间的利益是直接的或间接的矛盾冲突,表现为竞争、统治、冲突、服从等。美国学者詹·库伊曼(J. Kooiman)曾经提出并区别了三种互动类型 :“干扰”(interference)、“相互影响”(interplay)和“干预”(intervention)。“干扰是自然和人类生命的(动力)基础”,相互影响是“具有高度组织性并且以形式化模式出现”,“干预可能是被组织的或被引导的”。[6]223治理具有持续互动性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治理中的多主体间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主体间可能是合作性,表现为相互合作、相互适应等;主体间也可能是对立的,表现为相互冲突、相互干扰,但由于治理具有协调性,因而会消解主体间的对立,从而实现合作互动的转化,最终推动治理进程。这种合作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5]6。第二,主体间的互动是持续的。只要治理对象存在,那么主体间的互动就不会停止,这是治理主体所面对的共同事物发展的动力所在。
综上所述,治理是“众多不同利益共同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或取得认同,以便实施某项计划”[7]16-17,也就是多个成熟主体在一定范围内,运用协调机制、互动合作、达成共识、共谋发展的过程。相比而言,“管理”强调主导规则的支配力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隶属关系遏制了被管理者的主体性,进而使得他们之间的持续互动难以实现。
三、治理理论与当前我国大学管理的适切性
治理理论若要适合指导我国大学发展实践,需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治理理论适合于我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即治理理论的“中国化”是可行的;二是治理理论适合于指导我国的大学发展问题,即我国大学治理的合法化与实体化是可行的。关于治理理论的中国适用性问题,目前明显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还不具备治理的内在条件。如臧志军认为,“当今中国总体上并不存在着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现存的党政一元化政治结构制约并将长期制约着多元主体的独立成长”[1],缺乏多元管理主体和民主协作精神,治理就成了“空中楼阁”;刘建军认为,“在中国当前政治还没有完全成型之前,对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的过分呼唤,会使中国重新掉入政治浪漫主义的陷阱”[1];等等。还有一种观点是在回避前者疑虑的前提下,探索中国治理的结构、途径①,认为“这种倾向可以视为对臧志军、杨雪冬等论者怀疑态度的某种间接回应”[8]138。第二个条件即中国大学治理是否可行的问题。大学治理必然是在社会治理的框架下进行的,只要社会治理可行,那么大学治理也是可行的。当前我国的社会治理在“备受质疑”与“主动探索”的夹缝中艰难行进。一方面,在党政一元化的政治结构中,行政主导体制在集中资源和集体意志实现上的优势使这种政治结构在过去几十年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国家权力集中,其他主体的成长空间极其有限,社会治理实现受到质疑;另一方面,行政主导体制中行政权力支配一切,创造了更多的权力寻租空间,增加了掠夺社会公共利益的风险,官员腐败案件层出不穷,人们对“善治”“良政”的呼唤声与日俱增,有良知、有责任的研究者们在层层迷雾中陡见“治理”这一线光明,就迫不及待地将之奉为治疗社会顽疾的一剂良方,主动探索社会治理,为中国社会治理的真正实现献计献策。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治理尚在“备受质疑”与“主动探索”的夹缝中艰难行进,在党政一元化的政治结构中捉襟见肘地变通与发展。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中大学治理的实现则更是雾里看花,社会基础还不成熟。因此,一切认为我国大学治理已成实然状态的研究,均是对治理的误读与滥用。
四、当前我国大学治理实现面临的问题
“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大学主体性的缺失”是当前我国大学治理实现急需解决的问题,它们消解了大学治理的过程性、协调性、多主体性、持续互动性等特征,使得我国大学治理成了名副其实的“空中楼阁”。
(一)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设计的缺陷使得“行政主导”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指挥棒”,从而导致对大学治理的偏离。
1.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设计的缺陷
“大学像其他人类组织——如教会、政府、慈善组织——一样,处于特定时代总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9]1作为我国社会结构中的大学,在一元化的政治结构背景下,以行政主导为主要特征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是制约大学治理的关键因素。这里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包括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和高等学校内部管理制度。我国高等学校行政管理制度是行政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与高等学校之间的行为规则及其结构,行政主导是这一制度的本质特征,近三十年来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早在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作出了改革政府与高校关系的论述,文件提出“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高等学校统得过死”,“政府应该加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起来”,并提出“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1992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教委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
①王诗宗将中国学者对中国治理的探索概括为四种情形:以政府为主导,通过引入社会中的诸如第三部门、市民社会等参与群体和参与者来实现治理;通过发展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以及公民社会来实现对于公共事务的治理;主张通过政府内部诸如沟通机制、层级结构的改革来实现治理;必须同时进行上述几种论点主张的改革,通过具有紧张关系的多方主体的互动才能实现治理。参见:王诗宗著:《治理理论及中国适用性》,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页。意见》提出要“理顺政府、社会和学校三者之间的关系”;1993年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解决政府与高等学校”的关系;1995年国家教委发布《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划分、规划举办者、办学者和管理者的权利与义务”;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明确了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进一步强调了中央政府和地方的省级人民政府对高等学校的行政管理的法定职权,并明确了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2004年教育部的《2003—2007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改革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清理教育行政许可项目”,“完善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人民政府管理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2007年国家发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还是强调“完善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人民政府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中提出了“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等,但并未涉及具体操作步骤。从以上制度规范中可以窥见三十多年来我国教育行政部门与高等学校之间的博弈历程,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力全方位地渗入与高等学校积极寻求办学自主权之间的矛盾是高等教育行政制度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虽然政府主张“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并通过《高等教育法》明确高等学校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以及在招生、专业设置、教学、科研、人事管理和财物管理方面的“办学自主权”,但这些并非真正的“自主”,是在一整套规则规范下的自主,并不能体现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究其原因是“其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涉及体制改革这样的阶段性问题”[10]。
从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来看,行政主导仍是其主要特征。当前我国高等学校内部管理制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中规定,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高等学校的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组建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力,党政一元化政治结构决定了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是不可能规避行政主导的缺陷的。从高等学校办学实践来看,当学术界将高等教育“去行政化”作为高等教育热门研究主题来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行政主导特征更是不证自明。
2.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对“大学治理”的偏离
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与大学治理是相互冲突、互不相容的。
首先,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意味着政府制定的一整套规则是大学发展的主要规则,是权威规则,是对高等教育各主体行为最主要的规范;大学管理是政府实现公共职能的一种活动,是“统治”活动,它强调外部规范,这与治理的过程性特征是相冲突的。
其次,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中,发挥决定作用的力量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权力,权力的行使向度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实现过程中具有强制和支配的特性;虽然由于政府失灵或者提高行政效率的考虑,政府会将一些权力让与或委托给大学,但大学很难与行政权力平等对话和协商,这与治理中的协调性特征相区别。
再次,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中政府作为“管理者”地位凸显,遏制、压缩其他主体的成长空间,“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构模式使得政府之外的大学和其他社会组织不具有实际上的主体地位,更无法发挥主体作用,这明显与治理的多主体性特征不符。
最后,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中,大学的办学行为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组织和被引导的。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下,政府以国家意志的名义要求被管理者服从而不是与其合作;虽然由于民主的需求,管理者会给被管理者一定的话语权和平等对话的机会,但是这种互动是负载国家意志倾向的,政府因其国家代理人的身份而忽视或放弃与非政府的合作,不重视甚至排斥公民社会的参与,这与治理的持续互动性特征不相容。
(二)大学主体性的缺失
大学治理中,大学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至关重要。大学的主体性是大学治理的必要条件。大学的主体性不仅体现在大学的主体身份上,还应体现于大学在治理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上。当前我国大学主体性的缺失已经成为大学的生存常态。
1.大学主体性缺失的表现
大学主体性的缺失与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政府与大学之间行政隶属关系过度放大的结果。1998年颁布生效、2015年修订的《高等教育法》第十三条、四十条分别规定地方省级政府“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管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这为我国政府与大学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确立提供了法律保障。政府对大学的行政管理权是国家权力得以实现的内容之一,也表明政府获得了对大学进行行政管理的合法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在政府的行政管理下就成了其“统治”的对象。行政权力的过度使用,加强了大学对政府的“人身”依附,政府通过人员任免、经费拨付、项目审批、选优评优等具体行为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依附关系。政府与大学之间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身份关系消解了大学的主体性,“大学的行为不再是基于自我价值和使命的自律性行为,而是更多地体现外界的他律性要求”,“大学逐渐丧失了履行自身公共责任的动力、能力和权力,更多的是外力驱动下的被动行为”。[11]在政府与大学行政关系过度支配下,我国那些所谓明晰大学主体地位的改革可能都只是隔靴搔痒。如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明确了大学的法人地位,确立了大学在招生、专业设置、教学、科研、海外交流、人事管理和财务管理七个方面的办学自主权,这对于我国大学自主性的发展确实是制度上的创新与进步,然而经过实践证明,“大学的自主性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提高”,表现在“高等院校的办学目标过于功利化、大学文化的政治化、学术管理中的官僚化,大学在传承和发展学术上的功能不断的弱化”。[12]2011年11月,教育部颁布《大学章程制定暂行办法》,要求大学制定章程,作为大学内部的“宪法”,从而引起全国大学制定章程的热潮,但是被嵌入国家权力框架之中的大学,已经演变为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性的社会组织机构,制定大学章程可以预见又是一次“摸石头过河”的探索,前景不容乐观。
大学主体性的缺失还体现在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单一与大学教师的生存生态恶化上。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长校人,是大学的法人代表,代表大学从事一切社会活动,因此校长的独立性对于大学主体性至关重要。但“现行的大学校长聘任、管理政策大体是延续或照搬一般党政干部管理条例”[13],行政任命仍然是当前构成我国高等教育主要部分的公立大学的校长的产生方式。2017年1月中组部会同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印发《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规范了高校校长的产生方式,校长要受到“严格”的选拔与聘任制度制约,但大学校长的产生并未“去行政化”,公立大学的校长仍然不能摆脱行政任免的宿命。这种方式下产生的大学校长,按照我国行政组织运行的“下级服从上级”这一基本原则,是必须服从其任命者的,不仅服从,在现实逻辑中甚至变成为“唯命是从”,导致如今的大学正如有的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大学的畸形——工具化、手段化、官僚化、行政支配学术,权威压倒理性,循规蹈矩办学”[14]764。大学主体性缺失还体现在大学教师生存生态环境的恶化上。大学教师作为大学学术象征的人格化力量来源之一,是大学教育的实施者、大学精神的捍卫者。当前我国大学教师的生存生态环境恶化,毋庸赘述,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教师张丽琴创作的诗歌《我是教师,我拒绝》、武汉大学夏琼教授的辞职信、四川大学教师周鼎的“酒后真言”等公众事件都是最好的说明。邓晓芒在《我的大学》一文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教师的地位‘提高’了,他们从被‘改造’的对象变成了‘创收’的工具,以及为官僚的学术头衔‘加冕’的祭师。但他们的行为必须服从官僚体制运作的程式。”[15]大学教师生存生态的恶化,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学独立发展的生存空间正在缩减。
2.大学主体性缺失导致“大学治理”难以实现
政府与大学的行政隶属关系中政府权力的过度行使导致了大学主体性的缺失。而大学主体性的缺失,意味着我国大学教育是一种行政主导下的办学活动,偏离了大学治理的基本要求,导致了我国的大学治理难以真正实现。
首先,大学主体性的缺失,使得大学在制约大学发展的外部规则形成过程中失语。而缺乏话语权的大学在行政主导的大学管理实践中又进一步强化了与政府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成了名副其实的“被统治者”。这与治理的过程性特征不符。
其次,大学主体性的缺失,使得大学很难对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产生多大的反作用力,无法实现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无法为自身争取到平等对话与平等协商的机会,这与治理的协调性特征不符。
再次,大学主体性的缺失,在大学管理实践中没有主体地位,无法发挥主体性作用,这与治理的多主体性特征不符。
最后,大学主体性的缺失,使得大学与管理者之间的持续互动失去可能,大学在管理者的组织与引导下办学,按照管理者的指令办学,这与治理的持续互动性特征不符。
综上所述,在政府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中,在多元主体还不成熟的条件下,我国的大学治理还只是研究者的一个构思与设想,不能理所当然地视其为事实。那些建立在我国大学治理“实然”状态下的研究是对“大学治理”的“滥用”,体现的是大学管理时尚中的“伪治理”。
五、实现大学治理的途径
既然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是影响我国大学治理的主要问题,还导致了大学主体性的缺失,那么我国大学治理的可能实现也就在于打破大学发展中“行政主导”这一弊端,变更政府管理模式,真正理顺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权责分工。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根源于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逻辑,即通过提升国家能力,对社会进行全面干预和强力整合,打造全能型政府,从而造就了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不可否认,随着社会事务的日益繁杂,需要一个超越社会之上的“利维坦”式的政府行使公共权力协调社会关系,但并不能由此证明行政权力在社会各领域(包括大学)中无限扩张的合理性。因此,打破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最根本的途径在于变更教育行政机关的管理模式,将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成功剥离,制定“良法”规范政府活动,使政府在限制公民、法人自由方面权力最小,而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责任最大。
1.通过变更管理模式,改变“无限政府”的错误定位。政府收缩权力触角的范围和职能边界,明晰大学作为知识生产与创新的组织机构所应享有的独立地位。政府对大学的监督与管理中,不必“事必亲为”,政府不能对大学管得过死,不必制定详细的条条框框去告诉大学应该做什么,而是应该理解支持大学自身的发展行为,并对大学的办学行为有一定的包容性。政府制定的规则不是大学发展的主导规则,大学的发展遵循自身的组织特性和规律,对大学的管理不是政府的统治活动,大学校长不是按照政府指令去办学。
2.通过变更管理模式,塑造服务型政府的角色,改变政府公共权力行使中的官僚特性。政府以提供健全完善的公共服务为主,不再扮演发号施令者的角色,不再以“国家意志”为借口对大学发展指手画脚,而是大学发展中的“理性思考者”和“有效监督者与建议者”。政府和大学作为大学发展中的“行动者”,以平等的身份加强对话、相互协商,从而有效解决大学发展中的矛盾。
3.通过变更管理模式,发挥政府“扶持之手”的作用,创造空间推动多元权力主体的成长。政府应放弃对公共资源垄断性地占有和调控,在社会多元化的趋势下,鼓励利益的多元化走向主体多元化,培育和创设多元主体独立成长的空间。政府在管理大学的过程中,尊重大学的独立法人地位,允许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更加民主和多样化。让大学选举产生校长、政府任用,对校长任期不作制度上的规定,使大学作为办学者的主体地位得到凸显,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4.通过变更管理模式,重新界定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即政府与大学之间应该是互动合作的关系。传统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定位阻碍了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持续互动。政府行使公共职权的过程和大学的办学过程中是二者的紧密合作、持续互动的过程。这种合作与互动不是统治活动,是政府与非政府之间基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合作,是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合作。
总之,“要使国家和政府有所作为的最好办法,就是对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和能力加以必要的限制,使其有所不为”[16]。通过充分有效地变更政府管理模式,改变行政主导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使得“在这里,政府就至少并非唯一的主角,也并非不可或缺的主角”[1],从而使得我国大学治理的实现成为可能。
[1]沈佩萍.反思与超越——解读中国语境下的治理理论[J].探索与争鸣,2003,(4).
[2]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G]//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龚怡祖.大学治理结构:建立大学变化中的力量平衡——从理论思考到政策行动[J].高等教育研究,2010,(12).
[4]顾建民.超越大学治理结构——关于大学实现有效治理的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11,(9).
[5]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G]//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6]詹·库伊曼.治理和治理能力:利用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性[G]//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7]辛西娅·休伊特·德·阿尔坎塔拉.“治理”的概念与滥用[G]//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8]王诗宗.治理理论及其中国适用性[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9]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 徐辉,陈晓菲,译.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0]周川.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9,(8).
[11]钟伟军,宣勇.现代社会中的公共精神成长与大学主体性建设[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3,(1).
[12]赵敏,章文杰.大学主体性的失落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13]龚放.以治校为志业:大学治理的新常态[J].高等教育研究,2015,(10).
[14]姚国华.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
[15]邓晓芒.我的大学[J].书屋,2007,(8).
[16]燕继荣.从“行政主导”到“有限政府”—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与路径[J].学海,2011,(3).
[责任编辑:罗雯瑶]
University Governance: An Abused Buzzword:Rethinking on the Study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in China
XIAO Wei-bing
( School of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China )
Many studies on university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are not carried out under the paradigm of“governance theory”. Governanc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cess, coordination, multi subjectivity and continuous interaction. University governance in China is struggling forward in the facts of“being highly questioned”and“actively exploring”.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ials lead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in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ies losing their autonomy are two major problems to enhanceour university governance. The university governance is much more doable by changing this pattern to optimize th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system.
university governance; governance concept; governance characters; officials-led government;university autonomy
G647.1
A
2095-7068(2017)03-0073-08
2017-05-31
10.19563/j.cnki.sdjk.2017.03.010
肖卫兵(1979— ),男,安徽安庆人,博士,苏州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研究。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青年资助课题“国民政府时期国立大学治理结构与特征研究及其当代启示”(项目编号:C-a/2013/01/0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