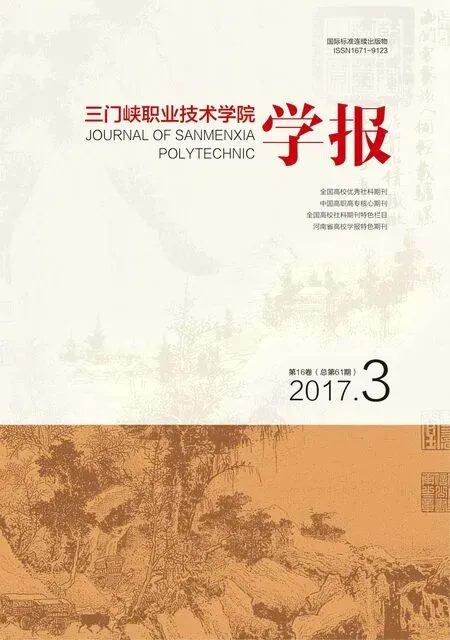从《牡丹亭》看明代思想家的“情”“理”观
◎王金文
从《牡丹亭》看明代思想家的“情”“理”观
◎王金文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师范学院,河南 三门峡 472000)
明代伟大戏曲家汤显祖的《牡丹亭》所表现的情理观反映了明代多位思想家的观点,其后的王夫之关于“人欲”“天理”的论述更可看出一脉相承的特点;之前的阳明心学也对《牡丹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汤显祖;《牡丹亭》;情理观;王夫之;阳明心学
明代关于情和理之间的关系论述最重要的有两大派别:一派是唯理论者,主理而抑情,此派以理学家为代表,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承袭了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的观点;另一派是唯情论者,主张崇情而黜理,此派以晚明人文主义者为代表,王阳明、王夫之即为其典型人物。笔者选取汤显祖的《牡丹亭》为主线梳理出以情反理,“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1]的情理观。
一、汤显祖的《牡丹亭》及其情理观
汤显祖,江西临川人,20岁中举,33岁中进士,明代伟大戏曲家。其戏曲作品有《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
《牡丹亭》又名《还魂记》,主要根据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记》编写而成。它是“四梦”中最杰出的一部,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艺术成就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为了充分表达杜丽娘为爱情而死和为爱情而生的强烈追求,作者驰骋想象,把天上地下、现实梦境交织在一起,人鬼神仙熔于一炉,使作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是一部最杰出的浪漫主义巨著。
汤显祖是明朝人,生于1550年,逝于1616年,但《牡丹亭》所描写的却是南宋时期的故事,显然作者采用了假托前朝的手法,目的是为了讽刺当今时事。这样的笔法在历代文学作品中并不鲜见。
汤显祖以“临川四梦”构建应和时代的“至情”理想,他一生“为情作使”、“为情转易”,《牡丹亭》对至情进行了直接大胆的描写和歌颂。但是作为儒生,合理合法的社会准则依然会作为一个尺度保留在儒生汤显祖心中。汤氏试图在《牡丹亭》中构筑一个情理兼顾、存理遂欲的人性社会。[2]杜丽娘南安太守小姐的身份和柳梦梅后来考中状元的情节都不啻是作者的刻意安排,也是他思想的表露,是他的情理观的显现。
正如剧中杜丽娘的唱词“生生死死遂人愿”,《牡丹亭》通过刻画杜丽娘生而死、死而生的情感历程展示了戏剧冲突——情与理的冲突。此“情”是表现为爱情的人的自然本性,此“理”则是表现为礼义规范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汤显祖所处的年代并不像清末那样一个外来文化入侵、新思潮蒙发的年代,所以他创作中的很多突破理学束缚及叛逆的思想都是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种总结和超越,并且这种思想的形成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他的良师益友。
要真正理解汤显祖其人及其创作思想,就必须知道他的一些经历。汤显祖从祖父和父亲那里受到道家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后来受到老师罗汝芳、徐良傅的影响,在不惑之年终因不附权贵弃官隐居家中,专事写作。弃官后他与当时的左派大师李贽以及“名震东南”的达观禅师交往密切,李贽是封建卫道者们的洪水猛兽,而达观以禅宗反对程朱理学。汤显祖不肯结交当时声名颇大的王世贞等名流,却与公安派的袁宏道等人来往密切。
《牡丹亭》创作于汤显祖从遂昌弃官回家之后。这时的汤显祖对社会生活和宦海风波已有了很深的阅历,但他对生活和政治的热情并未衰减,他的艺术创作此时正处于顶峰,无论是思想、阅历还是戏曲艺术,都为《牡丹亭》的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说:“天下好有情,宁有如杜丽娘乎!”作者这段话,是对《牡丹亭》以“情”抗“理”的总括,也是这部传奇剧中艺术形象赖以表现的基础。其中的情与理,是指人欲与天理之间的斗争,而不是情感与理智的矛盾。
二、王夫之及其“人欲”“天理”观
汤显祖非凡的人生和丰富的经历让他的思想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在他死后三年,即公元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湖南衡阳诞生了一个日后成为明代思想家的孩子——王夫之,他自号“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他所建立的哲学体系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他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将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相结合,从而将中国古代自老子以来的辩证法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他还痛斥宋明道学家的“惩忿”、“窒欲”、“灭情”等扭曲人性、伦理异化的谬论,主张天理即在人欲中,“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这种思想对后人也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3]
王夫之还认为:“集注云‘人欲净尽,天理流行’,朱子又云‘须先教心直得无欲’……盖凡声色、货利、权势、事功之可欲而我欲之者,皆谓之欲。……只缘他预立一愿欲要得如此,得如此而为之,则其欲遂,不得如此而为之,则长似怀挟着一腔子悒怏歆羡在,即此便是人欲。而天理之或当如此,或且不当如此,或虽如此而不尽如此者,则先为愿欲所窒碍而不能通”。[4]
“朱子有正胜邪,天理胜人欲两段解:其言正胜邪者,即新安之说;其言天理胜人欲者,推本正所以胜邪之理尔”。[4]
“故不于性言孝弟,则必沦于情;不于天理之节文言孝弟,则必以人欲而行乎天理。……性、情之分,理、欲之别,其际严矣。”[4]
“天理、人欲,虽异情而亦同行。……故遏欲、存理,偏废则两皆非据。欲不遏而欲存理,则其于理也,虽得复失。非存理而以遏欲,或强禁之,将如隔日瘧之未发;抑空守之,必入于异端之‘三唤主人’,认空空洞洞地作‘无位真人’也。”[4]
“故曰‘天者理之所自出’。凡理皆天,固信然矣。”[4]
王夫之企图说明“理”和“欲”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理必在欲上见”,没有欲,也就没有理,以此反对道家唯心主义“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观点。但他仍把道德观念看成人性的内容,把孝慈等道德看成天生具有的,同样强调君臣父子之理,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5]
王夫之又说:“理者,天所昭著之秩序也。”[5]“人欲者,为耳目口体所蔽而窒其天理者也。”[5]
王船山的“情”“理”观与汤显祖的《牡丹亭》一脉相承,何其相似,反映出明代思想家对于“情”“理”的看法。人欲与天理,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和谐统一地存在于万事万物中,并且不断斗争,推动事物发展。这种哲学观点对于今人来说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三、阳明心学及对《牡丹亭》“情”“理”观的影响
汤显祖和王夫之皆生活于明代晚期,在他们之前,明朝还曾出现了一位哲学家——王守仁(1472年生),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
王守仁的哲学思想是陆象山(九渊)“心学”流派的继续。他进一步发挥了陆象山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象山先生全集杂说》)的主观唯心主义命题。他认为“心之本体无所不该”(《传习录》下),客观事物的存在乃是人之主观知觉作用的结果,一切都是从“心”派生出来的。在他看来,没有被心知觉到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他说:“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为之物。”(《答罗整菴少宰书》)又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按当时一般人认为鬼神是确实存在的)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传习录》下)
与这种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直接相联结的,是他的“致良知”的学说。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致良知”就是恢复“良知”,达到“良知”的极致的意思。王守仁认为“致知在于格物”的“格”当“正”字讲,“物”是指人的意念,而不是指客观事物。他说:“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他既然认为“心自然会知”,“心外无理,心外无事”,要“知”,当然不必“外心以求理”(《答顾东桥书》)。“心”(即“良知”)就是“天理”,因此“认识”在他看来不过是“良知”的自我认识而已。因而他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答顾东桥书》)
从“致良知”的观点出发,王守仁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学说。他反对朱熹派的“外心以求理”,他认为:“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答顾东桥书》)可见,“知行合一”的学说是建立在他的所谓“致良知”(即“求理于吾心”)的基础之上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的“知”,是他认为人所生而具有的“良知”。在符合“良知”条件下,他认为“知”即“行”,“行”即“知”。对于“知行合一”的涵义,他还认为:“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谓良知也。孰无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谓‘知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为一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五《文录》二《书与陆之静》辛巳)。人要“知”,无须外求,只要“求理于吾心”就行了。做到这一点,就是“知行合一”了,也就是实现了他所谓的“知行本体”了。如果他的“知”和“行”有层次的差别的话,差别也就在这里。
在《传习录》(上,节录)中,他又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他还说:“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他还有话说:“先生曰:‘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
“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先生曰:“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渐有见。如今一说话之间,虽只讲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间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窃发而不知者,虽用力察之,尚不易见,况徒口讲而可得尽知乎!今只管讲天理来顿放着不循,讲人欲来顿放着不去,岂格物致知之学!后世之学,其极致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的功夫。”
在《传习录》(中,节录)《答顾东桥书》(一)中,王阳明论述道:“来书云:‘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晦菴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闇而不达之处,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在《传习录》(下,选录)中,王阳明又阐述道:“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了,亦何缘能尽知得!但不必知的,圣人自不消求知;其所当知的,圣人自能问人,如‘子入太庙,每事问’之类。先儒谓‘虽知亦问,敬谨之至’,此说不可通。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然他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不知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
他还说:“尝闻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什么教做心?’对曰:‘只是一个灵明。’”[6]
如此等等,皆是王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高度体现,其中不乏精辟至极的高妙之论,值得仔细咀嚼它的深刻涵义。
阳明心学对《牡丹亭》情理关系有很大影响。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情与礼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这与汤显祖的用世之情紧密相连,更与阳明心学促成的哲学转向深有关系。心学主张本心至善,反对视理与气为对立存在的两物;情与理乃“为物不二”的关系,情即理。[7]
汤显祖的传世剧作《牡丹亭》中的男女主人公杜丽娘和柳梦梅也是“人欲”、“天理”学说的亲身实践者。他们由相遇—相知—相爱,然而,他们也并非做到了如朱熹所说的“存天理,灭人欲”,而是不断在矛盾中斗争、发展、变化。其中“游园”、“惊梦”、“寻梦”等情节都是非常著名的片段,集中反映了男女主人公的经历及其心理变化过程。这些故事情节的发展也符合“人欲”“天理”说,印证了阳明心学及王夫之等明代思想家的“情理观”。当然,全剧还是脱离不了老套的窠臼,最终柳梦梅考中状元,“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也是传统中国戏剧“大团圆”结局的又一体现。
汤显祖的《牡丹亭》因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成就成为明代戏曲领域最优秀的作品。该作品的巨大成功在于将“情”与“理”的对立推向了极致,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效果。“情”“理”冲突在《牡丹亭》中的细节表现十分突出。从这一特征出发,可以透视“情”、“理”之争的社会、经济和哲学背景。[8]
阳明心学和出现在他之后的王夫之的“人欲”“天理”之说有相似之处,应该说对王夫之有很大影响。汤显祖的《牡丹亭》承前启后,在其中体现出的以“情”抗“理”情理观,反映了“人欲”“天理”之间的矛盾斗争,对后世产生了深刻而远大的影响。
[1]张泓.从“三言”看冯梦龙的情理观.江南论坛,2016(2):60-61.
[2]翟华英.〈牡丹亭〉“至情”观[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6(2):59-60+63.
[3]王之春.船山公年谱[M].清光绪鄂藩使署刻本.
[4]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M].北京:中华书局,1975(6):369;706;708;717-718;719
[5]王夫之.张子正蒙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5(9):9-10;115:129
[6]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宋元明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3(2):247-263.
[7]丁芳.情即理:阳明心学对〈牡丹亭〉情理关系的影响[J].兰州学刊,2012(12):67-63.
[8]张志凌.论汤显祖〈牡丹亭〉的“情”与“理”[J].安徽文学,2012(12)(下半月):60-61.
I207.3
A
1671-9123(2017)03-0089-05
2017-06-19
王金文(1967-),女,河北枣强人,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汉语、金石学研究。
(责任编辑 倪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