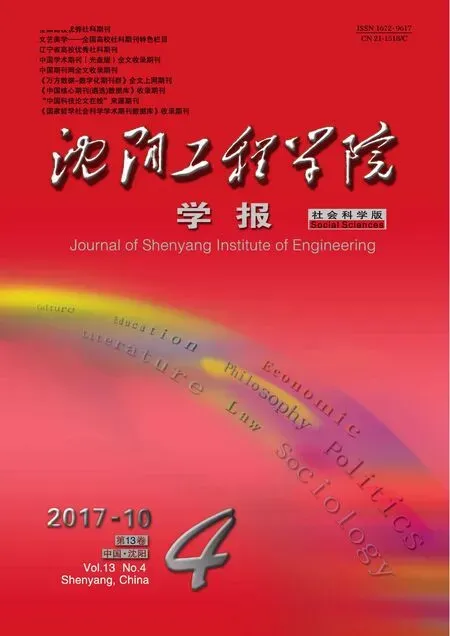林泉美感的和合奏鸣
吴玉杰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林泉美感的和合奏鸣
吴玉杰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五四”运动之后,新诗崛起,旧体诗迅速地边缘化,旧体诗写作逐渐淡出作家视野。虽然早期新文学作家仍然从事旧体诗写作,但它并不是他们的“主业”。旧体诗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20世纪发生断裂。作家早已意识到旧体诗的文化魅力与凝聚力:“中国旧体诗词是一大文学瑰宝,是汉语汉字魅力的极致的表演,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些年,在弘扬传统文化、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主旋律之下,旧体诗创作似有勃兴。然而,不同的人对于旧体诗创作有不同的诉求。旧体诗,对于有些人来说是“闲暇的把玩”;对于那些有“传统的人生意趣、情感方式和审美意向”的人来说,有的是交游的唱和与赠礼,有的是精神的伴侣;对于国画家来说,其作为题画诗而成为艺术的必需。不过,对于著名的国画家冯大中来说,旧体诗却是日常的创作,成为他自觉表达自由的一种文体。虽然他说自己对古体诗词是“票友”,可是他对诗的爱好非同一般。写诗,和他作为一个国画家有关,作画时“题字补空”,因为题画诗是对画中表现的创造主体审美情感运动的延续与上扬。但实际情况却不尽如此,他的旧体诗创作具有常态性,已经成为他日常表达情感的自觉方式:飞机延误时写诗,长途旅行时写诗;秋日登山写诗感怀,心绪不佳时写诗暇怀,雨后登山赏泉得诗骋怀。诗,成为冯大中生活的必需。由此他创作的旧体诗,逐渐脱离画之“母体”、脱离朋友“互赠之礼”而成为独立的审美性存在。诗,不再是附属品,而是精神的伴侣。
冯大中作诗的题材指向和主旨意向多集中在林泉。林泉在诗中有时是显像式存在,有时是潜隐性存在。他创作的很多诗寄情林泉,有的诗心向林泉,并没有出现山水,但却是山水转化的自然的另一种存在。所以,我们可以推而广之,冯大中对于林泉审美之观照,时而近距离地“身即山川而取之”,时而远距离地“心即山川而神游之”,获林泉之乐、品林泉之趣,拥林泉之梦,追林泉之思,美感油然而生,和合奏鸣,而这一切源于他怀林泉之心。
一、林泉之乐的审美自得
冯大中寄情林泉,一方面林泉指自然的具象化,诗人“游山玩水”,观日出日落,赏花开花落,徜徉自然之中,抛却化不开的意绪,悠悠然;另一方面林泉指自然而然的状态感,诗人吟诗作画,邀朋谈话,纵酒啜茶,沉浸畅意人生,领略不一样的情致,欣欣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身即山川而取之”,“泉石啸傲,所常乐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冯大中面对林泉,常处、常乐、常适、常亲,审美主体进入自然之中,细致观照自然。
诗人在林泉中的快乐使他悠然自得。《和友人》写道:“山人没有威,只愿泰安随。寄意林泉乐,悠然载月归。”对于诗人来说,平安康泰,是心中所愿。把自己的情感与意绪寄托在林泉,载月而归,自然获得轻松与快慰。不仅如此,在心绪不佳时自然还给他带来愉悦。《夏日感怀偶成》写道:
向晚雨初晴,驱车唱大风。
心随绿波远,怀敞赤霞迎。
最狂笔和墨,难舍痴与情。
闲来邀好友,纵酒啜香茗。
这首诗是《大中诗钞》中的第一首,可见诗人对它的偏爱。在题记中诗人说“甲申夏月,余心绪时有不佳”。所以才在骤雨初晴后驱车郊外,见绿野晚霞,心境敞开,“偶成一首,以寄暇怀。”诗人在观照自然获得自然之乐的铺垫中,转入观照自身,表达自己对诗画的一片痴情,最后又转入与好友纵酒啜茶的快乐之中。因而,林泉就有了多重的含义,既是身即山川的自然,又是诗画对象化的自然,还是自我本真的自然。当然,林泉之乐相应地也有了多重的含义。
冯大中的诗多有登山感怀。每天早上登山早已形成习惯,登山中灵感不期而至,偶成、偶得之作迭出。恰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所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身即山川,诗人进行诗歌创作,抒发情感,获得美感,是自我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但诗人并没有止于山川之中,而总是从自然中生发关于创作与生活的诸多联想,在这些联想中,主要和友、茶、酒有关。比如,“涧水烹茶效陆郎”(《庚寅秋日登青云山、关门山感怀》);“五湖烟水今归去,旧雨新知把酒欢”(《骊歌》);“最念神交朋友事,与君畅饮话香茶”(《畅饮》)。诗人时常与友“畅叙兼豪饮”(《乙未之春赠凡修先生》),而一旦“温火煮茶浓”,不知“谁是知音从” (《炊烟》)时,却感怅落。由此可见,身即山川,与友相邀,谈诗论画,饮酒吃茶,成为诗人创作题材指向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诗人获得审美愉悦的本源。
在诗人那里,如果不能“身即山川而取之”,那么则会“心即山川而神游之”,创造属于自我的林泉世界,从而获得林泉之乐。农家小院或自家小园寄寓诗人这样的意向。“男人饮酒敲牌闹,女子烹茶引玉泉。老犬杏阴低首卧,新雏葡架敢孤眠。”(《初秋农家小院感怀》)初秋时节这样的农家小院,我们不妨说这是诗人的“桃花源”,具有家的情怀。诗人虽踏遍万水千山,但他钟情故里林泉,显现出强烈的恋乡情结。《题画荷花》之二写道:“塞北江南两样天,神游万里好江川。纵然放眼皆佳景,最是情痴故里山。”诗中赫然可见对故乡的痴情。《原韵和奉王向峰题冯大中艺术馆六首之二》写道:“不恋皇城恋故乡,青山无尽有精藏。小园一统别天地,笔墨相融古籍香。”诗人把对小院的眷恋、对于小园的钟爱诉诸笔端。《赠友人》写道:“小院今天雪更白,陌阡谁伴玉人来?敲诗润墨煮茶道,把酒兴酣踉月台。”这里的小院、小园,是自然山川的转化形式,是诗人自己建构的林泉。
无论是自然之在的林泉,还是诗画对象化的林泉,乃至于自我建构的林泉,都给予诗人林泉之乐与林泉之美。诗人在林泉之中,意气飞扬,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和人生,创造美的世界。
二、林泉之趣的生命自在
林泉之乐之于诗人来说,是审美之愉悦。显然,诗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似乎更愿意成为林泉之一部分。不过,作为红尘客的他,并不能总是如愿以偿。因而,在不同的情境与心绪中,作者对自我的身份定位都有所不同,他是“红尘客”“伏虎君”“老夫”,也是“林下客”“逍遥翁”“山人”。这些不同的身份定位彰显出他与林泉关系中的不同情趣。这其中,“山人”最能表征诗人品味林泉之趣的生命自在。
“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何者?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故画者当以此意造,而鉴者又当以此意穷之,此之谓不失其本意。”这是郭熙针对林泉与画者、观者的关系而言,但林泉和文学创作者、读者的关系与其具有同构性。诗人抒写林泉,亦有此本意,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林泉是神游之地,是精神的栖居之地,这是诗人作诗的情致与趣味所在。他和林泉的关系因不同的情境,有时显现为可行、可望,有时显现为可居、可游。在他的诗中,当他以“红尘客”“林下客”“老夫”等自况时,林泉则是可行、可望与可游,而以“山人”“逍遥翁”自况时,林泉则是可居。更准确的表述是,前者为行之、望之、游之的状态,后者则是居之的状态。而就“我”相对于“林泉”的存在而言,则可表述为他在与自在。我们先看前者在诗中的表达:
我是红尘客,五十悟禅林。
芸芸追逐梦,醒觉有何人?
——《访九华山有感赠友人》
今日惯为林下客,
山花啼鸟共吟诗。
——《山林咏》
且看老夫行健步,
青峰顶上掠流云。
——《夏日游山偶感》
第一首诗是诗人访九华山有感而写,九华山是中国佛教名山,诗人说“我是红尘客”,而访九华山之“访”则表明“我”不在,“我”对于林泉来说是他在。第二首诗中的“山花啼鸟共吟诗”,似乎写的是诗人与自然共在,但前一句“今日惯为林下客”,则表明诗人的客体性,因而“我”之于林泉也是他在。第三首中“老夫”的自况表明登峰掠云的豪迈之情,渗透着“我”和林泉之分明的意向。因而“红尘客”“林下客”和“老夫”的自况,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我”和林泉的非共一性。
但当诗人以“山人”自居时,“我”和林泉则具有共在性,或者说“我”处于一种自在状态:
山人寄意林泉胜,
风月依然恋夏秋。
——《林泉有思》
山人没有威,只愿泰安随。
寄意林泉乐,悠然载月归。
——《和友人》
山人天性自由心,寄意砚台伏虎君。
自恋小园花果茂,乐邀高友酒杯深。
——《赠兴文公莅临草堂遣兴》
酒后山人露率真,直呼俚语笑翻君。
醒来却惭斯文尽,须炼身强更炼心。
——《无题》
在所有对自我的身份认定中,诗人最爱“山人”,因为“山人”无威,天性自由,坦诚率真。相对于“林下客”“老夫”的自况,“山人”对自我的认定更符合诗人的“期待视野”。“山人”介于“禅林”、道中人与人世间的俗人之间,他有俗人之举(“乐邀高友酒杯深”,酒后“直呼俚语”等),但却有佛道之心。在诗人那里,“山人”是自然之一部分,林泉为山人可居之所,“我”与林泉共在。“我”与林泉处于自然而然的状态,也是一种自在状态。“山人”的自况是诗人的自白,是诗人的自谦,也是诗人的“自恋”,这其中蕴含独特的人生情趣与生命意味。
三、林泉之梦的心灵自寻
冯大中说:“我不喜欢所谓的文人画那些小情调、小聪明、玩技巧。我追求的是大的气象,以及自然的生命力。”这是作为画家的表述,同样也适用冯大中作为一个诗人的表述。他的诗歌创作同样推崇自然,表现自然的生命力,追求大的气象。他的诗画都是表现自然,所以,我们可以说,他的诗画人生皆在自然。自然,不仅是他的表现对象,更寄寓他作为诗人画家的梦想。《题画二首之二》写道:“天地苍茫雪野浑,春风放胆扫残云。而今谁有林泉梦,归去来兮亦问津。”拥有“林泉梦”之人之少引起诗人的慨叹,而这一慨叹也是自我拥有林泉梦的自证。
林泉之梦为诗人所拥有,也为诗人一生心灵之追寻。宗白华说:“艺术的根基在于对于万物的酷爱,不但爱它们的形象,且从它们的形象中爱它们的灵魂。”诗人酷爱林泉,爱林泉的形象,它们是自然生命力的象征;爱它们的灵魂,它们的灵魂在于林泉之心。前者造就了诗人林泉之梦的心灵自寻,在林泉世界中追求自己富有生命力的诗画人生。后者导引诗人林泉之心的人格自洁,在世俗世界中提升自己以至纯净的澄明境界。在林泉中寻找、寄托自己的梦想,是诗人看到林泉生命力之所在:
秋雨涉塘送晚晴,鸿归蝉遁起蛩声。
萧萧黄叶从风叹,挺挺琼枝剪月惊。
有意残红温旧梦,无愁冻绿孕新生。
来春日照池波暖,菡萏重开色愈明。
——《荷塘四首之二》
秋天多以悲凉意象或成熟意象出现在惯常的审美视野之中,而前者尤以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最为经典。冯大中另辟蹊径,其所写《荷塘四首之二》中首联和颔联写的秋天似有悲凉,但至颈联笔锋转入“有意残红”和“无愁冻绿”,化轻悲凉氛围,语意指涉“温旧梦”和“孕新生”,别具一格;而尾联更以春的暖明色调彻底荡开悲凉意绪,凸显一片崭新的生命气息。在诗人那里,林泉之梦和诗画人生融为一体:“丹青寄我林泉致,泼墨怡情笑梦乡。”(《赠友人》)
冯大中追梦林泉,更重要的是,林泉为他创作之缘,灵感之泉。面对“衍水苍茫瑞雪飞”,他便“情动诗添酒满杯”(《初六瑞雪》);夜起听潮,他便“师法群山追梦影,独寻妙境骋云霄”(《三亚旅思》)。无论是身即山川还是心即山川,诗人总能够“迁想妙得”。五古《闻蝉》记录了诗人登山过程中的“恋诗”和“炼诗”:
今上玉皇顶,未闻蝉树鸣。
余闲常健步,始觉履将轻。
渐渐秋风起,飘飘黄叶零。
登山人激走,我却时而停。
只恋敲诗句,传君细细听。
“闻蝉”的命名,引导读者对蝉鸣的期待,但诗中却写“未闻蝉树鸣”,造成读者情感的落差。这是诗人的写作策略使然。“闻蝉”不过是一个“引子”而已,登山恋诗才是主旨所在。所以,“我”和一般的登山之人不同,在走走停停中诗兴勃发,进入“林泉之梦”。从诗的整体结构中,“闻蝉”只是一个能指,诗的所指则是自由自在,享受登山、在山的过程,因而欲闻蝉而未闻蝉并不影响登山心境。或许从这个角度更可以看出“伏虎君”“山人”的趣味。这首诗的妙处在于,读者在“闻蝉”“未闻”的情感落差之后,跟随诗人的思绪,进入诗人走走停停的“炼诗”之境,“只恋敲诗句”使读者“原谅”了诗人的“闻蝉”“未闻”,而“传君细细听”则彻底消解了诗人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感,完全捕获了读者的心,从而使读者对诗人和诗达成陌生而后的熟悉。诗中的“敲”和“传”二字颇为讲究,似乎是电子媒介时代手机写作和信息传递的方式,但又恰是推敲诗句和情感传递的内在隐含。“身即山川”,灵感频至,可见林泉与创作不可分割的深厚“渊源”,故此林泉之梦就成为自我心灵世界中“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永恒之在。
自然之生命力,身即山川与心即山川的创作灵感,使画家诗人自然而然地追求林泉之梦。诗画人生成为现实,而林泉之梦仍在继续,心灵自寻永远在路上,有诗为证:“忘情名山不辞远,梦寻莲界进堂奥。”(《题新年贺卡赠友人》)所以诗人发出这样的感慨:“万里神游一日间,寄情翰墨几得闲?”(《题画感怀》)也许画作《夏梦》是他诗画人生的另一种心灵自寻与“心理补偿”:“三虎睡态各异,或酣睡如醉,或睡眼惺忪犹在梦中。画家在描绘中注入美丽的梦幻,梦得温馨烂漫。”微妙的意味情趣不仅为“伏虎君”“山人”梦中渴望,也为读者观者所期待。诗人由此从林泉之梦进入林泉之思与林泉之心。
四、林泉之思的精神自觉
林泉之思,是指林泉所引发诗人的思考。冯大中的诗,往往以社会、人生与自然相照,自觉追自然之意,审自我精神,品人生滋味。面对林泉,诗人反观自身,一方面进行自我告诫、自我觉醒,另一方面获得自我觉悟、自我超越。
冯大中说:“自然界的丰富远远要大于我们的想象,要想将作品画得生动、耐看,你就得认真去向自然学习。”诗人画家意识到自然的无限丰富性和我们的有限想象力,因此他提出认真向自然学习。在他看来,向自然学习永远不可能完成,所以他有“师法群山追梦影”的执着精神。向自然学习,追求大的气象,而不是雕虫小技,《平生》可见他的凌云壮志:“平生作画岂雕虫,立志山君世不同。倘若苍天恩我健,心攀绝顶傲青空。”但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就,他都告诫自己:“高卧无忧居草堂,修心厚德岂能狂?”(《赠友人》)诗人不断自我告诫与精神醒觉,因而他寄情林泉,而“林泉有思”:“宦海飘蓬见逐流,英雄远志更须谋。山人寄意林泉胜,风月依然恋夏秋。”(《林泉有思》)
与自然林泉相比,功名社会、宦海人生令人精神疲惫、心灵赘累,从这个意义上说,林泉之思的现实指涉与诗人的精神自觉更彰显出特殊的意义与价值。《苍松》表明诗人的态度与情怀:
苍松野径上天台,古刹晨钟破雾开。
祈愿檀香香透骨,托情明月月移来。
填词尊羡苏辛体,命笔师从李杜才。
淡漠功名学五柳,心澄正道不徘徊。
随着首联自然环境的敞开,颔联转入诗人主体的移情——“托情明月”,颈联开始观照自我的诗化人生理想,尾联则是自我告诫与精神醒觉,像五柳先生那样淡漠功名,一心读书、饮酒、写文章。正如诗人在《逍遥》一诗中所写,“我在围城外,却行城市中”,与君同此,而“君累我轻松”,关键在于“车书为巨富,卧榻逍遥翁”。因此,诗人在自我醒觉的同时,获得自我超越。《题画感怀》也有同样的林泉之思:
万里神游一日间,寄情翰墨几得闲?
暮登九顶云光洞,朝谒五台宝刹山。
身恋功名心却累,魂驰砚海梦非凡。
何时作伴邀君往,西子范蠡不计年。
诗人“心即山川”,神游万里,寄情翰墨,在魂驰砚海中追梦林泉,远离身恋功名之累。诗人在林泉之中,精神自觉,超越俗世。这是诗人面对社会、人生的林泉之思。不仅如此,林泉对于诗人的“启迪”或曰诗人在林泉中的醒觉还在于对生命的感悟。面对人生衰老之必然,诗人从自然中获得感悟与超越。《回望》写道:
韶华虽逝意难消,回首人生志未挠。
含嫩春花虽老去,恋秋霜叶带情飘。
胸学子史方思远,眼望云山始论高。
闭目禅林闻暮鼓,再听虎啸卷松涛。
在时光的流逝中诗人一直追求人生之志,正如恋秋的霜叶一样情致依然。没有怅叹、没有怨怼、没有徘徊,从自然的生命历程中获取内在的力量,“胸学子史”“眼望云山”“闭目禅林”,继续自己的诗画人生。“秋天的悲凉”化为“意气”的“飞扬”,正如《庚寅秋日登青云山、关门山感怀》所写,“老去逢秋意气扬,云深壑顶赏秋光”,诗中昂扬着自觉的精神与向上的力量。
林泉之思,诗人从林泉转而向社会、向人生、向生命的追问和思考,诗中饱含深刻的哲思。面向林泉,在“车书”“砚海”“禅林”之中,诗人自我告诫与自我超越,获得精神的自觉。
五、林泉之心的人格自洁
诗人的乐、趣、梦、思,因林泉而起,又指向林泉,而贯穿其中的是,诗人的林泉之心。郭熙认为:“看山水亦有体,以林泉之心临之则价高,以骄侈之目临之则价低。”诗人以林泉之心观自然万物、社会人生与自我生命,以自然为高,因而以静心与炼心不断进行人格自洁,追求澄明之境。
冯大中说:“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皆有感而发。”《黄山写生》写出了诗人的心声:“万壑黄山搜画稿,千阶古道觅诗敲。云泉满眼澄心澈,忽醉玉兰笑俊梢。”诗人身即山川搜画觅诗,追林泉之梦。而云泉涌入眼帘,使内心澄澈,诗人沉醉林泉之中。这是诗人黄山写生的真实,也是诗人内心的真实。其实,是诗人以“澄心”观云泉,才获得自身的“澄心澈”。正如徐复观所言:“以超越于世俗之上的虚静之心对山水;此时的山水,乃能以其纯净之姿,进入于虚静之心的里面,而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因而人与自然,由相化而相忘;这便在第一自然中呈现出第二自然,而成为美的对象。”虚静之心的审美观照,使诗人与林泉融为一体,固有“静听天籁悦心胸”(《骋怀》),“心斋清净墨如云,笔底磅礴气壮浑”(《题画诗》)的心灵感应。
静心,对于诗人来说,不仅仅是观照林泉的心理状态,更是由林泉转向面对社会人生的心理状态。而一旦转向,就不仅仅是单一的心理状态,更是一种整一性的人格追求。换句话说,静心,是诗人林泉之心在社会人生中的人格自洁。面对凡俗之音乱耳、功名之累缠身、利禄之欲熏心、人性冷漠寒心等“乱象”,画家诗人静心以待。《桃仙机场见思小记》是诗人在京都与泉林之间奔波,于机场候机之时静看众生所思所写,可以看出其静心之力:“躲进书房里,遥看山起云。晨读思夜画,春种连夏耘。檀案浮香气,端砚研翰襟。全神画猛虎,率意泼云深。”诗人全神贯注于“诗情画意”之中,以此“悟道”“修心”,求“素心”之趣。诗人以静心之力不被世俗所扰,保持人格高洁。他以静心待物,也以静心待友,《直言达友人》说:“我现童心露坦诚”“率真留得对友朋。”此时的静心以道为上,正如其在《晨阳》中自白:“俗尘弟子怀诚敬,修得清心近道家。”但林泉之心在诗人那里不仅仅近道心,他时而说“闭目禅林”“悟禅林”“悟学禅意心未凋”又近佛心。
林泉之心以静心为表征,需炼心才能达成。炼心,是诗人人格自洁的路径。红尘俗世,心易被蒙蔽,需通过炼心才能剥离蔽障,心才能被重新照亮。《强弱》写道:“示弱逞强皆是弱,强弱原不在谁身。我无金甲却执玉,无辩无争炼静心。”诗人辩证看强弱,知静心须无辩无争才能炼成。炼心不止在林泉,也在日常生活之中。诗人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炼心,“将生命的存在刻画到‘尽精微’的境界”。《无题》写到酒后山人露率真之气,醒后觉无斯文,告诫自己“须炼身强更炼心”。炼心之后的静心之境,是人生的澄明之境。
六、结 语
也许,我们抱怨,林泉离我们太远,我们无法“身即山川而取之”。但不是它远离了我们,而是我们远离了它。我们可以“心即山川而神游之”,就像诗人那样。郭熙说:“自然布列于心中,不觉见之于笔下。”冯大中执着于林泉美感的追求,创造“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的艺术世界,实现他的“林泉之志”——“身即山川而取之”,“心即山川而神游之”。林泉生存于他的诗画之中,生存于他的审美世界、心灵世界与精神世界。他以人格自洁的林泉之心观照自然、社会、人生、生命,林泉之乐的审美自得、林泉之趣的生命自在、林泉之梦的心灵自寻、林泉之思的精神自觉,他与林泉融为一体。不是林泉走进了他,而是他走进了林泉,也可以说,林泉走进了他,因为他走进了林泉,创造林泉美感和合奏鸣的人生艺术与艺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