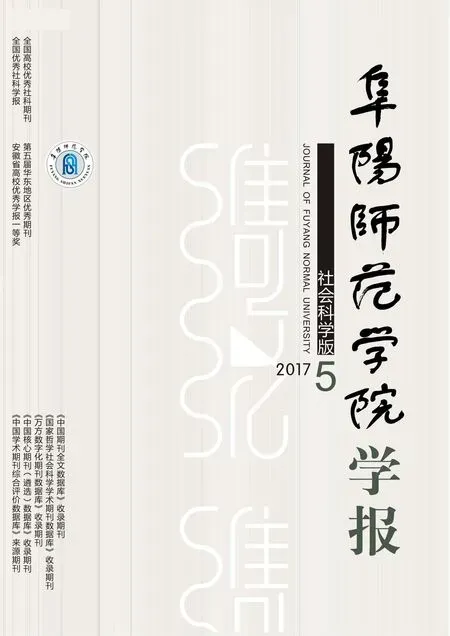个人意志与上帝力量:“陌生人”形象新解
潘丹丹
个人意志与上帝力量:“陌生人”形象新解
潘丹丹
(阜阳师范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易卜生长诗《在高原》中的“陌生人”,他的身份是上帝遣来的。随着“年轻人”内心矛盾的激化,上帝从隐身为自然界的“光”,到显现为“陌生人”的身影。“年轻人”相信“陌生人”的引导,他才克服了感情的磨难,最终坚定了自己“在高处”生活的决心。而“陌生人”带领“年轻人”找到的是自己心中的上帝。从本质上说“陌生人”是“年轻人”自我意志和上帝力量的统一,他具有神性,永恒存在,全知全能,将“年轻人”从尘世的痛苦中解脱。“陌生人”是诗人易卜生有意创造的神秘形象,体现了他在面临种种社会问题时对宗教的一种深刻认识。
“陌生人”;“年轻人”;个人意志;上帝力量
比约恩·海默尔认为易卜生在他的学徒年代(1851-1857)缓慢地“摸索建立起自己的、有强烈个人特色的创作天地”[1]46。1859年末,他倾心创作的长诗《在高原》,成为他诗歌的代表作之一。诗歌以独白的形式描写了一个“年轻人”一年多的生活历程,讲述了“年轻人”为了心中的理想独自一人去往高处,虽然遭受了种种考验和磨难,最终坚定了“在高处”生活的信念。这部长诗的故事情节清晰明确,人物关系简单明了,除“年轻人”外,还有“年轻人”的母亲、未婚妻、来自南方的“陌生人”。通过阅读全诗,我们对“陌生人”的形象印象深刻,在“年轻人”上高原生活的过程中,他不断给“年轻人”引导,对“年轻人”的选择与命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陌生人”与上帝
“陌生人”来自哪里?“陌生人”是谁?我们在长诗的故事情节中得知,他“从南方来到我们这里/渡过了无边无际的大海”,他“欢乐里响着哭声/思想寓于他的沉默里”[2]131。除此之外,我们无法查询他更多的身份信息。但是他的经验和思想,足以指导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在每一次紧要关头,在“年轻人”需要心理引导的时刻,“陌生人”总是如约而至,他的及时出现坚定了“年轻人”在高原生活的决心。没有人知道“陌生人”的行踪,但他似乎又无处不在,而且,“陌生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神秘,他们的每次相遇似乎都是必然的精心安排,就像上帝一直在“年轻人”身边,在关键时刻解救他一样。“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便得到了救赎。”我们足以相信,那“陌生人”就是上帝遣来的使者。不过,这个使者的身影是随着“年轻人”内心矛盾的激化,从隐到显慢慢地浮现出来的。
1.隐身:上帝之光
诗歌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年轻人”告别母亲,告别美丽的女子前往高山。此时,因为“年轻人”上高原的过程相当顺利,上帝只需隐身在自然界的物体中,以光的形式引导“年轻人”。在西方的文学传统中,“光”具有神性和永恒性,代表了上帝和天堂,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曾描写上帝就是光,隐身在荣耀的光明里,谁也看不到他[3]91。易卜生的这首长诗自然也是如此,“光”与上帝的指示联系了起来。诗歌第一节呈现的是月光的引导,“月亮把它虚幻的清光/从天上洒向峡湾”[2]123。月光对“年轻人”的引导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年轻人”告别母亲,在虚幻的月光下,走在通往林莽的小路上。紧接着,“年轻人”仍然在虚幻的月光下,见到了美丽的女子,两人沿着通往森林的小路前行。诗歌到了第二节,月光的引导变成了山上冰雪的光辉的引导,“深谷的上空,四面八方/闪烁着冰雪的光辉”[2]126。太阳已经出来,“年轻人”躺在山上,望着南方。在高处冰雪的光辉的引导下,他血液冷却,头脑冷静,继续前行。第三节是杜鹃花明光的引导,“在我所处的深谷的上面,只有火红的杜鹃花明光耀眼”[2]128。“年轻人”在杜鹃花明光的引导下,追寻“伟大的事业”,沿着山间小道奔向前去。在诗歌的前三节中,“年轻人”一路走下来,没有太多的犹豫和不安。此时,上帝和自然融为一体,以“光”的形式隐身于高处的月亮、冰雪及杜鹃花之中,指引“年轻人”前行。
2.显现:上帝的使者
从第五节开始,诗歌的紧张气氛扩散,“年轻人”开始犹豫要不要继续待在高原上,他常常梦见母亲,想念未婚妻,他思想摇摆不定,甚至一度精神萎靡,急切想回家找他们。此时,上帝从隐身状态显现,以“陌生人”的身份给他引导。
“陌生人”从南方“流浪”来,“欢乐里响着哭声”,他有冰冷的“视线”和冰川的“眼睛”,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寓于他的沉默里”“像鸟一样飞翔”“像旋风一样”漫卷[2]131。拥有这样的思想,一方面,他对尘世间的事物有更深远的想法。他将教堂的钟声与自然界的瀑布比较,“大瀑布轰轰隆隆/岂不更使人心神激荡”;他将母亲和未婚妻去教堂祈祷和年轻人的事业比较,“我们在外面把事业开创/总胜过在那里去踩马路”;他还将教堂里的歌唱和祭坛上的灯光与太阳和暴风雨比较,“更光明的是早晨的太阳/更动人的是暴风雨的轰隆”[2]133。另一方面,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在高山上,“年轻人”做梦想念家里的母亲和猫时,他知道梦的内容,“为什么做梦?莫非生活中/真正的事业你未曾找到”[2]132;圣诞夜的钟声诱惑年轻人回家时,他站在“年轻人”背后,“我的朋友心事重重/那还用说——亲爱的家屋”[2]137;在母亲居住的房屋燃烧时,他机智的进言,“只不过是燃烧,破旧的家园/脱了毛的猫,外加啤酒”[2]138;在未婚妻嫁给他人时,“年轻人”在悲伤中认识到“怎么努力也是白搭/于是摆脱了痛苦的折磨”,正在这时,陌生人又传来笑声,“已经到了分手的时辰……我不再是你需要的人”。“年轻人”在山上想念谷地的教堂生活、想念家中母亲和未婚妻时,他及时出现;“年轻人”的母亲被火烧死、未婚妻嫁人时,他又及时出现。他是上帝的使者,拥有睿智的思想和远见,拥有无所不知的能力。当“年轻人”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感情磨难,并且在磨难中醒悟时,他再次隐身,消失在自然界中。
二、“陌生人”与“年轻人”
“陌生人”作为上帝的使者,在整个长诗中,随着“年轻人”感情磨难的升级,他才现身在“年轻人”身边,给他做出引导。“年轻人”相信“陌生人”的引导,他才克服了感情的磨难,最终坚定了自己在高处生活的决心。“陌生人”是上帝的使者,可是这个上帝不仅仅是基督教的上帝,他兼具“年轻人”的个人意志。因此,“陌生人”是“年轻人”心中的上帝的使者,他带领“年轻人”找到的是“年轻人”心中的上帝。
1.“年轻人”相信“陌生人”的引导
当“陌生人”隐身为自然界的光时,“年轻人”信赖光的指引。诗歌的开头,“年轻人”在虚幻的月光下离开母亲;也是在虚幻的月光下来到美丽的女子身边,与女子林中缠绵;接下来,“年轻人”离开女子,在高处冰雪的光辉的指引下继续向前,“我要直抵山顶”[2]128;随后,“年轻人”感到疲倦,他想念女子,想保护女子,在这两种想法的激励下,他再次受到山上杜鹃花发出的明光的指引。“年轻人”在高处虚幻的月光、冰雪的光辉、杜鹃花的明光的指引下,决心直达山顶,更加接近上帝。当“陌生人”的身影显现后,“年轻人”信赖“陌生人”的引导。一方面,他在“陌生人”的劝说下过清贫的清教徒生活,在暴风中打猎,住简陋的山间茅舍,睡冰冷的雪地,这样的磨练不仅使年轻人的心变得更加坚强,“心儿已不再去想家乡”“心已变得更坚强”;而且他的思想更加自由,“思想在群山中飞腾”“思想像长上了翅膀”[2]134;在高原上生活,他感觉自己很幸福,心胸也开阔。另一方面,在“陌生人”的劝说下,他远离谷地的教堂生活,并克服感情的困扰。当圣诞夜的钟声响起时,他想着“在山下是我的妻子和老母/和他们在一起这就是幸福”[2]137,但“陌生人”的劝说让他变得勇敢而坚定,圣诞的钟声也无法使他“意乱心烦”。当母亲居住的房屋着火时,“陌生人”的进言让他克服了慌乱,真相是“母亲的灵魂飞上了天堂/天使们陪她同行”。[2]139当未婚妻嫁人时,“年轻人”意识到“从高处看着人群/看清了他们的真正的本质”。[2]141在每一次“年轻人”面临感情危机、想离开高原时,“年轻人”都会听从“陌生人”的劝说,在他的指示下变得情绪高涨,坚定了自己在高处生活的想法。
2.“陌生人”引导“年轻人”找到心中的上帝
“陌生人”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他的任务是带领“年轻人”找到上帝。而“年轻人”离开母亲和未婚妻,走向高原,孜孜以求的也是寻找上帝,他的态度执着而坚定。在诗歌的第二节,他克服对未婚妻的回忆,找回了自我,“我现在更接近上帝”[2]128,经历变故和磨难后,他找到了高处的自由和上帝,“我并非白白地从低地向这里攀登/这里有自由和上帝。我一个人得到了他们”[2]142。可是这个上帝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诗歌的第三节,“年轻人”想起了在谷地教堂中的上帝,“就像人群无数/一起拥到我们的教堂/做完了忏悔,然后散场”[2]129。紧接着,“年轻人”将上帝指称为“你”,“你可以在河上筑起拦河坝……你可以让她浪迹天涯”[2]130,在基督教的信念中,作为“全能和全知的创造者”上帝不能被指称,不能被讲述,不能被思考和谈论[4]4。使用表示平级关系的第二人称“你”,表明“年轻人”不相信在谷地教堂中的上帝的力量。令人奇怪的是,“陌生人”和“年轻人”的态度一样。他反对“年轻人”回到谷地的教堂中祈祷。他认为教堂的钟声不如自然界的瀑布声,教堂的歌声不如暴风雨声,祭坛上的明灯不如早晨的太阳。即使在圣诞节这个宣布上帝降临的日子里,他也没有让“年轻人”回家,相反,他劝说“年轻人”不要受到钟声的诱惑。由此看出,“陌生人”作为上帝的使者,他带领“年轻人”寻找的上帝,不仅仅是谷地教堂中的上帝。
仍然在诗歌的第三节,“年轻人”恳求上天“不要使我的未婚妻/命运更加艰难”,随即他又对此表示否定,认为自己“年轻又刚勇”,会给她帮助。不仅如此,“年轻人”相信自己的伟大事业可以和上帝的力量相抗衡,“新的磨难,谁战胜谁/咱们就试试看”[2]130。当“年轻人”一个人适应在高山上的生活时,他认为自己“足够坚强,可以克服忧闷”[2]136;当他经得住圣诞钟声的诱惑时,他认为自己“重又变得勇敢而坚定/重又得到了锻炼”[2]137;在经受感情打击(母亲死亡、未婚妻嫁人)面前,他仍强调自己的力量,“作为一个男子汉/应该走自己的真正的路”[2]141;当一切尘埃落定,他不再需要往日的梦想时,自我的力量还是不可忽略,“我受到了锻炼,自己做自己的主人”[2]142。“年轻人”坚持生活在高原上,一方面他要寻找上帝,另一方面,自我价值的体现是找到上帝的必要条件,显然,在他寻找的上帝那里一定要体现出自我的内心力量。
至此,“年轻人”找的上帝不在谷地教堂中,而是存在于高处,高处的上帝必须体现出“年轻人”自我的价值,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正因为此,所以他对教堂中的上帝表示怀疑,对谷地的教堂生活不再留恋。而“陌生人”是在遵循“年轻人”内心意志的前提下,引导他坚持生活在高原上,进而找到了心中的上帝。
三、“陌生人”:自我意志与上帝力量的统一
“陌生人”是“年轻人”执着走向高处的坚强动力,他伴随“年轻人”一路走来,见证了“年轻人”内心的感情变化,也见证了“年轻人”追求高处的坚定信心。“陌生人”作为上帝的使者,引领“年轻人”克服清贫的物质生活,拒绝谷地世俗生活的打扰,并且经受住了母亲被火烧死、未婚妻嫁给他人的感情磨难。“年轻人”信赖他,在每一次“年轻人”思想犹豫、不知所措时,他都听从了“陌生人”的引导,并因此变得意志坚定。而到了诗歌的最后,“陌生人”的使命完成,再次悄然隐身于自然界中,“年轻人”也找到了存在于高处的上帝和自由。“陌生人”的存在将“年轻人”的个人意志与上帝的引导完美的结合,是“年轻人”自我意志和宗教中上帝力量的统一体。
1.个人意志以“陌生人”为推力
“年轻人”的个人意志相当强大,他将自己的愿望等同于上帝的指示,借助“陌生人”推力,最终他才成功地生活在高原上。诗中的“年轻人”向家中的母亲告别时,曾承诺不久就会回来,然而直到母亲被火烧死,他仍抑制住了自己下山的愿望;“年轻人”和美丽的未婚妻情深意浓,称她为妻子,恨不得马上去教堂结婚,可是直到她嫁给别人,他也没有后悔在高原上生活。为了寻找高处的自由,他牺牲了母子之情,夫妻之情。当他在高处并习惯那里的生活时,他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很幸福,他足够坚强可以克服孤独和忧愁。当他母亲死亡、未婚妻嫁人时,他认为他从高处看清了人群的真正本质。昔日的梦想已经破灭,“年轻人”却认为自己得到了锻炼,“自己做了自己的主人”。到诗歌的最后,“年轻人”认为他的思想境界凌驾于在谷地生活的人们之上,“这里有自由和上帝/我一个人得到了他们/其他所有人都在谷地踱步”[2]142。“年轻人”坚信,高处有自由,他去高处追求早晨太阳的光明,暴风雨的轰隆,在山中飞腾的思想及高处的一瞥。高处有上帝,上帝那里有自由的呼吸和太阳的光芒。
2.上帝力量以“陌生人”为具化
上帝通过“陌生人”完成了对“年轻人”的引导。“陌生人”作为上帝的使者,他对“年轻人”梦想的实现至关重要。他并没有给“年轻人”新的指示,只是在“年轻人”想上高原生活的愿望的基础上推了一把,正是这恰如其分的推力,“年轻人”自己心中的主观愿望得以变得强大。“陌生人”的创造性思维使“年轻人”茅塞顿开,他因此认清了谷地生活与高地生活的区别;“陌生人”丰富的生活经验使“年轻人”不受世俗生活的诱惑,他因此在深渊的上面站稳脚跟;“陌生人”使“年轻人”看清母亲死亡、未婚妻嫁人的真相,得到双重启示(忏悔和罪行)。
上帝的力量以“陌生人”为具化。首先,“陌生人”具有神性。他尊崇自然,永恒存在。他在“年轻人”没有经受过多的感情纠结时,与自然融为一体,存在于高处的月亮、冰雪及杜鹃花之中,以光的形式引导年轻人,“年轻人”在走向高原的路上,变得聪明和坚强,心灵获得新生,并且被梦想激励。当“年轻人”感情遭受磨难时,他及时出现,化身为思想深邃、有远见的“陌生人”,使“年轻人”的心更坚强,思想更自由,让“年轻人”克服忧闷,重又得到锻炼。“年轻人”走在高处找到自由和上帝时,他又告别年轻人,再次隐身在自然中。从隐身到显现再到隐身,“陌生人”与自然共存,与上帝同在。其次,他全能全知。他知道在“年轻人”会想念世俗的教堂生活,他知道“年轻人”的母亲会遭受火灾,他也知道“年轻人”的妻子会嫁给他人,因此在每一次“年轻人”遭受感情上的痛苦时,他一定会出现在“年轻人”的身边,给他相应的指导。最后,“陌生人”具有拯救性,他将“年轻人”从尘世的痛苦中解脱。“陌生人”从隐身状态中显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年轻人”在高原上生活的日子的增加,他内心的矛盾开始剧增。他想念母亲,想念未婚妻,一度打算要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并且已经到了无法自我解脱的程度,上帝只有通过“陌生人”现身,他才能在痛苦中得到拯救。谷地教堂的钟声折磨他,圣诞夜的钟声诱惑他;他在母亲被火烧死时血液沸腾,在妻子嫁人时咬紧牙根,而只有“陌生人”的引导,才能将他从尘世的痛苦中拯救出来。正是“陌生人”的永恒存在、全知全能和具有拯救的神性吸引着“年轻人”,让“年轻人”虽然不知道“陌生人”是谁、来自哪里,仍然相信他的引导,最终从尘世的痛苦中得到解脱,成为“年轻人”坚持生活在高处的强大动力。
3.“陌生人”是自我与上帝的精神复合体
《在高原》写于易卜生个人生活最艰难的时间阶段。1857年他在一个濒临倒闭的剧院担任艺术总监,1958年结婚,妻子没有工作,1859年儿子出生。他这段时间既要搞剧务编剧,还要管理剧院,个人写作没有什么进展。除了处理繁忙的剧院事务之外,他还不得不面临经济的压力。他要承担起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还要抚养一个私生子。事务繁忙、经济压力、对婚姻的不确定等个人生活的种种不幸让作者曾“祈求上帝让我经历一次大悲痛,能使得我的存在更加圆满,赋予我的生命更多意义”[5]11。生活的不幸经历是作者在诗歌中出现陌生人的直接原因,他幻想那个陌生人能带他走出世俗生活的困扰,从而赋予生命更多的意义。然而,上帝显然不能拯救人类,因此,相比于对宗教的信仰,易卜生更愿意将人物的选择建立在宗教之上进而剖析复杂的人性,从而才有了易卜生对宗教中上帝的怀疑,以及兼具内心力量和上帝力量的 “陌生人”的存在。
比约恩·海默尔认为,易卜生对宗教生活本身敬而远之,他总是把人放在中心位置,不是简单化地将他从属于自我之外或自我之上的权利[1]50。通过“陌生人”角色的塑造,他成功的将个人的自由置于上帝的目光中,强调了个人自由及独立人格的重要性。易卜生曾经说过“陌生人”的不确定性是他故意选择的创作方法中的本质要素,不应该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不必知道他是谁[5]288。因为“陌生人”与上帝之间无法切断的关系,这一形象的塑造,凝结着易卜生在面临社会问题时对宗教的深刻认识。李志艳认为易卜生宗教的倾向“不是圣徒式的墨守成规,而是民族精神经过宗教洗礼之后的新发展”[6]57。汪余礼认为在易卜生的早期和晚期的艺术创作中,“他身上似乎有着基督耶稣的影子,或者说他心中一种有着自己的上帝;而来自那个上帝的目光,使他既志存高远,又严于自审自律”[7]15。在现实生活中,易卜生发现上帝不能解决社会中的诸多问题,不能拯救人类的灵魂,只有加入个体的意志才能找到自由的出路。因此,在诗中他创造了一个高于世俗的上帝,以“陌生人”为具体形态。在这个形象身上,体现了易卜生的内心意志与自我力量,同时也体现了他对于上帝的信仰,寄托了他对于宗教的认识。长诗中的“年轻人”无疑是现实生活中的易卜生本人,他的种种困境也就是易卜生所面临的困境,他的内心矛盾也就是易卜生的内心矛盾,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创作这首长诗时易卜生本人的影子。从长诗中的故事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年轻人”只是凭自己的力量无法实现人生的目标,特别是“在高处”的精神超越与生命寻求,因此他只得借助于上帝的力量,而“陌生人”正是上帝的代表,当然是诗人自己所理解的、所迷信的上帝。诗人正是通过“年轻人”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种“自我”与“上帝”、“自我”与“他者”、“外在世界”与“内在自我”之间的张力结构,抒写了年轻人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也表现了长诗独到、深刻与繁复的思想主题。如何理解“陌生人”形象的内涵与价值,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这首长诗的主题与易卜生当时的思想,也直接关系到易卜生创作这首长诗的原因与目的。通过反复阅读与细致分析,我们认为“陌生人”并不是上帝本身,也不纯粹是诗人自我精神的一种投射,而是自我与上帝、自我与他者、自我与世界相遇而产生的一种精神复合体。由此,“陌生人”正是自我意志和上帝力量的统一,他永恒存在并且全知全能,“年轻人”最终在他的帮助下,走向地势和精神的高处,找到了心中的自由和上帝。
[1]比约恩·海默尔.易卜生——艺术家之路[M].石琴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2]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八卷[M].绿原,卢永,贺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
[3]约翰·弥尔顿.失乐园[M].朱维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4]阿尔文·普兰丁格.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M].邢滔滔,徐向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易卜生.易卜生书信演讲集[M].汪余礼,戴丹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6]李志艳.易卜生诗歌的人文情怀[G]//王远年,主编.易卜生诗歌研究.香港:雅苑出版公司,2006.
[7]汪余礼.译者前言[M]//易卜生.易卜生书信演讲集.汪余礼,戴丹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Unity of Personal Will and God’s Power: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Stranger” in
PAN Dan-dan
(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Engineering,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41, China)
The “stranger” in Ibsen’s long poem, is a messenger of God, who changes from the invisible “light” in nature to the figure of a “stranger” as a young man’s contradiction intensified. The “young man” believes in the stranger’s guide, so he can overcome emotional suffering and become determined to live in the highlands. While what the “stranger” leads the “youth” to find is the God in the young man’s inner heart. In nature, the “stranger” is the unity of young man’s will and God’s power, holy, eternal and omniscient, so he can save the “young man” from agony. The “stranger”, a mysterious figure created deliberately by the author Ibsen, represents hi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igion when he confronts many social issues.
the “stranger”; the “young man”; self; God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7.05.18
I533.2
A
1004-4310(2017)05-0095-05
2017-06-17
2016年安徽省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易卜生后期戏剧中人地关系研究”(SK2016A0710)。
潘丹丹,女,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