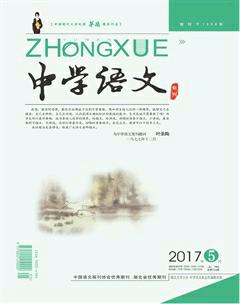语文:言语生命的赋形
苑青松
语文规律是语文课程科学化建设的根本,语文课程批判和争鸣的现实生态表明,对语文规律的认知需要新的框架,本文试图以新的范式对语文规律作出探索。
一、范式转换:“波拉德”田野文本在语文规律阐释上的尝试
从语文课程发展的历程来看,科学范式构成着语文的研究生态,然而,语文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文化只能被描述而无法被证明的特质决定着语文研究范式的必然转换,语文规律也才可能被真正获取,石门坎个案选用正是语文研究范式转换的结果。
石门坎隶属于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县,是以苗族为主的苗、汉、彝等多民族聚居地。1905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来到这里传教办学并取得了辉煌成就,由此,石门坎教育个案被称为“波拉德”教育。为了展示其典型性,本研究把石门坎的要素以存量和变量的形式呈现出来,存量要素指石门坎的面积、位置、地貌、人口、历史等,反映地是石门坎田野文本的静态性指标,它是石门坎场域运动变化的基点,分别用Q1、Q2、Q3、Q4……Qn来表示,具体类型如下表:
变量要素反映的是石门坎存量的动態性指标,分别用V1、V2、V3、V4……Vn来表示,具体类型如下表:
从存量要素信息表上可以看出,当时石门坎苗族生活在“三零”平台上,土司压榨、巫师控制、生活力低下、整体文盲、自然封闭等是石门坎苗族的生存概况,正如石门坎苗族溯源碑所言:“天荒未破,畴咨冒棘披荆,古径云封,逞恤残山剩水。访桃源于世外,四千年莫与问津。”①
经过四五十年的努力,柏格理及其同事在“三零”平台上创造出了惊人的成就——苗文创制、学校创办、三语教学开展、社会机构建立、全民读书实现等,石门坎由一个偏僻封闭的小山村一举成为“西南边疆最高文化区”,实现了苗族文化的复兴并成为西南边疆近代教育史上的典型个案。正如柏格理墓志铭所写:“一片荒地,极端经营,竞至崇牖栉比,差别有天地。”②
三语教学、苗文创制、全民读书是“波拉德”教育最具特色的内容,其中必然地蕴含着对母语规律的遵循,对此,我们可以作出基本的预判——这在揭示语文规律上充满着价值。
二、言语赋形:新研究范式下语文规律表达
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框架去观照问题,就可能产生创造性结果。在此观念下,本研究从田野文本和哲学分析两个维度来审视语文的规律。
(一)田野文本下的语文规律呈现
石门坎“波拉德”语言教育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创造了辉煌成就,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既基本扫除了文盲,又培养出了2名博士生、30多名本科生和5000多名高中生;二是构建了新的社会组织体系,相继成立了孤儿院、农业技术推广站、电报代办站、医院、学校等五大社会机构,极大地提高了当地社会的组织水平;三是激活了石门坎苗族的精神生命,在“波拉德”教育的引领下,石门坎苗族的精神状态迅速从沉醉麻木走向清醒振作,他们的心灵世界也迅速实现了由万物有灵的蒙昧状态到知识追求的科学理性转向。
石门坎的成就声名远扬,当时在海外寄信只要写上“中国石门坎”就能收到,国内三大政治领袖(蒋介石、邓小平、胡锦涛)对石门坎或亲历或熟知,柏格理本人也被西方称为“五大圣人”之一。
“波拉德”教育成就达到了享誉海外的高度,而这一高度是以语言教育为基础达成的,这恰是本研究的关键所在并必然地成为关注点,就语言教育来看,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石门坎苗族表现出狂欢式的语言学习情感。柏格理日记对此有着细腻地描述:
“在厨房里,在餐厅,在书房,在起居室,在客厅,在教堂,在学校教室,在院落,在马厩里,在台阶上,早晨、中午和晚上,他们无处不在!”
“有些天他们以十几个、二十几个人一伙来到!又有几天是六十多个或七十多个!随之来了一百人!二百人!三百人!四百人!最后,说来也凑巧,在一天之中竟有一千名山里的苗族汉子到来!”
“远近的苗民都各自背自己的包谷——食粮,及行李,来参加识字、读书会,读书的人数不一,有的头痛齿落,有的龙钟潦倒,有的血气方刚,这其间有多少是父子共读,但集合在一块儿读书,绝没有父子老少之分。”③
当然还有很多关于读书的田野故事,诸如“赌命与读书”“识字的文盲”“自杀的青年”“太初有道”“采集亮篙读书的青年”等都呈现出语言学习的狂欢性质。
这是一种难以解释清楚的奇怪现象,没有人能够为它作出计划或组织,再或以最奔放的思想设想出来。
其次,“波拉德”文字的创制,使苗族人真正走进了新世界的入口。最初,柏格理及其同事以汉文为教学内容,结果难度极大,“一个人要学会汉语,要有铜铸的身体,铁铸的肺,橡木脑袋,苍鹰的眼,要有圣徒的心灵,天使的记忆,麦修拉的长寿。”④汉字难学难记的问题很快使他们意识到,如不创制出适合苗族人的文字来,他们的学习热情将很快消失殆尽,这决定着柏格理事业的成败,“波拉德”文字的创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波拉德”文字在创制上表现出多元组合的特点:一是创制人员的组合,即汉族知识分子、苗族知识分子和西方传教士的三元组合;二是“波拉德”文字本身也呈现出多元组合的式样,它是由大字母、小字母和音调组成,大字母是文字字形的主体,其形状取自于苗族人的生活元素,小字母取自于英文的拉丁字母,声调借用汉语的四声。三是“波拉德”文字的世界性和本土性,“波拉德”文字的创制一方面反映出儒、苗、基督三种文化融合的观念,另一方面内隐着民族、国家、世界三个维度走向的意识。新文字的创制使苗族人的神性记忆成为现实,他们奔走呼号、到处传唱“蚩尤佬的文字”又找到了,苗族知识分子朱焕章编制了《西南边疆苗文课本》,它被喻为苗族人的“圣经”,几乎人手一册地充斥在田间、地头、家庭、学校、集市、教堂等,整个石门坎都成了读书识字的场所,“柏格理因提供了能代表苗语发音的语言学符号,加上修改过的用于手写的字母体系而使问题得以解决。这种文字体系后来被称为波拉德文字而闻名,因为它对于苗族人既简便又易学,他们为拥有一套可以称之为自己的、根据他们的语言产生的文字结构而变得自豪起来。”⑤苗文体现出巨大的“引力”作用并成为族群认同和愿景实现的主要工具。
这使石门坎苗族真正走进了新世界的入口。
最后,“三语教学”的开创,使他们不断创造着新的世界。 “波拉德”教育于1905年开展“三语教学”首开国内三语教学之先河。石门坎的博士生、本科生、高中生正是在三语教学的基础上培养出来的。据笔者调研发现,现在90多岁的老人还能听英语广播、讲英语。我们不禁会问:石门坎的“三语教学”为什么会取得如此成就呢?而今天的双语教学,无论师资水平、教学设备、教材质量和学生基础都要远远好于当年石门坎的条件,为什么结果却大相径庭呢?从整体考察,石门坎“三语教学”的价值不仅解决了苗族人教学层面的技术问题,更是激发了他们向主流文化迈进的精神想象。因此,石门坎苗族人在精神和技术的互为下取得了惊人成就,如果忽略精神想象而单从专业技术上考察“波拉德”三语教学问题,永远无法真正理解它的特质。
“波拉德”教育中的语言学习不单单是技术性工具的掌握,而是以语言为凭借的生命奋进和关系贯通的人本质体现。
(二)哲学观照下的语文规律认定
语言价值在“波拉德”教育中的显现,是符合语言哲学传统的,人不可能脱离环境而存在,而是必然地存在于某种环境中,二者之间存在着特定逻辑上的互动关系。人与环境在长期的互动中必然产生生命经验,生命经验是主客观统一的隱性存在,生命经验的被表达是人作为生命本能的、内隐的存在性表现,而要想使隐性的生命经验得到表达,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媒介物为其赋形。赋形是指为了呈现某种复杂关系、无形思维、内隐情感而赋于其相应的形态,从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或传承生命经验的目的。
语言是表达思想观念最具表达力的赋形物,人是通过言说而体现出语言性,“人的生命本能中有着天然的言语欲求和言语天赋。”⑥人的生命本质是如何表现为语言性的呢?维特根斯坦从语言和世界逻辑边界的同一性阐释了语言的本质,人是在语言贯通世界过程中而得以存在的;海德格尔从人与语言的居有关系上探寻语言的本质,阐释了人在倾听和应和语言中走向人本质。维氏和海氏虽对语言本体的论述有所差异,但在说明人的本质存在上表现出一致性,即言语生命是人的本质。言语生命的人本质,决定着人生命经验的表达赋形物必然地成为语言,言语生命是标示生命处在言说之中而存在,相对于个体的人而言,言说是永不停滞的,言说的停滞喻示着人生命本质的消失,处在言说状态下的语言肉身及其表达形态即是语文。
具体可从两个层次来理解:一是语言肉身是为着表达而存在的,语言肉身只是言语表达形式的材料而已,脱离表达的语言肉身没有意义,因此,语言肉身是语文的重要内容但不是本质性内容。二是语言肉身和言语表达形式的运用是为着人的本质存在而开展的,即言语形式的学习是人用以实现自己生命奋进和关系贯通的本质存在而进行的。郑也夫先生对此有一个恰如其分的比喻:“‘戏词可以突出地反映其特征,你要在社会的舞台上演戏,就要学‘戏词。戏词是微妙的,是博弈的过程和产物,是特定时空与人格的函数。”⑦两个层次的内涵都标示着言说形式是语文的特质,第一层次是形而下的言语技术具体运用,第二层次是形而上的人本质的终极体现。
语文定义呈现出关系性、言语性和形式性内涵,关系性标明了语文存在是什么的问题,这彰显了语文课程的形而上主题;言语性标明的是语文的存在用什么表达的问题;形式性标明的是语文存在如何表达的问题;语文内涵的关系性和形式性是言语的关系性和言语的形式性,言语形式的训练理应成为语文教学的主体。
据此,言语生命的赋形指人在与世界的互动中生成的生命经验必然地以言语的形态来赋形。
其内涵具体呈现为:人与自然的互动必然产生生命经验,而生命经验是广泛的、复杂的,它包括自然的、情感的、劳作的、信仰的、思维的等等,人作为言说性动物必然本能地以言语形态来为生命经验赋形。因此,语文的特质表现出语感和形式的特征。
三、三层贯通:基于语文规律的教学框架设定
语文是人对生命经验化了的生活形态进行的言语性表达,表现出形式本质,其形式物是以语言为主体,以声音、图画等为辅助构成的,它们综合性的表达出人对世界经验的言说,表现出符号的多重化特征,即线条(或字母)是声音的符号,声音是心灵体验的符号,心灵体验是事物的符号。
语文规律的认定为语文教学标示出基本路径成为可能,具体呈现为两种机制:一是学生如何通过语篇读出文字背后的意义和活生生的现实,其目的在于形式的学习,其机制为:
文本——文意——义理——理据
二是学生如何利用习得把自己活生生的现实用文本赋形出来,其目的在于形式的运用,其机制为:
事物——义理——文意——文本。
语文教学的重点是学生对形式表达的掌握,那么,语文教学的过程就是对多重符号的层次转换,正如朱熹所说:“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⑧
在言语生命赋形观念下,语文课型框架可以设定为四重赋形的转换,具体呈现为:
第一层转换:线条(或字母)是声音的符号——由文字到声音。
第二层转换:声音是心灵体验的符号——由声音到生命经验。
第三层转换:心灵体验是事物的符号——由生命经验到赋形物。
第四层转换:赋形物是文字的符号——赋形物到文字表达
言语生命赋形的语文观旨在说明人的本质呈现样式,力争在丰腴生命与经典文本之间实现贯通,这为语文学科未来发展型模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本文系2014年度全国民族教育项目“民族教育育人规律研究:以少数民族预科生为例”(项目批准号:MJZXWT1406)研究成果]
————————
参考文献
①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②沈红:《石门坎文化百年兴衰》,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5页。
③塞缪尔·柏格理:《未知的中国》,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页。
④周宁:《人间草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9页。
⑤William H. Hudspeth,东人达译:《 Stone-Gateway and the Flowery Miao》,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409页。
⑥潘新和:《语文:表现与存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⑦郑也夫:《吾国教育病理》,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页。
⑧黎靖德:《朱子语录类》,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62页。
[作者通联:河南周口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