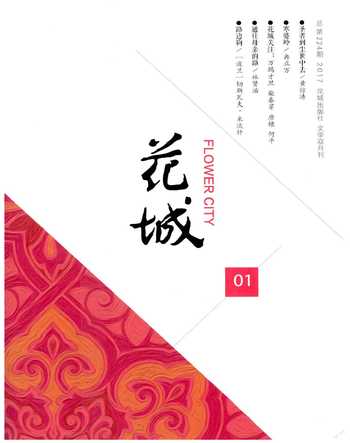一个报信人,来自中国文学现场
何平
现在这个“开栏的话”是一个修改过的文本。和原来的文本相比,我检讨并滤去了俨然真理在握的肯定和专断。自以为真理在握容易让人滋生自大、盲视和陋见,进而丧失基本判断力。比如对中国当下文学生态,从某一些局部观察,确实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种不尽如人意的观感是不是也囿于各自预设的位置、立场和见识呢?作为一个批评家,难免会对当下中国文学下各种各样的判断,但往往是我们下的那些判断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全称”的中国当下文学说话?我们对“全称”的中国文学知道多少?甚至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学”这个概念,是不是也要放在今天的文学写作现实中加以涤新和再造呢?20世纪末到现在,中国文学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现在还不能作充分的衡量,而且变化还是未完成时。不过,经过近二十年网络新媒体的洗礼,全民写作已经是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文学”事实。大众分封着曾经被少数文学中人垄断的文学领地,那些我们曾经以为不是文学,或者只是等级和格调都不高的大众文学毫不自弃地在普通读者中扎根和壮大,进而倒逼专业读者正视、承认和命名,文学的边界一再被拓展;与此同时,一些更为极端更小众的文学实验却也顽强地在小范围的圈子里被少数人实践、传播和欣赏。不仅如此,“文学”弥散为和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学性”。是的,離开了“文学性”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几乎难以被充分建构起来。我们已经习惯我们的生活是“文学性”的,虽然许多时候这些“文学性”被冠以“鸡汤”“轻抒情”“小而美”“文青”等名词来调侃和嘲讽。
关于中国当下文学,正在发生什么?写作者在写什么?什么是我们时代的“新”文学?如此等等,文学期刊和专业读者应该是一个来自现场的可靠的“报信人”。现在中国活着的文学期刊,几百家还是有的吧?虽然几乎没有一家文学期刊自我感觉活得风生水起的痛快淋漓。文学期刊动辄几十万份的“80年代”盛景也可能永远是白发宫女说前朝旧事了。但活着还是活着,纸媒的日子不好过,死掉的也是那些走市场的报刊们,文学刊物都按期在出在发,平庸虽然平庸,读者少也就少了,总有一帮层出不穷的写作者维持着,也总会偶然有人冒出头,激起文学界,至多也只是在文学界的一点小浪花。而且,大家现在似乎也熬过了20世纪末文学期刊的寒冬。何其幸运,没有要抱团取暖,大家就活下来了。至今,还有多少人记得当时甚至喊过“必须保卫文学期刊”那么悲壮苍凉的口号呢?
事实上,那个90年代中后期的世纪末时代,是文学期刊的危机时代,也是一个锐意进取的时代,是一个文學的好时代。一个好刊物是一个有着自己传统的刊物,这几百家刊物里,《花城》为什么是《花城》?大概一年前,我和朱燕玲主编商量着做一个栏目,起点就是什么可以是《花城》做的?按照期刊惯例,我们当时也想从年轻作者做起。这不只是一个生理年龄新陈代谢的问题,而是人类文明传承的常识,也是文学更替的常识,所谓在进化的链条上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是“中间物”。无论前代作家多么有创造的活力和勇气,他们终将衰老和退场,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记忆。“新”文学和“新”的文学时代最终还是要移交到“新”人手里。既然“发现文学新生力量”从来以为是文学期刊可以提振士气的良药,我们也可以做,哪怕换个花样做。于是,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动用各种资源,让大家推荐年轻作者。这个时代还真不缺少年轻的写作者。
客观地说,“80后”“90后”,甚至更年轻的千禧年之后出生的写作者,写得并不坏。他们出生和成长在“中国回到世界之中”的时代,他们几乎都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他们也不存在前辈作家文学学徒期的文化荒芜和阅读匮乏,他们从一开始就在世界文学中阅读和写作,但在一个“文学”富足到过剩和平庸的时代,成熟,甚至过于成熟的文学起点,“同质化”的文学趣味,对更具异质性和个人化的文学探险是有所伤害的。而且,仅仅依赖成长经验,时代赋予他们的本来就是琐碎。所以,郭敬明写《小时代》,香港闻人悦阅写《小寂寞》,最近的电视剧干脆也叫《小别离》。事实上,“小”在今天不单单属于年轻作者,或许“小”本来就是我们时代的文学气质。但每个时代还是应该容忍捣蛋的文学坏小孩,只是对今天的年轻作者,做一个坏小孩难度更大。想象中,应该更多一些年轻人不计得失的冒犯和反叛,而不只是谨守文学惯例,因循文学既有秩序,或者沉湎一种彼此接近的同人式写作时风。
除了年轻作者的各种写作尝试,我们的栏目还想做得更多些。《花城》是改革时代的产物。翻开那时的《花城》,你哪怕只看栏目——外国文学、香港通讯、海外风信、电影文学、流派鉴赏——也能够感觉到蓬勃着的气息和气象。这是一个刊物的传统,《花城》从一开始就不只是感触和捕捉中国文学最前沿的信息,而是与世界同时刻的文学站在一起。今天的《花城》也应该是这样的。你可以说,《花城》创刊之时,身处南国,居改革开放的前沿,得风气之先。我们再看20世纪90年代之后呢?现在文学界有一种观点,大致是说1980年代末先锋文学被粗暴地终止。如果我们读完那之后全部的《花城》,我们还会下这个判断吗?正是从那一刻开始,《花城》几乎聚集了中国最先锋最具有探索精神的一批作家和文本,如果不只把先锋理解成是形式主义的炫技。当然,《花城》并不排斥炫技,甚至有专门的栏目“实验文本”鼓励出轨越界的炫技,但《花城》的先锋不仅仅是形式主义的炫技,而是充盈着探索文学在我们时代“可能”抵达边界的精神气质。这种“可能性”在1990年代的《花城》,可以是王小波,可以是毕飞宇,可以是阎连科,可以是林白、陈染,可以是北村、吕新,可以是残雪,可以是崔子恩,可以是李洱,可以是朱文、鲁羊,可以是“新小说”“花城出发”的年轻作者,可以是已经被经典化的王蒙、张承志,等等。不以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划界,不温吞,不妥协,不察言观色,进取,铺张,飞扬,自由。
这是我想象《花城》的开放性和可能性,众声喧哗,杂花生树,也是我们想象的“花城关注”栏目未来的样子。“花城关注”该给中国文学做点什么呢?今天的文学形势,只要不是妄想症,就不会自以为是地臆想自己可以创造出一个轰轰烈烈的文学时代。那就做点自己能做的事,就做点《花城》一直在做的事情吧,哪怕只是尽可能地打开当下中国文学的写作现场,尽可能看到单数的独立的写作者在做什么,哪怕只是敞开和澄明一点。我们置身的现实世界,不说最好和最坏的,确实是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从不同的路径和时代遭遇,被伤害,也可能被成就。作为写作者,理所应当贡献的应该是不同的现实感受、不同的文学经验、想象和不同的文学形式,我们的栏目就是要让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一起浮出地表。
北京回南京的旅途上,读到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的《策展简史》。2006年,他采访费城美术馆馆长安妮·达农库尔时,用“策展人是过街天桥”的说法问安妮·达农库尔“如何界定策展人的角色”?安妮·达农库尔认为:“策展人应该是艺术和公众之间的联络员。当然,很多艺术家自己就是联络员,特别是现在,艺术家不需要或者不想要策展人,更愿意与公众直接交流。在我看来,这很好。我把策展人当做促成者。你也可以说,策展人对艺术痴迷,也愿意与他人分享这种痴迷。不过,他们得时刻警惕,避免将自己的观感和见解施加到别人身上。这很难做到,因为你只能是你自己,只能用自己的双眼观看艺术。简而言之,策展人就是帮助公众走近艺术,体验艺术的乐趣,感受艺术的力量、艺术的颠覆以及其他的事。”和艺术一样,当下中国,写作者和读者公众的交流已经不完全依赖传统的文学期刊这个中介。类似豆瓣、简书这样基于实现个人写作的网站、博客微博、微信公号、独立出版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学印刷品等挑战的不只是传统的文学期刊,甚至包括“起点”“晋江”这样的大型网文平台。其实,每一种文学发布行为、媒介和途径都类似一种“策展”。策展人只是一种选择,读者也只是选择。因此,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栏目理解成一次文学策展呢?那如何“避免将自己的观感和见解施加到别人身上”?或许,我们只是诚实地做一个文学现场的漫游者和观看者,一个“报信人”。我们当然有我们的观感和见解,但在我们没有把握已经充分打开文学现场之前,观感和见解还是隐微、协商和谨慎一些好。
责任编辑 李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