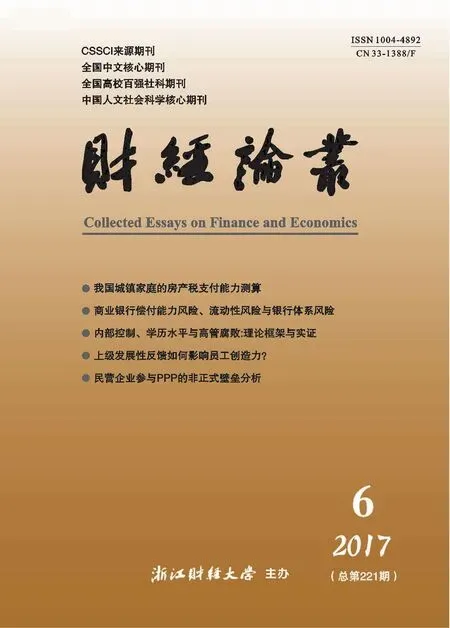上级发展性反馈如何影响员工创造力?
——一个被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
王智宁,高 放,叶新凤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上级发展性反馈如何影响员工创造力?
——一个被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
王智宁,高 放,叶新凤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在积极赋能、激活个体的组织情境下,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机制有待明确。突破被动适应视角局限,本文基于创造力领导理论与个体成长整合模型,对上级发展性反馈、工作旺盛感、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影响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通过对384位企业全职员工的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工作旺盛感与员工创造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对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员工工作旺盛感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工作旺盛感对员工创造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旺盛感在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员工创造力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隐性知识共享与上级发展性反馈的互补性调节作用会通过工作旺盛感进一步影响员工创造力。
上级发展性反馈;工作旺盛感;隐性知识共享;员工创造力
一、引 言
在我国“转型升级”、“创新驱动”、“中国智造”的发展背景下,创新逐渐成为组织获取和维系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作为组织创新的理念源泉与核心要素,员工创造力为创新目标达成提供新颖实用的思路、理念或想法,对摆脱思维桎梏、突破工作局限、解决关键问题意义重大[1]。因此,员工创造力研究引起学界持续关注,并主要从六个方面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2]:个体因素,包括个体特质、内部动机、知识、认知能力与风格、情绪、行为等;工作任务,包括工作复杂性、工作压力、工作资源、工作奖励等;领导特征,包括领导风格、监管行为、交换关系等;团队属性,包括团队认知、知识异质性、团队目标、团队认同等;组织氛围,包括组织支持、组织公平、组织文化等;社会网络,包括网络强度、网络效率、网络位置等。其中,后五个方面又可以归纳为情境因素。作为工作场所的重要情境因素,领导特征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近年来倍受重视,并逐步发展出创造力领导理论[3][4][5]。其主要观点认为,不同的领导方式与行为会对员工创造力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领导的鼓励与支持,如变革型、授权型等领导风格,对员工提供信息传输、言语鼓励、技术指导,以及进行创新性行为示范等有助于提升员工的创造力[4][5][6];反之,敌意与权力的滥用,如权威型领导风格、对员工密切监视、实施辱虐管理等会破坏员工的创造力[3][7][8]。作为领导鼓励与支持的重要内容,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机制亦成为研究热点[9][7],并主要从下属情境调节焦点[10]、领导—成员交换关系[9]等角度提炼出可能存在的中介变量。然而,既有中介视角具有明显的被动适应特征,并未回答“在上级发展性反馈影响员工创造力的过程中,员工自身的主动性与进取因素是否以及如何发挥中介作用”的重要问题。
基于创造力领导理论与个体成长整合模型,本文提出,工作旺盛感在上级发展性反馈影响员工创造力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并且,依据非冗余信息互补原则,本文认为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对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工作旺盛感的关系产生调节作用。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提出并验证了上级发展性反馈—工作旺盛感—员工创造力理论模型,从主动性与进取因素视角明确了工作旺盛感的中介作用,提出上级发展性反馈影响员工创造力的新路径,为创造力领导理论补充新内容;第二,发现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在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工作旺盛感之间的正向互补性调节作用,为上级发展性反馈影响工作旺盛感的作用机制提供情境化理论成果;第三,发现隐性知识共享与上级发展性反馈的互补性调节作用,会通过工作旺盛感进一步影响员工创造力,深化对上级发展性反馈—工作旺盛感—员工创造力作用机制的理解。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个体成长整合模型与工作旺盛感
个体成长整合模型[11]认为,个体在工作中所展现出的成长,如绩效、积极性、适应性与健康,受到个体可塑性工作状态——工作旺盛感的影响,并且工作旺盛感取决于嵌入工作中的情境因素,如决策权、信息共享、信任/尊重的氛围、反馈等。其中,工作旺盛感可以定义为有关活力与学习的联合主观感受,其反映了员工在工作中的心理情况[12]。与性格等相对稳定的个体特质相比,工作旺盛感属于相对易变的个体状态,是衡量员工在工作中心理成长的重要依据,在工作中的任何阶段都有不同的强弱程度。工作旺盛感以积极主动的视角评估员工的工作感受,其会随着工作阶段的转换、时间的推移和任务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具有很高的情境嵌入性。工作旺盛感由活力和学习因素构成,二者缺一不可。其中,活力指能量充沛,对工作饱含热情的感觉,是个体成长中的情感状态;学习指个体获取/应用知识和进取的感受,是个体成长中的认知状态。学习有余但活力不足,会造成个体身心疲惫甚至精疲力竭;活力有余但学习不足,则会使个体停滞不前[11]。
(二)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工作旺盛感、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上级发展性反馈指上级向员工提供的有助于其在工作中学习、发展和提升的信息反馈[7],属于个体成长整合模型中绩效反馈的范畴[11],而绩效反馈是工作旺盛感的重要前置变量,因此上级发展性反馈会提升员工的工作旺盛感。具体而言,上级发展性反馈属于促进型信息反馈,提供有助于员工学习和发展的信息,给予员工心理自由和情绪激活的体验,能有效提升其活力与学习的感受。并且,上级发展性反馈提供了有关当前工作进度、绩效目标以及专业知识要求等方面的关键信息,有助于消除员工在工作中的不确定感,使员工更为精确地评估自己,看到自身问题及潜在的改进方向,激发工作热情并带来成长进步的预期[13]。此外,由于主动方是领导,上级发展性反馈能避免员工在面临困难时寻求帮助所伴生的紧张与焦虑感,上级在反馈过程中的言语鼓励和情感关怀能拉进领导与员工的关系,促进二者之间有效互动,增强信任与归属感,提高员工的工作与学习热情。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工作旺盛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创造力指员工为达成任务目标而提出的新颖且实用的观点、思路或想法[14]。依据创造力领导理论,领导的鼓励与支持有助于提升员工创造力[4][5]。作为积极的领导特征与行为,上级发展性反馈包含着大量有助于员工学习和成长的信息,能有效提升员工的能力与素质,为创造力的实现提供知识基础[4]。其次,上级发展性反馈所提供的积极信息使个体更为精准地理解自身工作情况,促进内在的自我决定感、胜任感与内部动机水平,进而催生创造力。Zhou[15]的研究表明,当个体接收的反馈是信息型的,且在高水平工作自由度情境下,其产生的创造力水平最高;Shalley等[16]的研究也证实,与控制型预期评估相比,信息型预期评估能使个体产生更高水平的内在激励和创造力。再次,上级发展性反馈属于上级对员工的鼓励与支持,根据Madjar[6]的研究结论,上级与员工讨论工作问题、回应新颖想法等支持行为,有助于员工积极情绪及创造力的提升。此外,上级发展性反馈在提供学习和发展信息的同时不苛求短期回报,有助于营造轻松良好的组织氛围,缓解工作压力,有益于员工多样性思维的培养和创造力的提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员工创造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对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工作旺盛感关系的调节作用
隐性知识指个体拥有的难以编码和清晰表达的知识,其不仅涉及通过亲身实践所得到的不易言传的经验、见解、诀窍,还包含个体的信念、价值观、心智模式等重要因素[17][13]。隐性知识共享则是为了高效完成工作或创造性的解决问题,在不同主体之间发生的隐性知识交换与转化等活动[13]。由于隐性知识具有难以评估、识别、沟通和表达等特征[18],其共享需要主体之间的密切互动才能实现。而在员工的工作情境中,同事之间处于相同的组织层级和部门,关系较为密切、互动相对频繁,更容易进行隐性知识共享。对于员工而言,上级和同事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关系。员工与上级主要是一种垂直和正式的关系,而与同事主要是一种水平和非正式的关系。上级更多传递有关工作过程、结果以及发展建议等方面的显性知识,同事更多传递涉及经验、教训、感悟、诀窍等方面的隐性知识。
依据非冗余信息互补原则,员工从不同渠道获取的非冗余性信息有助于其工作旺盛感水平的提升[19]。首先,在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水平较高的情况下,上级发展性反馈向员工所传递的有关学习、提高、成长与发展的显性知识,能够与同事分享的经验、体会、感受等隐性知识相互补充,通过反思、印证与吸收等过程,被员工认可与应用[20]。员工对经过融合、比较与选择,有助于其工作进步的上级发展性反馈更有信心,强化其对领导鼓励与支持的认知,在应对各种工作挑战时保持乐观预期和活力,并在积极、正面的工作中感受到自我成长与进步[13]。在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上级发展性反馈向员工所传递的信息,无法得到来自同事隐性知识的足够印证,员工在困难出现时难免产生自我怀疑,使工作旺盛感的提升效果有所折扣。其次,上级发展性反馈所提供的信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所涉及的内容更具全面性,在其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能够凸显上级发展性反馈对于员工工作的意义与价值[7],增强个体的活力与学习感受。此外,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能够促进员工之间的密切互动,使员工融入组织,增强归属感,正面、积极的理解上级发展性反馈[19],进而提升其工作旺盛感。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在上级发展性反馈和员工工作旺盛感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四)工作旺盛感的中介作用
作为反映个体创新性的变量,创造力无疑属于个体在工作中所展现出的成长因素范畴,依据个体成长整合模型,其会受到工作旺盛感的影响[11]。具体而言,个体通过学习行为获取专业知识是创造力产生的基础条件[21]。当员工在工作中感受到学习和成长时,意味着专业知识的获取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进而有更多的机会发现新的问题并打破现状、尝试新的工作方式方法,保证创新持续性[22]。并且,当员工在工作中感受到活力时,通常伴随着一种积极的体验,能够扩展员工的注意力和认知元素的范围,提高个体反应的灵活性,进而使产生创意所必须的变化和联系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创造性活动的本质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工作行为,需要员工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寻求、发展、拥护新的理念或想法,尤其是在面对墨守成规者的怀疑和阻力时,主动性与进取性显得极其重要。积极的体验能够提升个体参与创造性工作的主动性,并超越常规角色和责任进行创造性思考,进而承担特定的创造性任务或表现出特定的创新性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工作旺盛感对员工创造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作为近年来提出的组织行为学新构念,工作旺盛感的相关研究目前以概念探讨与理论构建为主,涉及的前因变量包括自由裁量权、信息共享、主管支持和信息反馈、信任和尊重等,涉及的结果变量包括组织忠诚度、职业倦怠、工作满意度、组织公民行为、工作绩效、创新行为等[23][12]。依据个体成长整合模型[11],工作旺盛感会受到嵌入工作情境的重要因素——上级发展性反馈的直接作用,又对员工的成长性指标——创造力产生影响,因此,工作旺盛感会在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并且,基于前文的分析,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调节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工作旺盛感的关系,而工作旺盛感又对员工创造力产生正向影响,故而上级发展性反馈、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工作旺盛感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形成一个被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详见图1。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工作旺盛感在上级发展性反馈影响员工创造力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H6:在影响员工创造力的过程中,工作旺盛感中介了隐性知识共享的调节作用。

图1 研究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采集
本研究以企业全职员工为调查对象,为控制同源误差,采用纵向调查设计。第一次采集上级发展性反馈、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与主要控制变量数据,第二次采集工作旺盛感与员工创造力的数据,间隔期为两周以上。数据搜集主要通过三种方式:(1)课题组直接进入企业现场发放与回收;(2)课题组委托合作企业负责人现场发放与回收;(3)通过电子邮件发放与回收。共发放初始问卷1000份,得到有效问卷38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38.4%。有效样本分别来自制造、建筑、通讯、批发零售、教育等行业,涵盖生产、销售、市场、客服、人力资源、财务、技术研发等不同性质的工作岗位。就有效样本的构成而言,男性受访者占52.3%;年龄在40岁以下的人员占比89.8%;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的占比为76.8%;79.7%的人员具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30.7%的受访者为普通员工,69.3%的受访者为不同层级的管理人员。
(二)问卷设计与测量工具
对于上级发展性反馈,初始测量量表来自Zhou(2003)[7]的研究,结合李磊[9]有关领导反馈风格的描述,包括5个题项;对于工作旺盛感,初始测量量表来自Porath等(2012)[24]的研究,包括10个题项;对于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初始测量量表来自我们的前期研究[17],包括7个题项;对于员工创造力,初始测量量表来自Farmer等(2003)[25]的研究,包括4个题项。在将量表翻译为中文的过程中,我们与本领域的2名教授与3名博士生多次讨论,并依据便利性原则,将初始问卷发放给102名企业员工进行小规模前测,根据前测结果对量表进行修订,形成正式量表。其中,上级发展性反馈、工作旺盛感、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与员工创造力的测量题项个数分别为4、10、4、4,对应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5、0.91、0.82与0.89。除了受访对象基本信息,正式调查问卷的问题均采用李克特7点式量表进行测量。
(三)同源误差分析
采用Harman单因子测试,将所有题项放在一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未旋转),共析出5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解释方差的68.22%,其中,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15.31%,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同源误差问题。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在表1中,员工创造力与上级发展性反馈、工作旺盛感、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

表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注:** 表示P<0.01,* 表示P<0.05(双尾)。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运用MPLUS7.4软件,将上级发展性反馈、工作旺盛感、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和员工创造力放在一起做四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χ2/df=3.20,RMSEA=0.076,CFI=0.91,TLI=0.90),并据此分析聚敛效度与区辨效度。聚敛效度指同一潜变量所对应不同题项测量结果的相似程度,一般采用标准化因子载荷、平均变异萃取量(AVE)和组合信度(CR)来衡量。依据表2,各潜变量所对应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超过0.5的阈值,据此计算的AVE均超过0.5的阈值,CR均超过0.7的阈值,反映各潜变量的聚敛效度理想,具有良好的操作性定义。
区辨效度指不同潜变量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程度。本文采用AVE与相关系数平方比较法判别潜变量之间的区辨效度,结果如表3所示,对角线元素代表潜变量的AVE,非对角线元素代表对应潜变量相关系数的平方,由于任何两个潜变量AVE的均值均大于其相关系数的平方,因此潜变量间具有理想的区辨效度。

表2 测量模型的聚敛效度
注:“R”表示反向计分题。

表3 潜变量区辨效度分析
(三)假设检验
首先,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对H1、H2、H4与H5进行检验。在表4中,Model1—4是以员工创造力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Model5—6是以工作旺盛感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Model1与Model5是只包含性别、学历与工作年限三个控制变量的基础模型。Model6的结果显示,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工作旺盛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51,p<0.01),H1得到支持;Model3的结果显示,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员工创造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54,p<0.01),H2得到支持;Model2的结果显示,工作旺盛感对员工创造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83,p<0.01),H4得到支持。Model4的结果显示,当自变量上级发展性反馈和中介变量工作旺盛感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由0.54(p<0.01)降低至0.19(p<0.01),因此,工作旺盛感在上级发展性反馈影响员工创造力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H5得到支持。
为进一步验证H5,运用MPLUS7.4,依据Bootstrap法(2000次)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上级发展性反馈通过工作旺盛感对员工创造力的间接效应显著,ind=0.353,p<0.01,95%的置信区间为[0.267,0.446]。因此H5进一步得到支持。

表4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注:** 表示p<0.01,* 表示p<0.05(双尾)。
其次,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对H3和H6进行检验,结果详见表5。在表5中,Model7—9是以员工创造力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Model10—11是以工作旺盛感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Model11的结果显示,当上级发展性反馈、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的交乘项同时进入对工作旺盛感的回归方程时,交乘项回归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β=0.08,p<0.01),说明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在上级发展性反馈和工作旺盛感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H3得到支持。Model9的结果显示,当上级发展性反馈,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的交互项、工作旺盛感同时进入员工创造力的回归方程时,工作旺盛感的回归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β=0.57,p<0.01),且上级发展性反馈×隐性知识共享的回归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β=0.09,p<0.05),但系数比Model8的0.13有所下降,说明工作旺盛感部分中介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的调节作用,H6初步得到支持。

表5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注:** 表示p<0.01,* 表示p<0.05(双尾)。
为了进一步验证H6,使用MPLUS 7.4,依据Bootstrap法(2000次)检验如图1所示的被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结果显示:上级发展性反馈和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的交互作用通过工作旺盛感对员工创造力的间接效应显著,ind=0.05,p<0.05,95%的置信区间为[0.01,0.09]。由此可知,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和上级发展性反馈的互补性调节(交互)作用,被工作旺盛感中介,进而对员工创造力产生影响,H6得到进一步验证。
为直观的显示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的调节作用,本文分别以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为基准描绘了不同水平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情境下,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员工工作旺盛感以及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员工创造力关系的差异(如图2、图3所示)。

图2 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在上级发展性反馈和员工工作旺盛感间的调节作用

图3 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在上级发展性反馈和员工创造力间的调节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证实了上级发展性反馈对员工创造力的积极影响,并且明确了员工工作旺盛感在上级发展性反馈和员工创造力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不仅回应了有关领导反馈与员工创造力关系的研究成果,还拓展了中介视角,对领导反馈—创造力研究领域有所贡献。既有研究主要从被动性与适应性视角研究领导反馈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理,如下属情境调节焦点、领导者—成员交换关系等。本研究则依据个体成长整合模型,从主动性与进取性的视角提出上级发展性反馈影响员工创造力的新路径——工作旺盛感,不仅为创造力领导理论补充新内容,而且验证了个体成长整合模型在员工创造力方面的有效性,拓展了其适用范围。第二,证实了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在上级发展性反馈—工作旺盛感作用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并且这种调节作用具有互补性(交互作用),即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与上级发展性反馈能够相互强化,进而对员工的工作旺盛感产生协同放大作用,为上级发展性反馈—工作旺盛感的作用机制提供隐性知识共享视角的情境化理论成果。此外,由于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与上级发展性反馈属于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且具有隐性与显性的区别,具有典型的非冗余性,因此,本文研究验证了非冗余信息互补原则,揭示出具体呈现规律。第三,证实了工作旺盛感对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在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员工创造力关系间调节作用的中介作用。已有研究曾探讨领导与同事的交互作用对创造力的直接影响[7],但未揭示具体的影响过程。本文则通过对一个被中介的调节模型,发现隐性知识共享与上级发展性反馈的互补性调节作用,会通过工作旺盛感进一步影响员工创造力,不仅弥补了相关研究的缺陷,而且基于上级发展性反馈视角打开隐性知识共享调节作用传导至员工创造力的黑箱,为深化理解上级发展性反馈—工作旺盛感—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机制提供情境化理论成果。
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提升员工创造力提供启发:上级与员工进行互动时,不仅要注意方式方法,加强反馈的引导性与推动性,放眼长久,侧重传递有利于员工学习、发展和改进的信息;而且要时刻关注员工在工作中的心理情况,尤其是员工主动性与进取性的感受,如活力与学习等,在必要时通过积极赋能、培训开发等措施提升员工的工作旺盛感。此外,还需对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进行有效干预,创造条件强化同事间的互动,营造互信互助的氛围,改善隐性知识共享水平。通过上级发展性反馈、工作旺盛感、同事间隐性知识共享水平的改善与强化,产生协同促进作用,有效提升员工创造力。
本文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取样数量与范围有限,未能获取更多的调查数据,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拓展样本的类型与规模;其次,论文未考虑个体特征、团队氛围、组织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引入上述因素进行差异性分析。
[1] Amabile T. M., Conti R., Coon H., et al. Assessing the Work Environment for Creativ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39(5): 1154-1184.
[2] 王智宁, 高放, 叶新凤. 创造力研究述评: 概念、测量方法和影响因素[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 56-67.
[3] Liu D., Liao H., Loi R. The Dark Side of Leadership: A Three-Level Investigation of the Cascading Effect of Abusive Supervision on Employee Creativ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55(5): 1187-1212.
[4] Zhang X. M., Bartol K. M. Linking Empowering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Creative Process Engagemen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53(1): 107-128.
[5] Gong Y. P., Huang J. C., Farh J. L. Employee Learning Orientatio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ployee Creative Self-Efficac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52(4): 765-778.
[6] Madjar N., Oldham G. R., Pratt M. G.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The Contributions of Work and Nonwork Creativity Support to Employees’ Creative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4): 757-767.
[7] Zhou J. When the Presence of Creative Coworkers Is Related to Creativity: Role of Supervisor Close Monitoring, Developmental Feedback, and Creative Personality[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3, 88(3): 413-422.
[8] Zhang H., Kwan H. K., Zhang X., et al. High Core Self-Evaluators Maintain Creativity: A Motivational Model of Abusive Supervision[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40(4): 1151-1174.
[9] 尹晶, 郑兴山. 上级反馈对员工创造力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领导-成员交换的中介作用[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1, (12): 153-159.
[10] 李磊,尚玉钒,席酉民,等. 基于调节焦点理论的领导反馈对下属创造力影响分析[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3, (9): 2280-2291.
[11] Spreitzer G., Porath C. Self-Determination as Nutriment for Thriving: Building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Human Growth at Work[A]. Gagne M.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ork Engagement, Motiv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45-258.
[12] Spreitzer G., Sutcliffe K., Dutton J., et al. A Socially Embedded Model of Thriving at Work[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5, 16(5): 537-549.
[13] Wang Z. N., Wang N. X., Liang H. G. Knowledge Shar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Firm Performance[J]. Management Decision, 2014, 52(2): 230-258.
[14] Anderson N., Potocnik K., Zhou J.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in Organizations: A State-of-the-Science Review, Prospective Commentary, and Guiding Framework[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4, 40(5): 1297-1333.
[15] Jing Z. Feedback Valence, Feedback Style, Task Autonomy, and Achievement Orientation: Interactive Effects on Creative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8, 83(2): 261-276.
[16] Shalley C. E, Perry-Smith J. E. Effects of Social-Psychological Factors on Creative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Informational and Controlling Expected Evaluation and Modeling Experience[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01, 84(1): 1-22.
[17] Wang Z. N., Sharma P. N., Cao J. W. From Knowledge Sharing to Firm Performance: A Predictive Model Comparison[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6, 69(10): 4650-4658.
[18] 戴维奇, 李强. 正式与非正式知识搜索、知识属性与产品创新[J]. 财经论丛, 2016, (9): 81-91.
[19] Peet M. Leadership Transitions, Tacit Knowledge Sharing and Organizational Generativity[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012, 16(1): 45-60.
[20] Swift M. L., Virick M. Perceived Support, Knowledge Tacitness, and Provider Knowledge Sharing[J].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2013, 38(6): 717-742.
[21] Ford C. M. A Theory of Individual Creative Action in Multiple Social Domai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6, 21(4): 1112-1142.
[22] 任华亮. 员工的自我发展诉求能否带来创新?——基于价值观的视角[J]. 财经论丛, 2016, (2): 81-88.
[23] Paterson T. A., Luthans F., Jeung W. Thriving at Work: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Supervisor Support[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4, 35(3): 434-446.
[24] Porath C., Spreitzer G., Gibson C., et al. Thriving at Work: Toward Its Measurement, Construct Validation, and Theoretical Refinement[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2, 33(2): 250-275.
[25] Farmer S. M., Tierney P., Kung-McIntyre K. Employee Creativity in Taiwan: An Application of Role Identity Theor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3, 46(5): 618-630.
(责任编辑:闻 毓)
How does Supervisor Developmental Feedback Influence Individual Creativity?——A Mediated Moderation Model
WANG Zhining, GAO Fang, YE Xinfeng
(School of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In the organizational context of positively empowering and activating individuals, it is not clear about the mechanism how supervisor developmental feedback (SDF) influences employees’ creativity (EC). Breaking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passive or adaptiv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SDF influences thriving at work (TW) and EC,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acit knowledge sharing among colleague (TKS), according to leadership theory of creativity and “Integrative Model of Human Growth at Work”. Based on 38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 find that SDF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both TW and EC; TKS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impact of SDF on TW; TW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EC; TW plays a partial mediation role between SDF and EC;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KS between SDF and TW will lead to EC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TW.
Supervisor Developmental Feedback; Thriving at Work; Tacit Knowledge Sharing; Creativity
2016-06-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30214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014T70565);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课题(JGZZ16_079)
王智宁(1978-),男,江苏徐州人,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高放(1992-),男,辽宁沈阳人,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叶新凤(1980-),女,江苏泰州人,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F129
A
1004-4892(2017)06-008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