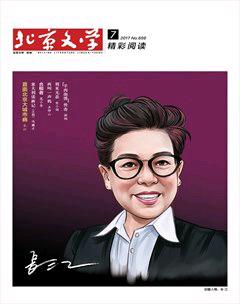病床上的感悟
张成起
我住医院了——是清晨外出散步时,一不留神,被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一辆捷达小汽车轻而易举地撞进医院的。
这是我走过的整整70年的人生路上第一次“正正规规”地住院。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庄稼汉,常年风里来雨里去,身体原本没那么娇贵,日常极少患病。即便偶患头疼脑热的小疾,无非是皱皱眉头扛上个三天两夜,也就不药而愈。而这次在医院一躺就整整18天,而且实实在在地做了一次耗时近4个钟头的接骨手术。
一
肇事司机是X保险公司的一位年轻员工。清晨我去公园遛早,中途路过一个加油站的进出口,我小心谨慎地瞭望确认没有进出的车辆后,便紧走两步想快速通过这个宽约10余米出入口。 此时一辆小车在丝毫没有减速的情况下,突然由机动车道右转驶入加油站,我被重重地撞倒在地。紧急之中,我立即掏出手机,迅速呼来了执勤交警110。
现场勘察后,交警对事故迅速地作出了“由肇事司机负全责”的责任鉴定。 120救护车把我迅速送到了医院的急诊室。X光片显示,我的左脚腓骨和胫骨末端已经完全断裂移位,我心中还是不免簌簌一惊——这次看来手术是在所难免了。 这次被车所祸给我留下的,是脚踝上部的小腿上密密麻麻缝了36针的28厘米长的两条恐怖的手术刀痕;两个骨折处植入了两条镍合金钢板,并打上了19颗固定钢钉。
面对这场飞来的横祸,我心中的愤怒和诅咒悠然而生。但冷静后细细咂品,人生或许理应如此。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人人都在期待和追求着有一个完美的人生。而到底什么样的人生才堪称完美,世人所求各异,众人难以趋同。但我隐隐悟到:作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除了为着一个神圣的心灵约定而终生苦苦追求和不懈奋争自不待言,完美的人生大概不仅仅是花前月下的绵绵私语,绿荫婆娑下的款款漫步,锦衣玉食的少虑无忧,雅斋静室的品茶唱和,赏景观光的五洲漫游,一帆风顺的心想事成。真正完美的人生,似乎还应该包括历尽酷暑严冬的风霜雨雪,踏遍前行荆棘路上的坎坎坷坷,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品咂不期而遇的六难三灾。
二
谨遵医嘱——也是出于手术后,输液管、导尿管、创口污物清洗管、麻醉剂微量导入管、血压脉搏监测仪等诸多管线缠身的无奈,我被迫规规矩矩地在病床上静卧了漫长难熬的整整18天。 随着身体状况的日渐好转,身上的各种管线相继被一根根撤掉。当终于有一天,我腿垂床沿伸脚触地吃力地站起,手紧扒床头忍痛艰难地试着迈出小半步时,虽然当即遭到了在场医生丝毫不留情面又饱含爱怜的严厉斥责,但我对自己终于又能够站立起来,并且还能试着迈出小半步的激动和喜悦,却是少有人知的。
人大概是天地间少有的一种只有失去后才知道珍惜的怪物。独自站立,蹒跚学步,本是乳童之举。车祸前,天天站立,每天走路,也没觉得多了或少了什么,不曾有过半分珍惜。但这次病床边的重新趔趄站立,蹒跚学步,却好似重开了我人生路上的一个什么崭新的纪元。大概如同人们天天都在呼吸,却没有多少人觉察到空气的珍贵。原来类似站立、走路这种从未被察觉到的幸福,竟然曾经默默地离我们如此之近,却忽而无声远遁,离我们又是如此之远!
值得庆幸的,不仅是医生告诉我,以手术情况判断,康复后完全可以恢复正常人的站立行走。更重要的是经过痛苦孤独的半个多月的卧床面壁,在漫漫人生路上,不经意间,我又跨越了一座不期而遇的高山,受到了一场醍醐灌顶的洗礼。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距离人生“完美”的目標似乎又微微地近了一小步。
三
我出院大约一周后,院长和骨伤科主任到我临时借住的一座平房,为我拆掉了最后尚存的4针刀口缝线。为了在医生面前展示一下康复效果,也是出于对他们精湛医术和多日精心护理的一种褒扬,我有意手拄双拐,一步一点头地迎出了老远。
大大出乎我的预料。他们对我的“展示”之举不仅毫不领情,而换来的却是对我这个特殊伤号“不遵医嘱”的满脸无奈和十分严肃认真又似带几分乞求般的请托:“不行啊——老爷子啊!这怎么能行?常言道,伤筋动骨100天。您老人家可倒好,手术还不到一个月,两处骨伤处还远远没有愈合,竟敢扶拐拄杖走出这么老远,而且还走得这么快。一旦造成内置钢板断裂移位,出现二次伤害怎么得了!你可以不在乎你自己,但也要为我们着想啊——您手术的成败,可是我们医院的一块对外的招牌啊!”
沉思。无语。
同样都是住院疗伤治病的患者,但我只能把对肇事者的满腹愤懑默压心底,不能向任何人发泄半句;只能默默忍受钻心的伤痛,以手掩面,暗中切齿眦目凝眉,但不能张口畅叫一声;本来是常规的手术,本地的医生却不敢操刀,只能被迫无奈地延长着痛苦。更没想到,就连术后的康复效果,竟然也被贴上了一块足以示众的“招牌”标志。看来,曾经的社会公众人物卸任后即便真的想淡出公众视野,实实在在地去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公民,在实际生活中也非易事。
我开始清醒地意识到,昔日头上御封的官职光环,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许会轻而易举地淡掉;而一种无形的社会责任可能将会陪伴我的终身。淡出官场易,淡出标准依旧特殊的社会监督——难!冥冥之中,我似乎感觉到了在我的肩上,还承载着一副隐身潜形难以卸载的“不忘初心”的重担。
四
住院18天,全是由家人昼夜陪护的。肇事方的单位领导曾几次主动提出,可以雇个护工,所发生的劳务费统统由他们来付——这倒也天经地义,但却遭到了两个儿女不容分说的回绝。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的老爸推给一个素不相识的护工来照顾。用他们的话说——护工的陪护是护在钱上,我们的陪护是护在心里。
护工没雇,但几天来,走马灯似的主动找上门来的“护工”却不少。他们神鬼兮兮地说:你这人不要太死心眼。实际上护工雇与不雇都没关系,但护工劳务费的发票我们都可以照样给你开。反正有赔付单位,又不花你自己的钱。只要把开票领取的钱返还给我们一部分就行,现在不少人都在这么干。这种事你我互利双赢,谁也不吃亏。
呜呼——大开眼界!平时我再也想象不到,就连住个医院,竟然还有这种见不得人的狗苟交易!看来我这个顽固不化的“老古板”,真的是不可救药的孤陋寡闻了。腐败的癌细胞竟如此猖獗地无孔不入,实在令我如蝇入喉、背若覆冰!
住院头10天夜间的陪护,几乎全部由儿子非常“霸道”地揽了下来,他拒不让任何人插手。老伴儿、女儿和儿媳除了白天轮流倒一下班外,主要负责后勤保障。后来,为了减轻儿子的负担,姑爷和在廊坊打工的侄子、外甥也陆续加入了护理队伍。
看到孩子们白天既要尽量坚持正常上班,又要一刻放心不下地轮流来医院照顾我,我实在心存不忍。再加上几天来探视的人势头不减,每天总会有那么几拨。就连我曾经就职的省审计厅得知消息后,也派人从石家庄专程来探视。外地得知信息的一些同学和朋友也电话中吵吵着要来。于是,我下定决心,尽早出院。
在反复协商征得院方勉强同意后,手术刀口处的线尚有4针没有拆完,我便迅速逃之夭夭,躲避到提前预订好的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城郊偏远的地方“隐居”去了。
十几天来,络绎不绝的探视的人群中,除了血缘至亲、旧时同窗好友和昔日政界同僚,大都非亲非故。既然是来医院探视,固然少不了几句温馨的问候和尽早康复的良好祝愿。但他们每每谈及廊坊的往事,又不时多了不少赞誉之词。我判断他们倒不见得仅是违心地循着“批判稿上无功劳,追悼词中无罪状”的老套路,怀着怜悯之心,面对受伤卧床的我,说的都是些言不由衷的奉承话。但我从政40余年,仅在地(市)领导岗位上的时间就占去了28年。不菲的薪俸浸透着老百姓的血汗。我身居要职多年,到底干了些什么,又真的干成了些什么?哪些光彩的事本来不是我 ——或起码不只是我一个人干的,我心中比任何人都清楚。只不过善良的人们往往习惯于把许多象征功劳之箭,并无恶意地统统集中射在了我这座他们心中虚拟的理想箭垛上。
勿劳竹帛书成败,惯听茶肆论短长。朴素而真诚的言语,颠覆着一些人对时下“人心不古”的忧天之叹,彰显着善良的人们对现实、对明天、对时下“官员”们的一种殷殷期盼。
但我敢断定,肯定还有另外一些他们没有听到或听到也不便当面说的话,并没有对我直讲。
我一贯认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多年从政担任要职的人,期待达到人人称颂、有口皆碑的境况,几乎是可视而不可至的海市蜃楼。连一句被批评甚至挨骂的话都从来没有过的领导,不见得是一个真正合格的领导。且不说,一个再优秀的领导者,他可以做到秉承宗旨、恪守人格,保证不去做那些损国害民的坏事。但不可能做到一切都料事如神、万无一失,从来都不因失误失察而做出有悖初心的错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既然有“过”,受到人们善意的批评甚至一些过激的指责,全在情理之中。
作为一个敢于担当的领导者,必须有“海水”与“火焰”两种情怀和“天使”与“魔鬼”两副面孔,集褒扬与惩戒之责于一身,承惩恶与扬善之担于双肩。即便是你再坚持原则、秉承公道,做的全是为国为民的好事善事,但同时你又在伤害着某些心怀不轨的人的既得利益,断了某些投机钻营的人龌龊有加的官路财道。这些人轻者丢了饭碗,重者被绳之以法。某些人发狠要挖了你家的祖坟也是毫不足怪的。所以,今天如果有人对我出车祸兴灾乐祸,或者再发上几句类似“活该”“撞死才好”等类型的诅咒的狠话,也都在预料之中。
五
静卧病床,屈指盘算,不经意间,我的一双儿女原来也都已年逾不惑了。
平时他们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他们煞费苦心地把节假日中的各种补习班、兴趣班安排得密不可支,忙得不亦乐乎。而我们父母子女们相聚的机会却越来越少。即便偶逢周日,往往也就是中午一顿饭间两三个小时的短暂相聚。我对这种回家“扫荡完就撤”的相聚,背后也曾经絮絮叨叨的颇多微词。
只是有了这次我重伤卧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才有了儿女们不分昼夜的床前陪护,也才有了我难得少有地对他们当面四目对视的细细审视。仔细端详中发现,在我眼中一直是孩子们的发间已银丝偶见,额头碎纹渐露。面对他们天天精心地为我洗脸擦身、温茶奉汤,我心中暗暗地掠过了几丝少有的充满愧疚的悲凉······
我的一双儿女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山城张家口隔年相继降生的。当时,我还在地区外贸局业务科当业务员。一家四口,夫妇二人80余元的月收入,还要奉养夫妻双方家在农村生活的老人。一间狭小的住房,还要兼作厨房、餐厅和杂物储藏室,其生活窘况是可想而知的。
当儿子刚满五周岁、女儿即满3周岁时,我即离家奉调到距张家口近200公里之遥的坝上沽源县任职,这一走就是7个年头。孩子们6年的小学生涯,都是老伴儿每天把家门钥匙挂在孩子们的脖子上,反复进行“路上要小心,要走人行便道”牵心挂肚的叮嘱后,两个小家伙背起书包,哥哥拉着妹妹的小手乐颠颠地上路。不管骄阳酷暑还是风雪交加,我从没有接送过孩子们一次;没有看过一次孩子们的作业;没有参加过一次学校的家长会;更没有时间给他们讲故事,陪他们做游戏;没有陪他们爬过一次山;没带他们看过一次电影;甚至没有和他们一起点上蜡烛,唱着“Happy birthday to you”,共同过一次生日……
1983年全国机构改革时,我奉调回到地委工作,也仅不过完成了一次表面令外人羡慕的家庭团聚。而承载着组织信任的地委副书记的重担,贫困落后山区百业待兴的工作压力,刚满37岁争强好胜的追梦年龄,迫使和催促自己不敢有半分懈怠。
机构改革后新组建的地委和行署的班子成员中,论年龄我最年轻。当时地委车少,况且我也没有资格 ——更不敢忘乎所以地“摆谱”,天天上下班让办公室派车接送。但又总觉得每天我应该赶在其他人之前提前到机关 ——谁叫咱年轻呢。从我居住的工业大街中部到长青路上的地委机关,南北纵跨大半个市区。山城的上坡路,冬天肆虐呼啸的北风透衣如纱,单程就需要足足骑车40分鐘。也曾有人背后讥讽我是在“有意作秀”。而这辆七八成新的自行车,陪我一“秀”就“秀”了整整9年,直至1992年调离这座山城。每天早晨,孩子们还没起床,我便骑自行车离家。处理完当日公务,到晚上结束必不可少的一些公务接待应酬,疲惫不堪地骑车回到家时,两个孩子又早已进入了梦乡。所谓“家”,充其量是我终年免费寄居的客栈。
静卧病床,尽享着孩子们每天嘘寒问暖、梳头揉脚的精心侍奉,我一向倔强的心在无声地流泪。几十年来,作为人夫、人父的我,到底为家庭,为妻子、为儿女们尽了几分责任?
不经意间,我老了。不知不觉间,曾经天真顽皮却十分懂事的两个孩子,也已经携他们读中学的子女,步入了他们人生的中年。时下,他们不仅在职要为国效力,在家要为子女尽责,还要时时不忘为双方父母尽孝。同时,还要不时观察我的眼色脸色,处处小心谨慎,以免作出有损老爸形象的事而遭到我的严厉训斥。他们太难——也真的太难为他们了!
孤肩难挑双重担,一烛难点两头明。我的最大欣慰是,今天,我这个一向不称职的父亲,最终得到了孩子们对老爸当年尽责不到的充分理解。
余下的最大企盼,也仅仅是默祝我的孩子们能在自食其力的正路上勤勉不怠、审慎笃行。还有就是,我尽量做到老而缓朽、自我珍重。假设有那么一天,我的苟活只是在体现着一个人生命力顽强,而已经失去了起码的生存尊严,那么,我祈求老天大发慈悲,不吝垂怜,尽早送我到我最终应该去的那个地方。以便把眼下捉襟见肘的社会公共资源腾出方寸空间,留给比我更需要的那些尚能为国效力的人。同时也别让自己的这副已经毫无价值的残躯朽骨,为孩子们再添新累。
(标题书法:周润天)
责任编辑 王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