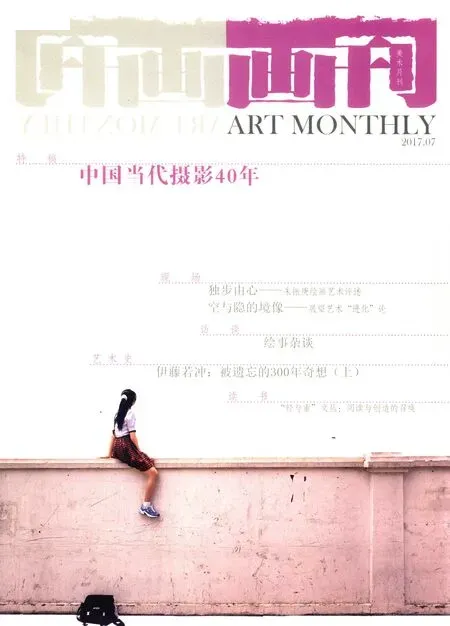存在的意义
——写在“半百·半百”江荣谢海展之际
吕明翠
存在的意义
——写在“半百·半百”江荣谢海展之际
吕明翠
我们身边的大部分人,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如苦行僧般的坚持和简净,执著于日常生活的满足;一种则是开疆拓土似的骑行和闯荡,探索在辽阔和神秘的远方。这两种不同的生活和经历给了他们风格迥异的际遇,也磨砺了或欣喜或寂寥的人生。是个体的差异构成了这些区别。即便如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 , 1888-1978年)和乔治·莫兰迪(Giorgio Morandi,1890-1964年),他们同样是20世纪著名的意大利艺术家,几乎生活在同一时期,却因为心性的不同,造就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创作风格。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艺术现象,是艺术的本质使然,也是艺术的无穷魔力之所在。
生活在淮安的江荣和从淮安出走的谢海,是一对艺术上的诤友。以他们几十年的人生历练,江荣无疑是一个身段柔软且认得清形势的人,他不做与潮流和现实对抗的事;比他小几岁、起点相同的谢海,却选择了一条极为叛逆和极具挑战的路,和基里科的壮志雄心有得一拼。
让我们把历史拉回26年前的1991年。那一年,谢海还未离开淮安;那一年,美术界恰逢“八五美术新潮”余波未了。在当时的中国画领域里,一方面是新观念、新技术的西方艺术语言的大量移植和挪用,一方面是传统的绘画遭受质疑和“新文人画”呼之欲出的当口。“江荣、谢海新水墨特别展”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下被推出。年轻总是无畏没有尝试过的事所面临的困难,也为这一切赋予更深的意义。让他们二人苦恼的是:如何向一个又一个好奇的询问者解释“新水墨”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是特别展?这里面是否有什么玄妙?面对各方的压力,28岁的江荣和21岁的谢海没有胆怯,他们直接、真实而又有锐气,他们像笛卡尔那样游走在思想的峰峦与现实的平地之间,寻找属于自己的“罗陀斯”。
20世纪80年代全国上下刚刚走出“文革”的阴霾,迎来文化、哲学层面的深刻持久的反思和研讨,并对90年代以后中国的历史走向和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文化热”催生了西方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带来了全民个性和思想的解放。在以古典乐和民乐为主要音乐表现形式的中国遇到西方传过来的摇滚乐和港台的流行音乐,让经历过集体狂欢、个体自由刚刚上场时代的江荣、谢海欣然狂热。二人一边听着给他们带来无限激情的音乐,一边在脑海中幻想它们会有什么样精彩的画面,激动得实在忍不住。他们效仿磁带封面小虎队的形象,穿上了满身的牛仔,戴着墨镜,走路摇头晃脑,目空一切,颇有香港电影里“古惑仔”的派头。他们在崔健的带动下唱着《一无所有》,并在“一无所有”的背景下开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追求:在那些与音乐独处的深夜,已为人父的江荣,用画笔记录荒唐而真实的青春,分享一个匮乏、遥远但也美丽、富足的故事;有文艺青年气质和艺术家理想的谢海,一边用文字喊出鲜明的文化立场,一边用水墨描绘独特的精神追求。
这边是相同的背景,那边是有差别的人生。一场展览,让江荣和谢海都找到了传说中的乌托邦,找到了希腊神话中的“阿卡迪亚”。不同的是:江荣说它就在淮安、就在眼前,谢海却坚持它在遥远的远方。他们分开了,继续走在寻找“阿卡迪亚”的路上。由于工作、学习和交通的限制,分隔两地的两人只有每年春节的时候才能见面,但他们的绘画并没有因为忙碌而停止,像两条轨道在并行不悖地进行着。
江荣出生和生活的淮安,是典型的苏北平原,典型的里下河风光所在地。在中国美术史中,里下河是艺术家极少去描绘的题材——相比于其他地区的地形地貌,里下河属于没有特色、比较难表达的题材。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艺术家也是如此,他们最擅长创作的莫过于熟悉的风景。“艺术是时代的产物,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取决于周围风俗和时代精神的产生和发展”是丹纳的哲学观点,他在论证这一学说时反复采用类比法,用大量的例子说明艺术与周边的关系。所以,江荣画他最熟悉的淮安,画他日常所见的里下河风光,并非偶然。
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江荣的画笔下,山不是单纯的山,水也不是单纯的水,而是一种情怀、一种境界。言下之意,江荣通过创作释放心中的激情与梦想。其实,江荣只是单纯地喜欢画画,没有障碍、没有羁绊,也没有特别的诉求。如果一定要有一个诉求,那就是江荣没有局限于描绘里下河,他也尝试画江南的山水,温润的、烟雾缭绕的,似乎只有这样的地方,才会是诗意的栖居之所。而他还没认识到的是:一个人的心灵归宿是最忠实的、最不会欺骗人的,他画着画着,还是会回到他最熟悉的那一方土地。
而迁居西子湖畔二十几载的谢海,在中国美术学院接受了林风眠“中西融合”观念的影响,亲身体悟了“八五美术新潮”先驱的变革精神。这两样东西交织在一起,激发起他骨子里的“骑士”精神,敦促他在跌宕起伏的风云际会里看到了闪烁的星光和别样的风景。那仿佛是如饥似渴的情不自禁,是情到浓时情亦深的自觉,让他在夯实基础的同时不断从传统中剥离、从传统中升华,创作了带有明显个人“存在”的新画风。
通常,我们在对“存在”的理解中发起活动,展开思考。正是出于这种理解,我们去揣摩物体和物体间的关系时,会探索它们“存在”的价值和目的。在谢海的《瓶花》系列作品中,物体和物体的交错摆放呈现的艺术是对日常生活的分析,是基于真实的“存在”,而《抽象》系列作品则倾向于探究艺术“存在的意义”。We are what we have,《抽象》系列是谢海不自我满足精神层面需求的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通过层层渲染,谢海借由“书写享受”的方式进入纯粹审美的过程。那内敛而深沉的艺术气质,是隐藏在画面里的气势、气魄和气派。谢海说:他自己的感知会比其他人来得更直接、更强烈,因为在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中,根基的坚实与丰富足以支撑起所有的情感,让他深深地沉醉其中。

《绝色江山之十七》 谢海 纸本水墨 35cm×69cm 2017年
通常,我们把艺术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探讨。但在艺术家面前,艺术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如果音乐以声音传递感觉,绘画则用直击人心的图式诉说一段过往和际遇、梦想和未来。莫奈的《睡莲》描绘的是他居住的吉维尼寓所池塘的景象;凡·高画面里大面积使用的橙色是他出生的国家荷兰的颜色;晚年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是他每天推窗可见的风景;黄宾虹描绘的山与水,是他不停辗转地从歙县到金华、又从金华到歙县途中的四季变换……很多人不会理解谢海心里那化不开的乡愁,也无法明白一个游弋于他乡的游子对淮安的眷恋。从清江到淮阴到淮安,从苏北平原到淮左到里下河,这几个词汇是他的文本里、画里和嘴巴里永恒不变的吟唱主题。而从未远离的江荣也坚信,淮安的独有气息是他所走过的所有城市都不曾具备的。
沈从文的凤凰、莫言的高密、汪曾祺的高邮、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都是他们笔下无法绕过去的精神家园。精神返乡式的文化追问,让一个艺术家拥有专属于自己的艺术领地,让一个作家找到文化的皈依。乡愁让艺术家心仪的故土变得与众不同,他们总能从那里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因为那里藏着全部的秘密。
观察中国的社会百态和风土民俗,得出的结论是:出走和回归,是作家和艺术家永远的心态。而在艺术创作中,地理地形学在画面中大面积地重复出现,就是精神归宿所导致的记忆呈现。所以,滋养江荣和谢海成长的淮安和里下河,在他们的内心埋下了深深的烙印,让他们不自觉地以艺术的方式进行追问。如果26年前“江荣、谢海新水墨特别展”见证了两个愣头青的青涩、理想和不堪,那这场26年后举办的“半百·半百——江荣、谢海新水墨特展”则是年过半百的江荣和年近半百的谢海致敬青春的展览。如果有幸见证当年那场展览的人遗忘了当时的那种热情,没关系,那些穿越时空的文字、图像和画笔总能串联起昨日的历史和当下的人物、故事,对当年的情景作出一次深情的回望。
2017年6月23日
于湖北美术学院藏龙岛校区

《好雨知时节》 江荣 纸本水墨 68cm×68cm 2017年
注释:
展览名称:半百·半百——江荣/谢海新水墨特展
展览时间:2017年7月23日-8月3日
展览地点:淮安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