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图像与凝视的对决
——论鲍德里亚对克鲁格的批评①
万书元(同济大学 艺术史与艺术哲学研究所,上海 200092)
克鲁格:图像与凝视的对决
——论鲍德里亚对克鲁格的批评①
万书元(同济大学 艺术史与艺术哲学研究所,上海 200092)
克鲁格是鲍德里亚非常欣赏的当代艺术家。鲍德里亚认为,克鲁格的作品具有一种掌控和牵制观众的魔力,一种凝视的魔力。克鲁格的作品虽然没有像克雷格.欧文斯所说的像美杜莎那样的用凝视将观者石化的效应,却足以使观众在阅读和欣赏其作品时产生身份焦虑、价值焦虑和文化认同的焦虑,从而陷入尴尬之境。克鲁格作品的力量,在于其洞悉人情,体察世态,感时忧世,不畏权势;在于其敢于为弱者立言,向强权宣战;在于其非凡的智慧、胆量和气势。
当代艺术;美学;绘画;鲍德里亚;克鲁格
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1945年-)是颇受鲍德里亚赞许的少数几位当代艺术家之一。也许因为她是活跃在纽约的美国艺术家,又因为她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广告特性,克鲁格显得比鲍伊和莫赛特的名头更大②Enrico Baj和 Olivier Mosset分别为意大利画家和瑞士画家,是另两位颇受鲍德里亚关注的当代艺术家。。
克鲁格出身贫寒,早年多有不顺,虽然先后上过两所大学,但是实际经历的大学生活不到两年。辍学后,克鲁格应聘到著名的康泰纳仕传媒集团担任助理设计师,负责集团旗下时尚杂志的平面设计工作。克鲁格后来曾经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我在时尚杂志工作了很多年,我必须明白自称为艺术家将意味着什么。女人那时候根本就别指望凭借一纸大学文凭找到工作,除非你愿意为公司老板端茶送水。如果年轻的姑娘们想在工作和兴趣之间找到平衡,想做自己的主人,康泰纳仕就是一个很好的避难所。”[1]克鲁格最终能够成为举世闻名的艺术大家,她的出身和康泰纳仕的这段设计经历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贫寒的出身决定了她的反叛立场,康泰纳仕的经历决定了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取向。
从现有的资料看,我们还找不到证据来证明,鲍德里亚自己的出生和克鲁格的出生之间存在着什么特别关注的共同性。但是,两人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甚至在思维方式方面都存在共同性,两人都是站在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的对立面,以反叛的姿态,揭示各种矛盾,展开尖锐的批评。鲍德里亚之所以喜欢克鲁格,和他喜欢莫赛特与鲍伊一样,既有同仇敌忾(价值体系)的成分,亦有趣味相投(审美旨趣)的因素
鲍德里亚1987年专门为克鲁格的展览撰写了一篇评论,后来收录在《鲍德里亚未收入论文集》(Th Uncollected Baudrillard,Edited by Gary Genosko,SAGE Publications,2001)中。原文无标题,收入文集时起名《芭芭拉·克鲁格》。在这篇文章文中,鲍德里亚从三个方面(但是贯穿始终的是对她的反讽的肯定)分析了克鲁格艺术的特点。
第一,鲍德里亚认为,克鲁格通过其大量的艺术作品,深刻地揭示出世界本身的矛盾与荒诞,展示出一种“客体性反讽”状态。克鲁格试图用我们世界的图像和与之相配对的文字向我们证实(图像来自于既有的报章杂志,文字也经常来自于文学著作或文献或日常警句),我们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正本吞噬了副本的世界(如同人类用自己的肉身抹除自己的影子一样),一个没有深度的肤浅的世界,一个以现实驱逐现实的非真实的世界,一个只剩下人造物、工艺品、符号和商品以及碎片化的现实的世界。鲍德里亚指出 :“克鲁格的非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她能够以一种神奇的引力把星散四处的现实碎片拼合起来,构成一幅我们既感到熟悉,有感到陌生的图景——我们世界的颠倒的图景。”芭芭拉•克鲁格以其特有的图文互渗的呈现方式警示世人,“我们不再需要像超现实主义过去所作的那样,以一种诗性的不真实的方式把物品和它们的荒诞功能进行并置。现在,事物都已经主动地使自身变成一种反讽状态。它们毫不费力地抛弃了自身的意义。我们无需强调欺骗或荒谬;因为荒谬和欺骗就是事物的形象的一部分,可见性的一部分。”[2]
克鲁格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反对堕胎的领导人中77%的是男性,而他们100%的人永远都不会怀孕》,其聚焦点就是标题所显示的这些按照六行排列的红底白色文字。克鲁格用两个简单而至关重要的数据,揭示出寓于现实世界之中的一个真实而荒诞的事实:一个数据是,反堕胎的领导人中,占77%的是男性,这就说明,虽然干预和反对堕胎的领导人中有女性,但是比例很低;干预和反对堕胎的主体力量来自男性;第二个数据是这个作品的亮点,也可以借用罗兰.巴特的术语,是一个“刺点”。它把前一个数据的统计学关系翻转为一种具有本质意义的荒诞关系,而且也使这个作品充满了幽默和反讽:这些男人百分之百不会怀孕。男人不会怀孕是一个普通的常识,但是,这个常识在这个特定的语境中一经点出就起到了翻天覆地的奇特功效。因为这里包含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拥有怀孕身体的女人,没有掌握怀孕与不怀孕、生育与不生育的决定权,而根本不可能怀孕的男人却掌握着女人怀孕即必须生育的权力。作品的背景是五个身着西装,表情冷漠、威严、傲慢的男人,虽然画面上只露出五张表现出不可违抗神情的冷酷嘴唇,但是可以想见,这五个男人正在用威胁的眼神威逼着想要堕胎的女人:你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放弃堕胎。虽然作为受虐一方的女性并不在场,但是下面一行细小的、并不显眼的文字,却以故作胆怯的方式,从隐匿处发出微弱而坚定的呐喊:这是你们的身体。是你们来决定是否堕胎。你们要参与关于堕胎的公共教育项目。你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堕胎。(It's your body.It's your decision.The pro-choice public education project.It’s pro-choice or no choice.)整个作品以图文的直接对话和男女的潜在对决的方式,揭示出男权社会乃至权力社会中存在的悖谬现实,从而让现实本身产生一种自讽(已经不需要下面那行文字来为女性呐喊了)效果。

图1 反对堕胎的领导人中77%的是男性,而他们100%的人永远都不会怀孕

图2 你很漂亮

图3 这绝不是我们的错
如果说《反对堕胎的领导人中77%的是男性,而他们100%的人永远都不会怀孕》是从生育(或反生育)权的角度向男性社会提出严正抗议,那么,《你很漂亮》和《纯天然无污染》则是向消费社会堕落的消费观和道德观提出抗议。在这里,女人不再是人,不再是享受人类应有和共有的尊严的人,而是类似于放在超市货架上的商品或物。在《你很漂亮》中,那张漂亮的脸显然刚刚被人用三庭五眼之类的标准比例测量过,脸上的参照线尚未消除。因此,“你很漂亮”这个对普通女性的最普通不过的赞美,在这里变成了类似法院判决那样的令人恐怖的叙事,甚至比法院的宣判更为可怕,因为法院的判决可能有死刑,也会有缓刑,甚至无罪释放。但是,在这里,只存在两种判决,一种是“你很漂亮”;一种是“你不漂亮”。前者可能意味着生(不一定保证是有尊严的生);后者只能是死,只能是不存在。因此,“你”这个称呼,在这里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引出了一个高居于女人这个类属之上的世界,从而揭示了这个世界对女人这个类属总体的拒绝和有限的接纳。只有类似于“你”这样的“漂亮”者才有可能得到男性世界的青睐,被上货架挑选。否则,只能被厌恶地抛弃。《纯天然无污染》在此变成了第一人称,使画面中的美女充当一种类似餐馆或商店的自荐广告。这个作品的奥妙在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遭遇到了一种可怕而邪恶的错位书写。我们知道,那些通常被人类按照生态标准进行描述和评价的对象,要么就是大自然,要么就是大自然中的动物或超市中的商品,在此,广告的主体居然主动将自己的身份降格为自然中的动物或超市中的商品,这就使对象本身产生了一种自相矛盾的自讽效果,同时又使观者对引发这种自讽境遇的社会和阶层发出了哂笑。
作品《这绝不是我们的错》采用了一种自辩的被动语态,使动物将人类与自然之间本然的自洽关系引入一种因果困境:气候变换,北极冰雪融化,一只北极熊半蹲在即将倒塌的蘑菇状冰雪帽上,两眼茫然而又无助地望着天空。它的头上写的就是这个类似连环画表达法的内心独白:这绝不是我们的错。两条红色条块构成一个表示错误的红叉叉。红叉叉的上面“It’s never’”是白色,“our fault”则用黑色,“fault”运用了大两号的黑色字体。这样,在北极熊、白冰雪帽与顶部的白色文字之间就形成一种间隔和对比,同时,黑色的“fault(错)”字,犹如音乐中陡然增高的加强音,把“fault”的严重性和悲剧性推向了宇宙的规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作品强调的不仅是客体的自讽,也是客体直接向主体发动反讽和攻击,是另一种客体的反讽——对陷入到自取其害的尴尬境遇之中的人类的客体性反讽。
鲍德里亚说∶
更为有趣的是,我们的世界注定要走向其劫数,这种劫数并不是超越于,而是内在于我们的生命的过程中,事物的过度麇集和超速运动以及过剩繁殖中,还有我们的平庸中;这也显示出事物对其(是否具有)意义的不在乎(indifference),结果对其(是否是由于那个)原因的不在乎。所有这一切又使世界回到了它的起点,回到了由(笛卡尔的)邪恶的魔鬼凭借其无言的策略幻化出的那个世界。这不再是主体对客体秩序(objective order)的反讽,而是陷入到自取其害的尴尬境遇之中的事物的客体性反讽(自我讽刺——译者),这种客体性反讽,不再是消极性的历史活动,而是以倍增(reduplication)效能来提高赌注的活动,与作为语言的宿命策略的载体的俏皮话(witz)如出一辙。[3]69
客体性反讽是鲍德里亚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与鲍德里亚的所谓宿命的策略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为了说明客体性反讽的威力之大,影响之巨,鲍德里亚举过两个例子:一是抗生素与细菌,一是科学研究与研究对象。鲍德里亚说,我们人类(主体世界)确实很厉害,厉害到不仅已经实现了一切想要实现的,而且已经达到了超度的实现,这就是他的著名的“过剩”理论。但是,客体世界(对象世界或客观世界)并不是被动地听任我们的折腾。在主体世界和客体世界之间其实也存在着一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状态。比如,人类为了杀灭侵害健康机体的细菌,发明了抗生素;但是,处在客体地位的细菌也不是吃素的,它们也逐步培养出一种耐药性和抗药性来抵抗来自主体世界的这种杀灭,使主体在这场遭遇战中陷入尴尬地位;又比如,随着科学的发展,“随着方法学的成熟,科学毁灭了它的客体(对象):为了生存,科学又必须按照仿真模式为自己复制一个人工的客体(对象)。”[3]72仿真的客体一旦形成,它就反过来对主体(科学)进行报复,其结果是,主体(科学)面对的将不再是真正的对象(客体),它只是我们的技术控制下的一种仿真客体而已。也就是说,真正的客体,借助于仿真的虚像,躲过了科学的纠缠。科学研究的对象变成了一个伪对象,一个被科学自恋的幻影。科学(主体)变成了客体报复的对象和反讽的对象。这也是鲍德里亚所说的“晶体的报复”。
这就是主体的宿命,这也是客体的宿命。鲍德里亚之所以重视并且赞许克鲁格,就是因为克鲁格通过自己的作品展示了这种宿命,这种反讽。
第二,鲍德里亚认为,克鲁格借助于她独有的媒介手法,通过向男权社会和权力阶层喊话与质询的方式,创造了一种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当代妇女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作为一位女性主义的头号批评家[4],鲍德里亚对克鲁格由此建立起巨大声誉的这种女性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质疑。
在普通观众和批评家的心目中,克鲁格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与女性主义(还有概念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克鲁格本人并不认同并且强烈反对。鲍德里亚在1987年写《芭芭拉.克鲁格》这篇评论时,克鲁格已经顶着女性主义艺术家的名头红遍欧美。克鲁格作品虽然题材多样,有着广泛的关注点,但在鲍德里亚写作这篇评论的时候,克鲁格创作的女性主义作品也已经非常可观(当然,在1987年之后更多),可能是由于鲍德里亚这篇文章篇幅较小,也比较随性,因此对克鲁格的具体作品涉及并不是太多。
鲍德里亚对克鲁格女性主义观念的批评,主要建立在他对诸如《我是您(圣灵)的无染感孕》,《我们是你们的旁证》,《我不再是你们的镜子》,《我们将不再是你们所喜欢的隐身术》这样几件作品的考察上。在这些作品中,正如很多论者注意到的,克鲁格主要是通过两类人称代词,即第一人称“我(的)”和“我们(的)”与第二人称“你(的)”和“你们(的)”,来区分男性和女性、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讽刺者和被讽刺者、抗议者和被抗议者这样两种社会、政治和文化身份(关于鲍德里亚善于使用人称代词的问题,下文有详述,此处不赘)。

图4 装饰你的监狱

图5 你不是你自己了,1981

图6 我们是你们的旁证1983

图7 我是您(圣灵)的无染感孕,1982
《我是您(圣灵)的无染感孕》(1982)是克鲁格对天主教教义中的童真圣母玛利亚语录的一种反讽性挪用。根据天主教教义,虽然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使人类陷入了原罪之中,但是,生育了耶稣的童贞女圣母玛利亚却与原罪绝对无涉。原因是,第一,她的受孕方式是通过圣灵感应而非肉体接触;第二,她孕生的对象,是一位神人兼备的救世主,这位伟大的救世主将以在十字架上受难然后再复活的方式把人类从原罪之中拯救出来。因此,圣母玛利亚曾经骄傲地向世人宣告:“我是圣灵无染的感孕!”
不过,克鲁格的《我是您(圣灵)的无染感孕》并没有展现出任何与圣母玛利亚感孕相关的神圣的场景:没有带翅膀的报喜的天使,没有神圣的灵光,没有吉祥的鸽子,也没有可爱的圣婴形象。画面中出现的唯一图像,就是一双女性的手的特写:一只美甲的右手(局部),正拿着一把清洁刷,洗刷着沾满了肥皂泡沫的左手。也许是一双刚刚接过生的手?一双为所谓的“无染感孕”的圣洁的女性接生过的手?但是,清洁刷和肥皂沫以及清洁的动作,也即作品的整个图像和文字间,显然与这种所谓的“无染感孕”产生了巨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因此,作品实际上是正话反说:“我何曾是您的无染感孕”?“谁说我是您的无染感孕”?“我们又如何可能无染感孕”?人类的生育又怎么可能像宗教所描述的那样神秘、神奇而又轻而易举?
如果将这个作品与克鲁格的另一件作品——《你反堕胎却又支持死刑》相比较,我们就不难看出,克鲁格在作品中所要诉求的,不是一般地主张女性与男性的平权问题,而是要揭示出这个由男性控制和主宰的世界的残酷与荒诞:未出生的胚胎(没有自主的生命),你偏要赋予它们生命权;已经活着的生命,你偏要强加他(她)们死亡权(死刑)。你愿意给不该获得生命权的非生者以生命权,却不愿意放弃给未死者以死亡权。两相对比,就使男权社会和权力部门在反堕胎而又坚持死刑的问题上陷入了难以自拔的道德困境与人权困境。当然,《我是您(圣灵)的无染感孕》可能还包含女性的某些自辩——具有进攻性的自辩:不要肤浅地把女性当成和男性一样的人,实际上,女人根本就是与男性完全不同的一个物种,一个有着自己特有的生理特性和心理要求的物种;男性必须充分了解和尊重她们的生理特性和生理选择,要尽可能地减少女性在孕生和哺乳时的痛苦,而不是以事不关已的姿态,打着空洞虚伪的人权幌子,以忽视和掩盖女性的痛苦和苦难的方式来加剧她们的痛苦。
《我们是你们的旁证》(1983)和《你不是你自己了》(1981)都采用了黑白照片和镜像方式,而且表现的主体都是集中于破碎镜像中的年轻美女的形象。在《我们是你们的旁证》中,那双映现在破碎的镜子中的美丽而锐利的眼睛,一直坚定地凝视着我们,与照片中间从上至下排列着的文字“我们是你们的旁证”形成奇异的互动。“旁证”是一个法律术语,指与案件相关的,能够为案件提供事实证明的证据。镜子碎片中的那双坚定而愤懑的眼睛确实能够让我们确信,这双眼睛不仅见证了一切,不仅最有资格充当旁证的见证人,而且必定愿意做“你们旁证”的见证人。但是,这里的不幸在于,还有一个“他们”横亘在“我们”和“你们”(其实是“我们”)之间,而且“他们”是如此嚣张,如此放肆,显然已经用暴力毁灭并且控制了旁证。克鲁格1981年的作品《你不是你自己了》倒是为《我们是你们的旁证》提供了一个注脚。这个作品以“not”为圆心,用“you are”和“yourself”构成一个圆圈,圆的中间是一个女性在被子弹击碎的镜子上映照出来的表情痛苦的脸。作品的左下角有一只举着镜子的手。这就给观众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是谁打破了这张身份之镜,又是谁在举着这样一个身份之镜?是谁在宣告“你不是你自己了”?是谁让一个完整的自我变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非我,一个不完整的自我?谁是旁观者,谁是“你”?由于“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因此,“我”也不再能够充当“你们”的旁证了。
1989年,华盛顿举行了一场由妇女组成的声援堕胎合法的游行。格鲁克创作了《你的身体就是战场》作为这场游行的徽标。这个作品可以视为克鲁格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隐喻,或者一个图解。一张女性的脸从中垂线位置被一分为二,左明右暗,象征着一正一负的两极正在进行生死搏战。从作品本身的图文关系来说,既包含了男女之间围绕女性肉体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搏斗,当然也揭示了外在于女性的两种(或诸种)男性势力为控制和占有女性身体而展开的激烈争夺。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女性是“100%的天然无污染”,更因为女性本来就不是人,而只是男人的战利品——因为“我的脸是你们的财产”(克鲁格作品)。从宏观的隐喻层面来说,这一左一右,一明一暗,象征着一善一恶,一女一男,一弱一强的二元对立关系。《装饰你的监狱》和其他女性主义艺术家创作的展示女性惨不忍睹的美容手术过程的作品完全是同构的,只不过克鲁格更加生猛,也更加哲学,更加带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反思性而已。
在80年代早中期,乃至90年代,甚至更晚近的作品中,克鲁格一直是把女性置于一种泛社会权力架构之中。在这类作品中,世界变成了一个由压迫的男性和被压迫的女性构成的不公平的世界。女性不断地发出痛苦的绝叫,要求走出男性为女性设置的象征性的监狱,要求获得应得的、与男性平等的权力,同时,要求获得女性应得的尊严和社会地位。
当克鲁格利用其作品向男性社会进行激烈的女性主义质询和批判的时候,一向对女性主义运动抱有成见的鲍德里亚就有些沉不住气了。他按下赞许的话头,转而质问道:既然这些作品借助道德优势,以一边倒的方式,把男性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辩解的可能性的尴尬地位,那么,“还有能够回应这种质询的所谓男性气质吗?还有能够见招拆招的权力吗?还存在着足以让这种对抗性交流存在的性别差异吗?让男性承认,现在,毫无反击之力的是男性,这有什么好处?男性只能以消失的方式——它也确乎已经消失——来回应。然后呢?同理,是否仍然存在一种足以向权力发起彻底的、对抗性的挑战的权力关系,政治矛盾这样的东西呢?不过,逼迫权力承认,此时此刻,它已经不再拥有任何手段或政治能量,这有什么好处呢?”[2]
鲍德里亚认为,女性主义其实是一种最高级的憎恨形式,是一种怨妇情结,是一种要把男性往死里整的报复倾向。女性主义要求获得自主性主体的权利,要求获得明确的身份标志和生存的安全保障,其实是一种幻觉①鲍德里亚把女性主义的诉求粗暴地概括为“要求合法的权利和合法的吵闹(recrimination)”.Baudrillard, J. (1993c) Baudrillard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1982-1993), ed. M. Gane. London: Routledge.1993.p.209。鲍德里亚曾经尖刻地指出,女性主义试图穿越结构性的障碍,到男性那一端安营扎寨,实现“跨性”(cross terms,即交叉的性别),但是最终依然一无所获。因为即使跨性成功,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结构依然如旧,只不过是乞丐与皇帝换位而已。当然,女性主义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让这个传统的两性结构彻底崩溃,但是,这将意味着不再有男女,不再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只有一种零度结构,不再有女性主义存在的基本前提。[5]
鲍德里亚认为,在当今,西方社会已经处在一种多元化的、性别无区分的语境下,变性人地位获得上升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现在正在从性别区分走向总体的性别中性化。这才是女性当今面临的真实境遇。鲍德里亚说:“被解放的恰恰不是她们(女性)性别的特异性,而是她们与男性的异质混合。”[6]在《论诱惑》等著作中,鲍德里亚提醒女性同胞,她们发起的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因为女性压根儿不是她们自己用怨怼塑造出来的那种处在受排拒和受歧视地位的悲剧形象,恰恰相反,她们是在男女两性的对抗之中占尽先机的一种富有巨大的诱惑威力的形象。
鲍德里亚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创立了他引以为自豪的诱惑理论,而且将这一理论和宿命理论熔为一炉,广泛地运用于他的批评理论之中。在他看来,诱惑是一种命运,是人世间最伟大的力量,它“代表着对象征世界的控制,而权力只代表对现实世界的控制。在政权或性权的掌控方面,诱惑的权威至高无上,盖世无匹。”[7]诱惑恰恰是女性的特权。这才是她们反抗男性中心主义的利器。遗憾的是,女性主义者们扔下威力无比的机枪,却拾起一根秸秆来与男性世界对抗。她们用“自主,差异,欲望与快感的特异性,女性身体、言说和写作等方面的差异关系”,或者,像克鲁格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用反讽,用酷评,来反抗男权统治的世界,“但是从来不是诱惑。她们以诱惑为耻好像诱惑就是暗示一种身体的虚夸的表演,或一种奴仆式的或卖笑的人生”。[7]
如此一来,女性巨大的特权——作为象征权力的宰执者和外表王国的绝对主人的特权就被轻而易举地抹除了。诱惑内在的威力,诱惑通过外表的纯粹游戏挫败一切权力体制和意义体制的巨大威力,这个唯一等同于并且超越于所有威力的威力,被女性主义者们白白地丢弃了。她们明明只需一个简单的外表的策略游戏,就可以把其他所有威力(包括男性中心主义——引者)掀翻在地。[7]女性主义者们偏偏以南辕北辙的错误方式,陶醉于身份/差异结构的斗争,她们不知道,即使她们在这场战斗中大获全胜,其结果只能是把她们自己封闭在那个恶心她们的结构之中。[8]
鲍德里亚对女性的诱惑威力的渲染,甚至崇拜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中国古老的红颜祸水的故事。从极端的意义上说,美丽至极且善媚(seduction)的丽人确实拥有(或者说可能有)倾城祸国的巨大威力,至少足以让男性在女性面前变得服帖从而让女性实现自身的地位和价值。但是,诱惑是否真的具有如此神奇的力量,能够持久地掌握其象征权力,控制男性和权力世界?我们的世界难道整个就是一个由年轻漂亮精力充沛春情无限的男女构成的世界吗?我们的世界难道只是一个单纯由欲望和性构成的世界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毫不迟疑地说,鲍德里亚的诱惑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具有局部价值的控制模式而已。它根本不能解决女性主义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不能解决当今已经泛化为超女权的女性主义的问题。因为当今的女性主义已经不再只停留在自身的权力和价值乃至差异性的诉求之上,而是变成了一种为弱小者争取权力的普遍社会运动,比如为有色人种争取权力,比如为动物争取生存环境,比如参加生态保护运动等等。
英国通俗文化批评家安德鲁.茹斯(Andrew Ross)说:“由于鲍德里亚对女性主义策略的宽广的内涵和实践的紧迫性,以及对女性主义政治的重要性缺乏认知,因此,诱惑以抽象的方式获得的任何东西都将付诸东流。”这个评价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是美国文学理论家简.盖萝(Jean Gallop)认为:“鲍德里亚,这位男性法国理论家对女性主义采取了一种最明目张胆也是最直截了当的敌视态度。”[8]这个评价似乎有些过火,至少是忽视了鲍德里亚的诱惑理论与他对女性主义的态度之间的紧密关系。
总之,鲍德里亚对克鲁格的女性主义艺术颇有微词,作为当事人,克鲁格对鲍德里亚的批评却是予以谅解。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

图8 纯天然

图9 我的脸是你的财富

图10 你的身体就是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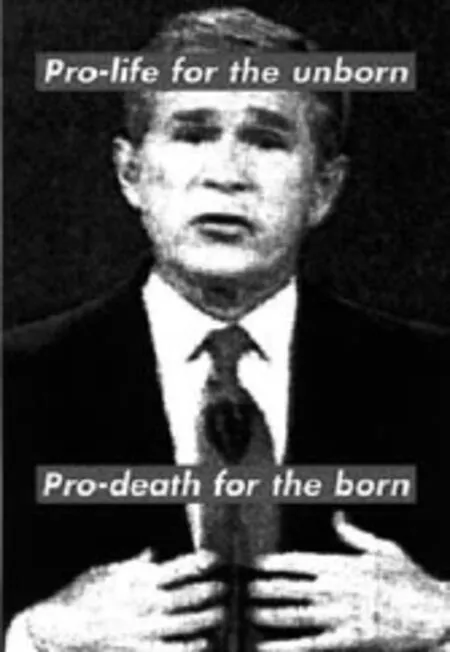
图11 对未生者你反堕胎,对未死者却要用死刑
第三,鲍德里亚认为,克鲁格开创了一种开放的、适应于当代媒体社会的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鲍德里亚注意到,克鲁格作品的呈现方式,灵活多变,在信息传播上兼具广告和艺术的双重效能,完全突破了艺术固有的空间限制,实现了艺术呈现的多样化和展览(展演)空间的多态性。鲍德里亚说,克鲁格的作品“……尺度不仅突破了画框的限制,甚至突破了传统的美术馆或博物馆的那种传统的展示空间的限制,它具有电影屏幕所具有的新的自由。她们相互之间没有隔绝,相反,它们共同构成一种链式反应。它们如同这一系列反射面板所构成的连续轨迹,展现了我们的‘过度的’现代状况。它们把自己从分格线中,从僵硬的定位中,从作为艺术的美学定义的确定的视觉模式……中解放出来。”[2]从作品的尺度上说,克鲁格完全打破了传统画框的限制。尺度可以奇大无比,大到遮盖整座大楼的外墙;从作品的展览方式来说,完全突破了美术馆和博物馆这样的传统的艺术展览空间的限制:可以布置在楼梯台阶上,也可以布置在楼梯的斜面、反面或其他地方,还可以布置在地板和天花板上,甚至可以像所有广告那样,布置在公共汽车外壳上,或其他交通工具上。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戏拟了广告的无所不用其极的传播方式,扩展了作品传播的空间广度,增加了阅读与观赏的频度,提升了信息可达性的强度。[2]
1991年,克鲁格在纽约玛丽.布恩美术馆举办了第三次个展。在这个展览中,克鲁格调动了美术馆的几乎全部空间。所有的墙壁、地板和天花板,全部被用黑红白三色的作品所覆盖:地板和天花全部是红底白字标语,墙壁上全部是图像加文字。整个美术馆简直就是一个浪涛翻滚的红色海洋。白色的文字犹如浪花点点,在波飞浪卷的海洋上涌动。
整个美术馆变成了一个喧闹、炫目、杂乱、冲突的场景,观众置身于其中,有一种被撕裂、被压制的感觉,也有一种要挣脱、要叫喊、要争辩的欲望。
把展览空间转化成一种躁动的、体验的、调动观众思考、激发观众情绪的场所,这不仅是克鲁格作品本身的特点,也是克鲁格展示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图12 你的任务就是分而治之1983

图13 克鲁格在纽约玛丽.布恩美术馆的展厅之一,1991

图14 什么都不懂,什么都相信,什么都忘记,1987

图15 金钱可以买你的爱1985

图16 剽窃是最诚实的模仿形式

图17 你们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头脑,那就让别人来控制你

图18 想起你
鲍德里亚认为,克鲁格作品善于运用摄影(图像)蒙太奇和挪借的手法,通过图与文的纠缠而形成信息短路,或形成图文互渗和互补,从而实现一种拨云见日、祛蔽启真,为世界驱魅的功能。换句话说,克鲁格的作品,善于在图文的纠缠中创造一种冲突的或悖谬的境遇。《什么都不懂,什么都相信,什么都忘记》(1987)拼贴了三个视觉元素:眼睛注视着上方的年轻女人的侧脸、医疗检测仪器和医生。医生其实只是一截穿着白大褂的身子,既没有出现脸,也没有出现手。观众只能依靠图像信息来推测:医生正把那个检测仪器对准那双天真的、“相信一切”的眼睛。因此,单纯从图像角度看,这只是一个非常日常化的医疗场景。但是,一旦画面嵌入这三行红色文字时,瞬息之间,整个画面就被解构了。医生变成了目光锐利的启蒙的智者,女人变成了没有常识、盲从盲信的庸众的代表。“什么都不懂,什么都相信,什么都忘记”犹如三记鞭子,重重地抽在观众身上。
《金钱可以买你的爱》(1985)和《什么都不懂,什么都相信,什么都忘记》一样,图文之间形成互相抵牾的紧张关系:图中的女孩年轻、漂亮、活泼,做着怪脸,有点自命不凡,有点桀骜不驯,有点聛睨一切。但是,有个画外音在她的耳边响起:别神气!金钱可以买你的爱!画面信息否定并颠覆了图像信息,图像信息最终归于失效或短路。
《剽窃是最诚实的模仿形式》的文字是对美国钢琴家、作家和演员奥斯卡.莱文特的名言的篡改性挪用。莱文特的表述是:“模仿是最诚实的剽窃形式”,克鲁格改为“剽窃是最诚实的模仿形式”,用以讽刺建筑行业中流行的剽窃和移植。背景中的凯旋门,就是建筑和城市史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恶劣最典型的剽窃案例之一。用人类语言中形容真实的一个最高级的词汇来形容人类最不真实的行为——剽窃行为,这就在图像和语言之间,在词语和词语之间,构成了一种极具张力的悖反状态。在这里,不仅文字信息使得图像信息短路,词语也使得词语短路。在词与物的并置,词与词的对照中,克鲁格对建筑与城市设计中乃至人类的一切创造行为中的抄袭、模仿之风作了辛辣的讽刺。
表情阴险的希特勒的头像和“你们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头脑,那就让别人来控制你”(挪用英国18世纪的名流约翰.阿尔斯顿的名言)组合在一起,一下子就把观众导入了一种恐怖的境遇之中。克鲁格警告观众,如果你们的头脑不是长在自己的脑袋上,极权主义者们随时可以让你们成为无脑人或躯干人。因此,人类必须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唯有如此,人类才有可能获得安全和自由。

图19 我们是你们的温柔陷阱的猎物1984

图20 你没法把钱带进你的坟墓
《你们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头脑,那就让别人来控制你》既可以理解为独白,也可以理解为旁白或画外音。从希特勒角度,是一种放肆的、霸道的、冷酷的独白,法西斯的独白法西斯向被吓坏的公众的申斥;从克鲁格的视角,又可以视为一种旁白,对观众的旁白,对观众的警示《我们是你们的温柔陷阱的猎物》则是一种内心独白画面是一只被用绳索编织的罗网网住的手,手的右边是字幕:“我们是你们的温柔陷阱的猎物”。和前一幅作品一样,克鲁格不是像通常那样采用图像与文字背离的逆向组合方式,而是采用顺向组合的同谋的形式使图像和文字产生某种互补,使作品的主题在图文的相互映照下得到强化的表现。世界充满了诱惑。权力奴役我们的方式,不一定总是采用暴力的形式,有的时候也会采用温柔的形式,我们必须时时小心,否则难免成为这种温柔陷阱的猎物。尤其在消费社会,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往往命定就是商家温柔陷阱中的猎物。你们想逃离这种温柔的陷阱,还是愿意沉迷于其中呢?
鲍德里亚指出,克鲁格在作品中广泛运用人称代词,不仅在图像内部建立起一种强制性的对话关系,而且在作品和观众之间也建立起一种强制性对话关系,尽管“这些图像没有创造一种意识形态深度只有一种反讽的深度,通过你们(YOU)和其重复创造出这种反讽,这实际上强化了他者的缺席——对话者的缺席,或者至少是它的成问题的在场。这是一个自身不能交流的交流社会的连祷,在这个社会,媒体存在,所有的媒体都存在,但是却不能交流,甚至没有一条单独的信息可以被共同的解读。”[2]
《你没法把钱带进你的坟墓》(You can't drag you money into the grave with you - 1990)呈现给观众的只有一双崭新的黑皮鞋,还有在画面的四角一中心这五个点位布置着的五组文字,即画题所示的对皮鞋的主人的冰冷而严酷的警告:“你没法把钱带进你的坟墓”。构成对话的主体均不在场,只有代表金钱和欲望(或带走之冲动)的皮鞋和(也许是)代表坟墓的荒地以及空寂的世界在场。这是普通的、受压制的平民对为富不仁的财阀和权贵势力的挑战,或者说,是普通民众对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富人阶层的鞭笞。这里的“你”其实也是作为他者的“你们”,是不得不接受“我们”的鄙视和批判的“你们”或“他们”。因此,在这里,与在克鲁格的其他作品中一样,这些人称代词充当着一种具有高度认同性和组织性的力量。所有观众,无论贫富,都将在对“你或你们”的仇视中聚合起来,形成一个同仇敌忾的“身份”共同体。
《买我吧我会改变你的生活》显然是对媒体广告的戏拟和讽刺。“我”代表的不只是一件儿童玩具,“买我”也不只是买某件商品,而是代表宏观意义上的消费指令,而且是带有规训性或强制性(而不是规劝性)的消费指令。因此,参照《我消费故我在》(I shop therefore I am, 1987),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这个作品的内涵。在这个购物化生存的时代,《买我吧我会改变你的生活》代表了一切广告对待消费者的通用方式:包含着某种带有恫吓意味的幸福的承诺——不买我,你将失去应得的幸福(应有的“改变”)。画面的布局极为巧妙:大张着嘴巴的唐老鸭,用夸张的声音,以逗儿童的方式,拖长声音劝告那些被严重低龄化(或弱智化)的顺从而乖巧的观众:“买我吧我会改变你的生活”。“买我”面对的是“你们”,“你们”来买“我”,而这里的“我”,对这里的“你们”,即站在面前的观众而言,又变为“他或他们”、“它或它们”。在此,消费不仅变成一种幸福的许诺,也是一种软性的控制或温柔的陷阱。在这一过程中,媒体扮演了重要的但是并不是那么光彩的角色。克鲁格从正面劝诱的方式设置这么一个广告语,显然是以正话反说的方式,对无处不在的商业谎言和陷阱发出警告:“我们不要你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因此不会跳入“你”为“我们”挖下的陷阱。
值得注意的是,克鲁格的有些作品,其所指并不很清晰。比如《我是无名之辈! 你是谁?你也是无名之辈吗?》引用了美国19世纪末著名女诗人迪金森的同名作品。这里的“我”和“你”很难定义。但是,它能够引起观众的深思:“有名之辈如何”?“无名之辈”又当如何?难道我们整个社会不是由成千上万的“无名之辈”构成的吗?在“你”和“我”的比较之下,观众陷入了关于“你是谁”的思考之中,陷入了寻找社会认同的紧迫感之中。
《你永远不会从这个美梦中醒来》(You Will Never Wake Up from this Beautiful Dream2006)“你”指的是谁?“谁”在做梦?为什么要做梦?做的是什么样的美梦?“你”该不该做梦?做了“梦”该不该醒?你是否应该并且已经到了“梦醒时分”?很明显,“你”所指不明,令人困惑,正因为令人困惑,作品就起到了引人反思,促人自审的效果。
《恶心你们,我们愉快》(It's our pleasure to disgust you,1991),这里的“我们”和“你们”既具有矛盾性,也具有交互性,“我们”和“你们”处于敌对位置,那么谁是“你们”?观众会在“我们”和“你们”之间作出两难选择:因为权力是“我们”的时候,观众愿意选择“你们”的角色,当“我们”是“我们”的时候,观众显然更愿意选择“我们”。前面提到的1991年克鲁格在纽约玛丽.布恩美术馆举办的个展中,大厅的地面整体由这样一些文字所覆盖:“所有在你之下的人似乎在和你说啥。所有看起来是聋子的在听你说啥。所有似乎是哑巴的知道你在想啥。所有似乎是瞎子的看透了你的心。”在这里,“在你之下的人”、“聋子”、“哑巴”、“瞎子”四类处于弱势的群体和处于强势地位的“你”构成对话的两端,观众一走进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一段文字。因此,观众最初认同的角色,很可能是“你”的角色,而后在经过思索之后,可能再转换为“在你之下的人”、“聋子”、“哑巴”、“瞎子”这样的角色,变成鲍德里亚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虽然如此,他们当然并不甘心于被视为眼瞎、耳聋、嘴哑、地位低下人,可以被随意用谎言欺骗、用强权压迫的人。恰恰相反,克鲁格想要警告作为权力阶层的“你”,不管是你们认为的是“在你之下的人”、“聋子”,还是“哑巴”或“瞎子”,他们其实都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且思维敏捷、辩才无碍。谎言也好,强权也好,狡辩也好,在他们面前,全都避免不了一触即溃的命运。
克鲁格的艺术,无论是平面作品,还是装置作品,在艺术上都产生了巨大的突破。这种突破不仅表现在前面所说的作品的尺度和呈现以及传播形式上,还表现在艺术的接受和鉴赏方面。虽然,现代主义艺术之后的艺术,在审美接受和鉴赏方面,已经大大地突破了和谐,走向了非和谐的审美体验。但是,在艺术鉴赏的冲突性、紧张性和哲理性方面,很少有艺术家能够达到克鲁格这样的强度和高度。欣赏她的作品,观众不仅常常会有一种心理上的违和之感,甚至有时候会引发一种羞辱之感,遭受鞭笞和锤击之感,甚至产生所谓的眩晕和呕吐之感。曾经有研究传统艺术和现代主义在审美效果上的区别的心理学家指出,现代主义的艺术鉴赏在背弃了和谐主义美学之后,把观众引向了反和谐的焦虑和心理动荡之中,反应强烈者会产生神经紧张,痉挛,甚至引发孕妇流产。我不敢说克鲁格的作品会产生如此强烈的负面效果,但是,她的作品在调动观众积极思考,促使观众展开身份认同,从而坚决抗争社会不公方面,是很多艺术家所无法企及的。
鲍德里亚在谈摄影时,曾经对艺术家罗斯科(Rothko)关于艺术作品的论述大加赞赏。他说,罗斯科“认为,作品,就是那种使客体(object对象)和凝视,使图像和凝视走向对抗的东西…这是一种游戏……游戏就是一场对决。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不是一个反射或折射的问题,而同时是一个删除各自的极性和双重性的问题。”[10]又说:“我们在思考世界,不过是因为世界在思考我们吧?在图像中,我发现了同样的可逆性:客体(object)在思考我们,惊吓我们,走它自己的路。”[10]
鲍德里亚的这些评价也适合于克鲁格的作品。观众走进美术馆或者在大街上凝视克鲁格的作品,克鲁格的作品也在凝视观众。观众在思考克鲁格的作品,克鲁格的作品也在思考观众。观众和克鲁格的作品玩着游戏,也展开着对决。克鲁格的作品虽然没有像克雷格.欧文斯所说的可以用凝视将观者石化的可怕的美杜莎效应[11],却足以使观众在阅读和欣赏克鲁格作品时产生身份焦虑、价值焦虑和文化认同的焦虑,从而陷入尴尬之境。
克鲁格作品的力量,在于其洞悉人情,体察世态,感时忧世,不畏权势;在于其敢于为弱者立言,向强权宣战;在于其非凡的智慧、胆量和气势。克鲁格的作品产生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对中国当下的艺术创作乃至社会改革来说,这些作品无疑具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启示意义。
[1]Barbara Kruger: back to the Futura http://www. dazeddigital.com/artsandculture/article/33251/1/barbarakruger-interview-2016-pop-culture-reality-tv
[2]Barbara Kruger,Gary Genosko,ed.,The Uncollecte Baudrillard,SAGE Publications,2001,PP.134-137.
[3]Jean Baudrillard,Bernard Schutze an Caroline Schutze,trans., The Ecstasy o Communication,Semiotex(e),2012.
[4]Victoria Grace , Baudrillard's Challenge: A Feminis Reading , Routledge,2000, P.73.
[5]Jean Baudrillar,Seduction, Brian Singer,trans.,Montréal:New World perspectives,1990,P.6.
[6]Jean Baudrillard,The Perfect Crime, Chris Turne Verso, trans., 1996,P.118.
[7]Jean Baudrillar,Seduction,trans. Brian Singer,Montréal:New World perspectives,1990, P.8.
[8]The Baudrillard Dictionary, Richard G. Smith,ed.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0,PP.72-74.
[9]Rex Butler. The Defence of The Real,London:Sage Publication,1999,P.72.
[10]Jean Baudrillard,Fragments,Conversation wit Francois L’Yvonner, Chris Turner,trans.,Routledge,2004,P.85.
[11]Craig Owens,“The Medusa Effect, or Th Spectacular Ruse,” Craig Owens, Beyond Recogniation Representation, Power, and Culture,Berkeley: Universit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责任编辑:夏燕靖)
J023
A
1008-9675(2017)03-0011-09
2017-02-10
万书元(1956-),男,湖北仙桃人,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鲍德里亚的艺术哲学研究”(14BZ111)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