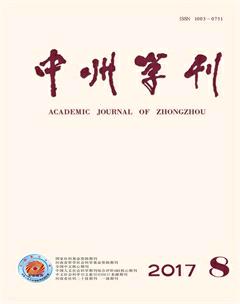刚柔与中国古代的身道
摘 要:正如《周易》以“刚柔”来指称阴阳那样,“刚柔”无疑是中国哲学极为始原也极为重要的概念。然而,要对“刚柔”思想有真正的认识,就在明确“刚柔”的触觉的“身体觉”性质的同时,必须“刚”与“伸”对应,“柔”与“屈”对应,最终回到亦屈亦伸的身体。正是在亦屈亦伸的身体里隐含着“刚柔”的真正秘密,才使以刚柔立本的《周易》推出“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的命题,在屈伸的相感之中发现了生命生生不息的真谛;才使中医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八纲”得以实际的成立,其中的每一纲都可视为亦屈亦伸的身道的生动展示;才使中国哲学在身的屈伸的亦此亦彼、莫得其偶之中消解了人类哲学的种种二分对立,并标志着与思维的“同一律”法则不同的身觉的“感通律”法则在理论上的真正挺立。
关键词:刚柔;触觉;身体的屈伸;感通律;中国哲学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3-0751(2017)08-0099-08
刚柔范畴,就其往往与阴阳相接和并称而言,无疑是中国哲学的极为核心的概念。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其“形而下”的性质而始终难入哲学家真正的法眼。下面,笔者将不揣冒昧地从触觉理论切入,对刚柔范畴给予一种全新的思理的探究,以正其哲学视听,使其久掩的真相和内隐的深义如拨云见月般地得以如如呈现。
一、作为阴阳原型的刚柔
一如主张“切问而近思”的《论语》、提出“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的《中庸》所言,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是一种“下学而上达”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决定了一旦我们要对“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阴阳之道”的真正所指给予探究,就会发现,这种形上之道看似远在天边,实则近在眼前,它就发端于我们至为直觉、亲身可感的触觉触感①,或更确切地说,刚柔的触觉触感。“刚柔者,立本者也”,一如《易经》所言,正是这种触觉触感的刚柔,作为阴阳概念的原型,以“立本而道生”的方式,为我们揭示出了玄之又玄、扑朔迷离的阴阳的真正答案。
为了说明这一点,对阴阳概念的追本溯源的考古学的考查在所难免。众所周知,究其起点,中国古老的阴阳概念最早可追溯至《周易》,具体地说,可以追溯至《周易》的阴阳两爻。而易学史的研究发现,最初的阴阳两爻并非今人所看到的“—”和“--”这一符号形式,而是“—”与“∧”这一符号形式。据易学家的解读,后者之所以取“—”与“∧”形,乃在于占卜时取一小直段蓍草“—”以示其刚性,另取一小段蓍草折弯成“∧”以示其柔性,故“—”称刚爻,“∧”称柔爻,只是殆至战国始,才有了阴阳爻之称。这一点在文物发掘、考古发现中也得以印证。2001年长安西仁村西周窑址出土陶拍,其上的柔爻已有“∧”。即使在阜阳双古堆西汉竹简《周易》中,依然可以看到《易》初创时的“∧”形,这可视为古老的符号形式的遗存。这一切,恰恰就是《说卦传》里的“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后来,由于新鲜的蓍草易折成“∧”形,陈旧的干蓍草或其他代用品折弯时折点可能出现断裂,筮人照此画下来,刻写到竹简上就成了“八”形,“八”被拉平成“--”。至此,卦画符号就由刚柔(— ∧)的形式转变成阴阳(— --)的形式了。②
故无论是徐复观还是小野泽精一,均提出了刚柔早于阴阳的观点。这种观点不仅可见之于《易传》的《彖传》和《小象传》中,后世所谓阴爻阳爻统统以“刚柔”称之,还可见之于小野泽精一的统计。按小野泽精一的详尽统计,就整个《易传》(十翼)而言,“刚柔”在《彖传》《小象传》中出现的次数占“刚柔”概念在《易传》中出现次数的64%。另外,“刚柔”出现的频率数要远远多于“阴阳”出现的频率数(而且集中在《彖传》《小象》之中),考虑到《彖传》《小象传》最古老(成立于先秦),《系辞传》《文言传》继之(成立于秦汉之际),《大象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最后(成立于前汉末期),由此可以得出的是,一部《易传》史表明,“是发端于《小象》《彖传》的刚柔思想,进而为《系辞传》、《文言传》的阴阳思想,最后被阴阳思想所归纳取代”③。
此外,作为“原型”的“刚柔”除了指示两爻爻性外,还用来表达爻位。例如,关于刚柔当位说,有《彖传》中的“刚柔正而位当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关于刚柔应位说,有《彖传》中的“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关于刚柔得中说,有《彖传》中的“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柔丽乎中正,故亨”;关于刚柔承乘说,有《彖传》中的“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样,刚柔不仅规定了两爻的爻义,也规定了六爻位的位义,从而标志着以刚柔为基和“易六位而成章”的系统完整的《周易》体系的真正确立。虽然在《彖传》中刚柔主要是就两爻而言的,但实际上其不仅指爻象,也指卦象,如《彖传》所谓的“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后世解易者皆以为刚柔分别指内卦震和外卦兑。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其说是与刚柔乃为阴阳两爻原型之说相悖,不如说是以“两仪”衍生“八卦”的方式表明了刚柔概念向宇宙论的延伸和扩展,从而使“刚柔原型说”更加颠扑不破,而这正是后来的《系辞传》的作者所做的一大工作。④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殆至汉的来临,这种在易学中几乎自成一统的刚柔思想开始全面退隐,取而代之的是阴阳思想的盛行。按小野泽精一的观点,这种此消而彼长,除了表现为从此解易的话语业已完全阴阳化了之外,还表现为集阴阳思想之大成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思想的形成。无独有偶的是,这种新的思想态势恰与“三纲”说的出现形成互为呼应之势。关于“纲”,《尚书·盘庚》谓“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吕氏春秋·用民》谓“壹引其纲,万目皆张”。故与“三纲”合流的“阴阳”之于《周易》的“刚柔”的取代,与其说是名称的改变,不如说是把握事物的方式的改变。也即从具体的、复杂的、相济的“以身体之”的触觉方式,向抽象的、教条的、归一的“以思知之”的知觉方式的改变。与这种改变相伴的,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去魅化”时代的真正开显,还有中国思想上“阳尊阴卑”之于“刚柔相济”的不无诡谲的偷换。
二、从触觉的刚柔到身体的屈伸
一旦论及刚柔,我们就会发现,刚柔并非属于由物自身所决定的“第一性质”的物质属性,而是属于由感觉所决定的“第二性质”的触觉属性。进而,一旦我们再对触觉属性进行分析,其得出的结果必然是:这种触觉作为“身体觉”,是与我们的身体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
故正如佛教“六根说”中将“触根”视为“身根”一样,现代哲学家胡塞尔也提出了“躯体本身只能原初地在触觉中以及在一切以触觉感觉定位者中被构成”⑤的命题。换言之,对于胡塞尔来说,具有触觉双重性“现象学的构成”决定了,一方面,身体构成触觉;另一方面,触觉亦与之相应地构成身体,构成胡塞尔所例举的冷暖的身体、痛苦的身体,乃至可进一步构成更为直接也更为根本的为中国古人所强调的刚柔的身体。这种刚柔的身体,与其说如同《释名》训柔为肉、训坚为骨那样体现为“骨肉”之身,不如说以即用显体的方式,体现为功用上的“曲伸”之身。在这里,如果说以其积极进取、一往无前而言,“伸”指向了“刚”的话,那么,以其消极顺受、一味退让而言,“屈”则指向了柔。唯其如此,才使帛书《衷》引孔子语曰“曲句焉柔,正直焉刚”,也即在中国古代哲学词典中,刚柔不过是屈伸的代称。在老子那里,其以柔克刚谈论的恰恰就是以屈求伸;在太极拳那里,其刚柔相济的一招一式展示的不过是《拳经》里的“纵放屈伸”。这样说来,中国哲学的“以刚柔为本”实际上是“以屈伸为本”,身体的屈伸最终成为作为身道的中国哲学的至为根本的规定。
“刚健有为”的中国文化精神,决定了中国古人极其强调以“伸”训“身”的身体之伸,而这一点恰与现代身体哲学家南希以身之“触”解“身”、又以“扩展”(extending)解“触”的思想互为呼应。与此同时,“刚柔相济”又决定了中国古人并非仅仅就“伸”而言“伸”,而是就“屈”而言“伸”,就“屈”与“伸”的“之间”而言“伸”,就“屈”与“伸”的往复循环、物极必反的关系而言“伸”,从而使“伸”变为“以屈求伸”“随屈就伸”之“伸”。这样,正如南希从身体相互“折叠”(folding)与“扩展”(extending)的双重结构最终走向“张力”(tension)之身,并由此使身内蕴的“生命力”得以真正彰显那样⑥,中国古人也从身的亦屈亦伸之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从中国的“身”字本身谈起。在古汉语中,“身”字也即“躬”字,如《诗经·大雅·烝民》中“缵戎祖考,王躬是保”的“躬”字所指,和《诗经·邶风·谷风》中“我躬不阅,遑恤我后”的“躬”字所指。而“躬”字以其从“身”从“弓”,表明二者所指深深相契,内在一致。也就是说,古人从“弓”的以驰求张中看到了“以屈求伸”这一身的生命之张力。这说明了太极拳何以有“一身备五弓”之喻,并且太极拳大师认为唯有做到“一身备五弓”,才能使我们的身体调动起内劲猝发、无坚不摧的“弹簧力”;也说明了古人何以对弯弓射箭的“射礼”“射艺”如此的备极顶礼,以至于其不仅将人生命的诞生与射礼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在古“大学”里通过“习射”来体验生命力的真正奥秘。⑦
如果说在“身”(躬)字的亦身亦弓里,我們看到的仅仅是对身的以屈求伸的生命力的一种暗喻的话,那么,在《易传》里,古人则对其阐幽发秘,大书而特书,使之成为大白于世的明晓的真理。故与此相关的,《周易》提出了“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的命题。此处的“屈信相感”也即“屈伸相感”,而此处的“利生”也即有利于生命力。值得一提的是,有解易者从“咸”卦九四的“贞吉悔亡”出发,将“利生”解读为“利”或“利益”的产生。后者的解读实际上是颇值得商议的。因为,《易传》中,把“屈伸”与“生命力”相关联的表述并非仅此一处,而是多处可见。如《系辞上》提出“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在这段极富身体的“性联想”的文字中,显然,其“专”、其“翕”与“屈”相应,其“直”、其“辟”与“伸”相应,而其无论“大生”还是“广生”显然都可视为对蓬勃而强劲的“生命力”的指称。其实,岂止在这里,甚至可以说整个《周易》都是以“屈伸相感而利生”这一命题为其主旋律和基本规律的,从而才有《序卦传》里的“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物不可以终动,故受之以《艮》”,“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等等,这些卦的联袂而次第的推出。否则的话,将不是屈伸之间的生生不息、自强不已,而是伸的无所不用其极的“亢龙有悔”“晋角之躁”“羝羊触藩”的悲惨的命运在等着你。因此,《宋论》中有“屈而能伸者,唯其势也”。一如王夫之所云,《周易》的屈伸之间的生命力的概念,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法国著名汉学家余莲所强调、所高标的作为中国哲学核心概念的“势”,因为他所指出的势的“组合之中起作用的潜势状态,机能运作的两极性、交替作用的趋势”⑧这一特质,不正可看作是对屈伸之间的生命力性质的精准表述吗?
这一切,把我们带向了中国古人的“神”的概念。虽然,作为一个无神论的国度,中华民族似乎对“神”“敬而远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如其他民族一样对“神”给予肯定并极尽顶礼膜拜之能事。然而,这里的“神”既非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第一因”的神,又非其实质主义的“终极实体”的神,而是《管子》里的“有神自在身”的神,身的以屈求伸的充满生命张力的神,作为无限潜能和极富“大生机”的神。唯其如此,才有了《朱子语录》里的“神,伸也”,《说文》里的“申,神也”,而后者的“申”字作为“伸”的原型,在甲骨文中取象“交媾”,引申为“繁殖”,其“生生”之义表露无遗。唯其如此,才有了《说卦传》里的“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说文》里的“神,天神引出万物也”,《系辞上》里的“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知几其神乎”;并且才使中医著作《医学入门》里提出“神者气血所化生之本也,万物由之盛长”,从中不仅孕生出“神机”一词,而且还以其“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的主张,使“神机”切切实实地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神”既然被哲学视为至高无上、至为根本的东西,同时又是以生命力为其内核,那么这使中国哲学最终通向的是一个“能”的世界,使中国哲学实质上与其说是一种观念论意义上的“表象优选”的学说,不如说是一种热力学意义上的“能量经济”的学说。如果说前者更多关注的是“形下”与“形上”之间如何取舍的话,那么,后者则更多关注的是我们自身的生命能量如何产生、维系、代谢、交换的法则。从这种“能量经济学”中,不仅产生了以太阳为其象征的“乾元”之说,“寒暑相推”的宇宙之说,作为“能量流”的“气”之说,以及所谓“圣人成能”的圣人之说,还有中医著作《类经附翼》中所谓“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的生命温补之说。故唯有将中国哲学定位于一种“能”的学说,我们才能了解扑朔迷离的中国哲学究竟是何物,才能使中国哲学之谜得以真正破解。因此,当尼采主义者巴塔耶基于尼采的“强力意志”和“燃烧的生命”,从物的“商品经济”走向生命的“能量经济”,并宣称借此使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业已实现的时候,殊不知这场革命早在中国古人那里已经着其先鞭了,并且以其涉猎之广泛、内容之丰富以及思想之深刻而比巴塔耶的观点更为经典,也更具典范。
三、身的屈伸与中医的“八纲”
如果说在《周易》中身体还尚以种种卦象的形式登场的话,那么,在中医理论中身体则成为我们直接照面的对象。故唯有在中医中身体的曲伸之道才进一步地得以真正确切的彰显。为了说明这一点,就不能不涉及中医的“八纲辨证”“八纲论治”的“八纲”,也即所谓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这“八纲”。而一旦涉及这“八纲”,我们就会发现,无论其中的任何一纲实际上都可视为身体的曲伸之道的具体体现和进一步的伸张。
在此“八纲”中,“阴阳”显然为其纲中之纲。何为“阴阳”,帛书《黄帝四经·称经》答曰:“伸者阳而屈者阴。”在这里,“阴阳”直接被解读为“屈伸”。如若你认为这种解读不是简单而武断的话,那么,正如《传忠录·明理》中张景岳的“阴阳既明,则表与里对,虚与实对,寒与热对。明此六变,明此阴阳”这一观点所指出的那样,对“阴阳”的变式的表里、寒热、虚实的一一考查将使我们发现,这一解读的确是极其准确的不刊之论。
首先,“表里”是从显现形态上对身体“屈伸”的表明。一方面,“表”是身的由内向外的扩展的“伸”的产物,“里”是身的由外向里的收缩的“屈”的结果。另一方面,屈伸的互为前提、互为依据又决定了真正的表里也必然是互为表里的。而这种互为表里恰恰可以与南希的“正是通过我皮肤我才接触到我自身,并且我从外在接触我自身,我并非从内在接触我自身”⑨之说对接。唯其如此,才使中医宣称的“有诸内必形诸外”“视其外应,知其内藏”,以“黑箱”式的辨证与西医的“白箱”式的诊断形成鲜明对比。唯其如此,才使中医基于“里证出表,表证入里”,提出了“里证表治,表证里治”的施治之术,而令那种拘泥于“外科”“内科”之别的西医分科治疗相形见绌。
其次,“寒热”则是从能量界限上对身体“屈伸”的表明。既然身的屈伸之间的张力导致了生命力也即生命能的产生,那么,身的屈伸实际上就与热能的产生、变化息息相通。如果说高能量的“热”指向了身体的“伸”的话,那么低能量的“寒”则可视为身体的“屈”的指称。同时,正如身之屈与身之伸之间可以相互生成、相互转化那样,中医的寒与热之间的关系亦如此。中医主张寒热之间也可以相互生成、相互转化,如《素问》里就有“寒极生热,热极生寒”,“重寒則热,重热则寒”,“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治寒以热,治热以寒”。寒热作为中医医道的纲领,从中不仅产生了“五脏各有寒热论”的生理理论,产生了“万病皆须分寒热论”的病理理论,还以其药性之寒热的区分,使“寒热型”的药理理论成为可能。故,一方面,中医凭借提供生命能源的“命门之火”的揭示和提撕而成为一种东方古典的“热力学”的理论;但另一方面,该理论又不同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规定。如果说该定律使生命自身作为一种封闭的系统最终通向无生的世界的话,那么中医则如同梅洛-庞蒂所说,“因为我的身体能拒绝世界进入,所以我的身体也能使我向世界开放”⑩,在生命自身的亦合亦开(也即身的亦屈亦伸)的动态开放系统之中,生命得以热极生寒和寒极生热,并使自身最终通向寒暑相推的生生不息的世界。
最后,让我们再来看看“八纲”中的“虚实”。应该承认,在中医的“八纲”中,“虚实”也许是最具争议、最富歧义的一对概念。关于其真正定义,几千年来论者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医家或以正气之盛衰分虚实,或以邪盛正衰分虚实,或以气血分虚实,或以寒热分虚实,或以壅陷分虚实,或以顺逆分虚实,或以动静分虚实,或直接以病与不病分虚实。这种虚实概念如此含混不清,不仅有碍于“八纲”之分的合理性,也由此使中医整个理论体系备受“科学人士”的诟病。
值此虚实概念亟待正名之际,当今的李燕翀等学者所提出的观点以其鞭辟入里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们直接从中医经典出发指出,所谓虚者,是指气的退出;所谓实者,是指气的进入。在他们看来,这一定义不仅完全忠实于《黄帝内经》中的“夫实者,气入也;虚者,气出也。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之义,也与《难经》四十八难的“病之虚实者,出者为虚,入者为实”相契合,还与《难经集注》的“阴阳者,主其内外,今阳不足,阴出乘之,在内俱阴,故知出者为虚也。阴不足,阳入乘之,在外俱阳,故知入者为实也”的解读相契为一。?
需要补充的是,要使这种虚实观真正得以成立,还有待于对这种出入的“气”为何物给予解读。实际上,“气”对外人来说看似虚无缥缈,但在中国哲学中却是最为实质性的,它就是一种堪称“能量流”的东西。?正是这种“能量流”,才一如王夫之所说“盖气者,吾身之于天下相接者也”,使吾身真正成为一种可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的开放系统。也正是这种“能量流”,才一如《内经》“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所指,使气的出入的虚实与能的多寡的寒热可以相提并论。这样,与寒热之于屈伸的对应一致,气的出入就导致了虚实与屈伸之间的对应。但凡气的自内而外的出作为身体能量的耗损、不足,就显然表明了其为身体之屈;反之,但凡气的自外而内的入作为身体能量的扩充、有余,则显然表明了其为身体之伸。进而,正如身体的屈伸的相互转换决定了中医提出“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之说那样,这种身体的屈伸的相互转换,也决定了中医以“至虚有盛候,大实有羸状”“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立论。但是,虚实与寒热之间的一致之处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二者之间的不同。这种不同表现为,如果说寒热更多强调的是身体生命能量在度量上的高低的话,那么,虚实则更多强调的是身体生命能量在取向上的流向。这种亦出亦入的流向具有非线性的、可逆的特征,可视为生命开放系统所特有的“自组织”性质的真正的彰显和弘扬。
依此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在中医“八纲辨证”中,往往位处其后的“虚实”之纲是“表里”“寒热”之纲的集大成者,它既可以就其“出入内外”而囊括“表里”,又可以就其“虚寒实热”而统摄“寒热”。无怪乎《内经》称“百病之生,皆有虚实”,“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其不仅将虚实视为百病之源,甚至将虚实与“神机”的变化等量齐观。于是,“虚实”毋宁可视为纲中之纲的“阴阳”的集中体现。这说明了中医何以有“虚实,人之阴阳消长也”之称,也说明了何以有作为中国哲学之“原符”“原型”的“阴阳太极图”的产生。如果说该图的黑白相间的黑白是虚实相生的虚实的表示的话,那么,贯穿全图的“S”路线恰恰是身的以屈求伸的生命运动之道的申明,从而为《周易》的“屈伸相感而利生焉”之说提供了鲜明的象征。
四、一种中国式的普遍的“感通律”的推出
既然刚柔可近取诸身为身的屈伸,并且这种身的屈伸也即身之屈与身之伸的互为前提,那么,这就意味着恰如梅洛-庞蒂所说的“回到身体就是走出身体”,也意味着身体的自身化与非自身化的同时发生。这样,恰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身体的同时发生与身体触觉的“双重统握”之间的一种重叠、偶合、相通。所谓身体触觉的“双重统握”是指,我们的触觉既是对外在对象的触,又是对触者自身的触,以至于我们很难从中区分何者是触,何者是被触,何者是能动,何者是受动;以至于中西方哲学中冥顽不化的主客二分业已荡然无存,存在的仅仅是主客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主体性”。?
正如笔者多次指出的那样,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表述,这种触觉的双重统握就是以《周易》的“咸”卦为“典型范例”,为中国哲学所大力阐发的此感彼应、感而遂通的“感应”。耐人寻味的是,《周易》咸卦的咸字,在马王堆帛书中作“钦”,“钦”通“针”,故“咸”含针石术之义。?这使触觉的双重统握(也即感应)在中医里表现得尤为真切、显豁。
首先,在中医诊断学上,触觉的双重统握的感应得到有力体现。其之所以如《内经》所主张的那样倚重触觉的脉诊,而非像西医那样求助于视觉的“透视仪”,并且之所以如《三国志·魏志》中记载的那样“治其病,手脉之候,其验若神”,也即脉诊对疾病的把握料事如神,就在于触觉的脉诊所具有的触觉双重统握的感应。正是这种感应,才以其“互主体性”的性质,使脉诊的诊断与其说是对患者生命的反映,不如说也是医患双方生命的触类旁通。也正是这种感应,才使得程子宣称“切脉最可体仁”,才在医者与患者的“一体之仁”中,使双方的生命相感,息息相通,以至于可使中医诊断臻至那种不可语会只能神交的“观其冥冥”的化境。故中医的医生恰如梅洛-庞蒂笔下的“将身体借给世界”的画家。画家唯有将自己的身体借给世界,才能把世界变成如身体般生动的绘画;同理,医生唯有将自己身体的感觉投身于患者,才能使患者的身体实现从“物体”的客体向“活体”的主体的转化。因此,触觉的双重统握的感应以其亦客亦主的“模棱两可”的性质决定了,试图将中医脉诊的任何完全“客观化”的努力都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中医的“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的说法,以及近代以来各种脉象仪的发明最终都无疾而终的事实,无一不是这一点的明证。
其次,在中医生理学上,触觉的双重统握的感应同样得到有力体现。所不同的是,如果说在中医诊断学上该感应主要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话,那么,在中医的生理学上它则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之间。如《素问》里有“人与天地相参”,“盖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灵枢》里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这种坚持“人之常数”也即“天之常数”的“天人相应”,坚持人与自然互为因果的“肉身辩证法”,既可视为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具体体现,又不失为梅洛-庞蒂的人与自然“交织”的身体概念最早的发端。这样,正如南希基于这种“交织”把身体理解为一个“开放”的系统那样,中医亦基于这种“天人合一”推出了一种“交通”的理论。人们看到,从这种“交通”出发,一方面,中医坚持表里的内外通、寒热的能量通、虚实的出入通,使生命成为一种人与自然间的“无之不通”的系统;另一方面,中医与王夫之的“盖气者,吾身之于天下相接者也”主张相应,使无往而不入、“一气之流行”的“气”及“气化”思想得以空前的形成和应用,并标志着一种不同于西医解剖学“肉身”生命的中医经络学“灵枢”生命的系统论体系的正式奠定。
再次,在中医病理学上,触觉的双重统握的感应也成为其理论的不二法门。为了说明这一点,就必须涉及中医对邪正关系的理解。也就是说,中医虽然极其重视“为外所因”,即由自然界的寒暑燥湿风热所引起的所谓“六邪”(“六淫”)之“邪”,认为它是导致我们生理紊乱、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医无视健康的肌体在“抗邪”中所固有的重要作用,而是在正视外之“邪”的同时,也强调内之“正”的不可或缺性。正如《素问》提出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清净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金匮要略》提出的“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难经》提出的“旺者不受邪”。凡此种种,不仅使在“气质”“禀赋”名下的“体质理论”在中医中得以凸显,也使体质的强弱被中医视为患者病情轻重考量的最重要的变量。因此,在病理学上,如果说西医把疾病的发生更多视为某种异己的致病因子單一决定的产物的话,那么,中医则把疾病的发生视为身体自身正、邪之间互为因果、互为消长的结果,乃至把《释名》中“病,并也,并与正气在肤体中也”这一信条奉为中医理论的至上圭臬。这意味着,在真正意义上的中医那里,是不可能像西医那样有着“病人”与“健康人”之分,每一个人都可以以其亦邪亦正而使自己跻身于“众生平等”的众生之列。进而也意味着,一种“邪不可干”的“正气”的固有,使中医的身体实际上“自性圆满”地成为一种典型的自组、自完善、自修复的“自组织系统”,使每一个人都可成为自己生命的真正主人。故中医理论开出了“依自不依他”的中国哲学精神的先声之鸣,并以一种为中国哲学所特有的生理、伦理相统一的方式,使儒家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的主张成为真正的生命可能。
最后,在中医治疗学上,这种触觉的双重统握的感应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它使中医的治术既讲药物干预,又讲养性移情;既讲去邪,又讲扶正;既讲养形,又讲养神;既讲外练“筋、骨、皮”,又讲内练“精、气、神”。这一切,都可视为中医的“天人合一”之旨在其治疗学上的反映。同时,也正是基于这种“天人合一”思想,才使中医在治疗学上还推出了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这一特有的理论。关于因时制宜,中医有自己的主张,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强调“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王冰主张“春食凉,夏食寒,以养于阳;秋食温,冬食热,以养于阴”。而关于因地制宜,中医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如《素问》提出“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曰:地势使然也”,“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正是基于“天人合一”观点,才使中医在治疗学上有“药食同源”的原则。这种“药食同源”,正如《内经·太素》所载的那样,“食养正气,药以攻邪”,“食借药之力,药助食之功”,“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从而指出了二者作为“生命能”的摄取和提供,都可以使我们生命“增益其所不能”。而一旦我们把治疗视为生命的“增益其所不能”,那么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作为“支持医学”的中医与作为“对抗医学”的西医的迥然有别,还有“上工治未病”理所应当地被视为中医的无上的圭臬。也就是说,中医更多看重的是“扶正”而不是“去邪”,是“养生”而不是“医治”;更多体现的是“防患于未然”的“预防医学”,而不是“亡羊补牢”的“疗癒医学”。这一点与中医的“正气在内,邪不可干”的病理学思想不谋而合,也与今天的基于“自组织”和“生命全息”的“大医学”思想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周易》“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一语所示,触觉的双重统握的感应除了体现在我们最为切己的自身的身体上外,还体现在作为身体之延伸的世间一切人伦事物之中。例如,在人际关系方面,孟子的“恻隐”,孔子的“恕”,《大学》的“絜矩之道”,儒家的“仁”,戴震的“理”,焦循的“旁通之情”,郭店竹简的“夫不夫,妇不妇,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的“六德”之德,都是这种感应。
显然,就这种人际关系方面的感应而言,一方面,它完全有别于汉儒的“三纲说”所确立的人际关系。因为,如果说“三纲说”更多强调的是一种线性因果的单向决定的人际关系的话,那么,与触觉的双重统握一致,“感应说”则更多力主的是一种互为因果的相互作用的人际关系,以其“互主体性”关系而与“三纲说”的“上尊下卑”关系迥然异趣。另一方面,这种人际关系方面的感应又根本不同于西方伦理学上的“同情说”所坚持的人际关系。固然,由于对“共感”“共情”的强调,这种“同情说”与“感应说”看似不无合辙,但实际上却是形同陌路的。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同情说”从“自我意识”出发,而使我们的趣向我他之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理的归同;与之不同,“感应说”则从“身体间性”出发,一如梅洛-庞蒂所指出的那样,使我们的趣向我他之间“此感彼应,随感随应”的情感的“协同”。?故最终前者是通向“无差别的同一”的“同”的,而后者则是通向“非一非异”的“通”的。“同”与“通”一字之别,实际上却标识出了西方“同情说”与中国“感应说”之间的真正的分水岭。
庄子认为,“道,通为一”?。正如“道”是无所不在的那样,“通”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故“通”不仅体现为天人相通、人我相通,还体现为事物之间的相通。如果说人我相通主要为儒家所津津乐道的话,那么,万物与万物的相通则成为道家的殊胜之论。唯其如此,才使老子如此地强调事物间的相反相成,以至于在他心目中,这种相反相成业已成为一切事物的必然属性。故老子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有无”是这样,其他事物亦如是。例如,老子断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这彻底消解了美丑、善恶二分的“常识”;再如,老子推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命题,以其对祸与福的互倚互藏的强调揭示了“祸福”内蕴的不二之谛。而老子“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则以一种“尽人事以推天道”的方式,把事物的相反相成之理发挥到了极致境地。
庄子“齐物论”的推出,则可视为老子的万物之相反相成的“通道”的进一步的提撕和破译。因为,所谓“齐物”的主旨,就是在万物的“不齐”(相反)之中把握到“齐”(相成)的真谛。故在庄子笔下,“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大小、夭寿的区分已失去了意义;“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美丑的区分同样亦不成立;甚至“庄周梦蝶”的故事中,连梦幻与现实的区分都无从谈起。凡此种种,使庄子得出“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哲学的“祛唯知主义”思想在庄子那里业已臻至登峰造极,而且还意味着在庄子那里,取代区分和对待的知识的,必然是“感而遂通”的“通”的真理。一言以蔽之,庄子认为,“道”与“通”最终化归为一,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
这样,经由庄子的阐发,一种有别于西方“同一律”的中国式的“感通律”就在中国哲学中得以正式确立。這种“感通律”虽大明于庄子,实则深植于“阴阳相感”的《周易》,旁援于“致中和”的《中庸》。方以智所谓庄子乃“《易》风《庸》魂”的观点?对庄子的“感通律”同样成立。也正是这种出入《易》《庸》的钩深致远,才使“感通律”在超越中国哲学种种派系的同时,业已成为最为普遍性的规律。故它实际上不仅适用于事物间的“真”的领域,同时也适用于人际间的“善”的领域,还适用于天人间的“美”的领域,从而作为真正的“大全”规律,令仅仅停留在“求真”一隅的西方的“同一律”瞠乎其后而望尘莫及。
而这种“感通律”的普遍性之所以成立,恰恰在于它是以普遍的身体觉的触觉为其依据的。换言之,正是在触觉这一“感觉之感觉”的“元觉”里,隐含着“感通”之无所不在、无所不适的真正秘密!
注釋
①关于触觉的至为直觉的性质,参见张再林:《论触觉》,《学术研究》2016年第3期。
②以上解读,可参见冯昭仁:《周易的历程》,华龄出版社,2013年,第33—35页。
③[日]小野泽精一:《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与人的观念的发展》,山井涌编,李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8页。
④参见赵法生:《〈易传〉刚柔思想的形成与易学诠释典范的转移》,《文史哲》2014年第1期。
⑤[德]胡塞尔:《现象学的构成研究——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2卷,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4页。
⑥参见张再林:《触觉与中国哲学》,《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⑦参见张再林:《老子的以屈求伸之身道及其体现》,《中州学刊》2016年第11期。
⑧[法]弗朗索瓦·余莲编:《势——中国的效力观》,卓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引言叁。
⑨Jean-Luc Nancy. Corpus,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28.
⑩[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17页。
?李燕翀等:《在中医经典中观“虚实”》,《中华中医药学刊》2001年第5期。
?参见张再林:《从当代身体哲学看中医》中“‘流动的身体与‘气”一节,《周易研究》2016年第6期。
?关于触觉的双重统握,参见张再林:《论触觉》,《学术研究》2017年第3期。
?参见张再林:《从当代身体哲学看中医》,《周易研究》2016年第6期。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76页。
?庄子提出的“道通为一”的“通”字有两解,一者解“通”为副词,一者解“通”为名词。笔者在这里从后解。
?方以智:《向子期与郭子玄书》,《浮山文集后编》影印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Hardness and Softness" and the Body′s Tao of Ancient China
Zhang Zailin
Abstract:As the book of YiJing refers to Yin and Yang as hardness and softness, hardness and softness are undoubtedly the very primary and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 of Chinese philosophy. However, to approach a real understanding of the hardness and softness, we should illustrate the body consciousness of touch of hardness and softness, meanwhile we should correspond the hardnesss to Shen, softness to Qu, and eventually return to the body with both of Qu and Shen. The real secret of hardness and softness lies in the body with both of Qu and Shen and that makes Zhou Yi launch the proposition that Qu and Shen′s interaction is conducive to life and find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Hence the eight principles of Yin and Yang, Biao and Li, Han and Re, Xu and Shi are actually established, and each of the principles can be regarded as a vivid display of the body′s Tao with both Qu and Shen; by the same token, the Chinese philosophy dispels all sorts of binary opposites of human philosophy in the context of both this and that of the body′s Qu and Shen, and it marks that the law of GanTong of body consciousness is established as a theor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law of identity of the thought.
Key words:hardness and softness; touch; Qu and Shen of body; law of GanTong; chinese 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