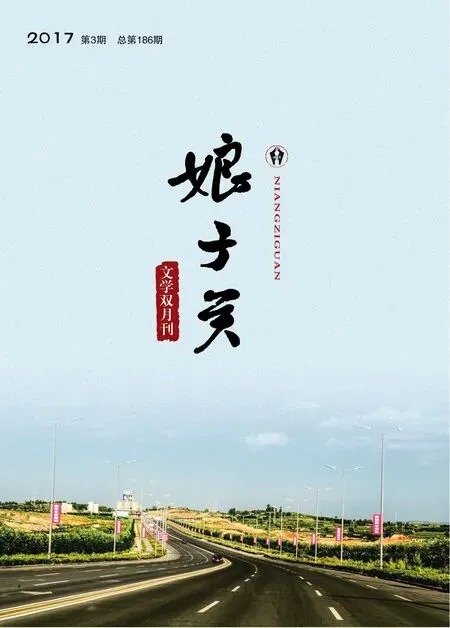骑车子咏叹调
●张行健(临汾)
骑车子咏叹调
●张行健(临汾)

上
我是二十岁的时候才学会骑自行车的。
对于一米七五的身高且貌相老面(貌相苍老与年龄不符)的我来说,确实会得有些迟了。
我的同龄人们无论男女,一个个早在少年时代十二三岁就已经会骑车子了,有的个子矮小坐不到座儿上,左脚蹬在这边的车踏上,右腿便从车梁下掏进去,右脚勾着另一个车踏,小小的屁股因了身子扭曲而歪歪地撅着,右腿的吃力蹬踏使那两瓣小屁股欢快地扭动,人和车子都处于倾斜状态,一边倒的车子却裹挟着一个虾米一样的小人儿,呼呼地在村巷里和场院上疾跑着,这让我惊讶又羡慕,常常呆呆地停下脚步,呆呆地望着远去的小人儿,远去的破车子。
后来才知道,那叫“跨车子”。
我对会“跨车子”的小人儿也心生敬畏。
我自愧不如啊。少年的我细细高高,如同一棵豆芽菜,连跨车子都不会,不是徒有身高么。
一个人细细思谋,过滤一下家族成员:爷爷,那些年已上了七十岁,不会骑车子,可能连自行车都没有摸过。他年轻时,自行车是稀有的,等村里有了车子时,人已年迈,失去了驾驭车子的雄心;奶奶,旧时代的小脚妇女,那个年代的小脚女人是没有会骑车子的;父亲,早年间的大学毕业生,一直在外地当中学教员,他不会骑车子一是缘于生性胆小,根本原因是自尊心强,自己买不起自行车,也低不下架子借朋友和同事的车子学骑;我母亲年轻时身材修长灵巧,也属于很有力气,很能干活的女性,不知什么原因也不会骑车子。我曾了解过她们那个年龄段的人,也有个别妇女会骑的。农业社里农活儿很忙,一年四季上工下工劳作不断,收工回来还要赶着缝衣做饭,对学骑车子就少了兴趣没了精力;小爸力气小个子小又天生的胆量小,不会骑车子纯粹是自身原因;我大姑小我妈七八岁,理应会骑的,可能因为敏感多心,就不愿借人家的。在我的印象里,她像我的父亲母亲爷爷小爸一样,常常是步履匆匆的,迈着快疾而利落的腿脚,穿越在乡村的大小胡同和田地场院之间。
不知是生来的功能还是上苍的眷顾,我家上上下下凡不会骑车子的人,都有特好的腿脚功夫。不敢说是神行太保,但比起一般人来要快捷许多。
从我记事儿起,印象最深的是爷爷的两条腿两只脚,爷爷常年是两种颜色的衣衫:春夏是白色的粗布上衣黑粗布裤子,秋冬是黑色的粗布衣服,鞋子当然四季都是黑色的布鞋。从村巷往田地里走去,爷爷的双脚如同两把乡村的镰刀,急匆匆收割着紧促的日月。他对田地的吃苦和用心是其他农家汉子无法相比的。听老人们说,单干的时候,从家里朝地里的路程也几乎是小跑着奔去的,他不愿意把大好的时光晃悠在漫长的村路上。朝地里挑茅粪那样苦累脏的活计,别家的汉子一上午也就顶多三趟六桶而已,爷爷因了腿脚的麻利动作的快速一上午就能挑六趟十二桶,两大木桶浓稠的茅粪,一百斤的样子,瘦小而结实的爷爷挑在肩上,平稳沉实,双腿双脚快快移动时茅粪担子也随了身体的节拍而稳当地晃动;爷爷的双脚是呈外八字形的,尤其是绑了裤腿挑担快走时,外八字的双脚如同张开的一把剪刀,在乡村的土路上剪裁着永远也干不完的活路。
爷爷走路快疾同他急躁而暴烈的性格有关。大晌午从地里收工回家,洗罢手坐在厅里的方桌边时,奶奶必须及时把煮好调好的干面端到他面前,他呼呼噜噜风卷残云吃两碗面条再喝一碗面汤后,顶多吸两锅子旱烟,又去上工了;如果回到家里才看到奶奶她们和面擀面时,火气一下就顶上脑门,铜锣一样的亮嗓子就当当地敲响,骂做饭的人不能及时把饭做好误了他的下地干活儿……每每这时奶奶或是妈妈婶子们静悄悄一声不吭,带了愧疚的表情加快了做饭的动作。
常常地,去往田地的村路上,乡村的一伙儿老汉们就无意中相随着了,说着田地里的事情拉呱一些生计的零碎,脚步常常就缓慢下来。爷爷有时也在其中,随话答话说笑几句也是常有的事儿。爷爷却受不了老汉们滞涩的步子和悠闲的情状,他尽量让自己的脚步慢一些,以随着老哥儿们几个的节奏,表现出一副合群的样子,忍一忍,再忍一忍,可是不行,他见不得缓慢,不愿意和慢性子的人相处,更不想把大好的光阴磨蹭在村路上。他便迈开外八字的步子,噌噌噌噌走了前去,把众老汉远远甩在后面了。
这样性子急躁脾气暴躁而又不轻易对别人开口的爷爷,在他那个自行车作为稀有物的年代是绝对不会借人家车子学骑并借用的,不会!山村的庄户老汉以种庄稼为本分,闲暇了赶集逢会走亲戚是全凭两只脚板去丈量山路长短的。
父亲走路的快疾也是出了名儿的。
从小就在临汾的三完小读书,之后又上了临汾一中的初中、高中。每到周末,年幼的父亲要步行回到二十五里外的家乡,来回五十里,这是每星期要走的路儿,近十年的中小学时光使他饱尝了艰辛的滋味也练就了他的一副铁一样的脚板,直到考取了山西大学,才结束了每周五十里的“走读”岁月。
不知是常年走路的缘故还是生就的“天足”,父亲的脚板扁平阔大,鞋店里很难买下适合的鞋子,强买下一双三天两天就被脚掌撑得鱼嘴一样裂开口子,所以,结婚前一直穿奶奶做的布鞋,而婚后则一直是母亲给他做鞋。家做的鞋结实耐穿,适合宽大的脚掌脚面,还有一个特点是底子很厚耐磨,对于一个不会骑车而善于步行的人来说,鞋底的厚重是必需的。
分配到蒲县中学教书之后,父亲一年也只有寒暑两个假期回家,汽车到了临汾城后,无论天有多晚,他都要赶夜路回去,怕住店花钱嘛!不同于当年上学时的赶路的是,他有了较沉重的行李,换季的衣物和给爷爷奶奶买一些蒲县的土特产,梨儿核桃糕点之类,这样两个重重的皮包用一条毛巾系起来,一前一后搭在肩上,他依然快疾地走,累了,肩膀麻了,也一定坚持走到沿路的某一个村子边上才会放路边小歇一会儿,自己使着心劲,不到村边不能休息,如周家庄过去孟家庄,孟家庄过去是靳家庄,再兴村、杜村、县底……记得某一个腊月天的深夜父亲背着包裹回来时,厚厚的棉衣已被汗水湿透,那可是西北风呼啸的冬夜!
以后的日子里,临蒲公路一直时通时阻,路况不好时,父亲从蒲城坐车到黑龙关,从黑龙关步行到土门,再从土门搭车坐到临汾城里,中间那段六十里弯曲绵延的山路是父亲宽阔的脚掌走过来的。我在蒲县当代教的第一年麦假,路又不通车了,我与父亲坐车到黑龙关之后,在刘家沟煤矿住了一夜,一清早起来,冒着浓浓的晨雾,也冒着一个小小的风险,我们决定走一次小路,攀爬一次鲜有人走的小山路,即从刘家沟山半山坡钻进山沟,沿河沟进入岔口河,再从土门西涧北的岔口河口出来,计约四十里山路,比原山路近了二十里。烈日当头,炎热无比,一条似路非路时有时无的所谓山路,常常被淹没在一大片山野灌木里,我们每人手拿一条山木棍子,先得把藤条野草拨拉到一边,才能小心着迈动。身子下面的沟涧里,奔腾着野马一样的黄色山洪,污浊的洪流卷着顽石树木野猫死兔朝下游的岔口河冲击而去,而沟畔上的父子俩则顺了河岸艰难行走,口渴了,则蹲下身子,在石头坑的积水里,双手掬起,一捧一捧地喝……十七岁的我,还是能走能跑的小年轻,可我走不过四十岁的父亲,渐渐地,我脚步迟缓地拉后面了,父亲走一截便停下等我,或伸手拉我上陡坡绕岩石……漫长的五六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走出了岔口河,来到东涧北的公路口。
那次跋涉,我真佩服了父亲的脚功,我想大约是凭借了这样的腿脚功夫,父亲是不屑于骑自行车的吧。
同父亲的腿脚走功比较,母亲还要更胜一筹。父亲虽说行走快速,却承袭了爷爷外八字的遗传,速度快却不勉拖带些泥土,常常是裤腿鞋子上要沾些路上的浮尘脏物,自然显出一些吃力;母亲自年轻时就苗条利落,身骨轻巧,一米六三的个子最轻时仅八十斤重,最多时也九十斤出头。据说她少女时最喜欢上树爬树,乡村再高大粗壮的树木她片刻就噌噌上到树梢了,如同一只轻巧灵敏的毛猴儿。
农业社里时,父亲在外地工作,家里就是母亲操持着光景,还要天天下地干活儿,割麦摘花挑粪担水样样活计都拿得下来,活儿干得又快又好。母亲虽瘦,却有好饭量,和小伙子饭量差不多,浑身便有使不完的劲儿且不要说轻装走路儿了,那真是利利落落,快疾如风。我们还年少时,每遇姥姥家有事,母亲左手提着花儿馒,右臂抱着年幼的弟弟或妹妹步行十多里山路到姥姥家,山路上再多的趟土,再多的泥巴,母亲的鞋上裤腿上总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多年后全家住在临汾市内,再遇到姥姥家有事情,而我和弟弟又一时忙碌找不下汽车时,六十多岁的母亲依旧从城市步行到姥姥家,那可是三四十里路程呢,母亲从心里一点也不惧怕,走路,步行,对母亲来说从来都不是负担,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在走路的过程中,母亲能体会到一种回忆与想象的愉悦感吧。
可惜的是,九九年的冬日,母亲晨起给父亲打奶时,被一个骑车飞奔的女学生撞倒了,右腿严重骨折,治疗出院后,落下了小腿部残疾,走路有些跛了,这无疑严重地影响了母亲之后的生活,当然包括走路在内。我就非常奇怪和疑惑,一辈子不会骑车子也很少坐车子的母亲,可以说和自行车无任何缘分,年纪大了却要遭受自行车的碰撞,伤到了直接影响走动的腿部,这是何因又是何果?!
完全是遗传基因的作用吧,我承袭了父亲走路的耐力和柔韧,也全盘接受了母亲走路的快捷与利落,这两大先天优势使我不仅善于走路喜欢走路热爱走路,也具有快速走路的能力。据母亲说,小时到姥姥家时,母亲抱着一岁的妹妹,而六岁的我跟在她身边一直步行十五里山路;九岁那年夏天母亲病了,我一人到姥姥家请姥姥去了,这我记得很清楚,一条窄窄的小土路,两边是茂密的庄稼地,有玉茭、高粱,中间还要翻河里沟和南乔沟,风吹庄禾哗啦啦,我怕呀,几乎一路小跑去了姥姥家,姥姥家无人,她一早从姨姨家去了我家,走岔了。九岁的我又一气跑回来……现在想一下,一个虚岁九岁的娃娃,一上午来回要走三十里山路,胆儿大且莫说,那得能跑动才行,那会儿就在练就着我的走路功夫呢。
后来成了城关学校教工篮球队队长,蒲县一中教工篮球队队员,教育学院中文系篮球队队员,除了爱好篮球,掌握了一点技巧外,主要是腿脚麻利,抢断快速,能跑善跑的特质在起着作用吧。当然这是后话。
还是返回到多年前的有关学骑车子话题吧。
还能因了我家几代人有着快速走路的特点,年少的我就永远不要学骑车子了?
我的三爸,小姑,他们同样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他们居然就会骑车子,为什么?
我曾细细想过,这是人的性格使然,要强的,不服人的个性,使他们在那个自行车奇缺的年代,厚着脸皮,赔着笑脸,蹭一会儿,借一会儿,见缝插针,千方百计学会了骑车。
年少的我想,难道我也要像爷爷父亲他们一样,因内心深处的那一层脆弱的自尊,那一抹只有自己知道的懦弱,就一辈子不骑车子一辈子用双腿快快走路么?
再快的腿脚,能快过轮子飞转的自行车?
快快远去的自行车把一个步行者抛在其后,是代表了现代文明的交通工具,把一个落伍者抛在时代后面了。
年少的我那会儿就这样朦胧且懵懂地想着,学车儿的欲望忽地充满小小胸腔。
机会来了,是邻居会计家来了骑车子的亲戚,亲戚吃饭呢,会计的小儿子就趁了机会推车出院,在附近的小场院里学开了跨车儿。
场院边的我,眼馋地看小家伙跨了一圈儿又一圈儿,小家伙个头矮,起先跨车时,我给他在后面一直稳着车座儿,没有功劳有苦劳,我的苦劳感动了他,终于,学跨累了的他,慷慨地让我学骑两圈儿。
第一圈儿几乎是推着走的,脚踩在脚踏儿上,一用劲儿,车子便倾斜着欲倒;第二圈儿我勇敢了一些,掌握了一些平衡,踩在脚踏上居然能行驶一截儿了。转圈儿时毕竟还紧张,一紧张,车身倾斜,啪——踏——连人带车,倒在场地上……
恰这时会计的女人叫孩娃儿吃饭来到场边,正好看到这一幕,一张胖乎乎的脸盘倏忽间便阴下来,对了他的孩娃儿,指桑骂槐道:
你个小仔儿脸皮可真厚呀,一下的功夫就把人家客人的车子骑到这儿啦,占便宜也不能这么占吧,把车子摔坏算怎么回事儿,是你赔呀还是我赔呀,再说了稀活了光景能给人家赔得起吗?咋就不长一点点人脑子呀……
那时我已有十三四岁,被这一骂脸臊得没处搁,赶快扶起车子快快地离开了场院。
骂话句句如刺,深深刺疼了我的心。
从那会儿起我暗暗发誓再不蹭别人车子借别人车子学骑了,除非将来自己有了钱先买车子再学骑,敏感的心再承受不起别人哪怕一点点的嫌弃和责怪。
中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已经成了身高一米七五的大小伙子,也已经离开故乡到百里之遥的蒲县城关学校当了一名代理教员,先后在李家坡、郑家塬、红旗小学、荆坡学校、蒲县二中、蒲县一中任语文教师。由于环境和身份发生的变化,借用同事的车子学骑一下仅仅是一句话的事情了,同事中毕竟车子很多嘛,对于我高高的个子近二十岁的年纪却连个自行车也不会骑,已经成了私下里大家的一个笑谈,把我不会骑车子的缘由归结为:家庭困难,一时还买不起车子;古板的性格和要强的自尊又不愿借别人的车子;家教过于严格,使得小小年纪成了一个古人一样的做派;性格奇怪,不愿学车子也学不会骑车子……众人猜测云云,我都一笑了之。其实,我心里又有一种想法,这个想法只有我心里清楚,不可说给任何人的。
从七五年到七八年的整整四年代教时光,我遭遇了许多因不会骑车子而带来的尴尬事情,今日想来,仍觉不好意思。
七六年正月里,刚开学吧,那会儿我在城关红旗小学代教,在全联校的一次大会上,联合校长师光荣在布置一次任务时,点名要我第二天一大早骑上他的车子通知河西村的两个教师到联校报名去。师校长布置任务时是前一天的晚上,他以为我会骑车子,按理说第二天一大早骑车子跑十几里地也不算什么事,我那么年轻跑腿儿捎个信是再正常不过了……校长说过后我就听到下面有人在窃笑,哈哈,行健不会骑车子他明早怎么去通知呀……声音很低,我还是拾进了耳朵,听那话音有好笑、嘲弄、看笑话的意思,我装作没听见,第二天起了个大早,洗把脸后一口气跑到了河西村,找到了那两个老师的家,并和他俩一块来到了联校,我们比其他人早到了整整半小时。我就是要做给那个看我笑话儿的人,不会骑车子怎么了?不是照样儿叫来了人!
在荆坡学校教书时,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县城里一爱好文学的杨姓女孩儿专门找到我,谈文学谈电影儿,眼看一下午过去了,天色渐黑,女孩准备回家时,学校校长推来他的自行车,让我送女孩儿回去,荆坡虽在城边,离女孩儿家也有三四里地。校长这一举动很得体也很细心,一是表示了领导对下属的关怀;二是让我和女孩有进一步接触的机会。多好!可是,不争气的我却不会骑车子,一个绝好的对女孩献殷勤的机会无法把握住了。看着杨姓女孩儿明亮多情且期盼的目光,我尴尬之极又难堪之极,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我涨红着脸子,喏喏地嘀咕着自己不会骑车子,干脆步行送女孩儿回去……
女孩惊讶地看着我,觉得这么大个子的年轻人居然不会骑车子,未免太迂腐,太刻板,太不可思议了吧。
在荆坡学校,我教一个中学班的语文,城郊的学生大多年龄稍大,有十五六岁了,个子也一个个杨树一样可劲儿地往高里长,大他们三四岁的我,和学生们相处很好,学生们均来自荆坡大队的五六个自然村,如天家庄、闫家庄、石墩村和十里铺。学生们全会骑车子,来到学校上水灶,下午天黑前才回去,一排高高低低的自行车就存在教室一侧的场地上,没有课时我要学车子的话,真是信手推来方便极了……可是,我决定还暂时不学自行车,我以为时间还不到,这个缘故,只有自己心里明白。
那是七七、七八的年份,祸国殃民的四害已被清除,社会政治社会文化面临着大的颠覆和变革,不时地听人们私下里传说,学校招生要实行考试了,各行业招干部也一样要通过考试。那时我已当了三四年的代理教师,要知道教师这个行当里民办和代教是低人几等的,代教就是个临时工的角色呀。要改变命运,就必须通过考试,我没有其他的任何门路,一缕朦胧的希望向我招手,我感觉到了召唤的力量……要么考学,要么考试转正,二者必居其一之后,再学骑自行车吧,一个连泥饭碗都没端上的小代教有什么脸面骑车子呀?!
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想法一旦确定,就异常地执着或叫固执了。
其实考学、转正和骑车子之间不存在任何相悖和矛盾的地方,但我就是这么一个认死理的人。
那些年学校里倡导教师家访,冬日吃过晚饭,天就快黑了,我踏着暮色,从荆坡到石堆村,到闫家庄,到十里铺,一个来回二十里地,叩开每一户学生的家门,迎来的是家长们诧异惊喜的目光,因为我夜色里徒步而来,故而深深感动着家长……
父亲对我不会骑车子的迂腐样子深深忧虑,我说,为人性僻眈佳句,不转正时不学车!周恩来在抗战时期留一蓬大胡子,抗战不胜利不刮胡子呢,我这算什么!父亲见我态度果决,心情复杂地不再劝说什么,七八年我刚二十虚岁,那时已不算小了,有好心而热情的老师已在父亲面前给我提说某个姑娘,如甲姑娘与我同岁,在某个学校也当着代教,乙姑娘就在她的本村当着民办云云,见我这般固执死板,他能不忧心忡忡么。
七八年深冬,蒲县教育界同全国一样,破天荒第一次在全县四百多名合格的民办代教中招考十三名公办教师,考中了就立刻转正为国家干部,吃商品粮,月薪三十四块五,顶一个中师毕业生呢,但又无须上那三年师范。
这无异于天上掉馅饼。
可是抢这十三块馅饼的居然有四百多号人哪。
结果出来之后,我居然名列榜首,教育局新贴的列有十三名单与考分的红榜,如隆冬一团火,在十字街头燃烧着,烤热了我久已期盼的心。二十岁年轻的心就此活泛起来。
等办好一切手续,就进入腊月二十了,马上就要放年假,我想,大年前一定要学会骑自行车。
腊月二十三放的年假,回到老家临汾故乡时,已经二十五了。第二天,我借了三爸家的一辆半新旧自行车,在南沟的打麦场里正式学起,记得三爸在车后给我稳了一圈儿后,我自己就开始能蹬能骑了,一米七五的个子,一偏腿就能骑上,只是两手把车把抓得太紧,左右拐弯时两臂死死用力去扭动,下坡时捏闸也很机械,前面有了行人和车辆时更为紧张。虽说一上午,学会了骑自行车,可是车技水平多年来仅仅是那一上午的水平,没有明显的长进。
学会骑车的第二天,我就骑车上县底赶集,去时一路下坡,紧捏车闸还是害怕撞车碰人,远远的,看到车前的半坡里行走着一伙姑娘媳妇家,她们是并排走着图了说话方便呢,还在坡上的我就慌了神儿,双手僵硬地把着手把,便朝土坡中间的行人大喊几声——
“快让开——”
“快快让开——”
弄得大伙莫名其妙,回头看时,还有几丈远呢,嘴快的姑娘家便不客气地说,骑个破车子瞎嚷嚷什么,大老远的就让让开,你以为你是皇上的车辇么?神经病啊!
尽管如此,前面有人时我还是万分紧张,无论下坡还是平路,大老远就高喊:
快让开——
快快让开——
制造了好多紧张气氛,其实是我的不自信和心理紧张,有时骑车下坡怕碰到前面的人时,干脆一扭车子把,连人带车碰到路边的土墙地垅上,常常弄得车子把歪歪的,我也倒地沾了一身一脸的脏土。
只要不碰到别人就好,我在心里安慰自己。
整个腊月正月里,我的故乡翟村和县底一带的人们流传着一个歇后语:
张行健骑车子——快快让开。
那时候我已经到了蒲县中学任初中语文教师,前一年我一边代教一边在文科复习班听课,无论同学无论老师知道我固执古板不会骑自行车,就像知道蒲县中学看门房的老汉是一个驼背一样,人人清楚,个个明白。忽然间,就有人看到我骑上车子了,或上街或穿行在学校的林荫道上,眼尖的学生娃儿就叫唤一声,快看,张老师骑上车子啦,自然引得许多人看稀奇一样看远处的我骑车子,人们的表情无异于看到天外来客。
文科复习班一高姓漂亮女生在后来同我一个办公室办公时,因为非常熟悉了,才对我说,她们文科班的女生看我就好像看一个古人一样,我和她们,和其他人,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古时候的人,忽然骑着车子出现在他们面前,不惊讶才怪呢。
虽说会骑车子了,家里因了困难还是在近期买不起车子,这不要紧,同事、朋友、同学、学生们中间车子太多太多了,大小事情,长短距离,借用时间,我心里有一个排队,平均下来,一个月轮不到一次,这就好办了。
可能因为骑车太晚,会骑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似乎有一种恶补心理,要把多年造成的骑车空白统统填充上,又如同一个晚婚的汉子有空儿就爬在媳妇身上永不满足一样,反正那几年我是有事便骑车,不论路长短。
记得一个同事结婚时,蒲县中学离他家有60里地,十几个同事借了一辆吉普车坐不下几个人,坐班车又得死等那个点儿,大多人只好等班车了。我没那个耐性,推了一辆车子骑上便风驰电掣,直朝山村弹去。那是一个大冬天,路是柏油路,只是一直在河滩里延伸着,西北风顺河滩打着呼啸,吹到脸上刀割一般,我埋了脑袋只顾骑,把骑车过程当作愉悦享受的过程……两个多小时,我到了朋友家,等班车的同事们还没到呢!
大冬天骑六十里地,上一桩礼,来回一百二十里,这在当时也成了蒲县中学师生的谈资。
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的,仍是一九八三年夏天我骑自行车从蒲县到临汾参加省教育学院招生考试的“壮举”。
那是省教育学院在新时期刚刚恢复招考的第二年,第一年即八二年还是中文班,到八三年已经成为中文系了。这是只考语文、政治、史地的一次全省统一招考,因为不考数学,对我来说是这一生都难得的机会。
晋南考点就设在临汾师范,运城和临汾的考生必须在考前一天赶到临汾市。
天公不作美,山区蒲县多日来暴雨如注,整个河滩里浊浪排空,山呼海啸。昕水河道一涨再涨,河水居然好几次漫上了东关的水泥大桥,百货公司涌进一米多高的洪水,把脸盆茶缸袜子裤子冲得满大街都是。
我家居住的是蒲县中学教师宿舍的两孔砖窑洞,窑洞也从窑顶的砖灰缝隙里渗水了,起先是一条一条的,随后是一道一道的,先是从砖墙上朝下爬,之后是从窑顶朝下掉,记得父亲母亲动用了盆盆罐罐外加一页一页的塑料布子,家里家外充盈了下雨接水的各种声响。
最可怕的消息是,从蒲县到临汾的公路被暴雨冲坏了,等雨停了以后才可以修路通车。
那几天,我一直盼着忽然有一阵大风刮来,刮跑满天乌云,刮来亮丽的太阳,不误我乘车到临汾考试一事。可是,老天专门与我作对,暴风雨外加连阴雨,一直不停点儿直到考前一天还是雨脚如麻未断绝。
之前我去过好几趟长途车站,汽车在半月十天不会开的。
怎么办?
天可以误我,我却不可以误我了,误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啦。在说服了父母朋友之后,我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骑自行车下临汾!无论暴雨有多急,山风有多猛,道路有多险,一颗参考的心,坚不可摧。
这是无奈之举,但也有好几天的思谋,我借了朋友父亲的邮电局的绿色坚实耐用的自行车,披一身雨衣,带一支钢笔,上路了。
自行车如一支绿色的箭,载着我,劈风斩雨,射向茫茫雨雾中。
三十年前的所谓山区公路,是崎岖又窄小的沙土路,洪水一冲,坑坑洼洼,多处路面出现断裂,每遇这等路况,我得扛着车子从围边绕行,就这样,我骑一段车子,车子又骑我一段。暴雨时紧时松,因穿着塑料雨衣汗水也欢快地排出来,与雨水汇合着在周身涌动。我当时的信念是,车轮每转动一圈儿,就离临汾近一圈儿,我每迈动一步,就离目的地近一步。
过了黑龙关,推车七里坡,两边是陡峭石崖。崖壁的条条缝隙里,以及缝隙长出的无数松树柏树杂木灌木的根须上,都源头一般喷射着水柱,千丝万条不绝如缕……推至半坡,我已累得大口喘气,甚至吐着舌头,像被人追急的野狗。看到路边一块干净的白岩石,我真想放下车子,在干净平整的岩石上坐一会歇一会儿,在犹犹豫豫迟疑片刻之后我还是从容地走了过去,哎,不歇了,慢慢上吧,此时就把自行车当作自己的拐杖吧,这样我两手拄着车把走过去了那块洁净的岩石……走过十余步或七八步远吧,身后便传来惊天动地的坍塌的轰轰响——
哦——没待我回头看呢,我的脚下已滚来大大小小的石头和流沙,再回头看时,是高高的石崖整体塌了下来,把我刚走过的沙土路,把路边的那块白石头,整个地覆盖了!
啊!我大惊失色,那山堆一样的泥石流把整个路面给堵住了,如果前一分钟我在那块白石上休息的话,这会儿连人带车全给压住了,那泥土中巨大的石头,会把我砸成肉饼,会把自行车砸得扭曲的。
风雨中的我,哇哇哇——大叫几声,那是惊怕之后的歇斯底里地大叫,又是带有几份侥幸的狂叫,肆无忌惮的大叫声被山风暴雨一起挟裹着,一串石头一样滚落到长长的坡下了。
七里坡,七里坡,日你丈母娘的西葫芦脚!
骑上车子我没命地狂蹬着,歪歪扭扭爬着坡,骂了一句顶脏的话。
上到山顶时,雨忽然停了,四周都是白茫茫一片雾幕,身边的深沟里,乳白的雾霾在沟沿,在我的脚边涌动着流荡着,极具诱惑力,那一刻,我真想骑着车子朝那雾幕碾去,在浓浓的云雾之上腾云驾雾。我知道,幻觉是美好的,美好到了极致就是悲剧的产生。我紧紧把握着车头,不让它有一点点自由主义倾向。
夜幕降临的时候,远远看到了临汾城,那里灯火点点,一片城市入夜的气象。自行车平稳地载着我,下土门过田村,跨越汾河大桥,向心向往之的临汾市驶去,尽管途中多次双脚插进淤泥,塑料凉鞋的带子也断了一条;尽管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我还是在城郊的水渠里洗了脸,洗了头,洗了胳膊、小腿、大腿,最后认真洗了一遍自行车,我们要干干净净很有尊严地进入临汾城,迎接我的又一次至关重要的人生考试。
一九八三年六月,在临汾考区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山西省教育学院中文系,教育学院的经历改变了我的命运。而那辆绿色的自行车对于我功莫大蔫!
下
一九八六年七月,我回到临汾市教育局工作之后,才真正拥有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的。
那辆车子是永久牌的,跟了我将近二十年的漫长时段,其间的悲悲喜喜,容后文再叙。第一辆车之后,先后还有六辆车子陪伴伺候过我。如果说第一辆车子是原配妻子大太太的话,后面的六辆则是一个一个的小妾了。
先说原配第一辆车子吧,也真巧,那是我结婚前订婚后,未婚妻送我的礼物,新崭崭,黑乌乌,亮锃锃一辆名牌自行车。对于它的喜欢,如同未婚妻一般情有独钟呵护有加的。
那时我一人在临汾,自然过着单身生活,工作之余要上街要访友要娱乐看电影看晚会等,一刻也离不开它作为忠实的坐骑。星期天回老家村里或者平时同学家有什么红红白白的事情,我也是蹬着它一股风去,一股风回。更为重要的是,车子和我的工作有着直接的关联。
我办了一份《平阳教育报》,起先是小报,后来成了对开报,一月一期,版面详细,各有侧重。这就忙了我一人,要跑各个中小学约稿、采写,要发动各文学社的活动和举办相关征文,还要骑车跑乡镇,当时临汾市(尧都区)除了河底、枕头、西头三乡是坐吉普车去的,其余的全是骑自行车下乡,可以说这辆永久牌车子跟上我后,轮子碾过了临汾市的山山水水了。
记得那次从县底中学回来,已是深夜,怕机关大门十二点时关闭,我发疯地骑着,车子驶进五一西路时,这条路上一片漆黑,是停电了还是其他缘故,我只顾蹬着车子,不料猛地一下撞到某个物件上,车人分离,我倒在街道一边,眼镜也不知飞到了哪里,我顾不上自己身体的酸麻,赶紧起来看被撞的人车(我以为撞了人车)连连说道:“路太黑了,一点也看不清,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师傅。”待我到了物件跟前,半天才辨出原来是一只高高的塑料垃圾桶,受伤的我还对它客气歉意了半天,我愤怒地骂一句“操你老妈”,扶起摔在一边的车子,却无论如何摸不到眼镜了,我就这样瞎驴推瞎马,好不容易回到了教育局机关。
这辆车子因为天天有任务,时时要载重,几年下来就零件松动车身破旧了。尽管我常常擦拭,精心呵护,尽量不让日头暴晒,不让风吹雨淋,但它还是无可奈何地破旧并且身躯一点点残缺不全了。
首先是那颗锃亮的铃铛让人卸走了,当初的铃铛声多么清脆悦耳呀,拐个弯儿或前面有了人与车,丁零零一阵脆响,脆生生,麻酥酥,响到人的脑子仁里面,听了浑身上下一阵舒服。现在车头上光光秃秃,像一匹马儿让人剪了耳朵;再是那根撑子不知何时断掉了,没了撑子的自行车要停下时,先得事先寻找一面能停靠的墙或是一棵可以依靠的树。远远的还在车子上,就得看停车子的地方,周边有无墙壁有无树木,哪怕是一棵半大的树,像看到救星一般,直推了车子朝小树走去,常弄得迎接我的主人十分惊异,热着一张笑脸准备欢迎我呢,却见我直朝了一棵杨树或是一棵桐树走去,待我将车子靠在上面,才明白过来,不免哈哈一笑。
三是护链板子在不断地坏掉,再找修车铺里接上,再掉,再接上,等又一次掉了,就失去修理的耐性,索性不去接了。没有护链板的车子像一头少皮没毛的驴,很是丑陋,并且扑尘土扬泥巴,弄得链子上满是脏物,人的裤腿上也不干净。
下一项是该车链子常出问题了,因车龄过长,因护链板子丢失,因不能及时擦泥上油,链条子便常常断裂,或因过于干涩咬合在一起生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常常在关键时候脱链,骑车上到半坡里,脱链了;有顺路把朋友捎带一段路吧,朋友刚在后座坐稳了,脱链了;刚从粮店买了一袋面两壶油上了车子要骑呢,脱链了;下班回家骑到半路里,暴雨下来了,正准备快快蹬一阵子呢,脱链了……让人尴尬又恼火。
第五是脚蹬子又叫脚踏子不断地坏掉或脱落,往往只脱落一只,留一根光光的亮亮的车轴儿,也懒得去按它,就凑合着蹬吧骑吧,有时候不经意地踏上光轴儿鞋底儿被滑了一家伙,人和车子就短暂地失控,或歪歪扭扭欲倒没倒,或一不留神儿就连人带车扑倒地上。
第六是前后车闸常常失灵,出于惰性心理,一只车闸失灵后还有另一只能用,便不去修理,还是一如既往凑合着骑,前面出现紧急情况了,便赶紧捏闸,要快速下车被车子前行的惯性催得蹬蹬蹬小跑几步方可停下。
(未完待续)
张行健,山西临汾人。1959年出生,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山西省首届签约作家,山西省委联系的高级专家。
自1983年发表小说至今已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山花》、《山西文学》、《黄河》、《清明》、《延河》、《当代作家》、《绿洲》、《长江文艺》、《青年文学》、《广州文艺》、《现代小说》等刊发。先后获得“人民文学优秀散文奖”、“山西文学优秀小说奖”、“路遥青年文学奖”、“第二届赵树理文学奖”、“第三届赵树理文学届”、“山西首届优秀签约作家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