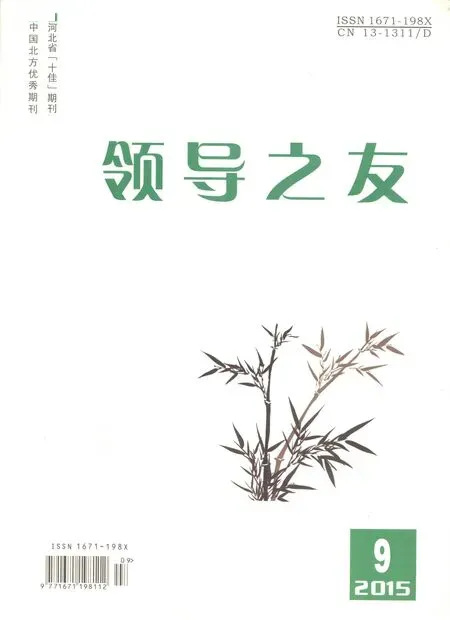建构性共同体: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一种现实选择
唐礼勇,丁盛熔
(浙江农林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
建构性共同体: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一种现实选择
唐礼勇,丁盛熔
(浙江农林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
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传统村庄共同体,给村庄的生存形态和治理转型带来了严重危害。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建设是重建农村社区共同体的一种努力。建构性共同体是当下农村治理转型的一种现实选择,它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在充分考量村庄实情和特质的基础上,通过重建社区文化、加强社区服务、推进社区治理、培育社区组织来建构“四位一体”的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具有可操作性,它对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及农村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建构性共同体;共同体;农村治理;现实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性因素是农村社区共同体式微、解体的重要原因,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打破、瓦解了传统农村“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1](P13)具有高度封闭性、同质性的传统农村“熟人社会”逐步呈现为开放性、流动性、异质性较强的“半熟人社会”。现代化所形成的农村社会分层直接导致农民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农村的思维逻辑逐步偏向理性的“经济人”行为。个人主义和私利意识的凸显使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张力增强,传统农村社区共同体对个体的控制力和凝聚力下降,传统农村社区共同体不断衰败和瓦解。具体来说,表现为村庄人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淡化和冷漠,传统互帮互助、守望相助、基于伦理道德和共同信仰的礼俗规范秩序流失,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削弱。这些给乡村社会的生存形态和治理转型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乃至直接危害到农民的切身利益。
“共同体”作为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和独特的研究视角一直备受学界的青睐。自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首次提出“共同体”概念(Community,亦译作社区)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是持久的和公共的生活”,“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2](P58)他认为共同体不同于社会,共同体是一定地域内的人基于共同信仰和道德、习惯等自发形成的,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守望相助、互帮互惠、具有人情味的人际关系,并由此产生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社会则是以契约和理性为纽带的简单的机械整合。韦伯更多的是对滕尼斯的理论进行继承和深化,他认为“共同体”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社会行为调节是建立在主观感受到参加者们的共同属性上的”,[3](P8)主要强调主观认同上的社会关系。鲍曼认为,“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挡雨”;“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相互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4](P57)虽然共同体给人生存生活以美好愿景和希冀,但面对现代性的不断冲击,传统农村社区共同体开始瓦解。学界对共同体重建持有乐观和悲观两种态度。以滕尼斯、鲍曼等为代表的悲观主义学者认为共同体的衰败瓦解无法挽回,“共同体一旦解体,她就不能像凤凰涅槃一样再次被整合为一体”。[4](P16)换一角度说,鲍曼认为,现代性导致不确定性、不可靠性、不安全性,与共同体所强调的确定性、稳定性、安全性等背反,个体很难舍去自己已经获得的自由而重归共同体生活。相反,以涂尔干、米德、帕克、杜威等为代表的学者持乐观态度。涂尔干用社会分工和集体意识来解释社会团结,认为现代社会就是“有机团结”。[5](P11)他认为,传统的共同体解体就意味着新的共同体的产生,或者说,为孕育出新的共同体提供了契机。持消极观点的学者将共同体过于理想化和浪漫化,他们把共同体与现代性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因而持悲观态度。这未免失之偏颇。笔者相对认同后一观点,在现代性社会中,需厘清共同体所谓的“确定性”和现代性下的“自由性”“不确定性”的悖谬关系,重新审视共同体的核心要义,用发展的观点来寻找重建共同体的理论支点和实现途径,以此来重新构建新型共同体。
自费孝通提出“乡土重建”[6](P1)思想以来,国内学者对重建农村社区共同体也做了大量的学术努力。郑杭生(2008)认为,社区建设与社会建设一样,是为了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7]吴理财(2011)认为,当前的新农村社区建设应以农村社区认同重构为切入点,通过“建设农村社区公共福利、生活化的社区文化、社区公共生活”[8]来实现社区共同体的重建。项继权(2009)认为,要加强农村公共服务,用服务将人们联系起来,在服务的基础上重建农村的社区及社会信任和认同,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9]汪火根(2011)指出,通过构建地域性共同体(现代社区)、培育“脱域性共同体”(各类社会组织)[10]来重建农村社区共同体。李增元(2009)从乡村治理转型视角考察社区建设的困境,并从“城乡融合、组织体制、公共服务模式、资源渠道、社区民主文化”[11]方面提出社区共同体的构建路径。其他诸多学者(贺雪峰,2006;毛丹,2010;刘祖云、孔德斌,2013;李增元、袁方成,2012;张良,2013;韩洪涛,2010;周永康、陆林,2014;李钢,2009;宋梅,2011;等等)从不同视角和不同维度来对农村社区进行研究,并提出多元化的社区共同体重构模式与实践方法。
可以说,城乡一体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到了一定阶段的现实选择,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面临治理转型的一种探索。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农村社区共同体是否需要重建?重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如何?应该如何来构建新型的农村社区共同体?换句话说,构建新型社区共同体的路径和选择有哪些?应该构建一种怎样形态的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通过对理论研究、现实实践的考量以及对共同体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我们认为,在统筹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建设需要构建一个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建构性共同体。建构性共同体作为重建农村社区共同体的一种实践探索尝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消弭共同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冲突,可以有效实现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起到调适和过渡作用,为新的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和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的形成创造良好条件、夯实坚实基础。
二、建构性共同体意旨阐释
面对传统农村社区共同体的衰败解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在新的历史基点上重新构建农村社区共同体的一种努力。那么,在现代化新形势下,建构性共同体是一种怎样的共同体呢?应该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形态呢?
(一)建构性共同体的含义
建构性共同体的概念由学者李传喜(2011)在《建构性共同体:村落社会管理秩序的现实解读——基于浙江省T市Y村旧村实践改造的分析》一文中首次提出。我们所说的建构、构建或是重建并不是恢复传统的共同体,也不是再造“滕尼斯型”的具有理想化的共同体,而是寻求、塑造、建构一个具有现实可操作的,能够“在公领域以及私领域,重新建立一种现代人能够接受的‘共同体关系’,这种关系形式象征着一种连带感,让个人不致有无根漂泊的恐惧。”[12]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及治理转型需要构建一种建构性共同体。所谓建构性,就是将分散的、不完整、不系统的状态重新进行整合和加工,力图按原貌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新”的观念客体,起到一种“重构”或“重建”的作用。我们认为,所谓建构性共同体不是简单机械地构建,而是在考量村庄实情的基础上,结合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整合政府、社区、村民等多方力量,实现村民与政府、社区,村民与村民的多维良性互动,缓解、调适传统共同体与现代化新型共同体构建的矛盾冲突,培育出新的社会资本和适应村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公共秩序、伦理规范和共同体精神,在农村与城市的双向互动中最终形成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具体来说,就是以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新农村社区建设为基础和载体,通过新农村社区建设来整合有效资源和社区资本,重建农村社区的公共性;通过政府主导、社区自治、农民互动参与等多维力量来实现农民与政府、社区,农民与农民的有效互动和公共参与;调适个体与社区、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建构起一个与农民需求和利益相结合、与村庄实情相吻合、与村庄发展相适应、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相协调的共同体;在农村社区与城市的充分互动中寻求一种“动态平衡”,以此建构起一个具有新的社区规范秩序、伦理道德、公共规则,具有共同体意识和共同体精神的共同体。
(二)建构性共同体的特征
显然,从上述表述中可以概括出建构性共同体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具有现实性。建构性共同体的构建是在充分考量村庄实情、村民本位的基础上的共同体再生产,其建构的维度和方向是依据村庄现实可用的社会资本和社区资源,它并不是绝对的、固定的、僵化的、理想化的生活形态,也就是说,其具有较强的可塑性。第二,具有操作性。共同体的构建可以是村庄(自然村)自发形成的,也可以在政府部门(行政力量)、社区自治(主导力量)、社会团体和组织、积极分子(协同力量)等多股力量协作下的构建,它们共同参与、合理协同、有效统筹,充分发挥各自的力量和功能,也就是说,其具有较强的弹性。第三,具有公共性。公共性其实也就是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建构性共同体的实现自然也离不开公共性的建设。通过村民与村民、村民与社区、村民与政府在多维的公共生活和公共参与中的充分互动,培育或增强相互之间的信任、认同感和归属感,也就是说,其具有一定的活力。
从现实性角度来说,建构性共同体不是传统共同体的复归,也不是简单的机械整合,而是在充分考量村庄实情的基础上,利用现有或可用的社会资本,通过村庄、村民主动或被动的形式来重新构建一个与村庄特质及发展相适应、与共同体宗旨相吻合的现代化新型共同体。从可操作性角度来说,建构性共同体的构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纳原子化的农民,使农村漂泊游离的心灵得到归属,可以培育共同体精神和共同体意识,可以重新有效整合农村社区资源,发挥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和牵引力的作用。从公共性角度来说,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公共服务的下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为建构性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利益保障。村庄的合并和整合、农村社区的推进为建构性共同体提供了现实的物理空间,使公共性建设成为可能。就战略层面而言,建构性共同体是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实需要和实践尝试,是现代化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形成的推进路径和有效实现形式。
三、建构性共同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新农村社区建设亟须实现治理转型,而建构性共同体是该背景下的现实选择,是实现共同体再生产的一种可操作形式。那么,建构性共同体的构建的价值何在?其合理性又是体现在哪里呢?
(一)建构性共同体的必要性
第一,村庄实情考量和社区治理的客观需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直接措施就是将原来自然村庄整合和兼并,这一方面,是为了改善部分地区出现农村空巢化、原子化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农村治理的需要和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因此,很多地方设立农村社区,即实行农村社区化治理,出现“一村一社区”“多村一社区”“一村多社区”“集中建社区”等多种乡村治理模式。从共同体的历史角度或特征维度方面来说,传统的村庄(自然村)是共同体的典型代表,一定的地域性、地缘关系是共同体的主要特征之一。而城乡一体化下的农村社区(行政村)其实是多个“共同体”(实际中并不一定都存在,或是处于逐步解体中)的整合和再生产。从内部成员的人情关系来看,现有的农村社区其实就是“半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交往互动的关系可能已经被打破。因此,现代农村社区需要重新建立起“新邻里关系”和“新熟人社会”,这是农村社区实情的客观需要。
第二,村庄秩序规范和道德维系的伦理需要。现代性对农村社区侵蚀的最大特征就是使农民成为思维行动逻辑偏理性的“经济人”。传统农村秩序的维持靠血缘关系、姻亲关系或是基于共同一致默认的伦理道德规范,此即所谓的“礼俗社会”,[1]用道德、用礼俗来约束规范农民的行为。而在市场经济下,农民变得理性,人情关系逐步量化为金钱关系,价值理念发生转变,农村传统的人情关系逐步淡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亲密无间、互利互惠、守望相助,恰恰相反是逐渐地冷漠。对亲戚、对邻里、对村庄的事物不再热情不再关心,只要不涉及切身利益,就表现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缺乏,道德下滑,传统的村规民约、伦理道德对村民的约束力和控制力大大削弱。村庄秩序失范,直接影响到农民的生活和生产,乃至直接危害到村庄的治理和发展。因此,农村社区的现代化治理面临转型和挑战。
第三,农民心理希冀和现实诉求的迫切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集体经济的瓦解以及户籍制度的松动是现代农村社区具有较强流动性的主要原因。而较强的流动性是传统共同体解体的主要因素。伴随着村庄的衰败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民在“新”“旧”生活中有着诸多的矛盾心理。集体经济的瓦解和村庄经济的外向型使农民的眼光从“一亩三分地”转移出去,农民向往并渴望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导致很多人脱离农村到城市生活,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农民工。但是,他们又难以调适个人生存能力与城市的高生产生活资本之间的矛盾,同时,又希望有可信任的老乡、熟人等,一起来建立社会资本或是一起共渡难关、共同打拼。他们处于“脱域”状态,渴望建立新的社会资本和关系网络,试图以此来寻找心理慰藉和安全感、信任感,这需要通过一个新的团体将他们吸纳。基于此,很多学者提出了构建“脱域共同体”的观点,它也成为建构性共同体的现实依据。
(二)建构性共同体的合理性
首先,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统筹城乡发展就是在新农村建设一定阶段的基础上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将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到城乡一体化的总体战略部署中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对农村社区建设提出“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目标。这些为建构性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制度保障。
其次,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大量公共服务下乡,公共产品供给逐渐向农村社区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并提供了利益保障。传统单位制的解体、集体经济的瓦解很长一段时间内使原本紧紧依附依靠村庄的农民一度失去了保障、迷失了方向。而现在新型社区建设中经济合作社、合作组织等的组建其实是一种社区资源的“再分配”和利益的再协调,这为创造一定的公共生活提供了可能,也为农村社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利益的保障提供了较好的平台,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农民的合作参与意识,有利于农村社区的公共性建设,确保了农民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关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最后,共同体构建与农村社区建设相耦合。从宏观层面来看,如果说城乡一体化建设是“重形式”的话,那么,农村社区建设、共同体构建就是“重内涵”的。如果说农村社区是共同体的“外显形式”的话,那么,基于相互信任和认同并以此产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就是共同体的“内生属性”。一方面,从词义本身上来看,滕尼斯提出的“社区”德文为Gemeinschaft,一般被译为共同体、团体、集体、社区等,后英译为Community。英文中共同体一词也译为Community,一般含有公社、团体等含义。从两词的翻译来看,这两者都强调一种“公共性”。最后费孝通等学者将它翻译为“社区”引入社会学领域。社区一词的含义发生了很大改变,有时更多理解和强调的是居住的物理空间而忽视或淡化对其本质属性的考量,但共同体与社区其实在本质和本源上就是一回事情。另一方面,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目标之一是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将农村社区建造成为文明、和谐的农村社区生活共同体。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不断推进,在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以说,在物质层面上农村社区已经相比以往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但在精神层面上仍然匮乏,因此农村社区的建设越来越需注重精神层面的实质性建设。农村社区大力开展的社区文化建设、社区文娱活动就是为了培育社区精神,注重社区建设的内涵式发展,这从共同体视域来说与培育共同体意识和共同体精神是吻合的。
四、建构性共同体的现实路径选择
这种建构性共同体在现代化的农村社区中应该怎样建构呢?应该以哪些方面为抓手和切入点呢?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四个层面来进行实践。
(一)重建社区文化,构建精神共同体
共同体强调的是一种基于认同而产生的某种维系的纽带作用,而文化具有规范、凝聚、整合、协调社会群体的心理和行为的功能,它恰恰是共同体维系纽带的“黏合剂”。重建社区文化,就要建设一种生活化的、具有公共性的村庄公共文化和农民文化。公共性的建设不是回到传统的总体性社会,而是探讨在一个日益分化、多元、差异乃至个体化的现代社会中何以实现一种新的公共生活。[13]这种公共性文化可以是村庄传统文化的升华,也可以是注入新元素的现代化的通识文化。培育公共性文化离不开以下两点。第一,要有较强的农村公共性文化基础设施。公共性文化基础设施是公共文化孕育的摇篮和生长的公共区域,很多农村社区文化礼堂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文化礼堂作为村民公共生活的公共领域,可以办喜事、搞活动、开村民大会等等,它可以使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交流互动更加频繁,增加彼此感情和信任。这也就是公共空间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功能价值所在。正如哈贝马斯所说,人们通过在公共领域中自主的交往、沟通,可以重新发现人的意义与价值。第二,要充分挖掘传统文化,延续发展特色文化。挖掘传统文化,让村民寻“根”,有利于整合离散的文化形态,充分发挥文化的聚合力,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加强文化自觉和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村民对社区的认同。同时,继承和发展村庄特色文化对共同体的维系也起着重要作用,可以提升村庄的伦理价值,维护村庄道德秩序。另外,一些传统文化要素经过现代性改造和转换,仍然可以发挥其独特的精神功能,如“孝”文化保留其“敬”和“爱”的成分,增以“人格平等”的新内容,仍可适用于当下社会。社区文化精神也是村庄共同体的命脉所在。
(二)加强社区服务,构建经济共同体
“没有共同的经济活动,没有共同的公共财产,没有共同的利益维系,乡村共同体的重建就是一句空话。”[14]服务就是重建共同体的经济基础。从农村现实及实践来看,我们认为农村社区及共同体建设应走“服务之路”,即通过“服务”将分散的人们重新联系起来,在“服务”的基础上重建社区认同。[14]社区服务一是来自政府输送的公共服务,二是社区的自我服务。从公共服务角度来说,政府要加大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输送,加速完善建立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尤其是在农村医疗、卫生、养老保险等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项目上,同时社区要主动争取各项公共服务,以功能服务作为社区工作的主要抓手。从社区自我服务来说,应该充分利用和挖掘社区资源,重新整合利用,努力创建和搭建社区服务平台,协同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共同致力于社区服务,协调好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为群众提供有效服务。农民经济合作社就是农村自我服务、提高村民经济收入、增强村民合作参与意识的有效平台。只有增强社区服务,建构社区经济共同体,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村民对村庄的认同以及对村庄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新型农村经济共同体的建构方向应以市场导向和共同富裕为基本原则。当前,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社是一个重要的路径选项,在不影响个人私有经济的前提下,不断壮大发展村庄的“集体经济”,加强合作意识,构建公共经济规则,才能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互利互惠的新型农村经济共同体。
(三)推进社区治理,构建政治共同体
长期以来,村庄与政府、与村民的治理主体关系一直没有被很好地厘清,加上传统的“官本位”和“小农思想”根深蒂固,直接导致各自的角色定位以及行为期待有较大的差异。同时,在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建设中,社区作为政府推进和输送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载体,同时又是政府政策方针贯彻和下达的直接渠道,社区既是政府的“配角”“代理人”,又是村民自治的“主演”“当家人”,处于政府和村民的“夹缝”之中,容易产生角色冲突和角色紧张。同时,加上部分村庄治理中信息的不透明、村干部的腐败,直接导致村民对村干部的不信任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既而导致对村庄的认同和归属感缺失。因此,如何有效推进社区治理、构建村民对村庄的“政治认同”显得至关重要。一方面,村庄应该治理透明化,决策民主化,信息公开化,应该及时进行信息政策的宣传,定期更新村务信息和财务信息,村庄公共事务需要多征求群众意见,集体决策,营造平等、民主的氛围;另一方面,要还村民作为村庄自治主体的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地位。要通过各种措施、方法等让群众有参与意识,在村庄公共规则的轨道中让群众共同参与到村庄事务的管理中来,提高村民参与集体事务的一致行动能力。通过制定、完善相关的村庄规则和创新群众参与机制,实行有效的奖惩措施,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在村民公共参与中加强对村干部和村庄的认同,才能厘清“村民自治”和“乡政村治”之间的两大关系,缓解村社“双重角色”的角色紧张,增强村庄主体地位和自治功能,以此来达到村民对村庄的“政治认同”,从而建构起“政治共同体”。
(四)培育社区组织,构建合作共同体
在集体经济时代,农民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的集体组织,在这样集体生产生活运作下,农民紧紧地依附在这个经济体中,过着朝夕相处的日子,尽管是一定意义上“强制的共同体”,但人们之间的交流多,互帮互助的机会多,自然相互的认同度也高,集体荣誉感也强。集体经济解体后,农民相对更自由了,但是农民之间合作的机会少了,甚至是没有了。市场经济的冲击与社会流动的加剧从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村民之间的合作与认同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减少,缺乏合作意识和公共意识。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城乡一体化统筹推进的大背景下,当前很多社会组织、社区组织正不断地萌芽和兴起,因此培育好这些组织,是构建农民之间合作和交流的合作共同体的重要载体,应该着力培育新型农村社区组织和社会组织,发挥其特有的功能,从而建构起新时期农村新型合作共同体。比如,老年人武术协会、民间书法协会、民间表演艺术团体(诸如腰鼓队、秧歌队、舞龙队、广场舞队等)和多种多样的农村合作社等等。这些团体的组建可以是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扩张,也可以是充分发挥社区积极分子的作用来调动搭建,还可以是依靠政府部门和社区委员会搭台创建,从而改善传统农民之间“善分不善合”的尴尬窘境,实现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区之间的多维互动,增强合作意识和集体认同感。总之,让农民在相互的合作交往中建构起具有相互信任、具有共同价值的合作共同体。
五、小 结
建构性共同体的构建是对传统共同体的升华和提炼,又是新形势下的现实合理选择。它既有共同体理想的一面,又有客观实在的理性因素,追寻的是一种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动态平衡”。我们需结合新型农村建设的主要实践,通过重建社区文化、加强社区服务、推进社区治理、培育社区组织四个维度的建构路径来实现农村治理转型创新的现实性选择,最终将村庄构建成为“四位一体”的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德】马科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5]【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敬东,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
[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7]郑杭生.中国特色社区建设与社会建设——一种社会学的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1).
[8]吴理财.农村社区认同及重构[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1,(3).
[9]项继权.中国农村社区及共同体的转型与重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
[10]汪火根.社会共同体的演进及其重构[J].社会与人口研究,2011,(10).
[11]李增元.农村社区建设:治理转型与共同体构建[J].东南学术,2009,(3).
[12]罗中峰.共同体的失落与重建[A].当代社会发展研究:第一辑[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13]吴理财.论个体化乡村社会的公共性建设[J].探索与争鸣,2014,(1).
[14]周永康,陆林.乡村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学思考[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责任编校:张立新]
Constructive Community:A Realistic Choice of the New Rural Community Governance
TANG Li-yong,DING Sheng-rong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Zhejiang A&F University,Hangzhou 311300,China)
Modernity,to a large extent,has disintegrated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community,which has brought serious harm to the survival of the village form and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an effort to rebuild the rural community.Constructive community is a realistic choi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at the moment with its necessity and rationality.On the basis of fully considering the fac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llage,to construct the“four-inone”new rural community is feasible by rebuilding community culture,strengthening community service,promoting community governance,fostering community organization,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onstructive community;community;rural governance;realistic choic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人言语行为的语言社会学研究》(12YJCZH183);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涂尔干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探究》(13NDJC116YB)
唐礼勇(1978—),男,浙江台州人,浙江农林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丁盛熔(1993—),男,浙江慈溪人,浙江农林大学学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学。
C916.2
A
1671-198X(2017)05-0013-07
2017-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