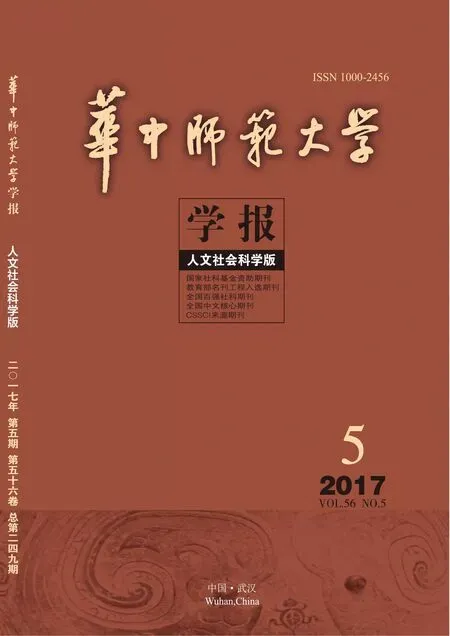变动中的差序:农民人际信任变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2-2015年江西40村五波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
余泓波
(南京大学 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政府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变动中的差序:农民人际信任变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2-2015年江西40村五波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
余泓波
(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政府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江西40村2002至2015年五波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农民人际信任在十余年间呈现“U型变化、波动提升”的整体态势,同时具备“相对稳定、小幅变动”的差序式内在结构。传统差序格局中亲属关系的递推逻辑,则在农民人际信任方面表现为“家庭本位——嵌住关系——开放关系”由内而外地层级过渡。文章从程度与幅度两个角度分析了农民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相对于理性路径的解释,制度与文化的解释更具适用性。因此,如果要营造具有更广更深信任水平的乡村社会,则应一方面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取信于民;另一方面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创建和谐的人际交往环境。此外,政府信任、传统文化对人际信任不同结构的影响同样值得后续关注。
人际信任; 信任的幅度; 差序格局; 农民
“信”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据学者统计,“信”字在《论语》中出现有38次之多①。虽然包含儒家经典在内的汉语语境中的“信”与本文所讨论的“信任”并非完全对等,但由于其长久地作为古代中国启蒙教育的基本内容,并伴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最终汉语语境中“‘信’的主要含义注入‘信任’之中”②。于是有研究者强调正是此种文化传统使得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得以在中国社会萌发,并持续至今,形成了显著区别于西方基于理性计算的另一种文化式的信任资源③。然而,传统价值中的“信”文化并未能直接地成为中国社会信任可靠资源,福山就曾做出中国是一个低信任社会的判断④。随之而来,却也不断有研究发现认为中国社会的信任水平并不低⑤,并引起了学界的相关讨论⑥。
随着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中国乡村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地区仍然更大程度上延续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特质。基于此考量,本文将对信任的关注进一步聚焦于农民群体,并通过2002到2015年对江西40个村进行的五波问卷调查来分析以下问题:十余年间,农民人际信任的总体趋势如何变迁?农民人际信任具有何种的内部结构?其信任的程度与幅度,又分别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人际信任的界定、结构与变迁
西方学界对信任的关注由来已久,其理论脉络与流派已得到国内研究者的广泛引用与评述⑦。国内学界对信任的研究也成一定规模,以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为例:篇名包含“信任”的文献总量已达21620篇,且近五年维持在年均2000篇左右;篇名包含“社会信任”的文献总量1417篇;篇名包含“人际信任”的文献总量则有833篇,且逐年递增;篇名包含“农民”或“农村”,且同时含有“社会信任”或“人际信任”的文献仅28篇。⑧由此可知,在对信任有着浓厚学术兴趣和研究积淀的国内学界,对“人际信任”这一分支的研究相对薄弱,而将此置于农民社会心理与农村社会文化之中进行探讨的尝试则较为缺乏。
在社会学家卢曼把信任区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以后⑨,对前者的讨论逐渐深入和细化。Yamagishi与Yamagishi从对善意行为的预期来理解信任,将信任对象二分为交往对象与制度机制⑩,显然前者是对社会活动中交往者的人格化预期,而后者则是对社会活动得以进行的制度与机制的预期,这与卢曼的二分是一致的。Kramer与Tyler使用不同的概念进行了这种尝试,将信任分为身份信任与认知信任。Misztal则将一般信任视作将心理特质,而将基于身份的特殊信任视作一种情感。不难看出,人际信任主要以某一身份成员为信任对象,而不包含对于机构或制度的信任以及对价值的信念。
对于西方人际信任研究,已有学者系统评述过其路径与困境,而国内学界对于中国人际信任的研究也已取得一定进展。杨宜音使用“自己人”这一本土概念,使用质化方法研究了中国人信任建构的逻辑。杨中芳、彭泗清则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中国人际信任的概念化及研究思路。除了整体性的探讨,也有研究者将分析对象聚焦于某些群体,如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大学生等。还有学者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了中国与其他社会的社会信任异同。
如果仅从测量工具来看,国内不少文献虽为对“信任”或“社会信任”的讨论,但其中亦含有对人际信任的分析(如表1所示)。整体而言,对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与分析路径主要围绕着信任者对信任对象的信任度、对人际关系与交往的信任度两方面,并由此发展出不同的概念界定与操作化测量。在对中国人际信任的内在结构进行分析时,除了“普遍信任—特殊信任”的二分法以外,最常使用的是费孝通对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的概括以及本土化的“关系”“圈子”等概念。如表1所示,不同测量路径的研究者基本都发现了一种随着人际关系所负载的乡土血亲的淡薄而呈现从亲到疏、从近到远递减的差序人际信任,而既有研究往往是基于某一截面数据进行的静态描绘,未能检验这一差序结构是否具有纵向上的稳定性。

表1 国内部分研究中人际信任的概念、测量与结构
由于人际信任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密切联系,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某些结构性的变动,必然会带来人际信任的变迁。而信任本身又是社会资本的重要部分,因而更加得到学者关注。如帕特南对美国社会信任衰退的研究,其发现美国社会的年轻人是最不信任他人的群体。杨明、孟天广、方然利用1990年至2010年间12个全国性调查的数据资料,通过趋势分析认为转型期中国的人际信任并未下降,而是呈现以2002年为波谷的U型趋势;马得勇综合各种机构的调查数据认为,中国的信任度虽然有所波动,但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并把这种变化归因于中国社会转型期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增加。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资料来自肖唐镖教授主持的“村级选举与治理的观察和调查”项目中江西40村的持续性调查。该项目自1999年起,每三年一次,均在村委会换届选举前进驻,并在换届后开始问卷访谈。本文使用的是2002年、2005年、2008年、2011年、2015年的五波数据。某些年份的调查还配以了山西、重庆、江苏、上海等不同省(市)的样本,用以进行地区间比较。但为实现纵向的趋势分析,本文仅使用了江西40村的样本。在删除部分无效样本后,五波调查的有效样本依次为529个、676个、672个、828个、875个。该项目所涉江西40村均来自采用立意抽样方式选择的C、T两县。C、T两县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居全省中等程度,其文化具有浓厚的“赣文化”特征,其中40个样本村是由分层等距抽样方法选择的并持续跟踪的,受访对象则借助样本村当年的选民名册采用等距方式抽取。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假设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针对同一母体的五波问卷调查形成的截面数据,因而采用趋势分析的方法来考察农民人际信任在2002至2015年间的变化。此外,我们将使用因子分析来探究人际信任的内在结构,并通过不同时点的比较来检验其稳定性。在探讨农民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时,受篇幅所限,本文仅以2015年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
如果从理性出发来解释人际信任,则至少需要考虑两类因素“甲对乙失信可能性的判断”与“甲的相对易损性”。胡荣发现担任村干部和收入较高的农民由于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从而具有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王绍光、刘欣针对四个城市的数据分析也发现收入和财富以及稳定的工作能够带来更高的社会信任水平。但在全国调查中,收入的分层对信任的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假设农民的人际信任受其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具体而言:
假设1:控制其他条件,农民收入越高、住房与消费品水平越好、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具有外地工作或乡村精英经历,则其人际信任幅度更广、程度更强。
不同于理性路径,制度学派强调制度环境对于信任的决定性作用,其中有效的政府则是关键。虽然不少学者专注于研究信任对民主的促进作用,但也有学者聚焦于制度对信任的影响:Knack与Keefer通过跨国数据发现了有限的政府权力和独立的司法对于一国国民信任水平的提升效应;Rothstein与Eek发现好的政府能够促进民众之间的信任;朱虹基于全国性资料的分析指出政府信任是重树社会信任的关键;苗红娜发现了政府质量评价对于中国社会信任水平的显著影响。基于此,本文假设农民的人际信任受其对政府绩效的评价以及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具体而言:
假设2:控制其他条件,农民对政府治理评价越好、政府信任度越高,则其人际信任幅度更广、程度更强。
如果将文化视为一种结构性的宏观环境,则其更适合于不同社会间信任的比较;如果将文化视为一种个体性的主观心理取向,则其亦可用于同一社会内部信任程度高低之别的解释。从后者来看,有研究者探究了儒家文化与一般信任的负向关系;而唐文方的研究认为“儒教并不是中国人际信任的基础”。此外,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中和谐和睦的价值期待会使中国人的评价避免极端化,且中国人习惯于熟人圈子的往来,而导致其对外人的信任较低。本文从传统文化与人际交往满意度两方面做出文化心理解释的假设:
假设3:控制其他条件,农民的传统文化认同度越高,其特殊人际信任越高,而一般人际信任越低;农民对日常人际交往的满意度越高,其人际信任的幅度越广、程度更强。
(三)概念与变量操作
1.人际信任及其测量
由于本文为采用调查路径进行的实证研究,以信任者个体为分析单位,从信任者一方来讨论人际信任,所以本文将人际信任视作信任者对具有某一身份的对象的信任程度。这种描述性的操作化界定,既避免了信任概念本身含义的复杂性之争议,也使得对这一概念的测量具有操作性与便捷性。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这样的题目“一般来说,有些人可信,有些人不可信,对于下面几类人,您相信他们吗?”,题目提供的类别有:“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本家族的人”“同村的人”“村干部”“经亲朋好友介绍认识的人”“经常有生意往来的人”“同学”“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选项为“完全相信”“相当相信”“有点相信”“有点不相信”“相当不相信”“完全不相信”“说不清”。我们将各选项分别赋值,通过因子分析获得各类人际信任程度变量(见表3)。此外,本文将各个项目中表示信任的选项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在按照个案进行加总,得到了农民人际信任幅度变量。人际信任幅度即指受访者对所列10个项目中表示信任的数量,区别于信任因子对信任程度的考察,信任幅度考察的是针对不同信任对象的广度。
2.自变量与控制变量
家庭社会经济情况:此类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家庭年收入(元)、住房(钢混住房=1,其余类别=0)、家庭消费品得分(家电、汽车等,1-10分)、职业经历。此外,还包括受访者的主观家庭社会地位、经济地位。
制度绩效与政府信任:政府治理评价因子由因子分析获得,其中因子1包含受访者对本地的社会治安、干部作风、干部能力、道德风气、人际关系的评价,因子2包含受访者对本地经济发展、交通状况、医疗服务、学校教育、文体娱乐、环境卫生的评价。政治信任为受访者对各级政府(村组织)的信任程度评价,经过因子分析生成两个因子,一者为中央、省、市三级,二者为县、乡镇、村三级。
传统文化与人际满意度:将包含6个项目的传统文化量表中表示认同传统文化的选项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之后加总得到传统文化变量。日常人际满意度因子由受访者对自己的“亲戚关系”“邻居关系”“朋友和社会关系”的满意度评价经过因子分析获得。
控制变量:性别(男性=1)、年龄、教育年数、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1)、党员身份(中共党员=1)、土改时的家庭成分(上中农、中农、富农、地主=1,其余=0)、宗族背景(大族=1)、地缘背景(大自然村=1)、家庭人口数量、父亲的职业(普通农民=1,其他=0)、父亲的教育(小学以下=1,小学=2,初中=3,高中及以上=4)。
三、农民人际信任:变动中的差序格局
正如前文所述,受访者在回答“是否信任他人”这类问题时,可能出于“社会期望效应”抑或文化传统里“中道”“和谐”的影响,而避免给出极端选项(如“完全相信”)以及否定性的回答。而本文使用的问卷资料在设计之初采用六个层级的有序选项,则有助于我们通过对不同选项应答比例的比较,来尽可能接近其回答的真实意涵。基于此,表2中分别统计了2002至2015年间五波调查中对各个项目选择“完全相信”的百分比和选择“完全相信”“相当相信”“有点相信”的合计百分比。受访者对“自己家的人”的信任程度最高,五波数据中均在九成以上。其次,对亲戚、朋友的信任在五波数据中均分列第二与第三,处于较高水平(70%以上)。2002年,信任度最低的两类为“经亲朋好友介绍认识的人”(34.6%)、“社会上大多数人”(36.1%);随后的两波调查中,信任度最低的均为“经常有生意往来的人”(2005年31.8%、2008年29.5%)、“同学”(2005年33.5%、2008年17.3%);而最新的两波数据中,信任度最低的项目则为“经常有生意往来的人”(2011年50.5%、2015年54.3%)、“社会上大多数人”(2011年49.2%、2015年55.9%)。此外,通过比较每波调查中“完全相信”比例和信任比例加总可知,两者的差距在“自己家的人”项目上最少,也就是说,不仅在选择相信的比例上“自家人”最高,而且这种信任绝大多数是一种高水平的、完全的信任。而这种“完全相信”与“相信”之间的百分比差距,在对其他对象的信任中迅速拉开。这也提示我们,在解读问卷调查数据时,应该自觉地区分问项的字面含义与调查场景中的实际意涵。
概言之:农民人际信任呈现明显的由亲到疏、由内到外递减的差序格局。其中,自己家的人、亲戚、朋友在十余年间较为稳定地位居最信任的前三项,构成差序信任的内圈,而自己家人的信任又是其中程度最强的。家庭本位的信任格局较为明显。信任度最低的则为经常有生意往来的人、同学、社会上大多数人,构成差序信任的外圈。其余对象则处于差序信任的中圈。
为了更为直观的展现2002至2015年间农民人际信任不同对象的纵向变化,本文将表2中“相信”的百分比制作成为图1。如前文所述,现有文献对中国社会的信任水平变迁有“U型”和“下降”等观点,而本文则发现:农民的人际信任总量在十余年间在整体上有所提高,但这种信任的增加存在着不同对象间的差异,2008年农民人际信任的总量在图中明显“塌陷”,2002至2015年整体上呈现U型变迁。虽然现有文献表明社会转型、经济危机等结构性因素会造成信任在年份间的波动,但未能明确其影响的是人际信任的何种内在结构。本文则在分析方法上具有一定新意:图1清楚地表明以家庭和血缘为核心的内圈人际关系(自家人、亲戚、朋友、同族人)和一般人际信任(社会上大多数人)保持了较高的稳定性,而2008年人际信任的塌陷则由内核与外缘之间的人际关系信任度降低所导致。结合后文的发现可知,这类人际信任对制度绩效较为敏感,也即是说,不同时期的结构性变化最可能先通过经济绩效或政府绩效对其产生影响。

表2 农民人际信任的变迁(2002-2015,单位:%)
注:表格中“相信”为选择“完全相信”“相当相信”“有点相信”的百分比之和;表格中的百分比均是在包含缺失值的情况下的结果。

图1 农民人际信任变迁的“岩层图”(2002-2015,单位:%)
上述分析表明了2002至2015年间农民人际信任的变迁趋势,并大致区分出其内部结构:农民人际信任以“自家人”为最核心,其信任度最高,且纵向来看也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其次为对亲戚的信任,基于血缘关系的信任成为农民人际信任的最内一圈。为了更清楚地分析农民人际信任的结构,本文使用因子分析,得到了如表3所示的因子构成。除2002年外,其他年份均自动生成了3个因子。各个年份因子的内部项目虽有不同,但并非无规律可循。比较来看,农民的人际信任可分为三个人际信任圈子:最内一圈如上文所述为自己家的人、亲戚,即家庭本位的血缘关系;中间一圈为朋友、本家族的人、同村的人、经亲朋介绍认识的人、村干部,即一种嵌住关系;最外一圈为经常有生意往来的人、同学、社会上大多数人,则是一种开放关系。
农民人际信任的结构以家庭为内核和起点,这与传统差序格局理论一致,且表现出学者所概括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家庭本位特征。不同的是,人际信任的“水波纹”并非严格依照宗法伦理下的亲属关系推展:信任的水波纹由家庭本位的血缘关系为起点,随即进入一种朋友、同村、同族等人际构成的嵌住式的熟人关系,而这一依靠“人情”的逻辑运行的人际圈具有较强附着性,不易随意取消或退出。这种的熟人关系的人情纽带自然在信任上弱于家人关系的血缘纽带,而更外围的开放式人际关系的信任水平则更低。正如裸露在外的岩层最先受到侵蚀而导致其结构不稳一样,农民差序式人际信任的外层结构在纵向数据上也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在经历了深刻社会经济变革的乡村社会,亲属关系虽仍以家庭本位的形式稳定占据人际信任格局的中心地带,但其外延的结构却为嵌住式人际圈和开放式人际圈承接。传统差序格局至少在人际信任的方面,需要将亲属关系的逻辑进一步拓展至更为现代和开放的人际范围,以适应社会现实的变动与时代的发展。

表3 农民人际信任的因子分析(2002-2015)
注:主成分提取方法;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均未限定输出因子个数;为使表格更简洁,删去了部分较小系数。2002年至2015年五波数据的KMO检验值分别0.849,0.766,0.784,0.857,0.851,Bartlett球形度检验Sig.均达到0.000。
四、农民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
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民人际信任幅度及人际信任的内圈、中圈、外圈的影响因素,本文使2015年的调查数据构建了四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见表4)。
从家庭社会经济类变量的统计结果来看,理性路径对农民人际信任的解释力有限。家庭年收入在四个模型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住房与家庭消费品则分别对中圈和外圈信任起到了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农民在人际信任的决策中,较高的客观生活条件并不会使其降低相对易损性的评估,反而会使其增强风险意识,从而降低对于血亲-情感关系、嵌住关系的信任。而这些客观家庭经济变量,对于一般化的外圈信任则无影响。这些因素不仅对信任的程度影响有限,对于信任的幅度也无显著影响。仅主观家庭社会地位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受访者的信任幅度。在职业经历变量中,相对于仅有本地工作经历的农民,外地工作经历者显著地更不信任内圈对象,而乡村精英工作经历则会显著地提升其外圈信任程度。
制度类变量中,两个政府治理评价因子均在0.01的显著性水平表现出对中圈人际关系的正面影响。政府治理对于农民信任的提升主要集中于嵌住型的业缘、地缘关系,而这类人际关系恰恰既是公共性的,又是固定性的。更为有趣的是政府信任因子的影响模式:中央省市政府信任显著地提升了内圈人际信任,而在其他模型中不显著;县乡村政府信任则仅提升农民的中圈与外圈人际信任,并扩大了信任幅度。可以看出,在农民的信任内部心理机制中,对高层政府的信任与对血缘关系的信任具有内在联系,而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则与嵌住式和开放式的人际信任密切相关。若按理性与认知路径解释,则表明:值得信赖的高层政府可以提升农民对于社会确定性和风险最小化的信心,而值得信赖的基层政府则有助于培育社会之中作为个人特质的公共信任和一般信任,并扩展了农民的人际信任幅度。
文化类的解释中,我们纳入了传统文化和日常人际满意度。统计发现,和一般认识不同的是:传统文化对于内圈信任和外圈信任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本文所使用的传统文化变量具有明显的家庭和生育内涵,其能够强化基于血亲的内圈信任并不奇怪。但同时,儒家文化本身具有很强的伸缩性,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作为社会价值的传统文化也一直承载着教化作用,其对于一般性的个人特质的养成同样发挥着正面效应,从而使得一般性的人际信任得以提升。因而,现有的对于儒家文化与社会信任,尤其是与一般信任的关系的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此外,日常人际满意度对信任幅度的扩大、对内圈和中圈信任都有正向影响。
制度类与文化类变量对农民人际信任的幅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体来说: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基层政府信任的增强、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日常人际的满意均会显著地使农民在更多人际关系中倾向于相信对方。如果要在深度与广度两个方面促进人际信任,则应该既提升治理品质与基层政府公信力,又注重传统文化传承与和谐人际关系营造。
作为控制变量的家庭背景因素中,大宗族的受访者显著地具有更强的中圈信任,这是由于中圈信任这样一种嵌住关系中本已包含家族成员身份。父亲为普通农民的受访者,会有更广的信任范围以及对中圈人际关系更强的信任度。若受访者父亲为小学学历,则相对于小学以下者具有更强的外圈信任。

表4 农民人际信任的多元回归分析(2015)
注:表格中报告的为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中均为标准误。†p<.1,*p<.05,**p<.01,***p<.001。
最后,男性、教育年数较长的受访者,会具有更广的信任幅度和更强的外圈信任。年龄对内圈信任是负向影响,对中圈信任则是正向影响。有宗教信仰的受访者对于内圈和中圈信任程度都显著更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土改时的家庭成分较高的受访者相对于贫下中农,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更加不信任中圈人际关系,而中圈人际关系恰恰是政治运动中牵涉最深的。即便未曾亲身经历,但这种政治记忆仍旧显著影响了农民对于邻里乡亲的信任程度。从表4中各模型的R平方值来看,模型1与模型3中因变量的变异得到了较好的解释:现有模型的自变量解释了信任幅度变异的16.6%与中圈信任因子的19.5%。而模型2与模型4的R平方值则相对较低,这意味着对于农民人际信任的内圈与外圈,现有解释路径的解释力相对较弱,仍需在解释变量上进行新的思考与开拓。
五、小结
由于本文研究主要是基于江西40村的问卷数据展开,并不一定能推而广之代表这一时期中国农民人际信任的全貌,但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相对的变迁趋势却又具备一定的参考意义。此外,依据美国政治学者墨宁的研究,本文虽使用地方样本,但涉及多元回归分析,其理论解释仍具备一定的可推广性。
现有文献关于整体社会信任的测量侧重反映信任的一般水平,而无法体现真实社会交往中不同人际关系的信任状况及其总量;而某一时点的人际信任调查,则由不足以检验信任变迁本身的稳定性。本文则通过趋势分析,不仅发现农民人际信任在十余年间呈现“U型变迁、波动上升”的总量变迁,而且进一步探究了这一整体态势的内部结构来源和纵向的稳定性。
如果将人际信任看作不同人际关系信任度累积的岩层(如图1所示),则本文的分析表明家庭本位是农民人际信任的内核,更为稳定、坚固;不过,在信任的差序波纹拓展的过程中,亲属关系逐渐向嵌住关系过渡,熟人式人际信任成为靠近内核的中层,而开放式的人际关系则处于农民人际信任的外层,且更易受到侵蚀。因而,如果我们把人际信任当作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进行培育,则应将重心置于嵌住与开放式人际关系之中,防范其侵蚀衰退及引起的整体信任态势的塌陷。借助因子分析,我们可以给人际信任的“岩层”做更明确的结构划分:从内在构成来看,农民人际信任具有相对稳定但具小幅变动的差序结构:最内一圈基于血缘的自家人和亲戚信任最为稳固,且信任的比例最高;中圈则一般包括对朋友、本家族的人、同村的人、经亲朋介绍认识的人、村干部的信任;外圈则为经常有生意往来的人、同学、社会上大多数人。
在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时,现有文献更多地关注的信任的程度,而对于信任的幅度则讨论较少。本文将这二者作为因变量纳入讨论,从而为拓宽人际信任范围、强化特定信任关系起到了一定参考。具体而言:理性解释并不完全适用于对农民人际信任的分析,客观经济条件并未增强农民对于风险与不确定性的评估,从而未能提升信任水平。从制度解释来看,政府治理绩效显著地提高了中圈信任水平,并对信任幅度的扩展有正面影响,这也表明,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位于差序中圈的嵌住型人际信任将逐步提升。
此外,政治领域的信任同样可以外溢到社会人际领域。其中,农民对中央与省市政府的信任显著地关联于其人际内圈信任;基层的政府信任则既能够拓展农民的人际信任幅度,又显著地与其中圈和外圈人际信任正向相关。政府信任的不同层级和人际信任不同组成部分之间显著关系的发现,有助于我们思考农民观念世界中不同层级的政府形象与不同类别人际关系的内在心理关联。个体主观维度中的信任,其本身的心理机制或许能够超越信任对象与信任场景的政治与社会差异,而具有某些微观层面上的内在共同之处。
最后,传统文化虽然提升了家庭本位的内圈信任,但也并非是一般信任的阻碍因素,其对农民外圈的开放式人际信任的提升值得进一步讨论。尤其是儒家价值的不同面向,应该得到更为充分的概念化与操作化思考。综合制度解释与文化解释来看,应该从政府和社会两方面来营造具有更广更深信任水平的乡村社会:一方面提高政府治理品质,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取信于民;另一方面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创建和谐的人际交往环境。
注释
①郑也夫:《信任:溯源与定义》,《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②参见郑也夫:《信任:溯源与定义》,《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王飞雪、山岸俊男:《信任的中、日、美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杨中芳、彭泗清:《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
③马得勇:《信任、信任的起源与信任的变迁》,《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
④Fukuyama, F.Trust:TheSocialVirtuesandtheCreationofProsperity. 1995.
⑤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1页。
⑥参见王绍光:《民主四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第124页。
⑦如杨中芳、彭泗清:《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胡荣、李静雅:《城市居民信任的构成及影响因素》《社会》2006年第6期。
⑧检索时间为2016年6月28日19时,检索网址为http://www.cnki.net/。
⑨Luhmann, N.TrustandPower. John Wiley & Sons, Chichester, 1979.
⑩Toshio, Yamagishi, and Yamagishi Midori. “Trust and Commi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Motivation&Emotion,no.2(1994): 129-166.
责任编辑王敬尧
On the Change of Chinese Peasants’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Its Determinants: Analysis of the Data from Five Waves Survey (2002—2015) in40Villages of Jiangxi Province
Yu Hongbo
(Public Affairs and Loc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five waves survey from the 2002—2015 data at 40 villages in Jiangxi province,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interpersonal trust of peasants is emerged as a U-shaped change and general increase. Meanwhil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peasants’ trust demonstrates a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The sequence from inside to outside of interpersonal trust of the peasants is “family relationship——embedded relationship——open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by its degree and range, and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factors are more applicable for explaining this interpersonal trust than the rational factor. Therefore, the paper advises that to create and improve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in the rural area,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to inheri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for creating a harmonious interpersonal environment is necessary. In addition, government trust,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n the different structure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is also worthy of subsequent attention.
interpersonal trust; the range of trust; a 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Chinese peasants
2016-12-10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公民政治价值观的实证研究”(16AZZ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