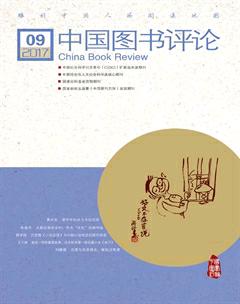当代艺术的新媒介挑战及出路
陈海
中国传统艺术源远流长,各种艺术门类精彩纷呈,千变万化,呈现出不同面相。随着当代新媒介技术不断推进,艺术赖以发生和发展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通过具体分析新媒介技术带来的巨变,探索当代艺术如何在新媒介技术挑战下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呈现。
一、新媒介及其挑战
(一)何为新媒介
从时间维度来看,所有媒介都是“新”媒介。因此“新媒介”一词指涉的内容在不断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那里,“新媒介”是电力的大众传播媒介(如电视)和巨型计算机。而到了2007年洛根那里,“新媒介”又指的是“这样一些数字媒介:它们是互动媒介,含双向传播,涉及计算,与没有计算的电话、广播、电视等旧媒介相对”[1]。到了今天,“新媒介”又指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各种数字技术产品,如VR、AR、ER等设备。从内容上看,大致可以认为其具有以下14个特征:双向传播;“新媒介”使信息容易获取和传播;“新媒介”有利于继续学习;组合与整合;社群的创建;便携性和时间的灵活性,赋予使用者跨越时空的自由;许多媒介融合,因而能同时发挥一种以上的功能;互操作性;内容的聚合与众包;多样性和选择性远远胜过此前的大众媒介;生产者和消费者鸿沟弥合(或融合);社会的集体行为与赛博空间里的合作;数字化促成再混合文化;从产品到服务的转变。[2]42—43总之,媒介即技术,技术不止步,新媒介也层出不穷。那么它们的出现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改变呢?
对新媒介的文化后果进行大张旗鼓的思考,肇始于北美媒介生态学的诸位理论家。媒介生态学(MediaEcology)是20世纪后半叶在北美兴起的传播学三大流派之一。它奠基于以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为代表人物的多伦多学派。从媒介生态学公认的几位代表人物的理论来看,他们都深入分析了“媒介”和“技术”问题。比如伊尼斯讨论了媒介偏向问题、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即信息”、波兹曼分析了书籍与电视媒介的文化差异,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媒介生态学虽然表面上围绕“媒介”展开,但“媒介”只是其思考的表象,他们真正关注的是“媒介”背后生产媒介的“技术”及“技术”背后的人类文化。从媒介、技术到文化构成了媒介生态理论的基本应用之场链。电子媒介、电子技术到电子文化的兴起,使每一个人都处于媒介技术的应用场中,因此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被卷入问题的话语场之中。下面我们具体看看它引发的自然、社会和艺术之变。
(二)新媒介技术对自然的挑战
新媒介技术首先带来自然内涵的巨变。一般而言,“自然”有自然界与自然状态两大含义。如果将自然理解为“自然界”,我们看到当代技术已经超越了对自然的“摹仿”,而达到对自然的“再造”。这一再造既包括再造一个真正的自然界(克隆技术,复活灭绝的生命)也包括再造一个虚拟的自然界(VR、AR、ER技术再造场景)。如果将自然理解为“自然状态”,我们会发现技术正在颠覆达尔文的进化论,正以远远超过人类自然进化的速度飞速改变人类进化了数百万年的身体。就个人而言,电子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自然生命进程,参与我从生到死的全过程。最为典型的是基因工程。从试管婴儿到器官移植,自然生成的生命遭遇到技术的全面接管。基因技术可以预测新生儿的基因缺陷加以人为干预,克隆技术可以克隆人体器官进行移植,甚至技术产物可以与人类身体结合,使人变为哈拉维(DonnaJ.Haraway)所说的“Cyborgs”(赛博格),成为与自然人不同的新人类[2]。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身心一体的生命,人类对自己身体的技术处置必然影响人的精神,引发新的精神问题。一旦技术开始对“自然”有了如此改变,我们的“自然观”将发生改变,作为结果,文化对“自然”的阐释也应发生变化。
(三)新媒介技术对社会活动的挑战
新媒介技术也带来了社会内涵的巨变。此处的“社会”主要涉及两方面: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社群组织。个人的日常生活在新媒介技术的冲击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新的交通技术(如高铁)改变了空間,新的交流技术(如微信)改变了时间,新的制造技术(3D打印)带给我们新的产品。这些结合在一起,我们不难发现,新媒介技术极大影响了个体的日常生活,使其越来越依赖媒介技术。这种依赖外在方便了生活,使得个人目标更易达成;内在导致个体感官比率的变化,构建了基于当代技术的感官文化(如当代视觉文化的崛起)。更进一步,新媒介技术也改变了社群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比如在政治、经济乃至军事领域,媒介技术重组了它们的表现形态和内容:网络意见左右政治局势、网络极端组织的出现、互联网经济的崛起、军事冲突数字化等。如此巨变需要从文化高度进行阐释,或者说,激发了新的文化问题。比如如何评价人造美女、如何看待技术与人的关系、如何理解技术社会的审美趣味等。当代文化需要回答新媒介技术所带来的日常生活的挑战。
(四)新媒介技术对艺术活动的挑战
新媒介技术不仅带来自然和社会的巨变,而且也带来艺术活动的变化。总体来看,新媒介技术正在成为当代艺术新的发生点,当代艺术呈现出明显的技术化特征。
“技艺”作为“艺术”的来源,包含着明显的技术内容。中国古代艺术本就有丰富的技术内容,但往往被其承载的超越内容所掩盖,尤其是宋代文人大量的参与,包括禅宗的影响,导致艺术的精神性被置于艺术的物质生产技术之上。从中西方艺术史角度看,一直存在艺术的技术手段与表达内容之间的融合与割裂。今天的问题是,新媒介技术对艺术形式的改造远超古典技术,人们明显地感觉到了艺术所具有的技术性。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我们一般公认的传统艺术(建筑、音乐、舞蹈、绘画和文学)会因新媒介技术发生形式上的新变化。比如文学的网络化传播,绘画、音乐大量采用电脑特效,随着技术进步出现的观影新体验(3D电影的普及)等。虽然现在开始的是形式的变化,然而形式即内容,形式的变化也必然会引起艺术内容的变化。其二,如同摄影术催生摄影艺术、摄像技术催生电影一样,新媒介技术也将会催生出适应其表达优势的新艺术形式。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与之前艺术截然不同的新艺术,但新艺术的发展和确立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更不能轻视人类创造新艺术的永恒冲动。无论如何,新媒介技术必将成为未来新艺术的核心维度。endprint
总之,新媒介技术正在极大地改变自然、社会和艺术实践,迫使我们文艺研究者反思当代艺术的出路。当代艺术要产生高峰,必须面对新的自然、社会和艺术实践。具体来说需要解决三个问题:艺术如何呈现新的自然状态?艺术如何反映新的社会现实?艺术如何创新自我?下面一一回答。
二、当代艺术的现代性呈现
(一)新天人合一/人机合一
新媒介技术造就的新自然如何被艺术化地表达?这是当下文艺理论思考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第一,面对被新媒介技术重塑的自然,我们的艺术活动也要与时俱进,要从工业时代中走出来,进入数字时代,使用数字时代的手段来进行创作。
第二,面对被新媒介技术重塑的自然,我们不能舍弃它,更不可潜在地对抗(如工业时代那样)。因为这一新自然就是我们自己选择重塑的结果,是最具有现实性的当下的自然。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对这一自然进行某种审视和批判,以此来为当代的艺术表达摄取材料。
第三,艺术表达需要依赖新的天人关系。从马克思所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角度来看,今天的数字生产所依赖的基本逻辑再也不是工业时代的机械力学,而是量子力学。因此建筑在这种生产之上的哲学要走出工业时代传统哲学的桎梏,尤其要反对工业思维的主客二分模式。20世纪人类早已经发现了西方工业文化的弊病,因而在文化层面兴起了反理性思潮,在实践上出现了自然主义、生态主义等实践诉求。然而,虽然生态文化等试图表达一种人与自然的新关系,但它的局限在于: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基础没有变,总是先有主体的“我”和作为主体对象的“自然”,再有“我”与“自然”之间的协调。然而如上文所述,当代新的媒介技术带来的不再是这样的“自然”,不再是“我”之外的“自然”,而是数字化的自然。在这样的“自然”中,“自然界”和“自然状态”都已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数字技术重构的“自然”。或者也可以认为,数字技术已经消灭了“自然”,它所創造的就是真实的自然。面对这样的自然,机械工业时代的自然观已经无法解释。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然观。这时,量子论和相对论赋予了中国传统天人关系以新的生命。虽然传统天人关系所强调的天人合一从根源来看具有浓厚的巫术残留,然而历史总会螺旋式地重复,天人合一在面对新媒介技术所生成的自然面前,它的和谐具有了特殊价值,获得了新的生命。
当然,数字时代的“天人合一”建构在“地球村”语境下,具有数字文化的独特风貌。与其说是“天人合一”,不如说是一种“人机合一”。因为这种“天人合一”的“和谐”不同于传统天人关系的“和谐”:它们的共性在于都具有整体性、模糊性和混沌态,差异在于前者基于外在工具,即数字技术这一人类自己拥有的工具之上,而后者则来自人的内在想象。新的“天人合一”将自然处理为自身的一部分,最终指向基于数字技术的人机一体化状态。
(二)提炼数字生活
新媒介技术导致新的个人生活和社群组织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由新媒介技术改造成新的组织形式,博客、微博、QQ、微信等组织方式客观上导致吸引眼球的惊悚内容的出现和传播。视觉冲击变得尤为重要,能够被直接观看的短、浅、快的内容大行其道。这样的浅阅读更容易引发偏见,使个人的生活产生不安定和无谓的恐惧。更严重的是,在资本控制的消费逻辑下,这些新的组织形式都变为了最广义的广告形式:商业资本无孔不入地对技术进行适合自身的改造。从结果上看,这样的改造极大地激发了人的享乐主义、物质崇拜,消磨了斗志,瓦解了青年人奋斗乃至平静生活的内在动力。
面对这样的媒介后果,艺术何为?它如何对当下新媒介技术引发的社会变化进行回应?我认为,当代艺术既要继承传统,又要对当下数字生活进行深刻体察,提炼数字生活的内在能量,艺术化地表达正能量。以视频直播为例,它基于视觉快感,构建出了只留恋外在形式的审美趣味,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如各种修图软件)塑造出千篇一律的“网红脸”。从表面上看,这些表演者无法与传统表演艺术者相提并论,然而除去稚嫩的形式,视频直播有传统表演远远不能达到的即时互动、生动活泼、跟踪热点等优点。因此,可以对其进行恰当的艺术化提炼,融入当代艺术表达之中,这正是我们艺术现代化呈现的必须。
(三)呼唤新媒介技术的参与
当代艺术实践已经在新媒介技术的冲击下发生了改变。我们如何看待?是抱怨道之不存,还是无限欢呼新的时代?我觉得都不是。海德格尔指出,艺术就是不断从存在之“场”中汲取真来成就自己。今天这一“场”还在,但是经过了媒介技术的遮蔽,汲取更加困难。新媒介技术形成的这一环境“场”,艺术在其中“游戏”,危险在于有可能沦为真的“游戏”。若要将艺术从这种审美的游戏中拯救出来,获得对真理的解蔽,就应该重返媒介技术,对技术去蔽,然后才知道艺术发展的道路。同样,麦克卢汉也从媒介角度谈到对技术的去蔽问题。他指出,所有的媒介都是旧媒介。因此所有所谓新媒介的问题其实都是旧媒介的问题,只不过问题呈现的角度不同。摄影技术造就了新的摄影艺术,然而其开始出现时也被攻击并无艺术性。在与绘画搏斗中,摄影慢慢脱离技术的遮蔽,寻找到自身的艺术价值。同样,电脑游戏当然也可能成为艺术,只要它能够超越技术,获得艺术本真的体认。
因此,面对新媒介技术激发的种种偏见和恐惧,当代艺术的呈现并不需要一味排斥,相反,一种宽容的艺术将在这些挑战中逐步生成。在一种宽容的艺术精神中,才有可能对当代媒介技术进行无偏见的理解:新媒介技术永远是新的艺术建构的生命力,即便它一定会有成长的烦恼,但只要我们消除新媒介技术带来的艺术“平庸化”和“商品化”取向,就可能依靠新媒介技术来找到新的艺术生成点。正如前文所述,艺术活动从根本上离不开技术。当代的新媒介技术当然也会成为新的艺术活动乃至新的艺术门类的推动力。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越是发展新媒介技术,其“艺术化”倾向就越明显。在视频APP上,从最初的聊天、谈话,到如今主播必须具备一定的“才艺”才能引起关注,这一发展的最终指向就是新的艺术活动的发生。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说一切技术都通向艺术,通过艺术通向“道”。
总之,新媒介技术虽然改变了我们的自然、社会和艺术实践,但是当代艺术的现代呈现却是可能的。对于新的自然,当代艺术需要确立新的天人关系;对于新的数字社会,当代艺术应当提炼数字时代的生活;对于普遍数字化的艺术活动本身,当代艺术应该主动呼唤新媒介技术的参与。这样,中国当代艺术才能够借着新媒介技术获得自身的现代呈现。
注释
[1][加]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4.
[2]DonnaJ.Haraway.Simians,Cyborgs,andWomen:TheReinventionofNature.Routledge,1991:42—4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