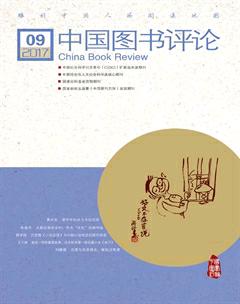当代大学生文学阅读调查报告
王昱娟+雷鸣
一、问题缘起
王晓明教授在《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1]一文中指出:“最近十五年,中国大陆的文学地图明显改变”,文学图景的改变首当其冲的是“网络文学”的兴盛,因此,这“六分天下”的文学首先因为“网络”与“纸媒”的传播形式,分为两大部分。其中,“纸面文学”领域中近15年新生的以郭敬明及其代表的80后青春作家群体给自己圈了一块田地,使得《最小说》成为“新资本主义文学”的沃土;与此相对应的,是同样标签为“青年领袖”的韩寒阵营,既不想走“主流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老路,又不屑于成为大众消遣阅读的对象,当然,随着《独唱团》的流产,这一有意在“主流/严肃文学”以及“商業/新资本主义文学”之间竖起“第三方向”的文学操作实践并没有完全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尽管他们也幸运地收获了一批粉丝,但很难说这种吸引来自于文学创作本身。与这两块“版图”相对应的,是“严肃文学”的影响范围明显缩小,不仅老牌出版刊物(比如《收获》《人民文学》等)的受众越来越少,严肃文学作家想要在接受领域杀出重围,也常常需要倚靠大众传媒的关注,譬如获奖报道,或是将作品改编为影视剧。
当代文学图景的巨变毋庸置疑首先是由于文化生产机制的变化,其中包括了技术变革、政治、经济体制等诸多方面相互关联的结构性变化,“纸面文学”如此,“网络文学”更甚。从20世纪末以“榕树下全球原创文学网站”上线为标志的大陆网文的肇始,“网络文学”走过了最初10年“小清新”的历程。进入新的世纪,成立于2008年的“盛大文学有限公司”连续收购多家文学网站,创建了中国大陆“网络文学”的托拉斯。与此同时,“六分天下”中的“网络文学”版图也迅猛膨胀、急剧分化,然而,起初绕过出版机制“自由”发表的网络文学与私语化的“博客文学”很快就被“盛大文学”挤到了网络文学的边缘。这种状况与“纸面文学”中的“新资本主义文学”的盛行如出一辙,并且这二者某种程度上已经结成联盟。
更有意味的是一种现实的反差,作为高校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的教师,笔者每个新学期都要对新生做一个随堂小调查,问题包括“请问大家以往的课外阅读经验中,是否有文学阅读的习惯?”以及“是否读过网络小说?”这两个相关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会得到截然相反的反馈,譬如当问及“是否有文学阅读的习惯?”时,举手的人寥寥无几,而当问到“是否读过网络小说?”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读过。在学院内、专业课堂上的调查或许恰恰显示了主流的文学研究与当下文学阅读现象之间的巨大差异———正是在前述“文学地图”的重新绘制中,解决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之间的裂隙问题,已经成为文学评论和研究者们不得不面对的事。与此同时,这一阅读现象背后所影射的身份认同与青年文化问题一直是贯穿文学与社会文化领域的重要问题,无论是“五四”还是“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青年问题伴随着新文化、新文学以及人文精神等关于国家、民族的重大讨论与发展走向的课题,不断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当然,“新的”研究对象的出现势必要求人们从传统的文学研究路径中拓展出新的思路和分析工具,以“文化研究”的方法研究今天的文学阅读,使其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一“社会—文学”对读的研究方式正是本文所采用的方法。
二、田野调查与深描
在2014年度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的支持下,来自中文、社会学专业以及文化研究领域的几位研究者在西安、上海两地三校之间展开了问卷调查,针对“当代大学生阅读状况”设置了23个选择题及描述性的问题[2]。整个问卷设计包含三大部分,其中第1—11题倾向于调查大学生原生家庭情况对其阅读状况的影响,第12—18题希望了解调研对象普遍的阅读状况,第19—23题则针对具体的“文学阅读”及其与传媒的关系,希望获取具体的文学文本以及前述“网络文学”或通过大众传媒流行的文学作品的实际影响效果。问卷调查所面向的大学生专业领域包括人文社科类、经济管理类、理工类、艺术类等,具有一定的效度,比较能够获得普遍性状况的描述。
本次调查一共发出600份问卷,实际收回57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468份(题目选项有空白或少选的视为无效),本文针对问卷第三部分进行总结和描述,第三部分的问题包括读得最多的文学作品类型、喜欢的网络文学类型、获取图书的渠道等,其中第21题为描述性问题,题面为:“您印象最深或对您影响最大的三部文学作品是什么?”我们在468份问卷中一共统计得出391种图书名录(其中部分不属于文学作品)。除按照一般定义区别文学与非文学作品之外,我们依照传统的分类方法,将391种图书名录首先分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文学(包括港台文学)、非文学作品四个大类。从统计的数据来看,中国古代文学所列出的书目最少,只有26种(非文学作品类都达到35种),域外文学有138种,其余全部可以归类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名录。这一题的统计结果也印证了第19题的统计数据:该题询问“读得最多的文学作品类型”(最多选三项),选项包括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诗歌、网络文学及其他,统计显示选择古典文学的有163人,选择外国文学的有215人,选择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有282人,选择网络文学的有296人,分别占这一题回答总人数的28.8%、38%、49.9%以及52%,这一结果可以直观地看出“网络文学”在这一群体中拥有绝对多数的阅读受众。
在第21题统计出的近200部可以归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名录的作品中,我们也明显可以看到两个大的趋势:一是传统的主流作家创作依然在调查对象中具有一定的受众,与此同时,网络文学(或者说依靠大众传媒被广泛知晓的文学)大有盖过前者的势头。据此,我们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又细分为两个子类型,一是“主流文学”,再者就是“大众文学”,后者不仅包括了“网络文学”,还包括了“影视文学”以及早期与“严肃文学”相对应的、以取悦大众为目的的“通俗文学”(如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
从所有作品的重复率来看,排名前三位的书目分别是《平凡的世界》(路遥著,1986年出版)、《红楼梦》(曹雪芹著,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活着》(余华著,1993年出版),重复回答的人次分别为88、82、38。除前两者有比较多的人当作第21题的答案之外,其余作品的分布比较均匀。二级分类之后,我们获得了一份关于“大众文学”的书目及统计数据,在对“高雅/通俗”“精英/大众”文学做以区分后,传统分类的“主流文学”只有70余种[3],而“大众文学”项下则多达117种作品,这一数据仅次于“域外文学”的统计结果[4]。在这100多种书目当中,“网络文学”[5]约占60%,甚至有些人将网文改编的影视剧名称写作答案(比如鲍鲸鲸的《游记,或是指南》改编的电影名称为《等风来》)。与之相关的第20题的统计结果显示了“网络小说”的阅读类型偏好,该题内容为“如果上一题选择了‘网络文学,那您喜欢的网络文学类型是(最多选三项)”,选项包括言情、都市、玄幻、穿越、军事、推理、游戏、历史、同人耽美以及其他,排在前三位的选项是推理、言情、历史,选择的人数分别为167、135以及111,较为符合第21题书目的统计结果。其余归在“大众文学”项下的作品类型分别为“青春文学”(比如郭敬明及其旗下作者、大冰、卢思浩、张悦然等人的作品)、“影视文学”(这部分也包括前述的“主流文学”作品通过影视剧改编而获得更广泛的受众)以及比较难归类的、常被称之为“鸡汤文”或“励志文”的名人写作的书(这其中大部分出书的名人都是影视或主持界的,如柴静、孟非、高晓松、白岩松等)。当然,必须认识到的是,无论怎样细分,这些书目内在的联系是显然的,倘若我们观察“网络作家”与“青春作家”之间的联系时,就会发现这其中的奥妙:持续的媒体曝光率是这二者共通的追求。更有网友总结出所谓的“IP消费一条龙”:成为“网红”(或媒体宠儿),然后出一本说得过去的文集,然后编剧或拍电影。尽管对此现象从来都有人持有异议,却不影响他们在传播中成为资本代言人。endprint
数据所反映的的确是更为普遍的现象,然而在问卷调查的分析中,研究者们仍然注意到某些差别。譬如以地域来看,对“大众文学”的接受程度明显在西安与上海两地呈现出不同的状况,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上海高校学生对“网络小说”“青春文学”以及“影视文学”的接受程度明显是高于西安高校学生的,问卷中阅读偏好选项与所列书目显示的“大众文学”受众的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68%,而西安的数据则是43%。此外,在人文社科类专业与理工类专业的调查中也发现,后者对“大众文学”的接受程度也明显比前者高,在两地三校的调查中,理工类专业的90份问卷中的28份甚至不能完整地填写出第21题要求的三本书目,而他们填写“网络小说”或其他“大众文学”的答案则占有效问卷的51%,远高于平均水平。从性别构成看,男生对于“网络小说”的追捧也略高于女生,这一点在“大众文学”的类型上得以体现,统计得出的类型最多的是“盗墓”“修真”“玄幻”以及历史题材。其中以南派三叔的“盗墓系列”为代表,搜集到的书目几乎包括了这位网络作家所有的作品(如《盗墓笔记》《大漠苍狼》《藏海花》等),这些通常都是“男生频道”的题材;年轻的女孩子们则偏向于既看脸又温暖的“鸡汤文”青春写手(譬如卢思浩、张皓宸、张嘉佳等人)的作品。
除了问卷统计,在调查研究的具体操作中,我们还可以采用“深描”的方法[6],来看看是否能够从更深的层次揭示现象背后的问题。首先,从中文专业的调查结果看,学生普遍倾向于一般意义上的“主流文学”,所列出的书目也大都是经典作家的作品。然而有趣的是,以排名前两位的《平凡的世界》和《红楼梦》作为范例,我们反而可以看出一种“主流文学”的“大众化传播”趋势。实际上,我们要首先强调调查时机的重要性,2015年对于《平凡的世界》这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而言是具有非凡意义的,尽管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早在1990年就拍摄了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获长篇连续剧飞天荣誉奖),然而年轻的读者们更为熟悉的则是2015年2月上映的由SMG尚世影业、华视影视、上海源存影业、陕文投集团、乐视网、榆林文旅等联合出品的当代农村剧《平凡的世界》,这里的“当代农村剧”的标签不禁让人浮想联翩,看起来似乎是《乡村爱情》的同类作品,然而关注其执导与演员阵容就会发现,这部由毛卫宁执导,王雷、佟丽娅、袁弘、李小萌领衔等主演,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首播的电视剧明显有着“偶像剧”的倾向。其中佟丽娅、袁弘两位演员则分别以参演过两部同类型的古装穿越题材偶像剧而获得了大量的粉丝。其后,笔者在教授“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过程中,请学生随堂讨论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报告人无一例外使用的是这部电视剧的剧照甚至剧情描述[7]。这不免使我们将目光转向另一部古典名著《红楼梦》,事实上,从对87版电视剧的追捧到对李少红版《红楼梦》的批评,这些年轻读者的关注点无一例外都包括了对同名影视作品的评价。至于对其内容上的解读,《平凡的世界》则依旧难以摆脱“成功学”的消费主义误读,譬如马云、潘石屹等资本大鳄对其追捧的结果使人们误以为《平凡的世界》真的能提供使人(在经济和身份地位上)“不平凡”的养料,顺便用“道德”弥合了资本造成的社会阶层的裂隙;对《红楼梦》的解读则停留在对其中女性角色的分析和偏好上,譬如“钗黛之争”的老生常谈,这一点与类型化的武侠、言情、职场小说等如出一辙。
关于“青春”与“文学”以及“梦”的关系,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些趋势:一方面,没有审美距离的阅读,使得“大众文学”与其读者构成了一个很特殊的关系,这个关系和具有独创性的严肃文学作品跟其读者的关系不同,缺乏“间离”的阅读使得读者与作品之间是相互认同的关系,更为直白地说,读者沉溺其中,丝毫没有反思整体生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即使是传统的主流文学,在大众传媒的包围下,在接受领域的解读也变得越来越单一。
三、文化分析
毫无疑问,“读图时代”早在世纪初就宣告到来,如果不简单粗暴地将“视觉文化”打上“反智”的烙印,我们或许要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技术”本身是无辜的。倘若我们执意诋毁影视剧的受众不如文字阅读者,其实恰恰犯了威廉斯所说的那个错误,即将“技术本身和他们在特定社会的用途混为一谈”,尽管有人用陈多友和小森阳一的《大众媒体墙与心脑控制》来说明新的媒介更容易产生控制的效果,我们仍要审慎地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改变显然不仅是由技术带来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共同生活的整体环境发生了变化。”[8]
当我们用“大众”一词来修饰“文学”时,关于“大众文化”的两种翻译就需要小心区别:massculture与popularculture的表述正好体现了两种态度,尽管对于“文化工业”所造成的把社会的个人塑造成无个性的群体一分子已经既成事实,这种无意识的“认同”却是在对于现实生活中公共生活的失望中建立起来的。换句话说,在那些承认自己是“网络文学”的受众,却拒绝认可这些作品文学性的中文系学生看来,之所以看网文,是因为它们能满足自己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某些“白日梦”,就好比本我的释放,只追求感官刺激,而不去管是否有利于社会人生。也正因此,几乎所有的“网络文学”题材都可以被总结为“弱小者的逆袭”。在这个意义上,自称“蚁族”“X丝”“宅男/女”“学渣”“腐女”等的网文受众,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同的“身份认同”,即现实中的“弱小者”。而这些“弱小者”并没有像现代文学中的青年形象,做出突破桎梏的努力,用青春文学惯用的词表述就是“不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而是世界改变了我们”[9]。
如果我们分析这些作品的“传输意图”,会发现这恰恰是一种传播策略,按照威廉斯的说法,如果生产者的意图在于“操纵(manipulation)”,那么大众也就随之被看作“群氓”。这似乎使得我们对于“大众文学”的分析陷入僵局,一方面承认这其中有大量低劣的作品,另一方面又想还原“大众”的另一种意義。或许将目光转移到另一种“大众文化”上才能看到希望?然而很遗憾,尽管问卷调查结果中包含许多“主流/严肃文学”书目,甚至还有以“打工文学作家”身份著称的王十月的作品,“低劣”和“优良”的分布终究不能成为对等的考察结果。于是,最终的核心问题产生了,那就是倘若我们无法建立起相对平衡的文学阅读(理想的文学阅读与消遣的阅读),在“大众文学”逐渐占据接受领域的状况下,是否还能建立起新的公共生活?倘若我们的判断是这部分作品与当代青年都在回避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领域的问题,而转为关注个人的日常生活领域(网络小说的类型化和鸡汤文的流行恰恰说明这一点),我们是否还能在这种状况下产生新的共同生活?endprint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以及更多的文本和案例分析。事实上,威廉斯在论述“传播与共同体”时已经提醒人们注意如下问题:“就传播问题来说,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对传输采取一种不同态度,以确保传输具有真正的多种来源,确保所有的来源都能够通过共通渠道得以传播。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认识到,传输永远是一种供应,而这个事实必须决定其传输的基调:它不是试图支配,而是试图传播,试图达到接收和回应的效果。主动的接收和鲜活的反应反过来又取决于一个有效的经验共同体;当然,反应的质量取决于是否承认实际上的平等。”[8]329—330透过威廉斯的理论表述总结而言,本研究课题想要着力解决的,正是将目光投注到“大众文学”上,通过文本研究来研究接受状况,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传播”的范例,“青春文学”受众年龄普遍在18岁以下正好说明这一问题。事实上,郭敬明的读者呈现的低龄化趋势,恰恰说明在进入大学之后,更多的年轻人选择脱离“四迷”[10]群体,甚至自发成为“高级黑”群体。所以,反对(或者说批判)“大众文学”时,也应该反对单向的传输,真正将目光投向作品(而非不读而论),才能够与其受众成为实际上的平等关系。
当然,如果上述问题的结论是:成为一个上B站、看网文、追新剧的“大众文化”研究者,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而后的文化批判才有实际意义,才能够建立起真正的“共同生活”,那显然是不够的。将作者、作品与读者放在同一系统中考虑,或许才是问题的关键。事实上,对于诸多文学研究者而言,当代文学一个最令人尴尬的问题恰恰是创作与阅读的分裂。尽管主流文学一直对网络写作抱有比较复杂的态度,网络作家中的一部分也意图跻身主流文学圈,却无法改变这个分裂的事实:一方面主流作家仍在书写当下社会百态,思考时代的问题与出路;另一方面,大部分读者已经从文学中寻找共鸣、净化与领悟转而寻求直接的感官刺激,不仅仅“读图时代”在瓦解文学阅读,即使文学阅读本身,也趋向于单一的娱乐与消遣。
究其原因,前述“六分天下的中国文学”的背后正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和大众消费社会来临的新形势下形成的文化的“三足鼎立”,其中大众消费文化、政府主导文化和精英高雅文化尽管彼此之间并不那么界限分明,其内在差异仍是显而易见的。基于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理想型”就不仅要体现文学的审美性,而且要满足官方意识形态和大众娱乐的需要;同时,既要在思想内容上拥护当代社会文化的主旋律,体现政府主导的意识形态,又要让老百姓喜闻乐见,获得经济利益的回报。因此,即使今天仍然存在“主流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区分,文学的“大众化转型”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主潮。这意味着,严肃文学不仅正在失去受众,很可能连其捍卫的价值空间也被鲸吞蚕食。
这并非危言耸听,实际上,相比作者与读者的分裂,创作主体的分裂是当今文学困境更深层的问题。对于创作者而言,一方面,能够认识到生活的复杂和多样性、认识到当下社会某些普遍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对公众生活缺乏足够的兴趣和期待,转而回归个人生活、专注于个人体会,因此,当下的文学创作似乎只是重复现实生活中人们已经很普遍了的经验,而缺乏更为深刻和复杂的表达。于是最吊诡的状况产生了:一方面创作与阅读产生了裂隙,另一方面创作主体和受众在历史主体的自我生产的过程中共同走向主体性的背反。如果说文学现代性的表现包含对现实以外的世界的想象和探索(而不仅仅是对现实的重复),那么大众文学在此意义上或许意味着“现代性”的倒退?
这个观点在网络小说的叙事方法上很容易找到佐证,相比现代派的文学,大众文学的形式更贴近于小说的远传统:情节至上、塑造典型形象、多采用圆整型叙事……这些故事讲得可谓精彩的网络小说在功能上也更像是饭后茶点,与真正的“精神食粮”尚有一定距离。有趣的是,无论作者还是读者未必不清楚这一点,相比主流作家的“纯文学”追求,网络文学的作者则更倾向于把写作当成一门生意经营。时尚杂志《智族GQ》2014年11月刊发了题为《了不起的唐家三少和他的畸形成功》的访谈,这位占据作家富豪榜榜首的网络作家坦率地表达出要“保持自己的水平不提升,以保证核心受众群永远是最基层的小白读者,因为这个群体的量是最大的”。尽管在访谈中唐家三少不喜欢别人给他定位的“商人”身份,也想要与主流文学一较高低,不过量产的神话已经将他的创作钉在了文化工业的流水线上。像他这样“拎得清”的作家并不在少数,“青春文学”的代表人物郭敬明也毫不避讳大众给自己的三个身份排序:商人、艺人、作家。
当“拎得清”成为网络作家的创作原则时,“文学追求”和逐利的目的之间也就不需要太多的调适。追求与“主流文学”的分庭抗礼只是表象,名利双收的野心未遂之下退而追求盆满钵满才是当下真实的写照。既然创作的状况如此,读者“花钱买乐子”也就变得理所应当,不过,通过网络小说获取的娱乐感并非单纯来自阅读。事实上,个别访谈的反馈已经提供了另外的思考路径。比如,参与此次问卷统计的大二英文系女生给统计结果的excel表格起的名称叫作“看看你们读的都是什么玩意儿”。再比如,像前文所述脱离“四迷”群体,转而成为“高级黑”的例子非常普遍,甚至常常演变成群聊的狂欢话题。而讨论的方面也并不局限于作品,包括作家形象、私人生活、抄袭事件、娱乐话题等,通过调侃、讽刺甚至自嘲,曾经深陷其中的读者重新找回主体性,并以此作为青春期迷茫终结的象征。
唐小兵在《蝶魂花影惜分飞》一文中分析“鸳鸯蝴蝶派”时指出“现代性”的一个根本矛盾:“人们用极其崇高甚至悲壮的气概和‘淋漓的鲜血换来的现代进步或解放,最终却必然是对平民那种安宁琐碎的日常生活的肯定和保证。”进而指出“新文学”与“鸳蝶派”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浪潮,本质上回响的是对现代城市平民文化的竭力抗拒,也就是对人类生存的世俗性的最后抵抗。”[11]这一结论放在网络小说的阅读上,颇具启示意义。事实上,当青年亚文化被“大众文化”所召唤,其与主流的“被压迫”关系的取消恰恰意味着这种“反抗”从外部回归自身。无论是迷恋还是厌弃,欲望和反叛的冲动都意味着“青年文化”不会永远维持同一样貌,这也是“青年亚文化”的悖论与合法性所在:一方面因其青春感性冲动、青春偶像崇拜以及都市文化的特质[12],很容易被主流文化征用;另一方面,一旦意识到自身的“大众化”,它就会转而投向其他的内容与形式,“亚文化”身份的保留恰恰意味著对抗性的持续。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创作主体和作品无法摆脱“现代性倒退”的质疑,阅读与传播本身却有可能成为“自反性现代化”,当一个又一个的唐家三少、郭小四被追捧继而被抛弃,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共同文化”的结果,青年身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重新确认,如此,或许也就有了构建新的共同生活的可能性。
[本文获得2014年度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2014I11)资助。]
注释
[1]王晓明.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J].文学评论,2011(5).
[2]“当代大学生阅读状况调查问卷”调查时间为2015年4—9月。该问卷针对不同的学校招生情况(如上海大学是大类招生),在专业一题的选项上有微调。调查范围包括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安邮电大学以及上海大学,填写问卷的学生包括本科一至三年级(在1993—1996年出生的青年人)。
[3]由于某些作品的界限没有那么鲜明,因此统计数据也无法做到绝对的精确。
[4]由于划分体系的多样化,使得金庸、琼瑶等作家重复出现在两个类型之中,这里主要考虑其“大众文学”的属性。
[5]这里的“网络文学”特指在网络上首发并且以网络阅读为主要接受途径的作品,尽管这一类作品中的绝大多数都有在线阅读资源,但如果不符合网络“首发”的前提条件,便不算作“网络文学”。
[6]这里的“深描”与“结构式访谈”的区别在于本文所描述的现象是从笔者执教以来所获得的所有信息中选取相关的内容进行“民族志”式的描写,不一定都是在调查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访谈。
[7]事实上,《平凡的世界》2015年版电视剧对于原著的改编不可谓不大,从人物设置到情节再到最终的结局,都与原著呈现出差别。
[8][英]雷蒙·威廉斯著.文化与社会[M].高晓玲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316—317.
[9]电影《致青春》与《中国合伙人》都不约而同的用了这句话。
[10]郭敬明粉丝的自称。
[11]唐小兵.蝶魂花影惜分飞[J].读书,1993(9).
[12]王一川主编.大众文化导论(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97.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