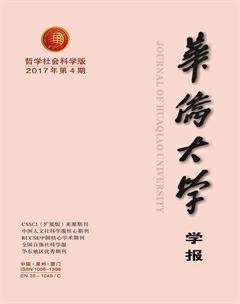《红楼梦》诗词对先秦文化元典的受容探赜
李春光
摘 要:诗词歌赋作为《红楼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如《红楼梦》文本本身一般,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之处甚多。就文学接受而言,《红楼梦》诗词于经史子集四部亦多有染指。单就经部而言,《诗经》在《红楼梦》诗词中的大量出现,亦绝非偶然。《红楼梦》借径《诗经》言说自家块垒,或潜塑人物性格,或暗示人物命运,或小示情节发展,或幽构周遭环境,可谓匠心独运,穿凿无痕。由《红楼梦》诗词对《诗经》的受容,亦可管窥作者对以经、子二部为代表的先秦文化元典的接受与态度,即《诗经》优先、重道轻儒的原则。
关键词:诗经;红楼梦;诗词曲赋;文学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7.4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7)04-0129-14
相对而言,《红楼梦》诗词研究并非红学研究之重镇。陈独秀先生曾在《<红楼梦>新叙》一文中放言:“我尝以为如有名手将《石头记》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单留下善写人情的部分,可以算中国近代史的文学作品中代表著作。”林文光:《陈独秀文选》,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随后,茅盾先生在《<红楼梦>(洁本)导言》一文中作出回应,他认为“大观园众姊妹结社吟诗,新年打灯谜,诸如此类的风雅故事”可以“全部删去”茅盾:《茅盾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520页。陈、沈二位先生作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学者,深受西方叙事学典型人物理论之濡染,加之当时对一切传统文化价值进行重估的文化风气,直接导致其观点的时代局限性。且当时的红学研究尚未普及与深入,考据索隐二派搅动风云的红学气象,《红楼梦》诗词研究被弃置一隅亦在情理之中。然而,一部叙事文学作品的成就,不仅体现于这其中的人情世故,诗词歌赋亦会增加文本的思想内涵与审美情趣。正如宋克夫先生所言,贾宝玉所追求的“任情恣性”的存在方式便是“诗酒生活”宋克夫:《宋明理学与章回小说》,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235页。如果离开了诗词歌赋,大观园这诗意地栖居将会黯然失色。更何况,《红楼梦》诗词是作者逞才的绝佳载体。如《秋窗风雨夕》便是《春江花月夜》的仿作,但前者的意境已然超脫后者藩篱而自成一家。《红楼梦》诗词在承继前代优秀文化成果之时,从神髓上则是把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文化元典作为其逞才的精神内核。《红楼梦》熔淬《诗经》之雅言,或潜塑人物性格,或暗示人物命运,或小示情节发展,或幽构周遭环境,可谓匠心独运,穿凿无痕。
一 《红楼梦》对《诗经》的受容概况简论
概而观之,《红楼梦》对《诗经》的受容可以分作三种类型。
类型一:《红楼梦》文本对《诗经》的直接引用。
例如: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中,贾政审问李贵宝玉的学习情况时,李贵就直接“误用”了《诗经》里的句子:
(贾政)因向他(李贵)道:“你们成日家跟他上学,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倒念了些流言混语在肚子里,学了些精致的淘气。等我闲一闲,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长进的算帐!”吓的李贵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碰头有声,连连答应“是”,又回说:“哥儿已念到第三本《诗经》,什么‘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说的满座哄然大笑起来。贾政也撑不住笑了。因说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偷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从上面这一段对话可以得出四个结论:第一,这种引用属于因人而异型的“误用”。正如蔡义江先生所言,红楼诗词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按头制帽,诗即其人”(在论及红楼诗词时,蔡义江先生认为红楼诗词有如下六个特点:1.真正的“文备众体”;2.借题发挥,伤时骂世;3.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4.时代文化精神生活的反映;5.按头制帽,诗即其人;6.谶语式的表现方法)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7页。曹雪芹在旁征博引之时正是遵循了“按头制帽,诗即其人”的原则,李贵胸无点墨,因为跟着宝玉才旁听了些许内容,把“食野之苹”说成是“荷叶浮萍”,如此谐音相近的错法,亦在情理之中,恰好吻合了李贵的地位和身份。第二,这种引用同时又属于环境指向型“妙用”。“呦呦鹿鸣”出自《诗经·小雅·鹿鸣》: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毛诗序》云:“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周振甫:《诗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31页。这时,这种引用刚好有提示环境的功用,与“贾政回家早些,正在书房中与相公清客们闲谈”的情况吻合,而贾政厚遇这些清客更是不言自明。而面对李贵的谐音之错,贾政与清客们“哄然大笑”,这错愕与欢笑的对比,说明儒家入仕之知识仍然掌握在少数士大夫手中,下层民众仍然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知识。第三,有些学者认为,这句“误用”暗示了贾宝玉将来的命运,是典型的借典明志。陈子为认为:“‘呦呦鹿鸣者乡闱报捷也,‘荷叶浮萍者闱后潜逃也,宝玉之末路已兆于此也。”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见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03页。此评虽有穿凿附会之嫌,但以“呦呦鹿鸣”喻指“燕嘉宾”,亲朋故旧前来道贺,证明宝玉乡闱得中;以“荷叶浮萍”喻指水流云散、万境皆空,进而暗示宝玉“悬崖撒手”、皈依三宝。亦可自成一说。第四,表明了曹雪芹推崇《诗经》的态度。在贾政看来,贾宝玉对《诗经》的学习只是“虚应故事”“掩耳盗铃”,并无实际功用,所以让贾宝玉跳过《诗经》,直接从《四书》开始。这就是贾政父子对于儒家经典——以《四书》为代表的科考文化和以《诗经》为代表的怡情文化——价值取向的根本分野。明清科考以《四书》为纲领,贾政此举无非是让贾宝玉早日习得科举的文化语境,以备日后走上仕途,光耀门楣。事实上,宝玉的逆反就体现在对《四书》的睥睨,进而对诗词歌赋这些怡情文化情有独钟,大观园所题楹联、《芙蓉女儿诔》等作品中均引用《诗经》的篇什便是佐证。可见,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轻视《四书》的行止,肯定并推崇了以《诗经》为代表的怡情文化的价值。endprint
类型二:《红楼梦》的整体建构模式深得《诗经》之真传。
解盦居士在《石头臆说》一文中开篇名义:“《红楼梦》一书得《国风》、《小雅》、《离骚》遗意,参以《庄》《列》寓言,奇想天开,戛戛独造。”解盦居士:《悟石轩石头记集评》,见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84页。
紫琅山人在《妙复轩评石头记序》中说:“古者著人之不善,无非望人之复善耳。莫不善于淫奔,而《风》诗采之;莫不善于弑逆,而《春秋》笔之。可以知作者之苦心矣。”太平闲人:《妙复轩评石头记》,见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7—38页。王梦阮在《红楼梦索隐提要》中说《红楼梦》“美刺学《诗》”“书法学《春秋》”“参互错综学《周易》”“淋漓痛快学《孟子》”王梦阮:《红楼梦索隐提要》,见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94页。。由此可见,《红楼梦》于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元典之中借力不少,并在其建构模式之中留下了它们的痕迹。
首先,《红楼梦》的意旨暗合《诗经》之意旨。《红楼梦》“大旨谈情”,这就暗合了《诗经》“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的题中之义;若是要告诫后人勿行淫奔无耻之事,就必然以《诗经》正之、导之。孔子“《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论断大体可以说的过去,即使仍有异议存在。清人江永有言:“《诗》亦自有淫声”,闻一多先生亦在《诗经的性欲观》中明言“《诗经》可以说‘好色而淫,淫的厉害”,并进一步认为“《诗经》是一部淫诗”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9、190页。。20世纪初叶,随着欧美文化人类学的兴起,泰勒、摩尔根、弗雷泽、格罗塞等人的论著或观点,经由日俄的文化传输濡染了中国学人。学者们以重估传统文化为视阈,借用西方新观念、新方法,解构性地反刍、剖析民族文化。这些阐释虽然是西风东渐、大胆创新之举,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语境的忽视,以及对西人学说的无条件受容,势必会导致异质文化对接过程的水土不服。需要申明的是,还原到《诗经》生发的时代,不可否认,《诗经》中确有像被后世诟病的“郑卫之音”这样的、些许的“色”“淫”成分,但当时采诗人采之的目的是引人“复善”,不再“淫奔”。同理,《红楼梦》之所以不同于《金瓶梅》,主要在于《红楼梦》以“情”为主旨,隐“性”而谈“情”。因此,《红楼梦》借助《诗经》意旨以“正贞淫”,来告诫后人亦算水到渠成。故张新之有言:“三百篇固各自蔽一言,《红楼梦》固不淫靡烦芜,而整齐严肃也。”五桂山人:《妙复轩评石头记序》,见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5页。
其次,《红楼梦》中某些人物的塑造也遵循了《诗经》中人物塑造的旨趣。以林黛玉为例,曹雪芹对林黛玉“幽淑女”的定位可以追溯到《邶风·静女》的“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与《周南·关雎》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有机结合。而对于林黛玉的住所“潇湘馆”的前身“淇水遗风”的建构,更显示出《红楼梦》对《诗经》情趣的遵循。“淇水遗风”中的“淇水”,在《卫风》中被多次提及(《淇奥》《氓》《竹竿》)。大凡提到“淇水”,多会涉及到竹子的描写。以《淇奥》为例: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瞻彼淇奧,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朱熹在《诗集传》注曰:“淇上多竹,汉世犹然,所谓淇园之竹也。”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4页。
这样的描述刚好符合潇湘馆“有千百竿翠竹遮映”的特点。因此,潇湘馆的建构,是相当符合卫风的风格的。究其文本内蕴,《淇奥》所咏实为女子赞颂君子之音。其一,这位君子仪表堂堂,衣着华贵,正是“充耳琇莹,会弁如星”;其二,这位君子文采菁华,处事圆融,正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三,这位君子幽默诙谐,待人宽厚,正是“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其四,这位君子忠贞淳厚,品德高尚,正是“如金如锡,如圭如璧”。以这四点反观红楼君子,也只有宝玉与之相配。宝玉说:“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来一百遭。”恐怕也只有这样的君子,才有资格进入“淇水遗风”。故从行文来看,潇湘馆的设置理念也深得《淇奥》雅韵。而对于黛玉葬花的艺术建构,很有《卫风·考槃》中“硕人”的某些特性,正如方玉润所言:“考槃者,穷而在下者之自乐难忘也”方玉润:《诗经原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4页。黛玉葬花又何尝不是一种寄人篱下之“穷”后,浇自家块垒的“自乐”方式。因此,对于林黛玉这一人物的建构从其性格特质、其环境模拟都深得《诗经》趣旨。
再次,《红楼梦》中的某些器物也遗存了《诗经》的余味。例如第十五回中,北静王水溶初次见贾宝玉之时,就赠其鹡鸰香珠一串:“水溶又将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来,递与宝玉道:‘今日初会,伧促竟无敬贺之物,此系前日圣上亲赐鹡鸰香念珠一串,权为贺敬之礼。”而“鹡鸰”一词就出自《小雅·常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毛诗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认为:“盖初民重‘血族之遗意也。就血胤论之,兄弟天伦也,夫妇则人伦耳;是以友于骨肉之亲当过于刑于室家之好。……观《小雅·常棣》,‘兄弟之先于‘妻子,较然可识。”钱锺书:《管锥编·毛诗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3—84页。“鹡鸰”作为《常棣》中的一个重要意象,后世便固化为表示兄弟之情的词汇。韩愈《答张彻》,叶适《送巩仲同》,李隆基《鹡鸰颂》等都是通过对鹡鸰的赞颂,以表达兄弟之间的真挚感情。不难看出,鹡鸰在漫长的文化变迁之中,从比喻血亲兄弟,到比喻一般兄弟,再到比喻好朋友,再到《红楼梦》中比喻初次遇见的朋友。虽然有文化下移的倾向,但是还是保留了《诗经》中的遗意,即兄弟关系。于此同时,第二回贾雨村在叙述甄宝玉时说:“每打的吃疼不过时,他便‘姐姐‘妹妹乱叫起来”。此处甲戌本有眉批云:“以自古未闻之奇语,故写成自古未有之奇文。此是一部书中大调侃寓意处。盖作者实因鹡鸰之悲、棠棣之威,故撰此闺阁庭帏之传。”曹雪芹:《脂砚斋全评石头记》,霍国玲、紫军校勘,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29页。这里对《红楼梦》所隐之历史暂且不谈,脂砚斋认为此书之深意在于慨叹“鹡鸰之悲”,进而证明《红楼梦》的建构方式深得《诗经》之真传。endprint
类型三:《红楼梦》诗词对《诗经》的受容。
如果说《红楼梦》文本对《诗经》的直接引用是“按头制帽,诗即其人”的随意点染,借道《诗经》激活文章窍脉是“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的诗性留白,那么《红楼梦》诗词对《诗经》的受容则是将随意点染与诗性留白相糅合,并付诸饱笔的大肆渲染,是将抒情文学的机括与叙事文学的章法熔铸无痕的淬炼。
二 《红楼梦》诗词对《诗经》受容的计量统计及分析
《红楼梦》诗词对《诗经》的受容,作为《红楼梦》对《诗经》接受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单独列出,并加以讨论。通过文本研究,现将《红楼梦》诗词中引用《诗经》的回目数以及相关诗词和《诗经》原文列举如下,见表1之统计,并初步证明《红楼梦》对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文化元典的接受特点。
经表一之统计,可知《红楼梦》诗词对《诗经》的受容具有四个特点:
1.对《诗经》引用方式的多样化。
(1)直接引用。如“逃之夭夭”“鸡栖于埘”“静言思之”。
(2)间接引用。第一种,字面上的整合与重构。如“厚地高天”“夭桃”“艳李秾桃”“思古人兮俾无尤”“辗侧”“蒹葭”等。第二种,意义上的挪用与派生。如:“芍药花”“蒸赏”“鬼蜮”“惟鹤有梁”“琴边衾里”“茑萝”等。
(3)句式套用。如“爰……爰……”和“之子……”等。
2.对《诗经》意义接受的章法性。
(1)于潜藏里塑造人物性格。如:贾惜春的判词《虚花悟》。原本借助《周南·桃夭》来表示青年女子貌美如花,以喻婚姻之事,而“说什么”三字直接证明了贾惜春与婚姻无缘,暗示了她“独卧青灯古佛旁”的“冷”性格。
(2)于隐晦中暗示人物命运。如:薛宝钗的《春灯谜》。原本借助《周南·关雎》中“琴边衾里”来表达夫妻恩爱和谐,而“总无缘”三字,则在晦暗之中昭示了“金玉良缘”的必然瓦解,薛宝钗独守空房的命运。
(3)于无形处巧提情节发展。如: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借助《小雅·何人斯》中“蜮”含沙射影的典故,巧妙的提示了晴雯之死与王善保家的这样的“蜮”搬弄是非有直接关系,故而是“鬼蜮之为灾”。
(4)于幽深下搭构典型环境。如:贾宝玉的《杏帘在望》。借助《周南·葛覃》和《鲁颂·泮水》中“入泮”“采芹”的典故,来构造稻香村人地和谐的典型环境,这其中,农家风貌是自然环境,李纨教子是社会人文环境。
3.对《诗经》的引用以《风》《雅》为主,基本没有引用《颂》。而《风》以“二南”为甚,《雅》以“小雅”为甚。
通过文本阅读与梳理,现将《红楼梦》诗词对《诗经》各部分的接受做粗略统计。概而观之,《红楼梦》诗词对《诗经》的受容,以《风》《雅》两部分为主,而《颂》的应用几乎无从谈起。如图1,横轴为回数,纵轴为诗词中《风》《雅》《颂》出现的次数。不难看出,《颂》出现的频率远在《风》《雅》之下。前八十回中,《风》《雅》各占半壁江山,不分伯仲。到后四十回中,《风》的数量远高于《雅》的数量。因此,從另一个侧面证明后四十回并非出自曹雪芹之手。为什么解释诗词要以《风》《雅》为主呢?解盦居士说:“《红楼梦》一书得《国风》、《小雅》遗意。”有学者认为,“国风就是各地的情歌——包括爱情和感情。前者如《关雎》,后者如《无衣》”郑慧生:《说“风”》,《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第75页。《红楼梦》的文本建构模式是以《国风》《小雅》的主旨作参照系的,“大旨谈情”与导人“复善”是殊途同归的。又因为,《红楼梦》中符合《颂》要求的诗词着实不多。最为明显的则是“除夕祭宗祠”一节,其楹联以《小雅·天保》中“蒸赏”一词指代祭祀之意,昭示先祖恩德垂荫万代。在最符合《颂》的情节中,居然没有《颂》的影子,所以对《颂》的有意规避,最终为《风》《雅》的大行其道提供了最为原始的可能性。
《论语·阳货》云:“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马融注曰:“《周南》、《召南》,国风之始,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纲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为,如向墙而立。”何晏:《论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77页。孔子暗喻“二南”的重要性,马融进而认为“二南”是“三纲之首,王教之端”,以儒家伦理中的纲常节义来论证“二南”的重要性。朱熹《论语集注》认为:“《周南》《召南》,《诗》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正墙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8页。也应和了马融的说法。不难看出,上述表格中引用“二南”最多的当属薛宝钗,她从儒家正统的三纲五常、修齐治平等思想出发,引用并诠释《诗经》,可见其对《诗经》的研读之深,符合了薛宝钗的人物个性。其一,以淑女君子的论调来为“金玉良缘”寻找理论依据;其二,用“二南”以正人伦的观念来规劝宝玉,以一副道学家的面孔出现在贾宝玉面前,这也正是贾宝玉厌烦薛宝钗的原因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前八十回中,薛宝钗援引《诗经》所作诗词多能昭示人物命运,彰显人物才华,体现其深受德言容功之闺训思想;而后四十回中薛宝钗援引《诗经》所作诗词,大多只是作者无关痛痒的炫技行为,而《与黛玉书并诗四章》中“惟鲔有潭兮,惟鹤有梁。鳞甲潜伏兮,羽毛何长”的慨叹,借用《小雅·白华》来感喟自己的生不逢时与怀才不遇,这与前八十回所塑造的人物性格相去甚远。故而,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绝非曹公一人完成。
4.受众是多元化与小众化的统一。
(1)文本受众的多元化。从广义的《红楼梦》诗词的受众来看,从诗词曲赋,到对联灯谜,再到酒令射覆,书信匾额,都或多或少的征引了《诗经》的内容。
(2)人物受众的小众化。从上述胪列不难看出,真正懂得运用《诗经》的是士大夫阶层,如周琼的信,皇帝所赐的匾额;其次是大观园的才子才女们,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为最;再次也是其中最少的一部分人,有如惊鸿一瞥的、深受“郑卫之音”以及前代浓词艳曲影响的优伶歌姬,如云儿等。因此,可以得出三个结论:endprint
第一,儒家文化经典仍然掌控在以士大夫为主的少数男性文人手中。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中,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当时士大夫阶层仍然钻研于儒家经典,而对其它怡情悦性之文体则显得力不从心。
贾政笑道:“你们不知,我自幼于花鸟山水题咏上就平平,如今上了年纪,且案牍劳烦,于这怡情悦性文章上更生疏了。纵拟了出来,不免迂腐古板,反不能使花柳园亭生色,似不妥协,反没意思。”
此处庚辰本作评为“是纱帽头口气”曹雪芹:《脂砚斋全评石头记》,霍国玲、紫军校勘,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208页。贾政作为《红楼梦》中相对正派的人物,其人品与官品在前八十回中毋庸置疑,他基本具备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所有特点:有忠孝节义的美德,兼之修齐治平的抱负。但是,其迂腐的一面也是不可忽视的。涂瀛在《红楼梦论贊·贾政赞》中认为:“贾政迂疏肤阔,直偪宋襄,是殆中书毒也。然题园偶兴,搜索枯肠,鬚几断矣,会无一字之遗,何其乾也?倘亦食古不化者与!孔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政之流亚也。”涂瀛:《红楼梦论赞》,见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33页。至于“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一句出自《论语·宪问》,大意是说有德者未必有才。涂瀛借孔子语肯定贾政之“德”,但对贾政的“才”却是不敢恭维的。贾政之所以有德无才,一方面,是因为贾政中了书毒。这里的“书”当然是指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就是像贾政这样的一群人,实用知识与技能寥寥无几,但是对于“书”却是烂熟于心,说明了儒家经典已经深深地烙印在士大夫的心上,官方知识下移虽有方兴未艾之势,但是其路漫长的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另一方面,康乾时期文化思想钳制较甚,士大夫钻研于古书注解与考证,对时事与实用技艺较少问津,正如梁启超所言:“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饮冰室合集》(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因此,贾政每天“案牍劳烦”,不仅说的是他要处理公务,还有的就是注释古典。
第二,闺阁之内可以研习经典,但是不予以提倡。如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中借薛宝钗之口点破玄机。
宝钗道:“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踏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大家闺秀也可以习读“正经书”,这正经书自然就是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但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训早已根植于女性心中,她们认为读书不是自己分内之事,是不应该予以提倡的,即使可以读也应该读那些“正经书”。在“无所不有”处,蒙古王府本给出一条意味深长的评语:“藏书家当留意”曹雪芹:《脂砚斋全评石头记》,霍国玲、紫军校勘,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12页。缘何要藏书家留意,薛家的藏书可能包括三类:(1)“正经”的儒家经典;(2)以《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这些“淫词艳曲”为代表的明清俗文学作品;(3)可能有一些反动书籍。在一个敏感的时代里,收藏一些敏感的书籍,并不是一种明智之举,很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难怪要“烧”掉。丁淑梅:《清代禁毁戏曲史料编年》,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在第二章“乾隆初年至乾隆末年”中,提到了“乾隆年间,《水浒》倡乱,《西厢》诲淫,金圣叹遭冥谴,《还魂》、《西厢》作者堕阿鼻”一条(参见王应奎《柳南随笔》和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和“乾隆年间,戏不可演,《琵琶记》、《西厢记》污毒古人,淫词艳曲不可作”一条(参见郝培元《梅叟闲评》),其他诸条都有明确的年限限制,可见《琵琶记》《西厢记》《牡丹亭》在整个乾隆时期都是被禁止的,是被视为淫词艳曲的。因此,“烧”了它们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和自保的选择。
根据《石头记索隐》的观点,蔡元培先生认为薛宝钗有南明遗老、康熙侍读高士奇(1645-1703)的影子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6页。,薛宝钗出现这样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戚序本的回前诗有云:“谁说诗书解误人,豪华相尚失天真。见得古人原立意,不正身心总莫论。”立松轩是在为诗书误人的观点作辩解。梁归智:《红楼梦诗词韵语新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3页。
误人的原因是个体不正身心,与诗书本身并无关联。这看似是对薛宝钗(曹雪芹)的反驳,但是他告知了读书的基本前提,就是要正身心,如果身心不正,读书也就没有意义。所以,对于闺阃之内的女子来说,可以读书,但不可大加提倡。
第三,边缘阶层研习经典,是为其谋生手段增加必要的砝码。如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中的锦香院的妓女云儿就是其中一个明证。
宝玉说道:“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字,却要说出女儿来,还要注明这四字原故。说完了,饮门杯。酒面要唱一个新鲜时样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风一样东西,或古诗,旧对,《四书》《五经》成语。”薛蟠未等说完,先站起来拦道:“我不来,别算我。这竟是捉弄我呢!”云儿也站起来,推他坐下,笑道:“怕什么?这还亏你天天吃酒呢,难道你连我也不如!我回来还说呢。说是了,罢,不是了,不过罚上几杯,那里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乱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endprint
云儿看没看过《诗经》不可考证,但就上面这段话而言,面对贾宝玉有关“四书五经”的刁难,云儿一句“怕什么”可见其底气之足,虽说不能熟谙,但是对儒家经典的大致内容应是了若指掌的。从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信息,妓女阶层开始以掌握儒家经典作为稳固自己地位的砝码。意大利学者安·罗莎琳德·琼斯(Ann Rosalind Jones)对文艺复兴时期名妓的描述同样适用于中国:“歌唱、作乐和诙谐的谈吐、通晓古典和现代文学——这些都是名妓的造诣,也是她们区分于身份较低的妓女的造诣。”[意]安·罗莎琳德·琼斯:《城市女性和她们的听众:路易斯·拉贝和维罗妮卡·弗朗哥》(City Women and Their Audiences:Louise Labe and Veronica Franco),见[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7页。无独有偶,17世纪中叶的日本名妓八千代(Yachiyo),不但能够讲解像《源氏物语》这样的文学巨著,她还工于书法,以至于“八千代体”成为当时日本妓女界的规范摹本。在几乎相同的历史文化境遇之下,妓女阶层都已经意识到,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里,要想得到身份地位质的飞跃,就必须迎合男人的文化品味与审美诉求。云儿能够出入于薛家这样的高级宴会上,其文化素质并非低级妓女可比,而且能够当场回应贾宝玉这样才子的战书的妓女,恐怕少之又少。云儿之所以能够挤进上流文化圈,其成功要诀就在于她的(儒家)文化素养为她加了分。
三 《红楼梦》诗词对先秦文化元典的受容特征
《红楼梦》诗词对《诗经》的受容,作为《红楼梦》对先秦文化元典接受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单独列出加以重点讨论。本部分拟选取蔡义江先生、陈文新和郭皓政先生、王士超先生三个版本的《红楼梦》诗词鉴赏文本(如下表1、2、3),并提取出其中对《诗经》《论语》《孟子》《庄子》的引用次数和内容,借以证明《红楼梦》的重道轻儒倾向,以及对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文化经典的接受特征。
上述三个表格存在着一个问题,即由于三个版本的解诗与鉴诗各有侧重,所以会出现同一回中诗词数目不同的情况,这里暂且忽略不计,直接讨论《红楼梦》诗词对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文化元典的受容特点。
1.对《诗经》的应用明显后劲不足。如图2所示,横轴为回目,纵轴为引用《诗经》解解诗词的次数,从中不难看出其总体下滑的走势,直到第八十七回才出现了一个小高峰,而第101-120回基本没有诗歌可言,即使有,也不存在《诗经》的诱导因子。从图二亦可以看出,王本对于诗词的解释过于细致,导致其《诗经》出现的频次明显大于其他二者;而陈本又过于忽略用《诗经》去阐释诗词的意义与出处,导致其《诗经》出现的频次明显低于其他二者。所以,蔡本的折线图更具有参考价值。又根据蔡本的曲线,后四十回出现的峰顶要比前八十回出现的峰顶高一点,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后四十回并非出自曹雪芹之手,因为后四十回引用《诗经》解释诗词的次数基本与前八十回引用《诗经》解释诗词的次数相等,故得之。
2.附庸《风》《雅》。《诗经》中的《风》《雅》(尤其是《小雅》)两部分成为解释《红楼梦》诗词的主要因素,而《颂》的应用几乎没有。如图3所示,横轴为回数,纵轴为“王本”(为效果明显,故选之)中《风》《雅》《颂》出现的次数。不难看出,《颂》出现的频次远在《风》《雅》之下。前八十回中,《风》《雅》各占半壁江山,不分伯仲。到后四十回中,《风》的数量远高于《雅》的数量。研读后四十回的文本可知,抒情成分锐减,且诗词引用《诗经》体现的只是随意掇捡并穿插其中的力不从心,与前情诗词中惨淡经营所塑造的人物性格与文化旨趣均相去甚远。因此,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后四十回并非出自曹雪芹之手。为什么解释诗词要附庸《风》《雅》呢?《红楼梦》“得《国风》、《小雅》遗意。”《红楼梦》的文本建构模式以《国风》《小雅》的主旨作参照系,又因为,《红楼梦》(尤其是前80回)对儒家学说颇有微词。故而,《红楼梦》中符合儒家颂圣要求的诗词着实不多,所以《颂》出现的频次远在《风》《雅》之下也就不难理解了。
3.《诗经》优先与重道轻儒。在同一个词或意象出现的时候,诸位学者优先选择《诗经》而不会选择其他经典。如图4所示,横轴为回数,纵轴为蔡本(为效果明显,故选之)引用《诗经》《论语》(《孟子》)《庄子》解释诗词的频数,不难看出,《诗经》的运用率远大于其他三本经典的运用率。又因为《诗经》是诸子文学共同的源头与参照,暂且把《诗经》的儒家特性抹去,可以看出,《庄子》的应用率(14次)大于《论语》《孟子》合起来的运用率(7次)。这就证明了《红楼梦》重道轻儒的思想倾向。正如解盦居士所言,《红楼梦》得“《国风》、《小雅》遗意,参以《庄》《列》寓言,奇想天开,戛戛独造。”由于中国文化中许多专有名词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当中,《诗经》优先是种必然,而《红楼梦》中,消极遁世和色空观念均可与《庄子》互为表里。故而,以《诗经》为“意”、以《庄子》为“参”的重道轻儒的价值取向,成为《红楼梦》受容先秦文化元典的基本特征。
在《红楼梦》第十七回中,曹雪芹借贾政的疑惑阐释了他题写诗词的一个基本原则。“方才众人编新,你又说不如述古;如今我们述古,你又说粗陋不妥。”可见,如何处理“编新”与“述古”的关系,决定着诗词能否臻于化境。一味“编新”未免有生涩隔阂之感,一味“述古”亦有陈词滥调之憾。只有“编新”与“述古”熔裁自然,“编新”作为“述古”的终极目的,“述古”作为“编新”的文化基因,二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才能淬炼出好的诗词。在《红楼梦》诗词话语形成的过程当中,先秦文化元典,作为“述古”的一种构成符号,在“编新”的过程中,在其本意的基础之上已然生发出新的文化内涵。正如福柯所言:“诚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話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不可减缩的东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53页。
《红楼梦》的作者作为稗史巨子,在征引先秦文化元典的基础之上,完成了《红楼梦》诗词话语浇自家块垒的这种“不止”的过程。正如洪秋蕃所言:“《红楼》妙处,又莫如讥讽得诗人之厚,褒贬有史笔之严……《红楼》真枕经胙史之文。”洪秋蕃:《红楼梦抉隐》,见一粟:《红楼梦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42页。李劼亦认为,《红楼梦》在风格上“如同《诗经》中原始民歌那样淳朴清新”,并把《红楼梦》“在气脉上对文化原始性的这种承继称之为文化皈依”李劼:《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84页。
有清一代,“《诗经》文学阐释者将诗教之情感延展到怨怒等激愤之情,使得《诗经》的文学阐释不再局限于‘中和‘含蓄这一狭隘的视域”何海燕:《清代<诗经>的文学阐释及其文学史意义》,《文学遗产》2016年第5期,第100页。这种新质的产生,为文学作品吸收《诗经》维度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以《红楼梦》诗词为个案来管窥《红楼梦》对以《诗经》为代表的先秦元典的受容情况,可以证明《红楼梦》在语言包装、行文建构、人物塑造、宗旨意趣等多方面都接受了《诗经》。这些正是“得《国风》、《小雅》遗意”,“以《国风》正贞淫”,以“《诗》学美刺”的最好注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