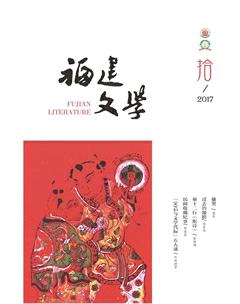奇人
黄长贵
一
地处闽西上杭腹地的泮境乡,是个茂林修竹、清静优雅、民风淳朴的小镇。小镇的中心有集市,集市又叫“圩”。每逢农历一、六(初一初六,十一十六,二十一二十六),乡民们便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前来赶集,当地人叫“赴圩”。圩便成了全乡人气最旺的地方,贸易集散地。因为小乡镇地缺人稀,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所以很少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大新闻,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随遇而安,每天演绎着相同的故事。
然而,在这个小圩上,却住着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小人物,村民们叫他“金佬公”,和他同龄人叫他金佬师傅。又因他讲话有点口吃,常常把“浊”说成“毒”,把“俺”(即我)说成“?”,所以调皮的后生们常在背后称他“?佬子”。其实他的大名叫范振文,是一位以制陶瓷器皿为业的手艺人。
金佬公生于1893年12月,和我们时代的伟人恰巧是同年同月的同龄人。世祖山西高平郡,先祖入闽地连城文亨乡李屋坑,世代制陶瓷。据说,其先祖兄弟俩在两三百年前,因为生计,一个前往泮境乡碗厂开居,一个前往湖洋乡五坊村创业。金佬公的祖上就是迁往湖洋乡五坊村的那一支脉。
我们儿时眼中的金佬公,那时五六十岁,中等身材,面色白净透红,很慈祥,对人总是笑盈盈的。头发开始花白,说话有点口吃,热天经常光着上身,平时穿一件黑色对襟布扣上衣,一条浅蓝色的粗棉布裤子,平底鞋。一到冬天,他就穿着一件黑色大面襟皮袄,一件卷毛的绵羊皮袄,那毛色都很黄了;一件是质地很好的山羊皮袄,那毛很长,竟然可以倒过来顺过去,光洁如缎。他留着三寸来长的白胡须,总是精神矍铄的样子。他性格随和,耿直,不修边幅。因为天天要去做手艺活,身上和头脸常常沾着白色的瓷土。有些胡须卷曲着,有些人便很谐趣地在背地里叫他“曲须佬”。
金佬公家曾有一个高一米、直径三十厘米左右的青花瓷瓶,听说是清代雍正年间景德镇的产品,也有人说是德化的,无从查考,一直放在二楼大厅天子屏风前的神案上。花瓶上用蓝色颜料,画着一株硕大挺拔的青松,树枝上站着两只丹顶白鹤。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一个识货的、外来的古董商用十元钱买走了。后来每当提及此事,家人一直懊悔不迭。
金佬公一生都爱喝点小酒,爱吃汤圆和糍粑。他常说:“猪补三(意思吃一次猪肉可以滋补身体三天)狗补七,糍粑能补十二日。”他吸旱烟,身上总有一股烟味。他有长短三根不同造型的烟杆,总有一根不离身,出了家门,就带一根约两尺长的短杆的,两根长杆的就放在家里。那烟杆都是从多年生的柑橘树中挑选出来的极品,大拇指粗细,最难得的是三根烟杆旁边都还有一根带刺的藤条,从小就紧紧地偎依着,缠绕着这棵柑橘树一同长大,从根部一直到末梢,绕了五六圈,虬龙一般。用的年代久远了,发出金铜般亮的光泽。制作烟杆时,是用一根烧红的粗铁丝,从柑橘树的末梢中间烧个洞,一直通到根部,根部大,做成装烟丝的烟斗。一有空闲,金佬公就拿起旱烟杆,装上金黄色的土烟丝,吸完后,举起烟杆望鞋底轻轻一磕,那烟屎就掉下来,换上一袋烟丝,又美滋滋地吸起来。这时候,金佬公总是眉头舒展开来,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二
1942年春,金佬公在上杭湖洋乡五坊村的老家发生了一场变故,只身来到泮境乡范家陶瓷厂,当地人称为碗窑下,投奔同宗梓叔谋求生计。他身怀建造碗窑和装窑(把做好的泥胚胎放进窑中烧制成型)的绝技,很快就在这里打开了局面。泮境乡盛产高岭土和马尾松,这都是烧制陶瓷器的必备原料。时当地范家、江夏村、凌屋村、院康村吴屋两三个村庄,及地名香公檀嘴上和陂隔里,共有五六个村落都开办碗厂,非常需要金佬公这样的能工巧匠。从事陶瓷业的人都知道,建窑和装窑都是瓷器业的顶尖技术活,但又是非常辛苦的消耗体力的活,通常半天干下来,全身衣服都能拧出水来。尽管这活的薪酬高,能硬顶硬的师傅还是凤毛麟角。许多年轻人不是学艺不精就是吃不了这个苦而半途而废。也许是学习任何技术都是易学难精吧,“千人学艺,出头一人”。天赋与体格缺一不可,金佬公得天独厚,二者皆备,日后自然成了这五六个村碗业行的座上宾了。当然,用当下时髦的说法,他也因此赚到了“第一桶金”。
1943年,对金佬公而言,那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正当他在泮境各个碗厂打开局面、事业顺风顺水,生活也安定下来时,一天下午湖洋乡老家来人,没说什么原因,只是叫他火速回湖洋去,说完来人就走了。他感到有些忐忑不安,于是临行前去到碑头三闾大夫(屈原)神庙去占了签,是第十六签:《赵子龙抱阿斗》,其后两句判词为“忽然跳出超群路,进万军中第一名”。他立即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草草收拾行囊,动身回家。走了五六个小时的山路,晚上九点多钟到达家里时,才知道老伴因急病于傍晚時分逝世。金佬公料理完后事,考虑到自己还得回泮境谋生,从长远看,必须把两个儿子送回连城祖基地,毕竟那里才是根之所在。于是,怀着一腔悲痛,继续回到泮境从事碗业。
同年秋天,一场意外又一次改变了金佬公的人生轨迹。从碗窑下到泮境圩,有两华里路,中间要经过一个姓黄的村子叫“江夏村”。村里的祖先是从湖北武汉入闽的。客家人遵循“无论子小走万里,改名改姓不改郡”的祖训,所以村名仍旧叫“江夏”。当年,五六十口人,半工半农,即忙时种田闲时做碗。从事这陶瓷业是一项很繁累人的手工艺活。首先得靠人工从山上把瓷土挖出来,用箩筐挑回厂里,通过水碓(一种借助水的推力带动装置,把瓷土捣碎)加工,再过滤出去除了杂质的瓷土,这中间要经过若干道工序,才能让瓷器的坯胎形成。所以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有活干,男人一般从事技术活,女人都干繁重的杂活。
这黄家有一户人家有三兄弟,长大后老三无嗣,于是去何家抱了个童养媳,当地人叫“等郎妹”。若干年后的一个冬天,也是一个湖洋乡来的林姓木匠,在这个村里揽活干,因家境贫穷,经村里人撮合,愿意入赘,就和黄家这位姓何的童养媳结成了夫妻,生下了四男两女。日子虽然过得很清苦,但因人丁兴旺,老三心里那高兴劲就别提了。不料天有不测风云,那年快到旧历年底时,听说有一伙外地来的土匪到泮境来偷耕牛,还带了枪来,说是偷走了好几头耕牛。有人说,土匪是湖洋乡西门背一带人的口音(泮境在上杭城汀江河东面,人称“东片”;湖洋在上杭城汀江河西面,故人称“西门背”)。当时,泮境和茶地同属国民党管辖下的茶境乡,乡公所设在茶地,乡长是温子祥。乡公所和当地的保甲长们凭着人们这一口说无凭的猜测,认为当时只有黄家这个入赘的林姓师傅是西门背人,除了梁山哪有贼?一定是他勾结了土匪做眼线,于是不容置疑,连夜五花大绑将这位林姓师傅抓到乡公所去严刑拷打。第二天一早,在押回泮境的半路上就把他枪杀了,连脑壳都打飞了!这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场突如其来的横祸,给这一家带来了灭顶之灾,两位老人两年内相继含愤去世。
何家大嫂孤儿寡母怎么活?只好把两个女儿送给别人当童养媳,最小的儿子送给白沙乡一个罗姓人家。即使这样,还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子怎么办?最大的儿子才十虚岁呀!可这何大嫂是个很有志气的女人,三个儿子就是她活下去的希望,无论吃再大的苦,就是乞讨也要把他们拉扯大。她忍辱负重,承担起了养育三个儿子的全部重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忙完家务农活,再到碗窑干最苦最累的活,为的是能多赚一分钱。到了第二年,这金佬公只身在碗厂做手艺,了无牵挂。何大嫂在碗厂做帮工,几年的相处,深知这金佬公为人耿直对人热心,手艺又好,对他很有好感。想到自己家庭的窘境,想到自己和儿子们日后都必须有个依靠,就含着眼泪对金佬公师傅说:“能不能救救我这个家,救救我的三个儿子?”金佬公当场没有答应。第二天,她又一手拉着一个儿子,背上还背着小儿子,让两个儿子跪在金佬公面前,母子四个哭着再一次求他。金佬公考虑良久,一方面被他们母子的诚心打动,一方面激起了他人性的恻隐之心,终于点头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于是一个新的、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家庭组成了。
金佬公进入黄家后,把三个孩子视为己出。俗话说,家有千金不如一艺在身。待孩子们稍长大,金佬公就手把手教他们学技艺,给老大老二建了做碗的厂房。做碗的瓷土从山上挑下来后,需要加工、粉碎、去除杂质,这需要专门的厂房设备,要利用水资源,厂房要建在合适的位置,开山筑水坝,修渠道,建厂房,当地人叫碓寮,要大量资金,全靠他一人操办。原先全家挤在一座几百年前老祖宗建的才三四十平方米的土坯房间,每逢阴雨连绵,特别是下暴雨时,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雨停了,里面还“滴答滴答”地下小雨。金佬公给这个家盖起了一幢一进三间的楼房,接下来又给老大老二讨老婆。待老三读完初中,又送他到龙岩学开汽车。在新中国刚成立的20世纪50年代,能去学开汽车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1946年秋天,金佬公考虑到在连城的两个儿子都长大成人了,总得成家立业,自己身边也要有个亲生儿子,就准备在泮境圩上开居,当即向李层村的李霞东买了一块地皮,这块地皮在市场上共花了五十块光洋。他曾告诉家人说,其中有三十块是民国三年(1914)的“袁大头”,二十块是“孙中山”。还说,“袁大头”比较值钱,每块光洋重七钱二,“孙中山”只有六钱八。我们都很少见过光洋,是否这样就不清楚了。金佬公于是在泮境圩上建起了一幢前后二进三屋的楼房,那建房所用的杉木,都是在老远的“陈婆寨”山上采伐买来的,质地非常好。翌年,他把十四岁的小儿子从连城接过来带在身边学艺,后来,给他讨了老婆。说来真是无巧不成书,这媳妇就是黄家何大嫂的二闺女。虽说是父母之命,但为了尊重客家人传统的习俗,还是请了媒人,这桩婚姻也就成了媒妁之言。这样,金佬公就有了两个家,虽然生活压力大些,但总是其乐融融。
三
在我们当地,金佬公是最相信风水说的男人,对简单的“论八字”“看阴阳”“掐时”(本地人称“捏时”)和“二十四个山头来龙去脉”,以及什么“案山”“面山”“沙手”“走口”之类他都能说出些道道。
金佬公一生对人慈祥,古道热肠,乐善好施。他常说:“害人之心不可有,害人终害己。”“世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中存一点子种贤孙。”他常劝大家多多行善。他说:“有钱之人赐功德,修桥、铺路、做凉亭;无钱之人赐功德,搬开(挡路的)石头,捡开‘勒(带刺的荆条)。”金佬公曾算过几次“命”。他小时候父母为他论过“八字”,做过“留言”,都说只能活到五十七岁,到了那年,就双枪插地——无路可逃了。
五十七岁那年中秋,他一早就动身回湖洋探望亲人。那时还不通车辆,往返两地之间全靠两条腿,而且都是山路。但他们兄弟每年至少互相探望一次,每次都是带上十来岁的孙子做伴。那次中秋回湖洋,走了十里山路,都是爬坡。终于到达山顶的枫亭里,就走进亭子里坐下来,吸袋旱烟休息一会儿。刚在石板凳上坐下来,就看见靠墙有一个蓝色的紧口小布袋。一拿起来,就觉得沉甸甸的,拉开一看,都是银圆、铜钱、银毫子。他就放进贴身的衣袋里,吸完几袋烟,正准备起身赶路,只见一个中午妇女急匆匆走进亭子里来,看见他就问:“大伯,请问一下,你见到一个蓝色的布袋子了吗?紧口的袋子……”
金佬公见她说是蓝色的袋子,就问:“装了什么东西啊?”这妇女立即说:“装了钱,去城里给我婆婆抓药,刚才坐在亭子里吃点东西,动身時放在墙边的袋子忘拿了。”金佬公确认了她是失主,就从衣袋里掏出袋子,交给她说:“我也没数多少钱,你数一下,看看还有没有那么多。”她接过钱袋,千恩万谢,说:“哪里还要数?你真是我们一家的救命大恩人,真不知怎么感谢你。”说着就要跪下去。金佬公连忙阻止她,说这东西本来就是你的,不要谢。后来他们就一起走路到上杭城。交谈中,知道她是泮境乡定达村何屋人。金佬公到湖洋后把这件事告诉了长兄振光。振光对他说:“金佬子,你不是算了命逃不过今年吗?现在不怕了,虽然俗话说‘有捡捡得,冇捡做得,但你把捡来的钱还给人家了,就是救了人家的命,就是做了善事,天老爷有目珠,会给你增加阳寿的。”后来,金佬公活到了九十四岁才逝世。他是当时我们泮境圩上最长寿的男性。
金佬公还跟我们讲过一件很神奇的事。那是有一年初夏,他接到老家来信,要他尽快回去办件事。他想,反正天气不冷,又有月光,不如趁天黑前还能走一段路,现在就启程。于是,他带着烟杆、手电筒、一把雨伞立即就出发。走了五里路,到了叫“可以亭”的地方,天已暗下来了,他想,干了一天活,干脆吸袋烟再走。然后,他借着手电筒的光又走了十里路,到了最险峻的地段,地名叫“猴子额”。顾名思义,这里山势陡峭,周围高山深壑,角蛙在深涧里发出“嘟嘟嘟”的叫声,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着,忽然手电筒照着眼前七八米的地方,一只斑斓猛虎正在路中间慢慢向他走过来!那猛虎的两只眼睛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发出令人胆裂的寒光。金佬公惊出了一身汗,心想,这下完了,怎么办?他忽然想到手里拿着一把雨伞,是油纸做的雨伞!他赶紧把雨伞打开来,手电筒照在纸伞上,然后慢慢把伞收拢,又慢慢撑开,反复了几次。老虎停止了向前,呆立一会儿,眼睛盯着眼前这忽大忽小的怪物,慢慢地掉转头,从旁边的一棵松树边转了个弯,终于不见了。金佬公站在那观察了许久,感觉危险已经过去了,立即加快了脚步奔向县城。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夜走山路了。
金佬公还会“掐时”。邻居们有时一些家禽走丢了,或在那通讯不便的年代有亲人出门未按时到家,家里人着急了,就来找他掐时,有时还挺准的。他会告诉你丢失的东西还能不能找回来,要在什么方位去找。出门的亲人今天会不会到家,还常常被他说准了。后来,我们问他怎么回事,他毫不保留地告诉我们说,这是撞机,要随机撞,不能故意有心去设定。如果不是随机就不会准。他说,掐时其实很简单,首先你对天干、地支、八卦要熟悉。然后伸出你的左手,用大拇指去点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个指头有三个节。那么,按农历的历法来计算,食指靠近掌心那个节就设定为正月和七月;食指顶上那个节设定为二月和八月;中指顶节设定为三月和九月;无名指顶节设定为四月和十月;无名指靠近掌心那节设定为五月、十一月;中指靠近手掌这节设定为六月、十二月。然后月上起日、日上起时。这六个指节又依次固定了口诀,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分别设定为:大安、流连、速喜、赤口、小吉、空亡。比方有人来掐时,问丢失的东西还能否找回,只要你随意报个时辰就行了。比方三月十七日,你报了个酉时,那么三月为中指顶节,食指第一节为十七日,无名指顶节为酉时。而无名指顶节为固定的“赤口”时,口诀是“赤口路上走”,那么丟失的东西可能已经迷路,被野兽叨去或被人偷走,找回来的希望已不大了。如果要找,必须立即抓紧,而且有可能还在不会很远的范围内。
金佬公说,如果丢东西的人不会报时怎么办?那也能掐时,他告诉我们,也有一个口诀,但你对八卦方位要熟悉,更不用说天干、地支了。他说,这口诀是:一、甲震乙离丙坤,丁乾戊坎己巽门,庚日失物兑上找,壬癸可在艮上寻;二、甲已阳人乙庚阴,丙辛童子暗来侵,丁壬不出亲人手,戊癸失物不出门;三、子午卯酉在路旁,庚申己亥归他乡,辰戊丑未身未动,书书参差细推详;四、甲乙五里地,乙庚千里乡,丙辛整十里,丁壬三里藏,戊癸团团转,此是失物方。金佬公把掐时的方法传给了他的孙子,现在村民们有时会请他的孙子们讲一讲掐一掐,他们都会毫不保留地告诉他们。
说来也许不相信,金佬公一生从来不生病,有时咳嗽几声,那也是吸旱烟引起的。可是,在他七十九岁那年,忽然不知得什么病,一直高烧不退,昏迷了两三天,家里人急得团团转,抓了几帖中药吃下去,就像热汤泼在冷石板上,毫无反应。家人们以为他大限已到,都给他准备后事了。那个在龙岩汽车队当书记的三儿子闻讯赶回,拿出一根羚羊角,在一个陶罐的底上放了点水,然后用羚羊角磨出了一小杯水,给金佬公灌下去。奇迹出现了!金佬公几天来的高烧竟然瞬间退去,很快就恢复了神志。第二天杀了一只小母鸡给他炖汤喝,第三天便复原如初了。
那时,乡村缺医少药,村里的小孩子有时发烧,金佬公就教给大家一个土方法,泡上一壶浓浓的茶,放上一把盐巴,大人用嘴含在口里,对着小孩的肚脐,吐出来,吸进去,换口茶水再吸再吐,几次就好了。金佬公说,这样就能把孩子肚子里的邪秽吸出来,就没事了。有人挑担走了很远的路程,回来后脚又酸又痛抬不起脚来,甚至脚都肿起来了,金佬公就教他,赶紧将双脚伸到尿桶里去浸泡一两个小时,包你没事。以前农村人哪有卫生间?加上种菜要用农家肥,人粪尿都会用专门的器皿盛放起来加以利用。金佬公这个治疗方法不花钱又见效快。
金佬公不是名人,更不是什么伟人。但是,在我们泮墟,人们称他是一个奇人。他传奇般的人生,是非常精彩的人生。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三五年之后,就很少有人会提及他,但金佬公不同,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泮境圩和周边的邻居们仍旧不时把他的名字挂在嘴上,他给所有认识他的人留下了深深的、难以抹去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