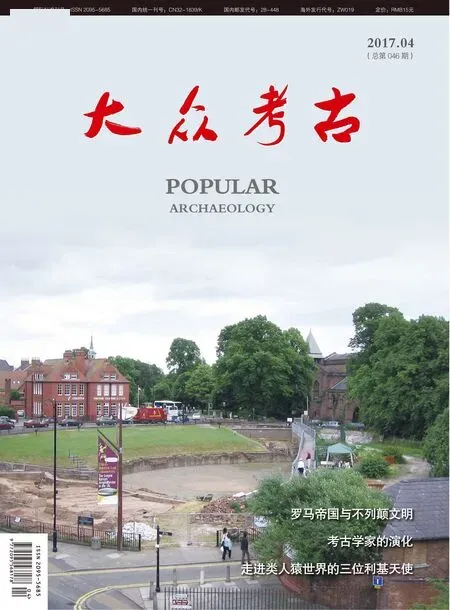千窑难烧一宝器河南大学文物馆藏铜红釉瓷器赏鉴
文 图/张建妍
千窑难烧一宝器河南大学文物馆藏铜红釉瓷器赏鉴
文 图/张建妍
“古瓷以单色釉为贵,单色釉中铜红为最”(清代陈浏《匋雅》),中国古陶瓷中的铜红釉瓷器以其种类多样、品种繁复、装饰华贵而闻名古今中外,包括釉里红、霁红、郎窑红和豇豆红等品种。河南大学文物馆藏有几件铜红釉瓷器,这里介绍出来,与大家共同赏鉴。

元·釉里红缠枝花卉碗
釉里红缠枝花卉碗
这件釉里红缠枝花卉碗,胎白精细,内外施釉,釉色白中泛青。碗直口微敞,唇沿比较薄,腹较深,圈足底无釉。纹饰皆施釉里红彩,碗内底绘折枝牡丹,内壁绘缠枝菊,外壁为缠枝牡丹,口沿内外及足部以回纹装饰。整体纹饰线条流畅,釉色红白相间,运笔舒畅,浓淡有致,凝重华丽,是釉里红早期的产品。因铜红在高温下易挥发,加之元代釉里红的烧制技术尚未成熟,故这件釉里红碗纹饰整体红色较暗。
釉里红的工艺方法与元青花的烧制工序大体相同,即先以铜红料在白胎上绘制纹饰,其上再施透明釉,于1250~1280℃高温还原焰气氛中烧制使釉下呈现红色纹饰,故名“釉里红”。元代釉里红存世稀少,民间有“十窑九不成”的说法。我认为原因有三:首先,由于铜离子对温度极为敏感,在窑炉中火候不到会呈现黑红色或灰红色;火候稍过铜离子便极易挥发,从釉层中逸出,呈现特有的飞红、黑斑或晕散,因此元代能够成功烧制纯正红色的釉里红的数量极少,可谓寥若辰星。其次,还与元代的民族文化心理有关,即蒙古人尚白。最后,用蓝色装饰器皿和建筑是伊斯兰文化的传统,因此元青花成为外销瓷器的主角,釉里红无法形成规模生产。
霁红瓶
霁红初期称为“宝石红”,而后亦称“祭红”“积红”,也是铜红釉瓷器的一种,和釉里红一样以铜为呈色剂,用普通制釉原料,加入釉灰、氧化锡,氧化铜含量少于1%,生坯挂釉,经1300℃左右高温还原焰烧制而成,釉面凝厚莹润,色调深红,釉子浓郁呈失透状,像是暴风雨后晴空中的红霞,故名“霁红”。
霁红器盛行于清代康雍乾三朝,其最典型之处在于器口与足根处均有醒目而地道的“灯草边”。清人龚鉽在《景德镇陶歌》有载:“官古窑成重霁红,最难全美费良工。霜天晴昼精心合,一样搏烧百不同。”由此可见霁红器是在釉里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与釉里红一样难以烧制成功,成器中有“大清康熙年制”官窑款识者当是最为珍贵的。

清·霁红瓶,喇叭口、长颈、阔腹、圈足,口径14厘米,底径13厘米,腹径2厘米,高34厘米


清康熙·郎窑红双腹碗, 喇叭口,双腹,腹壁弧收,圈足,口径20.5厘米,底径7.5厘米,高10厘米
关于霁红器的用途,清代蓝蒲《景德镇陶录》中有记载:“霁红也,肆考纪明厂窑作祭红,潘阳唐公记今厂器作霁红,而陶俗皆作济红,其实祭红为是,盖宣窑造此,初为祭郊日坛用也,唐窑纪霁红由宣窑霁青推写耳。”由此可知“霁”通“祭”,释为“祭祀”,也就是说霁红器可能为祭祀仪式上的器物。
河南大学文物馆藏的这件霁红瓶器形完整,釉面釉汁凝厚,釉色深红,色调均匀,失透深沉的红色在灯光的照射下娇而不艳,华而不媚,为清代官窑的典型作品。雍正时期,因上层统治者的独特爱好,霁红釉釉面润泽,釉色分深、浅、浓、淡,这一点可作为康熙与雍正年间制品的简单区分。乾隆年间的釉里红制品除御窑厂外,民窑也有烧造,质量上具有明显的界限,不流釉,不脱口,不开片,当是精品。
郎窑红双腹碗
郎窑红又称“牛血红”,其釉色鲜红艳丽,因18世纪始产于清朝督陶官郎廷极所督烧的郎窑,并对当时官窑与民窑的制瓷业产生深远的影响,故名“郎窑红”。
郎窑红器一般釉面光泽强烈,釉子清澈透明,光亮夺目,可谓“明如镜,其润如玉,其赤如血”。其典型特征即在于釉的流动性较大,釉色的变化活泼、灵动、多姿,因此口沿下常显露白胎,底足有一圈深褐色积釉,但不过足,素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风貌。值得注意的是:郎红器均无款,底足与器内或呈米黄色或呈浅绿色,俗称米汤釉与苹果青釉,也有少数底为本色的红釉底。至于米汤釉与苹果青釉形成的原因,陶瓷考古学界一般认为是其装窑烧制时使用垫饼垫底,器物圈足内壁被封,器物圈足部位与上端的烧制温度不同而造成的。

清康熙·豇豆红小碗,直口、弧壁、低圈足,口径12厘米,底径4厘米,高5厘米
河南大学文物馆收藏的这件郎窑红双腹碗格外醒目,该器为康熙年间的制品,1975年从河南省博物馆调拨而来,釉面光洁,口沿露出一圈白色胎体,底足褐色积釉明显,将“脱口垂足”的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用放大镜可以见到,该器釉内气泡既细小又稀疏,堪称郎窑红器的典型代表。“若要穷,烧郎红。”民谚一语道破郎红器的珍贵。
豇豆红小碗
豇豆红又有“娃娃脸”“桃花片”“美人醉”之称,其实就是淡粉红色,有如红豇豆一般而得名。其釉质一般匀净细腻,粉质红釉往往散缀,因烧制时氧化还原不同形成天然的绿斑苔点。豇豆红釉色有等级之分:上乘者名为“大红袍”或“正红”,釉色明快鲜艳,通体一色,洁净无瑕;居中者釉如豇豆皮,含有深浅不一的斑点,柔和悦目;下品者或色调更浅或晦暗浑浊,一般称之为“乳鼠皮”或“榆树皮”。豇豆红一般以小件器为主,小巧玲珑,如文房用具、太白尊、石榴尊、苹果尊、洗、印盒等。
河南大学文物馆的这件豇豆红小碗采用“吹釉法”上釉。“吹釉法”就是《南窑笔记》中记载的“吹红”,是在坯胎上先施一道青白釉,然后将桃花片呈色料吹在上面,如此工序重复两次,再在还原焰气氛下以1250~1280℃温度烧成。这件器物器身和口沿露出缺陷美的绿斑苔点,呈现出桃花春浓般的奇趣,如清人洪北江的描述:“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豇豆红器的三行六字款识值得一提。三行六字款识于明宣德与万历年间始用,清康熙年间的器物底部较为多见,其写法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件“大清康熙年制”的豇豆红小碗,其“熙”字四点为顺点,无逆点;“年”字一竖较长,三横中前二横较短,第三横较长,款识外饰有单圈,是康熙年间的典型器物。据检测分析,豇豆红器上的铜离子在器物上的不同地方其存在形态、质地、密度以及颗粒大小是不同的,所以才会呈现千变万化之色。在没有先进的科技设备的条件下,我国古代工匠能够制造出如此杰出的作品,其伟大的探索精神和辛勤的劳动值得被称颂。
釉里红、霁红、郎窑红和豇豆红均以铜红作为呈色剂,使用不同的烧制方法,呈现着不一样的外观状态与视觉冲击,这充分体现了古代工匠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技艺。如果说釉里红是工匠的偶然获得,那么霁红、郎窑红与豇豆红的出现展现的则是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其实,一件器物的诞生代表的并非器物本身,而是一个浓缩着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综合体或者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致谢:文章经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丽娜副教授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