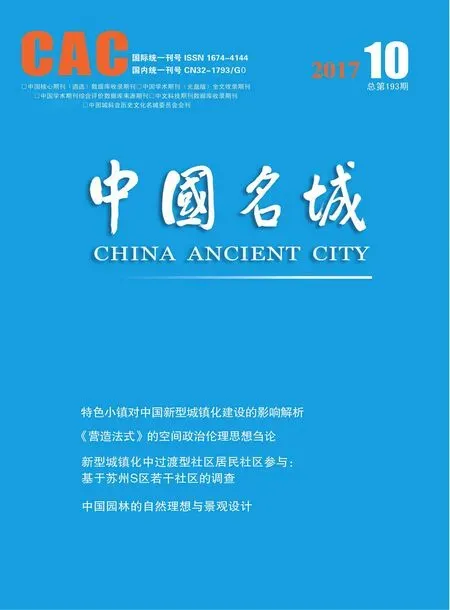新型城镇化中过渡型社区居民社区参与:基于苏州S区若干社区的调查*
张 晨
新型城镇化中过渡型社区居民社区参与:基于苏州S区若干社区的调查*
张 晨
基于对苏州S区三个城乡结合部的过渡型社区819位居民的问卷调查与访谈,分析了该类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的行为及其效果,并利用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回归分析等对过渡型社区居民社区参与效果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具体包括:社会参与意愿、政治参与意愿、实际参与行为、社区参与效能感,研究发现:第一,过渡型社区存在着政治冷漠倾向,高参与意愿和低参与行为并存;第二,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满意度对社区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第三,本地居民和外地居民在社区参与行为上差异明显;第四,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影响居民社区参与行为。
过渡型社区;社区参与;因素分析;结构方程模型
1 引言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相伴随出现了流动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务工的浪潮。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则更是掀起了新一轮城镇化运动的高潮。与此同时,在各大城市周边,处于农村与城市交界处的城乡结合部地区也伴随着城市的扩张而出现了大量主要由政府投资的失地农民拆迁安置小区,大量失去土地的、“退壳的农民”从此开始了向市民的转变。在苏州S区,源自于当地大量制造业为主体的外向型经济的繁荣,这些失地农民的拆迁安置小区由于天然的区位优势及价格因素吸引了大批流动人口入住,主要由失地农民和流动人口组成的、有别于城市街道社区和农村村落社区的第三类社区——“过渡型社区”[1]应运而生。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为共同体而存在的社区,离不开居于其间的居民对社区事务的积极参与;也正是社区参与带来了社区生成过程中人际信任和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因此,社区参与成为考察“过渡型社区”生成和演化的重要维度。然而,身份转变中的失地农民和外来流动人口,使得此类社区的人口具有不同于以往社区的强烈的异质性,这导致了过渡型社区的社区参与呈现出不同于其他类型社区的复杂特征。本文以苏州S区的三个过渡型社区为研究对象,考察该类社区的社区参与状况,分析影响该类社区社区参与的主要因素,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过渡型社区社区参与状况和效果的对策思考。
2 研究设计
目前国内的社区参与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城市社区参与的关注。多数学者认为当前社区参与总体上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参与愿望较强,但实际参与率不高;参与方式被动多,主动少,执行性参与多,参与层次不高;参与面窄,专业水平低,个体化参与多,组织化参与少;政治性参与少,非政治性参与多,参与领域不平衡,参与不深入;参与渠道不畅;社区参与机制运行的行政化严重。居民参与意识侧重于关系自己切身利益(主要是物质利益)的公共事务,不太注重社区文化生活与其他重大社会事务的管理。[2]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我国的城市社区参与正也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参与渠道、参与形式和参与内容都有所变化。而对于社区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较少,有学者对上海市社区居民参与意愿进行了定量研究,并得出结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受到其个人背景,其所处的社区环境的影响,且社区环境的影响力大于个人背景的影响力[3]。
关于社区参与问题的研究方法上,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城市社区,采用的多是定性研究或较浅层次的描述性的定量研究。本研究则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在两点上有所推进:⑴将社区参与问题的研究,从城市社区拓展到过渡型社区;⑵在对过渡型社区社区参与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性定量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究社区参与的各种影响因素,从而为过渡型社区的社区参与寻求改进之道。
2.1 问卷设计
综合前人研究及课题组实践,我们主要从居民的社区参与效能感、居民社区参与意愿、居民社区参与实际行为来综合评价过渡型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我们设计的“过渡型社区民众社区参与意愿与行为调查问卷”共5部分,分别为社区参与效能感(即居民对待社区活动与自身利益关联的认同感)、社区参与意愿、实际参与行为、社区满意度以及被调查者身份信息,前三部分详见表一。

表1 过渡型社区居民社区参与指标
2.2 数据来源
本文所依据的数据资料来自于2012年7月在苏州S区金益新村、莲花新村、淞泽家园三个社区所作的“过渡型社区民众社区参与意愿与行为调查问卷”的一部分。在了解各社区楼宇分布后,本次调查的抽样方法采用多级整群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入户收集信息。考虑到样本总体的规模,抽样的精确性,总体的异质性程度以及研究者所拥有的经费、人力和时间等因素,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最后回收并剔除无效问卷后共819份,回收率为81.9%。
2.3 数据处理
2.3.1 调查者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受访者基本情况主要包括: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政治身份、户口所在地、月平均收入等。详情见表二。
2.3.2 数据信度分析
问卷数据的信度分析,本文对调研数据的信度检验采用Cronbach α系数作为检验标准。经计算,调查问卷数据的总Cronbach α系数为0.706,这表明,问卷测量变量的设计达到信度要求,符合我们的预期目标。
3 结果及分析
3.1 探索性因子分析
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前,我们要对样本进行KMO样本测度和Bartelett球体检验,以确定调研数据是否适合用因子分析。经检验,论文数据KMO统计值0.708,Bartlett球度检验卡方值为1672.835,自由度为45,相伴概率为0.000,两者都表示调研数据样本量充足,适合做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提取,并按符合共同性标准的原则提取4个公因子。所有指标的共同度最小也达到了0.578,从表三可以看出,采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后,前4个因子的特征根均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达67.233%,说明这4个因子保留了原始数据中的大部分信息。
提取结束后,借鉴信度检验原理,把样本随机分成两部分,并对这两部分的被试结果进行因素分析,一共进行5次,发现累积解释比例基本达到65%以上,表明表三所示4个因子的解释是稳定的。

表2 受访者基本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表3 特征根和方差解释比例
从表四结果显示10个指标被概括为4个因子,根据各因子包含的内容分别命名为社会参与意愿因子、政治参与意愿因子、实际参与行为因子和社区参与效能感因子。
将4个因子得分按照标准分转化为0-100的值,其分布详细情况见表五。其中社区参与综合评价值是以4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进行标准化然后转换为0-100的分值。社区居民社会参与能力平均得分为72.18分。各项得分中,社会参与意愿因子得分较高(M=82.81),并且呈现明显的左偏和尖峰分布,说明分布在平均数上下较多,且多高于平均值。这表明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一般性活动,如文体、公益活动等的意愿是比较强的,调查的另外一题居民最乐意的社区参与形式证明了这一点,如图一。居民政治参与意愿(M=82.29)得分也较高,社区参与效能感得分(M=83.93)也较高,这表明过渡型社区居民有着较为强烈的社区参与意愿和效能感。但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则是实际参与行为(M=64.28)的不理想,平均得分远低于另外3个因子,且呈现右偏分布,表明较多的人仍在平均分下方,只是一些社区参与的积极行动者拉高了平均分。过渡型社区居民虽然参与意愿和效能感高,但是却缺少实际的社区参与行为,特别是社区民主自治活动,虽然居民参与意愿强烈,但实际参与行为却令人失望,见图一。
3.2 结构方程模型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基础上,本研究使用LISREL构建过渡型社区居民的社区效能感、社会参与意愿、政治参与意愿影响实际参与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经过模型拟合与修正,拟合指标如下:χ2/df=68.25/30=2.275,GFI=0.98,NFI=0.97,CFI=0.98,RMR=0.038,RMSEA=0.039,并且各个路径都达到显著,表明建构的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观测数据。模型见图二。
经检验,考察社区参与效能感、社会参与意愿和政治参与意愿对社区实际参与行为的影响,发现社会参与意愿和政治参与意愿对其影响达到显著,但影响均只有0.15,这表明,模型并没有发现重要影响因素,后续研究应当在此基础上深挖。社区参与效能感对于居民实际参与行为的影响并不大,可能的原因是居民参与效能感普遍较高,导致与其他两个因素相比影响微弱。居民社区参与意愿都对实际参与呈现正相关,即参与意愿强者,其参与行为表现也较好。
3.3 影响变量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影响过渡型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的具体因素,我们将个人身份因素,包括性别、户口所在地、政治身份、文化程度和社区环境因素,包括社区硬件满意度、软件满意度共6个变量分别引各因子的线性回归方程,结果见表六。由于经济收入和文化程度存在共线性问题,而且由于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偏好,也造成了经济收入指标的数据存在失真的风险,因此本研究未将该变量引入回归方程。社区硬件满意度的测量在问卷中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包括社区生活便捷、消防治安、环境卫生、道路灯光、文化娱乐5个指标,加总形成社区硬件满意度,社区软件满意度则包括社区村(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工作质量的满意度。
回归模型表明,本研究通过社区环境满意度和个人身份因素做自变量来综合评价社区居民社区参与,可减少17.2%的误差,社会参与意愿可减少12.1%的误差,政治参与意愿可减少12.3%的误差,实际参与状况可减少15.2%的误差,社区参与效能感则可减少10.3%的误差。各模型F值显著性均达到0.001水平,表明了模型是有意义的。但是,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并没有被发现,后续研究应当以此为努力方向。

表4 因素分析结果摘要表

表5 4因子分布状况

图1 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情况(%)
从具体自变量的影响作用来看,首先是社区环境因素。社区硬件满意度对社区参与综合评价值的回归系数为0.241(P<0.001),这说明过渡型社区居民对社区硬件满意度越高,其社区参与情况就越好。不难理解,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越好,无论是本地户籍的失地农民,还是外来务工人员对社区越为依恋,建设和融入社区的意愿就更加强烈,其社区参与的实际状况就越好。从对其余因子的影响来看,社区硬件满意度对居民社会参与意愿和实际参与行为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其回归系数分别高达0.221和0.194。这和国内外其他学者在相关问题上的分析是吻合的,同时还能说明过渡型社区在社区满意度的现状和趋势上更接近城市社区的发展态势[4]。这表明,要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度,社区管理者必须优先建设好社区基础设施,从社区生活便捷、消防治安、环境卫生、道路灯光、文化娱乐等各方面入手。
关于软件满意度,本次调查考察了对于居委会、社区服务站等社区组织工作的满意度评价,对社区参与综合评价值的回归系数为0.125(P<0.05),这表明虽然其影响程度比硬件满意度小,但仍然是对社区居民社区参与有重要影响的变量。对于其他4个因子,首先对社区参与效能感的影响达到了显著,回归系数为0.166(P<0.001),它是该变量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当居民对社区村(居)委会工作和社区服务站的工作满意时,居民将表现出更强烈的参与效能感;相反,如果一个社区的社区服务是低质量的,居民将更多认同自己的意见无足轻重,无助于社区参与行为的提高。另外,对于实际的参与行为回归系数为0.081(P<0.05),不难理解当社区居民是不满意社区服务的时候,他们对于社区的活动是一种什么心态,更多的是漠然甚至抵制。因此提升社区服务的满意度也是摆在社区管理者面前的当务之急。

表6 过渡型社区居民社区参与影响因素的线性回归分析(Beta值)

图2 过渡型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的结构方程模型
其次是个人身份因素。性别因素对过渡型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总体上是较小的。对于社区参与总体评价值得回归系数并未达到显著。对具体因子的影响来看,实际参与状况的回归系数为0.088(P<0.05),说明男性的实际社区参与水平更高。同时,对于一般社会参与意愿的影响也达到显著(P<0.1),回归系数为-0.06,这表明,女性对于一般的社区活动如文体、社区服务等其参与意愿比男性更高,只是由于照顾孩子、家务等原因而影响了参与效果。
户籍所在地对社区参与综合评价值得回归系数为-0.082(P<0.05),表明本地户籍的失地农民比起社区中外地户籍的务工人员,其社区参与程度更高。同时,对于具体因子中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也达到显著性(P<0.05),回归系数为-0.122。从这两个结果中,我们发现户籍限制对于过渡型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是有较大影响的,本地居民的参与意愿和行为明显要高于外来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在其租住地社区,通常只是把社区当成一个港口,一旦工作有变,房租上涨,他们就会选择或被迫离开社区,自然对社区的参与就严重不足了。因此户籍制度的羁绊对过渡型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带来极大的阻碍,取消户籍管理限制是一剂改善过渡型社区社区参与的良方,而事实上从政策层面,社区居委会选举中取消户籍限制已是大势所趋[5]。
从政治身份来看,它对社区参与综合评价值的影响未达显著。而在对各因子的影响中,对实际参与程度的回归系数为0.128(P<0.001),对社区参与效能感的回归系数则为-0.062(P<0.1),这反映了实施社区参与行为的主体主要是有党员身份的一些骨干人员,他们常常是社区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虽然主观意愿上可能不一定愿意,但是由于社区服务人员的宣传和组织到位,而使得其参与行为在程度上更高;而普通百姓则可能因为宣传组织动员不到位或自身觉悟不够,参与程度明显不足。因此,在改善社区参与的过程中,发挥积极行动者的影响,努力宣传组织动员到位,提升居民社区参与效能感,才能吸引更多居民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
文化程度对社区参与综合评价值的回归系数为0.157(P<0.001),表明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居民将更多的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对于具体因子,对政治参与意愿的回归系数高达0.232(P<0.001),是最有影响的因素,对社会参与意愿的回归系数为0.08(P<0.05)。在过渡型社区中,文化程度仍以高中及以下程度(74.1%)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的增加,也会有助于社区参与的改善。
4 讨论与建议
“社区建设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和谐社区是社会管理体制运转有序的重要保证”[6],社区参与是衡量社区建设质量的重要指标,通过对过渡型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的研究,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与诸多城市街道社区调查反映出来的情况类似,过渡型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也呈现出复杂性的特征。高参与意愿和低参与行为并存,同时参与领域分布不平衡,文体娱乐活动多,民主自治活动少。由于单位制的消解,居民呈现原子化特征,虽然过渡型社区的很多居民(主要是失地农民)在此意义上由于原来多同属一个村落,但外来人口异质性稀释了这种格局。居民利益所属关系的不同,导致了社区参与行为、尤其是政治参与行为呈“不积极”状态,另外,政府包办社区,社会活动处于“临时”状态。总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过渡型社区,社区制度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失效”状态,社区功能尚未完善;另一方面,由于异质性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过渡型社区居民之间缺乏相互交往和频繁互动的社会网络,进而降低了该类社区的人际信任度。[7]因此,过渡型社区的社会资本总体上是匮乏的,这也进一步降低了该类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愿。
第二,加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居民对社区硬件的满意度。社区的硬件满意度对实际参与状况的显著影响表明,在过渡型社区这样的外地人口占了半边天的社区,首先需要通过提升居民对社区硬件设施的满意度,积累该类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社区自豪感。调查中,59.4%的居民表示不参加社区活动的主要原因是没时间,这表明“居民存在着参与共识的困境和利益选择的矛盾”[8],在该类社区与外部工作生活环境相对重要性的评价中,社区处于不利地位。社区管理者应当继续改善公共物品供给质量,提升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准,从而进一步改善该类人群的社区融入过程。
第三,打破户籍制度限制,赋予外来务工人员在地选举权。上述研究中,以流动人口为主体的外地户籍居民社区参与的其余因子与本地户口居民差异不大,只有社区政治参与意愿明显不足。户籍制度的历史惯性,即使在逐步取消社区参与户籍限制的当下,也仍然顽强的影响着过渡型社区中两类人群的互动,本地户籍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两大群体的相互“污名化”[9]过程和隔阂仍有待转变和消除。
第四,完善社区居委会自治,提升社区管理水平,提高社区服务满意度。社区的软件满意度对于实际的社区参与影响明显,且反映出参与者多为具有党员身份的骨干,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提升社区服务水准,通过社区参与激励机制创新,拓宽社区参与平台和渠道,过渡型社区参与的状况一定程度上必将有所改善。但问题在于,现在的社区居委会及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通常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由于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基层政府及职能部门仍有大量工作下沉到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这就使得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趋向仍呈尾大不掉之势,社区工作人员的精力只够应付上级相关事宜,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仍然任重而道远。
[1]张晨.城市化进程中的“过渡型社区”:空间生成、结构属性与演进前景[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2]李霞,陈伟东.武汉市居民社区参与现状及制约因素——对武汉市的调查与分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5).
[3]马卫红,黄沁蕾,桂勇.上海市居民社区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社会,2000(6).
[4]单菁菁.社区情感与社区建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46.
[5]谈晓慧、李龙兴.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 流动人口也“说上了话”[N].姑苏晚报,2010-05-24.
[6]郑杭生.中国特色社区建设与社会建设——一种社会学的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6).
[7]张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过渡型社区”治理——以苏州S区莲花社区为个案[R].江苏省社科联研究课题结项报告(B-07-51),2008:26-28.
[8]顾训宝.十年来我国公民参与现状研究综述[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4).
[9]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36.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terviews of 819 residents of three communities in Suzhou Industrial Park,this article analyses and demonstrates what affects in participative behaviors of transitional communities by the use of factor analysis、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What’s more,we evaluate mainly include general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political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community self-efficacy and actual participation statu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tegrated circumstance,for these factors further describe conclusions.Results show that:first,transitional community exists political apathy tendency,high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nd low participation behavior coexist.Second,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goods,enhance the satisfaction of residents of community hardware.Third,break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limits,given the migrant workers to vote.Fourth,strengthen community service personnel of responsibility,improve community activities publicity.
transitional community ; community participation;factor analysis ;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C912
A
1674-4144(2017)-10-45(6)
张晨,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政治学和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阶段性成果;苏州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重点研究项目。
责任编辑:王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