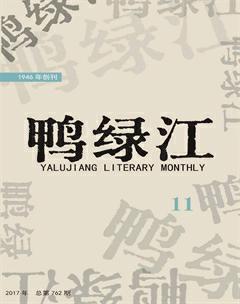行章(组诗)
李鲁平
一、渊而静
黄头鹭站在牛背上,只能从树枝的缝隙,窥见南河。
它一直凝视着毫无表情的河水,期待深不可测的历史
从水里凸显端倪。
河的两岸,生活过许多著名的武士或者战士,他们的名字
与他们村庄的名字一起,被当作指示牌悬挂在路的上方。
他们燃起的火把,龙一样弯曲,盘旋着向山的深处燃烧,
直到山中最后一个角落,点上电灯。如同这季节的淫雨,
几十年这大山里唯一的主题,是牺牲。无数的骨头化成
灰烬之后,蜜蜂在杜鹃花铺就的祭台,嗅着真理的
蛛丝马迹,忙着编织更甜的词语。
汛期未到,南河走到龚家潭,便消失在一片杨树林中,
一同消失的,还有埋葬在大山里的血腥、灵魂。
二、持竿不顾
过松西河,就是松东河。长寿河与白水河,只隔几里路,
从沙道观左转,两支烟工夫抵达沙洲。这些河流都来自
南河,这棵倒伏的大树,每根枝丫派生一条河。从南河
开始,河流只按自己的心奔流,或者选择方向。在这里,
地图是田边一张擦过屁股的废纸。
每一条河流都映照着麦子,并把麦子流向下游,如同打豆腐
摇出的豆浆,缓慢、沉重,但芳香。从早到晚,久保田孤独地
沿着河岸忙碌,所过之地,如同橡皮在莎草纸上擦过,袒露出
一条条土地的底色。每一条河流的岸边都没有人,羊和牛主宰
着自己的生活,啃噬着无边的空旷。我要横渡这些河流,
像蜘蛛,跨过那些枝丫。它们既不惊奇,也无戒备。
每一条河边的人,与河流一样,不知去向。只留下房子
和麦地,留下睡莲、菖蒲、芦苇,就如我的漂泊,留下
亲人、钥匙和争吵。住在这条河边,一些人发了财,
一些人破了产,一些人从村里去了省里,一些人从省里
去了监狱,一些人死去,一些人出生……
我坐在這条河边,装作一切都已忘记,但,每一条河流,
都会流上心头,每一条河流都连着动脉或者静脉,不管
有无硬化,都可以致命。
三、亡羊均也
风从堤脚下爬上来,在书页之间吹着哨子。那声音
跟图画一样美丽,从不同的音符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象,
街道、汽车、高楼,以及户口、办公桌、电话。我跟脚边
的蒲公英一样,等待一阵风,把我送到哨声消失的远方。
躺在堤坡的还有歪嘴,他叠着烟盒,问布谷鸟反反复复,
到底在说什么。春风告诉我的那些梦想,我从来不告诉
他。但他知道白沙洲的每条沟渠,即将欢腾起来。知道
队长家的桑葚熟了,李子也快熟了,记工员的姑娘又长
高了。跟我们放牧的牛一样,从来只盯着眼前的
沙洲、草地。我的牛,他的牛,已走进蚕豆的深处。
绿色的海洋不时浮起,它们对蚕豆低沉而粗鲁地赞扬,
同样低沉而粗鲁的还有队长的辱骂。我一直以为读书与
叠烟盒有天壤之别,就如凤凰与麻雀。
从春天到秋天,书页上的哨声,如亲人的叹息,城市
没有听到,大堤上的蒲公英没有等到温暖的南风。
四、待族而雨
下雨的消息从前天传来,从待收割的麦地掠过,
从即将插秧的水田溅起,然后与一只鸽子一起
落在我的阳台上。
阳台上的那株红番茄,它们红得跟我二十岁时
的心脏一样,年轻,血管畅通、思维清晰,皮肤
富有弹性。你轻轻地捏一下,它会马上还原,没有
抱怨和仇恨的痕迹。你使劲捏下去,它的青春
会汁液四溅,洒成一幅图画。
与我一样,很多人也在等待这场雨。沙洲上的乡亲,
等待雨流过沟渠,把土地泡软。工地上挥汗的民工,
看着头顶的乌云,读懂了其中的凉意。北方多沙的平原,
南方干涸的丘陵、山地,都在等待。甚至坟地上将要枯死的
野菊花,都在渴望一场雨的滋润,如果如愿,它们将继续
举着数不清的小太阳,照亮逝者的春天。
今天有大雨,我在阳台上迎接。很多年前,没有阳台,
它们便直接从春天、从头顶,砸在水泥地上。
五、山无蹊隧
初夏的一天,首义广场用挡板围了起来。他们钻开了水泥,
向黑暗挖下去,要挖出一个地铁车站。从地下源源不断
运出的,五十年前、一百年前、五百年前的土,看起来
表情如一,其实是不同的大气、温度、植物、动物的尸体,
是被一只神秘之手揉捏的一抔新土,他年之后可以埋我,
我也将成为这些土中的一颗。
而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前,那些爱情,就义,踉跄,
潦倒,那些阳光下的轰轰烈烈,月光下的窃窃私语,都在
这道上刻下过印迹。这一层有鲜血,这一层有爱恨、情仇,
这一层,有朝代更替的鞭炮或者火药。随后,新一代的雨水
循着上一辈的痕迹又落在首义路,洗亮了红楼,再顺着下水道
去向不明,雨水从不在首义广场聚集,就如云朵从来不在我的
头顶停留。现在,从这些渣土车上,从堆积的泥土中,消失的
事物已经不能一目了然。辨认不出血迹,触摸不到心脏的跳动,
听不见旗帜猎猎作响,也遭遇不到祈求和绝望的目光。
只有一模一样的泥土和水,
如同你我的皮肤,如同我们与祖先的轮廓。但,如果
你正在坠入毁灭,紧握一把泥土,你会听到真切的生、爱和死。
六、以丝罟鸟
姓罗的人都捕鸟,他们精于罗网。新郑、郾城直到
罗山,每根树枝都是驿站,住满了南来北往的鸟。
恒河沙数般的命运,从未从罗网里逃脱。
烤鸟的篝火彻夜不眠,天空飘洒着罗国人梅雨一样
不绝的安乐,它们浇灌的荆楚,滋长出漫天的恐惧、
担忧、嫉妒。循着鸟的足迹,追杀的弓箭落在汨罗江
的一块平地上。这里有卢水、汨水、沙洲、芦苇、鱼
和水稻,但没有鸟,稻田上瘦小焦虑的麻雀,无法承受
一个国家的饥饿。洞庭西下的辉煌,让罗国人的神通,
水一样从网里漏出,一点一滴也未留下。
布谷鸟飞过汨罗的时候,这些人只是抬头看了看,便埋头
插秧,罗网为生已成为集体的罪业,他们以见到鸟为耻。
后来,一个楚国的流亡者死在这里,
他们把他捞起来,埋在罗国,用插秧的手,打造龙舟,
在每年的端午接引他的灵魂,朗诵他的诗篇。
七、篦 子
从春天开始,我学会了写错字、别字。在电脑上
拼音为每个字或词提供多个替身,每一个都有
正确的发音,它们都是事物的别号,就如我也叫矮子。
桌子上不同版本的字典、词典,都不再重要。过去,
为一个字或者词,我找虱子一样篦过这些词典的
每一行,在絕大多数正确的世界里,甄别一个伪装
的内奸。有时,我就是那个捞针的人,我的
每一次发现,都让大海涌起羞愧的浪花。
没有人知道这一切是如何改变的,就像早晨醒来,
大街上的姑娘都穿着破洞的裤子,而过去,每一个洞
都必须用密实的品质缝补起来,从春天再穿到秋天。
我知道,的确有一种篦子,连风也不能漏过,
它们从真实的内心篦过,只留下世界的绰号。
八、曳尾涂中
南河边那只探头的老龟,不急于逃跑,也不急于告诉我
它知道的往事,它满身的泥泞让人想起庄子的曳尾涂中。
此刻有谁还会在意庄子的踪迹,我眼里只有蛇形的河流。
所有河流都不会在大地上写下一,南河也不会笔直地流淌,
它的讲述从来就是婉转、曲折。我的祖先早就遗传了河流的
沟回,在汉朝,他们用封代替邦。在唐朝,他们只说观音,
他们一次次的顶礼中省略了世界。在清朝,他们把正月说成
端月……他们一代又一代迂回地讲述心中的真诚,就如那些
河流,日夜倾诉却从未痛快地伸直过。
在南河,我把队长老婆的肥胖叫福气,说堂嫂的瘦弱是苗条。
我们描述只剩下麦子的乡村叫宁静。在南湖,我们形容一小时
挤不出去的隧道叫繁荣……我们从来就言不由衷,如同南河,
如果鞠躬、屈曲,甚至颠倒,都不能让沿途的大川或巨石
让开一线缝隙,就原地打转,每一个旋涡,都是绝望的眼睛。
九、知有所困
出三号线A出口,抬头向左前方,一个长方形砖石
大楼墓一样耸立。黑砖的墓壁,黑色的卷拱,白线勾的
弧形宝顶。几棵高大的樟树的摇曳,拂拭着尘世的不安。
有三十年了,我早上八点半走进这墓室,下午五点半,有时
六点、七点,从墓里出来,回到城市的南边,看一眼熟睡的
妻子、儿子,我爱的人都在梦中。我在他们醒来之前,返回
城市的北边,再次走进大墓,刚好也是八点半,或者不到
八点半。从去年开始,三号线使从南到北,从地下到地上
成为钻营。钻进去,是在地下;钻出来,便进入墓里。
不只我是这样,还有一些人也是这样,他们走进去,走出来
相互不说话,不微笑,也不点头。他们似乎并不认识,或者
丧失了问候的机能。地下唯一的声音,是车轮碾过黑暗的闷响。
地上唯一的声音,是汽车急驰的轰鸣。
不需要盗墓或者发掘,我告诉你,这墓室里有什么,除了几张
宣纸、几幅画、几本书、几封未寄出的信,以及已死、将死的
躯体,其他的都没有,连一颗心跳的声音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