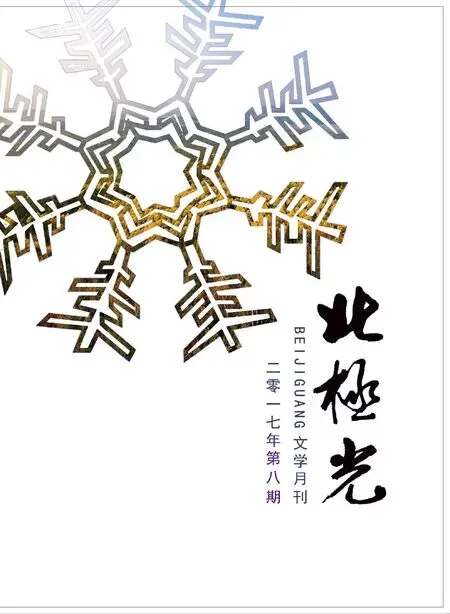忧伤的西部,我回不去的故乡
青岛 雨 桦
忧伤的西部,我回不去的故乡
青岛 雨 桦
那年夏天去新疆,最想去看一条河,孔雀河。
新疆有好多风光优美的湖泊水系。不知道为什么独独要去看孔雀河。我顺着孔雀河走向她的荒原深处。依如我想的一样,孔雀河的白天和黑夜一样寂静,日出和日落同样无声无息。有人来过,又走了。有人走了,又有人不停的来过。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游客,注定不会在这里永远停留。
河边支着一顶破旧帐篷,帐篷里面有全套生活用具。一位哈萨克渔民正在河边打鱼。看样子,他已经在这里停留很久了。我的猜测没错,整个夏天,他都在河边打鱼,如果没有人来买,打上来的鱼就会晒成鱼干,留做冬天吃,或送给亲人朋友分享。他是一个懂汉语又健谈的哈萨克老人,我正不知道如何打发这寂寞的时光,有了他,我的灵魂在这个夜晚有了最好的歇息地。一老一小,相聊甚欢。他的豁达以及慈祥让我感觉他像父亲一样温暖。至今孤身一人的他,也借打鱼来打发心灵的孤寂。我们在河边燃起篝火,通红的篝火劈啪作响,驱走了夜晚的寒气。他用哈萨克人的传统做法,给我烤了一条大鱼。火上架一个铁架子,把鱼放在上面,鱼挣扎着死去了,诱人的香味很快飘出来。虽然感觉很残忍,内心依然没有经受住美食的诱惑。一面喝酒一面慢慢闲聊,没有主题,东一句西一句,从他的故乡青海到新疆,从离他而去的妻子和不知何处的孩子到孤独此生,从死亡之海罗布泊到楼兰古城……
除了是一个渔民外,他还是一个民间资深音乐人,精通很多民歌,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喝了酒以后,他快乐得像孩子一样,给我唱歌,且歌且舞,自己吹奏乐器给自己伴奏。寂静的夜里,曲调在他的指缝间与篝火、水雾一起在孔雀河边缓缓流淌而出。满是皱纹的脸在火光和音乐中不停地变幻着沧桑的痕迹。我说不出那音乐的曲调是什么名,但一样触动我的灵魂莫名明其妙的忧伤。像他长长的一生,有高潮,也有低缓的部分。
无疑,这个晚上,我和哈萨克老人以及夜空那轮满月都是寂寞的,若说不同,寂寞也未必是一种寂寞。就像我不懂月光千年不变的姿势一直照耀大地,是不是为了春种秋收的等待?就像我不懂眼前的老人,他的寂寞是不是渴望离别多年杳无消息的妻子和孩子有一天突然出现在他眼前,所以,这漫长等待中的寂寞同样充满了幸福?就像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听到那音乐突然想放声大哭一样。
其实,我是明白的,只是我不愿意承认而己。一路上,映入我眼底的,很多原本水流丰盈的河床成了干枯的瓦砾,森林被沙漠掩埋。村庄在山涯边上同那些枯萎的树木一样,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破败的泥房子在风雨中歪歪斜斜,即将倒塌,一只死去的动物只有它的白骨在烈日下静静地承受阳光的亲吻。山路上,偶尔有赶着牛的老汉经过,在若大的山梁上显得孤独而瘦小。一个包裹着红头巾的老妪一脸汗水,在田野里劳作,佝偻的背影令我想起离开我多年的外祖母……
她的故乡是西北某地一个贫瘠荒凉的村庄……
我一路行来,大概也是替我的祖母来寻她的故乡吧。天堂里的人也怀念故乡,就像我们在人间也渴望归宿一样,何况她们那一代老人是念旧的。一路走来一路寻寻觅觅,在我的想像中,她的故乡早已经该山清水秀了吧。
可是……
如果我的祖母还活着,如果她看到故乡是这样的景象。
她一定会比我此时的心情更沉重,更难过吧。
大风裹起的沙土遮天蔽日,天昏地暗。我经过的西部已经没有了多少生命的灵魂。半枯半黄。丢了灵魂,无论天空还是大地,都会寂寞丛生。那一刻,激动的心变成了无言的沉默,尔后是隐隐的难过和心疼。我不知道我是在寻找祖父母曾经的故乡还是史书上记载的繁华与富有?还是专程为了西部的痛苦而来?
然而,我忧伤的同时,我也庆幸——
孔雀河得己活了下来,从远古时代活到今天是多么不易的事情,她又名饮马河,所传说东汉大将班超在此饮马。所以,后人也称她为饮马河。从遥远的斯腾湖西部溢出,经过荒凉的沙漠地区,由西北向东南方向缓缓流去。最后注入罗布泊。一路上,孔雀河注定是孤独的。因为她是罕见的无支流水系,这在很多河流中极其少见。后来因为人类过度取水,在她流经大西海子水库之后便季节性断流。
在她的岸边,生长着茂密的胡杨林。如果说这块荒漠是块黄色的画布,孔雀河就是这画布上的一条唯一的绿色飘带。她用自己柔软的身躯守护着这片土地的森林,绿草,不允许沙漠侵袭。可是,有时也很奇怪,这面是茂密的胡杨林,那面就是寸草不生的沙丘。那些在河边安静生长的胡杨林,朴素而张扬,到了秋天,她的叶子五彩缤纷。就像凡·高的画一样充满想像力。
我喜欢胡扬林,她让我想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在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仍然不屈不挠,坚守梦想,顽强的生长着。
这是胡杨林的可贵,我在想,若我们每个人都能长成自己的胡杨林,那该是何等壮观的景象?胡杨林坚守自己的同时,也为孔雀河守护着安宁与幸福。
很多河流却没有孔雀河这样幸运,她们在遥远奔来的路途上,死掉了,干涸了。像罗布泊,一九四二年测量时,湖水面积达三千平方公里,一九六二年湖水减到六百六十六平方公里,一九七0年以后干涸。而在汉代,楼兰古城在这里车水马龙,罗布泊的水清澈得能照进天空,云很白,风很柔。后来,罗布泊像个年事己高的老人,死了,城市变成了瓦砾。被岁月掩埋成了后人的传说。专家说,罗布泊干涸主要是作为上游的水源地塔里木河两岸人口急剧增多,五六十年代,大批内地人口迁移西部,扩大耕地,开采矿藏,大量用水。几十年间,塔里木河上游修建了一百三十多座水库,盲目抽取河水,致使塔里木河由六十年代的一千三百二十一平方公里萎缩到一千公里,三百二十公里的河道干涸,以致沿岸五万多亩耕地受到威胁,一九六0年,塔里木河下游断流,罗布泊失去补充水源,迅速干涸,一九七二年后,罗布泊最后干涸部分为四百五十公里。罗布泊干涸后,周围生态环境发生巨大变化,防沙卫士胡杨林成片死亡,沙漠每年以三到五米的速度向罗布泊推进,很快,罗布泊就与广阔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融为一体,从此,罗布泊成了寸草不生的地方,终年风沙肆虐。
罗布泊死的可惜,她曾经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湖,海拔780米,面积约2400—3000平方公里。她地处塔里木盆地东部古丝绸之路的要冲而著称。湖盆自南向北开始抬升,分割成几块洼地。罗布,古维吾尔语是聚水之地的意思。元代时她称罗布淖尔,淖尔蒙语的意思是湖泊。总之,在古代,罗布泊就是聚水的大湖盆。在汉代,罗布泊广柔三百里,其水亭居,楼兰就是罗布泊边上的一个古城镇。她在罗布泊以西,孔雀河道南岸7公里之处。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形之中,历史上的楼兰是西汉时期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是楼兰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东通敦煌,西北到焉者,尉梨,西到若芜,且末。楼兰城依山傍水,公元三世纪后,楼兰迅速地萎缩。从楼兰遗址发掘出的文物却震惊了世界,其中有珍贵的晋代手抄本《战国策》,考古工作者还在楼兰墓葬群中发掘了一具女性木乃伊,经测定距今约有三千年,干尸衣饰完整,面目清秀,也就是后来我们传说中的楼兰美女。以及做工精细的汉锦等。
我们是知道罗布泊为什么而死的。那样一个美丽的湖泊水系说没就没了。
河流消失的地方,最终也是人类消失的地方。
我在想有一天,美丽的孔雀河会不会遭遇罗布泊的命运?如果孔雀河像罗布泊一样死掉了,沿岸的城市没有一滴水,那些高楼林立的城市是否也会沦为死城?沿岸的广阔农田是否很快成为沙漠?我的问题没有人爱听,没有谁去真正关心。大家关心的是自己年薪多少,什么时间能拥有比他人更多的财富,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得到。只要占有着,哪怕是以破坏的手段得到,就是幸福的。
罗布泊死了,我们却活了下来,如果有一天,地球上的所有湖泊都像罗布泊一样死了,我们该去哪里养活我们的儿孙?我们如何逃得死亡一劫?如何继续我们心中未完成的梦想?
没有人告诉我这个答案。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地球有一天真会毁在我们的手里。
我居住的城市,三面被一望无际蔚蓝的海水包围,我时刻可以感受沙滩踏浪的陶醉,丽江山水皆风情,乡村婺源美得像梦境中的童话。周庄水乡淡雅宁静。凤凰神秘古老,香格里拉梦境一样纯净……
独独西部,每经过一个地方,我心里,愈发说不出的沉重。
她于无声无息中牵走了我灵魂的凝望和思考,一路走来,西部用忧伤填满我的眼神和心境。路经黄土高原时,大地干渴得四处是裂缝,地表裂开一处又一处的口子,像是人的皮肤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一样。令人心疼。不敢往上踩,生怕踩疼了大地。生怕伤口流出了血水。生怕大地疼得承受不了这样的痛苦。
偶尔有草的地方,也是稀疏的,远远地望去,一块绿一块黄,像得了皮肤病一样。
干渴。缺水。黄沙遍地。随处可见废弃的村庄与良田。
西部太渴了。渴到了焦灼状。渴到了寸草不生状。渴到了被死亡包围的状态。
曾经的那些宽广的草原哪里去呢?
那些丰盈的河水哪里去了呢?
华尔街有一句著名理财理论: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套用这句话,我想说一句话——
你伤害了大地,大地也会采取报复手段。
现在,我们收获了践踏大自然的苦果。还不及时醒悟。还不停止伤害。
大自然想哭,却流不出忧伤的眼泪。
河西走廊。
曾经被我们的教科书描写得十分优美,黑河,石洋河,疏勒河从那里经过,是的,她的确曾经优美得像天堂一样。现在不是曾经。著名的民勤绿洲早已经被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包围。因为缺水,民勤湖区已经有五十万亩天然灌木林枯萎,死亡,三十万亩耕地废弃,部分已经成沙漠。
站在被风沙包裹的湖区边,看着那些成片枯死的树木,死亡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那景象好像一个人,烧光了眉毛,头发,皮肤也溃烂掉了一样。你的感觉不是心疼,还是面对死亡来临前,眼睁睁却又无能为力。
在一处废弃的砖瓦房前,一个瘦弱的中年汉子牵着一只羊走过。羊咩咩地叫,大概是饿了,找不到吃的,它根本不听从主人的话,不愿意跟他往前走,往外挣扎,但绳子拴在它的脖子上,主人强行牵着它,往前走。命运有时就像这个山羊脖子上的绳子,由不得自己。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说不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那个黄昏,没有风,阳光暖暖的,我在那处废弃的房子前坐了很久,想像这一家的主人曾经是否年轻,日子过得可好?他们迫不得己离开故乡,现在他们在何处流浪,是否安居乐业?是否怀念曾经出生,长大结婚生子的故园?
一个老婆婆也从这里经过,我主动同她打招呼,说起这个地方,她恨风沙的无情,就这样夺走了她生活多年的家园。皱纹丛生的脸,有无奈,也有漠然。甚至连眼泪也没有。面对这样的场景,她已经习以为常,她不知道故园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她没看过大海,没见过壮观的黄河,长江,更不知道江南小桥流水的南国与此时自己生活的地方有什么不同。
所以,除了无奈与漠然外,我在她的脸上见不到悲苦,见不到怅然。
然后。她背着她的家什往远处走去,丢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无端的忧伤。
车子路过一个我不知道地名的地方,看见一条小河,河面上泛着或黑或红的泡沫,散发着难闻的臭气。河边散落着一些村镇,土路上不时有农用车和汽车经过,扬起的沙尘迷漫空中。燥热难耐。四周是一道道土梁,沟壑纵横,难见绿意。唱信天游的汉子一脸无可奈何地蹲在塬上,唉声叹气。几只小山羊因饥饿爬上了树,啃噬树上的叶子,更多的树被羊啃光叶子之后也无一幸免的死掉了,干枯的枝丫垂在山梁上,没有人注意一株株枯死的树。羊本来是吃草的动物,但是,地上没有草,不会上树的羊也就练了一身武功,爬上了树,寻找可以活命的食物。这是活下去的本能,我不知道是该为那些学会上树的羊庆幸还是为它悲哀?
荒草也恨春风。春风来了,荒草却没能复生,所以,草原是寂寞的。
冰河也念雨雪。雨雪来了,河床早已经没有了清澈的水流,所以,湖泊是寂寞的。
西部老了。不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那种老。不是除去巫山不是云那种老。西部的老是千疮百孔的那种沧老,苍老到让你感到悲壮和绝望。南朝《敕勒川》有诗曰: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地见牛羊。
我想像少年手拿皮鞭站在山冈上,在蓝天白云下追赶群群牛羊的情景。
而现在,这样的情景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有条件的家庭把大批牛羊圈在家里,牧民买草喂羊,也只有买牧草,那些羊才可以活下来,在草原上放牧已经成为十分久远的事情。过分的垦殖和放牧使一些曾是天然牧场的草地萎缩退化。毛乌素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正一点点吞噬着人类越来越少的绿色土壤。据一份调查资料显示,仅陕西省榆林市建国后沙漠化达18000多亩,相当于整个榆林市后垦殖的面积,也就是最初的榆林市早被沙漠掩埋了。
多么可怕的静态死亡。
为何要怪风沙无情?所谓适者生存。其实,风沙亦有情,她也需要生存,无情的是我们自己。把原野上的大树砍光,然后在城里的水泥大街上偏要种上树,喷药浇水施肥,生怕它死掉了。还是有许多外地移植树木不适应这样的生态环境而死去。楼兰,留给我们的只是大漠狂风中的一些残垣断瓦和想像而己。这样的警示难道还不够残忍吗?还不够醒目和深刻吗?
不要问,楼兰古城何时消失的。
不要问,她是为什么消失的,有些答案不知道永远比知道更好。
还有,我不想明知故问。
伤痕好了,如果不揭他就不会有痛感了。楼兰与罗布泊,大地的伤痕,终于被沙子掩埋了痕迹。她就像从来没有在地球上出现过一样。不过是一个醒来的童话而己。
我无法忘记东居延海,曾经仙境一样水草丰美的地方,老子曾经在那里居住,写出了举世瞩目的《道德经》,后来化海仙逝。那应该是曾祖母的故乡吧。可是,自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居延海也干涸掉了。如果不是后来国家有关部门往居延海补水,恐怕这个已经干涸了42年的湖泊就成了现实版的罗布泊,她身边的城镇也会成为多少年后的无数个楼兰吧。很多河流湖泊没有东居延海那样幸运。
悄无声息的死于人类贪婪中。
竟然没有人为她的死有一点忏悔和心疼。
神农架,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是我国现代唯一仅存的原始森林,那里有各种野生动植物。这样一个国家级保护区,也难免沦为GDP的牺牲品。为吸引游客增加地方收入,不顾破坏环境建机场。据说,为建机场,削去神农架原始林区的五个山头,填平数百个溶洞,终于建成了机场。我不知道是该为这个机场的如期通航庆祝还是保持理性的沉默?不知道这个机场对于神农架的明天来说是福还是祸?
原始林区,就该保有她的原始性,否则的话,就成了闹市。动物植物该如何生存?大兴安岭,原来是原始红松的故乡,人类过度开发后,终于没红松可以砍伐了。人类丢下狼藉的大自然逃走了。
为了得到,我们总是有无数理由。
贪婪,就意味着不择手段。
占有,意味着破坏。
车过秦岭时,有些山头已经被采矿业给开膛破腹,山体露出白哗哗坚硬的石头,为了挣到更多钱,有人不管不顾把树砍掉了,水,污染了,植被,破坏了。一些小矿厂隐在山林里,排出的废水里面含有各种重金属,直接排进河道里。流到下游,人喝了,得病,动物喝了,死了。癌症村层出不穷,我在黄河中游一个村子里经过时,村民告诉我,他们村里,每个月都有死人,都是癌症。罪魁祸首就是村边不远处的化工厂,排出的水呈淡红色,臭气熏天,夏天不敢开窗户。原来井里的水打上来就能喝,现在井里的水即使烧开了,仍有说不出来的怪味,上面漂着一层油污。污水流到的地方,庄稼死了。土地板结成硬块了,我看着一个五岁孩子畸形的身体感到惊讶,他长着三只脚,在地上爬,最重要的是他有一张青面獠牙的脸,很吓人,没有孩子跟他玩。村里的人都叫他怪物。
可怜的孩子还不知道什么叫歧视。
我看着地上的孩子,眼睛湿了。不是哭他可怜,而是心疼这块土地的命运和人一样,要给他人作践的。
我想,如果他是我的孩子,我是不是心都碎了?
如果他是那个污染制造者的孩子,他还会用污染的土地,水源,换取钱财吗?
一个天使的命运因一个利益至上的老板而改写了。他从此一辈子生活在痛苦里。
老板在别人的土地上盖厂,留下污染的土地和畸形发育的孩子,赚钱走了,到城市里过富人的日子,那些为他献出土地的农民却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为了赚钱而失去良知底线,失去道德底线,非常残忍。在黄河的中游,沿岸的排污口总是在你不容易看到的地方,大张着粗陋的嘴,吞吐着毒物,滔滔奔向黄河的怀中。没有人觉得惋惜。为了那一点可怜的GDP,我们的母亲河就这样被她的儿女人为的投毒了,里面鱼虾绝迹。鱼虾都死了,人还能好到哪儿去?
西部,不是被建设伤害,而是贪婪所致。
宽广的草原不见了。森林消失了。美艳艳的山丹花枯萎了。信天游在黄土塬上游荡,从未有过的孤独。生存是以死亡为代价的,没错,但也早已经被我们习惯。西京的都城依旧熙熙攘攘,车水马龙。没有人去预言多少年后她会不会重蹈楼兰古城的命运。就算能够重蹈,又与现代忙碌的人们有何相干?将来是将来,现在是现在。谁还想得那么远?
西部,每一寸地表都像一张纸一样,脆弱得不堪重负。刮过的狂风与黄沙,是对人类贪婪与破坏的最好礼物。你伤害了大自然,大自然也用风沙回击人类的无情。
百年以前,我的曾祖父也是西北人,本来安分守己的他不得不卖掉最后一只牛,领着三寸金莲的祖母和一双儿女逃往黄海之滨,他们相亲相爱的家园正被风沙吞噬。只有逃离,选择背井离乡。他们的逃离与我们历经沧桑的民族相比,祖父们为生死饥饿的奔波岁月仅仅是一场人生苦旅。对于整个民族史来说,这一场人生苦旅又算得了什么呢。
一代又一代的故乡人在田野永远挥舞双手劳作。想改变日月和生活,但生活依然贫瘠。只有逃离。曾经为生活所迫叫背井离乡,现在也是为生存,时髦的叫打工,意义是一样的。缺水导致的贫困,没有知识的贫困,没有绿色的贫困,一直困扰着西部。那个夏天,沿长城西去,我走了很久,很远,去找被城市和工厂撵走的田园牧歌。潺潺的水声和浪漫的信天游。去找祖父母们出生的地方,那是填表时叫做藉惯的地方,也是我的故乡。却发现,那是我永远都无法回不去的故乡,黄河带走了先祖的魂魄,只剩下黄帝陵和炎帝的传说孤独地漂浮在历史的天空中。只剩下西部大漠长河落日的壮美凄绝,无人理睬的孤独……
我的故园在何处?我茫然的寻找。
乡音已经陌生。哪怕长满荒草的坟头也好。哪怕一条清澈的小溪也好。大雁飞走了,鸟择良木而栖。只有长风浩荡。天地一片辽阔。
一路走来,我已经遗失了故乡。
在城里流浪了多时的乡愁无处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