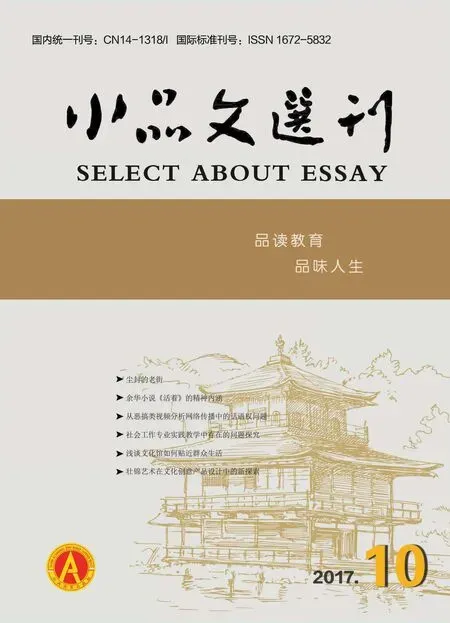多层次叙述的艺术力量与“金钱”话题的当代延伸
——《杜鹃钟》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
廖宇婷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多层次叙述的艺术力量与“金钱”话题的当代延伸
——《杜鹃钟》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
廖宇婷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从《杜鹃钟》的思想构成机制来看,努埃曼怀着东方人对本土文明特有的情怀,以批判的态度、辩证的眼光审视东西方文明的优缺点。其斥责不顾一切追求物质满足的异化心理,表达其对资本主义入侵中东给当地人民带来冲击与痛苦的无奈。从小说的艺术构成机制来看,其三个层次的叙述策略,充分体现了作品自身自觉的文体意识。小说三层叙述策略融为一体,使得作品露出出艺术价值与思想价值兼具的锋芒。
文体意识;多层叙述;中西文明冲突;金钱话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东地区受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到处都弥漫着殖民与反殖民斗争的硝烟,东方落后国家积弱积贫、民不聊生。但也使得东西文化交融形成强烈的潮流,其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精神也传入中东地区并产生一定影响。《杜鹃钟》也不乏思想性与时代性、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等等。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落后国家时,大量巴黎嫩作家被迫流亡海外,最终在美国相对松弛的环境中形成了“旅美派文学”也被称为“阿拉伯侨民文学”。努埃曼就是旅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创作的《杜鹃钟》正是以东西方文明冲突为题材,反映黎巴嫩人民在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夹缝中挣扎求存的困惑、痛苦与无奈。作者以其智慧而尖锐的语言,深邃而理性的思想见解,开阔的心境和高远的境界,将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融合,形成这篇“异乡人”小说。
1 三个叙述者所构建的三层叙述
米哈依尔.努埃曼是阿拉伯旅美派文学的旗手,阿拉伯现代文艺理论的先驱,与纪伯伦并称为近代黎巴嫩文坛双子星。他生长在黎巴嫩内部环境动荡不安,政治斗争激烈,反动统治勾结外部殖民统治侵害黎巴嫩的时期。因此他被迫侨居海外,却又思乡心切,所以描写海外侨居是他创作的一大主题,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杜鹃钟》。其是一篇有自觉文体意识的短篇小说,并有意识地采用了叙述策略,可以说,这个文本艺术力量,主要来自叙述者的变换和叙述层次的交叠。其三个层次的叙述策略是《杜鹃钟》成为比较经典的作品的内在原因。其三个层次叙述开辟了宽阔的阅读空间,当下的我们是“实际的有血有肉的读者”,俯视角地观察和评价其他各层次的读者。文本将“中西文明冲突的话题”再次提交到我们这些读者面前。
我们可以假设提问,《杜鹃钟》的叙述者是谁呢?恐怕就一时难以回答,因为在文本中不止一个叙述者。故事的叙述从“一封来信”开始,“我于1922年5月初收到这封信,间后,在信中竟找不到写信者的姓名和地址”。“发信者的地址是黎巴嫩的一座小村庄”。第一位叙述者“我”将读者引入故事,叙述了本篇故事的起源,“我只得自己负起责任来,于今天发表这封离奇的信”。“在删掉了问候致敬等一切格式文字后,读者请看下面的信……”。由此开始,也就是第二部分开始,叙述者自然而然的流转到了另一个“我——黎巴嫩村庄的一个人,哈塔尔的朋友”。“……昨天,村子里死了的一位伟人,我们今天把他埋葬了。呵,我给你写信,手上还沾有坟墓的泥土呢……”。在这封信当中,“我”为读者介绍了集美丽、善良、忠厚等人类的一切美德于一身的阿布.马鲁夫(美国人汤姆森或哈他尔),并告知读者,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能够战胜杜鹃钟,且在信中大量引用了哈塔尔关于对土地的论说。“你的衣、食、住房,都来自土地”。“土地是生存经典的第一章”。“幸福的人身居原地,知足常乐”。“土地就是纯洁躯売里的纯洁灵魂”。从这些言语当中,我们不难发现叙述者亦或作者对真善美的赞扬,对美的化身——阿布.马鲁夫的敬仰。马鲁夫所热爱的土地代表着人类的生存基础、香味、干净的灵魂、平等、诚实、无价等等。
接下来叙述者由第二个叙述者“我”转变为阿布.马鲁夫(哈塔尔),哈塔尔用第一人称叙述他自己的故事,于是,我们读者便遇到了第三个叙述者。我们已经知道,第一、二个叙述者均是以限制视角的方式,讲述并不完整曲折的故事,而第三个叙述者——哈塔尔则讲述了一个关于他自己的完整、曲折而又引人深思的悲剧故事。哈塔尔的讲述借助“我”的“一封信”形式,自然带有回忆往事和总结的情调:一切故事已经结束,“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很久以前……”。自己走过了恋爱、失恋、致富、婚姻不幸、回归故乡的全部过程,并且反思和回味了这个过程,在万念俱灰之际毅然决然的选择回到黎巴嫩,可以想见有一个非常漫长痛苦的思考过程。
小说在本质上是回忆性的,“杜鹃钟”隐喻西方资本主义财富与金钱的罪恶,在逻辑上所叙均是已经发生了的,并且被叙述者认定有价值的事件和经历。这样,我们发现小说文本存在三个叙述者:“我——小说的隐含作者”、“我——信件的作者”、“哈塔尔——故事的主人公”。三个叙述者构成了三个叙述层次,分别为“隐含作者我”的叙述、“写信者我的叙述”、“哈塔尔的叙述”。三个叙述层次中,哈塔尔的叙述是最里层的核心性质的叙述。但是其他两种叙述使整个叙述结构丰厚起来,问题具有了深度。
2 三个层面的叙述及其宽阔的阅读空
三个层次叙述中的“元故事”是哈塔尔叙述的故事,作为文本的“内核”起支撑作用。“元故事”与“隐含作者我和写信者我”所讲述的故事构成小说的纯主题关系。“元故事”与写信者叙述的故事,以及与“隐含作者我”的引言构成因果关系。
热奈特认为任何一个叙事性的文本,都存在着叙述层和故事的层次区别和关系问题。他说:“我们给层次区别下的定义是:叙事讲述的任何事件都处于一个故事层,下面紧接着产生该叙事的叙述行为所处的故事层”。[1]热奈特还认为,处在最里面一层的故事,是“元故事事件”。这就涉及到“元故事叙事”的问题了,热奈特也确实就“元故事叙事”进行了讨论。因为有元叙事,所以,就存在元叙事和其他几层故事的关系问题。
在《杜鹃钟》中“元故事”是哈塔尔自己叙述出来的关于他自己旅居美国的故事。这个层次的故事,和最外面一层的叙述,也就是“写信者我”所讲的关于哈塔尔的故事构成纯主题——东西文明碰撞,东部文明因势单力薄而不可避免的遭受非难以及贫困落后的人民的悲剧命运。而哈塔尔叙述的故事(元故事)和写信者叙述的故事(他对哈塔尔的认识、对其的了解,以及自己对哈塔尔的语言与思想的展现)以及“我收到来信”和“来信的内容讲述的故事”,这三个故事的关系,属于热奈特所说的第一类关系,即“元故事事件和故事事件之间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就是最里层和第二层,第二层和第三层的关系都是因果关系,其中以第二层为连接点,因为收到来,所以,信件被公开,并讲述了一个关于马鲁夫的故事,因为公开来信,于是哈塔尔自己讲述的自己的故事便被展现在读者面前。
下面再让我们从读者的角度来理解三个层次的叙述所开辟的宽阔阅读空间。费伦在自己的著作《作为修辞的叙事》中引用并分析论述拉比诺维茨所提出的四种读者的概念。这四种读者分别是:实际的或有血有肉的读者;作者的读者;叙事读者;理想的叙事读者。[3]写信者我与哈塔尔是朋友,写信者是“元故事”的第一个读者,写信者的读者则是作品的隐含叙述者,且写信者也已预料到信件可能被公诸于众。“隐含作者我”的读者则是文本之外的人们了,也就是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读者。因为“我”信件讲述放置在“我”的叙述框架中,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读者也自然地成为这份信件的读者。所知最多的是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读者,我们不仅知道哈塔尔的故事,信件的事情,各个人的不同看法。
文学经典可以被各个时代的读者反复阅读。而各个时代的读者就是“实际的或有血有肉的读者——特性各异的你和我,我们的会构成的身份”。这样的读者最活跃,最具有时代感,势必将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等带到阅读中,而审美价值就在这样的阅读中得到延伸。小说总体以倒叙恶方式逐层揭开,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给落后地区所带来物质冲击与精神奴役的,清楚的展现在读者面前,黎巴嫩的人民在这种冲击下,或禁不住诱惑或是被迫告别故土,义无反顾奔赴美国。为了幸福的生活、为了金钱、为了人生价值的实现。但最终却都归于平静,最终哈塔尔体悟到了一个人生哲理——土地才是人生的归宿,人生的港湾、是人类的依靠,而一切资本、金钱均是无意义的。
3 资本主义金钱势力冲击话题的当代延伸
努埃曼的作用难道仅仅在于他设计了三个叙述层面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我们依次对叙述者和读者的问题进行分析后,便不难看出作家的作用,即作者所选择的关于“杜鹃钟——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代表物”这个主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曾经说过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可怕的反精英主义的力量就是称为市场的东西,它消除一切差别,混淆一切等级,把一切使用价值的差别统统埋葬在交换价值的抽象平等性之下”。[4]准确地说,资本主义金钱势力冲击东方文明的话题被放置在这样一个小说的叙述框架中,直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依然具有普遍化与迫切性兼具的一个话题。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开化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5]《杜鹃钟》所要表达的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先时,由于发展需要,对其他落后国家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东方国家被迫从属于西方、遭受西方迫害、奴役。本部作品中的杜鹃钟意象就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四十多岁的男人法里斯.赫巴尔将其黎巴嫩,并诱惑走了马鲁夫的未婚妻祖木露黛,致使马鲁夫踏上远征他乡的求富路程。整个故事象征着西方文明对东方的冲击,而后马鲁夫的婚姻不幸、顿悟回归、以及祖木露黛遭受抛弃的全过程也象征着资本主义车轮滚滚向前、不可抗拒的同时,也在毁坏人性、致使其走向堕落,而即使顿悟者,也只能表现出迫于无奈的状态,而对其造成的迫害表现的束手无策。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杜鹃钟已成为诸多新兴科技产品中,最不起眼甚至过时了的一个东西。马鲁夫的叙利亚妻子经受资本主义熏陶,崇尚金钱、追求潮流,嫌弃杜鹃钟的存在,斥责马鲁夫的“落后、腐朽”。但马鲁夫却一直难以割舍杜鹃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深受杜鹃钟侵害所造成的一个难以割舍的“情结”。杜鹃钟意象本身就是一个隐喻,黑格尔指出“隐喻是一种完全缩写的显喻,它还没有使意象和意义互相对立起来,只托出意象,意象本身的意义却被购销掉了,而实际所指的意义却通过意象所出现的上下文关联中使人直接明确地认识出,尽管它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6]最后,马鲁夫、祖木露黛无一逃出杜鹃钟的圈套,即使马鲁夫战胜了杜鹃钟,但他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正如斯塔里阿诺斯所说:“中世纪的欧亚地区发生了一些神奇而又影响深远的事情,一方面,伊斯兰教和儒教帝国日益僵化衰退,另一方面,欧亚地区的西端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面的变革。”[7]努埃曼以象征西方物质文明的杜鹃钟为题,描绘了一些东方人趋之若鹜涌向西方追求财富的图景,最终发现财富并不能带来预期的幸福,带着迷惘、困惑返回东方。试想,侨居海外并获得财富的人精神境遇且是如此,那些没有获得财富的人更是何等的凄苦?
季羡林先生曾经评价“旅美派”说:“他们的作品往往具有深邃的哲理与丰富的想象,常令读者读后不禁掩卷沉思。这是因为旅美派作家、诗人受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加之丰富的生活阅历,较自由的政治、宗教氛围,使他们不必于偏见、迷信而人云亦云”。[8]《杜鹃钟》中哈塔尔的经历代表作者对东方、西方命运的思索。其中隐含作者或者叙述者带领我们有血有肉的读者,在丰厚土壤里寻找迷失的自我。在中西方对比中,展现西方万恶的资本主义车轮疾驰的疯狂状态,东方人或者全人类在跟随资本的车轮滚动时,只能以机械的螺丝钉、铁钉方式存在的悲哀。
[1]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1990年版,第158页、161— 163页。
[3] [美]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002年版,第111页。
[4] [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页。
[5] [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6] [德]黑格尔,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126页。
[7] 斯塔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第7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005年版:第369页。
[8] 季羡林.东方文学史:下册[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第1996年版:第 26页。
I206
A
1672-5832(2017)10-0057-02
廖宇婷(1994-),女,汉族,陕西,硕士研究生,文艺学,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