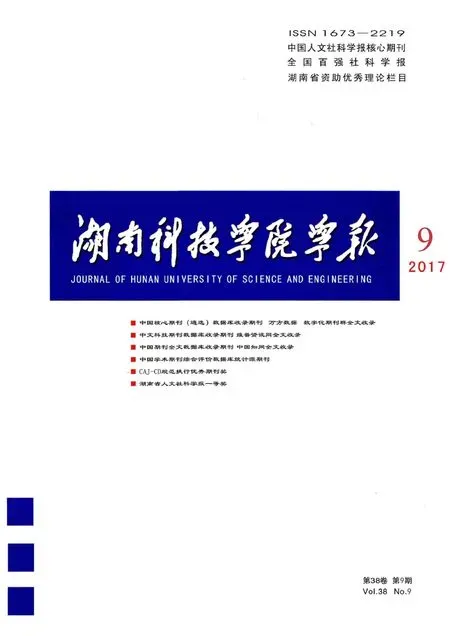柳宗元《湘源二妃庙碑》考释
吕国康
柳宗元《湘源二妃庙碑》考释
吕国康
(永州市教育局,湖南 永州 425000)
汉初平元年建的湘源二妃庙究竟在今湖南零陵,还是广西全州,成为一桩悬案。根据柳宗元《湘源二妃庙碑》的写作背景,以及永州的历史地理情况,湘源为永州属县,即古零陵,今全州。而唐开元年间修建的“潇湘二川庙”即潇湘庙,在零陵潇湘二水汇合处。两庙均祭祀舜之二妃,这是舜文化在湘桂地区的重要标志。碑文对二妃德行的歌颂,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舜帝的伟大。研究、宣传二妃,对于弘扬中华孝文化、建设和谐家庭具有借鉴作用。
柳宗元;二妃庙;潇湘庙;历史沿革;价值
唐元和九年(814)八月二十日,湘源县的二妃庙遭受 火灾被毁。经永州刺史崔能批准重修,十一月峻工,举行祭奠礼,柳宗元为此写下《湘源二妃庙碑》。碑文分两部分,前面是文,叙说二妃庙因火灾烧毁,刺史崔能马上组织重修的经过,后面是铭,采用四言诗,内容有重复之处,主要称颂了二妃的品德,着力描写了祭祀的场面和百姓的喜悦心情。这是柳宗元歌颂舜帝与二妃的德行,倡行“尧舜之道”的一篇重要文章,也是印证“舜帝南巡”的重要地方文献。对“湘源”所指及二妃庙的分布值得考辨,对《湘源二妃庙碑》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值得研究。据《元和郡县图志》,唐代元和年间,永州管县四:零陵、祁阳、湘源、灌阳。碑文中提到的人物刘知刚、崔能等,章土钊先生解释:“司功掾守令彭城刘知刚:司功者、司功参军也,参军为掾级官,故曰司功掾。守者,摄也,守令、谓以司功摄令,令当指湘源县令,湘源为永州刺史辖县。”[1]刘知刚以司功参军代理湘源县令。崔能,据《旧唐书·崔能传》:“(元和)六年,转黔中观察使。坐为南蛮所攻,陷郡邑,贬永州刺史”。其前任韦宙,元和七、八年任永州刺史。崔能元和九年继任,是柳宗元贬永期间最后一任刺史。柳文《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送易师杨君序》、《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均提及此人。碑文中的“湘源”是否指“零陵”?永州学者雷运福认为:“柳宗元笔下的湘源二妃庙就是永州零陵的潇湘二妃庙”,并提出四点理由:“从‘邑令群吏,告于君公’来推测,也应是零陵县,州府治地所在县名,通常省称,县令和众多的县衙官吏一同到刺史崔能处汇报,也说明是所在地零陵县”。“若二妃庙是在湘源县的话,那么湘源县治所距离永州府很远,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官吏同时来到永州向刺史汇报”。“湘源县建二妃庙,也不符合二妃寻夫到九嶷山的行程,即从黄河流域—长江—洞庭湖岳阳—湘江长沙—永州零陵县—道州—九嶷山。”“湖南的湘水,习惯上称湘江,严格意义上的湘江是从潇水汇入处为起点为源口,汇入处的二水上游均为湘江二级交流,二水汇合处可称‘湘口’,也可称之为‘湘源’,湘源、湘口在这里同义。”[2]实际情况是,湘源二妃庙建在湘源县,即古零陵,今广西全州。公元前221年,秦朝在今全州境内设置了零陵县,属长沙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置零陵郡,郡治仍在全州,辖7县4侯国,地域广阔达9万余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的湖南衡阳市、郴州市、永州市、邵阳市,广西的梧州市、贺州市、桂林市,广东的清远市、韶关市北部等地。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此“零陵”即古零陵,说明零陵的得名与舜葬九嶷有关,根据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辑录,“零陵”是我国夏代已出现的全国34处重要地名之一。“章帝建初四年(79),有甘露降泉陵、洮阳二县”[3],零陵郡治才迁到泉陵县,即今天的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时间跨度300年。隋开皇9年(589),撤零陵、营阳二郡,设永州总管府。废广西地的零陵、洮阳、观县(今灌阳)三县,置湘源县。改泉陵县为零陵县,将永昌、祁阳、应阳3县并入。永州总管府和零陵县治均设在今永州市零陵区。这一年可称永州、零陵一地二名的起始年。这时,在全州存在了810年(前211-589)之久的零陵这一地名,最终在今广西境内消失了。由此可知,古零陵是以全州为中心的。


司马迁说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苍梧为古国名、古地名,与中原华夏的尧、舜等古国同时并存。苍梧古国的分布范围主要在湖南湘江流域及南部地区、广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部地区。而九嶷山是其核心。故《山海经·海内经》说“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苍梧之野范围相当广泛,涵盖湘漓大部分地区。而在湘漓之野存在一个舜文化圈。所谓舜文化圈,指舜帝一生的活动轨迹所留下的文化遗迹,辗转播迁,经久不衰。这一文化圈包括湖南、桂北、粤北之地,以古零陵为中心。以桂林虞山为例,相传虞帝南巡曾到这里,秦人立碑纪念,唐代建虞帝庙,古往今来祭祀虞帝者络绎不绝。现已开辟为虞山公园,保存古代碑刻65件,其中以唐代韩云卿撰文、韩秀石手书、李阳冰纂刻的《舜庙碑》和宋代朱熹的《靖江府新作虞帝庙》最为珍贵。在遗址上重建的虞帝庙,为正殿;东西两边新修的配殿,供奉二妃娥皇、女英,对联分别为“虞山有幸祀贤女,湘水多情慰落英”,“斑竹泪凝千古事,湘君情系九嶷魂”。娥皇、女英是尧帝的女儿,舜帝的两个妃子,故称帝子、二妃,又称湘妃、湘夫人。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说:“世言大舜之徙方也,二妃从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九嶷山的传说却不同,说二妃到过九嶷。可是“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恸哭不止,泪珠洒在竹子上,“瘢痕苦雨洗不落”,指纹合血泪留于竹干,“色抱霜花粉黛光”。最后,二妃化作了娥皇、女英两座秀丽的山峰,仍然矢志不渝地守护着舜帝的英灵。刘禹锡《潇湘神》:“湘水流,湘水流,九疑云物至今愁。若问二妃何处所,零陵芳草露中秋。”“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潇湘神即二妃,后衍变成词牌。词中将二妃与湘水、九嶷、零陵及潇湘完美融合在一起,斑竹泪、瑶瑟怨,诉说着二妃与舜帝凄美的爱情故事。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对所辖4县的地理概念十分清楚,决不会用“清湘”代替“零陵”。如《覃季子墓铭》中“永州祁阳县某乡”。《零陵三亭记》中有“零陵县东有山麓”,“河东薛存义,以吏能闻荆、楚间,潭部举之,假湘源令。会零陵政厖赋扰,民讼于牧,推能济弊,来莅兹邑”。薛存义被授以湘源县代理县令。遇上零陵政令混乱,赋税扰民,老百姓打官司告到了州府,于是州府推举贤能的人士以革除弊政,薛又来到零陵任职。《送薛存义之任序》中云“存义假令零陵二年矣”,说明薛存义代理零陵县令二年。《愚溪诗序》开头“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潇水”,灌水即灌江,源出灌阳县西南。柳宗元写了《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诗,因潇湘二水在零陵蘋洲相汇,故称“湘口”,衍生出湘口馆、湘口关、湘口站、湘口驿、湘口渡、湘口津、湘口镇,无“湘源”之说。
雷运福先生说:“明朝《湖广通志》记载今湖南、广东、广西一带二妃庙只有二处,即湘阴县的黄陵二妃庙和零陵县的潇湘二妃庙。其他州县未见二妃庙的记载。”[2]事实并非如此。除泳超博士在“尧舜传说的地理分布”中指出:“黄陵庙在湘阴县北四十里,唐韩愈有记。……湘妃庙在巴陵县西南君山,祀尧二女”。“常德府二:祠庙:舜二妃庙,在武陵县西”。“永州府二:祠庙:潇湘庙,在祁阳县东门内,祀帝舜及湘君、湘夫人。”“二妃庙,在蓝山县东十五里,祀娥皇、女英。”加上零陵的潇湘庙,可知在今湖南境内,至少有6处祭祀二妃的祠庙。而在广西,除全州二妃庙外,还据《寰宇记》载,“临桂县有双妃冢,高十余丈,周回二里,相传二妃寻舜而卒,葬于此。”
现在回到碑文的内容。关于修复湘源二妃庙的目的:“祗栗厥戒,会群吏洎众工,发开元诏书,惧废守祀。”崔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一告诫,召集各位官员以及众位工匠,打开开元时的诏书,惟恐荒废了一直有的祭祀活动。“唐命秩祀,兹邑攸主”。在唐代,皇帝诏命进行官家祭祀,湘源县令负责主祭。说明在唐朝李隆基开元年间(713-741),由皇帝下诏对二妃庙进行官祭,规格极高。明洪武四年朱元璋敕封二妃庙神为“潇湘二川之神”,其祭仪载在国典上,与此一脉相承。从“神用播迁”、“神乐来归”、“神既安止”等铭文来看,这次修复是异地重修、迁徙庙神。碑中对修建过程做了简洁生动的叙述,资金的来源是官府筹集,“均节委积”,建材是就地取材,“斩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乃桴乃载,工逸事遂”。仅三个月时间就顺利完工,“作貌显严,粲然而威”,重修的二妃庙外观宏伟、威严,庄严肃穆。“十有一月庚辰,陈奠荐辞,立石于庙门之宇下,”崔公率领左右属官前来祭祀。柳宗元肯定也参加了祭奠活动。碑中重点歌颂了二妃的品德,“唯父子夫妇,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极其会”。父子夫妇,是人伦的大道。娥皇、女英这两位女神,都很好的做到了这两点。具体而言,有三个方面:第一,“为子而父尧,为妇而夫舜。齐圣并明,弼成授受”。作为女儿,她们的父亲是唐尧,作为妻子,她们的丈夫是虞舜。她们与圣明的虞舜平齐共耀,辅佐虞舜治理天下。这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的。作为尧的两个女儿,受到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列女传·有虞二妃传》载:“舜既嗣位,升为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封象于有庳,事瞽叟犹若初焉。天下称二妃聪明贞仁。”张京华解释“虞舜继续孝行,而湘妃也能善始善终。‘贞’意为中正,谓能合于中道,行于正道。清人解为‘所言所行,皆合礼道’,是对的,聪明而又合于中道,可以说是治家治国的最高评价了”[6]。可以说,二妃是名副其实的贤内助。第二,“内若嚚瞽,上承辉光。克艰以乂,德罔不至”,内心顺从愚蠢而又顽固的公公婆婆,又从她们的父亲那儿继承了光辉照人的品格。能够吃苦而且治理出众,德行没有不到的地方。刘向《新序·杂事》云“父瞽叟顽,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在家遭受种种磨难、迫害,几次死里逃生,仍行孝道。二妃的相夫之功值得称道,常常为舜出谋划策,使其化险为夷。患难与共、支持配合,并且孝顺公婆,爱护弟弟。刘向称颂“以尊事卑,终能劳苦,瞽叟和宁,卒享福祜”,居《列女传》之首,并称之为“元始二妃”。这是从家庭角度来讲的。践行仁爱、孝悌的二妃,在处理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方面是妇女的楷模,如此特殊的家庭,尚且能和谐相处,天底下还有什么家庭矛盾解决不了?在现代和谐家庭建设中,我们完全可以宣传推广二妃的德行。第三,“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兹川,古有常典”,舜帝死在了苍梧之野后,两位妃子也死在了湘水之间,神灵不得归返。在湘水间受到人们的祭祀,自古以来就形成经常的仪式。《述异记》云:“舜南巡,葬于苍梧,尧二女娥皇、女英泪下沾竹,久悉为之斑,亦名湘妃竹。”斑竹一枝千滴泪。斑竹的传说,是二妃与舜帝爱情故事的千古绝唱。“德形妫汭,神位湘浒”,二妃的德行形布于妫水之汭,可是你们死后的神位留在了湘水之滨。生为人杰,死作神灵,二妃与舜帝的英魂最终归属于潇湘、九嶷。这是从爱情的角度来讲的。二妃忠于爱情,至死不渝,书写了中国最早的爱情故事,留下无数歌吟的华美诗篇。屈原的《湘君》、《湘夫人》就是娥皇、女英化作湘水之神后的恋歌。李白的《远别离》直写二妃与舜帝生离死别的故事,迸发出“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的无穷感慨。在现代,郭沫若先生以此为题材,写出了著名的诗剧《湘累》。碑文最后归结到祈福。从二妃庙的因火灾毁坏,到高大的庙宇重新树立,“神既安止,邦人载喜。奉其吉玉,以对嘉祉。南风湑湑,湘水如舞。将子无讙,神听钟鼓”。民俗内情,历历在目,情调欢快,神民同乐。“丰其交报,邦邑是与”,神灵高兴之下,多多赐福给州县的百姓。首尾呼应,文铭结合,浑然一体,堪称完美。其中体现了柳宗元一贯的民本思想。全州的二妃庙虽然已不复存在,但是《湘源二妃庙碑》这一文献将永载史册!零陵潇湘庙虽破旧不堪,但框架犹存,经过修复,必将光耀千古。
[1]章士钊.柳文指要[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185.
[2]雷运福.柳宗元集版本探微[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80-181.
[3]蒋钦挥.历史的碎片:全州地域文化纵横谈[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21.
[4]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5]张京华.湘妃考[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73.
[6]陈泳超.尧舜传说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60-364.
(责任编校:张京华)
2017-06-24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代柳宗元研究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6BZW034)。
吕国康(1948-),男,湖南永州人,永州市教育局原主任督学,高级讲师,湖南科技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柳宗元研究学会理事,永州柳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柳宗元研究、潇湘文化研究。
I206.2
A
1673-2219(2017)09-0013-03